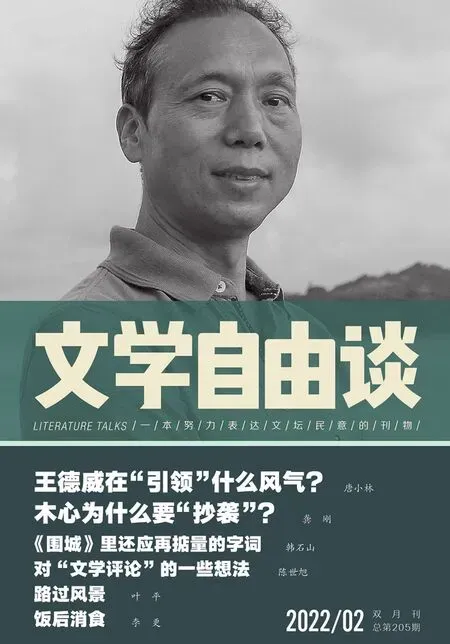饭后消食
□李 更
1
西吉县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十八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六十九人,这在全国罕见。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三人相继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牛学智、火仲舫、单永珍等十七人先后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
到过几次宁夏,但没去过西海固,我还是在珠海长期参与扶贫才知道这个名词的。这个名词几乎就代表着贫困,西吉还居首位。
贫困是文学之母。
饱暖思淫欲,贫困出文学;东西南北中,西吉有文章。
2
有人建议我把《南方文鉴》做得薄一点,便于携带。
问题是现在的纸质读物,阅读功能只是其中之一。因为阅读工具的变化,书,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要做一本立得住的书,就要有相当的体量。我们是在做民间文学的年鉴,不是黑板报,不是传单的集成,要有收藏价值,就要做成一件艺术品,所以,必须有相当的投入。如果我们也去做口袋书,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在丰盛的晚餐上又加了一道菜而已,可能最后成为一种剩饭剩菜,下场可想而知。
3
浩然在《艳阳天》里反映出的基本是历史的区域。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除了文本固有的语言、故事、结构的创新,还在于反映时代社会的政治特征。不论还原或伪饰,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要有鲜明的辨识度。
4
陈徒手研究的这些作家,以前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到陈徒手笔下,仍让人耳目一新。
吃别人嚼过的馍也能找到营养,这样的学者是饿不死的。
5
毕加索本人是这样说的:“我十四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之后我用一生去学习像小孩子那样画画。”能理解这句话,也许就会离大师更近一步了。
李某十四岁就会说大人话,然后用一生学小孩说实话。
6
我发现断章真可取义。几句话,不浪费别人时间,就像看电视的人,在他们用遥控器换频道前赶紧把内容播完。现在的读者越来越没耐心,八百字的博客都嫌长,所以我现在学习写邮票大点的文章。同时,给愿发这种邮票文章的,比如《今晚报》点个赞!副刊应该成为纸面微信。现在饭桌上没有人讨论谁的一本书了,而是谁又说了什么话。
7
我觉得现在写文章非常疲倦,不如画画。画画可以养眼,还是一种轻奢运动,尤其是在画面上写几句那种断章格言,或者以今天的说法叫截句,惬意。话多失言,文长柄多。不是追求什么微言大义,而是不易留首尾。我喜欢的书法就是笔要留,以前觉得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痛快,伸胳膊伸腿,现在觉得还是要藏笔锋。可能因为年纪原因,也可能因为身体欠佳,写出去还要能收回来,然后还要让人读出潜台词。说话过头,一般人不会犯,但说话过满,有些人还是不能自已。水满则溢嘛。然则,说得完全让人丈二和尚,也不行。我自己觉得理解能力还是不错的,但有些文章还是研究半天不得要领。比如以前读《废都》,那么多□□□□的,据说是为了出版,编辑代替做了阉割手术。以我小人之见,作者曾经说自己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咱们农民有多少对卧榻之欢有西门庆那样丰富的亲自体验?显然,他的发散思维除了并不繁花的想象,为了市场生存,只有故弄玄虚。
8
开发游戏和制造武器,我认为都是为了杀人!
9
冯德英,天才,二十三岁成名于《苦菜花》。
同龄,萧洛霍夫出版《静静的顿河》。曹禺出版《雷雨》。张爱玲出版《第一炉香》。
10
物质极大丰富后,艺术家作品的技术含量却越来越低。从沃霍尔开始,从恶搞开始,甚至把垃圾搬进室内,把垃圾分类放入庙堂,都变成当代艺术家用以乞讨的理由。他们语言的解说大大掩盖了画幅的不足,直至用谎言包装谎言。
文学也是这样,有人给我看几个据说现在被某些刊物包装成明日之星的年轻人作品,他们说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说是小说,没有故事且罢,没有人物,没有细节,没有对话。
对于看不懂,以前我会非常惭愧,如今也差不多花甲之年了,脸皮厚了许多,偶尔倚老卖老也是新常态。
我的常识是,要想不让人看见水浅,手法很简单,把水搅浑。
以前我总觉得与年轻人打交道一定要谦虚谨慎,但我也知道很多年轻人喜欢背后骂前辈。后浪要前进,必须把前浪拍在沙滩上。什么继承传统,那是守旧。一些年轻人甚至说,有些在文学历史书上出现的名字是历史的误会。
我就遇到一些以前称呼我老师的人,他们以前赞扬我有多肉麻,后来诽谤我就有多邪乎。原因很简单,觉得我没有资源了,甚至怕我和他们抢某些补贴。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在地方作协拿到一分钱好处,更不会跟他们抢饭碗,不是我清高,而是我和他们吃的完全是不同的饭。
大家都知道鲁迅喜欢培养青年,确实也培养出不少青年作家。但是,不断读鲁迅,才知道鲁迅最担心的是举起屠刀的青年。
11
我可能真的老了,一看旧照片就不免感叹,如同白头宫女说前朝。前不久曾静平发给我一张1985年她、华姿、梁必文、徐鲁和我的合影,就感慨:当年也青春了一把。
文夕最近也发来一张二十年前她和我的合影,她还是她,我已不像我。
这么多年,我认为深圳文学可能留下了文夕的四本书,她是深圳历史的见证人。邓一光、徐敬亚、杨争光都是外援,他们属于大鱼,大鱼沉水底,水面上吐泡泡多的都是小鱼。
文夕夫君胡永凯是绘画大家,帮很多画廊赚了大钱。他们也是我中山近邻。
12
关于高小华的《绿皮火车》,我觉得应该说几句。因为和文学有关。没有文学基础,甚至没有文学爱好的画家不可能成为大家。
四川美术学院出作品的都是入学前就了得的画家,他们主要受巡回画派影响。之后,市场经济的冲击,严重影响了川美的学术纯粹,出现了恶炒周春芽,甚至云南几个靠抄袭混世的所谓现代艺术家。真正的像高小华、陈可之那样走现实主义道路的艺术家被遗忘了。连罗中立、何多苓也被边缘化。
李霁宇说:现实主义的画作是源自我们的生活经验。现代绘画已经脱离生活经验了,所以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美其名曰什么概念、哲学。色块,涂鸦,还有各类现代艺术行为艺术,其实就是无法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另起炉灶的无奈之举罢了。文学亦是,什么什么主义,各种花样及新名词,统统是借口是遁词。
一个艺术家,你记录了历史,历史就留下了你。你想独立于历史而存在?是不可能的,作家亦是这样。
13
实际上中国远古历史是司马迁个人的思维史。
《史记》实际上就是散文,《圣经》也是散文。
14
我一直认为木心只是一个标准的教书匠。他的原创性不足,俗称搬砖,也就是当代文化人普遍存在的拿来主义。
刘宅宅说:2014年5月,南京大学有篇硕士论文,题为《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作者是位姓卢的女性。这篇足足有一百五十四页之多的论文,考据之精深、说理之透彻、材料之丰富、体现出来的阅读量之巨大,可以说是近年所见最扎实、最有价值的硕论。半年后,该论文缩写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杂志。知网可下载,随时能案验,可知有不诬矣。
这篇重量级论文,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近乎石破天惊地“揭秘”出一个惊人事实:一代“文学大师”木心,其大量文章,涉嫌抄袭,或曰洗稿。
没想到2014年就有论文说明了木心大量抄袭的问题,广州的张在军给我转来相关文章,证明我以前的判断是正确的。
大量的所谓“移植”,却完全不标明出处,这不是一个纯粹文人的做派,张远山认可我的意见。他认为可与钱钟书的《管锥篇》,还有弗雷泽的《金枝》做比较,《管锥篇》标明出处,体现的是学术的严肃性,而且内容不是文学。
关键是,木心是文学的。文学必须具备原创性。
上海的吴炫觉得文学也可以那样,比如曹操,如果借前人的词句赋予自己的意味,那就不算真正的抄袭。
张远山说:曹操只是个别词句,属于用典,用典属于文学继承。与木心完全不同。
吴炫说:木心的哲学受到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响,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关键是看作品的整体意愿。
我和张远山观点一致:没人把木心当哲学家吧?
吴炫说:那就不是大作家,所以没有必要去苛求。
张远山强调:但是他现在被炒作成了大作家。
吴炫直接有指:那是炒作者比较平庸吧。鲁迅前期的作品也是模仿为多。
张远山解释:学步期可以理解,但是木心成熟期甚至最终作品也是如此,只能一叹。
吴炫说:这样看来,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学者变相抄袭,没有自己的思想,必然是依附、模仿、抄袭,或变相抄袭。
张远山说:这是根本问题。又见于木心,他是否大师,不妨见仁见智,但是,仿写、模拟、抄袭、不原创,是不能原谅的致命伤。
木心在再生文本《法兰西备忘录》的“后记”中写道:“文学当然也像绘画一样可以将别人的东西取来加以变化、重组。”
木心还举莎士比亚、吴承恩为例:“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拿了你的东西,叫你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是强盗王,吴承恩这强盗也有两下子。”
因此,虽然木心的部分再生文本应属于抄袭、剽窃,但在他本人看来,这或许是合理、正当的。
梁艳萍同意我的木心只是一个“教书匠”的认定,她说:教书匠都不是高水平的教书匠,知识学方面落后而且还有错误,因为当年听他讲课的人都是才上了小学、初中的,乍一听当然感觉到新鲜,无法辨识其中的问题,以至于某些出版物上明显的错误都没有能力修订。现在陈丹青们竭力抬举,更是传播了不少不值得、不应该传播的东西。
我个人理解,陈丹青以一己之力能够把一个教书匠抬举成为大师,他可以担当炒作大师了。
我们质疑名家,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