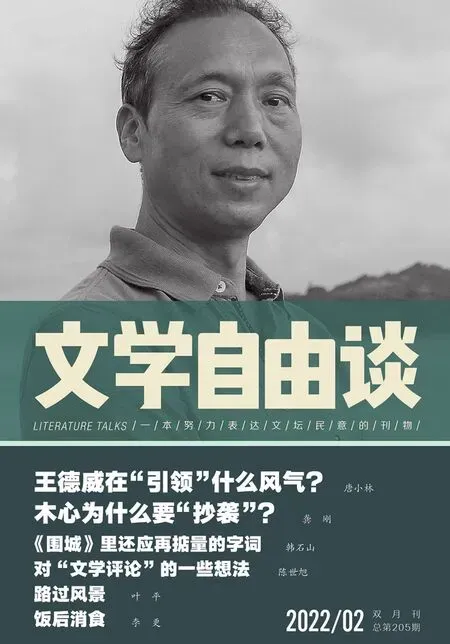花边文学
□张怀帆
1、“著名”青年诗人
参加一个朋友的作品研讨会,我老婆看到会议消息,问我:你什么时候“著名”的呀?连对门的邻居恐怕都不认识你吧!我告诉她,“著名”是骂人的话,谁要说我“著名”,你就还击说,你才著名呢!会议消息还说我是“青年诗人”,我老婆又笑了:你们这些人真逗,你看你脸上的褶子,还青年呢!我说青年诗人是指那些诗写得不够成熟,甚至有点稚嫩的人。我老婆就说,那就快别写了,要不然到六十岁还有人叫你青年诗人,你臊不臊啊?
我也反感别人说我是作家或诗人,我心目中的作家或诗人也不是我这样的,更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子。无疑,作家诗人唯一的凭据是真正的作品。
我是什么人?是一个失眠的人,一个和文字谈恋爱的人,一个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喜欢美女的人,一个忧郁的人,一个内心不宁静外表冷漠的人,一个虚伪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胆小谨慎的人,一个忧郁的人,一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人,一个矛盾的人,一个不受女人欢迎的人,但唯独不是诗人!
2、春天里读诗
在书店里买了两本诗集,一本的作者脑瘫,另一本作者聋哑。在当下喧哗的时代,我更信任那些安静甚至哑默的人。杜甫说,“文章憎命达”,在浮躁的年代,大概尤其如此。身体残疾只是一种局限,史铁生因此说,每个人都是残疾的。但我愿相信,“当上帝关了这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那或许是诗歌。读诗,便在春天。
3、直接崩溃了
开会,侧目看见一哥们儿在手机上刷小说,已看到了一千三百五十一章,当即崩溃!什么牛人把文字写得这么长?更有什么牛人有耐心看到这么长?依我看,这得有多遭罪和受虐呀!但显然,他一定是被吸引而不是无聊才能不断看下去,那又是什么样的牛文字呢?我算是彻底服了,外星人就在身边!《红楼梦》最多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也都百十回左右,陕西作家孙皓辉的《大秦帝国》,据称五百万字,已经令人望而生畏,那一千多回的网络小说怎么说也有这么多字吧?而且尚不知多少回才完了,总共该有多少字!网络写手,绝不会耗时很多年吧,想一想挺恐怖的。说一个人是写手,算不算蔑视?如果有人这样说我,我会感到受辱。但说作家就算尊重吗?得了吧!能认真把一部作品写到五六百万字的人,不论那文字品质怎样,都令人刮目相看!假若不是通过写作机器编辑而出,而是一个字、一个字从脑袋到键盘上敲出,得有多大的苦力和毅力,我会敬重他!但你要让我去看那小说,还是算了吧。我能接受的最长小说也就百万字左右,迄今看过最长的大概也就是《红楼梦》了。我是说,真的有必要把文字写得那么长吗?如果不是口水和垃圾,那得有多大的智慧!现在,还有哪些人愿意看那么长的文字?如果不是无聊,那得有多么大的定力和耐心!要杀头,才能讲一千零一夜呀!
4、酒与美女
《世说新语》好看,但不免夸张,有的几近吹牛。比如,说阮籍的邻居是一美妇,卖酒,阮常去买酒纵饮,有一次喝醉了就睡在美妇身旁。他丈夫觉得这醉鬼不怀好意,就窥察,但发现不过是烂醉,别无恶意。这我就不相信了,世间竟有如此无邪的酒鬼?更有如此大肚的丈夫?魏晋时人,是怎样一种风度呀!李白也写过胡姬压酒,但他绝无阮籍对酒的单纯。料那胡姫必是美女,不然怎会吸引金陵子弟!李白常常“长安市上酒家眠”,倘也有睡在胡姫身边的可能,胡姫的丈夫绝不会轻饶。唐人与魏晋人的风度已迥然不同了。再往后,醉翁之意就不在酒了,现在就更不用说,酒和美女,你会选哪一个?人越来越失了单纯。
5、鼻梁问题
眼镜戴久了,就往下滑。去眼镜店,他们会用钳子把眼镜腿往回扳一下,但戴上后,就显得太紧了,我便自己再往开扳一下,仿佛又回到原位。眼镜滑下来的样子,滑稽。我见过别人,就像裤子没提牢,不精神,有落魄书匠气。并且总不由自主往上扶,又像个书呆子。后来,我发现不是眼镜有问题,是鼻梁太塌了。
6、吟诵
路边冲出一个醉汉,一下子就钳住我的脖子,感觉他把整个身子都压在了我的肩上,无疑,他不是强盗,是我的一个熟人朋友。他的嘴巴,像打开的酒坛子,蒸腾着酒精,我似乎即刻就要中酒晕倒;而他的身子,像一个燃烧体,现在把火引到了我的身上。我问他喝了多少酒,就成了这样?回答说,没多少,也就半斤,人老不中用了,要是在年轻时,半斤算个啥!我心想,半斤不少了,如果再多,恐怕要被人抬回去了。可是他分明还清醒,走路不摇晃,说话也清楚,甚至目光都不迷离。我就把压在我肩上的手臂用力扳开,和他一起走路。不多时,他一边走路,一边开始吟诵,先是《后赤壁赋》,接着是《前赤壁赋》,借着酒力,他的声音慷慨激昂,抑扬顿挫,颇有豪气。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比记忆力让人更生羡慕的是,他是怎么做到人在坐班却能与诗酒为朋,超然豁达?因为苏东坡的二赋,我就原谅了他钳我的脖子。我想,作为小文人的我,本来应是他这个样子,不料我却活得谦卑消极,中规中矩。尤其是,我连一篇文字都背不下来,就是我自己写的,也前写后忘,吟诵不出。更别说醉酒走路,还大段吟诵,我是永远学不来的。
7、变成牛魔王
我见过许多酒喝高的文人,都喜欢自吹自擂,牛皮吹破天;都自我膨胀得忘乎所以,天是老大,他是老二。好像一喝酒,雄性激素就会成倍巨增,身体里装进了牛魔王。尤其是,当酒桌上一群文人群魔乱舞,开始发飙,那场面既壮观又好玩儿。
8、贪吃
肚腩是让人讨厌的家伙,我一直以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贫下中农出身的我绝不会长出这个怪物!但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小腹微微隆起,一把赘肉,顿生厌恶!莫非人到中年,都会发一点福?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借口,除了遗传因素,我坚信男人的肚子都是贪吃的嘴搞大的,而贪吃也是贪婪!
有的人贪吃很可爱,像苏东坡,无论多么困窘,总有一张乐观的胃,胆大到可以提着脑袋吃河豚,竟然能把肘子弄成一道千古名菜,于是便有了包容天地的大胸怀!让鼠肚鸡肠恨他的政敌牙根痒痒,气急败坏。林黛玉倒不贪吃,食以匙计,经常西施般地捂肚子,小心眼儿就让人很受不了,最终只落得啐一口血而香消玉殒。女人贪吃却不让人讨厌,无非是一些小零食小东东,果真有人大快朵颐、不顾吃相,必性格豪爽,让人痛快!贪吃的男人却多半不妙,酒肉之徒者多,美食家少,弄到脑满肠肥、肥头大耳的时候,一脸的物质势利横肉,一身的杀猪匠气息,一副膻气哄哄的臭皮囊,浊臭就自不必说了!
9、邮政所
自从有了“伊妹儿”,几乎不去邮局了。小镇上的这个邮政所,曾是我最牵挂的去处。很多年,我把一叠叠带有体温的信件寄往全国各地,那里装着我刚出炉的作品,随后很多天,我都满怀期许地等待着返回的好消息。那个绿色的邮筒,成了我在这个小镇上最亲密的挚友。现在,却再也不见它的身影。
我是为了取一位诗人寄来的包裹又去的这个邮政所。去了以后才发现,它现在主要成了一个储蓄所,信函的业务已很少,包裹却堆了一地。原来柜台下还会摆出新到的邮票,现在只卖年册。最主要的,原来有一个一笑两个酒窝的邮政员,现在却是一个壮实的中年妇女。原来站着邮筒的地方,现在站着一个垃圾桶!
10、手写体
自从有了一次性碳素笔,很多年都不用钢笔写字了;自从有了电脑,甚至很多年都不怎么写字了。从人类整体看,这当然应该算是进步,但也丢掉多少美好的情愫啊!想想我们的先人,用毛笔写字,一封书信,一篇文章,真的是见字如面。那素笺上的小楷,碑石上的隶书,卷轴上的狂草,无不神采飞扬,见情见性。“云中谁寄锦书来”,那锦书,该是字字情思,小姐的娟秀,相公的洒脱,全在一面帕上!那《兰亭序》、《寒食帖》、《中秋帖》、《落花诗贴》、《多宝塔碑》、《玄秘塔碑》,字字入心,千古墨香!当这一切,都变成规规矩矩的电脑字时,风流不再,风雅难寻。当然,今天还是有人在用毛笔写字,但那成了艺术的追求,市井巷陌,起居日用,寻常凡人,讯息往来,则再也见不到带着体温的手写体了,一个“伊妹儿”,三五句网络语言,一串表情包,鼠标一点,就OK了,相比古人,是多么简陋贫乏呀!我在想,如果今天还在沿用毛笔,人心会不会没有这么浮躁?也许,我还会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呢!
我很羡慕今天依然会写毛笔字的文人,他们不光文章好,字也好;文章写累了,写一会儿书法,喝一会儿茶,简直是神仙生活!可是,文章可以大好,字最好只是小好,一旦入了品,他们就会标价,要润格费,我就不喜欢了。我这辈子估计不会写毛笔字了,几十岁的人,就不强求自己。但我会坚持写钢笔字,找一个干净的本儿,抄唐诗,不光练性子,也是一种悠然的享受。也许遇到可以交心的朋友,我还会用钢笔写封信,只不知邮局这项业务终止了没有?
11、头顶星辰
在肤施小镇待了几十年,太阳从哪里升起我知道,但是月亮我就搞不清了,有时发现在东边,一轮满月;有时又见在南面,一弯新月;有时在早晨,薄冰一片贴在半空;有时在深夜,弯钩似的悬在山头。但古人能算得清楚,甚至年老一点的农村人也知道大概,真好!当然,要是拿个地球仪比照着看月亮,就没有一点意思了。
小时候看见过勺子状的北斗七星,也见过耀眼的北极星,还能从繁星满天中找到牛郎织女星。每次仰望星空,都会有强烈的神秘感,引发无限遐想。但自从到了城里,就再也看不到明亮、低垂、闪烁的星空了。
现在的孩子们大多都知道星座,却不关心星星。没有看见过满天明亮的繁星,那些繁星仿佛贴近地面,神秘、神圣、温暖却又孤独,美丽却又忧伤,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缺憾!就像没有见过大海、沙漠一样,人生都不完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把目光从喧嚣的尘世间抬起,去眺望那看不见的远山、大海,去仰望同样看不见的浩瀚星空?我们的目光如此短浅,因此我们的心灵多么贫乏!我想,不论多么平凡的人,如果能时时把目光抬起,便一定会获得超然和宁静。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人却极少极少?还有多少人知道,雾霾的天空不是空洞的,它的背后是繁星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