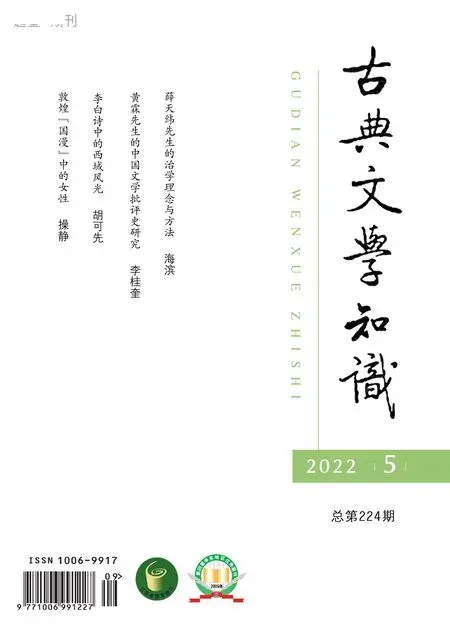山一程,水一程
——几件敦煌集部写本的丧祭仪式解读
邵小龙
一、 纸上的行旅
唐五代时期的招魂风俗,此前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囿于史料的记载,招魂的具体细节,难以完整恢复,目前仅知对横死、尸首不明者,或在迁葬的过程中,会使用招魂葬。在招魂仪式中,文学作品有怎样的作用,几件敦煌藏经洞所出的诗赋写本,提供了一定的答案。
《唐诗文丛钞》(P.2673)首尾皆残,卷首为残缺的《翟进玉状》,卷尾同为残缺的《江上羁情》。翟文和卷尾残诗间,抄《龙门赋》《王昭君》《北邙篇》《初度岭过韶州灵鹫广果而死其寺院相接故同诗一首》,这些作品和《江上羁情》均为古体诗。《龙门赋》题名下书“河南县尉卢竧撰”,《王昭君》题名下书“安雅”,《北邙篇》《初度岭》和《江上羁情》的题名下并无其他文字。
这件写本中出现的文体有文、赋和诗。不提卷首的残文,其后所抄的《龙门赋》,为洛阳当地的县尉所作,表现了清明时节,当地士女赴伊水两岸,在春光下举行登山乘舟宴乐赋诗饮酒等活动,作品最后借“光景不留人渐老”等句,流露出一种深切的忧伤。
《王昭君》一诗除本卷外,还见于法藏《唐诗丛钞》(P.4994+S.2049),以及分藏于圣彼得堡与巴黎的《唐诗文丛钞》(Дx.3871+P.2555),另有东方虬《昭君怨》,收入敦煌所出《李峤杂咏注》背面的《唐诗丛钞》(S.555+P.3728),以及收在法藏《唐诗词丛钞》(P.2748)中的《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法图所藏《玉台新咏》卷二残卷(P.2503),还收有石崇所作《王明君辞一首并序》。敦煌所出有关王昭君的叙事文学,则有残存后半部分的《王昭君变文》(P.2553)。昭君为历史名人,自然多为后人关注和咏唱,饶宗颐、邵文实、朱利华等先生皆有论述,兹不赘言。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昭君也因死后葬于他乡,成为未能归于故土的游魂。
《北邙篇》与下文刘希夷之作并无重合,为同题异作。这篇作品兼具怀古与游仙的意味。作品首先以洛阳南北的对照开篇,接着便发出“自为骄奢彼都邑,何图零落此山颠”之问。接着又描写邙山的青松丛冢,并追忆汉晋风流及石崇绿珠故事。进而笔锋一转,由“呜呼哀哉洛阳道”,转入“相斯(思)相望蓬莱岛”。在仙境游历后,作品以“与君携手三山顶,如何冥寞久泉台”结束。
《初度岭》和《江上羁情》的作者可能是南贬的宋之问,《初度岭》表现了作者度过五岭后,前往韶州寻访灵鹫寺和广果寺的所观所感。《江上羁情》后半残缺,内容正如诗题所言。
敦煌藏经洞中,还存有出自上述写本抄写者之手的其他几件写本,其中一件《唐诗丛钞》(P.3619)与前文所论的《唐诗文丛钞》,除字体外,在内容方面有共同的特征。
这件写本首全尾残,共收录48首作品。卷首为苏癿《清明日登张女郎神》。此诗又见法图所藏另一件《唐诗文丛钞》(P.3885),题名阙“神”字,但两件写本中的题名均颇为费解。结合正文中清明写作“青明”,铺写作“捕”,及后文中的种种讹误,不免令人怀疑抄写者水平有限,写成后也缺乏校对。因此或“登”字另作“祭”,或“神”下脱去“庙”字。任半塘先生便在《敦煌歌辞总编》中,将题名补充为《清明日登张女郎神庙》。作品中的“寒食尽,青明旦,远近香车来不断”,便生动地表现出寒食清明期间,贵胄显宦子弟出游享乐的场景。
苏诗后的《宝剑篇》写弃用之剑,《死马赋》写老马,《白头翁》和《北邙篇》表现手法相近,前者为老人与少女的对话,后者为白头翁向牧马人讲述往事,均将昔日繁华与如今苍凉形成对比。《捣衣篇》则如细致的镜头一般,记录了一位女性在秋日为夫制衣送衣的忙碌身影。《登黄鹤楼》《登鹳雀楼》《登岐州城楼》为三首相接续的登楼之作,前两处均为名胜,一位于武昌,一位于永济,唐人多有诗歌吟咏,本件写本所选为崔颢与畅诸所作的律诗。宋之问的《度大庾岭》作于贬谪途中。此诗后的一首五律以“城边问官使”起句,表现了行至长安的观感及心情,可惜抄者草率,题名和作者均未抄录,留下一个具有争议的谜题。蔡希寂的《扬子江夜宴》作于楚地,内容如诗名。李邕的五律《彩云篇》咏云,或借云表现离亲思乡的愁情。崔颢的五律《度巴硖》,表现了荆襄至巴蜀间的行程。佚名五律《秋夜泊江渚》,同样抒发了作者秋夜在长江漂游的感怀。
另一件法藏的敦煌所出《诗文丛钞》(P.3480),其结构特征与上述两件写本也有相近之处。这件写本首尾皆残,抄有七首作品。残卷开头抄刘希夷《白头翁》,之后为王粲的《登楼赋》。《登楼赋》又收入《文选》卷十一,不过这件写本所收应当是王粲赋的单行本,因此这篇赋未见于敦煌所出的其他《文选》写本,且文字也与传世本有异。
《登楼赋》后的《落花篇》作者已佚,描写众女游春赏花,群芳被风吹过,纷纷扬扬,或落于人身,或散入水中。日暮后众女收聚落花归家,次日早起无暇梳妆,犹恐落英被风吹尽。
《落花篇》后抄录范铸的阙题诗和陈子昂的《感遇》,二诗说教的特征都十分明显。《感遇》后的《虞美人怨》为冯待徵作,此诗以虞姬的口吻,讲述自己与项羽相识相恋,后随军出征,不幸楚军垓下失势,最终项羽“拔山意气都已无”,虞姬则“纷天隔地与君辞”。
《虞美人怨》后抄王泠然的《汴河柳》,诗称隋炀帝开运河下扬州,运河旁遍植垂柳。但不久“功成力尽人旋亡”,数经战乱后,以致“数里曾无一枝好”。待作者乘舟入帝乡时,但见“河畔时时闻木落”,同船人无不以泪沾裳。
综观这三件文学写本中的诗赋,就会发现《唐诗文丛钞》开篇的诗赋是《龙门赋》,同一书者所抄的《唐诗丛钞》开卷则是《清明日登张女郎神》。这两篇作品都表现了出游的场景,与清明节有明确的关系。两篇《北邙篇》虽然文字各异,但内容总不离北邙这一与死亡有关的地标,并由此展开各种回忆和想象。两件写本中的《初度岭》《度大庾岭》表现了跨越山峦,《江上羁情》《扬子江夜宴》和《度巴硖》,则表现了在水上的游移与滞留。《唐诗丛钞》(P.3619)连抄的三篇登楼之作,与《诗文丛钞》(P.3640)中的《登楼赋》,正形成对应。死马、落花、秋日败柳、弃用之剑、霸王别姬和白头老翁,种种与衰亡有关的自然和历史意象,贯穿于这三件写本中。
如上所论,这三件文学作品并非以审美鉴赏为主要目的,而是与唐五代敦煌寒食清明期间的祭拜有一定的关系。这三件写本中的诗赋,在祖先坟墓前祭拜的仪节中,应该有其相应的象征意义。换而言之,这些写本与其说是文学作品的选抄,不如说是清明祭仪的手册。
与敦煌其他诗文集相比,这几件写本中的作品较为凌乱,并不像《珠英学士集》残卷和《唐诗丛钞》(P.2567+P.2552)那样井然有序。王粲的《登楼赋》插在两篇歌行体中间,崔颢的《度巴硖》和《黄鹤楼》被分于两处,李邕的两首作品间,也加入了《秋夜泊江渚》等作品。因此两件开端较为完整的写本,都以有关清明的作品开端,反映出这些作品可能用于寒食清明的墓祭。《王昭君》和《捣衣篇》等作品,或用来为葬在远方的亲人招魂。《登楼赋》等有关登楼登城的诗赋和佚名《北邙篇》,或用于希望去世的亲人早登仙境。《初度岭》和《江上羁情》等表现游离山水的作品,既可能用于七日的祭祀,也可能用于招魂葬。
据学者研究,墓祭兴起于汉代,而寒食清明墓祭则在唐代才纳入礼制,吕思勉先生认为,寒食上墓并非华俗。高宗龙朔二年(662)拟取缔“送葬欢饮”“寒食扫墓”等风俗,但结合玄宗时的境况,寒食扫墓明显未能禁绝。开元二十年(732),寒食上墓成为朝廷认可的典礼,同时要求不得在祭墓时作燕乐。这说明当时有人借怀亲祭墓之名,行声歌娱己之实。寒食清明扫墓的风俗,在敦煌也有反映,法国所藏的几件敦煌文书(P.2049、P.3234、P.3490),均记载敦煌民众寒食节时以面、油、酒等祭拜祖先。张籍的《征妇怨》也提到,“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时局动荡,战事不息,在战场上殒命也在所难免。
然而时过境迁,无论清明墓祭,还是招魂葬等,其具体细节已无法确知,仅能借助千余年后重现的文学作品,略加推测而已。敦煌文书借助文学作品来开展祭仪,除上述写本外,还有更为典型的一件有关佛事活动的写本(P.3645)。
这件抄有《萨埵太子赞》等赞文和《请宾头卢疏》《礼忏文》的佛事应用写本,也夹杂了有关“太保”的八首诗,其中前两首为佚名的《放鲤鱼咏》和曾庶几的《放猿》。这件写本或许与张承奉追祭其父张淮鼎的佛事活动有关,在活动中的放生环节,无论被放生的动物是否存在,这两首有关动物的诗歌,都会在仪式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二、 楼阁与河水
结合藏经洞所出《目连缘起》及《黄仕强传》等故事,人死后会堕入地狱,生前信佛者,则能离开地狱,升于天上。生前未信佛教者,则需要请僧作道场,六时礼忏,悬幡点灯,行道放生,才能由地狱到天堂。《目连救母变文》所描绘的天堂,则是“红楼半映黄金殿,碧牖浑沦白玉成”,俨然一片金碧辉煌的楼阁。目连在天堂寻母不得,又去找阎罗问讯,蒙阎罗告知须往泰山,方知其母去处。于途又经过奈河,看到“牛头把棒河南岸,狱卒擎叉水北边”。
敦煌所出的《十王经》(P.2003、P.2870、P.3961等),则称人亡故之后,二七之日从初江王处过奈河。其中有两句赞文为“二七亡人渡奈河,千群万对涉江波”。赞文右侧的画面中,一条河蜿蜒展开,许多未着衣的亡魂,在河中艰难跋涉,与赞文正好对应,可见依据《十王经》的表述,死者被葬入坟墓后,不仅受十王的审判,还要经历跋涉。
有学者根据《长阿含经》的记述,认为逝者渡过奈河之后,便无法生还,因此大呼“奈何”,故此得名。但也有学者指出,唐人在送葬时,亲友一边哭泣,一边号呼“某某奈何”之类的词句。当然结合周一良先生的研究,唐人在报丧或吊丧的书札中,也会使用“某某奈何”的套辞。只是现在很难确定“奈何”与“奈河”形成的次序。当然有一点可以确定,奈河与奈何是由谐音产生。但汉乐府《公无渡河》有“将奈公何”之句,项羽《垓下歌》也有“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追问,联系这些作品,汉诗中的奈何,恐怕已有悼人或自悼的意味。
与《十王经》同出于敦煌石室的《唐太宗入冥记》和《黄仕强传》等,对亡魂进入冥间的记述,与《十王经》并不相同,更未出现奈河等。倒是明代完成的小说《西游记》,对唐太宗出冥府的逆行过程,记述较为详细。书中称太宗被判还阳后,朱太尉执引魂幡,崔判官陪着太宗,先过了幽冥背阴山,又过了十八层地狱,然后依次通过金桥、银桥和奈河桥,经过血盆苦界,最后通过六道轮回中的“超生贵道门”还阳。纵观太宗到地府又离开,前后经过了阴山、奈河等,真可谓山一程、水一程了。
还是回到唐代,据白化文、刘安志等先生研究,唐代民众的冥世观念中,人去世后的归向其实很不统一。因此《十王经》称礼敬世尊的队伍中,除阎罗王外,还有泰山府君。这明显是人为改造后的结果,但不管后世的读者信不信,反正当时的抄经人应该是信了。
结语、装饰与良媒
虽然和人世间相比,冥界更显得虚无缥缈,但《目连缘起》《十王经》及《唐太宗入冥记》等的描写,又是那样历历在目。就像P.3645中两篇有关动物的作品,不免令人在诵读吟咏时,想起鱼猿等活物。正如许叔重《说文》所言,春祭因物品少,故多文词也。自汉代以来,文学虽不完全依附于经,但也不再应用于交聘,一度沦落为生活中的挂件,以致扬子云有壮夫不为的慨叹。
然而无论物质是否丰赡,文词在祭祀当中,至少在唐五代敦煌的丧祭中,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可谓沟通生者与逝者的良媒。在唐代的祭祀文学中,不乏《祭十二郎文》等以情感人的作品,但也有些既成的作品,在祭祀仪式中被借用。反映在唐五代的敦煌,前文所言《登楼赋》等表现登楼越岭涉水的作品,本来是作者现实中足迹及心境的一种记录。但在祭祀中,与逝者往来天堂、冥界、泰山和东海的行旅,又正好形成一种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