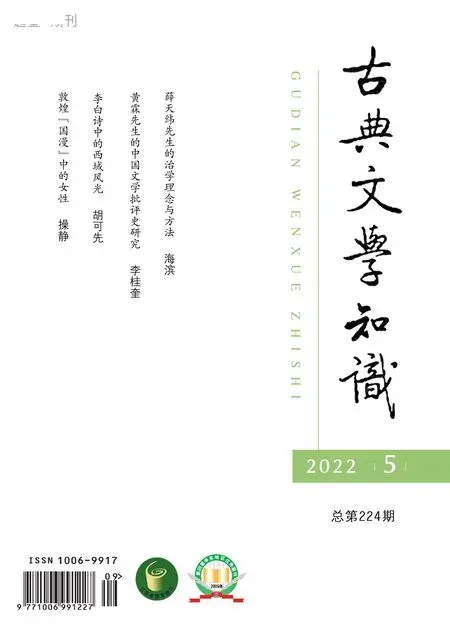杜甫文儒身份意识之形成和嬗变探析
张丹阳
中国古代士人身份意识颇为复杂,而文、儒为其两端。儒士的身份确立较早,具有文人身份意义的概念则是汉代以后才兴起,魏晋以后趋于明显。范晔《后汉书》“文苑”“儒林”别传,确立了文、儒分流的传统。隋唐之际,新兴的科举取士进一步推动了文、儒身份的转型,至盛唐时期身兼双重身份的“文儒”群体活跃于文坛。杜甫并非盛唐“文儒”的代表人物,但他文、儒身份意识的演变却有代表性。
杜甫文、儒双重身份意识源于家世两位荣耀祖先:杜预和杜审言。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杜预和杜审言所代表的“奉儒”“修文”两个传统,杜甫将之视为“先臣绪业”“先祖故事”,在诗文中反复致意,并作为自我认识的两维。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儒退文进。杜甫早期积极奔走于“奉儒守官”之路,其间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开元二十四年进士试,二是天宝六载制举。杜甫此时怀抱儒家济世宏愿,自信满满:“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然而开元二十三年赴试却铩羽而归,稍后的《杂述》记录了他落第后的愤懑心情。文中所诉贤不能进、士不见遇情况,与史载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政事后,“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相合。但未曾想,天宝六年杜甫又卷入一场被导演好的政治丑剧,赴选被黜。他对儒术的失望一度非常强烈,发出了“儒冠误身”“儒术无用”论。
经过两次科举的失败,杜甫的奉儒之路虽然遇阻,但文场的声名却为他带来了契机。杜甫积极展开了“修文”方面的努力,先后投赠诗篇给韦济、张垍等人,鼓吹自己的诗文,最终于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获得出身。杜甫在天宝十二载《进封西岳赋表》中自言“经术浅陋”,这是他没有汲汲科举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发现了“修文”这条捷径。表中说“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道出了真意。他赠集贤院试文的崔国辅、于休烈也说出了这一想法:“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国辅于休烈二学士》)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这次献赋经历,“往时文彩动人主”(《莫相疑行》)“彩笔昔曾干气象”(《秋兴》其八)。可以说,献赋成功强化了杜甫的文人意识。
第二阶段:儒进与文变。杜甫献赋出身,儒业似又可续,但这个过程被漫长的守选和突起的安史之乱打断。经历了身陷逆贼的危苦之后,杜甫开始重新思考人生路线,以奔赴凤翔行在这一非常举动为起点,他的人生进入儒施之于外的立功阶段。杜甫“麻鞋见天子,衣袖见两肘”(《述怀》)奔赴凤翔行在,古人津津乐道。黄生独具慧眼,发挥幽意:“公若潜身晦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杜诗详注》卷五)后人讨论杜甫一生出处大节有两派观点:一派以为是奔凤翔,另一派以为是疏救房琯。二者都是杜甫将儒术外化的典范行迹。杜甫拔贼中、赴行在是忠勇的行径,疏救房琯则是忠勇意识下的补衮职责。他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交代自己上疏救房琯的原因是“猥厕衮职,愿少裨补”。补衮意识是杜甫一生奉儒的重要心理结构。今杜甫文集中,存《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道,其一是:“今圣朝绍宣王中兴之洪业于上,庶尹备山甫补衮之能事于下……”杜甫将补衮之事带到策问题目,可见他内心的认同。
此阶段杜甫在诗文上的转向也值得关注,一个变化是诗论开始多起来,而且常常夫子自道,赵汸认为是“篇中说作诗,近于自注”(《杜诗详注》卷五引)。这正是杜甫对自己诗歌生命意义的明示。另一个变化是杜甫在此间对新诗体的尝试,尤其是长律。从至德元年的《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到乾元二年《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他有五次这样长律创作。相比之前二十韵左右的排律,这是一个突破,为其后“大或千言,次犹数百”的长律作了艺术准备。在古体诗方面,他的《北征》等诗更是鸿篇巨制。杜甫此间的诗论和诗体尝试代表了他对修文传统的更深理解,从施之于外的“献赋”转变为思考诗歌本身,再内化为一种诗学追求,是杜甫诗人身份认同深入的过程。
第三阶段:文儒融通。自入蜀至病卒是杜甫文儒身份融通的阶段,自知奉儒立功无为,遂聚焦立德、立言。郭受“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属望劳”(《寄杜员外》),准确反映了杜甫晚年立德立言、文儒融通的形象。
在文的方面,杜甫此期间在诗歌中系统阐释了自己的诗学追求和理想。首先,反复致意家世修文传统。他说“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赠蜀僧闾丘师兄》),明确以“吾家诗”(《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称杜审言,以赓续这个传统为己、为子任。《宗武生日》中他说“诗是吾家事”,在谆谆教诲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家世传统的眷念。其次,总结平生作诗心得和成就。此期杜甫论诗更为丰富,而且很多是他自己创作心得,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偶题》更是他一生创作心迹和诗学理想的总结,被王嗣奭称为杜诗“自序”、杜集“总序”。杜甫对自己的诗歌成就也是非常自信的。“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宾至》),自信中带有自负。“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名实因文章而著……反言以见意”(仇兆鳌注)。《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中说“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诬”,可谓自为定论。最后,整理文集。杜甫刚入蜀就开始整理自己的诗文,“书乱谁能帙,杯干自可添。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晚晴》)。往后,故旧纷纷离世,他寻检往日赠答诗文,对存稿又有过多次整理,还专门用一个“文书帙”保存交游唱和诗文作品。“久客多枉友朋书,素书一月凡一束”(《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为此,他常散帙“检所遗忘”。因为以文章安身立命,所以他对集子的保存和编集颇为用心。
在儒的方面,此前杜甫奉儒还有现实功利的考虑,入蜀后其儒家思想经过沉淀净化,事功的成分已渐渐退去,内化为一种精神食粮和人格力量。杜甫初入蜀,卜居西郭之浣花里,度过了一段闲适生活。随着宝应元年代宗即位,朝廷气象更新,杜甫关心时事的诗文开始增多,交游也广起来,足迹遍于阆州、绵州、汉州。在梓州其间,特地到射洪参观了陈子昂遗迹,有《陈公学堂遗迹》《陈拾遗故宅》等诗,瓣香陈子昂,心中的补衮意识再次被激发。当时吐蕃屡屡入寇,京师沦陷,南面边境戒严,杜甫写了很多关心战局的诗歌,如《西山三首》《收京》等等。他虽不能直接预事,但颇有建言,如广德元年《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回成都后,严武表为节度参谋参知军事,献《东西两川说》,展露了胸中韬略。除了积极献策外,他的忧国之情和恋阙之诚也表现在诗歌里面。杜诗中明说“恋阙”者六次,皆出现在这个时期,恋阙情结已成为杜甫晚年的精神支柱。与恋阙情结相表里,杜甫此期屡以“老儒”“腐儒”自许,致君尧舜的宏愿一直未曾褪色,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将之付与来者:“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
杜甫的一生是在奉儒修文双重身份意识的递变中走完的,文儒融通造就了他伟大的诗人气质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也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葛晓音教授指出,“文儒”型知识阶层在开元年间形成,整体经历了“分—合—分”的过程;因为时代背景、学术修养不同,开元文儒较重视文,而天宝文儒则多侧重于儒(《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杜甫连接了开元、天宝两个文儒群体而有其独特性。首先,他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于两大文儒群体。开元二十三年孙逖知贡举,拔萧颖士、李华等后来文儒代表人物,杜甫因落第未能融入这个圈子。查唐代登科记,献赋出身似仅杜甫一例。献赋对于儒学方面的要求大为削弱,这一点杜甫也与天宝文儒擅长儒术不同。其次,杜甫也没有预流天宝文儒的复古之风,而是走上了文、儒双修之路。究其原因,一方面天宝中杜甫在长安的窘迫生活,使得他对于外施的儒术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文的成就为他带来新的思路。杜甫濡染开、天文儒风气而能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既是他思想发露的自然结果,也与他家世双重传统紧密相关。在分析开、天文儒群体时杜甫的案例值得重视。
杜甫的文学成就与思想深度皆充实而有光辉,其双重身份古人已有论列,如朱熹尊之为“五君子”之一,李贽列之于“词学儒臣”。陆游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王十朋说“莫作诗人看,斯文似于长”(《诗史堂》),也在提醒后人注意杜甫的双面。杜甫对家世和自我的身份认识也对后世起到了垂范意义,如韩愈“余事做诗人”(《和席八十二韵》),屈大均“湘累辞赋吾家事,风雅能兼望汝曹”(《人日双桧堂社集与诸从分得高字》),毕沅“诗书吾家事,须俾仍业儒”(《哭延青三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