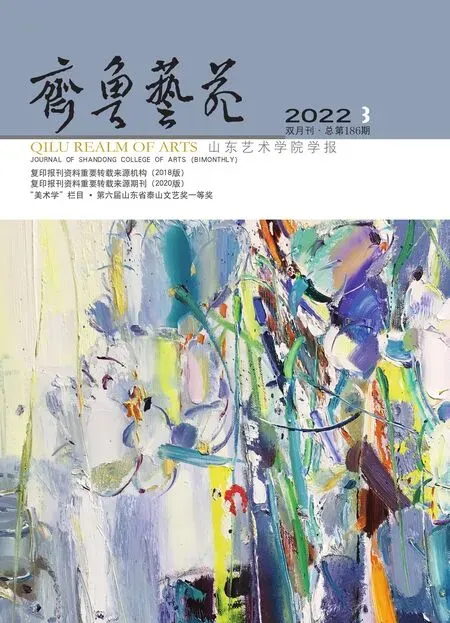“画论理不论体”:范玑《过云庐画论》
张建军
(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范玑为清代画家,擅长山水画,为江苏常熟人,号引泉,活动于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墨林今话》《桐阴论画》《清画家诗史》《书画书录解题》曾简略记述其生平,据说其社会地位不高,曾摆摊售卖书画、古玩为生,奉养母亲。其画多仿王翚、吴历而能稍变其法,其《过云庐画论》约成书于1795年前后。
范玑在《过云庐画论》中自述其师承说:“玑初学画于瞿翠岩先生,先生之师姜山人渔,山人之师尊古黄鼎也,名著宇内。”自认是黄鼎绘画传人。黄鼎曾得沈德潜称赞,师法王原祁,并上追黄公望。
一、“画论理不论体”
画论理不论体,理明而体从之,如禅家之参最上乘,得三昧者,始可以为画。未得三昧,终在门外。若先以解脱为得三昧,此野狐禅耳。从理极处求之犹不易得,而况不由于理乎?求三昧当先求理,理有未彻,于三昧终未得也。
画中谈理,始于宗炳《画山水序》,宗炳说的理,其实是通过绘画所体会到的山水万物之理。宗炳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
山水万物的理,通过画(影迹),而为画家与赏画者所体会,达到精神超越与感悟即“神超理得”。
范玑说“画论理不论体,理明而体从之”,就是说山水画本身的不同范式,本质上是来源于山水万物之理的,明了了山水万物的“理”,则山水画中不同范式,而有其不得不如此的道理,范式并非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画家根据山水万物的形态而创造的,山水万物之形态又是由其背后的理所决定的。
郭熙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拨,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下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欲激射,欲多泉,欲远流,欲瀑布插天,欲溅扑入地,欲渔钓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挟烟云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辉,此水之活体也。”
明了了山水造化的“理”,才知道一切画山水的具体的方法、范式都是根据山水形态而来,山水形态万变,但其理则有不变者,即万物之理,世间万物都有理,如所有山与水都不能摆脱地球重力原理。山之高下,水之奔流,都受此原理的作用。由山水万物之理,又引申出画山水的理——“山水,大物也”“山,大物也”“水,活物也”,那么画这样的庞然大物,就不能单纯以等比例缩小方式来表现其高、其远,而应该采取综合的方法,既有即时透视的因素,又有记忆与综合的因素,这才能够真正画出山水的高远之势与活泼之态来。
“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盖山尽出不唯无秀拨之高,兼何异画碓嘴!水尽出不唯无盘折之远,兼何异画蚯蚓!”
与郭熙关注从山水万物之理到画山水之理的探讨不同,范玑更感兴趣的是阐明山水画必须坚守“求理”的道路,而不能一味讲顿悟。
一方面,山水之理,有顿悟之处,“如禅家之参最上乘,得三昧者,始可以为画”。另一方面,即使是顿悟,同样是来自于从山水之观察到思考再到山水画实践。
对于明清画家来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将观察与古人的范式相比照,去寻求古人范式背后的理。
所以这种越到后世山水画家的艺术创作中,这种所谓顿悟之中,越需要更多的观察、学习、体验,除了对山水的体验外,更有对古人范式背后之理的探寻,单靠顿悟是不太可能一超直得的。所以范玑特别强调,一切顿悟必须建立在对理的掌握的基础之上。
“若先以解脱为得三昧,此野狐禅耳。从理极处求之犹不易得,而况不由于理乎?求三昧当先求理,理有未彻,于三昧终未得也。”
对理的探求其实有两种路径,一种是顿悟,一种是渐悟,作为一位地位不高、名位不显的曾沿街设摊贩卖书画古玩以奉养母亲的山水画家,范玑并不像苏轼米芾这样的文人画家那样相信顿悟,他是宁愿相信要在山水画的观察、学习与实践中先通过渐悟求理,然后才能有对范式的自由运用与发挥的。
但是鉴于传统画论中顿悟说的崇高地位,他也不敢否定顿悟价值,一边说“如禅家之参最上乘,得三昧者,始可以为画”,一边强调“求三昧当先求理,理有未彻,于三昧终未得也”,其实更倾向于求理,倾向于渐悟。
“不论体”,一方面,范玑不想谈具体的范式,另一方面,一谈具体范式就会涉及流派,自明末以来,山水画各种流派纷呈,互相攻讦,范玑不想陷入到这种门户与派别争议之中,而更想阐明,山水画中“理”的重要性,求理先于求体,求理先于顿悟。
“论理不论体”,也说明范玑并不是一位主张笔墨至上的清代山水画理论家,论理,是因为强调求山水之理,是为了得山水之真像,这说明范玑在明清山水画家们的笔墨程式与山水丘壑孰重孰轻的纷争中,属于更重山水丘壑的阵营。
正因为重视画理、重视丘壑,所以范玑对逸品的看法,也与笔墨至上派不同,他说:
从来画品有三:曰神、妙 能。学者由能入妙,由妙入神。唐朱景元始增逸品,乃评者定之,非学者趋途。宋黄休复将逸品加三品之上,以故人多摹而思习,为谬甚矣。夫逸者放佚也,其超乎尘表之概,即三品中流出,非实别有一品也。即三品而求古人之逸正不少,离三品而学之,有是理乎?
如此,则逸品只是从神妙能三品中所“流出”者,所以,有意追求逸品,是错误的。范玑以“流出”一词来说逸品与三品的关系,既含糊,亦无新意,但这样的说法,却显露出范玑对山水画笔墨至上派喜逸品,追求顿悟而忽视画理、丘壑这种风尚的不满与反拨。
二、“画以养性”
画以养性,非以求名利。世俗每视人名利之得失而重轻其画,此大可鄙,莫为所惑!尝见古人显晦蚤暮不同,多有如子昭、仲圭之异,苟或遇涩而遂汲汲于名利,致笔墨趋时,遗本逐末,多陋习矣。即志得意满,何足羡哉!
“性”,在古代有多种含义。
《广雅》:“性,质也。”《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又说:“自诚明谓之性。”人的先天本质,称为性。因为儒家尤其孟子的影响,中国古代一般都倾向于性善之说,认为人之性本善,所以范玑说画以养性,也是将“人之初,性本善”当成一个起点,认为画有助于人的善之本性的培养。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一方面,人性本善,另一方面,需要去内求,去发掘、去培养自己的先天本有的内心的善。
范玑认为,画的意义在于通过画去涵养自己美好的本性,而非追名逐利。世俗之失,在于汲汲于名利,所以不能坚守美好的本性,舍本逐末,盲目跟风,追求世俗的成功的后果就是人性的失落与艺术的堕落。
性灵之说自明代以来流行很广,影响深远,明代公安三袁提倡性灵。清代袁枚亦主张“抒写性灵”。
绘画一直与诗具有密切联系,山水画更是被视为诗的延伸,诗学中的性灵之说,也自然影响于山水画论。
范玑明确提出“画以养性,非以求名利”,一方面是自古以来的畅神说、自娱说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诗文论中性灵说的渗入的结果。
另外范玑所说“尝见古人显晦蚤暮不同,多有如子昭、仲圭之异”,是举来自传闻的吴镇与盛懋的故事,旨在说明绘画不要急功近利。董其昌《画旨》中说:“梅花道人吴仲圭,画师巨然,与盛子昭比门而居。盛虽工,实有笔墨畦径,非若仲圭之苍苍莽莽、有林下风气,所谓气韵非耶?人而已。”
范玑举吴镇与盛懋的例子,是根据董其昌的观点,认为吴镇与盛懋的境界之高下,主要是缘于其人格与气韵的高下。因为吴镇人品更高尚,其绘画之气韵也更高。所以画家人品高尚,养成高尚之人格,相比求名求利,更具有本质意义。
范玑还说:“画可观人之性而即可验人之行,行不立,工画无益,纵加绫锦装池未可入端人正士之室。故学画且须检身心,心澄则志高,身修则神定。亦如弹琴者淫僻之音也。”
一方面,画应当涵养人的本性、善性,另一方面,画亦可见出人之性,一个人的人品不过关,即使绘画技术高超,其画仍然不足观,人品的失落导致的绘画的精神失落,是技术与装潢都无法掩饰的。
范玑的观点是否一定合理?人品与画品之间究竟是怎样的?这里不拟深究,但范玑讲“画以养性”,并且继承古代关于人品与画品关系问题的观点,提出“画可观人之性而即可验人之行”,的确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人品画品关系的探讨。
范玑还说:
士夫气磊落大方,名士气英华秀发,山林气静穆渊深,此三者为正格。其中寓名贵气,烟霞气,忠义气,奇气,古气,皆贵也。若涉浮躁烟火脂粉皆尘俗气,病之深者也,必痛服对症之药,以清其心,心清则气清矣。更有稚气、衰气、霸气,三种之内稚气犹有取焉。又边地之人多野气,释子多蔬笋气,虽难厚非,终是变格。匠气之画,更不在论列。
自古论画,多谈气,“画以养性”,这个性,其实就是人格修养,也是人的精神气质,山水画中风格、风范、艺术境界,实与画家人格之气息息相关。
孟子讲“养我浩然之气”,养性也是养气。养性的正面效果,就是画中的“士夫气磊落大方,名士气英华秀发,山林气静穆渊深”,磊落大方的的气,来自于平时行为上的修为,英华秀发的名士气,来自于读书养成的才气,静穆渊深的山林气,来自于山林隐逸涵育的静气,这些体现在山水画中,都是正格。
三、“邱壑之难在夺势”
范玑对于绘画之难,是深有体会的,他曾说:“学画难于作文,并难于学书。”究其原因,文章可以通过抄写和印刷传播,比较容易取得、摹仿。画则“不能钞印摹勒,即托于木石成绣工花样矣”。
学画难,而对于山水画来说,创作更难。山水画创作之难,关键在于画出自然山水的变态万千的真实之势很难。他说:
作画莫难于邱壑,邱壑之难在夺势,势不夺则境无夷险也。起落足则不平庸,收束紧则不散漫。时而陡崖绝壑,时而浩渺千里。时而遇之意远情移,时而过之惊心摄魄,旷若无天,密如无地,萧寥拍塞,同是佳景。
我们从“画论理不论体”的讨论中,已知范玑在明清山水画家们的笔墨程式与山水丘壑孰重孰轻的纷争中,属于更重山水丘壑的阵营。
正因为重视丘壑,所以才能认识到丘壑之难,只有经历了对丘壑的探索,才能理解“丘壑之难在夺势”。
明清山水画的一个突出的弊端就是,笔墨程式本是为画出山水丘壑服务的,但是,随着笔墨程式的资源积累到异常丰富的地步,画家渐渐忘却了这一背景和事实,山水画的艺术追求与精神重心,发生了变异。
不少画家开始在笔墨程式内部进行山水画创作,不再从山水丘壑中去探索、更新那种能够表现真山真水之真性情的笔墨,而是将古人的以古人现成的笔墨,将古人的山水画程式“搬来弄去”,长久发展下去,则山水画可以与真山水无关,而仅仅与笔墨程式相关。
这一现象,在清末民国初,受到了陈独秀等人的严厉批评,陈独秀将清代“四王”尤其是王石谷作为一个反面典型,批评其摹仿古人、不能写实、不能创新,代表了中国画的失落。
美国学者高居翰则从正面理解这一现象,对董其昌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山水画史上的这一问题,非常复杂,而且讨论者各自又从不同倾向性出发,画家有不同宗派,理论家有不同理论背景、政治立场等,各自立论,互相难以说明对方。
本文欲另辟蹊径,跳出惯常的思路,从一个类比的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西方19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有“关于诗的诗”之说法,其代表人物有马拉美等诗人。意识流小说创始人乔伊斯,其代表作《尤利西斯》,模仿古希腊荷马史诗,从书名从故事,与原荷马原著,多有对应关系。当代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一生在图书馆工作,其文亦称“关于文学的文学”。其实,明清的众多山水画,从某种意义上讲,亦可称为“关于绘画的绘画”,这种关于文学的文学、关于绘画的绘画,是有其价值的。
但是无论是“关于文学的文学”还是“关于绘画的绘画”,都有这样的前提:
其一,这种艺术不能成为主体,所有的作家、画家都去创作关于文学的文学,关于绘画的绘画,文学与绘画都会失去其百花齐放的局面,变成无比单调的艺坛。马拉美称自己的诗为“纯诗实验”,明确标明其创作为高端、非主流、小众艺术,乔伊斯、博尔赫斯等人,都被视为稀少、另类、罕见的艺术家。
其二,这种艺术,虽以前人艺术为背景,但却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意识,它们须是现实的另类折射与表现,而非与现实毫无关联。马拉美执着于抒写纯美,正是对现实铜臭破坏美的反抗。乔伊斯塑造的尤利西斯形象正是失落、无力的当代“反英雄”代表,而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魔幻、重复,都是对当时拉丁美洲社会动荡与停滞之现实的抨击。
“关于绘画的绘画”却成了明清山水画主流,这是其一,即使是关于“绘画的绘画”——“关于山水画的山水画”,同样需要到真实的大自然、到真山真水中去汲取营养,就像乔伊斯、博尔赫斯小说中所汲取大量现实生活细节一样。
单纯的将古人笔墨进行反复提纯、变化,固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相沿日久,长期发展下去,其结果必然是山水画的语言与精神的贫乏,因为没有了“江山之助”,缺少对自然造化新的理解与吸收,山水画陷入于笔墨程式之自我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必将伤害山水画的艺术创造,也使得笔墨程式缺少源头活水,无法实现语言更新。
范玑是有眼光的,在明清笔墨地位超越丘壑的时代,他认识到山水画的关键还是在丘壑,要从丘壑中寻找各种不同的山水之“势”,将变化万千、精彩纷呈的自然吸收到笔端,山水既有惊心动魄,亦有浩渺千里,山水地貌本身有千万变态,而云雾霞光,风云变化,雨雪冰霜,阴晴朝暮,以及四时朝暮的变化,又带来无数风景情状的可能性,难怪苏轼认为山水是“无常形而有常理”的。郭熙说:“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晴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面对无比丰富的山水,而仅仅迷恋于山水画笔墨之内循环,岂非一件十分可惜的事吗!
山水画的本原与根源是山水,离开山水丘壑,而仅谈笔墨之精致与伟大,吾欲不称其为舍本逐末,可乎?
四、“画不可示于藏家”中的创新思想
范玑名位不显,其画虽属文人山水画一脉,其人实属隐迹民间的平民画家。其《过云庐画论》历来关注度并不高,但从其“论理不论体”,重视山水画中的丘壑之势,及对“山水养性”的阐述,其在山水画理论方面还是有其贡献的。
范玑还有一些议论,也很值得回味。如:“学画须得鉴古之法。鉴古不明,犹如行远而不识道路之东西,鲜有不错者。但世之鉴古都以真赝为准的,不以用意为高下,即有爱其取境新奇,仍不究合法与否,果曷故耶?盖藏家则以名之轻重,价之多寡,传之何氏,重题跋,考记载,验字迹与印文,别纸素之全损,及篇幅中繁简粗细而定之,与画却不关涉。……真鉴别者必画学精深,但辨工拙,不为名动,求其所以然之妙,而一点一画玩味之,可以自证功夫,资长不足。”
一方面画家创作须以鉴古为基,深入传统,继承创新,才是真正山水大家,另一方面,一般鉴古方法,不重艺术方面的推敲,只重视名头及其真假,还有鉴藏的历程,这些对于考证文物(作为文物的山水画),当然意义重大,但是,不能代替艺术的体味与分析。对于画家来说,鉴古,更重要是在鉴赏古画过程中,“求其所以然之妙”,探求古画之所以高超的真正妙处,从画理上弄清楚所鉴赏为何高妙,以此为起点,来进行学习,汲取其优长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又如:“画不可示于藏家,藏家多见名迹,若不相似何宗面目者,必不道好,所谓皮相者也。”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山水画的创作家,更需要的是对丘壑汲取,笔墨的学习是之前的训练过程,所以,山水画家需要有我自为我,“自我作古”的自信精神。而山水画的藏家,却往往会沉迷于古人巨迹名作的魅力之中,甚至慑服于古人的大名之下,总是如郑人买履一样,拿古人的作品这个“度”,来量一切当代的创作,其结果当然是都不符合其标准。这就是“画不可示于藏家的原因”。
范玑这里所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藏家不一定都是皮相之见者,但是如果藏家以自己所见古人作品的为标准去衡量当代作品,那么,凡是有创新性的作品,都不会符合其标准。
但其实只要画合于理,与古人的作品不一样,又有什么问题呢?反倒如果真的一样了,那就不是创作,又成复制了。从这点来看,范玑的山水画理论中,还是具有一定的创新因素,鼓励离开宗派面目的。
“画论理不论体”之说,其价值亦于此可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