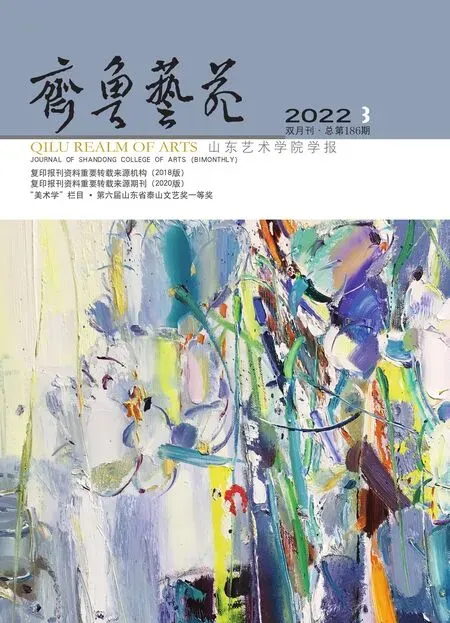明清小曲在戏曲音乐创作中运用的成因及特征
孙茂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编辑部,北京 100012)
一、明清小曲与戏曲音乐创作“同源性”的创作机制背景
明清小曲是指明清时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可反复填词并入乐演唱的通俗歌曲。明清小曲还有时调、时尚小令、俚曲等诸多称谓,但内涵上是一致的。明清小曲本来是作为与戏曲相对的一种音乐体裁形式而提出,即清刘廷玑所言:“小曲者,别于《昆》《戈》大曲也”,杨荫浏亦指出:“小曲是与戏曲相对的名称,‘小’只是指它的表演形式比较简单而言”。虽然明清小曲是作为与戏曲对立的概念提出,但随着小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呈现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时尚小令》中所描绘的:“不问南北,不问男女老幼,人人习之、亦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的情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受到俗乐领域中戏曲作家的重视,于是逐渐参与了明清时期的戏曲音乐创作。
学界对这一现象也有关注和研究,如冯建志《明清小曲对明清戏曲的促进作用》、尹蓉与魏亚冲《论汤显祖戏曲中的时尚小曲》、陈新雄《明代戏曲中的时调小曲研究》等,均是针对小曲在参与并推动明清戏曲音乐创作中的专门研究;翁敏华《明清小曲的流变及其他》、徐元勇《明清俗曲流变研究》、朱崇志《论明清咏剧小曲的传播特性》等均关注到小曲在戏曲、曲艺等多种音乐形式中的流变。
相关研究重在对小曲参与明清戏曲创作的具体内容、流变过程予以分析阐述,但对于其背后的原理较少探讨,基本默认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虽然有研究指出,明清小曲参与戏曲创作是因为二者处于同源文化语境,但这个“源头”究竟起自何时、何处?
应该看到,明清小曲在整体上呈现出这样的一般过程:明清时期社会上大量流行的时调、小曲,有一部分流传不久旋即被淘汰,有一部分却备受人们追捧,在不断填词创作中形成曲牌。明代形成了诸如【打枣杆】【挂枝儿】【劈破玉】【银纽丝】等具有“我明一绝”(卓柯月语)象征意义的小曲曲牌,清代亦有【叠落金钱】【剪靛花】【九连环】【绣荷包】【鲜花调】等曲牌彰显时代特色。成牌的小曲被明清时期戏曲作家关注,纳入其音乐创作。明清小曲自身通过一曲叠用、多曲联套、曲间加说白、曲间加帮腔、板腔化改造等开始作为中间环节向戏曲、曲艺迈进。这些创作过程及特征显示出对曲子及其创承机制的因循与发展,对此笔者在学位论文《从明清小曲探究曲子创承机制》中已有探讨。简言之:曲子这种形式在发生学意义上始于隋代。曲子的艺术本体以长短句式配合依曲填词(定声、定腔传词)为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其上承古歌、古乐府一脉重视音乐、声律的传统,下启唐五代曲子词、宋词、南北曲、明清小曲的发生与发展。由于较高的艺术性要求,曲子主要有专业乐人(唐宋以降至明清主要以乐籍群体为主)在体系内创承,同时面向社会广泛传播,文人与乐人在唱和中互动创作,曲牌的意义得以彰显,词曲创作进一步雅化,同时曲牌依宫调类归,其后被纳入诸宫调、唱赚、杂剧、南戏等大型戏曲、曲艺等形式中运用,由此构成了“曲子创承机制”的完整历程。这一创作机制以曲子作为专业音乐创作的核心,文人与乐人互动创作为主体,国家制度下组织化、体系化创制、传承与传播为背景,并可以从历时层面梳理出“曲子—曲子词—曲牌/词牌—南北曲—明清小曲”的整体发展脉络。曲子、曲牌的创作如大浪淘沙,有些被淘汰,有些曲牌不断积累,由此构筑起庞大的曲牌家族,为历史上围绕曲子为基础的戏曲、曲艺、器乐等多种音乐体裁形式的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明清小曲参与戏曲创作背后的机制、原理,这种“同源文化语境”根源于曲子创承机制。
明清小曲创制仍是以专业乐人与文人的互动创作得以推动。但明清时期“文人”与“乐人”的来源更加多元化、复杂化,其中隶属乐籍的官属乐人群体仍是音乐技艺创制、传播的主体与主导。明清时调、小曲的传承、传播仍以体系化传承与多渠道面向社会传播的方式相结合,呈现出以王府与高级别官府所在城市为中心,通过青楼歌馆、茶楼酒肆等商业平台及营运性班社面向社会广泛传播的过程。大运河沿线、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等形成的自然传播路线,仍以州、府一级为重要的传播中心,继而通过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面向社会广泛传播。由此造成了明清小曲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并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极强的渗透力,因而被戏曲作家重视并应用于戏曲创作。明清小曲与戏曲创作相辅相成,又互相促进了各自体裁形式进一步的发展。以下本文即对此展开,论述明清小曲参与戏曲创作中的具体运用与表现以及相应的阶段性特征。
二、小曲以灵活的方式参与明清戏曲音乐创作
小曲在明至清中前期用于戏曲创作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使用起来自由、灵活,主要目的在于活跃气氛,但小曲曲牌不纳入套数结构体制内。如明汤显祖《邯郸记》第二十六出《杂庆》在南吕过曲【大迓鼓】中使用了小曲【银纽丝】。如下所示:
“〔众〕这等权把你当小娘。唱个小曲儿。……〔乐〕也罢。便做小娘唱个银纽丝儿。
〔唱介〕爱的是奴家一貌也花。亲亲姐妹送卢家。好奢华。独自转回衙。风吹了绿帽纱。斜簪一朶花。小攒金袖软靴儿乍。撞着嘴唇皮疙癞。臭冤家。把咱背克喇。钻通鬬不着也他。我的外郞夫呵。唰龟儿我龟儿唰。
〔众〕唱的好。再唱再唱。〔乐〕罢了。”
这首《银纽丝》配合前后剧情创作,虽遣词造句在模仿民间作品风格,却是一首文人拟作,显现经一定程度上的文词雅化内涵。但这首《银纽丝》并不纳入《杂庆》一出中所用套数体制之内。《杂庆》所用的套数体制是【大迓鼓】四调“重头”连套。任中敏《散曲研究》中说“南曲中两调或四调重头即可成套”,此处即采用此种套数体制。
【银纽丝】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中仅有这一次运用实例。他在戏曲创作中使用频率更高的是“打歌”。“打歌”是类似【吴歌】【山歌】一类的时调、小曲,但又不完全相同。对于“打歌”的作法,汤显祖在《邯郸记·第十三出·望幸》中写道:
“话分两头。且问二位仙乡何处。〔贴丑〕江南人氏。〔净〕会打歌儿哩。〔贴丑〕也去的。〔净〕……劳你打个歌儿。将月儿起兴。歌出船上事体。每句要弯弯二字。中两句要打入帝王二字。要个尾声儿有趣。〔贴〕使得。
〔贴歌介〕月儿弯弯贴子天。新河儿弯弯住子眠。手儿弯弯抱子帝王颈。脚头弯弯搭子帝王肩。帝王肩。笑子言。这样的金莲大似船。”
“打歌”要有起兴,此处按规矩用“月儿”起;歌词内容贴合规定的对象,每句歌词要有“弯弯”二字,中间两句要嵌入“帝王”二字。而随后所唱的这首《打歌》显然满足了打歌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打歌”类似酒令艺术中的“打令”。前文所引唐代流行的打令,同样有起兴的要求,规定歌词描写的对象等。因此此处的“打歌”或只是这一类小曲作法的代称。“打歌”也有固定的结构体式,好比词调音乐中“令”也形成了“十六字令”“百字令”等固定的长短句结构,但这种结构不具有曲牌意义。“打歌”也不应该以曲牌定位。
小曲进入戏曲创作在清代也有相同情况的延续。清乾隆时完成的《升平宝筏》是一部西游记剧本,叙写玄奘西游故事,此剧本中有多处需要演员随意发挥演唱时调、小曲的环节:
第十四出【高宫套曲·脱布衫】:“二鱼精作唱小曲,随意发诨[挥]”;
第十七出【黄钟宫正曲·画眉序】:“(赛太岁赞科,白)这清曲,果然唱的好!……(白)李姨,你可唱夸调与我听!(一宫女随唱时行小曲科)(赛太岁赞科,白)这夸调,果然唱的好!”
这里根据故事情节,“鱼精”“宫女”均需要演员作唱时兴的小曲,随意发挥。这里对小曲使用的方式仍强调灵活、随意,同样不入所在套数结构体制之内。小曲这种应用方式还有很多,如戏曲集《缀白裘》记录的清初梆子戏《花鼓》(第六集),有一出富家恶少请打鼓卖艺夫妇二人在庭院唱小曲的过程,另有梆子戏《打面缸》(第十一集)有一出表演官吏、衙役等人在周腊梅家听唱小曲取乐的场面,等等。
以上所列举的小曲在戏曲创作中的使用方式,是把小曲以一种较随意的方式灵活插入戏曲表演之中,或是通过前后故事情节填词新制,让处于配角地位的演员自由发挥演唱,用以活跃气氛。但所用小曲曲牌不纳入所在剧目的套数结构体制之内。
但随着小曲在明清间的发展,小曲曲牌开始连缀,形成套数体制,如《霓裳续谱》卷五的《扬子江心》使用【粉红莲】【锁南枝】【尾声】连套;卷五中《乡里亲家我瞧瞧亲家》用【银纽丝】【秦吹腔】【京调】【数岔】【南罗尔】【秦腔尾】六曲连套,分角色表演,还有对唱、数板、剁字、说白等多种戏曲、说唱手法的运用,篇章结构庞大,已经是戏曲剧本的意义。以下以卷八《万寿庆典》中《独流乡景》,由【银纽丝】【永清歌】【清江引】联套为例举证:
【银纽丝】丰乐太平五谷也么收,土产芦蒲在独流,胜似大秋,五日一集永长周,卖些钱和钞,买鱼又沽酒,丰衣足食神天佑,草亭避阴推碌轴,一家大小莫要把闲偷,叫声长青儿,嗄咳,抱蒲子咱把活来做。【永清歌】乡村太平歌,重独流的生活指著这个,每日里织蒲席才把那日子过,淀池不扬波,重芦花深处听渔歌,罾网无空载得满船过,荷花馥馥香,重红绿争妍满池塘,皆赖君有道,才得率士旺,清秋桂枝香,重吾皇千秋万寿无疆,众乡民叩祝皇恩荡。【清江引】军乐民安太平景象,万国来朝皇,歌舞升平世,人人都欢畅,庆无疆,永绵绵,常把千秋享。
【银纽丝】【永清歌】为明清小曲曲牌,【清江引】可以作为“尾声”,由此构成纯粹由小曲曲牌联套的套数体制。此外,清代戏曲集《缀白裘》卷三《青冢记》的《出塞》用“【西调】—【西调小曲】—【西调】—【弋阳调】—【弋阳调】—【尾声】”;卷四杂剧过关中【西调】与小曲【四大景】(春夏秋冬)连套;同卷二关中【夜夜游】(呀呀油)与【京腔】连套等,均是纯由小曲联套。
套数体制的形成对戏曲创作有重要的意义。一个套数可以表现一段完整的故事情节,因而当小曲曲牌联套用于戏曲创作,显然推动了以曲牌联缀体为基本结构体制的戏曲音乐的发展。另外,小曲作为单支曲牌被清代地方小戏所用,或是进行板腔体改造,对推动清代戏曲繁荣同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小曲在清代小戏中为用
“小戏”是指篇幅简短,故事情节、表演形式简单,演员在一至三人以内,与篇制长大、结构复杂的大戏相对的一类戏曲形式的统称。从戏曲艺术发展历程来看,大体都经历了从“小戏”到“大戏”的过程。如宋代以前,产生于隋唐时期的歌舞戏《踏摇娘》就属于小戏类型。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踏摇娘》在民间生发,然后有一个纳入乐籍体系后经历规范、上升、转化、反播,进入教坊体系,其后在各地扮演的过程。南戏的前身“永嘉杂剧”也是南下乐人结合当地村坊小戏、里巷歌谣等多种原生艺术形态歌舞音乐加工后形成。因此“小戏”这种形态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并通过乐籍体系,以各个地方专业乐人为枢纽,与成熟意义上的“大戏”始终存在互动关系。小戏可以通过专业乐人的选择、加工、提升、雅化向大戏过渡;大戏也可以吸收小戏在腔调、故事、表演等方面的特色为自己所用。这一情况在明清时期依然延续,以清代小戏的发展尤为典型。
清代地方小戏有些就是在流行时调、小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简单的戏剧表演。李家瑞《北平俗曲略》曾以《小放牛》一剧为代表说明这类戏剧的特点:
“《小放牛》一剧,系集流行小曲而成戏剧,如‘正月里来什么花几开……’一段,集《对花》曲词也;‘姐儿门前一道桥……’一段,集《十支红绣鞋》曲词也;而其全剧的意义,乃是演‘一牧童放牛郊外:与一女郎两小无猜,随意度曲调情’(原注:录《戏考》语)。大凡此类集曲的戏剧,其目的在[是]在戏台上唱小曲,戏剧的意义,则不甚注意。《小放牛》虽然是集各样曲词而成,但腔调却是自成一种,即通常所谓吹腔也。唱时且唱且舞,和以短笛,笛声与唱声,并起并落,与昆曲相似”。
《小放牛》一剧表演只需要两人,“一生一旦”,这种两人演的“对子戏”是小戏主要采用的方式;剧情简单,戏剧的意义不是主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歌舞表演吹、唱小曲。该剧所唱小曲音乐主要通过“集曲”手法得来,但经过规范、改造,在该剧内部达成腔调风格的统一。笛子伴奏音乐与演唱音乐“并起并落”,这一传统源于南曲,明南教坊乐人顿仁有言:“善吹笛管者,听人唱曲,依腔吹出,谓之唱调。”这里的“唱调”即此处的“吹腔”,笛子所吹的旋律与演唱的旋律完全一致。该书同时指出,昆曲亦为“吹腔”之一种,但另有称为“吹腔”的安徽人所歌之“枞阳腔”,名“石牌腔”,非吹腔,而是弦索调。这里还是基于“唱调”“吹腔”这种唱腔与伴奏乐器是否完全同步上的一种判断。
除了《小放牛》,《打花鼓》《打猪草》《王小赶脚》等小戏剧目,清代活动于许多地区的采茶戏、秧歌戏、花鼓戏、花灯戏、滩簧戏、落子戏、道情戏等也多为此类小戏形态。清代这些小戏的声腔体制或为曲牌体,或为板腔体,或是二者的杂糅形态。采用曲牌体声腔体制的小戏中,明清小曲是其曲牌的重要来源。比如采茶戏中,广西地区流行的采茶戏多采用【五更调】【红绣鞋】等曲牌。花灯戏中,云南花灯常用【打枣竿】【倒扳桨】【金纽丝】等曲牌,贵州花灯常用【叠断桥】【五更调】等曲牌,四川灯戏常用【银纽丝】,湖南花灯常用【虞美人】【红绣鞋】等曲牌。滩簧戏中,从小戏发展而成的沪剧,常用【寄生草】、【夜夜游】(呀呀油)、【紫竹调】等曲牌。道情戏中经常用到【耍孩儿】。秧歌戏中,唱腔有以曲牌体为主的类型,其音乐主要来源既有明清时流行的小曲、小调,又以演唱当地的民歌、音调为主,比如祁太秧歌、沁源秧歌等;也有唱腔以小曲与板腔体混合样态为主的,这种混合类型中的小曲又称为“训调”,如【跌落金钱训】【四平训】【苦相思训】【高字训】等,如朔县秧歌、蔚县秧歌等;还有一类秧歌以板腔体为主,如襄垣秧歌(襄武秧歌)、泽州秧歌、定县秧歌等。
有清一代,戏曲是人们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特别是在缺乏娱乐活动的乡村社会,节令戏、酬神戏等以各种名目为理由的演剧活动此起彼伏。人们除了欣赏大戏,小戏也是满足人们对戏曲欣赏需求的重要补充,还形成了在夜间搬演小戏的情况。有研究者对清代“夜戏”进行了研究,指出其主要演出花鼓戏、傀儡戏、傩戏、秧歌戏、太平鼓等类型,曲目以“新满江红”“思凡”等为主,并分析清代乡村社会“夜戏”兴盛的三点原因:其一是清政府对地方管理相对宽松;其二是乡民对戏曲的强烈需求;其三是“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竞争激烈的戏曲生态,使得戏价日趋低廉。……乡村社会的大量需求使得这一市场在清代变得异常活跃,竞争使戏价日益走低,无法确保戏曲搬演的质量,地方小戏因此日趋昌盛”。对于第三点原因,清代社会竞争激烈的戏曲生态在初期尚不明显,这一状况的形成在于乐籍制度解体后,原本官养的乐人转向“民养以及官民共养(尚有富商巨贾之包养)的模式”,“一般民众的欣赏需求成为主流”。戏曲艺人、戏班需要自负盈亏,不得不去开拓市场,迎合普通民众的欣赏需求,获取收入。
据山西蒲县柏山东岳庙现存清乾隆十七年(1752)《昭兹来许》碑记载:
“人每岁于季春廿八日,献乐报赛,相沿已久。嗣因所费无出,久将废坠,爰公募银二百两,付之典商,岁生息银三十金,以为献戏之资,至期必聘平郡苏腔,以昭诚敬,以和神人,意至虔也。乾隆八年夏,器等寔首其事,因所托非人,骗银误戏,暂觅本县土戏,以应其事……。”
从此处记载可知,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中专业乐人组成的昆班也需要下至县一级演戏,但雇佣此班花费不菲,此碑就记载乾隆十七年(1752)因托人请昆班被骗银两,短时无法凑齐只能用县里“土戏”。但酬神戏必请昆班以示敬重,以“土戏”献神恐神灵不悦,于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同一处的《用垂永久》碑记载了因“土戏亵神”故再请苏腔班而集资一事。酬神戏请昆班花费之巨,从《扬州画舫录》记载可见一斑。纳山胡翁曾请扬州昆曲名班“老徐班”下乡为关帝庙演戏,班头开价“每本三百金”,并且每餐必食“火腿及松萝茶”。尽管代价不菲,但胡翁仍每日以三百金置台上请老徐班演戏。另,今人李文军多年来在浙、皖地区收集了大量昆剧酬神戏抄本,可见以用昆剧酬神在各地已经形成了传统。乾隆时昆曲在“花雅之争”后日渐衰落,但由于文人群体对其偏好,各地酬神献戏的用乐需求,昆曲仍保持传承并维持了一定的规模,而广大民众显然把注意力更多转向花部乱弹诸腔以及地方小戏。
各地小戏经过发展,在清末民初时,部分已经通过自身艺术化的提升而向大戏过渡,尤以南方诸剧种为代表。20世纪崛起的一批地方剧种,“评剧、楚剧、越剧、锡剧、扬剧、淮剧、沪剧、庐剧、黄梅戏等,都是以小戏起家,后来发展为大戏的剧种”。这其中,清乾隆时首先以时调意义流行的“滩簧”,对推动南方诸小戏向大戏的过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清稗类钞》载:
“滩簧者,以弹唱为营业之一种也。集同业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旦浄丑脚色,惟不加化装,素衣,围坐一席,用弦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戏文,惟另编七字句,每本五六出,歌白并作,间以谐谑,犹京师之乐子,天津之大鼓,扬州、镇江之六书也。特所唱之词有不同,所奏之乐有雅俗耳,其以手口营业也则一。妇女多嗜之。江、浙间最多,有苏滩、沪滩、杭滩、宁波滩之别。”
滩簧是一种弹唱弦索清曲的形式,分角色、有歌白、有戏谑,围坐一席没有表演,类似大鼓、说书的表演形式,可以说兼有戏曲、说唱两种艺术形式的特色。滩簧在乾隆时的苏州地区率先流行,其后迅速蔓延至广大乡镇,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晚清时“滩簧”的曲调又有区分,“前滩”类似昆曲,“后滩”接近小曲,这种小曲小戏十分受欢迎,余治《得一录》记载:“今观于某乡因演《摊簧》数日,两月内屈指其地寡妇改醮者十四人。”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对当时因为滩簧演出影响人心一事进行了批判,不过也足见当时这种演出形式影响范围之广,对人影响之深。
滩簧其后传播至相邻地域,在与周边区域方言的结合过程中,清同光年间出现了的“沪滩、杭滩、宁波滩”,其后通过延伸、发展,直接以“沪剧、杭剧”等命名,苏剧亦从苏滩演变而来。这是小戏向大戏延伸、发展的一种方式。另外,滩簧亦对姚剧、甬剧、湖剧、瓯剧、婺剧、锡剧等大戏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时调”作为流行腔调意义上,上述剧种都有受到滩簧腔调影响,并把其纳入各自声腔为用的过程,或借鉴滩簧中成熟的音乐体制、曲牌唱调方法、歌白的戏曲表现形式等,这对于丰富相应声腔腔调材料,促进各自戏曲音乐体制、表演程式的成熟等,都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另外,明清以来各种“二人戏”“三小戏”,当下的各地仍有活态留存的采茶戏、花灯戏、二人转等均属于这种小戏类型。小戏之“小”是与其故事、人物、表演、音乐等戏曲本体形态相关,其中的关键是中国戏曲的脚色制。解玉峰考察了脚色制与中国戏曲的关系,他根据《中国大科全书·戏曲卷》所列二百多个“剧种”,把戏曲分为三类:一是使用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大戏”,如“昆剧”“京剧”等;二是不使用脚色制,只用两三个演员的“小戏”;三是与巫术或宗教祭祀仪式相关的戏剧,如“傩”。他认为,“脚色制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故使用生、旦、净、末、丑的戏剧可谓最富有民族特色,而各种歌舞小戏及各种‘仪式性戏剧’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并没有太多特殊性”。当然除了脚色制,中国戏曲与世界其他民族戏剧形式相比,使用曲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套曲体音乐结构体制极富中国民族特色,是中国戏曲艺术本体特殊性的重要方面。
清代小戏的出现与发展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具体的小戏戏种应具体分析,本文只是从小戏使用明清间流行小曲曲牌,从“时调”具有流行腔调内涵上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很多问题有待深入。但对明清小戏的研究,应该考虑到乐籍制度解体后,职业、半职业艺人将承载的诸音声技艺形式更广泛面向社会传播的时代背景。明清小曲曲牌,各种腔调具有的“时调”意义对各地小戏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向大戏的过渡均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四、小曲雅化后参与明清散曲创作
散曲不同于戏曲。虽然散曲与剧曲同源,二者所用的曲牌、套曲的结构包括歌词有些也是相同的,但又因是否带有戏剧表演,因而在艺术本体上形成了明显的区分。对于散曲、剧曲与民间歌曲的相互关系,杨荫浏《史稿》指出,民间歌曲与和散曲的关系是间接而疏远的,其与杂剧的关系是直接而密切的。联系曲子创承机制,曲子可以直接进入戏曲创作,而曲子形成曲牌经过雅化后方被纳入散曲为用。散曲创作,包括清唱的形式尤为文人所重视,选用的曲子、曲牌一般是经过雅化的。明清时期也有文人把经雅化的小曲纳入散曲中的套数结构体制为用,介入小曲创作,同样以“琦语相高”,这也促使了小曲曲牌与填词的雅化。这其中,【西调】就是较为典型的这一类小曲曲牌。
“西调”是清初在山陕一带流行的时调、小曲,又称“西曲”。“西调”的流行应该与明末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有关。农民起义军走南闯北,自然把他们喜欢的这种曲调散播到各地。明末清初的张潮在《虞初新志》卷十一记载了陆次云的《圆圆传》,其中写到,李自成得到陈圆圆后:
“惊且喜,遽命歌,奏吴歈。自成蹙额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操阮筝击缶,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
李自成听到陈圆圆演唱的吴语歌曲觉得俗不可耐,命群姬唱“西调”并击掌和之,显然他更喜欢听来自家乡的音调。这是由地域性差异造成的审美趣味天壤之别。这种情况在中国音乐文化中是普遍现象,但同时也促进了传统音乐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
“西调”的音乐风格与我们今天听到秦腔中欢音、苦音两种特色音调所带有的音乐风格应该是一致的。欢音善于表现欢快、愉悦的情绪,苦音善于表现悲愤、凄凉的情绪。尤其是苦音,这种带有“中立音”(四分之三音)特定音律结构的音调能够撩人心弦,给人以“热耳酸心”之感。这种区域音调风格与中立音特殊的音律结构由山陕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所共同铸就。西调应该就带有这种区域特色音调的风格。
“西调”明末清初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形成时调意义,尽管朝代交替、时局动荡,但这首时调仍经过艺术化规范后形成小曲。清代“西调”在不断的创承、传播中,文人参与创制而雅化。至乾隆时,这种雅化【西调】广泛用于小曲、戏曲创作。此时成书的《霓裳续谱》,苏州钱德苍编选《缀白裘》中均有多首雅化意义的【西调】作品。如《霓裳续谱》卷三中的《春光明媚》:
“春光明媚,梁上衔泥燕子归。春回,杏花芳草游人醉,黄鹂枝上叫,青春再不回。风吹,香馥馥,颤巍巍,百花放,蝴蝶飞,一对对形影相随。管弦处处催,又只见王孙公子,花边柳边,喜孜孜畅饮金杯。(叠)魂飞梦飞,秋千院内佳人会。(叠)”
这首曲词清新雅致,用语考究,带有典型的文人风格。《霓裳续谱》中的【西调】多使用“杨柳”“雕栏”“梧桐”“归雁”“铁马”“玉漏”“幽篁”“画舫”“秋叶”“秋水”“待月”“露冷苍苔”“流水小桥”等带有特定含义意象的描写抒发离别情绪,显示出文人参与雅化创作的特点。这与《霓裳续谱》前成书的《万花小曲》,其后成书的《京都小曲抄》中的“西调”作品形成鲜明对比,这里较典型的显示出小曲这种音声技艺形态在创制、传承、传播过程中官方与民间两条脉络并行。《霓裳续谱》采集自乐户传唱的曲调,显示出制度下官方创承、传播一脉的意义。但民间也有其传承、传播的途径。
雅化后的【西调】还通过与其他曲牌连缀,附以尾声,形成套数,用于散曲创作。这代表了小曲曲牌及其曲牌连缀的“散曲化”倾向加深。但使用明清小曲的这些“套数”并不标注宫调,这与元明散曲创作中套数有明显的不同。可能的原因是,明清时期随着工尺七调宫调系统的普遍运用,小曲使用工尺七调中的哪种调(笛色)已经成为专业乐人所熟知的常识,而且工尺七调也能够根据演员嗓音情况在相邻指法调内临时调整,小曲不一定固定使用某一种调。这与唐宋时期曲牌归入某一宫调(有些曲子、曲牌可入数调)并联套后就基本保持不变形成了差异。
小曲雅化后进入结构体制复杂的戏曲创作是其依循曲子创承机制的必然路径。今人谢伯阳、凌景埏编《全清散曲》并没有把明清小曲、以及小曲参与创作的套数纳入其收录范畴。《全清散曲》收录的清代散曲作家创作的套数(北曲套数、南曲套数、南北合套)、小令还是以元明散曲为标准,这体现出编选者的标准和立场。无可否认,明清小曲的确在推动清代散曲创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给了当时文人选用曲牌更丰富的余地。
结语
明清小曲在明清两代戏曲创作中都发挥着特有作用,但小曲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体现的地位呈现出渐进式的发展特征。清代地方小戏中同样使用小曲曲牌,其中有一些地方小戏对小曲曲牌进行了板腔体改造。清代散曲创作已经开始使用新出的小曲曲牌连套。总之,小曲在明清戏曲创作中的延伸、发展是其依循曲子创承机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明清小曲的创制、传承与传播也因为参与明清戏曲创作而获得更充分的发展。
附言:本文系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从明清小曲探究曲子创承机制》部分内容,论文得到导师项阳先生悉心指导,在此致以深深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