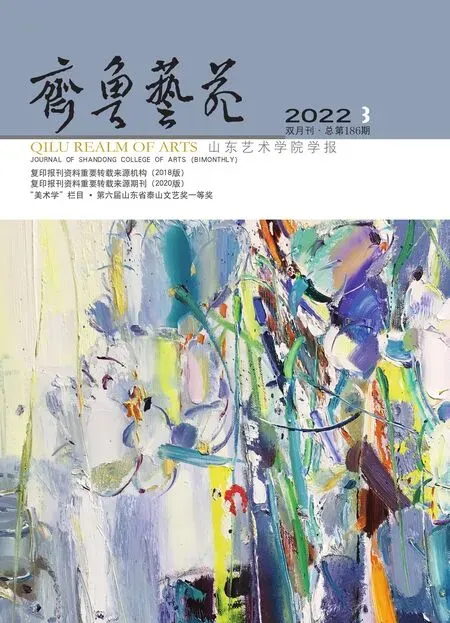游记文学中的蒙元音乐形象释读
陈 晶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辽宁 沈阳 110818)
引言
13世纪20至60年代,蒙古人横空出世,其三次西征的铁蹄势如破竹般蹂躏了中亚和东欧地区。在1240年马太·巴黎的一段文字中,将“新民族”的蒙古人作了详尽的描述:
“在这一年(1240年),一支可憎的撒旦人,也就是无数的鞑靼人马,从他们的群山环绕的家乡杀出,穿过(高加索)坚硬山岩,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Tartarus)……他们闪电般来到基督徒的国境,烧杀虏掠,无比恐怖和可怕地攻打一切人。……”
鞑靼人,是当时西方对蒙古人的称呼。因西方人视蒙古人“像魔鬼一样”,也就将“达达”(Tatar,当时东蒙古的著名部族)一名与古人对“地狱”(Tartare)之名称视为一体。
当时,以“蒙哥腾格里(长生天)”为最高神灵崇拜的蒙古人发动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大规模战争,使欧亚大陆各国兵戈扰攘、连天烽火。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蒙古西征对促进东西经济、交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蒙古西征,乃将昔日阻塞未通之道途,尽开辟之,而使一切民族种姓,聚首相见。”由此,凭借着宗教使命和商业冒险精神,各国传教士、使节、商人、旅行者纷至沓来,从而产生了大量以不同文本和语言对中国作记录的信件、游记等。13世纪,由两位传教士撰写的蒙古游记,即《蒙古史》(’)(中国学者习惯将其译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鲁布鲁克东行纪》()成为欧洲人对蒙古人最早的专门记述,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蒙古史的重要文献。
1271年,忽必烈即汗位,定都汗八里(今北京),蒙古人正式入主中原。此后,元朝历代统治者驰骋沙场、东征西讨,其疆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作为中国草原历史上的一座丰碑,中西交汇东鸣西应。被誉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意大利方济各教会会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65—1331,以下简称“鄂氏”)的《鄂多立克东游录》()和英国爵士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以下简称“曼氏”)所撰写这部被称为元亡明兴之时“关于东方最重要最有权威性的经典”的《曼德维尔游记》()作为中西文化认知沟通的历史见证,具有非可代之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这四本游记在为13至14世纪的西方国家描绘了陌生的、东方的、生动的图景中,也包含着相当部分的关于音乐的散在的、零碎的记述,它们有的如实、有的则是掠影,有的是亲历、有的是重塑,讲述着蒙古汗国与元朝时期的音乐历史与文化。毋庸置疑,这些记述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尤其是在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和蒙哥)统治时期的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为国内学者研究蒙古音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依据。同时,这也使彼时的西方人获得了对东方音乐最初与最基本的认知,并由此拉开了东乐西传的言说序幕。因此,这四本游记建构了东西音乐文化内容的双向交流与积累,成为异域对东方音乐文化探究的延展。
而在异域之视野中,其持有的特定的身份、目的与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共同合力又对其文本写作的视角、对象、修辞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蒙古汗国时期到访的柏氏与鲁氏的游记中更多聚焦于神秘而自然的蒙古民俗,以及质朴而热情的蒙古族传统民间歌舞音乐。而元朝时期拜访的鄂氏以及被冠以“座椅上的旅行家”的曼氏则不惜笔墨地渲染着具有煊赫地位的可汗,富可敌国的元王朝,以及充斥着管弦繁奏、歌舞俳优的奢华宫廷宴乐。由此,透过游记的文本,折射出的是蒙元音乐形象与音乐文化的历时性演进与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欧洲社会语境与游记作者身份复合结构的表征。因此,本文将通过游记中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与宫廷音乐等部分来探究13至14世纪西方人眼中的蒙古族音乐以及“多面”蒙元音乐文化形象塑造的深层缘由。
一、蒙元传统歌舞音乐与民间音乐的记述
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于1245年奉英诺森四世教皇之令,以六十五岁高龄出使蒙古。1253年,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自康士坦丁堡出发,携法兰西国王圣路易士九世的秘密信函赴蒙古。两位传教士奉命抵至蒙古汗国的时期,正值西方基督教国家惨遭神秘莫测的蒙古人重创而惶惶不安、束手无策之时。毫无疑问,两位的出使意欲了解与窥探蒙古人的动向、实力,通过厕身其中的游历而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向西方世界通报。由此,柏氏与鲁氏在游记中更加聚焦于蒙古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的陈述,这其中便包括对于蒙古族传统歌舞音乐的记录。
(一)蒙古族传统歌舞音乐
逐水草而居的诸游牧部落的蒙古人的歌声,历来是高遏行云且独步于一碧千里的草原的。音乐与歌唱在蒙古人的生活中从不会阙如,正如《蒙古行纪》中所述:“当他们有一两天断炊而水米不沾时,也完全不会显得愁苦不乐,而依然是歌唱和游戏,如同已经吃饱喝足一般。”甚至在挤奶时,都必须对奶牛唱歌,否则将无法进行。质言之,音乐与歌唱同呼吸,同笑一样成为蒙古人的天性,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
游记中还记录了迎宾舞、鼓掌欢跃舞等蒙古传统集体歌舞。依循蒙古人的风俗,每当帐外迎接贵客时,必唱祝酒歌,跳迎宾舞蹈,这便是“迎宾舞”。鲁氏一行人在遇到蒙哥汗的使者时,便受到了这种礼敬,“他们处处都给我们的向导唱歌、鼓掌”。根据鲁氏描述,这种“迎宾舞”的基本动作是“鼓掌、唱歌”,并且是热情好客的蒙古人经常演绎的集体歌舞,这从鲁氏的记述中便可佐证:“蒙哥的子民如此接待拔都的使臣,拔都的子民如此接待蒙哥的使臣。”
此外,在圣灵降临节第八天(1254年6月7日),蒙哥汗举行盛宴,邀所有使节到会。在这次宴会上,鲁氏看到:“所有人,贫富不分,都在汗面前又唱又跳,拍着手掌。”显而易见,这种舞蹈带有强烈的即兴性特征,且其舞蹈时的典型动作是“鼓掌、欢跃”。由此,鲁氏所见的应是蒙古族古老的自娱舞蹈——“鼓掌欢跃舞”。人们载歌载舞,并依歌击节,多在欢愉场合及喜庆宴会上表演,因以为名。
综上,柏氏与鲁氏在游记中记述了蒙古汗国时期,特别是蒙哥汗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传统而古老的舞蹈艺术。集体歌舞作为北方各民族发展最早的舞蹈形式,基本特点是步伐节奏一致,舞群的感觉和动作像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并且具有“歌舞不分离”的特点。这种传统的蒙古艺术形式始终伴随着蒙古人的生活,传承并发展至今。
(二)元代民间音乐
与柏氏与鲁氏不同的是,鄂多立克涉洋东至的时间是1322年,他眼中的“蛮子省”(指当时中国南方地区)有“两千大城,盛产面包、酒、米、各种鱼、各种人类使用的粮食”。无疑,鄂氏通过游记为遥远的西方国家建构了一个土地广阔、民物富庶而诱人的东方天堂。同时,鄂氏以不吝溢美之词地描摹了一幅“蛮子国贵人宴饮图”。
鄂氏行至“蛮子省”时,记述了一位达官显贵与音乐相伴的奢靡生活。他家里有一座“金银山”,其上筑有寺庙和钟楼,以及此类小型供娱乐之用的建筑物。他家有两英里大,家中的道路用金银砖交替铺成。鄂氏还描述了其饮噉醉饱的生活即景:“他要吃饭,坐上席桌时,菜肴是五盘接五盘地送上去”,并且,宴席由五十个少女侍奉,“唱着歌,奏着各种各样的乐器,把盘子捧入”,“把食物送进他嘴里,不断地在他面前唱歌,迄至盘碟光了。然后另五个少女捧上另五盘,唱着别的歌和奏着另外的各种乐器……就这样,他每日过活……。”毫无疑问,鄂氏张大其事地修饰了达官贵族荒淫奢靡的生活,也渲染出散落在民间以歌舞为业的歌伎乐工于席间表演歌舞以娱宾客的场景。
综上,游记们的记述从蒙古传统民族歌舞音乐至奢靡饮宴之乐,观察客体与语言修辞的转变,映射了13至14世纪西方人对蒙古人的了解、交流与认知从懵懂至深化的嬗变过程,而如果将游记文本置于一种更为广阔的且相互关联与交织的全球文化语境中加以研析,我们便可体察到,具象的文字所承载的是彼时东西交通的发达、东西贸易的加强以及元朝的崛起强大等颇为庞杂的历史互相作用的结果与呈现。同时,鄂氏对于江南地区音乐表演场景描写的修辞方式也隐喻了西方中世纪时期想象世界的图示。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实行政教合一,禁欲主义大行其道,基督徒们的生活中无不充斥着痛苦与无望。此时的欧洲人开始诉求一种可以摆乱和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乌托邦式的文化幻象。而富足且伟岸的东方帝国,成功地迎合了中世纪欧洲人的意念与幻象,成为他们心中可以改变逼仄的生活空间的理想国的楷模。鄂氏勾勒的这幅“蛮子国贵人宴饮图”是将现实与幻想合而为一的音乐场景,是中世纪时期西方唱响“中国赞歌”的缩微景观。
二、蒙元宫廷音乐的记述
“国朝大事,征伐、搜狩、宴飨三者而已”。宴飨,既是蒙古统治者挥霍享乐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汗权国威的昭示。而宴乐,是蒙古宫廷宴飨宾客时所用之乐。“拔都与鞑靼诸王在大庭广众宴饮之时,必有歌舞音乐相伴”,足见宴乐之蔚为风尚。
鲁氏以相关篇什记录了蒙古贵族的宴席歌舞。“在屋舍门前,总找得着忽迷思(即马奶酒),旁边站着个拿琴的乐人。我们有琵琶和提琴,在那里我却没有看见,但那里也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乐器。”文中提到的“琵琶”大约是中世纪时期欧洲的“琉特琴”。因“LUTE”一词也可译为中文的“琵琶”而被混淆,但应是“琉特琴”更为准确。
接下来,自由豪爽的蒙古贵族与歌舞旋律之间的脉动跃然纸上。
“当主人要饮酒时,一个仆人就大声喊道:‘赫!’于是琴手弹起琴来,同时他们举行盛会时,他们都拍着手,随琴声起舞,男人在主人前,女人在主妇前。主人喝醉了,这时仆人又如前一样大喝一声,琴手就停止弹琴。接着他们轮番把盏,有时他们放荡地和开怀地饮酒。他们要跟人赛酒,便抓住他的两只耳朵,拼命地要掰开他的喉咙,他们同时在他面前拍手跳舞。同样,当他们要为某人举行盛宴款待时,一人就拿着盛酒的酒杯,另两人分别站在他左右,这三人如此这般向那个被敬酒的人又唱又跳,他们都在他面前歌舞。他边喝酒,他们边唱歌拍手和踏足。”
在这段颇为传神的写照中,再次提到了“拍手”和“踏足”,由此可推断,这两个动作是蒙古古代舞蹈的最基本和典型的动作,并与鲁氏所“不知道的很多乐器”八音迭奏,以应“斗酒十千恣欢谑”之景。那么,鲁氏所“不知道的很多乐器”究竟有什么呢?我们只能根据已存史料窥见一斑,13世纪蒙古人在宴席之上常演奏的乐器包括“筝、琵琶、胡琴、火不思之类”。
另外,文中提到“当主人要饮酒时,一个仆人就大声喊道:‘赫!’于是琴手弹起琴来,……主人喝醉了,这时仆人又如前一样大喝一声,琴手就停止弹琴。”这一段描写的是“喝盏”,或作“唱盏”,是古代蒙古贵族的饮宴习俗。蒙古语曰为“月脱”,意为“进酒”,乃为承袭金代之时的旧俗。陶宗仪在《辍耕录·喝盏》便提到:“天子凡宴饗,……众乐皆作,然后进酒,诣上前,上饮毕,授觞,众乐皆止。别奏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鲁氏所述的这种歌、舞、乐并举之仪式,为“资料匮乏的蒙古贵族的喝盏表演仪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很显然,以上“歌舞相伴、拍手踏足”述写的是蒙古贵族随性的席间欢娱。一般地讲,蒙古贵族在宴饮娱乐时,有时也会亲自表演助兴。如鲁氏所见的“斯克台(拔都的亲戚)坐在他的卧榻上,手拿一把小琴,他的妻子坐在旁边。以及在撒里答(拔都之子)的斡耳朵(Ordo,蒙古语意为“皇家幕帐”或“宫廷”)里,鲁氏一行人站在他面前,他威风凛凛地坐着,弹着琴,叫人在他前面歌舞。
游记中并未以纤悉无遗的笔调罗致贵由汗与蒙哥汗的宫廷音乐。那么,是柏氏与鲁氏无缘大汗宴飨吗?据柏氏与鲁氏的两本游记所载,拔都在幕帐内曾亲自接见柏氏,并同席欣赏宴乐;在贵由的“金斡耳朵”,即金帐内参加贵由汗的登基大典仪式。而鲁氏也有幸多次与蒙哥汗在宫廷中会面。因此,两位是有机会耳闻目览蒙古宫廷音乐的。但是,从以上的见闻记录来讲,并未提供更多更详尽的内容。究其原因,正是蒙古汗国时期,由草原游牧文化类型过渡到游牧封建类型的体现。其宫廷音乐尚保留着部落时代的痕迹,其形式也比较简单,尚未系统化。因此,蒙古汗国时期的宫廷音乐尚处于逐步完善、次第兴起的阶段。
而在鄂氏与曼氏的游记记述中,“大汗有13万个乐工,15万个优人、幻人……”。这是烘托渲染的元代宫廷乐师、俳优与精通百戏幻术乐工的数量,也成为由蒙古汗国时期的突卫军“忽儿赤”体制向乐舞艺人体制转变的历史例证。并且,元代设有专司礼乐的官员,并由礼部负责管辖。
鄂氏提到,大汗在登基之日、诞辰日、大婚之日以及长子生日这四大节日之时都会在宫中大摆筵席,共襄盛举。在盛宴上,必会“召诸王、俳优及他的亲属都去参加这些节日盛会,所有这些人在节日盛会上均有他们固定的位子。”而且,“很多官员辛勤地注意有无诸王或乐人缺席,因为缺席者本人要受到严厉惩罚。”由此,列优伶、赏歌舞等是元代宫廷大宴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形成严格的典章制度。
在曼氏笔下,一幅神奇斑斓的宫廷盛宴大幕徐徐拉开:
“宫殿的厅堂布置豪华高贵,所有装饰让人惊叹不己。首先,最上头摆着高高的宝座,正好在宴席桌旁。这个宝座由宝石和珍珠做成,而登上宝座的台阶用各式宝石铺就,镶以金边。大汗的宝座左边是大汗的第一个妻子的宝座……大汗的右边坐的首先是他的长子,将来会继承大汗的王位……大汗的桌子下边坐着四个书记官,负责记下大汗所说的每一句话……。”
元代宫廷大宴典制之一便是列珍禽异兽,“在盛大的宴席上,在大汗的桌子前有金孔雀及其他不同种类的家禽。这些都是金制的,并被刻上名字。人们用它们来唱歌跳舞,一起击打它们的翅膀,发出很大的声音……。”并且还有“伶人带着狮子向君王致敬礼。”
曼氏接着发酵,“诸侯及大臣们站在大汗的桌子前,伺候大汗用餐。如果大汗不对他们说话便没有人敢开口说话,只有乐工们唱歌。”“在大厅门口站着许多全副武装的卫士,没有大汗的命令,任何人不可进入大厅,但大汗的仆人与乐工除外。”
除此之外,鄂氏以细致入微的笔锋陈述了庆祝大汗生日的豆觞之会。首先,赴宴者必须着皇帝所赐的一种特制样式的礼服,名曰“只孙宴服”。凡上至勋戚大臣、下至乐工卫士,均有只孙服的赐予。
“当应召参加这种盛会,诸王都戴着冠冕到来时,皇帝则如前述坐在御位上,诸王按顺序排列在指定之地。这时,诸王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在头一排的一些人,穿绿绸;第二排穿深红;第三排穿黄。这些人均头戴冠,各自手执一白象牙牌,腰束宽半拃的金带。”“所有的衣服都那么高贵,那么珠光宝气,镶嵌着黄金、宝石、珍珠。”
然后,
“诸王一千人一组,分四组依次进入。每个人都拿着一块由玉、象牙或水晶制成的书板。宫廷乐师们走在他们前面,一边弹奏乐器一边放声高歌。”“第一个千人仪仗结集行进,队列整齐,接下来第二个千人仪仗同样如此……。”
当行进仪式结束后,诸位鸦雀无声地站立。“他们四周是执旗、徽的乐人。”落座在大汗的桌子旁的是很多哲人,如占星者、巫师等。到了一定吉时良辰,一位哲人向全体宣布:“每个人都必须尊敬服从大汗。他是上苍之子,是世界的领主。接着吉时到,每个人都跪下叩头……。”“当仪式结束后,乐工们继续表演,旋律此起彼伏。”演奏一段时间后,“一名官员起身站到舞台上面,高声宣布:‘肃静’。然后,在座的王公贵族开始向大汗进献象征尊贵的白马作为礼物。典礼完毕,乐声再度奏响,一些男歌手来到大汗的面前,也有些女歌手,她们唱得如此美妙,使人很爱听,而这是我(鄂氏)最爱的”。
“玉堂盛宴,歌妓罗列”,据《元史·礼乐志》所载,元代宫廷乐师队伍包括乐正、乐师、舞师、执旌、执纛、执麾、舞人、执器等人组成,正应鄂氏所述宫廷四周站满“执旗、徽的乐人。”在陈述中,虽未详尽乐工人数与所奏乐器,但据《元史·礼乐志》所载,至元七年,乐工共三百二十四人,乐工所习乐器有大乐鼓、板杖鼓、筚篥、琵琶、筝等七种乐器,演奏乐器的乐工共七队,总数为四百人。单就乐工人数已达七百二十四人之多,那么据此可以想像,整个乐舞队的人数将数以千计。由此,游记描述“大汗饮宴,众乐皆作,乐器无数。”而且,鄂氏讲“他们演奏的各种乐器,其音乐和歌舞的吵闹声足以把你震聋。”那么,正应史书所稽,蒙古音乐皆“宏大雄厉”,乃“一代兴王之象”。
除歌舞之外,宫廷宴饮还伴有百戏、幻术及诙谐幽默表演。“魔术师把盛满美酒的金杯飞过空中,送到愿喝者的嘴上。”而曼氏则继续他颇具戏剧化的描述:
“变戏法的和魔法师创造了许多奇迹。他们从天而降,带来一片光明,好像太阳、月亮照着了每个人。然后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接着又是白昼,太阳令人愉快地照耀着。他们又带来世界上最美丽的少女跳舞。……还有许多其他奇异的东西均出自他们的魔法,令人惊叹不己!”
此外,大汗用餐之时,“俳优说笑话或做其他表演,慰藉圣驾。”“食毕撤席,有无数幻人艺人来到殿中,向大汗及其他列席之人献计,其技之巧,足使众人欢笑”。游记描述恰与《多桑蒙古史》所载,宫廷盛宴中“命优人、幻人、技人入献艺于帝前”相佐证。
如上所述,鄂氏与曼氏记述了大汗宫廷宴乐,玉箫金管、歌舞交织、幻术俳优,这一切体现了蒙古草原游牧音乐文化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由简入繁、循序渐进,步入鼎盛时期的历史记忆。而同时,两本游记将流光溢彩而极其奢华的大汗盛宴,如梦如幻的歌舞俳优表演等这些极尽物质化的描述与想象杂糅,实际上塑造了一个中世纪西方文化创造的一种“西方的中国宫廷音乐”,特别是曼氏在既定的文学框架中,通过丰富的想像力与夸张的修辞为西方人营造了一片人间乐土的画面。而这幅人间美景也正是中世纪时期欧洲人利用与借助他者的形象所体现出的自我欲望与期待,体现着西方集体想象与渴望中的超越黑暗而压抑的中世纪现实社会的理想社会。曼氏采用历史与虚构、真实与想象的语言修辞方式建构出“自我”与“他者”的形象。质言之,游记中的宫廷音乐作为一种载体与介质,其实质更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中世纪时期西方社会充满着想象的意识形态与权力运作的方式。
结语
13世纪的东方帝国——蒙古,对于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讲,是一本尚未翻开的巨著。而对于这本充斥着诡秘莫测、雄韬伟略的著述,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通过亲身游历为西方世界构建了蒙古高原上的鸿篇巨制的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索引。在这份索引目录中,既包含蒙古的战争武器、风俗习惯,也囊括了音乐文化。而柏氏以简练的笔法与清晰的轮廓将叙述的重点放置于蒙古人的传统歌舞音乐,鲁氏则擅用细致入微且绘声绘形的笔触聚焦于与蒙哥汗相关联的宫廷音乐,这些记录应该是最原始的,也有可能是唯一的史料了。
两本游记虽非真正意义上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但身负着窥探蒙古人动向的重要历史使命的柏氏与鲁氏还是以比较审慎的态度,将蒙古传统音乐与文化带回了西方,从这个角度来讲,两位应是促成东西音乐文化双向交流的第一批使者。同时,两位以“西方视域”来记述蒙古游记,在一定程度上为东方音乐文化的西方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创造了整个西方世界体认蒙古音乐乃至整个东方音乐的开端。由此,柏氏与鲁氏的游记是地理大发现以前,西方认知蒙古与东方音乐的最重要的参考书目之一。
此外,作为旅行者亲身经历的以语言文字为构筑手段的游记,在记录了空间与地理位移的同时,也隐喻了作者内心的精神位移的感知。并且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当时,蒙古人的急遽扩张使欧洲四海不靖,跼蹐不安。在当时的西方,蒙古人被称为“穷凶极恶”的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为摸清这股使人迷乱惶惑的可怕力量,在强大信仰力量的驱动下,柏氏与鲁氏鞭长驾远、穿荆度棘“进入异族的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作者脑中挥之不去的恐惧,使其实现了发现蒙古音乐文化到“发明”蒙古音乐文化的过程,即将西征背景中真实的蒙古人与欧洲视角中想像与虚构的蒙古音乐文化在游记中被结合、描摹,而其文字折射出的却恰是创造者的文化身份与文化价值观。
1279年忽必烈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遂下江南。这个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国度进一步激发了西方探索与想象的源泉,鄂多立克从个人体验角度出发,曼德维尔在既定文字框架中重塑,将“他者视阈”中的“天外版舆”的音乐文化展开了历时性记述。作为清苦的托钵僧,鄂多立克略带夸张的手法记叙了元朝的达官显贵的音乐场景。而曼德维尔采用更为娴熟的文学技巧,将虚构与现实巧妙结合,展开了一段奇异的精神漫游,将元代宫廷盛宴的珠围翠绕、歌台舞榭描摹的尽致淋漓。而在游记中,东方音乐大多是伴随着“神秘而富庶的中国形象”孕育衍生的。元朝大汗“在十字架前礼敬地脱掉那顶用珍珠和宝石制成的,比特利维索边区(位于意大利)还值钱的帽子”、大汗的“宫殿的厅堂布置豪华高贵,所有装饰让人惊叹不己。”鄂氏行至江南地区时,见一富人家“有一座金银山,他家有两英里大,家中的道路用金银砖交替铺成。”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视野中,中国一直是这样神话般的存在,游记作者大多在离奇的想象中将中国虚构成奇异的人间乐土。而这片迢遥的“奇异的乐土”则是西方在发现和认识东方过程中所赋予和创造的。中世纪时期,欧洲的落魄与混乱,使欧洲人迫切需求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从而获取一种逾越基督教文化困境的发蒙。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言:“西方希冀寻求原始社会来批评自己的社会。”因此,中国神话的幻想之门便被开启,这块“令人难以置信的、富庶的、神奇而又魔幻的土地”在唤醒了中世纪晚期西方世俗欲望与理念的同时,使其变成槁苏暍醒的文明发生的动因。而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东方音乐便从他者视域的文化视角,以被欣赏和赞誉的态度在游记文学中作地理空间的位移。正如汉学家孙越生讲言,西方在“十八世纪以前对中国的研究,是以好奇和赞美的心情为主要特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