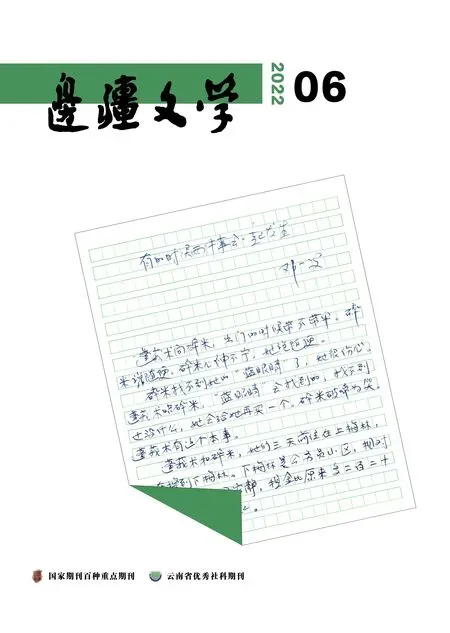底层、荒诞和写意
—— 我读2021 年《边疆文学》 『边疆开篇』中的小说
王 皓
2021年《边疆文学》“边疆开篇”栏目刊登了众多优秀中短篇小说,包括吕翼《穿水靴的马》、蒋在《等风来》、赵雨《流逝》、李浩《灶王上天见玉皇》、夏天敏《唢呐声近》等,它们所写的题材和表达的主旨各不相同,观察的视角不一,从底层农民的生存状况到当代人的精神剖析,均各有发现。本文从底层叙事、荒诞叙事以及写意叙事三个视角切入,试图分析潜藏在小说背后的审美特质。
一、底层叙事
“底层”这一概念在词典中解释为喻指社会、组织的最低阶层。关于“底层文学”的概念,学者李云雷认为它是“在内容上,它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形式上,它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在写作态度上,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但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他的观点普遍为学界所认同,可以说“底层文学”是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经验的文学作品,聚焦底层阶级的穷困和无助状态,揭示其艰难的生活现状以及底层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家主要呈现底层人民的生活日常和情感体验,以农村或城乡为背景,多以农民、城镇底层为对象,关注底层生活困境,展现出平凡个体为了改变困窘的现实处境而付出的努力。底层写作力图将底层的真相作最原生态的展示。这种创作意图就使得底层文学作品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写实的叙事风格,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往往采用现实时空形式和情节的紧密、场景的逼真、细节的真实、人物形象的丰满等现实叙事方式,流露出作家较强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意识。
例如海桀的《肠香无二》(《边疆文学》2021年第4期)从底层叙事中关注民生,从一种道德主义出发,揭露市场经济时期新旧两代食品经营者之间的观念冲突,批判新一代经营者为了“金钱至上”而砸坏传统摘牌的苟利行为;又如秦羽墨的《去明月寺练练枪法》(《边疆文学》2021年第5期)则对小镇里基层乡村官场丑态进行揭露,刻画了游手好闲的底层人物庄聪明与民警发生矛盾被扣押车具后进行暴力反抗而双双殒命的惨状。
吕翼的《穿水靴的马》(《边疆文学》2021年第1期)更是典型的底层叙事,讲述了易地搬迁背景下农民陇启贵从农村搬进城里新房而引发一系列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陇启贵作为新时代的农民和被脱贫对象,生活在基础设施落后的野草坪,住在破败不堪的茅草房,不通电,不通水,交通不便。然而政府实施易地搬迁工程,为贫困山区人民在山下修筑起幸福家园小区,这让陇启贵对新生活开始有了期望与向往,他牵着心爱的马“幺哥”想要上高速去参观新家园,经过一番周转终于来到小区。但小区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拒绝牲畜进入,他却不顾阻拦暗自牵着马进入小区,为了让马方便上楼,还将撕成四块棉布褂子把幺哥的蹄子包了起来,防止马蹄在瓷砖地面上打滑;为了躲避管理员他甚至让马坐电梯,结果马却突然在电梯里大小便,瞬时弥漫着冲鼻的腥臭,狼狈不堪。最后陇启贵只得在物业监督下将电梯打扫干净,并牵着马悻悻而归。
小说以喜剧的手法刻画了陇启贵这一漫画式的农民形象,再现了农村易地搬迁过程中,农民对新管理制度的疑惑不解和新旧生活方式的矛盾冲突。农民在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也面临种种困扰和落后传统残留的难题,外在的局限和自身根深蒂固的愚昧落后观点,依然顽固地潜伏在他们的意识深处,阻碍了他们摆脱物质贫困和精神愚昧的步伐,新的农村政策与过去的落后生活方式造成其认知的差异,也便由此生发出一场荒唐的闹剧。新时代的农民依然难以跨越和绕过这种城乡差异冲突对他们的有形和无形的钳制,作者敏锐发现了农民遇到的新的困扰,以主动介入的姿态,并采取一种“民间立场”,在对农民书写中实现对底层民生问题的关照与人文关怀。
不同于《穿水靴的马》的喜剧气氛,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唢呐声近》(《边疆文学》2021年第10期)却是聚焦底层农民的苦难生活,展现了作家一以贯之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悲剧色彩。作者以悲凉的笔触写下乌蒙高原山区一支支哀婉深沉的歌,他的笔尖流淌的都是乌蒙高原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苦画面,集中呈现了夏天敏底层写作的“苦难”主题,揭示了乡村农民的艰难生存状态和畸形的生命态度。
小说描写了贫苦山区云山老汉的悲苦人生,他的儿子顺来在一次矿厂事故中导致瘫痪,丧失自主行动能力,照顾他成了云山老汉多年来的职责,父子俩在清贫中艰难维生。然而老汉一辈子省吃俭用,贫困使他遭受歧视与侮辱,生前的不幸使他只想在死后有一口好棺材,扬眉吐气一番,“严酷的生活使他们对另一个世界充满幻想,一口好的棺木几乎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念想”(《边疆文学》10期第7页)。但老汉的钱只够买一副棺材,他不忍心死在儿子之前怕无人照顾,“棺材”又是他心中的一个症结,于是便上演了“活人出大丧”“花钱雇孝子哭丧”等“可笑”又“可悲”的闹剧。老汉对棺材的盲目欲望,致使其在生前潦倒狼狈,“这些苦难,并非仅仅来源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或颓败的现实秩序,而是更多地来自人性的崩落以及欲望的疯狂增殖。也就是说,这些苦难,在很多时候是由于人们自身的某些欲望所催发出来的,并非是一种不可超越的现实不幸。”云山老汉对贫苦现实生活的无奈以及不合理的欲望观和生活观,致使他陷入为自尊将毕生心血投掷在“棺材”的漩涡之中。作者在正视这些底层苦难的背后,剖析了隐藏在苦难之下所蕴含的复杂人性,从而引发对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其精神困境的深刻反思,并表达对乡村社会生存环境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展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通过对农村贫困落后的揭露,对农民群体苦难处境的展示,旨在呼吁社会对农村、农民群体的关注与理解。
一些评论家在讨论“底层写作”时,特别强调要“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后两位作者都深耕于乌蒙大地,用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片土地中的底层小人物,对他们投以人道主义的目光,描绘社会历史浪潮中地处偏远的乡村底层,呈现出中国乡村一隅的真实图景,揭露无法逃离乡土的小人物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生存挣扎。作家吕翼更加注重新时代的变化与落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作家夏天敏笔下的农民似乎仍旧锁闭在一个相对停滞的落后社会,少有外界力量的介入,更深究农民自身的困境。
二、荒诞叙事
文学意义上的“荒诞”最初被予正式命名是源于上世纪兴起于法国的反传统戏剧流派的概括,随着中西方文学的交流融通,西方文艺思潮涌入中国,西方的荒诞叙事的热潮开始在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其时产生了一批“荒诞文学”它们通过荒诞性的叙事手法,虚构事物和情节,背离现实,从某种主观感受出发来改变客观事物的形态和属性并深入现象的深处,揭示事物的本质。荒诞叙事技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采取内容层面和形式层面的荒诞形式来解构真实,或以非常态的外在语言形式的叙述产生一种荒诞的效果。
例如朝潮《好像在哪见过你》(《边疆文学》
2021年第6期),讲述了“我”因梦而寻一个名叫“大唐”的地方,却在途中认识令人可疑的樊先生,并由此生发寻找兄弟的想法,在一切谜团均为解开之时,樊先生却消失得无影踪,致使故事扑朔迷离,荒诞离奇。又或窦红宇的《春声醉》(《边疆文学》2021年第9期)则以幽默的笔调讲述了一对陌生男女频频相遇而发生的一些趣事,然而故事末尾却笔锋一转,以女人的离奇死亡将小说引向荒诞的暗门,叩响了男主人内心的疑惑与伤痛,无从以正常的因果逻辑追寻女人为爱而死的动机,故事在男主人公混乱离奇极尽崩溃的荒诞精神世界中戛然而止。
索南才让的短篇小说《葬身》(《边疆文学》2021年第12期)则更是一篇运用荒诞叙事的离奇怪诞小说主人公阿音木在遭遇一次意外雷劈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醒来后的他目光呆滞、眼神涣散,且开始做起了连续的怪异的梦,在荒诞的梦境中他预见了他人的死亡,且一步步成为现实,“他仿佛一个高明的杀手,无声无息置人于死地。梦就像准备过程,等梦做完了也就完成杀人任务了。”(《边疆文学》第12期第7页)这致使他产生了自己用梦境杀死他人的负罪感,在连续梦见好友桑德和心爱的女人死亡后,他在神经质的绝望中又梦到父亲,于是在不堪精神的重负下走向崩溃。小说撇开故事的合理情节与时空的均衡性,解构了传统小说中时间、地点、人物与环境等遵循逻辑的叙事要素,注重展示的是一种潜意识状态下的主观感觉、复杂情绪和抽象意念。用梦境杀人是一种打破常规的荒诞叙事手法,这往往产生一种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对立甚至偏离生活现实的“陌生化”效果,使主人公偏离传统叙事因果逻辑而堕入混沌的梦魇之中。怪诞的情节走向致使主人公陷入非理性的混乱世界,揭露了人不可知命运的残酷性。其次在结构和意旨上小说不具备合理的逻辑剪裁与秩序,甚至读不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与中心思想,人物也没有完整的性格指向。但这其中有关生命、死亡的思考,或许体现出一种虚空意识,一切都是梦魇无法穷尽和明确,没有规律可循,无法言说,带有玄妙的色彩。在充满荒诞色彩的情节、场景和结构中传达的人对于命运无可把握的一种无奈,从潜意识层面揭露人的生存本相,表现出作者对人存在状态的深切质疑与关照。
李浩《灶王上天见玉皇》(《边疆文学》2021年第6期)更是采取了一种“非常态”的荒诞视角,不同的是荒诞背后却暗示一种现实真实。文中是以一个曹府灶王的身份进行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描绘了他上天宫与各神仙共赴宴的荒诞奇崛体验。作为玉皇大帝百叟宴的观礼群仙代表,灶王来到仙气缭绕、威严庄重的天宫,然而天庭也有繁复的手续,经过重重关卡审查,终于到达仙驿馆休息,在正式晚宴前各神仙需每天学习各项天庭礼仪并模拟演习。在百叟宴当日,众仙齐聚一堂,场面盛大宏伟,但灶王谨遵天庭礼仪,不敢动几下筷子,最后饿着肚皮而归。荒诞的艺术实则敲开现实的大门,这种“非常态”视角的运用在审美格调上增添了感染力的同时也影射出人间的行活实况。看似荒诞的神界世界,实则却有着凡间的影子,不同时空呈示的奇异的天庭景观引领读者走进了现实迷宫,思考现实世界与虚拟神界世界的联系,在对照中唤醒其对现实的敏感。作家采取“灶王”这一非常态化身份描绘华丽庄严的仙界空间里的所见所闻所想,别具匠心地揭露在常态视阈中难以发现一些社会问题的“变异”和“疯狂”,以隐喻和反讽表达对一些官场形式主义的拒斥,在荒诞叙事中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反思。
这几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有荒诞叙事的倾向,有的是在一种草原牧歌式的语言中刻画情节和故事的荒诞性,以揭露人的命运的虚无;有的则是采取外在荒诞的壳子,以现实为摹本建立起的却是一个高于现实、具有魔法感的世界,具有现代哲学意义的追求,共同体现了作家们非凡的想象力与荒诞叙事能力,为《边疆文学》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三、写意叙事
传统的写实小说的中心任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重结构的完整,强调情节的跌宕起伏,和表述故事的前因后果。而写意小说并不以刻画人物性格为目的,它们减弱情节,结构不紧密,着重营造一种氛围、传达一种心绪,有别于写实写作的艺术构思。因此写意性的叙事不遵循传统叙事原则,不以塑造人物为中心,人物往往成了一种载体;淡化小说的故事情节,注重小说意象、与意境的创造,以空间为小说的结构核心等特点。写意叙事多借用意象、隐喻与象征等手法,“这些新的诗性方式改变了以往小说重在反映现实,再现现实的‘写实’的美学向度,而使小说出现了重在暗示、重在象征、重在形而上理念、形而上寓意的‘写意’的美学向度”
蒋在的中篇小说《等风来》(《边疆文学》第2期)也有写意叙事的倾向作者并没有通过连续的情节来讲述完整的故事,而是采用一种缀段性的情节组成,(所谓缀段性情节是指前后无因果关系而串接成的情节)插叙手法的介入使事件失去了时间的因果的链条。作者片段式地截取小女孩的生活场景,用插叙的方式追忆小女孩曾经与爸妈的温馨时光,与当下令人心酸的生活经历形成对比。其次,作者无意去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而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展现了一个处在孤独无依寂寞状况中的小女孩“她”的悲惨生存境况:她的父亲消失,母亲也在一次意外后在医院长眠不醒最后被拔掉氧气管,然而家里的两个表哥却也经常打骂她欺负她,善良的喜来帮助过她,愿意和她交流和玩耍,但命运却将他弱小的生命吞噬,女孩和哥哥们目睹了他的溺水过程却并未施救而是跑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似乎呈现一种以符号为意象的诗性方式,运用隐喻性的象征意象,小说围绕“风筝”这一意象符号,以它为叙事线索,牵引制约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展现小女孩回不去的温暖空间。每次它的出现,小女孩都置身在从前的快乐时光,它成了连接父母亲的物件,风筝成了她过去美好生活的一种印记,寄托着她对父母的思念,象征着女孩的期待与希望,“她把风筝放在腿上,静静地等待着,她相信等风来了,她的风筝就能飞起来,她的爸爸就能回来”(《边疆文学》第2期第19页)。在文末,她等来了风,将风筝放飞,她自己似乎也要飘起来了,在这一隐喻建构中完成了一个孤苦无依的留守儿童的凄惨人生的关照。
赵雨的短篇小说《流逝》(《边疆文学》第8期)则是采用一种写意的空间叙事,文中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多年以来一直独自生活在寂寞的屋子里,不与人来往,她将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困囿于社会边缘,独自留守。期间因为修缮房子与装修经理暗生情愫,多年未出门的她竟与男人一同前往丈夫的墓地,从“家”这一空间到“墓地”空间的置换是母亲封锁多年的一种心理突破。不料经理的妻子却找上门来对她大打出手,在狼狈中母亲又重新退守回自己灰暗的封闭空间。母亲自此成了区域拆迁钉子户,在刘主任的劝说中从那个“家”逃离多年的“我”又回去,再一次打破母亲的封闭空间。其间追述了曾经的家庭状况以及父亲去世的原因:母亲的尖酸刻薄和阴冷性情致使父亲逃离,他成为一名海员,但在意外中卷入海底丧生。他的日记冷酷记载了他的未来规划中并没有母子二人。但母亲并不知晓,而是一直坚守在家祭奠沉缅父亲。父亲本应是传统家庭秩序的轴心,对家庭关系的建构和走向具有引领作用,但他的逝世对母亲造成巨大精神打击,使家庭不再完整。母亲坚守的阴冷灰暗的家的文本空间实则影射现代都市破碎家庭的精神困境,展示了家庭的扭曲异化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失衡。家不再是亲人之间心灵相互依靠和抚慰的港湾,反而成了令人心痛和焦虑的地方,致使“我”和父亲的逃离,最后导致家园的失落,情感的分崩离析。
文中出现了“座钟”这一巧妙的意象,暗含时间的流逝与停滞,开篇便出现这一意象“上足发条,几十年来,它从未走快或走慢一次,在这么一面圆盘上,时间被不断刻制、重复,指针划出一块独立天地,和外面的世界全然无关”(《边疆文学》第8期第4页)。文本中时钟里的时间不仅是一种物理时间,可以计量和划分,是流动的,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纯粹时间,它显示出母亲个体的无奈与虚空,与外在时空的疏离,永远处于一种恒常不变的状态。直至一天母亲将其砸坏,时间的停滞使她黯然的内心支离破碎,她在时间中固守和回忆,又在时间中悄然消逝。她请求“我”将座钟修好,是想对往日时光的一种修复和期盼,这一意象意承载了母亲的创伤与期望。
两篇小说都属于家庭题材,并在语言和叙事上有写意的倾向,都带有一种悲剧色彩。“孤独”这一主题贯穿文本。《等风来》中的小女孩有着理想世界的美好期待和对落空的残酷现实世界的迷茫,让小说在深沉悲凉的意蕴中追问“她”的何去何从,显示作者对留守儿童的关爱之情。《流逝》则更侧重探讨当代家庭关系的建构,以诗化的语言和写意的叙事,描述了家庭关系的裂痕化,和家庭创伤下的精神危机。
以上所选取2021年《边疆文学》“边疆开篇”栏目中的几篇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都有各自独特的叙事特色,作家吕翼和夏天敏的底层叙事贴近人民,语言真实洗练而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书写农民这一群体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与关怀;作家索南才让和赵雨的小说则以荒诞叙事手法深入生活深处,揭示真实表层之下另一种生命真相,传达对生命和社会的复杂思考;以及作家蒋在和赵雨的小说则有写意叙事的倾向,他们用诗意的笔尖切入家庭内部,关注个体生命的孤独与无助。纵观以上文章,无论是现实主义倾向的底层叙事,还是现代主义的荒诞叙事,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写意叙事的这些小说都体现了《边疆文学》刊物的一种开放性、兼容性和思想性。《边疆文学》从办刊以来就坚守着纯文学刊物的神圣品位,坚持“边疆作家高地、民族文学家园”的办刊宗旨,显示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彰显独特地域人文精神,扎根中国大地的文化血脉,造就文学创作的千姿百态。它关注高原写作、民族写作、大地写作,诸如夏天敏、吕翼、索南才让等一批作家扎根自己脚下的土地,从高原出发,书写大地之歌,吟诵民族之曲。但《边疆文学》也广纳全国各地优秀作家作品,所刊文章无论是内容题材、文笔文风、叙事视角等方面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涌现许多有新意、有创见、有新格局和新视野的优秀文章。它提供给广大人民一个广阔的展示舞台,无论是文坛新秀或者资深作家,都能在这里绽放文学之光,产生思想碰撞,他们敏锐的发现力将复杂世相诉诸笔端,以独立的精神创造倾注对人类的关怀和至上的美善。作为《边疆文学》的忠实读者,每每翻开杂志都觉得“开卷有益”,且在“润物细无声”中收获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