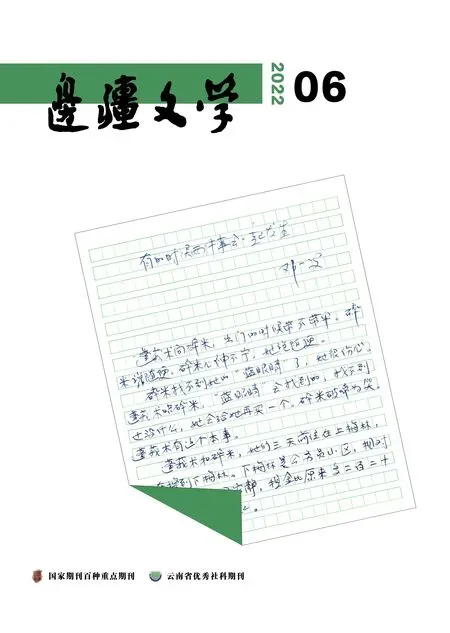一生中需要忘记或无法忘记的 组诗
罗杞而
她还是小孩
一个两三岁的女孩,突然离开母亲视线
从临街商铺中溜出来
蹲在街道上玩耍。她的身边是来来往往的车辆
她还小,不知道危险临近
她在欢天喜地
她以为她面对的,都是玩具或海绵
她以为她置身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她还小,
还不知道这个世界规则、秩序无处不在
她更不知道,如果她侥幸逃过一劫
她的一生将要经历
风雨、疾病、爱恨情仇的困扰,直到死去
一生中无法忘记的
20年后重回故地,睡在破败的老屋中
与幼年的自己在梦中僵持,对峙,谁也不妥协
他已经认出现在的他
他攥紧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响
冲那张疲态尽显的中年面孔——咆哮
然后,俯身捡起一块石头,狠狠砸向那个人
最后,他哭着跑了
——看得出,他失望至极,愤怒至极
——他已经把那个人当作最大的敌人
——如有可能,他一定会杀死那个人
而我面对他,竟说不出话,也不敢还手
只能怔怔地目送他远去
迎着风,任由泪水滑落
我害怕再次在梦中碰到他,于是匆匆返城
下了客车,我沿着通商南路往东走
此刻,我看见一个离开土地多年的老人
正佝偻着身子,用力从垃圾桶中扯出一根锈铁
装入麻布口袋
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他是谁?他就是我喊了大半辈子
都没有喊出口的父亲
直到父亲去世一年后,我终于鼓足勇气
一个人偷偷跑到他的坟前
见四下无人,悲怆地喊出那两个久违的字
幸福里酒吧
从她的语气和表情中,我能明显感觉到
她在试图回避,那个充满距离感的词汇
但她在说出替代称谓后,又意识到不妥
才不得不把那个词汇,从舌根下挤出来
“那个人。哦…领…导,他顾左右而言
无非暗示,就像落日暗示黑夜即将来临”
是的,她即将被解雇。详称甲方解除
乙方劳务合同。要知道
在来这个单位之前,她已经奔波半生
阳光真好。这是悠远的黄昏
我们在幸福里酒吧
喝到胸中涌起潮水,她忽然停下杯子
我以为她要说活着不易
没想到她抬起右手指着窗外
“你看太阳即将沉没
那只掠过幸福里上空的鸟儿
多幸福!天空才是它的极限”
我循着她的指向望去,只见天空正在辽阔
祭语风中
再远,也必须回去,即便你变成厉鬼
也是我祖宗
经历太多,早已不再指望你来保佑
活着时,你在茫茫人海中找我
你死了,我又跋山涉水去找你
草太深,荆棘太多,坟越来越多
辨识度越来越低
为了找到你,我只有读碑
其中一碑上,刻着周某某之墓
他生前作恶多端,是你的仇人
我又读另一块碑,他活着时呼风唤雨
哦,终于找到你了
我无声读着
那些按长幼尊卑排下来的一串名字
他们一个个相继离去了
有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排在最后的那个,是我
如今也人到中年——这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
风呼呼吹着。似乎只能呼呼吹着
似乎只能迎着风,一个人呆站着
送流水
一个人面对小黑江滔滔流水,竟会偷偷流泪
流过之后,回到人海,假装若无其事
面对普贤寺,不哭。里面藏经阁中
贝叶经多么安静
众僧早已看破红尘,眼泪进不去
流水覆盖了鱼群、河床
覆盖了溺亡者的冤魂,和许多看不见的存在
这对抗之后的沉默
我看不见,我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真相大白
全都来自经验和推理
涛声依旧,夕阳下风烟俱尽
目送流水远去,我一次次穿上回忆和风沙
卖狗记
1984年,秋,父亲拖着白狗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
白狗一路抵抗,父亲一路拉扯
那是白狗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挣脱村长的锁链逃回家
那是父亲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亲自将白狗押送买主
到村公所,村长将白狗吊树上,挥动木棍
白狗哀嚎一声,我跟着叫一声
白狗又哀嚎一声
我又跟着叫一声
有那么一瞬,白狗望向我,眼里泛着泪光
朝我艰难地晃了晃尾巴
就在那天下午,白狗被村长一伙吃了
父亲也如愿拿到十三块钱
第二天,父亲给我交完欠小学校的学费
跨过栅栏的一刹那
我发现他在偷偷拭去眼角的泪
你说过让我带你去看大海的
父亲,我还欠你一个愿望——
你说过让我带你去看大海的
如今你病入膏肓——已经下不了床
父亲,你为什么流泪
你不是从小训斥我要坚强吗
如今我早已不会再流泪——
即便面对你的眼泪
和你即将到来的——死亡
我拖着疲惫之躯,和灌满胸腔的风
一个人去看大海
站在大海边
我看到海底暗流涌动
看到沉船
看到死难者的遗骸
看到无边的浩渺进入我胸口
看到巨鲸倒立身子
一头插进深蓝
看到看不见的彼岸——
一群印第安孩子,转动黑眼珠
在看他们的彼岸
人到中年,还有什么是我看不见的呢
但我依然爱着大海——
替我狼藉的一生
也替你苦不堪言的一生
写在边境线上——兼致西双版纳
这是一条激情与梦幻交织的边境线
也是一条一不小心就引火烧身的边境线
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比如某毒犯硬闯关卡
一切都有可能莫须有
如有陌生人主动搭讪
我们必须装出冷漠样
我们白天穿过边防检查站,然后又被它穿过
我们穿过许多陌生的鸟儿
然后又一次次被它们穿过
我们试图穿过基诺族图腾
最终却惊动了一两只松鼠
我们穿过傣族村落和缅寺
试图进入贝叶经内部,最终以失败告终
我们漫无目的又别有用心
我们是被关进笼子的欲望
我们夜晚穿过告庄的辉煌
穿过形色各异的男游客勇敢的或叵测的心
穿过来来往往的女游客——
白色的大腿丰满的乳房
长短发,以及被遮蔽的,和被掩盖的真相
我们所到之处,万事万物
都在穿过与被穿过之间
在忽略与被忽略之间;在遗忘与铭记之间
我们像三个幽灵,游荡到附近的澜沧江边
陈发坤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他的高档照机,对着茫茫夜色说话
涛声阵阵。傅达康是一块164厘米长的条石
躺在一块巨石上。这个退伍老兵
他的战友像花朵一样
有的盛开在墓碑上,有的盛开在天南海北
我有满腹心事,只向澜沧江打开
我和它,一个走向未知明天
一个流向天际。我们之间有一道闪电
我和陈发坤已人到中年
傅达康更老一些
我们都是深水。深水是沉默的
别惹我们!我们有最后的底线
一旦我们拿起屠刀,肯定是忍无可忍——我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之一
我们在黄昏出生。又必将在黄昏死去
一只猫的黄昏
一连几个黄昏,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
那只母猫蹲在门口
发呆的画面
——从捡到它那天起,它就经常这样
它背对着我,落寞萧条
偶尔它转过头,望向我的瞬间,眼神恍惚
仿佛在向我传递这样一种信息
黄昏中,它是多么忧郁
我为何说它在发呆,而不是思考
因为思考这个词太沉重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遇到它
或者它没有遇到我,如果它没有朝我叫唤
如果在我蹲下身去摸它之际
它没有用头来回蹭我,我就不可能把它带回家
如果后来我不忙于生计,不东奔西走
我就不会将它送人
如果当初我没有收留它,它又会怎样
是被好心人收留?还是依旧浪迹荒郊
如果……如果就像秋天落叶飘在空中
如果说,刚捡来那阵子它发呆
事关风月,事关一只母猫
渴望做母亲的诉求
而当这两个愿望实现后,它又因何发呆
难道它想到不堪回首的过往
故而悲从中来
难道它想到短暂安逸背后
隐藏的不确定性
故而焦虑,故而充满警惕
如果我的这种猜测成立
我想说,猫都尚且如此,何况现实中人
写给子空,兼致自己
子空又进去了,我在为他感到担忧的同时
也为自己感到担忧
这世上,有两个地方我们最不想进去
一个是医院,一个是监狱
子空进的是医院,他不是去迎接新生的婴儿
而是去接受麻醉药
手术刀、各种医疗器械和药物的折腾
子空的零部件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
他那不争气的身子
已经没有女人爱了,除非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听说子空的第二个女人(前妻)又回到他身边
与其说这是他对生活暂时的妥协
(但不会和解)
不如说这是他对病痛所做出的无奈之举
当抗争变得无意义
再坚强的人也害怕孤独
尤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
之前听子空说,他已经和那个女人离婚了
因涉及财产分割,那段时间
他正四处兜售房子
他已做好了长期租房住,度过余生的打算
为此他还找到房东交了定金
听子空这么说,我也支持他卖房子
我说,卖掉后,你至少分到50万
反正你只活70岁,加上工资,可以应付过去了
(我给他算这笔账时,他55岁)
当子空说,他最多活到70岁的时候(也许更早)
我在一旁力挺
因为我知道他内心的想法,所以理解他
就像我理解海明威、川端康成一样
其实我也有过这种想法,我也是悲观主义者
景迈山
那一棵棵古茶树,每天被人指指点点
累了,就自己结一张网,钻进去
每次去,我都会用那双
受过应试教育的手去摸它们。以为这样
就能摸出一个故宫
摸出一个大观园来
其实,除了根连着根,沉默连着沉默
我什么都摸不到
即便在翁基,那些看似触手可及的烟火
都隔着山高水长的回望
一生中需要忘记许多
到打洛口岸。中途搭我们便车的女子
匆匆消失在国门尽头
车上还残留着她的香水味
有的窜到我们身上挥之不去
这是一款很容易识别她身份的廉价香水
她是云南临沧乡下人
二十来岁的脸上,刻满早衰的沧桑
听她讲,国门外有许多姐妹
正是黄昏,天空飘着小雨
陈发坤、傅达康我们三人在国门前转了一圈
头顶飘着鲜艳的国旗
不用说,我们爱它,一直深爱
当我们转身走过一排排棕榈
阳光穿透云层照下来
每一根雨丝都闪动金色光泽
当我们返回勐海,穿行在茫茫热带丛林中
间或路过三五个傣族村落
所有缅寺一反常态
静得出奇,仿佛睡着一般
大事件
普洱通火车了。那是时代的列车
它疾驰而过,留下我一个人在站台上发呆
如果我尚在幼年,或者正值青春,
我会满怀憧憬
可我已人到中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纪
这疾驰而去的列车,像青春远去
而我不是乘客,更不是司机
教科书
小时候班主任常教导我们
让我们长大了做栋梁之材
班主任确实美,追她的人
挺多,可她一个都看不上
一晃十来年过去。我听说
她最终嫁给一个街头小贩
她衰老得厉害,不到四十,就驼了背,
眼角爬满鱼尾纹
瞬间,我对她的美好念想
在一点点破碎一点点消弭
一座曾经的灯塔轰然倒下
如果再见到这位班主任
(不知多少次,她出现在我青春期的遐想中)
我一定要对她说
“老师,我们都没有活出教科书的未来”
活着
我们活着,谁不被卷入命运漩涡?谁能幸免
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活着
关键是迎着风,歌唱天地间美好的事物
关键是大浪淘尽之后
依然热爱生命
不热爱不行,除非我们不来到这个世界
夹缝中生存
那年在澜沧江边,我看见,
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
生长在悬崖上。确切地说,
它们从崖缝中挤出来
我实在无法想象,它们为了存活下去
如何艰难地把根深入地底
而那些裸露的根,则义无反顾勒紧悬崖
仿佛一群扛着炸药包,匍匐前进的壮士
如此置之死地而后生,需要多大的勇气
狂风中,它们迂回摇摆,四两拨千斤
从始至终,都在从容应对。风止,又挺直腰杆
这多像我们的世界,规则林立
人海中,那么多面孔,或祥和,或破碎
但谁都没有哭泣
谁都试图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