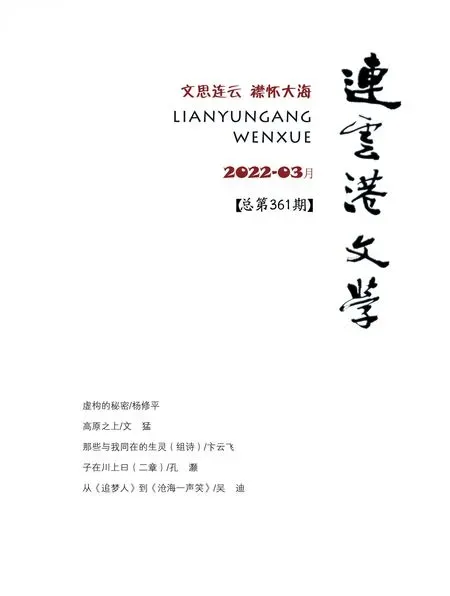虚构的秘密
陈修平
1
立冬那天,正值周末,梁新买了三斤猪肉和一袋水果,驱车上百公里去乡下看望母亲。
上大学前,梁新在乡下生活了十八年,对乡村的土俗民情有所了解。二十四节气,虽然他至今还没能记全,但当手机日历上依次显示出每一个节气的到来时,他却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知道,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节气,其实与土地与农业与农村联系得更为紧密。每一个节气,都有着与其相对应的农作物的播种、生长或收获。他也知道,二十四节气,其实早就深深印刻在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老农们的脑海里。母亲这些老农们对节气的感知,可以称得上非常敏感,而且还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梁新很惭愧,早年因为路没修好,又没私家车,回家很不方便,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几乎没有回家陪过母亲。近些年来,路好走了,也买了车,但由于要上班,也基本没有应着节气回家陪过母亲。而这个处于周六的立冬日,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陪陪母亲,于是他果断抛开了原本一两个可有可无的应酬,返回了老家。
母亲七十多岁了,依然坚持一个人留守在乡下生活。梁新知道,一方面,母亲确实是过惯了乡村云淡风轻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深层的原因,母亲为了尽量减轻儿女们的负担,更是为了避免与儿媳妇之间产生摩擦。母亲是过来人,知道婆媳关系最难处理。
为了把儿女养大成人,父母年轻时吃过不少苦。儿女长大后,父母又心心念念儿女们在城里打拼的不易,从来没有开过口向儿女要求过啥,到老来还是一直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没享过一天清福。因担心兄弟三人拿给父母的生活费不够用,梁新过年过节时总私下里往母亲口袋里塞一些钱,但过后母亲又找着借口把钱塞回了梁新的儿子。父母总是说,在乡下,有土地,有吃的,就行,又没啥别的要求……父亲去世后,梁新突然醒悟过来,父母辛辛苦苦把儿女拉扯大,其实儿女们反馈给父母的却很少很少。与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少,因此他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一起生活。
然而,每当梁新劝母亲留在城里生活时,母亲总是说:“两个碗碰在一起也难免会撞缺口子,牙齿和舌头也难免有互咬的时候。你们兄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轻轻重重说啥都可以;儿媳妇可不同啊,她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各自不同的脾性。在一起生活,日子久了,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我还是一个人在乡下过得好,免得遇上磕磕碰碰,你们夹在中间为难!再说,我这把老骨头,在城里鸽子笼样的房子里,没法活动筋骨;出门走动,又要下楼上楼。到了外面又是那么多车子,老眼昏花的,惹麻烦。在乡下,村里的路闭着眼睛都会走,有空侍点菜园,又能松松筋骨,又能吃上新鲜,多好!”
梁新想想,母亲的话也说得在理。
梁新了解自己的母亲,曾经的艰苦岁月让母亲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她一旦认准的事情,总是努力坚守,很难改变。兄弟三人,只有梁新一人有正式工作。吃公家饭的在村里凤毛麟角,梁新知道,这是父母辛苦送他读书的结果;哥哥和弟弟都在外地打工,家人也随同在外生活,只有年底返回老家山村过年。考虑到母亲的年纪,兄弟三人早年就商定了出钱供养母亲,母亲只要在村前地里种点自己吃的蔬菜即可。但母亲总想为儿女减轻点负担,前些年还偷偷种了油菜,榨了菜籽油。年底,还给每个儿子各分了一壶油,梁新这才得知母亲种了油菜,为此多次劝说母亲别再操劳了,母亲当时也答应不再种油菜了,可是第二年依然故我……母亲这么大年纪在山村里生活,加上近些年来村里人越来越少,梁新很不放心,所以有空就下乡来看看母亲。
一路上,梁新一边开车,一边回忆着母亲的过往,内心更加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恩。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母亲的晚年生活得更加幸福。
2
村口道路两边的田地里,一垄垄油菜苗吐着青绿,长得正旺。梁新虽没在家种过田,但大致知道一些农作物的生长季节。曾经,土地被农民视为命根子,农民从来不会浪费土地,更不会糟蹋土地,不少边边角角都被挖出来了,种上丝瓜南瓜黄瓜之类的瓜藤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秋收过后,为了不让土地闲着,乡亲们一般会种上油菜,来年春耕之前即能收割,正好可以赶上插早稻秧苗。季节,一季连着一季,田地里的庄稼,也一茬连着一茬。春夏秋冬,各有各的景儿。梁新突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母亲就像这土地一样,总是不知疲倦奉献着。
看到梁新带来的东西,母亲埋怨道,“现在肉这么贵,还买这么多干吗?”
“买来了,您老人家就尽管吃,我们做儿女的也该孝敬孝敬您啦!现在不像过去,我们手头都越来越好了,您放心,只要您身体康健,快快乐乐就好!”梁新笑着对母亲说,“中午随便吃点,不用弄那么多菜,一两个青菜就行。”随后,他到留守村里的其他三四户人家串门去了。
“我姆妈一人在家,还请平时多多帮忙照应照应,我担心老人家的身体!”梁新一户一户地打着招呼。
“你姆妈健康得很,种了好多菜,听说你要来,已经准备好了干菜、青菜让你带回去。”村里人都这样说。
“我姆妈今年没种油菜吧?”
村里人都呵呵地笑了,没有正面回答。
“那就是种了吧!”看到村里人这种反应,梁新似乎感觉到了。
“你姆妈早就跟我们讲了,让我们见了你别说。”
梁新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了四个菜,母子俩于是开始吃饭。
“姆妈,您今年又种油菜了吧!早跟您说了,只要种点自己吃的青菜就行,不要老想着要带菜给我们吃。您这么大年纪咋还能做那么多事呢?说实话,你的菜又保不了我们吃的。我开一趟车来回的花费,不知可以买多少蔬菜呢。”梁新笑着说。
“能做就做点,样样都要买,也难,你们兄弟也都有自己的家啊!”
“姆妈,现在是您养老的时候。油菜,不像其他蔬菜,光种下去不行,还得侍奉好几个月呢,后面还要收割、晒干、脱粒,最后还要送到集镇去榨油,要是这中间您老有个啥闪失,叫我做儿子的脸往哪儿搁?今年就这样吧,以后真的不能再种了。来年要是听说您种了油菜,我就去地里一棵一棵扯掉啊!”
看到母亲不作声,梁新沉默一会后,压低声音说,“姆妈,我告诉您一个秘密!”
“啥秘密呀?你还能有啥秘密呀?”母亲哈哈地笑了起来。
“姆妈,我已经存了一百万啦,现在是百万富翁啊,您放心,儿子有。需要啥,您就说,不用种油菜榨油了,我包您吃的油!”
“老二,你咋存了这么多钱?这几年听说国家抓了不少人,你这些钱都是干净的吗?”母亲脸上现出忧虑。
梁新哈哈地笑了起来,“姆妈,儿子啥样的人,您老还不知道吗?您老从小就教育我们要有良心,守规矩,我咋会干违法违规的事呢?放心,每一分钱都是我们省吃俭用积赚下来的,儿子保证百分之百绝对干净!”说这些话时,梁新底气很足,似乎每一句话都像踏在大地上一样坚实。
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一圈一圈地漾开来,梁新感到非常舒心,继而又低声说,“姆妈,这是咱们两人之间的秘密,谁也别告诉,连我老婆都别说!”
“我知道,知道!”母亲连声说道。
从母亲的声音里,梁新听出了开心,他为自己的话语能让母亲开心而有了小小的得意。梁新知道,只要听说后辈过得好,母亲就会开心,并非想着后辈能多孝敬一点。
3
过了一段日子,母亲给梁新打来电话,“听你弟媳妇说,你弟弟发了阑尾炎,这几天要做手术。他们在外面打工不容易,手头紧,你转一万块钱给他用吧。”
“姆妈放心,阑尾炎,只是个小手术。他们在外面打这么多年工,应该有手术费吧,不用您操心。我等下打电话过去问问情况。”
“做手术动刀子的事,没有小的。电话要打,钱也要打过去。只有今生的兄弟,没有来生的兄弟!”
梁新愣了一会,随后说,“好,好,我打完电话就把钱转过去。”
春节,梁新兄弟三人都回了老家。
平日里,村里村外很难得见年轻的后生和姑娘,都到外面打工去了。正月里,不少后生和姑娘返乡过年,大人们心中都有个想法,年纪轻可以挑别人,年纪大了就只能被别人挑了,最好能趁春节把孩子的终身大事给定下来。不然,一年大一岁,一年拖一年,一转眼就会成为大光棍、老姑娘了。家有姑娘的,还有一层想法,希望能把姑娘嫁在邻近的村子,老了,姑娘方便回家照应照应;要是被相隔太远的外地后生哄去了,日子久了,这姑娘可能就白养啦……
老大有两个儿子,按照乡下的习惯,口头上称呼大儿子为大佬,小儿子为细佬。在乡下,没考上大学的青年男女,到了二十岁就会被家里大人张罗婚事。大佬年纪有二十五了,大哥大嫂心里着急,年前年后四处托人做媒。正月初五,男女双方终于对上了眼。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商量订婚之事,彩礼、过门等费用算下来,需要将近二十万,而老大说只积攒了十来万,一下子冷场了。
“喜事,一个人弄不圆,那就一家人都出出力,大家一起做。老二,你借五万给侄子订婚吧;剩下的,让他们父子另想办法去借。”母亲突然对梁新说。
“姆妈,我手头也紧,前面还借了一万给弟弟呢。”梁新面露难色。
“你手头咋紧呀?你不是存了一百万吗?”
一大家人全都盯着梁新,梁新的老婆更是露出了异样的目光。
“我,我……”梁新红着脸,本想说啥,却又止住了,只是说,“好吧,我去弄。”
散场后,梁新的老婆把他叫到房里,“好呀,原来你还藏了一百万呀!”
“老婆你小点声!”梁新赶紧提醒老婆,“你傻呀,我多少收入你还不清楚呀?每月的死工资,一发下来全都交给你了。咱们买房还欠着银行的钱呢,每月还在还着房贷呢。我要有钱,不早就把银行的钱还清啦,还用得着付利息吗?儿子又在读大学,这几年哪还有啥积蓄呢?”
“那你姆妈咋说你存了一百万呢?你不说,老人家咋知道?肯定是你自己说出去的!”梁新的老婆盯着梁新,似笑非笑地追问。
“我这么说,是为了让姆妈安心养老,不要干那么多活,不要种油菜。”梁新涨红着脸说,“姆妈这么大年纪,还干那么多农活,咱们在城里咋能放心?”
“那好呀,怪不得上次姆妈让你拿钱给你弟治病,这次又让你出钱给侄子订婚!”梁新的老婆生气地说,“看你这个谎以后咋圆?就算这次侄子订婚你想办法借来了,要是下次家里还有哪个要用钱,向你开口,你还上哪儿去弄?”
“只能先这样啦,侄子订婚这样的大事,还是要想办法帮帮。要是后面有啥事,只能到时候再说。”梁新苦着脸对着老婆。
4
转眼,到了八月中秋节。
按照家乡的风俗,次年正月新婚的,男方需提前在中秋节送节时求得女方的生辰八字,以便把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放在一起,请风水先生看好结婚的黄道吉日。风水先生将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工工整整地抄在红纸上,而后写上测算出来的黄道吉日,一式两份。男方随后将其中一份送至女方家。
梁新回家陪母亲过节,看到大哥也回家了,估摸着大哥是替侄子来给亲家送节了。
大哥坐在客厅闷着头抽烟,脸上丝毫见不到快娶儿媳妇进门的高兴,反而一脸阴云。看到梁新进屋,也只是欠了欠身子,说了声,“回家啦。”
梁新转身进了灶屋,正在准备中饭的母亲,也是一脸愁苦。
“姆妈,您和大哥咋都不高兴呀?”
“咋能高兴得起来啊?过了中秋就是年,眼看年底也快到了,过了年就给大佬办喜事,哪知女方又提出要在县城买房子,还说不买房子这婚就不结了!”
“在县城买房,可不是小数目。大哥在家里建了三层这么大的房子,还要在县城买啥子房呢?结婚了,他们俩还会在外面打工,县城买房根本不适用。”
“知道不适用,她家也要啊。说到底,她家还是看到你大哥有两个儿子,还不是想在结婚前为自家女儿多争一些?大家庭的,能要一点是一点,婚后分家了,就要不到了。碰到这样不讲理的亲戚,唉!”母亲说着,不禁叹了口气。
“我去问问大哥咋打算的。”梁新转身进了客厅。
“姆妈说,你儿媳妇家说要在县城买房子呀。”
“是呀,不正为这犯愁吗。”
“你跟大佬商量了吗,准备咋办?”
“大佬说不结就不结算了。小孩不懂事,说句气话容易,越拖越难找到合适的。买房子只是一时难以凑钱,其实,想穿了,买了还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大哥边说边抽着烟,烟雾缭绕之中,脸上的表情忽明忽暗。
“话是这么说,但买房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梁新忍不住又问,“你们这大半年积攒了多少钱?”
“没积攒到多少。本来今年一家人的收入加一起,对付结婚的开销还马马虎虎,谁知又来这么一出?”
“河里不丢烂板船。女的,不愁没人要,呆的,傻的,离婚的,哪一个没人要啦?只是好有好配,歹有歹配。隔壁村里一个女人,快四十了,刚离婚,就有人上门说媒了。倒是男的,打光棍的越来越多!”母亲端来一盘菜上桌,接上话茬说开了,“还是要想想办法,把这婚事给圆了。”
“老二,要不再借我五万,让你大嫂也去她娘家转转,我也去四处借借,把首付付了。后面的房贷,就让他们小夫妻俩结婚后驼起背来还。结婚了,就分家,我们就不管了,也管不了,他们自己也得有点压力。后面我还要为细佬攒钱娶老婆呢。”大哥沉默一阵后,向梁新开口了。
“可是,我一时拿不出这么多。”梁新的脸瞬间涨红了。
“你不是有一百万吗?我又没说要你拿十万二十万。这是你自己的侄子成家,你不帮谁帮?”大哥的脸上明显不快,“放心,明年攒了钱,就还你一部分。”
“我要是能拿出来,就不会急着要你还。侄子如子,姆妈经常这样说,能帮我一定会帮。关键是,关键是我拿不出来。”中秋的天气逐渐凉了下来,而梁新的脑门上却冒出了一层层细密的汗水。
“要是存了定期,就牺牲点利息提前拿不出来,损失的利息我来付。”
“是呀,老二,你就再帮侄子一回,牺牲点利息,没啥!”母亲看着梁新,眼神里满含期待。
“没存银行,买了股票,被套住了。”梁新红着脸说。此刻,他更加觉得老婆说的话在理,为了宽慰母亲而编了个善意的谎言,而这谎言不是一时口快说出来就完事了,当时没想到会有一连串后遗症啊,这得需要多少谎言来圆啊,而且还不知要招引多少误解。前面借给侄子订婚的钱都是借来的,可这能实话实说告诉姆妈和大哥吗,更何况说出来谁会信呢?
大哥一脸的不信。
母亲满眼的无奈。
屋子里一时无人说话,气氛非常压抑,梁新却似乎能听到母亲心里的叹气声。
“要不,我回去就去找朋友借,尽量转满两万,可以不?”梁新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大哥,似乎不是他在帮大哥,而是大哥在帮他。
“两万有啥用,首付至少也得二十万。”大哥的话语中含着不满,脸上写满生气。
“老二能转两万就两万吧,到时要是差了两万,卖房子的人可不会跟咱们讲情面。老大,多想想办法,多找人借借吧。”母亲打着圆场,“先吃饭吧,饭总是要吃的。”
这个中秋节的饭菜,梁新觉得记忆中从没哪一顿吃得这么别扭,这么艰难,这么无味,他都不知道自己这顿饭是怎么咽下去的。虽然母亲做了满满一桌菜,但他觉得还没小时候一两个菜吃得香。
吃完中饭,梁新匆匆返回城里。尽管他想多陪母亲待一会儿,但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氛围,另外也想早点借上两万,转给大哥,不然这兄弟之情怕是不知咋样收场。他也知道,即使借了两万,大哥也是对他这个有正式工作的弟弟极不满意的,谁叫他“有一百万”呢?他也想过把大哥单独叫到一边,说明一百万只不过是说来骗骗母亲的,他还欠着外债和银行贷款呢,但这种情况下这样说,谁会信呢?说了也是白说,索性作罢。
尽管母亲一次次让梁新出钱帮弟弟、帮侄子,但梁新一点儿也不怨母亲。
梁新也不怨母亲把“一百万”的秘密给说出来了。为了儿孙,情急之下,如果不脱口而出,那才不是自己母亲的性格呢。
梁新知道,母亲就像村前那棵百年古樟的树干,儿孙们就像树干上面伸展开来的一根根枝条。尽管树干表面已经斑斑驳驳,中间甚至还空出了几个窟窿,但树干还是希冀着能够枝繁叶茂,并尽力挺起满眼葱翠。因为这都是从树干上面生发出来,继而开枝散叶的呀,每一个枝丫,乃至每一枚叶片,都连着树干的心啊!
5
大哥后来没能凑满二十万,只凑到了十来万,但房子还是买了。
媒人是远房亲戚,还是得力,思来想去,想出了个通融的办法。
按照惯例,订婚时男方给女方的彩礼钱,女方的父母是不能据为己有的,只是代为保管,结婚当日会当众把存有彩礼钱的存折交到女儿手中。有些亲家有能力好面子,还会多加一些一起存上。当然,也有少数亲家,会把彩礼钱克扣下来,起初男方也不好说这个,但事情慢慢会传开来,女方父母的面子在附近乡里乡亲间就会大大折损。
既然女方一定要在县城买房,而男方努力了又凑不满首付,媒人提出让大哥打个借条,把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彩礼先借过来,凑满首付款。大哥起初不肯打这借条,这钱终究是自己家的,打借条算哪门子的事?媒人便开导道,不这样做,钱就拿不过来,事情就僵住了。打这个借条,其实也就是做做样子,结婚了,你儿媳妇真能找你还?钱是给她买了房子,她说要还的话也不硬气。这就像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也就是做做样子打个借条……
这些,都是梁新给母亲打电话时,从母亲口里断断续续得知的。自中秋节过后,梁新不好给大哥打电话问侄子的婚事,因为他知道,这种境地,只有能拿出钱来才好说话,否则就是自讨没趣。
听说侄子的婚事扫清了障碍,梁新长舒了一口气。
正月初二,侄子结婚前一天,梁新一家三口回了老家,帮忙筹备婚礼的酒席。族下每户一人集中开会,安排结婚当日的人手,梁新负责接收礼金,梁新的老婆与一帮女人负责洗菜洗碗,梁新的儿子则跟着大人,到各家各户搬凳子抬桌子,聚拢到祖厅里摆酒席。
结婚那天,梁新的姑父姑妈带着表弟也来喝喜酒了。表弟坐在一旁,看着梁新清点登记一笔笔礼金,突然开口了,“表哥,我想买辆车,还少点钱,你借两万给我不?”
“是呀,是呀,你表弟也到了娶媳妇的年纪啦,买辆车,相对象时会打眼些!”姑妈跟着在一旁帮腔。
“姑妈,我这几年手头也紧,还是欠账户呢。”梁新笑笑。
“哈哈,老话说死啦,真是越有的越吝啬啊!谁不知道你是百万富翁呢?我只是找你借点,又不是要你的!”表弟生气地说,“也是,你亲侄子结婚要用钱,你也说没有,更不要说堵我这个表弟的口啦。”
梁新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回应表弟。幸亏人来人往,他得招呼来客,接受清点亲戚们送来的礼金,不然他都不知如何应付表弟所带来的尴尬。
婚礼当晚,梁新找了个借口,带着老婆孩子连夜回了城里。正月里,要是哪个亲戚家办大事需要用钱,他这个“百万富翁”不知该如何应对。虽然现在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多的是,但对于他这个拿死工资的上班族,对于他这个一穷二白从城里起步的乡下人来说,购买房子,孩子教育,还要希望没病没灾,能尽快实现不欠账就心满意足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6
乡村的春节是热闹的,每天都能听到鞭炮响,每天都能听到锣鼓声,结婚的,订婚的,添丁的,做寿的,平时人员聚不拢,便都聚到春节来办酒席。在乡下人看来,春节就应该这般喜庆,仿佛一年来经历的酸甜苦辣,全让这喜庆冲得烟消云散;仿佛一年来积攒的情感,都要在此时集中呈现出来;仿佛所有新年的愿景,要让这扑面的喜庆开出道来……
一过元宵节,年轻人包括多数中年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谋生了。只有几个老年人像村前村后的几棵古树一样,静静地驻守在村子里。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或者说孤寂。
江南,立春之后,雨水渐多。一场接一场的春雨,滋润着山林、田野,山上的树木,山下的庄稼,仿佛都被雨水鼓胀起来了,争先恐后地绽芽、拔节,到处是绿绿的一片。而这些草木的旺盛,多多少少能消弭一些村子的孤独。
当映山红在山坡上探出亮眼的脸蛋时,又一个清明节到了。
在乡下,清明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端午节,中秋节,在外面有事不能回家,谋生不易,都能理解,没人会说啥;但清明节一般是不能缺席的,已经过世的先人,尚在人世的老人,全都睁着眼睛看着呢!
老大老细都回村了,只有老二没回。自从工作以后,每年的清明节,老二都会回村,一次没落下过。尽管这次老二已提前打来电话,说清明节前后单位有事加班,但母亲还是隐隐感觉有啥不对劲。
清明节次日,老大老细都说要返回外地做工,但被母亲拦住了,“我总感觉老二家有啥事,要不他不会不来的。咱们还是上城里去看看吧,不然我不放心,心里总有个化不开的疙瘩!”
“老二家能有啥事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不用操心啦!”老大满不在乎地说,“我外面接了一家装修,约好这几天就要开工呢。”
“这么多年,老二家不管有啥事,都是他自己一人默默承担。结婚,买房,儿子上大学,哪一样向你们开过口?”母亲有点生气地说,“你们是亲兄弟啊,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们不关心他,谁会关心?”
“是呀,要不咱们还是去看看吧,看了没事就更好。”老细顺着母亲的心意说,“我开车过去,也快。”
母子三人到了梁新所住的小区,找到楼栋单元,按响了房号对应的门铃。
“谁呀?”门铃里传出陌生的声音。
“这不是梁新家吗,找梁新,我是他弟弟呢!”
“你们找梁新呀,他不住这儿,一个多月前就把房子卖给我啦。”
看到母亲的脸上瞬间变色,老细赶紧对着门铃问道,“知道我哥现在住哪儿吗?”
“好像听说租了后面第三栋底层的杂物间,当时看到他把东西往后面搬过去了。”
母子三人急匆匆地往后数到第三栋,一间一间地敲着底层的门。
这是十多年前建成的小区。这些底层原本规划设计建设的杂物间,当初卖的时候价格较低,其中不少是被一些人集中购买了,打通了,简单装修了一下,当住房出租。一些来城里打工的,为了租金便宜点,就选择租在这里临时居住。这样的住所,虽然空间不高,而且梅雨季节比较潮湿。当地面上,墙壁上,在不知不觉间冒出一层层细密的水印乃至水珠,严重时,还会顺着墙面瓷砖往下流——这便是要下雨的前兆,有时甚至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确。但这样的住所也有一个好处,脚下紧贴大地,不用上上下下爬楼,出入非常方便。
敲到最边上一间时,开门的正是梁新。仅仅两个月左右未见,梁新消瘦了不少,鬓角爬出了不少白发,母亲的眼泪簌簌地往下流。
进入室内,梁新的老婆正卧在躺椅上,身子下面垫着被子,脸上寡白寡白的,没有一丝血色,瘦得已经失去了原样。
母亲蹲在躺椅边,抚摸着二儿媳瘦削的脸蛋、稀薄的头发,继而抓住二儿媳软弱的手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外淌,“儿呀,这是咋啦?”
“姆妈,没事。乳腺癌,刚从上海做了手术化疗回来,现在是慢慢休养。”梁新边泡茶,边回应母亲。
“你咋的连房子也卖了?”母亲埋怨道,“这么难,也不跟家里人说一声!”
“治病要紧,只要人在,迟早啥都会有的。”梁新劝慰母亲,“家里人都难,说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必让大家都跟着为难。”
“老二,你应该还有钱吧。”老大皱着眉头说。
看到老公苦笑着动了动嘴却没说出来,梁新的老婆忍不住开腔了,“大哥,你自己弟弟的性格,你还能不知道吗?不要说他在单位没啥权,就算是有权,他是会往自己口袋里塞的人吗?他就拿点死工资,比你们在外面打工确实要轻松些,但也就图个安稳,发不了财的。”
“但还不至于卖房吧。”老大嘟囔了一声。
梁新的老婆缓了一口气,接着说,“不卖房咋办?我本来想向你们开口,让你们把前面借的钱想办法还回来,但他不同意向你们开口,说你们手头也紧,更何况开口了又能咋的?我说在本市做手术算了,但他坚持要到上海去。他先前跟姆妈说有一百万,那是安慰姆妈的,为了让姆妈不要太过操劳,你们还真以为他有一百万呀?前面给你们的钱,都是他从外面借来的。”看她的表情,她很想大声把这些在心里积压了许久的话抖出来,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是软绵绵的,有气无力。
“真有这么困难呀?”老大又嘟囔了一声。
“你们不信,我信!”从来温言细语的母亲,突然大吼着说,“都到了这般境地啦,你们还不相信自己的兄弟?”
一旁的老大、老细都惊住了,老大更是满脸通红。
梁新也是一脸惊愕,随即眼眶涌上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