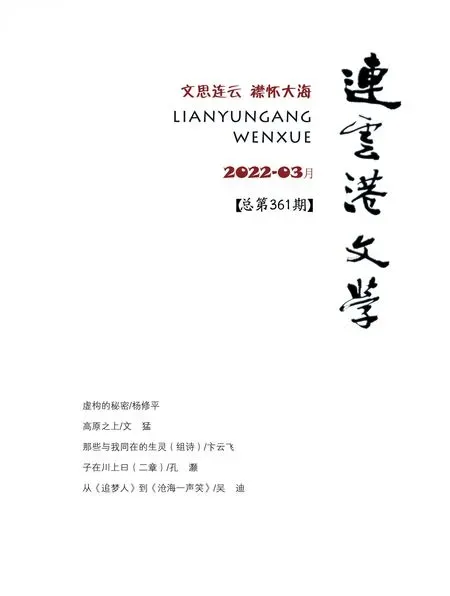石头
蒋晚艳
1
石头背靠沙发,嘴唇紧抿,喉结一鼓一鼓的,眼窝如泉眼,泪水汩汩而出,刻意压制的发声,风一样呜咽:“二十八年了,我和他,二十八年啊……”
石头是湖南武冈人,在广州开大理石作坊,两天前切除了喉腔息肉,手术后一周内不能发声。听到他的消息,我能够想象得出,那种想念不能说、心痛不能哭的滋味,“哑巴”石头肯定无助得像个迷路的孩童。
一九九二年,正月初六,邵阳至广州的货运火车上,我和石头、王老板,都挤在同一节车厢里。
春运期间临时充当客运的货运火车,没凳子没椅子,车厢就是个货柜,站的、蹲的、搂抱行李的,车里的人横七竖八地偎着各自大大小小的包裹。石头像泥鳅一样带着我往人群里钻,最后把我安顿在最里层的厕所旁边,“靠墙,别动,臭就臭一点,一天多就到了。”
石头说完话,两只圆鼓鼓的眼珠子叽里咕噜地朝车厢看。
“包,钱,都拿出来。”这声音由远及近,很快,几个流里流气的男青年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不敢说话,我看石头,石头没看我,他在看另一个人。那个人劫了一个又一个包,在他摸到石头前面一妇女的包后,妇女惊恐起来,“我的包!”妇女一边喊一边哭,大意是她包里的钱是进厂要缴的押金,没了钱,她就进不了厂。
“啪”的一声,领头的青年给了妇女两巴掌,“让你叫,让你叫,老子打死你!”
石头紧握拳头,脸涨得通红,青筋像蚯蚓一样在额头爬。石头是村里出名的猛子,脾气暴躁得很,我很害怕,又不敢拽石头,只在心里祈祷,“千万别惹事,千万别惹事!”
那是二十四岁的石头第一次下广东,他要找厂,当打工人,要赚数不过来的钱。
青年对着妇女一顿拳打脚踢。周边的人和我一样,人人恨得牙痒痒,却个个不敢吭声,谁开口,男青年便恶狠狠地对着说话的人挥拳头。人心都是肉长的,很快,大家都齐心指责起来。我以为事情有转机了。忽然,那个带头的青年扯着妇女的头发一甩,把妇女的头往铁皮车厢上撞。几乎同时,石头抓起旁边一个腊菜玻璃瓶,从后面朝男青年头部砸去,“嘭”的一声,瞬间,浑浊的血水从坏青年的额头上流下来。
“谁?到底是谁!”男青年捂着头,眼睛刀一样朝人群扫去。
我吓得嘴唇直抖,心都快跳出来了。要是抓到石头,石头肯定会被打死的。我好怕,石头却离我越来越远。我知道他是刻意离我远的,他怕坏人万一发现他,会带出我。
这时,火车长鸣,车轮开始滚动,停靠衡阳站的时间过了。
“既然大家不说,别怪老子不客气。”领头的男青年恶狠狠地叫,其他几位跟着挽袖子伸拳头,大有要血洗车厢的劲头。
石头被圈在人群里,青年似乎发现了苗头,凶神恶煞地逼近石头。就在车门要关闭的那一刻,一个和石头年龄相仿的男人,抓起石头的手,两个人从火车上一跃而下……
带石头逃跑的,就是石头所说的王老板。
这个王老板,是湖南怀化人,初中辍学后在工地打工,二十四岁时已是广州包工头,但凡室内外装修、泥水工、轧钢筋、石材加工等等与装修有关的业务,一律照单全收。石头火车上痛击闹事者,一旁的王老板都看在眼里,他欣赏石头的正气,但批评石头太过莽撞,说石头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坏人有多坏。
王老板把石头带回自己在广州的希望装修公司,安排石头在石材部上班。
浑身蛮力的石头,一做就是整整十年。
石头原本不叫石头,因为跟石头打交道,又陆续带动好几个亲属走进石头行业,石头的姐夫、妹夫、弟弟、妻舅、堂侄等人,都在石头的牵引下,一个个进了王老板的装修公司,分布在石材部主要岗位上,石头一家成为老家远近闻名的石头家族。在石材领域,石头是乡亲们的石头领路人,也是家族中的石头元老,所以,慢慢地,大家都叫他石头。
2
石头呜呜地哭,鼻涕和眼泪赶集一样挤到嘴边,两瓣紧抿的唇像两扇摇摇欲坠的门,声音撞在喉腔里,发出异样的声响。听不清石头的喉语,我干脆拿来纸和笔,叫石头坐到沙发上写。石头便歪歪扭扭地写道,“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一九九二年算起,十年光阴,石头娶妻,生儿育女,建老家的房,石头娘在老家带孙辈,养猪喂鸡栽瓜种菜,其乐融融。人人都说春运挤,但石头每年春节都能按时到家,每个春节,石头娘都备好腊鱼腊肉干豆角酸萝卜等特产,等着石头一家归来。每年暑假,石头爹带着孙子孙女,像那些邻居们一样,浩浩荡荡南下广东看世界,待到秋季快开学,又如迁徙般浩浩荡荡返回老家……总之,十年来,石头家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石头能当老板,也是因为王老板。
“广州大开发,楼盘一拨一拨建,咱们业务增多,我的应酬也增多,这样吧!以后石材部由你承包,我把单价定给你,多的钱你赚。”王老板拍拍石头的肩膀。
“行!”石头憨憨地笑了。
随后,石头叫来在中山灯具厂打工的石头嫂,“咱这回也是老板了,哈哈!”出租房内,石头拥着爱人。
“石头那么贵,我们哪有钱垫资买材料,万一没事做,那些工人的工资,我们出得起?”
听石头嫂一说,石头便又迷茫了,连忙找到王老板,摆着双手,“这事不行,我不行。”
“哪有男人说自己不行的!”王老板哈哈大笑,然后,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稿纸给石头看,大意是,总公司的石材单由王老板买材料,石头只管生产、加工和交货;公司外的石材单由石头自己买材料,遇到大单周转困难时,再找王老板协商解决;公司有业务给石头,就收档口租金;如果没业务,档口闲置多久,租金就免多久。
“话说到这份上,你如果还当乌龟,那我也没办法了。”
加工费、差价、额外收入、减免租金……一串串数据花一样在石头脑中转。
石头也听不得“乌龟”二字。
就这样,石头成了希望石材部的老板。
姐夫负责切割部,妹夫负责安装部,弟弟负责货运部,石头嫂后勤部,石头本人成品部和业务部,各司其职。说是部门,其实也就一个部门一个人,“人能少则少,钱能省则省。”石头公司和许许多多小作坊一样,开始组建起家族式的石头王国。
打工的时候,每天按时上班,到了时间拿工资,发工资那天喝几瓶啤酒,弄两盘花生米,生活倒也有滋有味。当了老板,石头成了石头磨,被业务催着日夜不停地转。天河、黄埔、佛山等区域,地板、橱柜、门套、楼梯石、广场、地铁台阶等业务范畴,王老板的石头单像钞票一样飞来。石头忙王老板的大单,也忙形形色色的小单,比如附近居民装门槛石、订洗手台、改旧翻新换橱柜等。
三个月后,除了工资、材料成本、加班费,收入比打工一年还多。
石头说,“还是当老板好,钱多。”石头嫂妩媚一笑,“要长期好才行。”
“肯定没问题,一切都会有的。”石头雄心勃勃。
3
把石头从天堂打入地狱的,是石头当老板后的第八个月,暑假接近收尾。
广州天河堂下一个楼盘的样板房要提前装修,王老板连夜从云浮进石材到石头公司,石头得加班配合下材料。二〇〇二年的广州,现场结算的临时搬运是众多流浪者的香饽饽。石头在临时工聚集的桥底一吆喝,找工的人瞬间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过来。
“你,你,还有你。”石头一连点了五六个。
“我也要,我要交学费。”这时,一个清瘦的小伙挤到石头面前。
石头见小伙瘦得像麻竿,脸白净白净的,纯粹一个书生相,“不行,你太年轻。”
“我行,我有力气。”小伙子猛地抱起身边一个大汉,“看,我都能抱起伯父。”
农药作为必不可少的农业生产资料,在我国防治病虫害、去除杂草、控制人畜传染病,以及提高农作物产量、质量起着积极的作用,为中国农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农药是具有杀虫、杀菌和除草功能的化学品,人们普遍认为农药是有毒危险品,而农药残留引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扩大了农药的危害,使人们对农药谈药色变,农药几乎成为过街老鼠。
“呵呵,好,你也过来吧!”石头便连小伙子的伯父也叫上。
晚上十点,货车轰隆隆地开进希望石材店。“四人车上搬,四人车下接。”石头指挥车停好,“石板分批放至三脚架上,左边架十块板,右边架十块板,两边要均匀,不要斜,不能倒。”
“一二三,起!”车上,四人光着膀子,肩搭汗巾,四双手紧抓石板四边,缓缓把石板挪到车厢尾。
“一二三,落!”车下,四人伸手,踮脚,像挪炮弹一般,把石板缓缓挪到地面,再慢慢抬到木架上。
三小时后,车上只剩两块石板了,石头松了口气,走到办公室咕咚咕咚灌水喝。
“救人啊,救人!”
忽然,惊悚的呼救声箭一样穿进石头胸膛。
“挪,快挪,挪石板。”
一阵手忙脚乱,石板是挪开了,但是,小伙子像石板一样躺在石头面前,再没醒来。
“还我侄儿!还我侄儿!”伯父的拳头雨点般挥向石头。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石头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家都在下车,小伙子怎么会独自落在石架边?这几分钟的工夫,那么有活力的渴望赚钱的小伙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档口停工,劳务纠纷。希望石材部彻底停摆。
“完了,一切都完了。”一个凄风冷雨的夜,石头来到离档口不远的珠江边,双手抱头,两眼一闭,泪如泉涌。
好像从十七年前的那夜至今,石头的泪一直没停过。
“如果没有他,这个世上早就没我了。”写下这句话,石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呜地哭,“那夜,我纵身一跃,又是他拉住我,他要我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
“都说不能发声了!”我凶石头。
石头停住哭,像只受伤的小兽,抖动着肩膀,久久地呜咽。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后三年,珠三角飞速发展,王老板的希望总公司和石头的希望石材部,天天加班加点。
二〇〇五年春节,秉承“七不出八不归”的湖南习俗,在阴雨绵绵的正月初六,石头家族返回广州。“包工头爱喝酒,喝了酒好谈生意”,石头爹像往年一样,装了两大桶自家酿的米酒。石头娘吩咐孩子们往堂屋走,“爷爷奶奶保佑你们兄弟姐妹出门平安。”石头弯腰挑酒桶,刚起身,一头绳子松了,酒桶“砰”的一声撞到地面,桶底裂了,白酒如水,哗哗地在地板上流。
“菩萨保佑,祖宗保佑,保佑我的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有事由我当娘的一人承担。”石头娘“咚”的一下双膝着地,对着神台双手合十,念念有词。
呜咽了好一阵的石头,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泪痕像蚯蚓一样留在他黝黑的脸上,那刚刚割了一块肉的喉腔,一直瑟瑟地抖。
我给石头盖好被,想起石头的娘,黯然神伤。
那年秋,石头娘走了,才六十岁。
娘在,家在。娘没了,家也散了。
娘忽然离去,石头的家庭结构也重新洗牌。读中学的石头女儿改成学校寄宿,读小学的石头儿子来广州读私立学校,石头父亲在广州接送孙辈上学。石头姐夫、妹夫、弟弟都离开了石头公司,陆续建起自己的石头作坊。石头老家新建的别墅,一把大铁锁快要生锈了。石头的希望石材部最终只留下了石头嫂和石头。
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大理石装修处处需求处处急,广州石材加工店忽然多了起来。蛋糕虽大,分的人多,石头想请人,想想又作罢,“累就累点吧,身体撑得住就行。”就这样,石头白天上工地量尺寸,跟包工头谈生意,晚上回到档口继续加班。
石头早出晚归,天天如此,雷打不动。
“快!鞋城老板柜台石,两小时之后要。”那一天的前一晚,石头整夜没睡,长期搬重物的腰已经明显弯曲。
“刚下单就要货,生孩子还要十月怀胎呢。”石头嫂忍不住发了一句牢骚。
“叫你招人你不招,忙一点又啰啰唆唆!”石头大嗓门一吼,石头嫂便低下头,更加拼命地干,抬石材、做加工、核尺寸。作坊虽小,但夫妻俩全能。
石头的繁忙对比同行的平淡,内心就有一股说不出的快活。电源一开,钻机声雷一般轰鸣,不大的档口顿时尘土弥漫、石砂四溅,四周灰蒙蒙一片,石头粗短的胡须没一会像染了霜。
“戴口罩吧!”石头嫂眉头一皱,“这样下去不行,会生病的。”
“戴口罩,想我死呀,我怎么出气?”石头侧脸张开嘴呼吸,蜜蜂一样嗡嗡地反对。
“哦,水!”石头嫂猛然想起没加水。
石头切割,介开的空隙有灰尘和石粒,所以开介时要顺着切口浇水,以抑制灰尘传播。石头嫂拿起盖子上打了两个孔的矿泉水瓶装满水,配合着石头一前一后喷淋着。
“这个,碍事!”石头猛地扯掉眼罩。
“口罩不用,眼罩也不用。”石头嫂像是说给石头听,又像自言自语。
“唉哟——”忽然,石头一声大叫,切割机的轮子“砰”的飞出几米远,飞旋的铁轮像扔到岸上的鱼,在地上跳动、翻滚。
鲜红的血喷泉一样从石头的左手臂上飞溅开来。
石头嫂最初没反应过来,待明白过来,吓得哭了。
“关电呀!”石头蹙眉呼喊。
医院,手术室内。
“缝线,打麻药。”医生吩咐护士。
“不要麻药,直接缝。”石头左手乌青、胀鼓,右手青筋凸起,似乎血管随时都会爆裂。
护士立在原地,看看医生,又看看石头。
石头重申,“缝,直接缝!”
松手,止血。只见,十几厘米长的伤口像条峡谷,两边的肌肉如破肚的鱼。此时的石头,硬是壮士一样挺着,“医生,缝吧!”
医生紧皱眉头,边缝线边说,“老板有没有帮你买保险?你这一次还好没伤到骨头,伤到骨头轻则没手,重则没命。”
“我就是老板。”石头呵呵一笑,“我有经验,伤不到骨头。”
5
“都没见他一面,怪我,我财迷心窍,忘掉了初心。”以为石头睡了,忽然又听他冒出这么一句,像梦话,又像实话。
我示意石头闭嘴。
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追忆,那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却让他不能讲不能诉,我懂这种难受和无奈。但是,人们不都是这样活着吗?包括我在内。
二〇一一年,石头抓住广州购房入户的尾巴,在从化买了房,入了从化户口,石头的儿子也上了广州公立高中。
装修行业的设备、材料、方式、方法,也在一天天更新。比如也许上个月流行的产品,这个月就被淘汰了;前几年的石头洗手台,如今变成铝合金材料的洗柜一体机,全电脑操作成型,轻便、干净、美观;还有电视柜、客厅大堂,原来“高档、大气、上档次”的大理石,现在被说成“有辐射、太笨重”,已经被字画或有田园意味的陶瓷背景墙代替;石材经营方式也花样翻新,网络、网店、微信,遍地开花,实体店举步维艰……总之,石头行业与众多行业一样,面临前所未有的洗牌。
石头变得现实起来。原来补灶台、门槛石或小地板,都义务帮忙,自五年前开始,石头也开始收费,“没办法,工钱、租金、水电都要钱。”
这不,为了省住房租金,石头和石头嫂退掉档口附近的租房,在档口放了张折叠床,“新房在从化郊区,14 号地铁通了,不忙的时候坐地铁住郊区,忙的时候就睡档口折叠床。”
原本,这样也挺好的。可是,今天不能占卜明天的事。
“拆!”
“搬!”
近几年,广州城市升级,石材加工有灰尘、有噪音,属于重度污染企业,不能留在市区。石头知道做石头有污染,可是,他几十年都这样过来了,现在五十岁了,两鬓斑白,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熟悉的地方、熟悉的街坊,时不时地上门客户可以保住日常开销。搬?要搬到哪里去?再说,新搬的地方,会不会又来抓环保?
“老板,合同期还有三年,我们按合同办事,到了时间我保证搬。”石头找到档口老板,希望老板出面,以当地人的身份放他一马。
“老嗮,姆嗨吾姆帮尼啊,是政府。”档口老板一口白话堵住石头,城管叫搬,不是他,他不违约,不退违约金。
石头压根不敢聊押金的事,怕得罪档口老板。可是,老板直说了,“档口要搬,押金不退”。半年押金啊,每月六千,得搬多少石头才能赚到三万六?
“你先做着,有风吹草动提前通知你,但你要有提前找好档口的准备。”石头找合作的城管,城管告诉石头,“环保是不可逆转的。”
“你把屋顶的棚子拆了,拍几张照,上传给我,我们好交差。”城管的话,石头是懂的,石头希望管他档口的人说的话像风,轻轻动一下就好。
想长久就得配合帮助自己的人,石头马上着手拆起棚子来。
石头的石材店其实是没实体房的,四边的石板是墙,石板上方用铝皮搭了个顶,石头只要把棚顶掀了即可。因为拆棚,当天,石头和石头嫂就住在石头棚里,累了一天的石头,用石头嫂的话,“睡得像猪一样”。
“下雨了,下雨了。”半夜,石头嫂的脸一阵冰凉,冷醒,才知道白天拆了的棚顶,雨水撒泼一样倒进来。
“看,他们并没拆,他们还在这!”手忙脚乱中,几束电光刀一样射进来,和着雨水和人声,塞满四面是石头的石头棚。
原来,有村民投诉,说晚上还听到石头档口有切割石头的声音,吵得街坊睡不着。
当晚,石头是没加班的,他忙着拆棚子呢。但是石头不能反驳,因为他平时经常加班,确实打扰过附近居民。
投诉的村民是档口老板亲戚,石头认识,但他假装不认识。生活中,有时的假装是善意,有时的假装是无奈。石头这时的假装,是千头万绪,前前后后,原因立体得没法用言语描绘。
“跟他原来的老板一个样,只知道做事,不管人家,看,现在死了吧!”
石头没想过反驳,搬档口就搬吧,天下这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是,人家说他可以,不能说他老板。
“你老板才死了呢!”
石头做石材近三十年,他打工的唯一老板就是王老板,那个从火车车厢把他拉下来、救了他命的王老板。搬运事件后,石头经历过生意的高峰发展,也到了如今的夹缝求生,石头从老家的农民,变成广州的新市民,石头家族由石头一个老板,发展成兄弟姐妹都是石头老板。王老板的装修集团发展壮大,自己早不管一线,工地都承包给各小包工头,石头不好意思找,怕打扰,怕他有负担。后来,听说王老板去了加拿大,就更没联系了。明明是出国,怎么就死了呢?
“你还在做梦,还想你老板帮你,他都死好几年了!”
石头一下子无语了,跌坐在地板上……
6
活着才是硬道理,命在,一切才在。王老板赚了那么多钱,事业整得那么大,说没就没了。一个人,一张嘴,一米多的身板睡张最宽两米的床,能吃多少?能用多少?能站多宽?能走多远?
石头想通了,走进医院,以刨削的方式,清除了存在若干年的喉腔息肉。
几天后,石头来微信,说读大学的儿子给他家族搞了个石材网店,石头、姐夫、妹夫、弟弟已计划合伙搞大型石材批发,从山东、福建、云南等石材产区进材料,有大工地就让材料商直接加工,他们转手送货。
“呵呵,现在已经谈好一个公园广场的地板石了!”石头以微信语音的方式对我说。令我钦佩又感到惊奇的是,如今,石头做的石头生意,居然跟当下同频共振,毫无违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