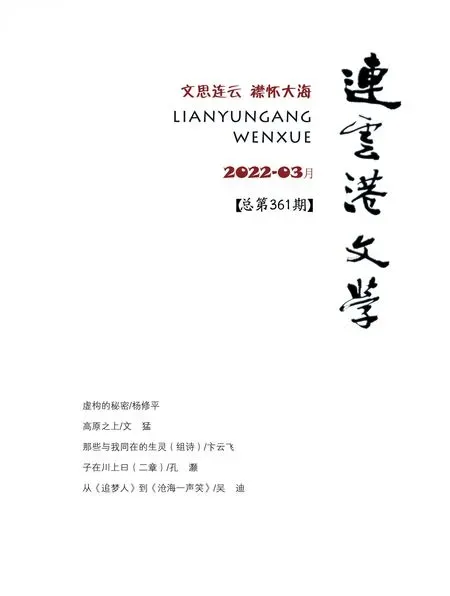葫芦琴
王淑彦
最后一次见到栾志贤,是在大哥的葬礼上。
他斜背着一把葫芦琴,直挺挺地跪在大哥的灵柩前。他已经在大哥灵旁守了三天,有时跪着,有时站着,每日里除了号啕大哭就是不停地拉琴。那琴音,如泣如诉。
我走到他跟前儿,“累了吧,歇会儿。”他抬了抬眼皮,把那双肿胀的眼睛使劲儿睁开,看了我一眼,就又低下了头。
栾志贤倔强地跪着、哭着,拉着琴,一直陪伴大哥到出殡的那天。出殡的日子是四月初十,那天,村里在家的人都来了,送行的队伍拉得很长。他戴着白色孝帽,瘦小的身子勉强撑着半旧的宽大深蓝色夹克,白色孝带在腰间一揽,感觉还算合体。他斜背着那把葫芦琴,胳膊上挎着一个荆条编的篮子,每走两步便向空中抛洒一摞外圆内方的白色纸钱。纸钱在风中自由飘荡,像片片雪花,慢慢落在了大地上。
上午十点,大哥的灵柩被缓缓降到墓坑里。栾志贤红肿的眼睛睁得溜圆,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抢过填土人的铁锹,躬身铲起第一锨土用尽全身气力撒到大哥的棺材盖儿上。那一锨黄沙土砸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让人心中一惊。“大哥,你别冻着。我给你盖上土。等着我,我去给你拉琴。”他扔下铁锹,把手放在嘴边做喇叭状,向着入地的大哥撕心裂肺地呐喊,“大哥,你好走,等我!”。喊罢,他朝着山坡下奔去,一边跑,一边哭,突然,他像一个没有情感、没有生命的木桩子倒在了太行山的黄土坡上。
后来,听说他失踪了。
一
栾志贤,这个名字其实早就被村人遗忘了,大家只记得他叫“傻贤”,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这么叫。最让村人确认他“傻”的就是他年纪一大把了还会到处找爹,见人就问,“我爹是谁,你是我爹吗?”
村里人说,他是个不该出生的人。他亲爹在本村不认他,后爹开始对他挺好,看他越来越没出息,失望了,慢慢就不当回事儿了。亲爹不认,他就不知道谁是亲爹了。
他的亲生父亲叫张宏,长着一张略带梯形的脸,颧骨突出,肤色黄褐,身材魁梧,村里人说他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后裔。张宏的家业殷实,有两处一进院落和五十多亩水浇地。他有一个嗜好,耍钱,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已经把家产赌完了,只剩下了北房三间。在媳妇怀孕出怀的时候,他把家业彻底赌干净了。
那天,栾志贤的母亲正在缝制小棉衣,眼看着窗花,口哼着小曲《四季歌》,心里想着孩子生出来后的样子。她好像怀抱着自己的儿子,看着窗外石榴的情形。生了这个再生下一个。她又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孩子们在树下看石榴花开、摘石榴、剥开石榴喂孩子们吃石榴籽儿的情景。她的嘴角咧向两边,脸上露出笑容,又给肚子里的宝宝唱着“宝贝、宝贝,我心爱的宝贝,娘等着你坐在怀里,慢慢长大,带上弟妹。”想着想着,她突然想起了她的丈夫有半个月不回家了,有些想他了。
“这是张宏家吗?”来了一行五个人。其中还有她的小叔子张利。张利一言不发。
“赶紧收拾收拾回娘家吧,这个房子卖给我们了。”一个人气势汹汹地说。
“你们是谁?”栾志贤母亲问。
“嫂子,我哥又把这处房子赌出去了。他写了休书给你,不要你了,让你回娘家。你走吧!”小叔子张利说。
“你哥呢?”
“找不到他了,他跑了!”
“那不行,见不到他我不走。”
“你不走也得走。”
栾志贤娘辩解着,争吵着。但来的人动开了手脚,连拉带拽把她撵出了家门。还套了辆车,把她抱到了车上。张利拉着她,逼她踏上了回娘家的路。
栾志贤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回了娘家。
栾志贤娘回到了娘家,她盼望着张宏来接她,但迟迟没有等来。她去找张宏,村上的人们说他让赌友领到大西北,再也没有回来。也有人说他死了,说他输光的那天跑到了跳狐峰上寻了短见,从山尖上摔下来,摔死了。狼吃了,狗咬了,连尸骨也没找到。她的小叔子们骂她是扫帚星,说她进门后,把张家妨害了,败家了,还说她没脸回来。
她穿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梳了头,抹上了杏子油,亮亮的,黑黑的,她离开了娘家,到村里拒马河最深的地方,一个叫弯嘴子的山崖上。她的目光望着西山脚下的村庄,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一闭眼,脚下就失去了平衡,扑通一下掉进了河里。
一个在河边草地上拾粪的老头救起了栾志贤娘,找来了村里的媒婆说和着把她嫁给了自己的儿子栾孝祥。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汉子,成了她的第二任丈夫。
栾志贤娘不想留下张宏的种子,推碾子的时候用力在碾棍上压,睡觉的时候趴着睡,还用手往下推高高鼓起的肚子,在炕沿上压肚子。可不管用什么方法,栾志贤都在她肚子里安安全全的呆了九个月,顺利降生了。生下来五天,他也不睁眼。栾孝祥的父亲上过私塾,为这个孩子起了个有意思的名字,栾志贤。
栾志贤家住在栾家胡同最东头,五间北房,三间东房。北房西侧有棵木槿树,树的南侧有一架葡萄。爷爷并不反感这个孩子,他想,木槿开花晚,花期长。这个孩子睁眼晚,但也许是最聪明的。我死了,有人续香火了。可栾孝祥不愿意养一个傻子。
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栾孝祥的父亲就去世了。门口戳着的白色样榜(实际就是一个简易家谱)上,老爷子有了孙子,栾孝祥的名字下面多了栾志贤的名字,圆了老人传宗接代的梦。
栾志贤从学会说话后,一直也没有把话说利索过。他能听见,能说话,但声音有些弱,还能想事儿,就是慢吞吞的。虽不是特别傻的那种,但上了一年学,也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其他的都没学会,不得不辍学游荡了。
二
我大哥本名王振林,因为排行老大,大家都叫他大振。身为长子,整个王氏家族都对他寄予厚望。大哥小时候长得快,比同龄人高很多,但是体格高挑,身子有些瘦弱。大哥后来长成了一米八的大个子,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杏眼长眉炯炯有神。他是当年村里同龄人中学历最高的人,也是家里唯一一个跟父亲学过二胡,能拉几首曲子的人。初中毕业后回到村里当了生产队的记分员、保管员、大队会计、兵工厂的车工、粮站的保安,直到65 岁才居家养老。这一辈子却有一个永远也弥补不了的遗憾,终生未娶,光棍而终。
大哥出生的时候,爷爷戴着个瓜皮帽子,对着曾祖父喊道,“你要当老太爷了,咱们家四代同堂了!”曾祖父有些耳聋,“你说什么?是个重孙子。起名了吗?要是没起名,就叫他振林吧。让他带个头,振兴王家祖业,兴旺家族人丁。给村里,给大伙做点事儿,做个帮助别人的好人。”曾祖父连想都没想,要是生个丫头咋办呢?
在王家胡同里,四个院落,有二十间瓦房,每五间一个院落。每个院落,有北房、南房和东厢房,分别住着爷爷、二爷和三爷。曾祖父和三爷住在中间的院落,爷爷及父亲住在东边的院落。母亲很争气,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小子,实现了爷爷们的愿望。1942年出生的大哥,在家境虽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去的家庭中成长着。叔叔伯伯爷爷奶奶们都宠着他,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刚刚两岁,爷爷用筷子蘸着酒,给他嘬。母亲提醒爷爷,不能惯着孩子,爷爷反驳道,“男人就要有男人样。不喝酒,哪叫男人!”母亲无奈。长大后,大哥有些软,不强壮。可他遇事不服输,什么都往前做。母亲对他说,“知道人们为什么叫你大振子吗?你祖爷希望你能帮助别人,别光顾自己。要帮助别人。”
大哥二十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望着七个弟妹,他仰望星空,看到了天空上勺子状的北斗七星,他心里想,七个弟妹,要凝聚在一起啊。生产队需要劳动力,家里也需要劳动力啊!他难以忘怀父亲去世前的情景。
临终前,父亲把大哥叫到跟前,做着最后的嘱托。“大振啊,我走后不担心别的,我就怕咱们这个家散了啊。你是老大,这一排七个兄弟妹子就靠你娘难以养活啊!你得帮着你娘,多干活,多挣工分,把这兄弟姐妹们拉扯大吧,咱们家不能散呀!”
“爹,你放心吧,咱们家不会散!有我呢!”
“咱们家那些乐器也没有教会你们用,谁要想学,你就给别人用吧。笙、箫、锣、叉、二胡、云锣、长管、短管,那是音乐会的家什,保管好,有需要的人,可以让他们用。看你对二胡感兴趣,也没有好好教你。这辈子不行了,下辈子,我一定教会你!”父亲说得激动了,咳嗽了起来。大哥拿来罐头瓶给他接了一瓶子白沫。他的下颌碰撞到了胸骨,使劲儿呼吸着。
父亲走得太早了,留下了太多牵挂。他惦记他的孩子们,更惦记他未竟的事业,惦记他的音乐。
父亲走后,邻村的朋友们取走了乐器,大哥留下了二胡,虽不能说学会了拉琴,但也时常模仿着拉些简单的曲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知半解吧。也由此,大哥和栾志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
葬礼上,栾志贤拉开琴袋儿的拉锁,取出一个长方形三合板做的盒子,又从盒子里取出了一个用绿底牡丹花被面包裹的一把琴。人们瞪大了眼睛。“栾志贤,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把琴么?”栾志贤没说话。他抬起头,看了看周围,把手放在布的一角,准备打开,他又把手缩回来,大声喊着,“大叔,我把葫芦琴拿来了,你看看吧,还新着呢。我自己邋遢,葫芦琴干净着呢!”说完,他又是一阵大哭。
当家的嫂子们、村里的叔叔伯伯劝他,“贤哪,别难过了。他走了,活不过来了,他也不管你了。你要是真想他,你看主家有啥活不,你帮着干点儿活,也算尽孝了。别哭了,越哭越伤身体。”
栾志贤是不能劝的,越劝越伤心,越劝越出来那个“傻”劲儿。“你们懂啥呀。别说了,一边儿待着去。”劝他的人也很识趣地离开了他,换了地方,陪着逝者。农村讲究“活着没人儿,死了一群儿。”大家聚在一起,不用说什么,不用做什么都是对逝者的尊重与思念。特别是得到过世者帮助的人,更是守灵陪伴。陪灵的人看着栾志贤,搭着话儿,“傻贤不傻,分得清好赖,以后不能叫他傻贤了。”
栾志贤把琴袋挂在了灵棚的柱子上,打开了包布,把琴放在了棺材盖上,又把包布掖进了琴袋里,还说了句,“谁也不许动我的,谁拿了,我就让大叔打你们。让我四奶奶捉你们去。这琴袋是我四奶奶给缝的,谁也不许偷。”他在草褥子上坐直身子目视灵柩,双手合十默念着。不爱洗脸的栾志贤,脸上伴着泪水,一道儿一道儿的。可那份面容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仪式感。默念之后,他站起来,拿着他的葫芦琴走到灵棺头前,拿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把琴箱放在腿上,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松香,擦着琴弦,正面擦了,反面擦;竖着擦了,放平擦,认真仔细的样子。
村人都很惊讶:
“贤哪,这就是你做的那把琴啊。还真是一把琴,像二胡,能拉出曲子来吗?”
“那不就是二胡吗,还像什么?”
“琴是琴。人家的二胡是木头做的,他这把琴咋是用葫芦做的?拉不响吧。”
栾志贤又站起来,在灵前鞠了个躬:“大叔,我给你拉个你最喜欢听的《东方红》。”
随后,一首《东方红》的乐曲在村里响了起来,那声音瓮声瓮气的。沉闷的空气中,洒下了缕缕阳光。太阳照在了头顶上,正午十二点了。
四
大哥和栾志贤的友谊,最初是因为同病相怜。大哥因为高挑体弱又白净,村里的嘎小子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白薯。为此,大哥生了不少气,吓唬这些孩子们不知多少次,很受伤害。停止叫他的外号还是因为大哥找到他们的家长,有的家长们训斥,有的家长们体罚,这些人才告一段落的。
栾志贤没有大哥的影响力,不是起个外号就完了,嘎小子们捉弄他欺侮他,栾孝祥也不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爱咋叫咋叫吧,他是不会护着栾志贤的。有一次,四五个被村里人称作“五害”的坏孩子正在欺侮栾志贤,恰巧让大哥碰上了,他连忙上前制止,从此栾志贤一步步向大哥靠近。
村上有大家公认的“五害”,那是五个所谓的“坏孩子”。那时在搞除“四害”,大搞卫生运动,孩子们互相起外号,说来也巧,这五个孩子叫作:李章郎、谷洛曙、李家巧、刘大臭、李苍鹰,活活对应上了“蟑螂、老鼠、麻雀(俗称家巧)、臭虫、苍蝇”,几个孩子发现这个谐音时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那个时候,他们内心美的程度不次于小孩盼望一年,到年底杀了猪,吃上肉的那种美。在寂静的山村里,能有个新发现,用现在的话说,脑洞大开,那是再美不过了。发现了每个人身边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儿。那种美比今天玩手机的孩子还美。他们可以一起胡侃滥说,可以你捅我一下,我摸你一下。你一拳,我一脚,有着肌肤接触,快活、亲切。于是,这几个外号也就叫开了,村里人把他们连在一起,叫“五害”。这几个从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不等,整天在一起腻乎,干了不少欺侮栾志贤的事儿。
戏楼院儿是村子里的一个聚会场所。戏楼改成了学校,需要演戏的时候就把课桌搬到一边儿,拆开前面的挡板儿就可以当成戏台了。戏楼院既是孩子们的操场,也是村里人的聚会场所。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大家都聚在那里,聊天儿,是全村消息的传播源。看着一张张体育成绩单贴在墙上,“五害”们你一言我一语又起了外号。
“栾志贤,10 分。怎么能考10 分呢?”蟑螂念着。
“牛丫丫,90 分”,这是百分制,可不是十分制啊,“栾志贤怎么能考10 分呢?”臭虫摇摆着脑袋分析着。
“傻呗,苶呗”,另一个没外号的孩子插着话。
“痴呗,呆呗,不就是傻呗。栾志贤,大傻贤。”“老鼠”叫喊着。从此栾志贤的名字,逐渐被人遗忘,傻贤的名字给叫开了。
“麻雀”又有了新发现,他把丫丫两个字认成了“了”字,他念着“牛了了,90 分,”了不起一个丫头片子,能考90 分,牛了了,真了不起。从那会儿,一个扎着小辫子的丫头,就被他们叫起了外号。从那个名单上,“五害”们发现着,思考着,一个个坏点子,坏名字就出来了。
最冤枉的就是大哥了。那会儿,他已经从本村的初级小学,邻村的高级小学毕业,到镇上的初级中等学校读二年级了。他到戏楼院找母亲的时候,正好碰上孩子们起外号。大哥看不下去了,吓唬了他们几句:
“兔崽子们,回家看书学习去。给别人起外号多没教养啊!没事儿,去大队拿张报纸给大家念。”孩子们不光不听,还嗷嗷地叫起来了。
“蟑螂”叫着,大叔,你的皮肤真白啊!咋也晒不黑呢?
“苍蝇”嗡嗡着,“他天天上镇上上学,早出晚归的,太阳晒不着呗。”
“老鼠”说,“其实也不那么白,他的脸色就好像俺们家白薯,白里透着黄。”
“那就叫白薯吧。他个子大,就叫大白薯”,“麻雀”叽叽喳喳着。
大哥随手拾起一块儿石头,“我拍死你们!看你们谁敢叫我,四六不懂的东西们。再让我听到你们叫人外号,我就把你们几个捆起来,交到派出所去!”
在一旁聊天的大人们也站起来,走到孩子们中间,训斥着那一帮坏孩子。坏孩子们散开回家了,一串串外号留下了。
大哥的外号只是背着叫叫,不敢面对大哥叫。栾志贤的命运没那么好,总是受到坏孩子们的捉弄与折磨。
那“五害”集体遇到大哥的时候,会齐声喊:“大叔,吃了吗?”这是一句问候语,相当于现在流行的问候语“你好”的意思。“大叔,你忙着呢?”那是友好地,亲切地打招呼呢。那个小山庄,在那个年代不会说,“你好!”“早上好,晚上好”等礼貌用语。人和人打交道,问候的语言就是问,“你吃饭了没有?”在粮食紧缺的岁月,问“吃饭没有?”也算是最大的关怀了。
集体见面,礼貌地、体贴地问候,“五害”们是鼓足了勇气的。单独见大哥的时候,都是溜着墙角走,把大街的中心让给大哥以示尊重。会响亮地问候大哥,或者干脆只叫一声“大叔”,就加快脚步跑掉了。他们怕大哥,不是大哥会打人,而是怕大哥找他们家长去理论,因为他们知道大哥是初中生,说话讲道理。
栾志贤就不那么幸运了。问候栾志贤是为了拿他发坏,拿他取乐。
“栾志贤,你吃了呗?”“老鼠”打头问着,
“没有。家里还没做熟呢。”
“我们几个请你吃顿饭吧!”“蟑螂”掏出几个小爆竹和一个二踢脚,拿在手上。
“我不吃你们的饭。你们不干好事儿,总是捉弄我。”
“你过来,我这里有块棒子面干粮给你吃。不过,你得叫我一声爹。”“苍蝇”嗡嗡着。
“我凭什么叫你爹。我有爹!”
“他是你后爹,不是你亲爹,你知道你为啥这么傻吗?你不是亲生的,你是带犊子,你根本不是栾孝祥的种儿。”“苍蝇”鼓噪着。
栾志贤有些听不下去了,好像也听不明白了。骂了一句村上的人常骂的一句话“我×你姥姥。”“蟑螂”上前,捏了一下栾志贤的脸,“别骂了,知道你饿了,“苍蝇”听说你爹不让你吃饱,光给你吃稀粥,不给你干粮吃。“蟑螂”心疼你,给你拿干粮去了。饿不,叫他个爹,他就给你吃了。你怕啥。”
“我不叫,我怕我爹打我。”
“不叫?要不,你用我这个爆竹把那堆猪粪炸飞,我就给你吃这块干粮。”“蟑螂”在手上拿着一块玉米饼子,金黄金黄的。饼子一面是烙渣,一面是手指拍过的手指印,“蟑螂”引诱着栾志贤,在旁边出着主意。说话的时候,脸上一副得意的样子,一条腿晃荡着,另一只手托着那块饼子。
栾志贤慢吞吞地把手从棉袄的袖口里伸出来,袖口油光光的,手上长了皴。“老鼠”嚷了句,“我们说话算数,快出去崩粪,崩完了给你吃。你看你的爪子,像那堆猪粑粑那么黑。你可别把你的手当猪粑粑给崩了。”
“别听他的,快去吧,你的手不黑,去了给你这块黄金棒子干粮吃,可甜了,放糖精了。你知道皇上叫这饼子什么?叫黄金塔。”“苍蝇”引逗着。那块黄灿灿的干粮,看上去比手巴掌小一点,吃到嘴里,就是看着也感觉到甜丝丝的味道,别说是栾志贤,就是那几个被叫成“五害”的坏小子,也都咽着唾沫,砸吧着嘴巴,胃里也在使劲儿抽动着。
“我去崩了猪粪,你们就给我棒子干粮吃。你们不能说给我爹,他老打我。你们也不能说我爹是后爹。他是我亲爹,我可不能叫你们爹。”
“他不傻呀,他能想出这么多事儿呢。”“苍蝇”给他这几个小哥们议论。
栾志贤拿着小爆竹和二踢脚走向了一堆猪粪旁。爆竹其实就是集市上卖的那种挂鞭,有100 头儿的,也有500 头的,还有1000头的那种。看样子,是100 头的那种,一头就是一支,个头比二踢脚小三分之二的样子。过年的时候,家长们买来爆竹,要把一挂鞭的爆竹一个一个解开,再分给孩子们一支一支的放。放着不过瘾,可孩子们多,人人都有份,大家也开心。过年的爆竹三十晚上分了后,怕受潮,藏在炕席底下,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孩子们会放半个月的炮。有的孩子,还拉长了战线,放到二月初二。这个潘苍鹰,把放炮做成了游戏,做成吸引小伙伴们聚在一块,寻找快乐的恶作剧。只是这次游戏做大了,还惹出了祸端。
村里人养猪爱放养,那些猪们大的、小的,老母猪、食肉猪在家的院子里或是猪圈里喝饱泔水后,就大摇大摆地去街上散步,听人们唠嗑,有时候还掺和到人们的谈话中,发出哼、哼、哼的对话声。大街上的猪粪多了,栾志贤就会挎上个篮子,拿个羊铲,每天拾粪,对猪粪,栾志贤很熟悉。栾志贤把爆竹和二踢脚插进粪里,外边露出了炮焾儿,“苍蝇”一手拿着干粮,一手伸出个指头,指着栾志贤,“往下按,要不崩不起来,往下按,往下按。”旁边的人也命令着。
栾志贤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摇晃着走进粪堆,接过“蟑螂”的火柴,先点着几支长炮焾的小爆竹,又点燃二踢脚的短炮焾。栾志贤看着二踢脚的短炮焾,还嘟囔着。
“炮焾忒短,不好点!”他往前探着身子,把火柴上的黄色火苗使劲儿与炮焾相接。他的手抖着,心里害怕极了。就在他心里揪到一起的时候,一支支小爆竹响了,炸起了猪粪,二踢脚也响了。第一响擦到他的脸庞,连粪带炮皮、火药崩到了他的脸上、眼上,飞向空中的第二截儿斜飞到了墙上,又在空中炸响了。
栾志贤什么也没听到,只感觉眼睛看不见了,脸上疼得厉害,“五害”们吓跑了。
五
听到街上乱作一团,大哥放下正在吃的玉米菜饼子和刚到嘴边的粥碗,迅速跑到了街上。
他看到受伤的栾志贤,骂着,“兔崽子们,又干坏事儿。小心我来收拾你们。”看到他脸上、身上的猪粪,问,“栾志贤他爹呢?你们帮忙,把他放在我背上,背到我家,让我二兄弟给他治伤去吧。”在村里大人的帮助下,大哥和乡亲们把栾志贤背到了我家。母亲急忙拿来脸盆、毛巾擦洗手和脸部的炮灰、猪粪,二哥拿来生理盐水为他冲洗。大哥揪心地问,眼睛瞎了吗?
“还好,没有伤着眼球,只是眼睑、眼眶受了皮外伤,养几天就好了。”二哥给栾志贤做了眼部包扎。
母亲又烧了热水,让栾志贤躺在炕上,头朝炕沿的方向,给他清洗着头上的粪便、污泥。
栾志贤的脖子、手臂上到处都是泥皴,母亲说,“你这是多少年不洗吧。”大哥说,“他夏天还去耍水呢,没有多长时间不洗,不太脏。”他给母亲解释。
栾志贤爹赶来的时候,栾志贤已经洗好头。看着一只眼睛肿起来,另一只眼打着绷带的儿子,他蒙了。“我的儿啊,你咋了?瞎了吗?这是谁欺负我们了,我找他们算账去。他的拳头在空中飞舞着,眼睛没看栾志贤。他看着乡亲们,好像求援似的。
乡亲们都劝他,别闹了,也不看这是在哪儿。要不是大振及时把他背这里来,王先生(当时村里把医生叫先生)及时给他处理,不瞎才怪呢。你咋不让他吃饱?吃饱了,他还会为个棒子干粮跟那“五害”们在一起吗?大家指责着他。有人问,“他娘呢?”栾志贤爹低下了头。
栾志贤娘弄着仨丫头在家着急呢。从生了栾志贤后,栾孝祥一直想生一个自己的儿子,没承想,连续生了仨丫头。生了第三个丫头还在坐月子呢。生产队挣工分少,分到的粮食自然就少。不只是栾志贤吃不饱,全家粮食都紧缺。
母亲端过来一碗粥,一勺一勺地喂栾志贤。说是小勺,其实就是小葫芦,特别小的那种,也可以说是袖珍亚葫芦,从中间横切面切开,把内瓤刮去后,再上锅煮一煮,就是极好的勺子了。母亲一边喂粥,一边把菜干粮掰开,掰碎,一块儿一块儿地送到栾志贤嘴中。乡亲们在不大的屋里聊着天,栾志贤也就吃饱了。
正屋里点起了煤油灯,哥哥姐姐们去了东屋写作业。母亲催促着,“贤哪,回家吧。你娘等着你呢。”栾志贤一动不动。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开了一个小缝,发出了微弱的“娘”的声音,好像从鼻孔里送出来的声音。栾孝祥拽了一把栾志贤,“回家吧!”他感觉栾志贤很沉,拽不动。又过了一会儿,大哥拉着栾志贤的手,“贤哪,快睡觉了,我送你回家去吧,大家都该睡觉了。”
大哥拉起栾志贤,他的腿很沉,像绑上了沙袋,一挪一挪的。走出大门口,是用河石铺成的一个斜下坡,再往左上方走,又是一个四十多度的大斜上坡。栾志贤脚下一歪,扑通一声跪倒了。大哥和栾志贤爹一人架着他一只胳膊,拉起他。可他的腿像瘫了一样,站不起来,嘴里喊着,“大叔!”
大哥蹲下来,脸朝坡道下方,“孝祥哥,你把他扶到我背上,我背他回去吧。”栾孝祥说,“造孽啊,我咋有你这么个傻儿子。”他把栾志贤转过来,把他的双手搭在大哥肩上,在后面使劲儿往大哥身上推,也许是惯性的原因,大哥被栾志贤压趴下了,大哥在下面,栾志贤在上边,大哥的手和脸都被擦破了,手上的血滴在地上。栾志贤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邻居听到声音后跑出来,把栾志贤送回了家,大哥也回到了家里。
从那次做坏事儿之后,“五害”好长一段时间内,不在一起聚了。听说是学校的老师罚他们站了,也听说是他们的家长打自己的孩子耳光子了。更听说是大哥训他们了。也有人说,大哥警告他们要是再欺负栾志贤就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让他们坐监狱。还有人说,大哥把他当警察的同学请来了,穿着警察制服,把他们几个集中在生产队的办公大院里训了一大阵子。说是,再犯这样的错误,真要让他们坐卡车,戴手铐,全县游行,再去坐大牢。究竟是什么,后来大哥说过,他的同学是警察。“五害”最怕的是犯法关禁闭,坐监狱。还有人说,“五害”是被真“五害”附体了,要继续欺负栾志贤,他们就变成真五害了。
栾志贤问栾孝祥,“你是我亲爹不?咋他们说我不是你的儿子,还叫我带犊子呢?”栾孝祥毫无耐心地回答,“我养你这么大,还不是你爹了?白眼狼!”两个人的对话不顺畅,栾孝祥动了手,打了栾志贤,“再问,我还打你,让你记吃不记打!”“你亲爹是我,记住了么?”
听说,后来栾志贤去找他亲爹了,栾孝祥把栾志贤吊在门框上狠狠打了一顿。后来,栾志贤真的傻了,一句话也不说,谁问也不说。他憋在家里,再也不愿意走出家门。
大哥惦记着栾志贤,去看他时,他望着大哥一个劲儿地流泪,就是不说话。“贤哪,你能说话了吗?”栾志贤不语,不摇头,也不低头。但从他的眼神里感觉他能听见人们讲话,也能看到人们在做什么,他在用心观察着世界。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如果能听见,你就点点头。”栾志贤还真点了点头。“那我说,你听着,我说对了,你就点头,行不?”
栾志贤点了点头,一把抓住了大哥的手,抱住大哥呜呜地哭了起来。是感恩?是惊奇?是害怕大哥离开,谁也不知道。
大哥感觉到了栾志贤心中的痛苦,也感到了栾志贤对大哥的愧疚。环顾这个家,北房五间,东屋住着他爹娘和三个妹妹,西屋就栾志贤一个人,一个炕席破了一个大洞,炕上有一条粗布被子,地上一双破鞋,再也找不到其他物件。东房是这家的库房,农具放在里面,还有两口大缸,里面盛满了腌菜,还有一个用荆条编成的长方形粮囤,里面放了半囤玉米,看上去也就七八百斤,那是这个家庭一年的口粮。得再吃八九个月才能接上新粮食。平均到一个月里,也就一百来斤粮食,五六口人要分到每个月里吃,没有吃干粮的份儿,只能配上些瓜瓜菜菜,一天天挨过去。遇上不会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前半年吃干的,后半年就得喝稀汤寡水了。
大哥问栾志贤,“你能走出去吗?我陪你转转去。”栾志贤蹦出几个字,“粪、炮、炮、崩眼,瞎了!”说不出连贯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崩出来,也不太清楚。但是大哥明白了栾志贤怕出门的原因,是被吓怕了。栾志贤娘对大哥说,“他天天晚上哭,吓坏了。让他出去也不出去。”大哥一脸茫然。
大哥想起了父亲去世的时候,自己曾在棺材前拉了一段二胡,声音嘶哑,吱吱啦啦的,比哭还难听。可那时候,栾志贤站在他旁边,一动不动的。停下来的时候,栾志贤去摸了那把二胡。大哥灵机一动说,“贤哪,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二胡去,回来给你拉一段《二泉映月》,行不?”栾志贤面部除了哭的泪水的痕迹,没有表情。大哥跑回家,拿出了那把二胡,急忙跑到栾志贤家。大哥掏出二胡,坐在炕沿上,“我给你拉东方红,喇叭里放的那首曲子,你每天都能听到的。”随着东方红乐曲的响起,栾志贤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不是喜欢二胡吗?你要了我这把二胡吧,我教你拉。”
栾志贤摇摇头。“你不喜欢?”栾志贤摇摇头。“你喜欢?”栾志贤点点头。“你舍不得要这一把?”栾志贤点点头。“那咱们就做一把!”栾志贤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那就做一把。”大哥说。
栾志贤点头了。大哥找了个碳块,比着二胡把图形画在了墙上。看着栾志贤的脸舒展了,他才起身回家。又过了些日子,大哥去看望栾志贤,告诉他学校唐老师有一把二胡,就在老师的墙上挂着。他想把栾志贤从痛苦中拉出来,让他走到大街上,和人们在一起。学校就是戏楼,要去学校必须经过戏楼院,走到戏楼院的时候,栾志贤就哆嗦起来。他怕差点把眼珠子崩走的地方。“贤哪,不怕。那“五害”不敢在一起了,他们不敢欺负你了!千万不要想了,把那个事儿忘了吧,咱们去唐老师那里看二胡去!”
全村只有两把二胡。一把是唐老师的,一把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栾志贤拉着大哥的手,走上戏楼一侧的小房子。从窗户的玻璃上望去,就看到了那把二胡。栾志贤扒着窗台,抬着脚跟儿,给大哥指了指,嘴角朝两边咧了咧,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是栾志贤被欺负后第一次走出家门。栾志贤做了个异常的举动,他拉着大哥朝村南头走,又从村南街转向东走过去,径直闯到张宏家。巧的是张宏还在家,看着急急忙忙闯进来的他们俩,问,“大振,有事么?”
大哥还没有接话,栾志贤一下子跪在地上,嘭嘭地磕起头来。张宏忙上前拉住,“贤哪,咋啦,快起来。”这时候,只听栾志贤哇哇大哭起来。也许是被羞辱太久了。也许是一直以来,自己还包在纸里,一下子火焰烧破了那张纸,或者那张纸被捅破,十几年的委屈一下子爆发出来。张宏把他拉到跟脚台上坐下来,张宏媳妇也从里屋出来,“这是咋了?”她盯着眼前的这三个人。
栾志贤好像是怕失去张宏那双手似的,使劲儿地攥着,他的嘴张开又闭上,闭上又张开,他长出了一口气,用力喊着,“爹,我爹。”只是他的话是一字儿一字儿蹦出来的。
大哥好高兴啊,“哎呀,贤哪,你会说话了!”
栾志贤五岁那年,张宏从大西北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还领着一个女人,听说是在西北娶得媳妇。张宏用从西北倒弄牲口挣得钱,又从当年的赌友手里赎回了那几间房,重新安家了。
栾孝祥心里很不是滋味,既怕张宏认儿子,又想让张宏把傻儿子领回去,很矛盾的心理。后来张宏也生儿子了,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张宏也没打算认栾志贤,栾志贤确实不聪明,谁养活他,都是个累赘。吃得多,挣分少,还傻了吧唧的。慢慢张宏对栾志贤从关注到了怠慢的地步。栾孝祥对栾志贤是不在乎的,不闻不问、吃饭限量。挑水,拾粪,捡柴火是他每天都要做的活计。栾志贤也感到了自己不被人待见。知道人们都说他是张宏的儿子后,他也就想方设法地去认爹了。
张宏媳妇嚷起来,“哪里来的傻小子,跑这儿来认爹了,滚出去!我这几张嘴还养不活呢,跑这儿认爹来了。”她破口大骂张宏,捎带着骂栾志贤。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大哥赶紧拉着栾志贤往外走。张宏追到街上大喊,“大振,你可别跟别人说,别告诉别人,丢人哪。”
大哥把栾志贤送回家中,栾志贤又陷入了不言不语。大哥去过他们家好多趟,栾志贤都很冷漠,没有表情。
六
自从栾志贤认爹不成后,大哥也渐渐地寂静下来。他后悔那天没有制止栾志贤去认爹。母亲说:“该帮的就帮一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大哥想了几天,把家里的药葫芦分出大中小几组,捡每组最好的一个送了过去,顺便还把二胡带给他。出乎大哥意料的是,栾志贤只留下了三个葫芦,把二胡贴在他睡觉的屋的墙上,学着大哥的样子,在大哥上次画的二胡旁边,又用烧黑的木炭画出了二胡的形状,还特别把琴桶的六边形、琴柄在墙上画了特写。起初,大哥也没有理解他想干什么。他为什么没有留下这把二胡?画完后,他咧嘴笑了。
自那以后,栾志贤对小喇叭里的乐曲留心起来。早晨播放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晚上结束一天广播时唱的是《国际歌》,他认真听着。中间放样板戏的时候,他也支棱着耳朵。谁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
第二年,他在木槿树前边的葡萄架旁洒下了葫芦种子。种子开始发芽了,出蔓了,爬上葡萄架了,他每天都去观察,慢慢地,脸上的愁眉苦脸不见了,开始说一句半句话了。他问,“娘,我爹是谁?”栾志贤娘说,“别问了,你爹是你爹,天天守着还要问。再问,我把你的葫芦拔了。”栾志贤怕娘拔了他的葫芦,还真不问了。家里的人看他不那么郁闷了,都让着他,对他种的葫芦还挺照顾。那葫芦还真挺争气的,长了一架。葡萄和葫芦在一个架上,葡萄开花早,在五月份就开出小穗花了,一串串的,像小蝌蚪,黄绿黄绿的。葫芦七月份开出白色喇叭形状的花。栾志贤扭着脖子,侧着脸端详着,“白白的,像喇叭,真好看!”他自言自语。在这两个月里,栾志贤总是在葫芦架下,左看右看,蹲下起来,伸头看着。
葫芦开花后结果了,他又忙碌了起来。忙着比照墙上的二胡琴箱做个六角形的壳子。他把模板准备好,找村里的木匠做了个六面体,顶部不加盖,直接把药葫芦装进去。只是等拉秧摘葫芦的时候,他装在壳子里的葫芦烂掉了,并没有变成六面体。
种了两三年的葫芦,他在等待跟墙上的音箱差不多的葫芦出现。这一年,他还真选出了几个葫芦,底部是长球形的,没有变成六角形,大小跟墙上画的六面体差不多,栾志贤把它放在阳光下晒着,拿玻璃片刮去葫芦皮。再次比照琴箱的长短画上印迹,让木匠师傅锯掉葫芦头部分。上木匠那儿要来清油,反复涂刷,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刷了多少遍,谁也不知道。几年工夫,他做出了圆滚滚的琴箱。
七
种葫芦的快乐,打开了栾志贤说话的闸门,他说话的功能慢慢恢复起来。村里的人们在聊天的时候,提起栾志贤,也多了不少新的话题。
大哥带他上山打柴,栾志贤的爹娘对大哥也心存感激。“大振啊,是你救了我的傻儿子,老天会报答你,让你娶个好媳妇,子孙满堂的。”说完,他们双手合十,向天祈祷。
到了娶媳妇年纪的大哥依然没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村里的闺女,不是没有对上眼的,只是他没有时间考虑。他得下地挣工分,晚上记工分。村里放假休息的时候,得上山砍柴。再看排成一队的七个弟妹,小的三岁,大的比自己小两岁,哪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事儿啊。
他领着栾志贤,领着临街一位比自己小三四岁的姑娘秀儿上山了。山上的灌木、百草成了他们收割的对象。那些开着紫色花的荆棵子,高高的黄皮草,细细柔柔的白皮草都是柴火的材料。村民们的燃料主要是收割庄稼后的秸秆,修理树木后砍下的树枝,这些都是不够用的,就得上山割柴火。人们从离家近的山走向离家远的山,三五成群,沿着崎岖小道走向大山深处。没有人领着,是不敢单个人往深沟里走的。栾志贤别说割柴,就是走着也走不快,可他特别愿意跟着去。李秀儿也特别愿意跟着大哥。柴草割下来,一捆一捆得收敛在一起,一根绳子铺到地上,再把柴草装成垛,捆起来背在背上,这些活儿都是大哥完成的。遇到难走的地方,大哥先把自己的柴草背过去,再帮李秀儿背过难走的路段,大哥成了李秀儿的靠山。
栾志贤跟着大哥还另有所图。他割上两三捆柴草后,他就慢慢爬上山旮旯,寻找六导木去。六导木是一种落叶灌木,在深山里的斜坡、沟谷里。黄色的、白色的、浅红色的花冠,椭圆形的叶片深绿深绿的。叶片边上还长着毛刺儿,像人的眼睛睫毛眨动着。栾志贤的哪一根神经被长长的绿叶、香香的鲜花给激活了。他对着离他不远的大哥喊起来:
“大叔、秀姑你过来!这里有棵大树,这花好看,你们没见过。”他喊着。
“大叔、秀姑,我下不去了!快来救我。”
大哥和秀儿的回声,他没听到。他吓唬着他们,顺手摘下了几片叶子,几朵小花。心里窃喜着。
他又喊起来“大叔、秀姑,快点救我来,我要掉下去了!”
大哥和李秀爬过来之后,他在一丛六导木边上坐着,露出了笑容。“大叔,你看这片叶子,细长细长的,像你”他把叶子拿起来,让大哥看。“秀姑,你看这花,好看,你像它”,说完,他站起来,把花交到大哥手上,把叶子放在李秀手上。
“大叔,你把花给秀姑戴上。”
“秀姑,你把叶子送给大叔”,他命令着这两个割柴人。大哥和秀儿对视着。大哥看着李秀儿。
“秀儿,谁说栾志贤傻啊,你明白吗?”
“这叫换定。我看咱们村的人,订婚的时候换手绢。这一片叶子,一朵六导花就代替手绢了。你们订婚了”栾志贤说。
李秀儿望着大哥,脸色比那朵粉红色的花儿颜色还深。
栾志贤把大哥和秀儿叫上来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献花和献叶子。他在找树干上有六个凹槽的灌木。
他曾请教过我母亲,“四奶奶,你们家胡琴上的那个把手是用什么做的?那个琴杆是什么做的?”
母亲告诉他,“听你四爷说,是紫檀木做的,那个琴筒也是紫檀木做的。上边那个叫琴轴,不叫把手,我问过,就跟家里的门一样,是用来调音的。琴筒那边的皮是蛇皮,也有蟒皮的。蟒皮的贵。”
“蛇是长虫么”
“是。”
“哪找紫檀木去?”
“咱们这儿不好找。听你大叔说你要用葫芦做二胡。要做着玩,就用六导木吧。那个木头瓷实,也好找。”母亲虽是家庭妇女,可她实干,给父亲打过下手,为村里的音乐会做过服务工作。
“哪去找六导木啊。”栾志贤问。
“跟你大叔割柴火去,山里有。”母亲在引导他走出家门,学会干活。
母亲叮嘱大哥,“栾志贤要找六导木,你可别让他自己砍去,他笨,别让他摔下去,你帮他砍几根。”大哥理解了栾志贤的意图,“你要几根,我给你砍。这个可不好砍,硬着呢。”
“我做二胡那个杆儿,还有把手。对了,我四奶奶说把手叫琴轴。多砍几根儿,我怕一次做不成”
大哥把最高的三根砍下来,一根有两米多高。
栾志贤没有背回柴草来,却扛回了三根六导木。
六导木是密实的。直接剥皮、晾干,颜色发白,也缺乏弹性,为了防止六导木出现开裂,大哥和栾志贤点上火,把六导木烤在上面,一边烤、一边移动位置。烤热了,烤出汁液再把六导木皮刮掉,六导木就从白向黄红的颜色慢慢转变。一根没有颜色的灌木就变成了一根神奇的艺术品。
八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解散了。
大哥和栾志贤不能像在生产队时那样天天见面了。但是他经常到家里来。
“四奶奶,从哪里买种子?大叔,你去买化肥时领上我。”他成了大哥的随从,大哥干什么,他干什么。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找蛇皮、马尾鬃,松油子,继续做他的琴。蛇皮还是“五害”带他去找来的,只当赎他们小时候犯下的错。马尾鬃是大哥找村上的放羊人,求他从放羊人骑的枣红马尾上揪的,慢慢攒了几十根儿,做了琴弦。松油子是大哥领着栾志贤上松树坡上找那一棵古松上涨出的松疙瘩里剜出来的。松疙瘩(当地人都这么叫)是在松树干上、树杈分枝的地方流出来的松油子,分泌多了就像个瘤子一样。他们俩把疙瘩剜下来,或者头年在老树皮上用刀划个“V”字形的裂缝,让松油子从那儿分泌出来,第二年再去剜。挖出来后上锅熬,把杂质分出去,倒在方形的铁盒子里,就形成了一块儿黏稠的松油子。
大哥成了栾志贤的偶像,他不愿意离开大哥。
大哥在生产队的时候,去了铁路当了一名修建铁路的副业工,就不再担任记分员了。再后来,他到兵工厂做了十年车工,又到矿山当管库员,到粮站当保安。栾志贤和大哥见面就少了。
一次,大哥正在做入库登记。栾志贤坐在了粮库门口。他是步行十五里地找来的。那时,母亲已经过世半年。
大哥来到大门口,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背影在粮站大门口左侧的大石头上坐着,手里拿着一个袋子。大哥心里有些酸、有些软。这个人是栾志贤吗?他怎么来到这儿了?
母亲去世的时候,栾志贤没有在村上。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跟随小妹妹到镇上去居住,说是给一个退休工人挑水,每个月给300 元钱。后来,也不要钱了,管他吃顿饱饭就行,说要跟那个老工人学习拉二胡,拉《二泉映月》《高山流水》,那个退休工人是从县剧团转到石棉矿当工人的,剧团解散了,得找个地方开工资。栾志贤不认识谱子。可看在他自己会做琴,还会拉《东方红》《国际歌》的曲子,尽管音不准,退休工人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
见到大哥走过来,栾志贤站起来,红着个眼睛,嘴巴一撇,“大叔,我四奶奶死了,我看不到她了,她听不到我拉琴了!”说着哇哇哇地大哭起来。装卸粮食的工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围过来。栾志贤抱住了大哥,哭声在山间回荡起来。
“别哭了,屋里说。”大哥把他领到了宿舍,给粮站请了半天假,专门陪着栾志贤。
“贤哪,这些年过得咋样?你在跟谁过呢?”
“我的仨妹子嫁人了。老大嫁给了你的当家兄弟,就是栾志英,她又生了两个孩子,顾不上我了。
二妹子嫁到山西五台了,老远的,很少回来。三妹子嫁到镇上,她把我带走了。只在她家住,我给人家挑水。我会拉胡琴了。”他笑了。
“你什么时候把胡琴做好的?”
“你到外面上班后,我想你。一想你,我就做胡琴。做了两把,一把好的,我想拉给你听。一把赖一点儿的,我专门练习用。我给你拉一个吧。”
栾志贤拉了个曲子,《东方红》。大哥跟着唱起来。“贤哪,你这调儿不准呢。”
“大叔,你凑合着听吧,我总也拉不准。”
再拉《高山流水》时,大哥不唱了,他听不大懂。有的时候,他问栾志贤,“你拉的是山顶的刮风声儿吗?”有的地方,他会问,“你这是拉得咱们拒马河的涛声吗?”栾志贤笑笑,你说啥声就是啥声。
“我听出来了,你这拉的是河槽里的流水声。你弄这么个葫芦,还真能拉出个音调呀!比小时候,我爹拉得二胡声音粗点,发闷,不如他那把琴脆生。”
这次栾志贤来,穿得干净了。穿着一条蓝格子的夹克衫,蓝色的裤子,脸上不像从前那样黑黝黝的了。
“贤哪,你变干净了。”
“我找你来,打扮了。我在镇里,不给那个老工人挑水了,他上楼了,平房拆了,不用井水了,都是自来水。我想回村里了。”
大哥想往他兜里塞上钱,栾志贤拒绝了。“我有钱,每天捡垃圾卖钱。我又不花。我还想给你点儿呢。”
“大叔,那‘五害’变好了吗?你不在村里,我都不敢在村里待着了。这儿不干了,你回村里不?我等着你,咱们一起过?”
“我还得再干几年。老家的房子没人住了。老二说,让我去县城跟他们过。”
“那我去看你。”
九
大哥在县城住的时候,栾志贤每年都去看他。
去县城,栾志贤不用掏路费。村里那“五害”都成了运输队的队长,每家都有三四辆车。有运矿石的,有跑班车的,还有跑出租的。也许是小时候伤害过栾志贤的缘故,他们想赎回“罪过”,也许是村上人说,“要向大振学习。大振光做好事儿,把兄弟姐妹们都养大了,他晚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村里人都念大振的好,就连‘五害’们也不说大振赖。大振成了乡亲们心中的榜样。”
“贤哪,去那儿?”“蟑螂”问。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不叫他栾志贤了。
“去县城,看大叔!”
“我拉着你去吧!把这袋豆角捎给大振。他爱吃玉米地里套种的豆角。这是一块家里的猪肉,猪肉炖豆角,大振爱吃。”“蟑螂”解释着。
“贤哪,再去看大振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磨了大棒子米了,给他带点过去。”“麻雀”看到栾志贤时问他。
是因为大哥的善行,还是“五害”们对恶作剧的反省。反正,他们对晚年的栾志贤好了起来。村里的人对栾志贤也尊重起来。
在戏楼院里,村里的干部和村民代表在选贫困户,实行精准扶贫。“五害”是村民中的代表,他们讨论推荐了两个贫困户,一个是大哥,一个是栾志贤。
大哥以及我们全家拒绝了。因为虽然大哥没有孩子,但是大哥的兄弟姐妹,侄男外女都是他的孩子。经济上,大哥在外打工也攒下了钱,生活上大家都关心着。大哥婉言谢绝了村干部们。他说栾志贤可以当贫苦户,吃低保。后几年,大哥在养老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满院的鲜花、满院的友情与亲情。
栾志贤到养老院里看大哥的时候说,“大叔,你好好活着,别得病。等过几年,我陪着你。”
“贤哪,我都住了十四次医院啦,出气憋得慌。我什么时候听你拉琴呢,用你那把最好的琴。”
“大叔,下次吧,我拿来。我把它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了。不好往外拿,我怕他们发现了。”
“贤哪,拿那把琴换个媳妇咋样?那么宝贝呢?”
“那可不行。我懂琴、琴懂我,媳妇懂吃喝。不换,不换!”
“大叔,我还给你带了个东西,是我秀姑给你的。她让我问你好。”
打开一个小包儿,是李秀儿的一个记工本。前半部分是大哥记得劳动时间、地点和项目、分数。后半部分有李秀儿歪歪扭扭的名字,后面有六个大大的圆点儿。
大哥的心里搅动起来,有喜悦、有疼痛,有向往、有懊悔,有自豪,也有悲伤。他就像个矛盾体,瞻前顾后,欲左还右,像走钢丝一样,找着平衡,缓步向前。有舍就有得啊,舍了秀儿,得了一辈子的思念啊!
十
大哥出殡那天,栾志贤用力拉着“二泉映月”,“高山流水”。调子有些不准,但是人们听出了他的悲伤。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那把琴。琴的总体颜色是黄色中带着点咖色。葫芦琴筒是上过桐油的,年久色素沉着,有点发深咖色了。蛇皮是墨绿中带着黑色的。深黄色的琴杆、琴柄上,还浸着大哥与栾志贤用火烤的体温与烟熏后的褐色。那琴弦上的马鬃还向往着大哥的抚摸。
处理完大哥的后事,我回城了。
村里的人说,大哥出殡后,栾志贤就不见了。
大哥的坟旁又多了一个小坟丘。大家不解,挖开一看,是一个琴箱,琴箱里装着那把琴。人们赶紧又埋好,埋得很深很深,那悠远的、低沉的琴声伴着涛涛的拒马河,在山涧里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