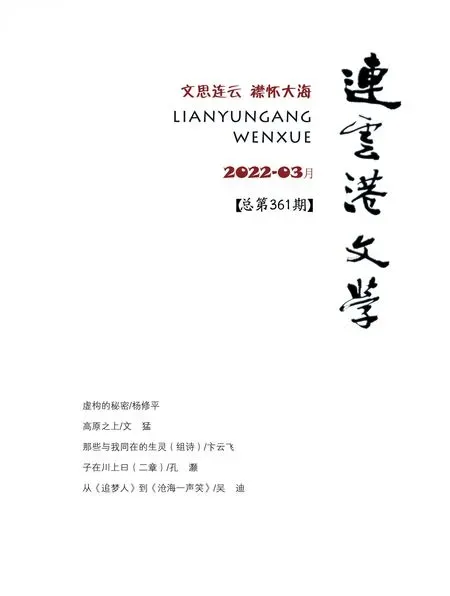高原之上
文猛
走向高原,高原的宏阔和高远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再宏大的形容词再壮美的动词在这空旷的高原都显得苍白。
比高原更辽阔的是思想,比思想更高远的是高原。
鲁朗林海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在大地上,脚步所能到达的最高处只有一个,那就是珠穆朗玛峰。那是一代又一代人向往的最高地。我们可能到达不了心灵的高处,我们可以到达脚步能到的最高处。
我们也是自己的高原。
朝圣之路从林芝开始——
古老的茶马古道、唐蕃古道被冷落。不再一步一步走向高原,一步一步适应拔节的高山和冷淡的空气,思想和脚步在高原上奔驰。
林芝是登高必需的马凳。
走进林芝,踏上川藏公路,踏上通往西藏的天路,去色季拉山口,去朝拜鲁朗林海。
高原处处皆神山。神山与神山站着说话,脚底为沟。神山与神山肩并肩思想,肩膀处为垭。去色季拉山,不从神山站着的山头处翻过,只想从神山肩并肩的山口处走过。色季拉山口是我们高原的第一道山口,就像人字,左想是一撇,右想是一捺,想来想去,人就是一山口。
鲁朗林海!纤尘不染的蓝天,茫茫的林海,在这片蓝和绿的世界,在大山思考的山口,松涛扑面而来,经幡呼呼作响,风把经幡上的经文祈诵,掷地有声。
一只藏狗蹲在山口,凝视着东方,雕塑一般。难道它也要像这座座神山,化为永恒?
穿行茫茫林海,走进神山与神山站着说话的脚底——鲁朗谷。这里清清的贡布河,溪流蜿蜒,泉水潺潺。长长的草甸,草甸之上报春花、紫苑花、马蒿花、油菜花怒放。木篱笆、木板屋、木头桥和牧民的村寨星罗棋布。云雾时聚时散,海海漫漫的雪山、林海时隐时现——
这是神的世界。
古老的贡布河,古老的吊桥。我们在扎西岗村丹增家的草场,躺在青青的草地上,天空之上是洁白的云朵,草地之上是贡布拉雪山。羊群悠闲地吃草,不时用“咩咩咩”的羊语问候我们……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忧思都随着这云、这雾、这风远去,风轻轻,草青青,心清清。
在鲁朗,我们就是一只羊。
有哈达捧上来,扎西德勒!
有酥油茶端上来,扎西德勒!
有锅庄跳起来,扎西德勒!
丹增说,我们是他今年接待的最后一批客人,明天他们全家就要到拉萨去朝圣。
沿着丹增一家朝圣之路,走向更高更远的高原……
那里,离天更近。
雍布拉康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洪洞是我们的老家,大槐树下老鸹窝是我们的祖宅。
“宫殿莫早于雍布拉康,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地方莫早于雅砻……”
源于山南,源于雅砻,源于雍布拉康。
我们记住洪洞,记住大槐树,记住老鸹窝。高原记住山南,记住雅砻,记住雍布拉康。
地名记着所有的事,记着地名好回家。
一望无际的山南平原,一碧如洗的蓝色天空,一沟碧翠的雅砻河谷,扎西次日山突兀、高耸,山上是雍布拉宫。以平原为背景,以天空为衬托。除了仰望,别无杂念。
牵过一匹马,在奔放的高原,在这马背的民族,马给我们高度和速度。
圣洁的雍布拉康,华丽、庄严的宫殿在永远不灭的香火中,在永远不灭的酥油灯的灯光中——
高原第一缕青稞香从这里飘出;
高原第一片经幡从这里扬起;
西藏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在这里住过……
拜天,拜地,拜神,拜庙,除了虔诚的跪拜,没有更多的表述……
为什么雍布拉康不在一望无际的山南平原,而在高高的扎西次日山上?为什么布达拉宫、江孜古堡、卡久……孜珠寺都在山上?
最早的回答还是雍布拉康。第一代藏王聂寺赞普是顺着天梯来到雅砻河谷,高原人崇拜天神,天神下凡时,总是先降临到一座大山上,天神顺着天梯从天而降,也可顺着天梯回归天上。世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崇拜过天,崇拜过天神,只有伟大的藏民族把对天和天神的崇拜转化为对山和山神的崇拜,也只有在高原,只有高原那些高入云端的雪山才配神的称号。
在道路经过的山岭垭口竖起经幡,系上风马旗;
在山顶、山腰堆起玛尼堆,堆起箭垛;
在倾斜的悬崖底部支撑起树枝、木棍架的天梯;
在屋顶上燃起松柏枝,让袅袅升起的烟雾和天相连……
把寺庙、宫殿和自己的思想都建在山崖上,离天更近,心灵与天更通。
走下山,不敢再骑马。
羊卓雍措
拜访过太多太多的湖,太湖,西湖,青海湖,洞庭湖……一踏进高原,朋友们说,羊卓雍措必须去,纳木错必须去,玛旁雍错必须去——
我该去哪汪圣湖?
择签。
羊卓雍措。
这是神的指示。
在岗巴拉山口俯瞰这片蓝,奔向湖边亲近这片蓝,沿着湖波洗礼这片蓝,想象和司空见惯被颠覆只是瞬间的事。词语的仓库,贫穷得只剩下唯一的“啊”——它也被卡在了声道。
静谧过滤着我们浮躁的内心;
高洁涤荡着我们视野的俗尘;
湛蓝驱逐着我们晦暗的阴霾……
它的蓝是融化一切的蓝。雪山,草地,牛羊。蓝天,白云,心思。尽数融化在这样一汪蓝中,天蓝,水蓝,心蓝。
它的蓝是不可思议的蓝。最罗曼蒂克的梦境,最美丽缥缈的童话,都未必能有这样的蓝。这汪蓝,任何画家恨不得以湖水作画。世间谁能调和出这样的蓝?这汪蓝,任何诗人赞美的语言都变得无力。奔到心中的只有那个最笨拙而又最恰当的词——蓝。任何凡人看到她,人世间曾经的收获和失落,幸福和忧伤,得意和失意,在这汪心灵的瑶池,都通体的碧蓝,不带一丝凡尘。
她的圣是佛法无边的圣。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凡夫草民,没有约定,没有告诫,大家静静地拜湖、转湖,没有高声喧哗,没有趾高气扬,圣湖圣境,大家的心都静了下来,静静地,轻轻地,清清地,享受心灵的宁静和洗礼。
她的圣是天地相通的圣。达赖圆寂之后,湖边诵经祈祷,湖中投奉哈达、宝瓶和灵药,圣湖显影中会神示达赖转世灵童的方位。虔诚的圣徒绕湖朝圣,跪拜圣湖,他们相信圣湖能够护佑所有的生灵,相信圣湖会印照出每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圣湖照着大地上每一个生灵。
萌生出转湖的决心,事实上这对于我们这些远远地朝圣之人是不可能实现的空诺,听说在这片600 多平方公里的圣湖,就是骑马转湖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别说让身体每寸肌肤都匍匐大地跪行。
在湖边见到一家从青海专程磕长头而来的小姑娘一家人,漫漫两千公里的长路,虔诚的三步一拜等身丈量的长头,不敢询问小姑娘朝圣的艰辛,询问小姑娘清澈的眼睛,她微笑着小声告诉我们,她终于看见了圣湖,终于看见了心中的佛。
跪在圣湖之边,跪拜雪山、草原的神灵。在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在这高原,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朝圣大大小小的寺庙,朝拜江河和圣湖,宁静让我们出离形的假象,了悟空的真理,宁静让我们削弱和减少对浮躁、焦虑、惶恐、贪欲、悲伤和绝望的恐惧,让我们的精神不再继续潦草。在遥远的空间和同样遥远的时间里,有这样一汪圣湖,无时无刻不在规约我们的行为,成为心灵观想的地址和心灵澄澈的天堂,让心随时回到这里——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心里
不舍不弃……
圣湖羊卓雍措,最能表达我们共同心思的,就是这首美丽的诗。
不必探究谁写的诗?
珠穆朗玛峰
走向高原,走进人间的净土,走进圣洁的天域,更多的情结就是为着那大地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不为登顶征服,仰望大地最高的雪峰,也是人生莫大的成就。
不远万里奔赴高原,不远千里奔赴珠穆朗玛,高空飓风,极地严寒,缺氧,雪崩,站在大地的最高处,站在人生脚印的最高处,这里不适合摆放风景,这里适合摆放思想。仰望珠穆朗玛,才能听见自己心中最深处的声响……
有一种高度叫仰望。
让眼睛的脚步迈出去吧!两座大山的正前方,圣洁的珠峰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巍然屹立在群峰之间,那样从容,那样超然,那样令人望而生畏。山的顶端,一团绒布般的白云,像一面圣洁的经幡,静静地念诵在这世界的脊柱、万山的顶点。
匍匐在这片仰望下,心清静了,一如头顶纤尘不染的蓝天。心透明了,犹似晶莹剔透的冰峰……仰望默默站立了亿万年的圣洁雪峰,在永恒的时空,我们太过渺小,我们太过幼稚,我们俗世中的荣辱名利、烦扰纷争荡然无存……
有一种坚守叫信仰。
山下有一座寺庙叫绒布寺,它不是最大的寺庙,但是世上最高的寺庙。雪域之巅,有这样一群人,在很少有生命可以存活的地方坚守着一份纯朴的信仰。不计较生活的艰苦,不在乎呼吸的局促,不去想世间的浮华,只为了能够每天陪伴着神山珠穆朗玛,只为了能在一片祥云下许祝愿——
山下就是珠峰河,它不是世上海拔最高的河,但它是从世上最高的山峰流出的河。那是矗立了亿万年、诵读了亿万年雪白经幡下的嘀嗒声,那是凝固了亿万年、坚守了亿万年冰峰下的嘀嗒声,那是仰望了亿万年、静谧了亿万年的大地上最高处的嘀嗒声,汇成一条河,静静地,清清地,从珠穆朗玛峰的脚下流出,流进一条没有鲜花、没有绿草、没有鸟鸣的河道——
最初的那滴水献给太阳;
最远的那滴水献给大海;
最高的那滴水献给天空……
一滴水最懂得一滴水,一座山最懂得一座山,一条河最懂得一条河。
有一种圣洁叫雪声。
雪声是非凡的人间之声,雪声从来不在人群之中,雪声在人迹罕至的山脉高处。我在大地上最热的季节仰望珠穆朗玛,眼中是雪声,耳边是雪声,手中是雪声……
我们总是用“雪”表述和记录世界的美好——
美丽善良的女孩叫“白雪公主”;
聪慧可人的女孩叫“冰雪聪明”;
洁身自好叫“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最温暖的期待叫“雪中送炭”;
最暖心的邀请叫“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
雪是上天投寄给大地最亲密的信件,是上天给诗人最美的诗句;
雪是上天写在大地上最古老的箴言,是大地给人们参悟的无字经文……
一片,一片,一片,就像经幡上古老的经文,装订在珠穆朗玛峰的雪线之上,装订在珠峰河的浪花之上,装订在绒布寺的钟声之上。在仰望中聆听,在聆听中仰望。风吹起胸前的哈达,吹拂毡帽上的尘土,未来的道路变得平静坦荡宽阔。
钟声响起来——
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