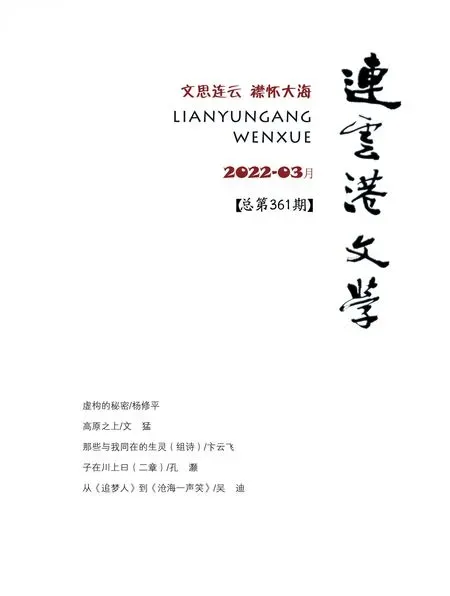微小说女作者专辑(六题)
陈敏等
长寿秘诀
陈敏
得知我要去曳山,采访一位年过102 岁的老寿星,并从她那里得到一些长寿秘诀时,单位采访组的几个女记者也都争着要去,因为据说,这个活过102 岁的老人不仅耳聪目明,身板硬朗,而且皮肤光洁靓丽,像苹果花一样的颜色。就连向来不太注重保养的女主编杨编也要跟着去,这样一来,采访组原定的两人就变成了一男四女,五个人。
提前预约了和老寿星同姓的杨村长,想必,我们的采访一定会顺畅而便利。
这几年,曳山村里出了个老寿星,杨村长的地位和身份也跟着显赫了不少。逢年过节,采访和慰问的人一拨一拨来,多数都得先采访杨村长,并让他带路引荐。村主任的名气也随之大了,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笔直的。
村主任个头不高,精瘦,四十二岁,头发黑油油的,两道眉毛又粗又长,有点长寿的骨象。我们边走边侃,纷纷鼓励他也要好好活,争取活过百岁,村主任乐得咧着嘴笑。
山路歪歪斜斜,穿高跟鞋的女士们普遍走不快,都纷纷在后面喊村主任放慢脚步,让他先讲点那位老寿星的事。毕竟,先从侧面了解一下寿星更为重要。
杨村长放慢了脚步,说,据他了解,老人的长寿也没啥秘诀,她一生没有孩子,但13岁时出嫁过一次,19 岁时被男人休了,从此孤身一人,再也未嫁。那个年代的男人普遍崇尚小脚女人,看女人不看脸,不看身材,专看脚。男人一看她的大脚顿时泄了气,大婚当晚就嘲讽她:“人说三寸金莲,四寸银莲,五寸铁莲,你的脚有六寸长了吧,连个铁莲都够不上,应该算个石莲。”从此,男人就为她更名换姓,给她取了个诨号:石莲。
她那会儿一直被村人嘲笑着,小孩以她的大脚丫取乐,给她编顺口溜,还有熊孩子向她扔石头。再后来,见她的肚皮一直不见隆起,男人便以六个铜板,将她休了。
她用男人的休妻费,从一个远方亲戚那里认养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从此,她有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早早娶了媳妇,一口气生出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她就有了八个“孙子。”
后来她的儿子儿媳都死了,全是老死的,大点的孙子也老死了好几个。只剩下了几个小孙、孙女和一群曾孙。他们都独自过光景,很少和她往来,也没几个人管她的事。不过,近些年,老人的名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大,政府部门和一些慈善机构送钱送物的人越来越多,她的那些混得不好的“后代”们会偶尔来“看望”她,但多半都是来蹭油水的……
杨村长带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后,终于指了指近在眼前的一处低矮的木房子,说:“到了,她就在那里坐着。”
寿星正坐在半遮半隐的核桃树下乘凉,见我们朝她的方向走,便迅速抬头,朝我们张望。果然如人们传说的那样,她看上去确实不像过了百岁的人,不细看,还以为她是个老头儿。她蹲靠在一块大石头边,乐滋滋地抽着旱烟,根根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皮肤有细细密密的皱褶,但整体很光洁,身子虽然干瘦,却依然硬朗。她的两只脚果然不是那个时代的“三寸金莲”,但走起路来腰板笔直,步履轻盈。我们正准备围上去,便见她给我们挥了一下手后瞬间转身进了屋,身后的两扇木门“咯吱”一声关闭了,这让我们百思不解。是她不欢迎我们吗,还是我们的突然造访搅乱了她的安宁?
此时,解惑的人也只有杨村长。村主任没费多久就敲开了寿星的门,没多大一会儿就出来了。他转达了老寿星讲给我们的原话:“前天来了一个种植木耳的老板,他让我说长寿的秘诀是多吃木耳;昨天又来了一个养蜂的,他让我说长寿的秘诀是喝蜂蜜水。今天他们是哪里来的?又要让我说什么?告诉那些姑娘们吧,长寿的秘诀是远离男人。人活多久不由自己决定,有肉就吃,有酒就喝,有烟就抽,想咋就咋,这就是长寿秘诀。”
神秘的鱼
佟掌柜
冬夜。大雪。
方鹏和婉仪来到小酒馆,坐下后彼此对望一眼,很快将目光移开。方鹏召唤服务生点菜,婉仪则茫然四顾。
小酒馆不大,暗黄色墙壁上用黑色隶书书写的《短歌行》,和印着玛丽莲·梦露的粗麻布座椅背套很不搭。昏沉的小柱灯在方鹏的头顶摇晃着,十五年前初见他的情景不受控制地挤进婉仪的脑海。
那天,她本来已经睡下了,同学在楼下给她打电话,非要带她去参加一个商务party。两人走进KTV 包房时,见屋里已经坐了十几个男男女女。婉仪现在一点也想不起都是些什么人,只记得那晚她一直被膨胀的男性荷尔蒙借助言语和肢体轮番进攻着。唯一一个既不和她搭讪,也不和其他女人搭讪的男人是方鹏。他独自坐在角落里独饮,仿若这房间里只有透明的空气。婉仪忘了怎么管他要的QQ 号,其实她也不过是对他的孤冷颇感好奇罢了。
那时,离婚两年的婉仪并没有恋爱的打算,她感觉男人都像沁了麻油的绳,总想油腻腻地捆着她。
“这些年你还好吗?”方鹏这句老套的开场白把她从回忆中拽了回来。她愣了愣,反问了句,“你呢?”
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方鹏的笑一如当年,浅浅地抿抿嘴,左腮上的酒窝像湖水的波纹漾了漾。
等服务员端上涮吃两用的锅子,婉仪看到锅子下层玉米和南瓜二合面做成的金黄色饼子时,鼻子一酸。
方鹏将一片烤好的牦牛肉夹到婉仪的盘子里,“当年你最爱吃这口,现在没变吧?”婉仪面色一红,想起和方鹏第一次吃这种锅子时,她醉到吐出了所有的胆汁。
因为生意的关系,婉仪久经酒场。她非常清楚,在酒桌上,漂亮的女人就是男人眼里的一道鲜美菜肴,谁都想吃上一口。女人随便就醉了那还了得?她早就学会怎么保护自己了。可那天她偏偏醉了。她知道她的醉,是因为他的懂。
那天他们聊了小半夜,从禽流感肆虐聊到诺贝尔文学奖,从无人敢扶倒地的老人聊到他家的老屋。她记得,他取笑她,这么细的腰,怎么装得下那么多的肉;她记得,他对她说,婉仪,你是上天特意给我派来的;她记得,她说,那就让今天永远停住吧。
“虽然肉不是原来肉了,但仍然是那么好吃。”婉仪吃掉方鹏夹给她的肉说道。
窗外的雪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两个人你一杯我一盏地聊着,仿佛十几年的时光,不过几日光景。
“婉仪,当年你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婉仪夹菜的手停在半空中,顿了顿,幽幽地说:“你应该问你的那条鱼吧?”
方鹏放下酒杯,诧异地问:“什么鱼?”
“‘岸上的鱼’,你没和她结婚吗?”
当年,大约在方鹏和婉仪交往半年的时候,有个网名叫“岸上的鱼”的,通过QQ 对婉仪说,她是方鹏的女朋友,说因为婉仪,方鹏提出要跟她分手,她要见见婉仪。
方鹏伸手摸了摸婉仪的额头,“婉仪,你记错人了吧?我那时生意做得不好,身边根本没有女人,哪有什么岸上的鱼?”
婉仪盯着方鹏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方鹏,这么多年了,我才提起她,你觉得我可能记错吗?”
方鹏皱起眉想了想,“真是奇怪,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岸上的鱼’。当年你为什么不问问我?你要是问我,就会知道根本没有这个人的。”
“我有什么理由、以什么身份问你的私事呢?你说没有这个人,可她为什么说是你的女朋友?她又怎么知道我的?”
“是啊,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什么啊。”方鹏陷入沉思,“当年是有个女人喜欢我,可是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再说我根本也没和她提起过你啊。”
方鹏和婉仪大眼瞪小眼地分析着这条神秘的鱼到底何许人,可最终也没有结果。
婉仪叹口气,“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既然没有这条鱼,你为什么也不和我联系呢?”
“我怎么没联系你?我给你发过信息的,可是你没回。”婉仪怔了怔,一口气把她杯中的酒喝干了。她没有告诉方鹏,收到他说爱她的短信后,她大哭一场。那时她认为,他根本就是骗子。
这些年,她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总是会想起方鹏的浅笑和曾经的深谈,甚至有时会后悔,为什么当年没跟方鹏发生浪漫的故事。十天前,当她看到朋友发的朋友圈里,有一张方鹏跟一个时髦的年轻女人合影时,她竟然没忍住跟朋友打听,那女人是谁。
“婉仪,你不知道啊?那是老方的新媳妇。”
婉仪看到这句回答,心突然像被一群马蜂蜇了。她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她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她鬼使神差地要了方鹏的微信号。
两人从酒馆出来的时候,雪停了。一轮缺牙儿的明月清亮亮挂在天空。月光下,一高一矮两个人影相对伫立片刻又分开。雪地上,朝着相反方向延伸的两行脚印格外清晰。
回家的路上,婉仪忍不住去想那条神秘的鱼。或许此刻她正躲在某个角落“喈喈”地笑着,或许当年她也曾经痛苦过,或许她不是“她”,而是“他”。
临到家时,婉仪突然想起一句话: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怕
蓝月
艾琪约了朋友小聚,朋友已经到了,她开车赶紧往那边赶。
路口右转弯的时候,艾琪观察了一下,感觉没问题,就打方向慢慢转过去。这时候,艾琪眼前一道人影一闪,接着“砰”的一声,一辆电动车擦着她的车头摔了出去。
艾琪知道坏了,赶紧点刹车、挂P 档、拉手刹、打双闪危险灯,然后下车查看。
“哎哟,疼死我了……你怎么开车的?”一个身材矮胖的女人躺在马路中间不停呻吟,不过看着没有受伤,连皮也没有擦破一丁点。
艾琪听了女人的指责,不由得有点生气,看到我汽车转弯,你电动车不减速,超我车头,现在还赖我!幸亏我车速慢,不然真要出大事。但是艾琪耐住了气,她知道事情已经出了,弄僵更不好解决。
“我,我开得很慢了呀!这位大婶,你不要着急,我立马联系交警。”艾琪拿出手机报了警。
这时候,车辆多了起来,艾琪看着女人躺马路中间,非常危险,赶紧说:“大婶,你还能走动吗?如果可以,我扶你去路边等交警。不然太危险了。”
女人抬起头看了一下,车辆确实特别多,说,“好,你扶我。”
艾琪扶女人走到马路边上。
不多久,两位交警就到了,问了事情经过,看了刹车痕迹,看出来电动车是擦车头弹出去的,没有大问题。就让艾琪和女人留下联系方式,拍了艾琪的行驶证和驾驶证,还有双方身份证。
交警对女人说:“你没有流血,也能走动,看来问题不大,你要是不放心,可以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有啥问题就联系她。”
艾琪说:“我要陪着吗?”
交警说:“你想陪着也行,不陪也没有关系,她的伤不重,我们会联系她家人送她上医院,她的治疗费用,你的保险公司会赔付给她。你联系保险公司了吗?”
“啊,好的,我立马联系保险公司,谢谢你们!”艾琪如获大赦,打心眼里感激交警,这交警叔叔办事真是干净利落。
打完保险公司电话,艾琪赶紧开车走了,和朋友会合。
晚上11 点半,艾琪刚想休息,电话响了,是女人的电话。
艾琪赶紧接听。
“你是艾琪吗?你撞了我妈,怎么不管不顾走了,你还有没有一点道德?”电话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凶。
“你妈当时没啥问题……”
“你怎么知道没问题?我妈现在说头疼,要是我妈死了,你要坐牢!”男人吼起来。
艾琪心里一急,倒不是害怕坐牢,艾琪知道她不会坐牢,她第一时间报警了,她急的是女人不要真的出什么事情。
艾琪赶紧问:“那你妈现在在哪?医院吗?”
“在家呢,医院没有查出什么就回家了,但现在她说头疼。”
“那你赶紧再送医院呀,脑CT 做了吗?”
“没做,当时没说头疼。”
“没说也要做呀!检查了没事才放心。”
“那你赶紧送钱过来,我没钱了,你马上过来!你不过来我过来找你!”
艾琪觉得这个当儿子的有点不可理喻,脑CT 也就两三百,竟然说没钱,会不会是骗自己出去?艾琪当然不敢出去,这三更半夜了,要是对方是坏人就危险了。
可对方明显很激动,艾琪只能好说好话:“你先想办法带你妈去检查,她毕竟是你妈呀!明天一早我来医院看你妈,三更半夜的我一个女人不敢出门的。”
“那行,你要说话算话。”男人做了退让。
“肯定的,你放心。”艾琪舒了一口气,立马关了手机,但是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急急忙忙赶到医院,那个男人和她妈竟然没在医院,联系了才知道昨晚压根没有去检查。见面后,男人说他妈后来头疼缓解了就没上医院。艾琪说还是检查一下吧,艾琪主动交了钱。检查下来没问题。
男人这时候脸色缓和了,他说:“昨晚太着急了,所以说话冲了点。”
艾琪说:“理解的,没事就好,可吓坏我了。”
男人说:“看得出来你是善良人,昨天我怕你耍赖不管我妈,后来听你说话挺诚恳,也就信你了。”
艾琪心想,我还怕你们讹诈呢!看来双方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现今社会还是好人多啊!
“你们也一样善良啊!”艾琪真诚地说。
没几天,保险公司的赔款就到了,事情打上了句话。
开车的时候,艾琪比之前更注意观察了,特别是转弯的时候,宁愿慢点再慢点。艾琪心里的后怕,真真切切的。
风 景
李春华
有人说李玫在婆家也就啃老。这话也不虚,她肚子饿了,保姆把饭端到嘴边。且白吃白喝,自己挣钱自己花……这并非她的本意。她觉着这样的日子寡淡,没滋味。老公是远洋海员,常年在海上飘着。偶尔,李玫跟他视频,娇嗔地撒撒娇。许是整日枯燥的海上生活所致,以前他爱说爱笑,如今神情木讷。只是瞪着眼睛盯着视频,不眨下眼睛。李玫变着法逗他,顶多上翘下嘴角。更别说浪漫情调。但他一边倒支持李玫——暂时不要孩子。这回又支持她出去买房子。
晴好的初夏,李玫搬到了星河湾。同事说,放着大别墅不住奇葩。她反剪着双手,脑后棕色的“马尾”来回摇晃。星河湾——璨若星河,蛮有诗意啊。真拿文学爱好者没招,连想法都缤纷浪漫。
刚到小区,她觉着哪儿都新鲜。每逢周末,李玫穿着宽松的家居服,蹬上运动鞋,立在蜿蜒的甬道上,舒展下腰身,举着双臂做个漂亮的燕飞。一群麻雀呼啦从银杏树杈上飞走。她感叹,金丝雀哪如麻雀有辽远的天空。
日子久了,李玫恍惚觉着小区虽然有烟火味,似乎也缺点什么。中心花园附近,仨一群俩一伙的比画着,有的还凑近对方的脑壳,捂着嘴咬着耳根。有个老太婆两臂交叉搭在胸前,两腿岔开像个圆规戳那儿,打嘴里窜出个高音:哎呦喂,瞧瞧,黄土都埋半截了,还见天腻乎。有几个妇人看不惯“长舌妇”的做派,指着她们的鼻尖说:人家相好碍你们事了?有能耐叫你男人稀罕呀!几个老太婆自知理亏,斜楞着眼黑着脸,像一群乌鸦无趣地散去。
有一对老夫妻,头顶花白头发,戴着同款的宽边墨镜,紧贴着对方的身子,五指合十,紧紧攥着。在树荫底下,踩着细碎的光影,蹭着碎步。不管边上风吹草动,两人都目不斜视。李玫心里一动,好美的风景啊!她猜测:他们肯定有段浪漫的恋情。或者,曾经历经磨难,才修成正果……反正背后的故事肯定精彩。她像个猎手捕捉到了猎物,捂着怦怦跳的胸口,老远望着。
周末,李玫直奔花园甬道。那对老夫妻如约五指相扣,慢悠悠走在树荫下。暖阳细碎地照着他们的驼背,影影绰绰很像两座连绵起伏的小山包,积蓄着一股力量。她忍不住掏出手机,拍下他们的背影。有对恋人,羡慕地停下脚,小声嘀咕着,也拿手机拍照。老夫妻则目不斜视,仍然擦啦擦啦往前蹭着。李玫越发觉着,看似他们外表平静,心中指定有丘壑。她跟在后头,盘算着哪天找个机会搭话。
每逢散步,李玫目标很明确,直奔甬道树荫。可怪了,有段时间没见老夫妻。她问过邻居也说没见他们。李玫有点沮丧。偏巧,婆婆打来电话,让她回去住。一走半月有余,她人在婆家,心在星河湾。而且,老夫妻竟然手挽手溜达到她的梦里。婆婆打趣说,看你神不守舍的,快回星河湾吧!李玫一听,瞬间心花盛放。
周末下午,她回到星河湾。她换上家居服,穿好旅游鞋,坐电梯下楼。一溜小跑到树荫附近。果然,老夫妻手拉手,慢慢悠悠往前蹭着。这回,她看仔细了,老太太的两条腿不利索,左腿的步幅老是迟缓要踮一下,她艰难地每走一步,老伴都抓着她的手攥成个拳头,随即往腰窝一拽。似乎他一旦松手,便是各自天涯。这拳头,这一拽,立刻给了李玫勇气,她不再迟疑,快步赶上去,定住脚:二老好!你们手挽手太恩爱了,真羡慕你们呀……听声音,你是个年轻姑娘吧?李玫这才仔细打量:说话的老爷子停住脚,直愣愣的并没瞅她这边。老太太一手扣着老伴的手,一手摘下墨镜,两人斜着站成一排:你好,二十年前,实验室爆炸,他的眼睛炸瞎了……李玫有点蒙,不知如何接茬。老太太朝李玫递个眼色。我把老伴送回家,咱再说话成吗?李玫点点下巴。
她们肩挨肩,坐在花园的木椅上。老太太把拐棍放边上,缓缓摘下墨镜,仰头望着暮色苍茫的天边,余晖照在她的脸上可见皱纹纵横。我们两地分居二十年。直到他失明,组织上把我调回本市。我是干地质的,常年在户外作业,落下严重的风湿病。无奈,也就有了默契——我是他的眼睛,他是我的拐棍……
老太太从衣兜摸出纸巾,擦着眼角流出的泪。李玫下意识伸手,想去抚慰她。老太太哧哧地笑,反倒双手捂住她的手。我是迎风眼,见风就流泪……唉!他刚失明那会,人很敏感。外出时会问,有人看我吧?即便身边有人咬耳朵,指点他。我一笑而过,告诉他,没人瞅你呀!以后啊,我也戴墨镜,也目不斜视。
老太太神情平和,李玫安静地听着。虽然话题跟她预想的相差甚远,但她似乎也悟到了些许。
有段时间没见二老,咋回事……呃,我得了阑尾炎住院了。眼下,我们都快八十多岁了,膝下无儿无女的。唉!可能是坐久了,老太太欠了下身。李玫起身弯腰,搀着老太太回家。可巧,老夫妻竟然跟她住一栋楼。
李玫进家,趴在床上,滑开手机屏,给老公发微信:老公,问个问题:咱俩视频,你咋不笑?可能是海上信号不好,十几分钟后,他在微信窗口回复:小傻瓜,你不知道我眼睛小啊,窄成一条缝儿,那不成“扒着门缝”看你了?我不想错过看你的每个瞬间……李玫鼻子一酸,泪水扑簌簌涌出,手机屏幕洇出几朵泪花。
老公,该回了吧?你要好好的,我想要个孩子,不,要仨……
他立刻回复:一个月后返航,老婆,怎么了?
父亲和画眉鸟
张淑清
这是一只已经被驯服的母画眉鸟,见到阳光和陌生人毫无应急反应。父亲一辈子住在乡下,那片土地上生长着连绵起伏的山脉,近年来封山育林,原始生态林保护得好,有上百种鸟类在树林中繁衍生息,春暖花开的季节,就有画眉在院外的杏树上叫春,父亲在树下搓草绳,磨刀,母亲在石凳上纳鞋垫。小时候,小军姐弟就是穿着母亲纳的鞋和鞋垫上学,读书,直到成家立业,在城市居住,母亲依旧不改初衷,每年纳几十双鞋垫,嘱咐孩子带回城里。画眉鸟每次来,父亲都习惯和它说说话,久而久之,父亲记住了画眉鸟。
现在,父亲注视着被关在笼子的母画眉,心忽然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他明白儿子的用意,叹了口气。捏一撮小米,放在木头盒里,画眉并不领情,反而上蹿下跳,欲飞出去。小军说,“刚换一个环境,过几天就好了。”谁知,那晚,画眉鸟时断时续地叫了一宿。小军家在三楼,幸亏房间隔音效果不错,不然,扰民。两口子都没睡好,何况才来没两天的父亲。小军推开卧室门,就看见父亲站在客厅的鸟笼前,一脸兴奋地冲着画眉说话。“唱了一夜,累了吧?来,喝水,哎呀,慢点喝,别呛着,老伙计,在这家,我陪着你,你不会孤单的……”小军不由湿了眼眶。
那天下班后,小军打开客厅门,听到画眉鸟说,“狗剩,你上班辛苦了。”小军愣了,他的小名叫狗剩,打小母亲给起得。画眉鸟居然会说话!父亲在一旁高兴得像个孩子,“画眉鸟真聪明,模仿力也超强。”小军点点头,“嗯,爸,你开心就好,”父亲说,“你炖个土豆瓣和排骨,今黑咱爷俩挠一杯。”
从这一夜开始,父亲把盛画眉鸟的笼子搂在怀里,父亲睡得很踏实,发出均匀的鼾声。
父亲吃了早饭,拎着鸟笼就出去了,他在小区广场遛鸟,和同样遛鸟的人搭讪,讨论着养鸟经验。画眉鸟与父亲形影不离,遛了两小时,必回来给花草浇水施肥。周末,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回家,小军唯恐父亲出什么状况,就到广场找,小区里的人小军问遍了,都说父亲好几天没在这遛鸟。父亲去哪了?
小军在城郊的一爿树林找到父亲,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地方,一条河奔腾不息,河水清澈,水面上有许多水鸟左右翻飞。一株株古木参天的树,住着数不清的鸟类。有几个人举着相机,对着鸟群拍照,他们脚步轻轻,不惊扰这里的一沙一石一只鸟儿。父亲痴痴地凝视着,沉思着。
父亲犹豫一次又一次,笼子打开又关上,用手死死捂着。后来还是缓缓打开鸟笼,“老伙计,你走吧,在笼子里委屈你了,你应该属于广阔的天地。虽然,我有很多不舍……”
画眉鸟不走,叫得很凄凉。父亲狠狠心双臂一抬,画眉落在地上,又折回父亲身边,父亲抡起一根枯枝抽它,吼它,最后,画眉扇动翅膀,飞了起来,围绕着父亲盘旋几圈后,潸然离去。
画眉消失在树林中,父亲一动不动,远远地看去,仿佛一棵老树。
父亲经常去那片树林,一坐就是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和鸟们也混熟了,它们落在父亲的手掌心,肩膀上,同父亲窃窃私语,父亲与来树林拍鸟的几位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了自己的朋友圈,父亲呢?再也不提回乡下的事了。
梳头谣
蒋冬梅
浑河一带的满族村子,婴儿出生和“洗三”都要到英额门去请金凤婆。
那时候,风从残破的柳条边墙吹进来,吹来了日本的花布和洋货。人们一打英额门经过,就说:“看,这地方原来是柳条边门哪。”三百年前的柳条边,是皇太极朱笔一挥隆起的褶皱。“英额”满语的意思是柳条,他们管满语叫“老话儿”。
后来,就连小学校里都传来日本话的读书声,他们还能听到的“老话儿”,除了那些打着弯的地名,就只有金凤婆的谣曲儿了。金凤婆的谣曲里有“一年生,二年生,三年生”野猪的名字;也有“秋水消减、大水响流、鱼游动的水纹”老话的说法;还有长着不同鹿角的鹿,能活到七十岁的狗鱼的满语发音。
金凤婆爱唱谣曲,她干每样事情,都要唱上一段谣。她给婴儿接生时唱:“一箭射到九霄宫,二箭射到龙王殿,三箭射到赫图阿拉城,老汗王听了真高兴,开口封个状元红。”她给婴儿“洗三”又唱:“金豆子,银豆子,咱家来了个狗剩子。”这些谣曲,她还能用“老话儿”唱。
金凤婆唱的最好听的谣曲是梳头谣,她只会用“老话儿”唱,唯独这谣曲里的满语她不懂,方圆几百里,也没有人懂。
婴儿出生的第三天,金凤婆来给“洗三”了。她用干槐条和艾蒿熬出春绿的水,滚落几颗红枣、桂圆、鸡蛋,再叮叮当当丢几枚铜钱进去,一起蒸腾着上下翻滚。等给孩子洗了身,她从头上拨下杨木梳子,在孩子头上梳上三下,边梳边用“老话儿”唱着梳头谣。说来也怪,她给梳了头,唱了谣曲的孩子,百日之内平平安安,所以远近百里,都争着请金凤婆,人都说,她唱的梳头谣是仙调儿。
喜薇是金凤婆接生的最后一个婴儿。
喜薇出生的那天,头天的化雪结了满地的冰,拉车的马一步一哧溜,嘴里冒着白气,像腾着云来的。等到了喜薇家上了炕,喜薇妈正疼得缩在炕头呢。金凤婆探手一看,倒先盘腿上炕卷上了旱烟,舌尖一边舔着烟屁股一边念着谣儿:“莫要娇,莫要喘,屋里屋外转一转,养个孩子八尺三。”她嗓子粗得像个爷们,等一棵烟抽到尾巴了,一双瘦手像打太极似的,暗中使劲,转腾挪移,等把个孩子整整装装地拿大红布包裹好,金凤婆也已一脸细汗。
家里人人脸上笑得开了花似的,金凤婆粗嗓大气地道喜,接下喜薇爹的赏钱。有人问她接生过多少孩子,她大粗嗓子一亮又像唱谣似的:“哪天要饭从清原走到南杂木,二百里一村一站,饿不死老太婆。”
喜薇爹送金凤婆回去的路上,在银锭子一样的冰面上,马蹄打了滑,连人带车翻进了沟,等人把金凤婆救上来的时候,她的脑子摔坏了,以后变得呆呆的,再也不能接生了。
那以后,村里的女孩们轮流着伺候金凤婆,她们都是金凤婆唱过梳头谣的孩子。金凤婆没有儿女,可她不缺孝子贤孙,绕着浑河的沟沟汊汊,金凤婆的谣曲唱了个遍。她闯过牛肺子沟;在母猪背迷过路;搁杨树崴子歇过脚;打庙后村出来,抬头正望见唐家大旺,路过一家门口,门楼底下站着爷俩,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都是经她手接生的,爹叫她凤婶,儿叫她凤奶。
不时地有人抱着新生的婴儿,走进金凤婆的屋子,看她拨下头顶的杨木梳,给婴儿梳上几梳子,她没了牙的瘪嘴里,唱出风一样的梳头谣。
喜薇天天来给金凤婆梳头,听她断断续续唱几句谣曲。春来的一天,柳条摇着暖风,金凤婆躺在炕上,喜薇像往常那样给金凤婆梳了头,她的白发上跳着水一样的光,脸上的皱纹像开了犁的土地。
金凤婆想起小时候的那一天,风吹过柳条边,吹进了屋子,里面一屋子的孩子。水莲老师背对着黑板,偷偷用满语教孩子们唱着一支谣曲。她身后的黑板上,写着东洋字儿,像一行行掉了胳膊腿的汉字,闪着冷冷的寒光。白墙上贴着方块卡片印刷的大红标语“大满洲国万岁。”
水莲唱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不懂那满语唱的是啥,只知道那曲调弯弯曲曲的,美得像暖风。可他们没看到,窗外日本教官眼镜片后面狼一样的眼睛,他身后还跟着一队端着枪的日本兵……
喜薇给金凤婆梳好了平安髻,把杨木梳轻轻插进银发说:“凤奶,再唱个梳头谣吧。”可金凤婆没有回答她。
喜薇知道,以后,再也没人会唱梳头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