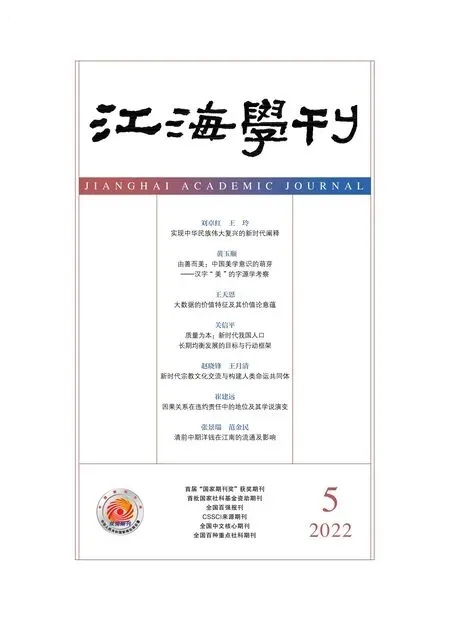清初“文人共同体”的书籍生成与流通*
——以张潮《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为考察中心
陈晓峰
学界以往对群落、社团的确认主要凭借地域、盟约等显性依据,而忽略了文人的心理向聚和精神关联。罗时进教授认为,文人处于网络化、团体化的关系之中,其复杂性在于,“对所谓流派、社团、体派的体认往往是凭借显性的盟约类为文字依据,但所有的盟约都有文字记载吗?心理向聚的盟约能够辨析吗?”(1)罗时进:《明清诗界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创作”》,《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斐迪南·滕尼斯定义了“共同体”,(2)参见[美]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艾尔曼认为清代考据学者在江南形成了“学术共同体”,“通过知识传播的组织与机制走到一起,就寻找、发掘知识的途径达成共识”。(3)[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周绍明在《书籍的社会史》中以“知识共同体”指称明清士子建立的非政府机构,“以促进某种类型的共享知识在感兴趣和有文化的人中间进行保存和传播”。(4)[美]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事实上,“文人共同体”既包括“面对面的实质形态”,也不可忽略精神同盟意义上的“想象存在”。
张潮(1650—1708?),字山来,号心斋,安徽歙县人。《尺牍偶存》收录张潮写给四方亲友的书信456封,《尺牍友声》收录各方寄赠张潮的信函1003封,散居各地的300余位文人由此建构了超越血缘师承和地理空间的交际网络,形成以中下层文人为主体的关于精神、文化与现实利益的“共同体”。尺牍中有意义的繁复碎片勾勒出一个“书籍世界”的存在,这为观察清初书籍的生产、流通提供了丰富细节,且以之为媒介的叙事具有过程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折射了文化转移的进程,有助于从细微之处发掘暗藏的演变规律,重新思考文本、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联,从群体、网络的层面考察书籍生产流转的机制以及与社会思想、政治、文化的关系。(5)书籍史研究奠基者法国让·马丁认为,书籍史是构成传播交流史的一个侧面。中国的传统出版物浩如烟海,这一研究却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书籍史和出版史纳入了海外学界的视野,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1991)、梅尔清《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2008)、周绍明《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2009)等,打破孤立视角和狭窄视域,探讨一定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下书籍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崭新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近年,书籍史及与之相关的话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引发诸多反响,理论和方法上的交流与对话正在开展。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2013)一文思考了西方书籍史、印刷文化史研究与中国文献传统的结合问题。同时,微观、个案研究也是趋势所在。徐雁平《〈管庭芬日记〉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2014)、《用书籍编织世界——黄金台日记研究》(2015)二文,聚焦文人世界书籍往还建构与维持社交网络,从日记材料寻求突破,细致探讨书商与书籍的流转、文人日记及读书生活、新学书籍的涌入及影响等。
“文人共同体”中的书籍生成
(一)以编刻者为中心的格局

在清初图书出版的编辑、刊刻、流通等环节,刻书者发挥了关键作用。吴肃公(1626—1699),字雨若,号晴岩、逸鸿,别号街南,安徽宣城人。晚明诸生,入清仅以卖字、行医和授徒自给,体弱多病,晚年手颤,足复瘫痪,两目失明。志既高,学又笃,著述甚富,因贫无钱印刷《读书论世》。张潮慷慨助刻,令其十分感激。“先生成言是践,命工付锲,俾垂死之年得附骥尾,不朽之业实心斋先生造之矣。”(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58页。此处绝非客套之语,张潮改变了该书极有可能湮没的命运,可谓作者、刻者共成“不朽之业”。刻书家是版权的直接拥有方,即使作者本人刻印书籍也要自备印资或纸张。吴肃公向张潮索《读书论世》廿余部,奉上一两六钱,买纸一篓。遇到版权纠纷与作者无关,“刻书家以卖书糊口,若被他人翻刻,则难以觅利,空费刻赀,是以必究之尔”,“就著书者论之,方喜人刻之不暇,岂肯禁而究之耶”。刻书家的署名和声望直接决定了书籍销量。张潮耗时三年、捐资七百余两白银刊刻了江都张中逵遗著《四书会意解》,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张中逵子张庸德分别索要酬金八十两银,令其惊骇且怒,“纵不能贴费,亦当感潮表章之功,何乃呶呶不休耶”,且欲将板片卖去解决生计。只是,“恐此板卖与他人之后,未必能行。盖潮素有薄名,世所共知,是以京省坊客肯要。若换去‘张山来’三字,势必与前大不相同也”(《与张紫裳》)。(9)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83—484页。中晚明以来书籍市场竞争激烈,刻者“张潮”而非作者“张中逵”的声名成为征逐读者群与效益的利器。
(二)联手合作的生成方式
张潮的书籍生成是群体相互交流、共同切磋的产物。王晫(1636—?),初名棐,字丹麓,浙江钱塘人,擅诗文,广交游。家既没落,然喜刻书,有《遂生集》《今世说》《霞举堂集》等。《檀几》的问世与王晫、张潮康熙三十三年(1694)西湖订交直接相关。张潮自陈:“甲戌初夏,于湖上晤王君丹麓。廿载神交,不期而会,固已大乐,而丹麓复出此编,相示披览。”(《檀几·初集序》)(10)王晫、张潮:《檀几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王晫将四方士大夫相赠文稿随手抄录,辑为《檀几》,因资金匮乏,无力付梓。张潮蓄有此志数年,只恨藏书不广,搜辑维艰,故欣然受命。王晫提供的时贤杂著37种成为初集主体,刻成署名“武林王晫丹麓辑,天都张潮山来校”。随后,两人复谋二集。王晫辛勤收罗:“谨呈样书十七种以备采择,加以《俗砭》《仕的》,并先生之收藏及阮亭先生所寄,或可足五十之数。倘尚缺几种,乞示来,以便广搜报命。”(1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81页。余集编刻中,王晫热心如故:“谨仿斗方之例奉呈九首,并开一目。中选者乞于顶上加圈;如不合式,下须注明所以不选之故,发还原目见示,以便后此搜罗,庶有所矜式耳。”(1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04页。两人搜罗商榷,互动频繁。
《尺牍友声》《尺牍偶存》收录了双方超过60封书信,贯穿《檀几》三集构思直至发行的整个过程,对体例、版式、署名、序跋、校订、印刷等深入商讨,可见当时杭州、扬州等地的文人互动。(13)Suyoung Son,Writing for Print: Publishing and the Making of Textual Author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8,pp.32-42.张潮还试图调动更大范围内文友参与其间,如《逸民四史》《禽史》《禅世说》《仙世说》《说梦》《月窟》《温泉志》等书之辑,“必广征之京省各路,各路中又须各有知交代为搜讨,并酌其可存可删,然后各成一书,亦游笈中所不可少之物也”(《寄家渭滨》)。(1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46页。信札中邀请张潮合作者比比皆是。通州范国禄(1624—1696),字汝受,号十山,欲对近代名家选本选精集萃,共成《选选诗》,遂锁定其中三十种,“曾收得一半,为王仔园借去未还,今作那移之想。郡中如尊府及朱其老、席允老各处,以三法那移,一则出赀交易,一则藏本兑换,一则逐部借看”。(1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55页。作为一介布衣,范国禄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显赫的社会地位,只能求助于社交网络,是谓务实可行。
清初这类文人互相成就的书籍生成方式很是常见,“征稿”成为诗文、小说、尺牍等各体选本流行的编辑方式。邓汉仪《诗观》、曾灿《过日集》、席居中《昭代诗存》等无不借群公之力,倪匡世《振雅堂汇编诗最》书前胪列“参校诸先生姓名”达426人之多,孙默征集送归黄山诗、词、赋、文近万首,袁骏《霜哺篇》汇集约计6000人的序跋题咏。
(三)开放持续的生成形态
张潮书籍世界中传统意义上作者和文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多重阐释空间中,读者通过阅读文本的间隙和沉默,凌驾于作者意图,在开放的结构中延伸理解,文本、读者和意义处于不断生成之中。
张潮《幽梦影》历经十五年辑录成册,主体部分为219则警句和格言,刊刻之前先在亲友之间传阅,邀请评点。最终参评人数达112人,主要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一带,合计701条,远超作者文本,在同朋交流意义上达到了空前程度。(16)参见张慎玉、赵益:《张潮〈幽梦影〉之成书及其同朋小品丛书略论》,《安徽文献研究集刊》2004年第1卷,第143—158页。根据人物卒年推断,最早当为纪映钟(1609—1681?)、施闰章(1619—1683)的评点。康熙三十三年(1694),同乡江之兰寄来评语。康熙三十四年(1695),冒丹书、王棠应命评点。是年,袁启旭承诺为《幽梦影》写作序言,且因入京之便代恳诸家评点。康熙三十五年(1696),张道深流寓扬州,与张潮相识,“妄赘琐言数则”,(17)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73页。实为83条之多。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淦、尤侗、顾彩寄来点评。是年《幽梦影》首次镌刻,共附350条评语。出版的最大特点是留有大量无字空行,共有刻版匠人故意未加触动的、宽窄各不相同的空白150处,以待增入补评。
随后,张潮频繁寄书京城文友代索评语。“其辞不须过誉,即与鄙意相反,或嬉笑怒骂皆无不可也。”(《再寄朱赞皇》)(1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88页。其策略不在于寻找作者的原初意义,读者的文本解读与作者的意图投注甚至可以互相矛盾。是书反响热烈,各家评点奔涌而来,时间跨度极大,第五则的十条评语前后相隔十年之久。(19)[美]戴廷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法]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0页。读者全程参与了文本创造,形成了众声合奏、交互阐释的对话模式,极具现场感。书籍不断增刻新收评点,众多版本即是这一出版历史的见证。
书籍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还表现为分期选刻、连续推出,这是张潮刻书世界的独特形态和自觉追求。《虞初新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初刻,书前题有“康熙癸亥新秋心斋张潮撰”。康熙三十二年(1693),“先以八卷成书”(《寄余澹心征君》)。(20)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52页。康熙三十八年(1699),“今续增四卷,共十二卷”(《寄谢阁学文宗张朴园先生》)。(2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22页。康熙四十三年(1704),“今又续成八卷,共二十卷”(《复张渭滨》),(2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67页。总跋题为“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张潮识”。他还将内容博洽的同朋小品以丛书的方式分期刊行,规划出先后接续的年度出版形态。《檀几丛书》初集成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二集成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余集成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昭代丛书》甲集成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乙集成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丙集成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这些书籍编刊改变了传统以作者为中心的生成方式和静态凝定的出版样貌,发展为以编刻者为核心、庞大交游为支撑的群体参与工程,印刷也并非出版的最终环节。在书籍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中,刻者、作者与读者产生了频繁互动,呈现出自我建构、动态开放的特征。
“文人共同体”中的书籍流通
《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中书籍涵盖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商品流动和依循人情网络进行礼物流动两个视角,张潮主动以书籍为媒介,穿行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和社会阶层,编织成一个更大的“社会文本”,获得一种秩序和意义。
(一)刻本崛起世界的写本环流
张潮以经营盐业致富,经济实力为文化活动提供了支持,是旅扬徽商积极参与刻书和文化传承的典型。其作品最初以抄本流传,为满足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遂充分发挥出版快速复制文本的优势。张潮刻书版口均镌“诒清堂”字样,缥缃秀整于外,琳琅触目于中。这些出版文本一旦进入阅读领域,具备了大众传播的属性,极大推进了知识在社会、地理层面上的交流,拥有了规模庞大的当世读者群。以江浙为中心,进入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四川、北京、福建、江西、湖北、陕西、山西等地,引领了文化消费的热点,覆盖之广、流布之速,代表了商业出版渗透的深度和广度。书籍与社会阶层具有关联,《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中的文人阅读较少经史考据,如张潮《檀几》《昭代》、李渔《十二楼》《闲情偶记》、郑旭旦《汉宫秋》《金焦记》等,呈现出随意自娱的阅读趣味。尽管清代江南是考据学的主要阵地,这些事实的浮现或许超越了个案的意义,代表了普通文人书籍生产和消费的真实面目。
《尺牍友声》《尺牍偶存》中还延续了“写本”的文化传统,在关系密切的小众文人圈中投赠往来,具有惊人的高比例。张潮将《花影词》稿本呈于余怀、狄立人、李沂、聂先、卓尔堪诸人。《笔歌》是张潮首次写作的杂剧散曲集,收录《瑶池宴》《穷途哭》《乞巧文》《拜石丈》四部短剧,一经脱稿,迫不及待地寄赠孔尚任,今天一阁存康熙刻本即附有孔评。这些写本的分享对象事先经过刻意选择,建立于信任的基础之上,覆盖官场与民间,对方在文本阅读时作序、圈点、删改,交流循环中发生了增值效应,推动了文本文献的有效凝定。
对于中下层文人来说,因卷帙浩繁、资金匮乏等导致了稿本形态的流转极为普遍。闵麟嗣将《史惧》寄给张潮时叮嘱:“此册乃弟力疾草成,苦无副本,千祈留神。”(23)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85页。吴陈琰,“生平杂著甚夥,苦无缮书者。是以草本多藏箧衍”,(2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28页。寄来《登科录记》《放生会约杂说》。这些稿本多数早已亡佚,甚至不见著录,尺牍中的零散记载保留了清初文人的著述事实。为了避免稿本流通可能导致的遗失甚至覆灭,遂以副本流转,形成了文本的二次抄写传播,其中不乏稀见之书。徐世溥《江变纪略》全书统用南明隆武、永历年号,记载金声桓、王得仁抗清之事,文笔奇诡,清初该书通过抄写秘密传播。故梅庚对张潮特别交代:“向从西昌仅抄得此册,祈留原本勿失,或先命侍史写一副本,即寄还为嘱。”(2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69页。抄写有助稀见之书脱离封闭状态,这也是该书在晚清收入丛书之前主要的流播方式。
事实上,16—17世纪刻本与写本共存是东西方的普遍现象。清初写本仍是文本传递的重要媒介,塑造着刻本的内容和形式。它带着强烈的私人特质,形成了私密的流转圈域,虽然路径简单、速度缓慢,但对控制流通范围和促进文人交往发挥了独特功用。
(二)多元的流通渠道
晚明以来,书籍市场形成日益成熟的贸易网络和流通体系。张潮在《昭代丛书》乙集《凡例》中广告同侪:“倘果癖嗜疮痂,何妨略偿工价。每书百页,宝银五分。或同志醵金合印,或携赀转觅坊间。”(26)张潮等:《昭代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此处透露出刊刻书籍的多种流通渠道,书坊亦在其列。王晫密切关注张潮丛书的坊间流通,“前后两集谅俱发坊,敝乡书肆尚未曾见,岂武林与维扬书贾不相通耶?不识何法得使各省风行为妙”,(27)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81页。建议覆盖更广的区域。明末清初的出版市场中,多数书籍的定价极有可能低于1两银,介于1钱到1两银的很多,张潮丛书的售价大致为“六钱三分”“四钱八分”。他善于捕捉需求,重视营销策略,寄给陈鼎丛书各以数部,“附上封面数张,烦付各书坊,粘贴肆中,如欲得书,听其买纸来印。至于板头,可以从轻,止得加一足矣”(《寄复陈定九》)。(2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05页。陈鼎将封面悉发各坊,这一广告颇为奏效,很快收到多处订单。不仅如此,他还以敏锐的目光发掘潜在的商机,预测“十月间书客一到,必蜂拥要此书,坊间必怂恿来印”。(29)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14页。清初北京成为全国书籍的又一交易中心,与江南桴鼓相应。张潮瞄准这一新兴商机,除了书坊“买纸来印”、交付板头钱的策略外,还将板片直接交予坊主,开拓京城书籍市场。“闻都门颇多购者,近扬州有一坊贾,付与板片似可放心,将来可以发兑矣。”(《寄王丹麓》)(30)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92页。这位扬州坊贾极有可能投资京城开设书坊分店,此举表现出灵活的商业运作和合作意识。
书肆贸易之外,同朋之间的书籍获取一般通过邮寄实现,先寄往各城镇交通便利的店铺,再送至本人手中。邮寄书籍在文人之间需求量极大,清初区域间的流通却远谈不上发达。余兰硕曰:“旧在金陵,刻有近稿四卷,借光大名,欲呈教削,奈无便鳞可寄。”(3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00页。卓尔堪言:“汉如居吴门,往来邮寄不便。”(3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11页。张潮感慨:“拙选颇多,艰于邮寄。”(《寄吴舒凫》)(33)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49页。江淮地区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更可想象。此时已出现专门邮书之人,沈思伦云:“邮书者云开正旋里,曾托领回音,或即属之此人亦可。”(3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70页。只是“云开”等邮人尚少,且耗时长,存在遗失风险,偏远地区尤其如此。葛常夏云:“沭距维扬道里不甚辽远,奈僻处淮朔,邮人裹足,欲觅一便鸿,终岁间不一二值也。去冬、今正二次小札,俱寄至东大店托戴友转达,直至二月间始接后次报章,而大著、佳箑仍不知浮沉何所。”(3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10页。这类书籍丢失尺牍中提及的至少有10次以上。
“便邮”“的邮”求而难得,于是熟人托带成为必要补充。陕西张鼎望嘱咐:“今后如承寄书,须托申舍亲或员舍亲,觅三原妥人付之,庶不致浮沉损湿。其卷帙如多,即与彼言明到家之日,望即补其脚价,则彼自不畏难矣。”(36)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68页。“脚价”当是收书时额外补贴的费用。扬州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张潮凭借水陆交通,形成了多元的书籍流转网络。其中,运河、长江以及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渠等尤为便捷,张潮委托文士、商客乘船之际运书各处。“兹以坊贾之便,寄上《甘泉宫瓦考》《瘗鹤铭辨》《昭陵六骏赞辩》各五十帙。”(《寄大司寇王阮亭先生》)(37)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34页。“客岁曾具数行并板片附上,系答项舍亲盐艘。”(《寄复程雯修》)(38)张潮:《尺牍友声集》,第465页。这些均是对清初扬州书籍流转路径、工具和数量的记载。
(三)书籍交际中的社会关系生产
社会中个体借助物质、文化、符号等资源维持且改进现有秩序,《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中的书籍之交具有多重维度,牵涉可观的文本与人物,这些细碎的交际背后是社会各阶层的微妙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意味深长的关系生产。
张潮试图接近政治权力中心,交游显要,主动向位高权重之人赠书。岳乐(1625—1689),努尔哈赤孙,饶余郡王阿巴泰第四子。岳端(?—1704),字正子,岳乐第三子,喜接文士,善诗词。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潮向岳乐父子分别寄去父亲张习孔《大易辨志》《近思录传》《诒清堂集》《云谷卧余》以及自己著述12种,“俾草野俚鄙之词,得接于屏藩之几席,其为荣幸,永世难忘”(《上勤郡王启》),(39)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41页。可谓极尽谦恭。这种通过刊刻家集赠送他人的交往方式盛行于清代文人之中,因为整个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都是从一开始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的,那些具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更是占尽便利”。(40)[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潮向孔尚任致书18通,其中涉及赠书的有13通。康熙三十六年(1697)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张潮写给王士禛的18封尺牍中,有15封主动赠书。书籍是张潮进入上层社会的通行证,通过四处投赠展示才华,得到一定程度的价值实现。李上德告知:“随呈主人大司徒马公,并旧主人显府殿下又三阿哥殿下。读大稿者,无不称快。”(4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05页。这是典型通过书籍实现自下向上介入的成功案例,具有强烈的功利意味。
张潮与中下层文人的书籍社交更为日常,“发起者”与“回应者”体现了单纯文化层面的交流。李淦以游记为贽登门拜见,张潮印丛书二十部以贺王晫五十大寿。梅文鼎有《舟过维扬张山来惠新刻六种》:“扁舟渺渺过芜城,长夏薰风放棹轻。久别故人重握手,相遗书卷慰平生。名山著撰原家学,通邑交游足友声。披读泠然炎暑失,扣舷高咏斗牛横。”(42)梅文鼎:《续学堂诗钞》,《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在名目繁多的交际中,书籍均是恰到好处的礼物,伴随着情谊的传递和维系。借阅也是文化交游的形式之一,以交换传览进行书籍资源的流通。其中还可看到女性的身影,张潮寄给吴舒凫、李德两夫人以及倩扶、偏红两校书小刻数种,实现了跨越性别的交流。当然,书籍交往中需要根据人际距离及“差序格局”斟酌分寸,作出恰当性和情境性的回应,主动或被动,且数量多寡不一。这些细微脉络牵动起人情关联,建立起书籍交流世界的秩序。
张潮以新刻书籍频繁开展社交,涵括不同阶层,送出远远超出回赠,整体呈现出单向的流动,在“强连带”之外发挥“弱连带”优势,(43)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理论,认为通过“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互惠服务的内容”四个维度的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强连带、弱连带和无连带。“媒介者”主动引荐亲友进入这一书籍社交网络,如同波纹漾散开去,带来人际关系的延伸。从社会交换的逻辑来看,文化资本是比经济资本更隐蔽的传递,赋予了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权力,是形塑自身的有效策略。张潮的书籍世界由众多以书投合之人构成,其交游圈正是在这类慷慨赠书的推动下猛烈生长、日益细密,最终达到群体集化的目的。
“文人共同体”的形成探讨
《尺牍偶存》《尺牍友声》中文人在依稀可辨的交游情境中,围绕着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因精神、文化乃至现实利益等高度一致,群体凝聚成超越血缘师承和地理空间的交际网络,具备了“共同体”的特质。其形成具有多重因素:
(一)布衣文人的意义追问

王鸿泰指出,明末清初士人的生命活动处于两种场域之中,“一则为科举之场域,另一为‘艺林’之场域,这两者各自衍生出不同的社会价值”。(48)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事实上,多数士人失意于场屋,落魄于功名,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或者处于政权的边缘,于是致力于寻求新的“意义世界”,其动向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他们通过出版的介入,以文化的显通来获得身份的确证,这是与强悍政治抗衡的仅有方式。即使如张潮场屋蹉跎,选择以经营盐业治生,最终仍然回归到从事书籍生产,以获得文化资本。书籍变成一种有力量和地位的事物,布衣文人将生命投注于此,舒缓场屋失意和功名落魄,这一职能的强化开启了社会发展的新契机,带来了底层文学的发达。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收录文人共计19700名,其中布衣逾半。这一阶层成为影响清代文坛的重要力量,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深刻变迁。
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争取合法性的斗争领域,文化是一种权力形式,具有独立于经济与政治场域的自主性和实施法则,获得了符号权力,亦即把现存的社会安排加以合法化,逐步发展、传播并控制自己独特阶层的文化。(49)[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148页。于是,以“留名”为深层心理诉求,尺牍作为一种特殊文体,选本超强磁力地吸附了许多底层寒士。其中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影像具有象征意义,堪称属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文献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布衣文人克服沉重的生存压力,究心书籍,前赴后继,为清代文学史和学术史的建构提供了丰富文本,带来“文柄下移”的新变。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是书籍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军,形成一个既相对稳定又动态发展的结构模型。作为共同体的底座和基石,他们为探讨历史深处的关键节点提供了一个维度。
(二)社会交往中的群体认同
社会网络化是明清社会的特征之一,文人好交乐游的时代风气极为盛行。交游代表着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交换、流动、移植、扩张,人际关系在社交场域中不断突破血缘与地缘的先天局限,跨出环环相扣的熟人世界,组建出迥异于“乡里社会”的形态。文人热衷于在艺文社交圈内,通过社会关系的自觉连接,建立起一个跨越地域,以声名为中心,同侪、师友、亲故交织而成的,伴随着物质赞助、信息传递以及书籍生产流通等互动的社会关系集合体。经由社会声望与人际网络的建立,进行社会关系的创造和社会价值的追求,表现出“权力再生产”的特征。其中,艺文活动是贯穿始终的线索,形成了文人集结异常兴盛宏大的文化生态,生成了丰富多趣的群落。文化的优越感带来对中央政治的淡薄和疏离,为文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促使文人群体完成了集体转向。清初这些科举落第或久试不售者,生活上的窘困和精神上的压抑令其身心皆有漂浮无力之感。随着数量的增多,带来了群体意识的高涨。在阴郁屈辱的生存处境下,“抱团”是他们寻求自我精神救赎的途径,借由各种人际交往,在交错重叠中构建身份与群体认同,心灵共同结成了一个“场”,以弥合与外界社会的裂痕。
清初尺牍成为文人交往的重要方式,最宜吐露心声、抒愤立言、问慰砥砺。《尺牍偶存》《尺牍友声》在持续的生成和传播中,容纳了多种声音,相互关联,具有互释意义,形成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空间”。现实世界中分隔的个人在尺牍中联结起来,结为精神同调,达到理解或一致,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又一标志。王鸿泰在《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一文中说:“信息的流通,已经交织出一张相当繁复、密实的传播网,这个传播网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场域,它深入一般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将被现实生活分割的民众重新整合为‘公众’。”(50)陈平原等:《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尺牍偶存》《尺牍友声》的刊行具有交际属性和广告功能,是穿越社会距离的管道,成为文人讯息和文学批评的集散地,制造出共同凝视的焦点和参与的空间,实现了跨越社会层级、地域、性别隔阂的多向互动和文化认同。选本被想象成充满信赖的舒适庇护所,营造出生动的“在场感”。空间上各自分散的读者,通过尺牍选本的阅读,享有一个共同的“公众场域”。
文人通过书信联络声气,共处于选本建构的文本世界中,离群索居或匿影荒乡者产生“吾道不孤”之感,以集体的力量消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挫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到安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基于此,以意气相投、文化自觉为基础的浮游士人,在书籍的世界中凝结成庞大的社会存在,砥砺提携,个人和群体的能量、资源均得到了增殖,形成了游离于主流社会、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文人共同体”。他们不是匀质化的扁平存在,呈现出立体的形态,通过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产生多向维度的关联,创建出一个意义空间,确认了作为特定阶层在知识场域中握有的权力。
(三)灵魂人物的建构与维系
领袖群伦人物的出现对于“文人共同体”的建立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康熙十年(1671),张潮侨寓扬州,雅好艺文,交接广泛,闻名遐迩,是当之无愧的好客主人。张潮笃爱故交寒士,善交久敬,《尺牍友声》中文友的各类求助超过50处。兹举吴应麟之札为例:“愧窃黉宫,家寒祚寡,穷经半世,未叨一遇。加以嗣息维艰,弟早鳏居,止存一侄,寒门宗祧,赖有此耳。不意客岁弟方幞被游都,秋时阿咸夭丧。应麟正悼伶仃,旋婴二竖,渐入沉疴。东主辞归,无枝可托,累居贫友村庄,呻吟枕箦。于兹五月,揭典皆空。妻泣饔飱,人悲身后。”(51)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57页。布衣寒士屡遭劫难,为避免亡侄暴尸荒野,向张潮告此不堪。如此危疑急难,张潮辄倾身赴之,无少趋避。又如,冒丹书言其经纪贫友之丧:“他乡客处,赖有先生厚敛,何减古人!诚所谓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也。”(52)张潮:《尺牍友声集》,第171页。可见古道高情、吊死恤生之义,深孚众望。张潮乐于接纳全国各地的文人,艺文社交圈逐渐成形,穿梭编织,营造出了凝聚大江南北文人雅士的文化场。
在清初蓬勃发展的商业出版中,张潮积极投身图书编纂,《尺牍偶存》《尺牍友声》等进入文人公共传播领域,助推了交游版图的拓展,书籍生产和流通成为其交际的手段和塑造个人形象的工具。张潮持续推出非经典性与非严肃性的小品丛书,寻求精神自足和个性释放,满足了特定群体对陌生、闲适、娱乐、消遣知识的阅读期待,构成了一个饶有意义的书籍社会,实现文化交流与人际扩展的双重功用,借以烘托自身的文才艺能和儒雅襟怀,文化威望因以树立。梁嘉稷曰:“天下读其书者,如见其人。即未读其书者,亦莫不想望风采,购求其书,而愿纳交于其人也。”(53)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86页。这些淡化道统、书写心声之作以漫话与絮语式的形态,与中晚明追求主体精神独立、突破传统秩序限制、崇尚好奇炫博的风气一脉相承,呈现出在文化领域内“推迟了的朝代变迁”这一特殊现象。
不仅如此,张潮道义素心,不遗余力地访求贫寒文友之作。邓劭荣,字若雍,邓汉仪次子。其致书张潮曰:“拙选《四集》已梓多篇,特恳瑶章赐教,以光枣梨,幸甚。余澹翁昨以新诗一帙,付荣授梓,而行李匆遽,未能自备杀青之资。荣思风雅而兼具肝隔者,惟先生一人。”(54)张潮:《尺牍友声集》,第98页。《诗观》有无《四集》是学界公案,这则材料可谓一锤定音,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邓劭荣继承父亲遗志编选过《四集》。张潮恐文友著述散佚失传,不仅为余怀等人承担刻资,还助刻黄泰来《清诗片玉集》、张炳睿《手让文》、孙默《国朝名家诗余》、卓尔堪《曹陶谢三家诗》《遗民诗》、陈鼎《留溪外传》等,其仗义轻财、表微阐幽之举海内共推。这是树立自身文化形象与提升社会地位的契机,个人声望在书籍社交中持续攀升。梅文鼎感叹:“刻古人书者多矣。同时之人,而不惮表章,且久而靡倦者几人哉!”(55)张潮:《尺牍友声集》,第244页。文人争与之交,声名鹊起。葛常夏赞曰:“文章道义为海内第一人。”(56)张潮:《尺牍友声集》,第301页。张潮置身于这一无形却又实实在在运行的“文人共同体”的中心,是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突破了“社团”等形式化、组织化和固定化的社交形态,形散神聚,形成“我们在一起”的文化表现方式。
张潮围绕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建成的“文人共同体”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可以把一大批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布衣寒士的事迹带出历史的海平面,提供了展示他们生活和交往的绝佳样本,还能深入倾听到一般政治史、社会史无法触及的精神史和心灵史层面的潜流翻滚,进行忠实、细致又贴近历史语境的描述和诠释。
余 论
康熙三十八年(1699)张潮遭诬入狱,此后一蹶不振,对这一“文人共同体”无疑是釜底抽薪。同时,主流文坛雅正之风逐渐形成,散发着雍容典雅的恭顺气息,以娱乐消遣为旨归的小品文遭到贬抑。政治焦虑在张潮为中心的印刷世界始终存在,随着国家力量强势介入对文本权威的争夺,官方审查机制日益严苛。王汎森认为:“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57)王汎森:《权利的毛细管作用》(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6页。以张潮为中心的“文人共同体”在“涟漪效应”下有命运共同体的意味,且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易受伤害的状态,它永远需要警戒、强化和防御”。(58)[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乾隆四十三年(1778),禁书史上的“去钱谦益”运动拉开了帷幕。张潮《虞初新志》因收录钱谦益《徐霞客传》《书郑仰田事》以及徐芳撰《柳夫人小传》遭到禁毁,导致了流传过程中因畏祸进行的剜改抽换和极为复杂的版本状况。乾隆四十六年(1781),《昭代丛书》因《板桥杂记》收钱谦益绝句八首,遭到两江总督奏缴抽禁。清朝为了树立统治权威,高张文网,加上告密诬陷恶习,文厄遂以风行草偃之势席卷而来,不但著者自身难保,而且累及书籍生产和流通各环节的参与者,丛书或选本因为收录诸家之作承担了更大风险。这或隐或显改变了群体心态,创伤性经验下人人自危、收敛心声,必然导致这一“文人共同体”的衰落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