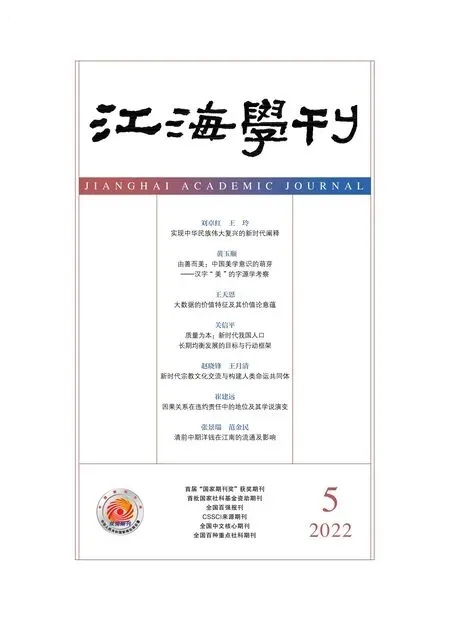六朝美学两大主潮: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
祁志祥
六朝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六朝美学是一个众说纷纭而又充满魅力的话题。关于六朝美学,现有的中国美学史或断代美学史的阐释不够简明,也不尽准确,影响很大的宗白华先生的概括实际上似是而非。宗先生认为从“魏晋六朝”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镂金错采’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1)王德胜编选:《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宗白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按照这种论断,谢灵运诗代表的“初发芙蓉”的美远高于颜延之诗代表的“镂金错采”的美,是“魏晋六朝”的主流,并在唐宋以后不断发展壮大。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史,就分两个阶段:汉以前偏重“错采镂金”之美,魏晋六朝以后偏重“芙蓉出水”之美。笔者过去也曾对这个论断深信不疑。然而,随着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这个论断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汉以前与魏晋以后美学追求两阶段论是一种简单化的分期,不符合六朝前后美学风潮马鞍形演变的三阶段实际。现撰此文商榷辨析,希望对人们准确把握六朝美学时代特征有所帮助。
汉代美学特征:以道德理性为美、以“情欲”和“淫丽”为丑
六朝美学是以汉代美学为发生演变的历史前提的。汉代美学的时代特征是什么呢?六朝美学对它是继承居多还是反叛为主呢?
美学是情感学。美是关乎情感快乐的。而在情感快乐背后,有着思想价值的主宰。人们永远不会对不以为然的对象产生快乐并以之为美。在审美实践中,美实际上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2)参见祁志祥:《乐感美学》第三章《美的语义: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101页。明白了这个真谛,我们分析某一时代的美学特征,就不会脱离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从而犯方向性错误。那么,六朝所面对的汉代思想界,价值取向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性善情恶”。这个价值取向是怎样形成的呢?
汉朝是在推翻秦朝暴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何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是汉代政治家、思想家耿耿于怀的严峻问题。陆贾告诫汉高祖:天下可“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打天下用霸道,但治天下必须用仁政。文帝时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取与守不同术。”取天下贵“诈力”,守天下贵“仁义”。秦朝覆亡的教训归结为一条,即“攻守之势”转化了,但“仁义不施”。武帝时期的董仲舒总结说:“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也。故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33页。君王如何使“万民往之”呢?根本方针就是实行以民为本、爱民利民的仁政。君王保证民利,就必须克制自己追求享受的情欲。君王为满足一己的享受亏夺民财,与民争利,必然致使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所以道家的清虚寡欲与儒家的爱民利民就殊途同归,走向合一。整个汉代,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虽然有过消长,但从未分离过,始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汉初,无情无欲、虚静无为的黄老学说为主,但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并未缺席。陆贾《新语》提出“行以仁义为本”,贾谊《新书》提出“民无不为本”,刘安《淮南子》强调“民者国之本”,主张“仁君明王”“取下有节,自养有度”,皆然。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道家的清虚淡泊、绝情去欲思想一直也没有消失。可以这么说,在整个汉代四百年中,儒家的爱民利民学说是政治本体论,道家的绝情寡欲学说是政治方法论。由于情欲与亡国之祸密切相关,所以为“恶”;淡泊无情的道家道德与以礼节情的儒家道德为天下长治久安之所必须,所以是“善”;这两种道德都属于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以汉人提出一个独特的价值命题——“性善情恶”。
关于“性善情恶”,汉代思想家是怎么阐述的呢?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从道家道德角度,首先提出“道善情邪”“性善欲累”。稍后,董仲舒从天人感应、阳善阴恶的角度论证“阳善阴恶”“性仁情贪”。人性就是贪与仁、利与义、情与理、恶与善的统一体。做人就当以“义”制“利”、以“礼”节“情”。西汉后期,扬雄继承董仲舒的二重人性论,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的命题。(4)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5页。“恶”指“由于情欲”,“善”指“由于独智”。东汉班固记录整理的《白虎通义》专设《情性》篇,将天赋的“仁义礼智信”叫做“五性”;将天赋的“喜怒哀乐爱恶”叫做“六情”,按照阴阳决定论的思路重申“性善情恶”。王充继承扬雄的思路,在《论衡·率性》中重申:“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这“恶性”是“饱食快饮,虑深求卧,腹为饭坑,肠为酒囊”的“倮虫”属性、动物情欲,“善性”则是超越“倮虫”属性的高贵的“识知”属性、理智属性。再后来,许慎《说文解字》中将“阳善阴恶”“性善情恶”的共识通过文字训诂的方式综合起来、巩固下来:“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东汉后期诞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则明白地概括:人性“半善半恶”。
在“性善情恶”价值理念的主宰之下,人们以放纵情欲的形象为不快的丑、以克制情欲的理性形象为情感欢乐的对象,便成为汉代占主导地位的审美观。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指出:“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从天下万物只能被情欲主宰,而人类可以凭仁义主宰情欲的对比中,董仲舒得出了“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的结论。(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466页。就是说,在天下万物中,“人”最高贵、最完美。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这样完美。由于情欲的作用,就出现了上、中、下三类人:一是无法教化、始终被情欲主宰的,这叫“斗筲”之性,属于丑陋的“小人”;一是教化得比较好,但还存在问题,因而有理有情、有善有恶的,这叫“中民之性”,属于美丑并存的普通人;还有一种是完全能够以理节情、仿佛无情无欲的,这叫“圣人之性”,属于尽善尽美的“圣人”。这便是“性三品”论。扬雄《法言·修身》本此提出“性三门”论:“由于情欲,入自禽门;由于礼义,入自人(普通人)门;由于独智,入自圣门。”圣人有智而无情,这就叫“圣人忘情”(6)晋人王戎语,可视为对汉人思想的概括。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0页。“太上忘情”。用以“善”为美、以“道”为美的观点去看世界万物,不仅圣人、君子的人格美如此,自然之美也在于道德象征,这就叫“比德”为美。刘向《说苑·杂言》记述君子所贵的玉之美在于六德:“玉有六美,君子贵之。”许慎《说文解字》释“玉”之美,在于有“五德”。汉代“美善同意”“性善道美”审美观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一直影响到三国时期。魏初何晏提出“圣人无喜怒哀乐”,直到魏国后期,钟会等人仍津津乐道。文学史上为人赞美的慷慨悲壮的“汉魏风骨”、寄托遥深的“正始之音”,其实是汉代道德为美、兴寄为美思想的余波。

汉代以克制情欲享受的道德理性为美、以远离道德宏旨的“情欲”和“刻镂”为丑,具有吸取秦鉴,重视民本、保障民生的积极意义,无疑值得肯定。不过,它也有过分、片面之处值得矫正。机械、笼统地断定“阳善阴恶”“性善情恶”,简单、片面地标举“圣人无情”“太上忘情”,对人的情欲的正常需求及其对形式美的合理喜好形成了过度挤压,剥夺了情感美、形式美的存在权利,埋下了严重禁锢自然人性的隐患。正是汉代对情感美、形式美愈演愈烈的长期压迫,引发了魏晋玄学“逍遥适性”启蒙思潮的爆发,催生了六朝情感美学和形式美学两大潮流。
魏晋玄学的两种追求及其主导形态
魏晋玄学“逍遥适性”的启蒙思潮,是为反叛汉代对自然人性的过度压抑而生。而它依据的前提,正是汉代思想界长期的儒、道合一。当然,魏晋玄学对儒、道思想作了重新组合,提出了自然适性、解放人性、解放情欲的人生主张。而这当中又经历了三部曲。
首先是提出“适性”“自然”的主张。其中,“适性”是更重要的核心概念。“自然”指自然之性,即天性。“适性”指适合、顺应万物的自然之性。魏晋玄学以庄学为圭臬。庄学的核心是“适性”。庄子屡屡强调:“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不失其性命之情”。在庄子看来,万物只要顺应自己生命的天性,就能达到“至乐”“自适”“逍遥”的完美境界。魏晋玄学将庄学的这个概念截取出来,高举“适性”的大旗,对此作了充分的诠释和发展。于是“适性”成为魏晋玄学的新的价值追求,也成为魏晋玄学的独特美学追求。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郭象的《庄子注》。《庄子·德充符》郭象注曰:“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则万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则天下一是也。”《逍遥游注》主张万物“各安其性”,指出形体有大小,能力有高下,但只要“适性”,皆可自得逍遥。郭象所说的“适性”之“性”,既指万物不同的自然本性,也指同一物种中各个体能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下、命运的好坏等。他阐释“适性”,用心更多地是强调不同物种、不同能力地位命运的个人都应安于自己天生的命定的生命本性,量力而行,追求自己的本分,不做力不能及的事,从而保证自得其乐,不徒生苦恼。
但是魏晋玄学并未在这个主题上过多停留。魏晋玄学更感兴趣的是人性的解放。那么,人性是什么呢?道家传统的看法是清虚淡寞、无情无欲之性,儒家的传统看法是仁义礼智、克制情欲之性。于是“适性”的原初涵义就是去除好恶、不动声色,具有“雅量”。唐代陈子昂崇尚的“汉魏风骨”“正始之音”,与此是同物异名。这是魏晋玄学的第二主题。从何晏的“圣人无喜怒哀乐”,到“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嵇康《释私论》所说“达乎大道之情”,“志无所尚,心无所欲”,“乃为绝美”,阮籍《清思赋》所说“形之可见,非色之美”,“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都是要求顺应道家所说的清虚无欲的道德之性。玄学还兼取儒家的人性观。在儒家看来,智慧、理性是人特有的本性。以此要求“适性”,结果就是以理节情、以智制欲。据何劭《王弼传》记载,魏初的王弼批评何晏的“圣人无情”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他指出“圣人”不是没有情感,只是“神明”、理智比一般人发达,能够以此克制情感,使情感不为物所累罢了。魏国另一位以研究人才学著称的刘劭也认为,“圣人”令人“不可及”的高明之处是理智的“智”。其《人物志序》指出:“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这个“聪明”的理智,使人能够认识“中庸之德”,使情感的活动处于“中和”状态,不逾礼教规范。晋人张辽叔在《自然好学论》中提出,人生来具有“好学”的天性,这就叫“自然好学”;而学习、修养的内容,就是“六经”和“仁义”。向秀《难〈养生论〉》也认为,“智”与“欲”都属于“自然”人性。当两者发生矛盾时,“适性”就应当走向以“礼”节“欲”。郭象《庄子·天运注》以儒释庄,认为“仁义者,人之性也”,“适性”应当以“至理”“遣”情。在控制情欲、毋使过分这一点上,儒家的“以智节情”与道家的“虚无去情”走向融合。于是,喜怒不形于色,泰山崩于前而不乱,就成为令人仰慕的“魏晋风度”。《世说新语》称之为“雅量”,东晋大将军谢安是具有这种“雅量”的杰出代表。
这种“魏晋风度”,与汉代的“太上忘情”一脉相承。表面上叫“适性”,实际上是对自然人性的压抑。它不是魏晋玄学标举“适性”的真实用心,也不是魏晋玄学“适性”追求的主导涵义。在利用传统树立了“适性”这面大旗之后,魏晋玄学便对“适性”的涵义往解放自然情欲的方向作了改造,“适性”即适应、顺从人的情欲天性。这是魏晋玄学的第三大主题,也是玄学“适性”追求的最终用意和主导涵义。
在这种改造中,魏晋玄学对儒家和道家的人性观作了重新截取。一方面,取用儒家情欲本有、不可去除的人性观,承认“情欲”是人的天性的事实,否定并取代道家“无情无欲”的人性观。另一方面,吸取道家“无思无虑”的人性观,否定和取消儒家“贵智”的人性观和以智节情、以理制欲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要求顺应有情有欲的自然人性,挣脱不符合人性的名教纲常。于是,“适性”就走向了人的情欲本性的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表现出思想的矛盾和言行的背离。嵇康一方面声称“心无所欲”,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性以从欲为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行动上,嵇康“滋味常染于口,声色已开于心”。阮籍一方面宣称“自然”之“道”以“无欲”为特征,另一方面又批判压制人欲的“礼法名教”不但不是“美行”,反而是“束缚下民”的枷锁,把按儒家名教“束身修行”的“大人先生”比作裤裆中的虱子。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与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相互唱和,肆意饮酒,酣畅纵歌,放浪形骸,不拘规范。《晋书》列传十九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阮咸更狂放:“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8)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第609页。时人不以为丑,反以为美,谓之“七贤”。《世说新语》记录了大量这样的事迹,谓之“任诞”。
显然,“任诞”与“雅量”同为“适性”,但性质不同。与不动好恶的“雅量”相比,“放情肆志”的“任诞”是魏晋玄学的主要人生追求。今人谈“魏晋风度”,标志性的代表人物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七贤”,即是显证。
“情之所钟”与“雕缛成体”:六朝美学的两大潮流
从玄学的“适性”分蘖、发展、壮大起来的“任诞”追求,旨在反抗汉代对自然人性的过度压迫。由此给六朝社会带来的重大变化,是改变了人们对情感的原有成见,公开为“情感”的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正名。汉代认为情感是恶是丑,六朝则认为情感是善是美。汉代谈“情”色变,说“圣人无情”,六朝则公开声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下不及情”,(9)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第530页。“终当为情死”。(10)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第637页。“情之所钟”成为六朝以情为美的时代标志。过去人们侧重于“情”与“礼”的对立,这时则注重“礼”与“情”的相融。如徐广《答刘镇之问》说:“缘情立礼。”徐邈《答曹述初问》说:“礼缘情耳。”袁准《袁子正书》指出:“礼者何也?缘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过去连亲人死了,都应“豁情散哀”,不宜流露出过度的悲伤,这时则可以“伤逝”,毋需掩饰悲伤的情感,甚至发生因悲伤过度、为亡妻而死的事情。那个才貌双全的潘安在妻子死后写下了一往情深的《悼亡诗》,终身未曾再娶。过去强调遇事要有“雅量”,克制喜怒,不动声色,现在则说“人生贵得适意尔”,(11)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第303页。即使“乘兴而行,兴尽而返”(12)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柳士镇、刘开骅:《世说新语全译》,第633页。
也没什么奇怪。汉代崇尚文章的“风骨”之美、“志义”之美,六朝则高度强调文章的情感之美。这在这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中有大量论述。
六朝是中国美学史上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而创作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即是从原来的“言志”向此间的“缘情”转变。汉代的《诗大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发乎情”的同时必须“止乎礼义”。六朝则突出了“情”在文章中的地位。陆机《文赋》强调文学创作是“情瞳眬而弥鲜”的活动。挚虞《文章流别论》强调诗赋应“以情义为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强调文章必须“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六朝的理论家明确把文章的美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指出有情则有美,无情则无美。如陆机《文赋》揭示:“诗缘情而绮靡”,“言寡情而鲜爱”。刘勰《文心雕龙·情采》重申:“辩丽本于情性”,“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从文章之美、文学定义、各种文体、创作过程与情感的联系四方面,对情感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深刻的剖析,成为六朝文学领域崇尚情感美的标志性人物。
与此同时,诗歌评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从五言诗必须具备的“滋味”美特征出发,标举“吟咏情性”,反对“理过其辞”,主张“长歌”以“骋其情”。梁代皇室爱好文学的萧氏三兄弟以皇家之尊,共同切入文学的情感美。梁武帝长子萧统在所编《文选》的序中指出:“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也强调:“至如文者……情灵摇荡。”文章所言之“情”范围很广,不只局限于“负戈外戍,杀气雄边”“胡雾连天,征旗拂日”的豪情,以及“拔剑击柱长叹息”的仕途不平之情,还包括大量的观景、宴游、聚会、思乡之情。如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说:“或日因春阳,其物韶丽;树花发,莺鸣和,春泉生,暄风至,陶佳月而嬉游,藉芳草而眺瞩。”梁简文帝萧纲《答张缵谢示集书》则说:“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这是对晋代吟咏自然风景的山水诗的理论阐释。到了南朝,文章所咏之情,甚至包括不受礼教约束的“放荡”之情。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告诫二儿子:“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说的这“放荡”之情,包括不拘礼教、欣赏女色的艳情。晋代的山水诗、南朝的宫体诗津津乐道于风花雪月、美女容貌引发的无关道德宏旨的愉悦之情,是六朝宽容情感、肯定情感、以“情”为美的典型证明。
六朝与情感美学同时并存的另一大美学思潮是以“雕琢”为美的形式美学。它是情感美学的对应物。既然以“情”为美,那么,引发情感欢乐的绮靡华丽的对象形式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喜爱的美。因此,在汉朝被“情恶”论贬斥的“雕琢刻镂”“闳侈巨丽”的形式美,这时翻身解放,受到人们普遍的肯定和热爱。六朝流行的充满文采的形式美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首先,在生活用品中,以奢豪靡丽为美。《世说新语·汰侈》记载石崇与人斗富是典型的例子:“王君夫以饴(糖)糒(干饭)澳釜(洗擦锅子),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亦以赤石脂泥壁。”富贵奢豪的享受对象和消费方式是显示自身高贵门第的符号象征。石崇的炫耀式审美方式并非个案,类似的例子在《世说新语·汰侈》中有许多记载,不一而足。
其次,在生活和艺术中,以山水、人物的形色为美。在汉代,自然物只有成为道德的象征,才有审美的价值。到了六朝,自然山水使人愉悦的形色本身就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眄庭柯以怡颜”“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陶渊明《归去来辞》)“修竹葳蕤以翳荟,灌木森沉以蒙茂。萝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谢灵运《山居赋》)“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庾信《小园赋》)。于是,以营造山水形色之美的私家园林及其园艺美学理论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陶渊明“怡颜”于庭园,写下《归去来辞》;谢灵运“寄心”于山居,写下《山居赋》;庾信“闲居”于自家“小园”,留下《小园赋》;潘安隐居于田园,写下《闲居赋》。“极貌以写物”的山水诗在这个时候也大量涌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山云遥似带,庭叶近成舟。”(阴铿《闲居对雨》)正如这时的理论家陆机《文赋》所揭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风花雪月”,构成了六朝诗歌区别于“建安风骨”的一大特色。《隋书·李谔传》批评说:“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批评:“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出于欣赏形色之美的同一审美机制,六朝人也毫不掩饰对俊男靓女的喜爱。梁朝诞生的宫体诗正是以描写宫廷美女的美色为主要题材的。萧纲《答新渝侯和诗书》指出:“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扮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例如,梁武帝萧衍《子夜歌》云:“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萧纲《咏内人昼眠》云:“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六朝时不仅男人可以公开地欣赏女人的美色,而且女人也可以公开地欣赏男人的美貌。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安唇红齿白,“妙有姿容”,少时走在路上,“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世说新语·容止》留下了这样的评论和记录:“何平叔(何晏)美姿仪。”“王敬豫有美形。”“王夷甫容貌整丽。”“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当然,欣赏男子美貌的并不一定是女性,魏晋人物品鉴也发生在男性之间。《世说新语·容止》记载:裴令公见王戎,感叹:“眼烂烂如岩下电。”山涛评论嵇康:“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挺拔)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倾倒)若玉山之将崩。”王右军见丹阳丞杜弘治,惊叹:“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这说明,六朝人对人物形貌的美是非常敏感,态度是非常开放的。
再次是对文艺形式美规律的发现和热衷,特别是对五言诗音节美、形体美规律的发明和追求。关于诗文的这个特征,用刘勰的话说就叫“雕缛成体”,用汤惠休的话说就叫“错采镂金”,萧纲谓之“珠玉生于字里”,陈子昂称之“彩丽竞繁”。晋代的陆机、宋代的范晔、谢庄最早意识到诗歌的格律美规律。陆机《文赋》说:“暨声音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说:“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齐武帝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等发明“四声八病”说,提出诗歌音节的声、韵、调必须按照“宫羽相变,低昂互节”的规律加以组合,“前有浮声,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于是,“永明体”作为最早的格律诗诞生流行开来。萧衍、沈约、王融、谢朓、范云、萧琛、任昉、陆倕等人在齐朝竟陵王门相互唱和,号称“竟陵八友”,都是重要的永明体诗人。此后至梁、陈100余年间,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90多位诗人创作过这种格律诗。格律诗的声、韵、调之美是在对偶中错综变化的。这种齐同与变化交错的规律也渗透到词性的配对方面。而音节和词性的错综对偶之美不仅体现在诗歌领域,也在文、赋领域广泛铺开。魏晋以来,散文和辞赋不约而同地向着骈俪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美文样式——骈文和骈赋。
诗文创作“析句弥密”,(13)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讲究句与句的粘对规则;“联字合趣”,(14)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301页。强调字与字之间声、韵、调、性的交错对比,还要求规避诗歌创作的“八病”,这些都是“剖毫析厘”、(15)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301页。精雕细刻的工作。于是“雕缋满眼”,“错采镂金”,成为南朝文艺创作中突出的审美追求。汉代鄙之为“雕虫”,这时誉之为“雕龙”;汉代斥之为“淫丽”,这时誉之为“绮丽”。曹丕《典论·论文》强调:“诗赋欲丽。”陆机《文赋》强调:“遣言也贵妍。”“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颂优游以彬蔚……说炜晔而谲诳。”萧统《文选序》声称《文选》所收文章“以能‘文’为本”,“文”即“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萧绎《金楼子·立言》也强调:“至如‘文’者,唯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萧纲本此,其《昭明太子集序》批评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观点,高度肯定以文采为特征成孝敬、移风俗的文章具有经天纬地的不朽价值:“‘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刘勰。关于文章的文采美、形式美,《文心雕龙》有各种视角、极为丰富的指称和表述,如“丽”“采”“文”“巧”“甘”“华”“文采”“文绮”“文丽”“绮丽”“朗丽”“雅丽”“新丽”“缛采”“采奇”“采蔚”“雕琢”“辩雕”“雕玉”“雕画”“雕缛”“绮靡”“艳说”“藻饰”“文藻”“夸饰”“斐然”“彪炳”“文炳”“惊采绝艳”“铺采摛文”“镂彩摛文”“鸿律蟠采”“麟凤其采”“飞靡弄巧”等等。刘勰认为,文章光有情感美还不够,必须文质相称,具备有文采的形式美,所谓“吐纳经范,华实相扶”“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割情析采,笼圈条贯”“致义会文,斐然余巧”。具备文采的形式美是文章不可缺少的特征:“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其为彪炳,缛采名矣。”(16)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277页。他以孔子贵“文”和儒经、诸子为据,论证文采对于文章的重要性:“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也。”(17)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26页。“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18)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277页。在刘勰看来,不同的文体以不同的方式与文彩美相联系,他在文体论中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论析。在此基础上,刘勰还对文章的听觉美、视觉美规律作了深入探讨和精辟总结。《声律》篇论析平仄相间的音调规律和双声叠韵字的交错相间规律:“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文心雕龙》另设《炼字》篇,对文章字形美、视觉美规律作了全新的分析和系统的揭示,集中凝聚为“缀字属篇”的四项原则。“一避诡异”,即避用“字体瑰怪”、多数人不认识的冷僻字。“二省联边”,即省用同一偏旁的字。“三权重出”,即斟酌使用相同的字。“四调单复”,即把笔画多与笔画少的字交错开来使用。这些都出于视觉美的考虑。对于晋宋时诗歌的绮靡华丽特征,《文心雕龙·明诗》中有一个客观的概括:“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大略也。……宋初文咏……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以近世之所先也。”
在普遍爱好文采的风潮中,不讲格律雕琢、以平淡自然见长的谢灵运、陶渊明和质木无文的裴子野并不被时人看好。如陶渊明在钟嵘的《诗品》中只被列入“中品”,萧纲《与湘东王书》批评谢灵运、裴子野:“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柏;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较之“初发芙蓉”的自然美,六朝人更偏爱“错采镂金”的雕琢美。这种时代特征不仅体现在“永明体”诗、骈文骈赋的创作中,也体现在六朝绘画、书法取得的艺术成就及其批评理论中。魏晋六朝不是如宗白华先生说的那样,是崇尚“芙蓉出水”之美的阶段,而恰恰是崇尚“错采镂金”之美的阶段。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以“雕琢刻镂”“富丽堂皇”的形式为美,是以“情之所钟”“缘情适意”为美的情感美学的对应物。二者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的。所以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构成六朝相互联系、双峰并峙的两大美学主潮。
“文章道弊五百年”:隋唐在批判中确认六朝美学的两大特征
在魏晋玄学“适性”追求推动下形成的六朝情感美学与形式美学两大思潮,在反抗汉代对情欲过度压抑、解放自然人性方面具有合理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矫枉过正的新的偏颇。扼杀基本情欲的名教概念是应该反抗的,但节制过度情欲的理性规范是不可完全抛弃的。笼统地提“越名教而任自然”,要求抛弃一切道德礼义,主张听任情欲无限地满足自己,沉迷于“奢侈淫靡”“风花雪月”“雕琢刻镂”的官能享受之中,必然会产生若干危害社会稳定的严重后果。于是从六朝开始,就出现了反思、批评的声音。如东晋王隐《晋书》批评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之者名之为‘达’也。”刘勰《文心雕龙·通变》评论魏晋以来的文学发展:“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谈。”钟嵘《诗品序》批评“永明体”的形式主义弊病:“王元长(融)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到了隋代,这种反思和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种来自官方的声音,而且很尖锐。如治书侍御史李谔“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为由,上书隋文帝:“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批判了六朝的形式主义美学、情感主义美学的弊病后,他提出文章的理性主义道德美学主张:“褒德序贤,明勋证理”,关乎惩劝,“义不徒然”。结合“大隋受命”、天下大变的现实,指出“屏黜轻浮,遏止华伪”,复兴“圣道”,刻不容缓。隋文帝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稍后,王通著《中说》,以恢复孔子儒道自命,高举“文者济乎义”的道德美学大旗,对六朝醉心形式、德行有亏的诗人一一给予批判。总之,六朝诗人浸淫文辞技巧,遗忘道德之大,都是对国家“不利”之人。
唐初,太宗吸取隋炀帝无道而亡的教训,命人重注五经,重修八史,儒家仁义礼智之道被进一步确立。其时文坛,儒家道德美学大旗被高高举起,用来批判六朝以迄唐初的情感美、形式美偏向。魏征《隋书·文学传序》批评说:“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萧纲)、湘东(萧绎),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返,无所取裁。”《隋书·经籍志》批判萧纲开创的宫体诗:“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姚思廉《梁书·简文帝纪》也批评萧纲:“雅好题诗……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批评说:“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原夫两朝(梁、北齐)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乎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批评南朝形式美学、情感美学风潮对北朝文人的影响:“然则子山(庾信)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与此呼应,在唐初诗坛,面对六朝形式美学、情感美学的顽强残留,有责任感的诗人强调:“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杨炯)文章的伟大意义在于道德事功,只有这样,“文章”才可以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能事”(王勃)。否则,就只能成为“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属于“立身之歧路”,“何足道哉”?(骆宾王)而六朝以来诗文领域的风气恰恰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所以,初唐四杰王勃、杨炯、骆宾王、卢照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给予反对。
到了武则天时期,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继承、综合隋代的李谔、王通及唐初史家和诗人道德为美思想的基础上,标举“风骨兴寄”,对晋宋以来“彩丽竞繁”的道德弊病给予猛烈批判:“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他认为六朝以来诗坛文苑斤斤计较于声律、骈偶、辞彩技巧,将文章降低为一种类似“俳优”的“薄伎”“小能”,因而在《上薛令文章启》中重提扬雄“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的主张:“文章薄伎,固弃于高贤;刀笔小能,不容于先达。岂非大人君子以为道德之薄哉!……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文章小能,何足观者!”他以诗文创作实践一扫六代之纤弱,促进了情感美学、形式美学风潮向道德美学、风雅美学的转变。此后整个唐代,道德美学成为美学界的主潮。如在诗歌领域,白居易主张“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元稹主张“雅有所谓,不为虚文”。在散文领域,韩愈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反对“以辞为工”,李翱主张文章是“仁义之辞”,反对“号文章为一艺”。宋代继续延续着这个方向朝前发展,如周敦颐、朱熹等理学家主张“文以载道”“道本艺末”,欧阳修等古文家主张“道胜文至”“文章为道之鉴”,无不指向以风雅道德为文章之美、做人之美的美学观。可见,陈子昂的一句“文章道弊五百年”,恰恰揭示了六朝美学区别于汉代美学和唐宋美学的时代特征,勾画出从汉代的“建安风骨”到六朝的“彩丽竞繁”,再到唐宋的“风雅骨气”“道德理义”的马鞍形走向。在这种注重以风雅道德的自然表现为美而不是以脱离道德内容的形式雕琢为美的社会风潮之下,“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才逐渐被确立为一种新的时代趣味和审美理想。(19)关于隋唐宋元的道德美学主潮的转向及其具体情况,参见祁志祥:《中国美学通史》第二卷第三编第一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8页;祁志祥:《中国美学全史》第三卷《隋唐宋元美学》第一章《儒家道德美学主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67页。
从六朝的反思、隋唐的批判及转向中,我们可以看出:六朝美学的整体特征是“道弊”而“丽淫”,是宽容形色快感,是形式大于内容,是雕章琢句、错采镂金、铺锦列绣。如果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是“魏晋六朝”的主流和特征,就无法理解隋唐人对六朝淫丽倾向的批判,或者说,隋唐人对六朝淫丽倾向的批判就不能成立。事实上这种批判已成为文学史、美学史上的一种共识。所以,宗白华先生将魏晋六朝与隋唐的美学特征视为一体、划归成一个阶段是不符合实际、难以成立的。重新审视宗先生的论断,从魏晋六朝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什么“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什么“新的理想”呢?就是“情之所钟”“从欲为欢”,就是“铺采摛文”“错采镂金”。二者是对汉代鄙薄情感和形式之偏的合理反拨,同时又以其矫枉过正、走向一偏,被唐宋的道德美学主潮纠正和取代。(20)参见祁志祥:《宋代道德美学主潮》,《文化艺术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