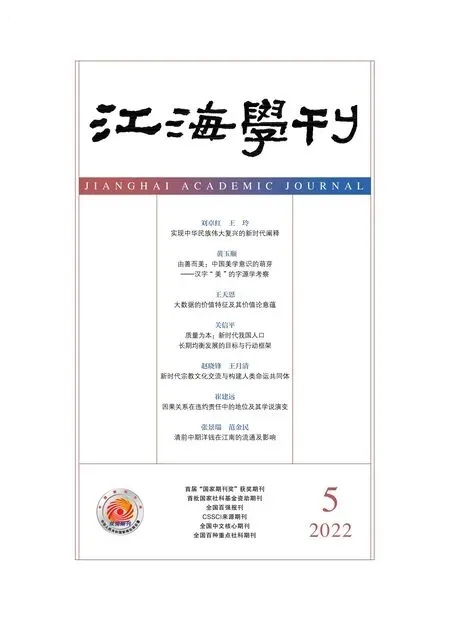“保残守缺”的艺术:欧阳修的拓本阅读
程章灿
“保残守缺”与“抱残守缺”
通常被写作“抱残守缺”的“保残守缺”一词,基本上被理解为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一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人生态度或思想立场。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保残守缺”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这是一篇经学史和文献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刘歆在这篇文字中批评当世一些没有见识的“缀学之士”“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1)《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970页。这篇文章不仅被作为重要历史文献而录入《汉书》,而且被作为经典文学作品编入《文选》,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2)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12页。直到现当代,很多选本依然选录此文,如高步瀛选注,陈新点校:《两汉文举要》,中华书局1990年版;又如李隆献编:《先秦两汉文选》,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保残守缺”一词也随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学者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讲到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位学者时,称“二君以瑰异之质,负经世之才……岂若抱残守缺之俗儒,寻章摘句之世士也哉”。(3)江藩撰,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65—866页。他没有承袭传统写作“保残守缺”,而是写作“抱残守缺”,可能只是一时误记,其意义内核并没有改变。如果非要分辨二词有什么不同,也许可以说,“保残守缺”可以重组为“保守残缺”,而“抱残守缺”只能改写为“抱守残缺”,“保守”一词似乎比“抱守”一词更为通俗,也更好理解一些,但在通常使用语境中,二者的贬义色彩却是一致的。实际上,从语源学和训诂学的视角来看,“保”(褓,襁褓)与“抱”之间也有相当多联系,(4)详细论述请参见杨联陞:《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都意味着对婴幼儿的保护、爱护和哺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保守”还是“抱守”,其实都有相当多正面与褒义的内涵。
另一方面,从中国古代文献历史尤其是先秦两汉文献历史来看,“残缺”往往被用来描述当时文献流传中的客观状态,甚至可以说,“残缺”简直就是古代文献流传的常态。即使在最早创用“保残守缺”一词并率先使其“污名化”的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也曾引用汉武帝诏书中“礼坏乐崩,书缺简脱”一词,以描述当时经籍的残缺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一段: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5)《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第1969—1970页。
这里所谓“学残文缺”,其具体所指,就是“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既包括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也包括刘歆在这篇经学文献中所力争的“三事”,亦即《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和《左氏春秋》。由于此“三事”未列入学官,未得到当时官方经学体系的承认,因此,整个经学体系就不免停留在“学残文缺”的状态。在刘歆看来,当时经学格局中只有增添这些逸书遗学,才能摆脱“学残文缺”的局面。他与代表当时官方经学体制的太常博士力争之时,极力强调这些残缺文本、残缺之学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刘歆并没有一概否认“残缺”的价值与意义。实质上,太常博士所保守的固然是一种“残缺”,刘歆所维护的也是一种“残缺”,双方固守自己的立场,互不承认。因此,刘歆抨击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指责他们“挟私意”“无公心”,也不免带有意气情绪,立场不无偏激。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刘歆所谓“三事”,都是当时新发现的文献,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出土文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欧阳修所收集的金石拓本,性质与之大同小异。欧阳修收集金石拓本的心路历程与阅读拓本的心得,都集中保存于其所撰《集古录跋尾》,其中,又以石刻拓本的收集与阅读为主。细读《集古录跋尾》,可以看出欧阳修对石刻阅读的方法态度及其心理审美体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欧阳修的石刻阅读,那就是“保残守缺”的艺术。
“保残守缺”以抗拒遗忘
古代石刻历经数百年或者上千年岁月,或者饱受风雨侵蚀,或者在幽暗的地下沉埋,及至被人重新发现或者重见天日之时,很多已是残缺之物。要么是断碑残碣,成为物质形态上的残缺之物;要么是字迹模糊,成为文本内容上的残缺之物;要么是时地不详,成为历史语境上的残缺之物;虽然残缺的表现各不相同,但终究皆为残缺之物。有着数十年集古经验的欧阳修,对于古今石刻的残缺有深刻的认知。“残缺”(少数写作“残阙”)一词是《集古录跋尾》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据检索统计,共出现20处23次,其中涉及汉碑者8处9次,涉及魏碑1处1次,涉及唐石者11处13次。今依次胪列如下:
1.卷一《后汉孔宙碑阴题名》:今宙碑残缺,其姓名邑里仅可见者才六十二人。(第30页)
2.卷二《后汉武荣碑》:其余文字残缺,不见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第36页)
3.卷二《后汉杨震碑》:文字残缺,首尾不完。(第37页)
4.卷二《后汉郎中郑固碑》:其余残缺不复成文。……汉隶刻石存于今者少,惟余以集录之勤,所得为独多。然类多残缺不完,盖其难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余,尤为可惜也。(第51页)
5.卷三《后汉田君碑》:自此以后,残缺不可次第,而隐隐可见,盖无年寿、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铭”之语。(第52页)
6.卷三《后汉竹邑侯相张寿碑》:其大略可见者如此,其余残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读尔。(第57页)
7.卷三《后汉杨公碑阴题名一》:首尾不完,今可见者四十余人。杨震子孙葬阌乡者数世,碑多残缺,此不知为何人碑阴。(第63—64页)
8.卷三《后汉杨君碑阴题名》:此碑阴者不知为何人碑,文字残缺。(第64页)
9.卷四《魏刘熹学生冢碑》:今碑虽残缺,而熹与生徒名字往往尚可见。(第84页)
10.卷五《隋尔朱敞碑》:碑文虽残阙,然班班尚可读。(第105页)
11.卷五《唐孔子庙堂碑》: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第114页)
12.卷五《唐孔颖达碑》: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缪不疑。(第122页)
13.卷七《唐中兴颂》:摩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残缺。今世人所传字画完好者,多是传模补足,非其真者。(第161页)
14.卷七《唐干禄字样》:此本刻石残缺处多,直以鲁公所书真本而录之尔。……而世俗多传摹本,此以残缺不传,独余家藏之。(第165页)
15.卷七《唐杜济神道碑》:碑已残缺,铨次不能成文,第录其字法尔。(第168页)
16.卷七《唐颜真卿射堂记》:如《干禄字书》之类,今已残阙,每为之叹惜。……惟《张敬因碑》与斯记为尤精劲,惜其皆残阙也。(第169页)
17.卷七《唐张敬因碑》:碑在许州临颍县民田中。庆历初,有知此碑者稍稍往模之,民家患其践田稼,遂击碎之。余在滁阳,闻而遣人往求之,得其残阙者为七段矣。其文不可次第,独其名氏存焉。(第170页)
18.卷七《唐颜勤礼神道碑》:唐去今未远,事载文字者未甚讹舛残缺,尚可考求,而纷乱如此。故余尝谓君子之学有所不知,虽圣人犹阙其疑以待来者,盖慎之至也。(第171页)
19.卷八《唐颜鲁公书残碑二》: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故虽其残缺,不忍弃之。(第176页)
20.卷七《唐湖州石记》:文字残缺,其存者仅可识读,考其所记,不可详也。(第176页)(6)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20条例证,皆出本书,其卷次及页码分别注于各条例证之首尾。
此外,《集古录跋尾》中所用与“残缺(残阙)”义同形异的词语,还有“残灭”(如卷一《后汉北岳碑》)、“残碑”(如卷三《后汉残碑》)、“讹缺”(如卷七《唐干禄字样模本》)、“残篇断稿”(如卷九《唐辨石钟山记》)等,其中,“残灭”一词出现多达7次,频率较高。由此可见,“残缺(残阙)”可以说是《集古录跋尾》一书的关键词之一,而“残阙”也可以说是长期从事石刻拓本收集与阅读给欧阳修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
欧阳修对于金石古物的收集兴趣,与其说在于金石古物本身,不如说在于金石古物上面的文字,其阅读金石古物的聚焦点,不在其物质形态,而在于其文本。面对“残缺”的石刻文本,他总是力图拼接零落分散的文字,尽量使其“成文”,使其具有可读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恢复其完整性。这种行为从字面上说就是“保残守缺”。例如《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杨震碑》云:“文字残缺,首尾不完,其可见而仅成文者云……其余字存者多而不复成文矣。”(7)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37页。从文本来看,《后汉杨震碑》是残缺不全的,很多地方“不复成文”。对于这类石刻拓本,欧阳修在阅读时,一方面透过残文断句,尤其是透过其中“可见而仅成文者”,来捕捉蕴藏的有效信息,例如卷一《后汉西岳华山庙碑》跋尾提到《华山庙碑》中出现了“集灵宫”之名:“所谓集灵宫者,他书皆不见,惟见此碑,则余之集录,不为无益矣。”(8)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49页。这就填补了既往历史文献的空白,指出了残缺文本的价值。即使“碑已残缺,铨次不能成文”,也仍然可以“录其字法”,(9)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68页。这就是说,即使文本残缺,不能提供有效的文献信息,仍然可以从其字法中挖掘出书法艺术的价值。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一定的文献考索,尽可能重构文本的完整性。例如《集古录跋尾》卷三的《后汉武班碑》,这篇跋尾作于治平元年(1064)四月二十日,欧阳修当时所读到的《武班碑》拓本,“字画残灭,不复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阀、卒葬皆不可见,其仅见者曰:‘君讳班尔。’其首书云:‘建元年太岁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识”,可以说,与《杨震碑》相比,《武班碑》残缺更为严重,碑主姓氏缺不可见,有关系年的年号下一字也不可辨。欧阳修根据《汉书》对其年代作一番推考,终于补出了年号的下一字:
以《汉书》考之,后汉自光武至献帝,以“建”名元者七,谓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宁、建安也,以历推之,岁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后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为建和元年,又岁在丁亥,则此碑所缺一字当为“和”字,乃建和元年也。(10)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41页。
五年以后,亦即熙宁二年(1069)九月朔日,欧阳修又获得一本《武班碑》拓本,“摹拓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讳班’,乃易去前本”。(11)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41页。由于有了较好的拓本,碑主姓武一目了然。读书必求善本,读石必求善拓。对于同一件石刻,欧阳修总是精益求精,致力于收集更好的拓本,与此同时,面对同一石刻,尤其是同一件石刻的不同拓本,他总是反复阅读,若有新的心得,就会多次题写跋文。
欧阳修对这些残缺的石刻文本的感情,可以用爱之深而惜之切来形容。他不止一次表达这种爱惜之情,例如,在阅读《武班碑》拓本之时,他说:“碑文缺灭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为可惜也。故录之。”(12)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41页。又如,在阅读《后汉郎中郑固碑》时,他说:“汉隶刻石存于今者少,惟余以集录之勤,所得为独多。然类多残缺不完,盖其难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余,尤为可惜也。”(13)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51页。《集古录跋尾》中的“录”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编辑这些石刻的目录,一层是存录其文字,目的都是传承文献,使这些畸零残缺的文献孤岛不被汹涌而来的时间之潮席卷而去,跌入遗忘的黑洞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欧阳修对石刻的收集与阅读,不仅是一种通过文字记录以对抗遗忘的自觉行为,也是一种与永恒的时间拔河的壮举。
欧阳修癖好石刻,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石刻也不免“有时而磨灭”。(14)欧阳修:《岘山亭记》,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卷四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4页。《集古录跋尾》卷五录有《唐孔子庙堂碑》,欧阳修自言:“余为童儿时,尝得此碑以学书,当时刻画完好。后二十余年复得斯本,则残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终敝,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于是始欲集录前世之遗文而藏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谓富哉!”(15)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14页。他的亲身经历,加深了他对“虽金石之坚不能以自久”的认识。金石虽坚,毕竟只是“孤军奋战”,制作石刻拓本,使其多有化身,固然有复制传承石刻文献之功,但棰拓同时也造成对石刻的破坏。因此,在收录、阅读拓本时,以纸张抄集文字、编成目录,使石本转换为另一种纸本,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刊刻将其转换为刻本,化身千百,石刻文献遂得以永寿。在这一方面,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开创了宋代金石学的新局面,对后学有垂范效应。其后,赵明诚《金石录》编制目录并撰写题跋,洪适《隶释》《隶续》不避残缺而过录汉碑全文,都是在欧阳修基础上精益求精,后来居上。名家的精心阅读、优美的文字书写、纸张的传播力量与雕版印刷的复制效率,使宋人在石刻文献保残守缺的成就上前无古人。这固然归功于宋代文献文化史的特殊背景,也归功于欧阳修这样大家的突出贡献。
总之,欧阳修对石刻拓本的阅读,可以视为一种“残缺之学”。对残缺的石刻文本进行拾遗补残,填补阙失的语境,发掘文本价值,才能显示石刻文献研究者的学术功力。清代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往往短小精悍,鞭辟入里,最见考据功力。(16)参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嘉定钱大昕全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在20世纪石刻文献研究名家中,马衡、鲁迅、余嘉锡、杨树达等人在这一方面也都有深湛的功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7)详细举例,参看拙作《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相对而言,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考证比较粗糙,态度也较为随意。例如他在阅读《刘熊碑》残拓时,虽然知道碑主姓刘,却没有进一步搜集阅读相关文献(如唐人王建《题酸枣县蔡中郎碑》一诗),就匆忙地将此碑定名为《后汉俞乡侯季子碑》。(18)参见程章灿:《〈刘熊碑〉新考》,《古刻新诠》,中华书局2009年版。这一方面是欧阳修的个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北宋金石学经验不足所致。
纪事怀人以重构情境
《集古录跋尾》中对石刻拓本的阅读,基本上是在室内进行的。室内的拓本阅读与石刻的现场阅读明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对象的物质媒介有石本与拓本之不同,一是阅读之时周遭空间环境有野外和室内之别。总体来看,室内拓本阅读缺少与石刻实物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现场体验的那种生动复杂的情形。如果只是记录在室内尤其是书斋之内对石刻拓本的阅读体验,跋尾就难免比较单调、枯燥。因此,《集古录跋尾》时常穿插纪事怀人的叙述描写,不仅使记录阅读过程的文字更具可读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情境再造的作用。
每一份入藏欧阳修家中的金石拓本,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只是有的被欧阳修讲述出来,被《集古录跋尾》记录下来,有的没有被讲述、记录。那些被欧阳修讲述、记录的故事,应该是对他而言更为印象深刻的。其中,有的是讲述拓本获得的故事。如《晋南乡太守颂》跋尾前面是一段关于南乡太守司马整其人及南乡其地的考述,结尾写道:“余贬乾德县令时得此碑,今二纪矣。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19)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87页。这段叙述虽然只有短短两句,却交代了拓本获得的时间、地点与作者当时的身份,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慨叹。又如卷三《后汉樊常侍碑》条,则是回忆初次邂逅这一汉代石刻的情景:“余少家汉东,天圣四年举进士,赴尚书礼部,道出湖阳,见此碑立道左,下马读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后三十年始得而入集录,盖初不见录于世,自予集录古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20)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47页。欧阳修与《后汉樊常侍碑》初次相见,是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那一年他年方20岁,在北上汴京参加进士考试的途中发现此碑,于是下马细读,并为之流连忘返。这大概不是有意的寻访,而是一次偶遇,但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古石刻遗文的兴趣由来已久。30年之后,大约在至和二年(1055)或至和三年(1056),欧阳修才获得此碑拓本,那时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拓本了。此条题跋写于嘉祐八年(1063)十月十四日,相隔37年,他仍然记得初见此碑的情景,足证印象深刻。这段题跋展示了欧阳修一边阅读拓本一边打开回忆的过程,后代读者可以跟随他的回忆,重返两个阅读现场,一个是他1026年初次读碑的那个现场,一个是1063年他在书斋中展读拓本的那个现场。也可以说,通过文字,欧阳修在这里重构了两次石刻阅读和两种阅读现场相互叠加的情境。
题跋中讲述的故事,大多是与石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故事。有的是关于石刻流传的故事,如《集古录跋尾》卷一《周穆王刻石》:“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于坛山模此字。而赵州守将武臣也,遽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21)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1页。由于相传为周穆王刻石,很多人对其十分重视,与欧阳修同有金石之好的宋祁就专门派人去模取拓本。也许是当时各方索取拓本的人比较多,地方官不堪其扰,于是,赵州守将才派人凿取这一刻石,移置州廨,便于就近制取拓本。尽管欧阳修本人对这一刻石的真伪仍存疑问,他对赵州守将破坏石刻现场的做法还是很不以为然的。这段掌故虽然不是欧阳修对个人石刻经历的回忆,而是有关此刻的联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叙述是对已遭破坏的石刻现场的修补。《集古录跋尾》中的很多题跋,都有这类睹物怀人、因物记事的内容,这样的题跋不仅再现了欧阳修阅读石刻拓本之时的浮想联翩,也为他实现了一种石刻阅读情境的重构。
身处书斋,面对拓本阅读之时,欧阳修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自己的访碑经历。特别是当他在拓本中遇见他所崇敬的前贤,如韩愈、颜真卿等,更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韩愈是欧阳修终生推重的人物,欧阳修一生立言行事,也与韩愈接近,苏轼甚至说:“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又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22)苏轼:《六一居士集序》,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某日,当欧阳修打开《唐韩退之题名》拓本时,他有这样一段亲切而充满风趣的回忆:“右韩退之题名二,皆在洛阳。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记龙潭遇雷事。天圣中,余为西京留守推官,与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宫,裴回柱下而去。遂登山顶,至武后封禅处,有石记,戒人游龙潭者,毋妄语笑以黩神龙,龙怒则有雷恐。因念退之记遇雷,意其有所试也。”(23)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85页。这段回忆文字写于治平元年(1064),距离天圣(1023—1032)已有三四十年。这段回忆中不仅有对青年时代与梅尧臣深厚友谊的怀想,也有两个年轻人对前贤毫无拘束的打趣。通过回忆,书斋拓本阅读与石刻现场阅读两种情境,一今一昔,便融合在一起了。
不管是实物还是拓本,石刻作为被时光侵蚀而留下的残缺文本,极易引起人们的今昔慨叹。《集古录跋尾》卷七《唐李阳冰庶子泉铭》写道:“庆历五年,余自河北都转运使贬滁阳,屡至阳冰刻石处,未尝不裴回其下。庶子泉昔为流溪,今为山僧填为平地,起屋于其上。问其泉,则指一大井示余,曰:‘此庶子泉也。’可不惜哉!”(24)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62页。这段题跋与《后汉樊常侍碑》题跋同中有异,其今昔对比不是通过时间的跨度来呈现,而是通过沧海桑田式的地貌景观改变来体现。“昔”“今”二字可以说是这段跋文的字眼。
人和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纪事与怀人二者总是难以截然分开。从本节的论述角度来说,与石刻直接相关的叙述就归为纪事一类,与石刻没有直接关系的叙述就归为怀人一类,但严格地说,《集古录跋尾》中怀念故人的描写,多多少少与石刻拓本阅读都有联系。例如卷五《唐薛稷书》:“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25)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23页。断章取义地看,这更像是一段诗话,似乎与石刻阅读没有关系。实际上,这条跋尾从一件薛稷石刻书法的真伪讲起,涉及文艺作品的鉴赏与理解,进而触及接受美学的问题。欧阳修与梅尧臣都是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以自己对梅尧臣诗的理解为例,论证了“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的道理,强调文艺知音之难。书画与诗学虽然一属于艺,一属于文,但美学原理是相通的。
集古访碑,离不开同道友朋的支持,欧阳修自不例外。读碑之时,他难免联想到朋友们提供的资源、传授的知识,以及当年与友朋一同登山临水的经历。这种回忆有的是对友情的温暖感念。例如,欧阳修喜欢颜真卿书法,认为颜书“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其收藏颜书石刻拓本多多益善,“虽多而不厌”。(26)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76页。其友人韩琦于书法亦“师颜鲁公,而颇露芒角”,(27)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43页。曾向欧阳修称道颜真卿所书《射堂记》最佳,并以家藏拓本奉赠。(28)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69页。北宋之时,秦泰山刻石真本已不易得,欧阳修拜友人江邻几之赐而得一珍本,江邻几当时恰好任职于泰山所在的奉符县,(29)据《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封禅泰山,改泰山所在之乾封县为奉符县。《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8页。乃有此地利之便,可谓机缘难得。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卷一《秦泰山刻石》中写道:“余友江邻几谪官于奉符,尝自至泰山顶上,视秦所刻石处,云石顽不可镌凿,不知当时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无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风雨所剥,其存者才此数十字而已。本邻几遗余也,比今俗传《峄山碑》本特为真者尔。”(30)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23页。欧阳修没有亲到泰山石刻现场,只好转述友人江邻几的现场经验,这是他人的石刻现场阅读体验与自己的书斋阅读体验的融合。
题跋中也有悲怆的回忆,《集古录跋尾》卷六《唐韩覃幽林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在洛阳,凡再登嵩岳。其始往也,与梅圣俞、杨子聪俱。其再往也,与谢希深、尹师鲁、王几道、杨子聪俱。当发箧见此诗以入集时,谢希深、杨子聪已死。其后,师鲁、几道、圣俞相继皆死。盖游嵩在天圣十年,是岁改元明道,余时年二十六,距今嘉祐八年盖三十一年矣。游嵩六人,独余在尔,感物追往,不胜怆然。”(31)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33页。也可以说,这段回忆是从温暖始,而以悲怆终。此外,这段文字中还有这样一层内涵:访碑集古虽为小道,然而吾道不孤,当年的同道友朋虽已作古,但他们的陪伴不仅使欧阳修的人生更加丰富,更有意义,他们留下的温暖也将永远被后来者铭记。
日常仪式与生活美学
从文献形态上来讲,《集古录跋尾》主要有三种存在形态:第一种是写本,也就是题跋真迹本,亦称《集古录跋》。历经千年,《集古录跋》仅有残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楷书,纸本,包含欧阳修手书跋尾真迹四种:《汉杨君碑》《唐陆文学传》《平泉山居草木记》和《汉西岳华山碑》。卷末附有宋代名贤赵明诚、米芾、韩元吉、朱熹、尤袤、洪迈等人题跋及明人题跋多种,弥足珍贵。(32)《〈欧阳修集古录跋〉简介》,《欧阳修集古录跋》卷首,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二种是刻本。南宋文献学家方崧卿“裒聚真迹,刻板庐陵,得二百四十余篇,以校集本,颇有异同。疑真迹一时所书,集本后或改定。今于逐篇各注何本。若异同不多,则以真迹为主,而以集本所改注其下。或繁简辽绝,则两存之”。(33)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775页。严格说来,这里包括三种刻本,一是欧阳修集本,一是方崧卿依据跋尾真迹的刻本,还有一种是糅合真迹本与集本的刻本,也就是现在通行本《集古录跋尾》的样貌。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所收《集古录》就属于这种通行本。第三种是拓本之后附有跋尾,是拓本与写本的融合。南宋学者周必大曾经见过这种形态的《集古录跋尾》,“集古碑千卷,每卷碑在前,跋在后,衔幅用公名印,其外标以缃纸,束以缥带,题其签曰,某碑卷第几,皆公亲迹,至今犹有存者”。(34)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古录后序》,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五二,第775页。这三种不同的文献形态,显示了《集古录跋尾》产生、衍生、传播过程的复杂样态。可惜的是,第三种文献形态的《集古录跋尾》今已不可得见了。
即使《集古录跋尾》真迹荡然无存,从现存题跋文本末尾所署时间地点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日常书写的痕迹。从时间上看,很多题跋写于旬休日,例如卷六《唐韩覃幽林思》写于嘉祐八年(1063)六月旬休日。(35)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33页。有的作于时令节日,如卷七《唐龙兴寺四绝碑首》写于嘉祐八年夏至日,同卷《唐杜济神道碑》写于嘉祐八年中元假日。(36)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65、168页。还有一种题署的写法比较特别,例如卷五《唐智乘寺碑》写于“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卷六《唐司刑寺大脚迹敕》写于“嘉祐八年重阳后一日”,卷五《隋丁道护启法寺碑》署“治平元年立春后一日太庙斋宫书”。(37)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27、132、110页。这几篇题跋作于某一节日或节气的前一天或后一天。节日或节气都是时间的坐标,意在赋予平凡的日子以意义。欧阳修在题跋中如此标注,就是为了突显节日或节气的坐标,使平凡的日子与有意味的时间坐标发生意义关联。旬休日也好,节假日也好,总能给欧阳修带来更多的悠闲感,他的题跋更多是写于这些日子里,是可以理解的。欧阳修的学生苏轼曾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38)苏轼:《病中游祖塔院》,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一〇,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5页。小病无碍,反而意外得闲,养病的日子于是有了一份悠闲的心境。卷八《唐汾阳王庙碑》末署:“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以服药家居书。”(39)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80页。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除了休息日和节假日,欧阳修在“了却公家事”之余,也会偷闲阅读玩赏他所收藏的石刻拓本,作为日常生活的调剂。尤其是书法精美的拓本,更是销闲忘忧之佳品。欧阳修所集颜真卿书刻拓本甚多,其中包括《唐干禄字样摹本》,此虽为摹本,亦是时人习书识字之楷模。宋英宗生日在正月三日,朝廷定为寿圣节。治平元年(1064)正月五日,欧阳修在锡庆院受赐寿圣节宴,(40)按:寿圣节是宋英宗的寿诞。《宋史》卷一一二《礼志》:“英宗以正月三日为寿圣节,礼官奏:‘故事,圣节上寿,亲王、枢密于长春殿,宰臣、百官于崇德殿,天圣谅闇皆于崇政殿。’于是紫宸上寿,群臣升殿间,饮献一觞而退,又一日,赐宴于锡庆院。”第2673页。归来把玩此拓,遂作题跋。值得注意的是,真迹本题跋末尾才有“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锡庆院赐寿圣节宴归书”的题署,而集本中则没有。(41)参见欧阳修:《集古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此条跋尾见邓宝剑等笺注《集古录跋尾》卷七(第165—166页),但无此句题署。对欧阳修来说,赏读这件拓本是他了却公事之余的身心放松。
李百药亦作李伯药,是隋唐之际的著名史家,欧阳修家藏李氏所书《隋泛爱寺碑》,他曾在公事之暇赏读此碑拓本:“‘李伯药’字仅存,其下摩灭,而‘书’字尤可辨,疑此碑伯药自书,字画老劲可喜。秋暑郁然,览之可以忘倦。治平丙午孟飨摄事斋宫书,南谯醉翁六一居士。”(42)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12页。这条题跋写于治平丙午(1066)孟飨之时,同一天,欧阳修还读了《唐明禅师碑》并为之写了一篇题跋:“秋暑困甚,览之醒然,治平丙午孟飨,致斋东阁书。”(43)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150页。这两篇跋文除了说明两次阅读时间、地点、气候环境等都一样之外,还表明欧阳修将不止一个拓本都带到了孟飨斋宫的现场。这一天确实很热,这两个拓本给欧阳修带来“览之忘倦”“览之醒然”的审美享受。这两条题跋篇末标注的时空信息,为两次日常阅读增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为异日的回忆设置一个时间和事件的参照坐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并表达诗意的行为。

总体来看,欧阳修诗作的题材范围甚广,类型甚多,但是,作为一个金石古物的收藏家和阅读者,除了《葛氏鼎歌》和《石篆诗》之外,(45)《葛氏鼎歌》(一作《葛氏鼎》),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46—147页;《石篆诗》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348—1349页。《石篆诗》序云:“某在馆阁时,方国家诏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阁下,因得见李阳冰篆《庶子泉铭》。学篆者云:‘阳冰之迹多矣,无如此铭者。’尝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来,已获焉。而铭石之侧,又阳冰别篆十余字,尤奇于铭文,世罕传焉。……因为诗一首……”此序可与《集古录跋尾》卷七《唐李阳冰庶子泉铭》对读。他几乎不用诗体来题咏金石古物,既没有前代韦应物《石鼓歌》、韩愈《石鼓歌》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之类的名篇,也没有同时代人苏颂《寄题吴兴墨妙亭》和黄庭坚《书磨崖碑后》这样的诗作。(46)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八《寄题吴兴墨妙亭》:“汉唐遗刻在江干,右史殷勤辑坠残。剔去藓文人乍识,传来墨本字犹完。六书体法从兹辨,二费声光遂不刋。何必临池苦萦思,燕闲时得坐隅观。”黄庭坚:《书磨崖碑后》,参见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卷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88—689页。另一方面,在现存欧阳修诗集中,却有《夜宿中书东阁》《摄事斋宫偶书》《夏享太庙摄事斋宫闻莺寄原甫》(卷一三)之类的作品,其写作地点与上述两篇题跋相同。这表明,这些地点是有诗意的,写于这些地点的散体题跋也是有诗意的。
对于欧阳修来说,拓本的阅读与题跋的写作,是日常生活美学化、日常生活诗意化的方式。他曾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嘉祐壬寅(1062)大雩摄事致斋期间,欧阳修为手中的一份法帖题跋时,就再次明确表示:“吾有《集古录》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归老之计足矣。寓心于此,其乐何涯。”(47)欧阳修撰,邓宝剑、王怡琳笺注:《集古录跋尾》,第223页。
总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执着的记录、温暖的回忆和悠闲的玩味,开启了中国文士的集古传统。《集古录跋尾》中纪事怀人的内容,与当时的诗话特别相似,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跋尾文字也可以称为“金石话”。以“话”体讲故事,既弥补了石刻阅读的现场情境,也体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状态:快乐、拥有和命名。(48)这个提法来自宇文所安,详参[美]宇文所安:《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美]宇文所安:《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刘晨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214页。题跋或题跋集,从此成为石刻阅读成果的主要呈现方式,并打上了北宋文化的深刻烙印。石刻收藏与阅读不仅是古代中国的文献生产和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古代中国士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启功先生为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作序时,曾将乾嘉以来金石家分为如下三派:
金石之学,乾嘉以来弥盛。石之存佚,字之完损,察入毫厘,价腾金玉,此鉴藏家也,以翁覃溪为巨擘。博搜曲证,贯穿经史,论世知人,明如龟鉴,此考据家也,以钱竹汀为宗师。至于收集编订,广罗前人考证之说,以为学者检阅之助,此著录家也,以王兰泉为山斗。(49)朱翼庵:《欧斋石墨题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翁方纲撰有《两汉金石记》等,以他为代表的金石学家属于鉴藏一派;钱大昕撰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以他为代表的金石学家属于考据一派;王昶撰有《金石萃编》,以他为代表的金石学家属于著录一派。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这三位宋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也可以按照这样一种思路来分门别类:欧阳修近于鉴藏一派,他的学术根柢在于文学;赵明诚近于考据一派,他的学术根柢在于史学;洪适近于著录一派,他的学术根柢在于文献学。当然,这是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的,实际上,鉴藏、考据与著录三者往往是连在一起,就欧阳修来说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