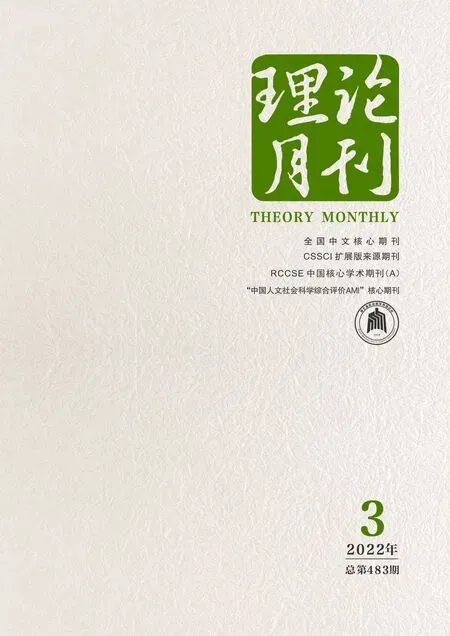列维纳斯和米歇尔·亨利:“超越性”和“内在性”之争
□彭 丽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意向性”是胡塞尔现象学的重大发现,通过这一概念他打破了封闭的意识世界,把外在事物引入意识构造之中,使之成为“内在的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从而解决了困扰哲学家们已久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难题。然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胡塞尔对“超越性”的理解对于“真正的超越者”(如他人、上帝)而言却是一种暴力。他认为,胡塞尔的哲学依然是一种“内在的”和“同一的”哲学。他要主张的是一种超越性哲学,即超出了意向性的理解范围的哲学。根据米歇尔·亨利的思想,包括胡塞尔在内的西方哲学依然是一种“外在性”的和“超越性”的思想,阐述的是世界的真理,而他要提出的是与之对立的内在生命的真理概念。从词意上看,“超越性”和“内在性”是对立的,因此列维纳斯和亨利的思想似乎也是对立的。列维纳斯和亨利的“对立”,在近年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研究者,如瑞士学者鲁多夫·贝尔奈特(Rudolf Bernet),认为二者的思想是“完全不一致的”。杨大春也认为,亨利对主体内在性的强调与列维纳斯的主张“明显相悖”。而另一些学者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调和列维纳斯和亨利的哲学思想。约书亚·卢波(Joshua Lupo)通过关注“情感”在列维纳斯和亨利的著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论证在列维纳斯的哲学里有内在性的踪迹,在亨利的哲学里有超越性的踪迹。扎斯洛·滕格义(LászlóTengelyi)认为,这两位思想家看上去彼此完全对立,但他们的哲学都把自身性(selfhood)奠基于被动性和情感性之上,在这一点上两人是一致的。
由此观之,大部分学者认为,列维纳斯和亨利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对立。即便是那些试图调和二者思想的人,也并不否认列维纳斯的超越性和亨利的内在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尽管这些学者各自持有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们都没有重新审视“超越性”和“内在性”在列维纳斯和亨利的文本中具体的含义。需要追问的是:二者是否在同一个层面使用这两个核心概念,列维纳斯和亨利之间的分歧是否是真实存在的。根据文本,列维纳斯强调的“超越性”并不是亨利意义上的“超越性”,且亨利强调的“内在性”也不是列维纳斯意义上的“内在性”。因此,笔者试图根据列维纳斯和亨利的文本,重新考察“超越性”和“内在性”的概念,以期深入理解二者的思想,并试图为重新理解哲学史上关于“超越性”和“内在性”的争论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笔者将梳理列维纳斯的著作中“超越性”和“内在性”的具体含义,指出他对超越和内在的划分核心在于他对“意识”的理解。他所说的内在性是指一切都被统摄在意向性之下,超越性是指超出意识的理解范围。第二部分中,笔者将梳理亨利文本中“超越性”和“内在性”的具体内涵,指出他所强调的超越性是指意向性将事物作为对象在主体面前呈现,内在性是指生命的“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在第三部分,笔者将通过分析列维纳斯强调的他者超越性的前提是“感受性”(sensibility)这个命题,论证这种“感受性”和亨利的生命的“恻隐与共”(pathos-with)具有根本一致性,从而证明列维纳斯和亨利思想上的一致性。
一、“内在性”和“超越性”在列维纳斯文本中的含义
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区分了两种“内在性”和“超越性”。第一种“内在性”是一种“真正的内在性”(genuine immanence),例如我的牙疼所给予的只是纯粹的牙疼。在胡塞尔看来,虽然这种内在性是无可怀疑的,但它不呈现除自身外的任何对象。与之对应的是第一种“超越性”,即在主体之外的对象。通过引入“纯粹的观看”(pure seeing)的概念,胡塞尔扩大了第一种意义上的“内在性”的范围,由此衍生出第二种“内在性”和“超越性”。胡塞尔指出,凡是能够被“纯粹的观看”所照亮的便是内在的,凡是不能被“观视”到的即为超越的。在胡塞尔看来,第一种“内在性”和“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分,而第二种“内在性”和“超越性”是认识论层面的区分。在第二种“内在性”中,对象能够被意识所把握,但它自身并不是意识的内在构成部分,因而对象是“内在的超越”。例如,在“这是一张桌子”这个判断中,桌子自身作为意识的相关项被呈现,但桌子并不是意识的内在构成部分。换言之,意识和桌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意识不具有任何形体,但其具有使桌子呈现出来的功能。简言之,通过从认识论角度重新解读“内在性”和“超越性”,胡塞尔将“内在性”彻底化了,一切事物都无法脱离意识而呈现自身,意识统摄了一切。而这正是列维纳斯所指出的“同一性”和“总体性”。
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一书中指出:“西方哲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存在论:通过置入一个对存在的理解进行确保的中间项和中立项而把他者还原为同一。”换言之,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同一性”(the Same)或“内在性”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一个对超越性摧毁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列维纳斯所理解的“同一性”或“内在性”指意识的意向性,即一切都被意识所统辖,因而也是内在的。而他要主张的是一种“超越性”哲学。他指出,《总体与无限》这本书的主题便是“分离和超越”。
列维纳斯意识到,突破“同一性”或“内在性”哲学的关键在于突破意识和存在,因为西方传统哲学正是通过把思想与实在严格对应起来,从而获得了尊严。依照这个传统,存在者的显现就意味着意向性的主题化。他认为,西方哲学把自己捆绑在存在上,虽然是对知识和真理的探寻,但是,知识在自身的本质中理解自己,这一理解过程是从意识开始的,而我们在定义意识的时候,又需要借助知识的观念。因而,在列维纳斯看来,知识和意识的外延是一样的,意识和“同一性”及存在的呈现是一致的。因此,对“同一性”或“内在性”的突破的关键在于对意识和存在的突破。
对意识和存在的突破一直贯穿于列维纳斯的著作之中。在其早期著作《论逃离》中,列维纳斯通过对愉悦、羞耻和恶心进行现象学描述和分析,试图揭示一种无法被存在所容纳的超越性冲动。其中期著作《总体与无限》的主题便是“分离与超越”。他的晚期著作《别样于存在或超越本质》依然体现着对意识和存在的突破。贝蒂娜·贝戈直言,“在列维纳斯的著作中,超越性正是这种对存在的突破的冲动”。
这种对超越性的突破在他对失眠现象的经典的现象学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列维纳斯这样描述失眠:“失眠不是自然睡眠的否定。失眠——作为清醒或警醒——超出了范畴的逻辑,先于所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注意和迟钝。总是处于清醒的边缘,睡眠和清醒相互沟通;同时睡眠试图逃脱清醒……失眠的范畴不能被还原为同一的同语反复的肯定,或者辩证否定,或者主题性意识的绽出……失眠或清醒是没有意向性的,没有固定的形式或模式。失眠这种现象无法被意识所把握,它是一种无限性(infinity)。”简言之,在失眠中,意识无法将其吸纳、涵盖,失眠状态是在“更少”之中的“更多”(a“more”in the“less”)。通过对失眠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了失眠虽在意识之中展开却无法被意识所容纳这一事实,从而实现了从意识内部解构意识的目的。
失眠现象的超越性不仅体现为意识溢出自身,同时在情感上体现为彻底的被动性。失眠作为超越性不再仅仅只是一种对存在的突破,更是唤醒、溢出和创伤。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一书中写道:失眠由无法平息的意识所组成,即无法从一种警惕的状态中退隐出来,这种警惕状态无休无止。在失眠状态里,时间没有任何开端,没有任何东西离开,也没有任何东西消退,只有外在的嘈杂还在标记着失眠的存在,表明这样一种无休无止的状态的开始。当你失眠时,你已经被钉在失眠的状态中,无法逃离。对意识自身而言,失眠的无可逃避性和不可控制性彻底倒转了“我思”的主动性特征。在意识内部,失眠作为他者,并没有排斥同一,而是唤醒了它。这样的唤醒就像一个命令,没有任何服从可以满足。
从失眠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列维纳斯对“超越性”的理解建立在他对意识的理解的基础之上。何为意识?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的本质特征是意向性。这是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发现。按照列维纳斯的理解,“意向性”具有以下三层含义:赋义(bestowing)、再现(representation)和符合(adequation)。赋义是指赋予意义。没有任何东西对主体来说是绝对陌生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不作为意向性的统一体在主体中呈现。意识是所有存在者的来源,也是对对象的构建(constituting)。再现不是指对外在事物的反映,而是意识能够让对象呈现自己,它有两个同义词——主题化(thematizing)和对象化(objectifying)。赋义和再现是对同一个行为的两种描述。符合是指意指和意向对象的符合或者说充实。胡塞尔所说的意识的意向性被列维纳斯理解为“同一性”或“内在性”。
于是,“超越性”具有与之对应的三层含义:不可赋意、不可再现和无法符合。换言之,“超越性”意味着超越意向性。失眠现象符合这三层含义,失眠现象中没有任何对象出现,因此意向性无法赋予其意义,同时也无法将其对象化或主题化,从而无法再现、符合或充实。因此,失眠具有一种无限性和超越性。失眠作为他者,超越于我的意识,无法被我的意识所涵盖,同时体现为情感上完全的被动性。
二、“内在性”和“超越性”在亨利文本中的含义
胡塞尔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内在性”,即“真正的内在性”,由于其过于内在,除了自身不涉及任何对象,从而在认识论上需要被改造和拓宽。通过引入“纯粹的观视”,它顺利过渡到第二种“内在性”,包含意向相关项,具有认识论意义。胡塞尔通过引入真理的标准,即明见性,将“真正的内在性”所具有的真理性扩大到了第二种“内在性”所具有的真理性,此后,胡塞尔便很少谈及“真正的内在性”了。从亨利的角度看,胡塞尔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内在性”之间的关系,从而错失了“真正的内在性”的重大意义。亨利所要做的正是重新看待第一种“内在性”,并指出包括胡塞尔在内的西方哲学实际上是“超越性”的。
亨利指出,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超越性”哲学,是世界的真理。世界真理必须在可见的视域的外在化中才能成为现象,所以,亨利认为,世界的真理本质上是超越性的。这里的超越性或外在化指事物作为对象在主体面前呈现。他提出一种与之对立的生命的真理。生命的真理是绝对内在的,不在世界之中显现。
亨利对两种真理的区分建立在他对“现象”这个概念的理解基础上。他认为,“古希腊的现象的概念决定了西方思想的进程——对事物的显现的解释,或者更严格地说,这种对事物的显现的解释作为世界的真理,其现象性是‘外在性的’(outsideness)——与之对立的是作为生命的真理概念”。换言之,西方传统哲学只看到了一种显现方式,即对象的显现。这种显现方式属于世界的真理。传统哲学和经典现象学揭示的是超越性的世界的真理,而没有真正看到让世界的真理得以显现的条件——生命,从而错失了另一种更为根本的显现方式,即生命的显现。生命的显现是完全内在的且不在世界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亨利的现象学是内在性哲学,也是现象学自身的彻底化。
为何世界的真理是超越性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世界”这个概念的含义。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并非所有存在者的集合,而是此在的存在论特征,是意义整体得以呈现和展开的场域。
同样,在亨利看来,世界不是一系列事物、存在者,而是光的视域,在其中事物作为现象呈现出来。因此,世界不是指是真的事物,而是真理(Truth)自身。它是视域,是事物显现的先在条件。传统哲学和经典现象学把意识作为真理的根基,而意识被定义为一个超越的行为,它把自己投射到存在者上,使它们成为可见的。而只有通过世界,并且在世界之中,每一个事物才能够成为可见的,因而成为一个“现象”。
亨利认为,世界的真理本质上是超越性的。意向性把对象置于主体面前加以呈现,本质上是一种外化,因而意向性也是超越性的。因此,列维纳斯所理解的被意向性所统摄的“内在性”正是亨利所阐述的“超越性”。之所以他们用完全对立的词汇去描述意向性,是因为他们站的角度不一样。列维纳斯站在超越的他者的角度反观意识,强调意识的有限性和总体性,即“内在性”。亨利则站在生命的绝对内在性角度,认为意识的意向性本质是把对象放在主体面前进行把握,对象在意向性的另一端作为现象呈现出来。于是,意识在亨利那里呈现出超越性。
现象学的核心问题不是显现出来的事物,而是事物如何显现的问题,或者说现象学关注的是显现自身。亨利进一步追问,世界的真理自身是如何显现的?他的回答是,世界的真理的显现是以生命的真理为前提的。何谓生命?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神经科学的视域下,我们把生命理解为神经元、神经递质等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但亨利认为,把生命还原为基本粒子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因为粒子是不可能感受到任何东西的。从本质上讲,生命和粒子是异质的。生物学将生命作为对象在世界中显现,但生命的显现方式完全不同于世界的显现方式。世界的显现是外在的显现,而生命只能在生命之中通过生命才能显现自身。这种呈现是完全内在的,在其中显现和显现者合而为一,是生命的“自行—感发”(auto-affection)。例如,当人牙疼时,他和他的疼痛是同一的,这种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是无法外在化且完全被动的。甚至当牙疼消失以后,人们也无法通过回忆的方式如其所是地体验牙疼。同样地,当人失眠时,他和失眠也是同一的,失眠的感受也无法用语言描述,是无法外化的、无法再现的以及完全被动的。而根据列维纳斯的说法,失眠无法被意识所容纳,因而是超越的。这样一来,列维纳斯所言的失眠的“超越性”和亨利所阐述的生命的自身感受“内在性”就有了一致性,二者都具有情感上的被动性、无法对象化、无法再现和无法符合等特征。
列维纳斯和亨利的“超越性”和“内在性”都是相对于意识的意向性而言的。在列维纳斯看来,以往的哲学把意识作为知识的根基,用意向性去统摄对象,因而是内在性的哲学。列维纳斯强调,他人是超越的,是突破了我们的意识的范围的。而亨利认为意向性是照亮事物的光,本质上是超越的,在其中,显现和显现者是相互分离的。但生命只能在自身之中依照自身而呈现自身,生命和生命中呈现的内容是同一的、不可分离的,且不在世界之中呈现,因而是内在的。简言之,在亨利那里,“超越性”指事物在意向性或世界之中作为对象而呈现,“内在性”指生命的“自行—感发”,是生命的自身完全内在的呈现。
三、“感受性”与生命的“恻隐与共”
在列维纳斯哲学中,“超越性”突出表现在他对伦理的理解上。与把伦理学视为一种关于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规范性学科的主流看法不同,伦理学在列维纳斯那里具有特殊的含义。在他看来,伦理学就是形而上学,是第一哲学。他指出,“我们把这种由他人的出场所造成的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称为伦理。他人的陌异性——它向自我、向我的思想和我的占有的不可还原性——恰恰作为一种对我的自发性的质疑、作为伦理而实现出来”。在他看来,存在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也是一种权力的哲学,一种不公正的哲学。这种不公正体现在,它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作为屈从于主体与存在的关系,这将无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暴政。实际上,把一切的关系都屈从于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的存在论,肯定了自由对伦理的优先性。而在列维纳斯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主导了整个西方哲学。换言之,在这种思维方式里,他者没有以其自身方式依照自身而呈现自身。因为对存在的理解不能够主宰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所以列维纳斯要做的就是让他者从存在视域中真正解放出来,让他者以自身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同一和他者的关系,我对他者的欢迎,是最终的事实。这种作为对话者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先于所有存在论的。存在论预设了伦理学,因而,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也是形而上学。
在列维纳斯看来,他人是超越性的。因为,第一,他人是不可对象化的、不可再现的:“形而上学关系不会是一种表象,因为在表象中他者会消解在同一中;任何表象本质上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先验的构造。”第二,他者与我之间存在着不同,没有任何先验的统觉可以发现和消除这种不同,因而,他人是不可赋义的。第三,他人是不可见的,因此也就不可被充实。他者的陌生性是不可被还原为我的思想的,对于他者,我没有任何力量(power)。他者通过一种本质性维度,逃脱了我的把握,即使他在我的处置之下。
既然他者是超越性的,那么他者是如何呈现的呢?列维纳斯认为,他者是以面容(face)的方式呈现自身。何为面容?和事物的不具任何深度的外观(façade)不同,他者的面容具有无限的深度和超越性维度,且通过语言(speech)而被表达。对列维纳斯来说,面容就是“‘一个要求,而不是一个问题,面孔就是一双寻求补偿的手,一双张开的手。’……我在一个小孩的饥饿的脸上或者一个乞丐伸出的手里,发现了我的伦理的责任”。面容虽然不能在直观之中呈现,但却是会说话的面孔。“面容打开了原初的话语,它的第一句话是任何‘内在性’都不允许回避的义务。”这种话语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经验,一种震惊性的创伤。这种完全的陌生性指导着我,向我发出道德命令。来自他人的面孔的目光将我置于一种完全的赤裸和赤贫状态。去认出他者就是去认出一个饥饿的人,就是去给予。换言之,他者面容是不可见的,无法在直观中呈现,因此他者的面容不是世界中的现象。他者的面容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他称为“临显”(epiphany)。他者的面容并不在直观中呈现,但它的呈现却比那些可见的呈现更加直接,同时,它也是一个遥远的呈现。这种呈现主宰着我,从遥远的、不可预见的地方来临。
他者的不可见的面容如何能够强加给我一种无法逃避的责任?这样一种被动性又是如何可能的?列维纳斯认为,对他者的责任根植于主体性之中,而这种主体性表现为一种比所有被动性还要被动的特殊的被动性。列维纳斯将这种特殊的被动性和“感受性”(sensibility)联系起来。他认为,“感受性就是主体的主体性”。何为“感受性”?感受性是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在《总体与无限》一书中,他强调这种感受性不属于思想的秩序,而属于情感的秩序。它并不低于理论知识,而是与内在的情感紧密相关。当满足了一个他者的需求,回应了一个倾向时,这种感受性便得到了滋养。感受性不是作为再现的时刻,而是作为享受的时刻而被描述。在《别于存在或超越本质》中,他指出,“感受性是(把自己)暴露给他者。不是一种惰性的被动性,处于静止或运动状态的持续性……感受性的暴露更像是一种自然倾向的倒转,一种毫无保留的给予,不寻求任何保护的状态……这种关于缺乏任何保护的状态的观点预设了易受伤害性自身”。简言之,列维纳斯试图用“感受性”来解释他人的面容带给我的被动性。我之所以会因为他人而感受快乐或痛苦,仅仅是因为我是为他的(I am-for-theother)。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原子式的存在,我的主体性内部具有一个本质结构,即我是为他的存在,我的主体性或“感受性”里已经包含了他者的维度。因此,我才会为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才会对他人感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列维纳斯对涉及他人痛苦的“感受性”的阐述与亨利揭示的生命的“自行—感发”中的“恻隐与共”(pathos-with)维度具有一致性。亨利认为,“如果没有生命的“自行—感发”,那么任何事物都无法被看见”。在亨利看来,生命是一切事物显现的先在条件,同时生命也向自身显现。具体地说,生命就是情感本身,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快乐和痛苦。换言之,生命是情感的“自行—感发”。在生命中,感受和感受的对象是同一的,二者不可分离且没有任何间距,同时也是完全被动的。因而,在亨利看来,生命的显现是完全内在的。“一切拥有这种自我感受的奇妙性质的就是有生命的,而一切缺乏这种(自我感受)的就是死的。例如,石头因为无法经验自身,所以是一个‘物体’。”而生命的自我呈现被亨利称为“享受”,他认为生命是不可能在意向性和感知中呈现的,因而不可能在世界的真理中呈现,生命的情感是先于意向性的。
在亨利看来,“自行—感发”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由他人所引发的异质感发,也被亨利称为“恻隐与共”。我之所以能够感受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到痛苦,是因为我和他人都拥有生命,同在生命的“共同体”(community)里。生命是先验的、不可见的,因此,生命的“共同体”也是先验的和不可见的。
亨利指出:“鉴于共同体的本质是生命或感受性(affectie),我们可以与任何受苦的生命一起共同受苦,‘恻隐与共’是所有可以想见的共同体的形式。”当我与他人面对面相遇时,他人对我的注视并不首先意味着他人对我的形象的再现。这种认知层面的意向性的构建是在后的,换言之,他人对我的注视以及他人与我的关系并不首先建立在再现或意向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生命的基础上。他人对我的注视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能够让这种目光成为一种欲望,在看之中,总是已经有不可见的生命在决定它了。从亨利的角度看列维纳斯,他人的面容也是情感性,这种情感性让他人的面容成为一种表达,一种道德命令。这种情感性和表达是先于意向性的,是基于生命的。
既然我与他者的相遇并不是我把他者视为另一个自我的意向性的认知过程,而是更为原初的建立在生命基础上的情感的互相感发过程,那么,这样一种原初的体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根据亨利所说,“这样一种原初的体验很难被思考,因为它逃脱了每一种思考……这是一种纯粹的经验,没有主体,没有视域,没有含义,没有对象”。在《物质现象学》第三章中,他举了一个例子:婴儿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意向性的认知基础上,因为这个阶段的婴儿并不把自己视为婴儿,也不把母亲视作母亲,婴儿将自己看作自己母亲的孩子的视域并未被唤醒。此时,婴儿既没有“我”的概念,也没有“他者”的概念。母婴关系里“还不存在一个世界,也没有任何能够构建这个世界的关系”,因而没有任何反思性的关系能够构建它。这种纯粹经验是生命的体验,根植于生命的“恻隐与共”。
在亨利看来,生命的“恻隐与共”并不仅仅局限在母婴关系之中,而是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关系之中,而且是这些关系的先验结构。他以康定斯基作品的爱好者为例说明这一点。康定斯基作品的爱好者可以完全没有见过彼此,却能够因为康定斯基的画作而结成一个“共同体”。因为康定斯基的作品不仅仅只是颜料的堆积,而是生命的再现,生命使康定斯基的爱好者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康定斯基画作作为康定斯基本人的生命再现,与康定斯基画作的欣赏者之间发生了生命的“恻隐与共”。康定斯基的作品并不是对可见物的模仿,作品上的颜料也并不仅仅只是物质材料的堆砌,相反,每一种颜色、每一个笔
触都是不可见的力量,它追踪着最内在的生命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定斯基的画作呈现的是康定斯基本人最内在的生命。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看到一幅画作会流泪。流泪反映的是生命的共鸣,正是作品自身展现的情感联合了康定斯基画作的欣赏者们。根据亨利的看法,“共同体”之间的“恻隐与共”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和他人都共同拥有同一个生命,都拥有同一个生命的来源。如亨利所言,每个人都从同一个源头饮水。
从亨利的视角看,我之所以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他人之所以能向我发出道德命令,正是因为我和他人具有“恻隐与共”的先验结构,这个结构先于我们的理性反思,先于意向性。因此,列维纳斯所揭示的他者的“感受性”和亨利所揭示的生命的“恻隐与共”具有一致性。
此外,列维纳斯的服从于(subject to)他者的交互主体性,也可以为亨利的交互主体性提供伦理学的维度。亨利认为,“绝对的现象学的生命,其本质由感受或经验自身的事实组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体性”。在亨利那里,主体性就是绝对的现象学的生命,就是生命的“自行—感发”,交互主体性表现为生命的“恻隐与共”。然而,亨利所探讨的生命的情感(如痛苦)是偏中性的,他着重论述的是生命的情感感受的绝对内在性。但是,在列维纳斯看来,真正的主体是伦理的主体,是服从于他者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作为“我思”的主体,而是一开始就处于绝对被动性之中的作为宾格的我(me),表现出一种屈从于他者的伦理关系,以及我对他人的无可逃避的责任。乞丐伸出的手,不仅述说着他的贫穷,更是向我发出的一种道德命令,让我感到我对他的贫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饥饿的儿童的瘦小的身形,更让我感到痛苦和羞愧,对于他的饥饿,我有着无可逃脱的责任。我是作为“为他者负责”的主体而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所讨论的主体性(subjectiity)可以为亨利的主体性提供更丰富、更具体的伦理内涵。同时,列维纳斯伦理学的丰富内涵,可以在亨利对生命的真理的论述那里得到更为清晰的阐述和说明。因此,二者的思想不仅是内在一致的,也是互相补充的。
结语
列维纳斯的“超越性”指向的是超出自我意向性范围和理解的他者,如若强行将他者拉入自我意向性的统辖范围,这无异于对他者的暴力。他站在他者的角度反观意识,看到了意识的有限性和总体性,即“内在性”,强调他者在本质上超出我的意识范围,因而是“超越的”。米歇尔·亨利的“内在性”指的是无法外在化和对象化的绝对生命的自身显现。他站在绝对内在的生命的角度,看到意向性意味着将对象放在面前去把握,呈现出一种对象化和超越性。因此,在二者的哲学文本中,“超越性”和“内在性”的概念的内涵具有相通性。
既然超越性的他者超出了我的意向性范围,那么自我如何能够接受他者发出的道德命令?列维纳斯通过对“感受性”进行阐发,表明自我不是一个原子式的存在,在自我的主体性内部具有一个本质结构,即我是为他的存在,在自我的“感受性”中已经包含了他者的维度。这一思想与米歇尔·亨利所揭示的生命的“恻隐与共”具有一致性。我与他者共有同一个生命,所以在我和他者的生命中都表现出“恻隐与共”的先验结构。基于这个先验结构,我能够体会到他者的痛苦,并且对他者的痛苦感到痛苦。生命的“恻隐与共”比意向性更根本,在意向性的把握之前,生命间的感受就已经通达彼此。因此,二者在核心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另外,列维纳斯的服从于他者的交互主体性,也可以为亨利的交互主体性提供伦理学维度。因此,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不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可以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