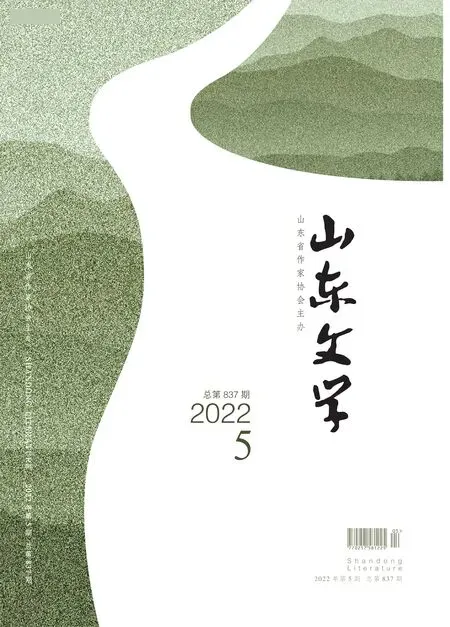我的妹妹马海美
亦 夫
曾经一度,我对我妹妹非常崇拜和充满暗恋,甚至常有娶她为妻的想法。我叫苏雷,随父姓,妹妹叫马海美,则是继母在嫁给我父亲之前,与一个姓马的男人未婚生育的。我父亲苏学伦和继母王慧是小学同学,据说一直青梅竹马,恋情甚笃。但由于家境的原因,苏家一直不同意儿子娶贫困的王家女为妻,所以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给我父亲安排了婚姻。王慧出于对苏学伦的报复,居然选择了镇上一个品行被人诟病的马姓二流子同居。但没几年,二人都抵不过对初恋的怀念,各自草草地结束了婚姻和同居生活,正式结为了夫妻。但他们的身边都多了一个“拖油瓶”,那就是我和妹妹马海美。父亲曾想让继母将马海美改为苏姓,但继母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马姓男人是你曾经对我流放的见证,我到死都忘不了。”
我和马海美因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我对她从小的崇拜,在上初中对成人之事半懂不懂之后,就开始考虑到了我和她结婚的可能性。我曾经把自己的这个令人苦闷的想法告诉给了好朋友孙成,没想到他却在同学间到处传播,结果“苏雷居然要娶他妹妹”的惊人消息就传遍了小镇。本来就爱嚼舌头的小镇住民对这件事津津乐道,并把我父亲和继母早恋期间的种种往事翻了出来,一时流言沸沸扬扬。父亲闻知此事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打了一顿。我记得那是一个春天的黄昏,我无助的求饶声不但没有熄灭那个男人的怒火,反倒让他变得下手更重。他一边殴打我,一边气急败坏地骂道:“人家不是在传你的闲话,而是在羞辱我们两夫妻无德又无能啊。”倒是从外面玩耍回来的马海美看到这一幕后,上前拉开了父亲。她并不替我求饶,而是愤怒地大喊大叫道:“再打要出人命啦。”
马海美那天的英勇举动让我大为感动。我甚至私下想,面对那样的流言蜚语,她不但不恨我,而且出手相救,莫非也与我有着同样的心思?事后不久,等我吞吞吐吐、满脸羞涩地试图一探她的心思时,她却表情厌恶而鄙夷地说:“你想什么呢?我就是嫁给镇上的王瘸子,都不可能嫁给你。”
从那天开始,我知道我和妹妹还没有开始的爱情便成了黄粱一梦,成了还没有发芽就被她一脚踩碎的一粒种子,连一丁点儿的希望都不存在了。
我对妹妹从小的崇拜和暗恋,在我成年后再去回味时,觉得简直荒诞不经。我喜欢马海美,不是因为她是那种聪明乖巧、听话懂事的女孩子,恰恰是因为她天生就是一个不良少女。逃学旷课、惹是生非、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事,没一样不是她喜欢并擅长的。从十三岁开始,她便成了小镇上一景:永远都穿着新潮得让人感到不正经的奇装异服,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男女混混们,招摇于镇子上的大街小巷,像一朵醒目的黑色花朵。父亲苏学伦可以随意找个由头打我一顿,却因为继母的态度而对马海美没有半点脾气。他有时会在背地里长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孽缘生出来的怪胎,果然怎么也成不了正果。”
我对马海美的崇拜,大概首先源自父亲对她的厌恶却毫无办法。一个让自己的敌人感到头疼的人,很容易被划为同盟者甚至偶像。何况妹妹不但让我讨厌的父亲抓耳挠腮,而且她作为那些大人和老师不待见、却在我们这些学生中享有绝对声望的所谓“坏孩子”们个个五体投地的领袖人物,常常只需振臂一呼,小镇上就会有成为热点话题的事件发生。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年龄比我只小一岁的妹妹,我怎么可能不对她心旌摇荡?
马海美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我则在父亲的威逼下上完了高中。看着我差得不着调的高考分数,继母王慧假惺惺地对父亲说:“你劝苏雷复读吧,读个五年六年的,他也许总能圆了你的望儿成龙梦。”倒是父亲有自知之明地叹了口气:“算了,也不是读书的命,但好歹比马海美强出不少。”王慧说:“话别说得太早,出水才见两脚泥。”
我在镇上一家磁性材料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上班不久就与同车间女工韩红梅恋爱结婚了。我结婚时,妹妹马海美不仅送了我一份大礼,而且由于她人缘广、路子野,许多价廉物美的结婚用品都是通过她才搞到的。在婚礼当天,马海美带着一大群打扮得花里胡哨的男女来参加婚礼。她私下对我说:“哥,别介意那些家伙们的身份,他们今天唯一的作用就是来随份子钱的。”我对她说:“哥没出息,真是羡慕你的神通广大。”她说:“你过不了我这样的生活,这是命中注定的。”
在我看来,继母王慧简直是拿妹妹当作她人生的一块试验田了:她似乎想在女儿身上,看看自己当年的离经叛道如果没有及时终止,人生到底会有怎样的结局。她对马海美的一切选择都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就连女儿在镇街上绯闻不断、按众人的话说就是“还没有嫁人就坏了名声”的事,她也从来都不置可否。父亲苏学伦从来都没有胆量数落马海美,他偶然私下对继母抱怨一两句,却都会招惹来王慧的反唇相讥:“我当年也是没有嫁人就坏了名声的,你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干吗要上赶着娶我?”这个时候,父亲就没了话,只会发出一声寓意不明的叹息。
大概是我从小对妹妹的崇拜和顺从,使得性格迥然不同的我们兄妹之间,保持了这个四口之家中最和睦、信赖和亲善的关系。所以在她厌倦了与各种不同男人的纠缠,打算找个人结婚过踏实日子的时候,她并没有将这个人选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而是告诉了我。
那是在我结婚第二年的那个夏天。妹妹给我说完这个打算后,我有些不相信地问道:“你是认真的还只是头脑一热?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状态适合你吗?”妹妹说:“不适合我,但我现在的状态也不适合我。走,我带你去见见他,算是有家里人替我把把关。”
说真心的,在去见有可能成为未来妹夫的路上,我一直觉得有些可笑:有镇上“最不着调女人”之称的马海美,让我这个老实巴交的哥哥去替她把关未来的结婚对象,还有比这更不着调的吗?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让我去见的人,居然会是一个年轻的屠夫!
马海美带我走进镇上规模最大、最豪华的“松林酒店”的后院的工作间时,那个叫关海的人正低头在一块巨大的案板上剁排骨。这是个身形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穿着背心裤衩,腰间系着一块油污不堪的裙布。工作间有不少机器发出一片噪声,马海美叫了三声,关海才从成堆的排骨中抬起了头,脸上立即露出一丝尴尬和惊慌,随后“嘿嘿嘿”地笑了起来:“怎么会到这里来找我,突然袭击啊。”
“这是我哥!今天算是让你见我的家人。”马海美说。
“哥!你好哥!”关海放下手中的砍骨刀,走过来就想和我握手。但他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不好意思地说,“哥,我手上尽是油腻,等我洗了手再和你握吧。”
我其实根本不在乎去握一只刚才还在砍排骨的油腻腻的手,我无法接受的是这个年轻的屠夫将会成为我未来的妹夫,成为那个从小在我眼中基本上就属于大神的马海美的同床共枕之人。大概我复杂的心情都表现在了脸上,妹妹对关海说:“我已经在你们这里定好了包间,中午你可得把哥陪好了。在我们家我就听哥的,你的小命就攥在他的手上。”我心说:“天王老子的话你都不听,你能听我的?”
这顿饭可谓穷极奢华,几乎将“松林酒店”昂贵的招牌菜都点了一遍。但却让我吃得极不舒服。洗过澡、换了一身干净行头的关海,虽然比刚才油渍麻花的形象好了很多,但依然摆脱不了不知是生而自带还是职业养成的粗俗与鄙陋:他吃饭时吧唧嘴的声音带着一种故意显摆式的豪放;他不时会站起身来,用手去抠一下屁股,然后大大咧咧地说,自己多年来患有肛门瘙痒的顽疾,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他会把已经咬了一口的烤鹌鹑重新夹回大盘,说自己这几天牙疼,吃不了太硬的东西……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反感。但其实最让我无法容忍的,是他对马海美几乎到了奴颜婢膝的顺从。在整个吃饭过程中,关海都不像是马海美的未婚夫,而完全是一副仆人兼保镖的嘴脸。名义上是陪我吃饭,但每道菜一上桌,关海连一句对我客气的话都不说,首先做的就是把这道菜的精华部分率先夹给马海美。这连马海美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她说:“别尽照顾我,你的任务是把哥陪好。”关海却笑嘻嘻地端起酒杯说:“女人主吃,男人主喝。哥,来,咱们走一个。”
我菜没吃几口,灌了一肚子酒,同时也生了一肚子闷气。在结束饭局回去的路上,马海美问我对关海的印象,我一改凡事都与她商量的口吻,不容反驳地说:“一个粗鄙不堪的屠夫,你真的会愿意嫁给他?”马海美笑道:“他为了讨好我,连你都敢冷落,你说天下哪里还去找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我愤然道:“那你找的不是爱人,而是一条狗。”马海美说:“你老实人不懂,关海可比狗好多了。”
我的把关只是一个摆设,妹妹对自己的婚姻像别的事一样自作主张,谁也干预不了。对于这样一个无论长相还是举止都过于粗陋的男人,就连对妹妹一切决定都不持否定态度的继母王慧,都有些坐不住了。她委婉地对女儿说:“你才23岁,多谈些时间,女人一旦结婚,如果再碰到确实适合自己的,就算对方愿意娶你,那身价也大大贬值了。”马海美说:“我从初中开始就谈,我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我。”然后很快就和关海领了结婚证。
起初,我对马海美选择“下嫁屠夫”,内心更多的是惊诧与失望。但后来,随着她婚姻生活不断创造出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我不但没有恢复昔日对她那种自愧弗如的崇拜,反倒变成了越来越强烈的蔑视和厌恶。
结婚后的马海美告别了昔日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她和关海在镇街最繁华地段租下一幢二层小楼,开起了镇上第一家民间信贷公司。马海美本来路子就广,客源自然不是问题。而关海的姑姑是镇信贷社主任,以曲径通幽的方式为公司提供了保障。短短一年时间,马海美就赚得盆满钵满,成了全县都排得上号的有钱人。她出入豪所,交游名流,从一个不良女子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颗冉冉上升的商业明星……马海美跻身上流社会,在小镇上居然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思维变革:过去对那个“到处闲浪的小妖精”嗤之以鼻的镇民们,忽然间对人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大家纷纷说:“从小看大,小时候越是顽皮的孩子,其实越聪明,日后越有出息,马总就是这类典范。”
令我大为郁闷的是,众人在对马海美不吝谀辞的同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我作为了反衬人物:再看她哥,从小乖巧听话,从不惹是生非,简直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可现在在干吗?工厂里整天一身臭汗的苦力工!
我内心自小对马海美所构筑起来的崇拜的大厦,开始变得摇摇欲坠起来。这是不是因为她的成功忽然给我平凡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不得而知。但我并不太关注这些,我只是觉得这个过去在我眼里率直、豪爽和充满叛逆色彩的妹妹,变成了一个极度功利和充满心机的人。比起给她带来人生机遇、对她言听计从的关海,我似乎更喜欢那些曾和她在小镇上肆无忌惮地闹出绯闻的年龄不一的各种问题男人。在我看来,那种离经叛道才给我暗淡无光的人生提供了一种模糊的希望。而摇身一变成为成功人士的马海美,不过是把她的聪明和胆识全部挪用在了人情世故上,而这向来都是让我感到复杂、压抑却又无力反抗的。
马海美的华丽转身,不但让我和她的关系发生了悄然变化,就连父亲和继母之间长期保持的那种微妙的平衡,也被彻底打破了。
我一直觉得,苏学伦和王慧这对一辈子都纠缠不清的冤家,把我和马海美都视为了自己手里的一件武器。结婚伊始,父亲觉得我乖巧听话,念书又好,从来不像马海美一样总是惹是生非,所以在继母面前总有一种耀武扬威的自豪感。但父亲的优势只是自我感觉,继母从来就没有觉得我有任何值得炫耀之处。我多次听到她私下轻蔑地对父亲说:“你还有脸说你儿子乖巧?一个男孩子,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长大了能有出息才怪。”父亲开始时还会反驳,但随着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乏善可陈,加上继母和马海美在家里的势头越来越强,我这件父亲曾认为尚可用来还击对手的武器,便被彻底弃之不用了。每当他看到我垂头丧气地从学校里回来,不是绝望地长叹一口气,就是莫名愤怒地朝我吼道:“饭菜都喂了狗吗?怎么整天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马海美过去种种不良少女的行为,一直是父亲嘲笑继母和她那段同居生活的噱头,但后来由于她们母女的优势日渐明显,他对马海美的态度,便只能变成在私下里不屑一顾而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在他看来,我这个儿子尽管没有什么大的出息,但起码有了正常的工作和正常的家庭,总比整天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在一起的马海美要强出许多。
但自从马海美忽然摇身一变,成了连镇长见了都得赔着笑脸的人物,我觉得父亲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他对继母的态度,从以前的沉默和冷脸渐渐变成了随声附和甚至主动讨好。
“妈的!一切都是钱闹的。”我一看见父亲那副放下身段、低三下四的样子,就觉得既可笑又可憎。
但我却也不得不承认,钱确实是世界上最有魔力的东西。夏天来临的时候,马海美先是出钱将父母的住处重新装修了一遍,栽花种草,更换家具,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立即焕然一新,变得既精致美观又舒适便利。一直想搬出去租房另住但又囊中羞涩的我老婆韩红梅,这下也笑逐颜开,看我的脸色也比平日舒展了许多。有一天晚上她在被窝里主动搂住我,喜滋滋地悄声道:“我听见咱妹子对妈说,入冬前将在镇上给他们买一套楼房。到时候,这个小院子就只剩下咱俩了。”尽管韩红梅是个善良且踏踏实实跟着我过日子的女人,但她的这副嘴脸还是让我非常厌恶。
我一直不明白,马海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让关海这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像个小跟班似的,对她不但言听计从,而且即便在盛怒的状态下,只要马海美一出现,他就立即会变得慈眉善目,像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马海美并没有觉察到我内心对她态度的变化,一如既往把我这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哥视为家中关系最亲近的人。她多次劝我辞掉工厂的工作,跟着她干,但都被我固执地谢绝了。为此不但韩红梅背地里气急败坏地直骂我是个“放着现成的金碗去讨饭的”,就连已经对我的人生不抱什么希望的父亲,也破天荒地主动和我做了一次长谈。父亲见怎么苦口婆心地劝我去做妹妹的手下,我都坚辞不从,这个一辈子都好面子的老男人,居然第一次用祈求的口吻对我说:“儿啊,就算爸求你了,爸一辈子吃亏就吃在本事不大却抱负不小上了。”
我不愿意听从马海美的提议,并非我有什么“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节,而是我坚定地认为,如果人心术不正,眼下爬得越高,日后必然跌得越重,我犯不上用自己的稳定职业去图一时之快。马海美大概正是通过这件事,看穿了对她态度的转变。有一次全家人聚餐时,关海正端起酒壶给我添酒,她却忽然拉起一张长驴脸,冷冷地说:“姓关的,你他妈的给我坐下!这个家里,什么时候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关海不知道这话其实是冲我说的,一时蒙了,愣在那里半天不知道这酒到底是该斟还是不该斟。
我失宠了,失宠于这个人人都在拼命巴结和讨好的女人了。这样的结果对我虽然毫无影响,但我父亲和老婆却如同遭受到了灭顶之灾一般。韩红梅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善良女人,在骂过几声“赖狗扶不上墙”之后,日子该咋过还咋过。倒是我父亲苏学伦却真的伤筋动骨了。自从马海美开始冷落我以后,他从开始对我哀其不幸的唉声叹气,渐渐转向了怒其不争的横眉竖目。我们家固有的二比二的阵营划分也彻底改变了格局,父亲彻底成了王慧、马海美阵营里的一员。父亲开始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发表对人生的各种见解,这让我感到十分迷惑:就如同大半辈子父亲都一闻到榴莲的气味就恶心欲呕,而现在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对其大快朵颐。
公司成立第四个年头的那年冬天,关海由一个杀猪的屠夫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凶犯。
在这家民间放贷公司里,关海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催收逾期未还的贷款。他手下原本有一帮凶神恶煞的壮汉,用不着他亲自出面。但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为了向老婆表达自己的敬业精神,关海对于上门催讨的事十分积极和着迷。短短几年内,他就以凶悍、残忍和决不妥协而威震一方,使欠账者闻风丧胆。关海过去在催讨账目的过程中,虽然也闹出过不少流血伤人事件,但最终都被马海美用金钱或找人出面摆平了。关海最终闹出人命,但碰巧那段时间马海美去了省城,死人的事没能及时捂住盖子,于是成了一桩人人皆知的丑闻。
这桩拖欠案对于放贷公司而言,只有二十几万的小金额其实根本不足挂齿。平时这样的小麻烦连喜欢冲锋陷阵的关海都懒得去管,可偏偏那天因为马海美不在,他在公司闲得无聊,便临时上了手下们的车子。而碰巧这次的欠账者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鲁夫,居然与关海的手下打了起来。站在一旁的关海还没弄明白,居然被左冲右突到自己跟前的那人挥拳打中了眼睛。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关海虽然眼冒金星,却兴奋地叫了起来:“刺激啊!小地方上居然真能碰到硬汉!来来来,我看看是你的拳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随即就从后腰上拔出了刀子……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不仅是关海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刑拘,而且放贷公司也因为怨声载道而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注意。一个由省上牵头的专案组绕开县上和镇上,直接接手了对该公司一系列违法犯罪问题的调查……
“马海美要完蛋了!上天有眼,不会让一个破鞋总那么人五人六的。”在这个阴寒的冬天里,镇民们总算有了一个让他们热血沸腾的话题。各种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到处传播,而话题的主人公并非杀人犯关海,也不是因此而受到牵连的他在信用社当主任的姑姑,而无一例外地是马海美。因为在所有人看来,无论关海还是他的姑姑,只不过都是马海美的卒子,拿下马海美本人才是这盘大棋的致命一将!
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最纠结的人无疑是我父亲苏学伦。马海美已经被人推上悬崖的状况,让这个郁郁不得志的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表达的尴尬:他像一个矜持地观望了半生、终于放下自尊而投敌求荣的人,却遭遇了新主子惨败在旧主子手上的意外之变,让他的处境真应了那句歇后语——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对马海美即将面临的粉身碎骨的厄运,既有悲观和失落,又有暗喜和亢奋。这种矛盾心理让父亲对继母的态度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既不愿意再像个降兵似的对她俯首帖耳,又不能公然像过去那样分庭抗礼,所以只能选择暂时远离,以便隔岸观火。那段日子里,这个已经步入老年的骨瘦如柴的男人很少待在家里,而是经常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半天半天地徘徊在小镇北边的骆驼河边。我下班后去喊他回家吃饭时,他望着我的眼神古怪而复杂,人也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焦点人物马海美那段时间很少露面,这也是关于她的诸多流言蜚语得以不断蔓延的佐证。有说她已经被抓的,有说关海的铁杆子已经将其秘密杀害的,更有说她已经走投无路而自杀的……关于马海美自杀的版本不下十个,但镇民们最愿意相信的,是她于一个月光皎洁的冬夜里跳入了骆驼河。这个版本之所以被广为传播,是因为不断有所谓的目击者出现,将自己亲眼所见说得有鼻子有眼。至于不同目击者描述的细节差异过大的问题,兴致勃勃的听众们哪里还顾得上细究?
但事件的结局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关海因涉嫌故意杀人、非法经营等罪名而被正式批捕,其姑姑也因为与公司的关系不但丢了公职,而且因涉嫌刑事犯罪而被拘留。而本来大家都认为是主犯的马海美不但没有死,而且得以全身而退,没有受到丝毫的牵连。对于马海美之所以能如此走运,说法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众人的共识,那就是关海将一切责任都独自担了下来,无论专案组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也不管许下任何减罪宽大的承诺,这个男人一定咬定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与妻子无关,马海美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家庭妇女而已。
“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这个结果显然无法疏导众人对马海美内心积攒已久的民愤,大家纷纷把咒骂发泄到了关海的身上。因为镇上有几位德高望重的有识之士,已经就马海美和关海的爱情和婚姻进行了虽然真假难明但精辟无比的总结:妖媚而满腹心机的马海美,之所以看上五大三粗的关海,就是为了利用其姑姑身为信用社主任的这层关系。这个看似浪荡其实却心思缜密的女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所以当初注册公司时就将法人写成了关海。现在,这个将马海美敬为女皇、替她背负了一切罪责的男人无疑面临死刑,而她却早已经私下里将所有财富进行了秘密转移,远走省城,重新开始了令井蛙般镇人更难以想象的上流人的生活……
这个分析我也难以判定真假,因为经历这场风波后,我们家的阵营再一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海美不知道是去了省上还是京城,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镇上露面了。我父亲和继母的关系因为这场变故又变得疏远和对立,开始经常像过去一样,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唇枪舌剑,并把几十年前的旧事翻出来相互挖苦。进入腊月以后,韩红梅忍受不了家中天天骂声不断的恐怖气氛,终于和我搬出去租房另住了。
大年三十晚上,我和韩红梅懒得大张旗鼓,便提了两把挂面,借着和两位老人团聚的名义回去蹭年夜饭。结果回到小院时,冰锅冷灶的家里只有父亲一人。父亲听完我说的拜年话,愣了半天才说:“一晃都过年了?王慧这个狠心的女人,独自扔下我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吃惊地细问后才知道,腊月初的一天,久未露面的马海美忽然开车回到小镇,接上其母王慧,一句交代的话没说就扬长而去了。
“真是条喂不熟的狗啊!开着上百万的车子,居然都舍不得给我这个当爹的留下点粮油钱。”父亲说。
“我还说来蹭顿年夜饭呢。”我笑着说,“还好,家里油盐酱醋倒也不缺,就让红梅把这两把挂面煮了,权当一顿年夜饭吧。”
父亲猛地吸了一口旱烟,顿时呛得大声咳嗽起来。他抬头望了我一眼,眼神显得比以往更复杂了,其中既有对我这个不中用儿子的失望,又有对自己老无所依的凄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