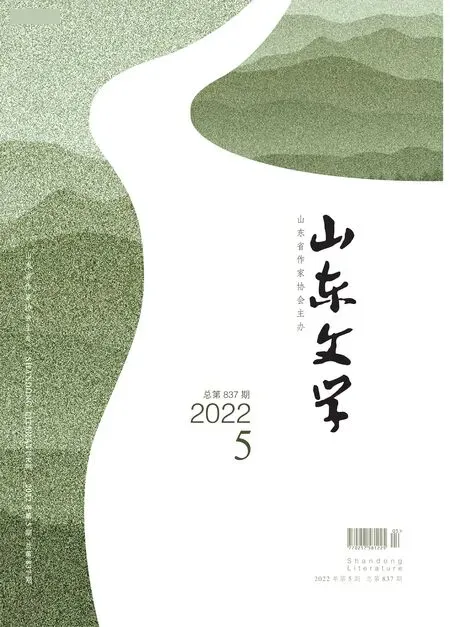蓝月亮
李建秀
陈默生每次回小城,都喜欢住在锦华酒店最顶层的套房。
站在落地窗前,可以眺望整个小城的夜景。这几年,小城的发展很迅速,彻夜不眠的璀璨灯火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无言地渲染着一种繁华。
默生曾经在无数个落地窗前欣赏过夜景:华盛顿、香港、台北、上海、南京、厦门、北京……他最初是在一家美国独资公司上班,后来跳出来单干,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又在南京、长沙、厦门等地开设了分公司,成天四处飞。无论在哪个城市,他都喜欢住酒店的最高层,越高的地方离月亮越近,潜意识里他还想验证一下,是不是近一点看,月亮就不会是蓝色的了。
在默生眼里,月亮一直是蓝色的。默生曾为那灰扑扑的蓝惶恐了好久,以为自己是色盲症。可是,白天,世界在他眼里是清晰的,红是红,白是白,黄是黄,绿是绿。即便是晚上,他依然分得清各种颜色。唯独天上的月,不是金黄色,不是白玉盘,也不是红月亮,而是雾霾般的蓝。
默生大学时选修过心理学,也曾旁敲侧击地咨询过心理学专业的师兄。师兄说不就是个月亮嘛,又不妨碍吃喝,啥颜色还不行。默生刚要急,师兄正色道,专家说所有的对月抒怀都是因为求而不得,把最想得到的东西搞到手试试。然后凑到他耳边小声补充了一句:尤其是女人。
默生哭笑不得,嘴里骂着什么狗屁专家,心里却存了几分疑惑。
默生的事业越来越顺,越来越大,往他身边蹭的女人各具风情。默生荒唐过一段时间,但月亮的颜色丝毫未改,他也就明白了,“过尽千帆皆不是”。
此刻,默生站在锦华酒店最高层的窗前,一边轻轻晃着杯里的红酒,一边尝试着把对面的小区还原成当初的模样。当初这里是一片平房,方格子家在第二排胡同东首。她家门前有一棵粗大的梧桐,春天时,满树都是小喇叭样的紫色花,花蒂处甜丝丝的。方格子的卧室并不很大,放着床和学习桌,窗户上挂着橘黄色的窗帘,墙上贴着一张明星海报。
默生在县一中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方格子。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他拖着自己的蛇皮袋子怯生生地走进高一三班时,教室里已经零散地坐着七八个同学了。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生拿着花名册在挨个统计同学的信息。默生没见过那么好看的白裙子,禁不住多看了两眼,恰好女生笑着回过头来,默生的眼睛立刻被黏住了,女生笑得像是窗外秋天的阳光,明亮,舒适。
那阳光走到默生面前停住了,一张表格伸到了他面前。他低垂着头,紧张地干咽了一口唾沫,握笔的手有点抖,写完了后他悄悄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里的汗。方格子瞪大了眼睛说,原来就是你数学考了满分啊。默生抬起头来,望着方格子那湿漉漉黑亮亮的眼睛,发现单眼皮居然也这么好看。他的心突然跳得厉害,脸颊烧得慌,赶紧把头扭到一边。平心而论,方格子只是中等姿容,可是,从第一眼起,默生就认定了她是美的。即便后来他见识过许多女人,也没有一个人能取代方格子的美,没有一个人的笑能像当年的方格子那样让他脸红心跳。
默生刚从马家埠回到城里。大学毕业二十多年了,他回马家埠的次数用一个巴掌就能数过来。但是这并不妨碍默生成为整个村子里的标杆和楷模,他年年寄回来的钱摞起来,怕是比老马头背后的罗锅子还要高很多。人人都感慨罗锅马命好,当年的拖油壶居然是个香油瓶,钱桶子,金罐子。他此番回来是奔丧的。如今丧事已了,他和马家埠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以后怕是不会再回小城了。可若真的从此和小城一刀两断,他又有些不舍,毕竟方格子还在这里。
默生不喜欢跟人谈论家乡,不喜欢谈论童年,甚至不愿意多谈父母,唯一一个让他敞开心怀,将自己和盘托出的人,是方格子。
高中三年,方格子一直坐在默生的前面。她时常回过头来向他请教数学题。每次默生讲完,她都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般地“哦”一声。起初说谢谢,后来就感慨他脑子到底怎么长的,那么聪明。那似喜似嗔的神情让默生挪不开眼睛。方格子的夸赞并没有让默生生出多少优越感。尽管方格子的数学经常不及格,可是她的语文和英语很出色,特别是她的作文,时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默生惊讶方格子读过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事,羡慕方格子思维的活跃,语言的生动。每次上语文课,默生都底气不足。整个小学和初中,除了课本,他几乎没有读过别的什么课外书。
方格子开始借书给他。从三毛到席慕蓉,从雨果到托尔斯泰,默生的世界一下子被打开了。他们常常就某本书进行激烈的讨论。方格子记忆力极佳,见解总让人出乎意料,默生觉得自己开阔了起来。默生给方格子写了好多信,夹在书里送给她。那些信,不是情书,有的是读后感,有的是他埋在心里不曾对别人说起过的委屈。
他在马家埠小学读了六年书,没有一个朋友。他们班全是姓马的,只有他一个外姓,大家看他的眼神,像是看集上耍猴的。没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拖油壶,说他妈是个病秧子美人,嘲笑他后爹的罗锅子,学他的口音。默生坐在四五十个人的教室里,却觉得自己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那些同学们,不仅同门同户、同根同源,还有着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你叫我小姑,我叫他堂兄,他的爸爸是她的舅舅,她的奶奶是他的大娘……那张细密的网里,容不下一个文弱的异乡人。
有一次,数学老师用的大三角板不知道怎么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截,六个马姓的孩子异口同声说是默生干的。默生急眉赤眼地解释说不是我,可他的声音是那么微弱,微弱到老师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根本没有听见他说什么。他委屈地直掉眼泪。他曾经尝试着讨好他们,想融入他们之间,把自己做的弹弓借给他们玩,结果,他们不还他了。他问他们要,却被他们取笑了一顿,说他是小黑狗,还骂他是小黑狗生的,要不怎么会叫“墨生”呢。他疯了一样扑上去打他们,却哪里是一群人的对手。他蜷缩在地上呜呜地哭,真的像一条小狗。后来,同学们渐渐发现这个拖油壶虽然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成天闷声不响,走路溜墙根,但多难的数学题他都不带皱眉头的。有时候老师都解不出来的题,他却刷刷刷就写出了步骤和答案。有些人开始拿着不会做的题找他,讨好地叫他默生,问他要不要放学后一起去村外的树上掏啄木鸟蛋,可那时的默生已经习惯了一个人。
那些事情,连默生娘都不知道。默生知道即便是跟娘说了,也不会有任何用处。他在外面挨了揍,回家从不吭声,有时候当娘的也会从他脸上身上看出点什么,看出来也就看出来了,顶多就是说以后离那些孩子远点。
默生并没指望方格子会回信,他只是出于一种信任,一种亲近,一种倾吐的渴望。没想到方格子很认真地给他回了,开导他,安慰他,鼓励他。她的信跟她的眼睛一样,温柔而明亮。那些信,默生一直珍藏着。他把心底那些黑暗潮湿的角落打开来接受过阳光的照射后,又关上了,从此再也没有打开过,譬如,就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八岁那年夭折了。
他给方格子发了一条微信,问她在干吗。方格子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他说瞎忙,配一个龇牙咧嘴的表情。默生犹豫了半天才说有空的话咱俩见一面呗。方格子惊喜地说你回来了?默生说嗯,住在锦华酒店。方格子笑骂了他一句,你这家伙,怎么舍得回来啊!
他们约好了在附近的料理店共进晚餐。
默生莫名地紧张了起来,他搓着手在房间里转了好几圈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看了看表,距离晚餐的时间还有三个小时。他飞快地下楼,去了酒店旁边的购物商场,给自己重新置办了一套衣裳;经过珠宝专柜时他停住了脚,挑了一枚水晶镶钻的胸针,一万来块钱,漂亮却不张扬,装在红色锦缎的盒子里,正是所谓的低调的奢华。
回到套房里,默生洗了澡,换上新衣裳,将自己收拾整齐,然后去了料理店。方格子还没到,默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手心里全是汗,心跳得很快。他抖晃着腿,用手指敲打着桌面,心却仍旧无法平复,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那时默生陷入了暗恋的痛苦,他的心里,长满了草,风一吹,哗哗作响。
默生自然没有勇气向方格子表白,非但不敢表白,连与人分享这个甜蜜的痛苦都不敢,唯恐被人耻笑。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被暗恋的痛苦折磨得喘不过气来,生怕被人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便转头跟另一个女孩好上了。那女孩也是单眼皮,齐刘海,脾气跟方格子有几分像。她对他很崇拜,吃饭、自习、跑操课间活动,一有机会就黏在他身边,两眼放光地看着他。因为那个女孩,方格子回头请教问题的次数明显少了。这更加深了默生的痛苦。
终于有人敲门。
默生忙起身相迎,方格子笑着拍了他一下:不愧是霸道总裁的范儿,就是头发有点短。
默生一边笑一边给方格子拉开椅子,说不光有点短,还白了不少呢!老了。
方格子说,别人的白头发是老的,你的白头发,是数钱累的吧!
默生大笑,欣慰又庆幸。方格子风采不减当年。她的身材依然很苗条,合体的牛仔阔腿裤勾勒出了细腰和长腿,白色上衣是纯棉的,复古味道的泡泡袖和系成蝴蝶结的衣襟既彰显了衣服的品质,也烘托出了方格子的优雅气质。脸当然不复当年的娇嫩和饱满,眼角有几道细纹,但是没有眼袋,法令纹也很浅,嘴角边的两个小梨涡依然很俏皮。方格子整个人的状态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默生注意到她背的是古驰的链条包,虽然不是当季的新款,但品位在那里,他暗自庆幸胸针买对了。
方格子问他回来是公干还是私事。默生说,我父亲没了,刚出完殡,他瘫在床上三四年了,话不能说,腿不能动,大小便都得人伺候,只剩下了一副骨架子,缩在他的罗锅子里。最后叹口气:走了好,算是种解脱。
方格子说,生恩是恩,养恩也是恩。你回来送他最后一程,也是应该的。
默生点头说是,他虽然没生我,但好歹养了我这些年,没打过,没骂过,还能让我一路上完学,我应该感激他。
现在自然是感激的,但默生小时候打心眼里恨老马。默生娘给老马生了个儿子,乐得老马成天咧着嘴笑,龇着他那被烟熏黄的板齿牙。默生嫉妒弟弟被老马背着抱着举高高,用胡子茬扎脸。默生也嫉妒老马的亲闺女,那个整天防贼一样防着他,动不动就拿白眼珠子剜他的姐姐。老马天天支使她,买烟,打酒,摆棋盘,洗筷子,洗碗,洗臭袜子,跑腿,传话……默生甚至羡慕家里那些鸡鸭鹅猪羊们,老马看它们时笑眯眯的,眼里泛着光,而看默生时,眼里冷冰冰,仿佛默生不是个活物。
方格子皱着眉叹口气说,人的一生就这样,不断遇上生老病死,躲不掉,只得受着。
默生不想继续这个有点沉重的话题,便把那个锦缎盒子拿出来,推到方格子面前。方格子看他一眼,又打开盒子,说你这眼光,挺洋气啊。然后把盒子又推回到默生面前说:太贵重了,我怎么敢收?
有什么不敢的,你也送过礼物给我,我不是也收了。默生的声音不自觉地低了,柔了。
上大学的时候,默生曾收到过方格子的一条围巾。方格子在信里解释说同宿舍的人都在编织围巾,她觉得好玩,就跟着学,可真上手了却不容易,编了拆,拆了编,好容易织成了,却发现没人可送。恰好默生写信来,她便寄给了他。方格子解释得云淡风轻,默生却如同收到了一个霹雳,捧着那条用蓝色白色红色毛线编织的围巾,脑子一片空白,继而热血沸腾。他当然知道那样式的围巾已经风靡各个大学,是女生送给男朋友最好的信物。他白天晕晕乎乎地傻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恨不得立刻坐上火车奔向方格子的学校,向她表白。可就在默生准备去火车站的时候,几个老同学到上海玩找到了他,他只得陪着同学去外滩游逛。他们聊老师,聊同学,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方格子。一个同学遗憾地说,方格子就连想都别想了,整个年级的人谁不知道,语文老师早就拿方格子当准儿媳了,要不然能那么宝贝她?默生蒙了,语文老师的儿子在隔壁班,从未见过他跟方格子打过交道啊。几个男生议论了一通便兴高采烈地岔开了话题,可默生的身上,却是热一阵冷一阵的,丢了魂儿一样。默生的心最终冷却了下来,就算方格子不给老师当儿媳,就凭默生的条件,怎么能配得上?定是他自作多情了。默生在教室里枯坐了一上午,撕了写,写了撕,最终也没能给方格子回成信。
方格子敛了笑,低下头搅咖啡。趁着服务员来上菜的空,恰到好处地把问题翻了篇,问默生家里都好吧。默生简短地回了个好字,两人便默默地吃了起来。
默生三十八岁才结婚。起初是不敢结,他不知道怎样经营婚姻,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丈夫,不知道怎么爱孩子。后来,是找不到他想要的。他想找一个能让他敞开心怀将自己和盘托出的人,却总是不能如愿。有一次跟方格子网上聊天,方格子说自己女儿都上学了,他要是再不结婚,连儿女亲家都做不成了。默生明白,自己要的东西只怕永远不会再有。默生最终选择了他的师妹,一个精致又精明的上海姑娘。妻子生了女儿后做了全职太太,过的是贵妇生活。默生的生活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只不过,那种井井有条是程式化的,习惯性的:衬衣被熨烫得一丝褶皱也没有,皮鞋被擦得锃亮,一日三餐都有菜单,参加各种酒会时妻子会穿着长裙,挽着他的胳膊,得体地应酬……女儿今年五岁,从小就公主一样宠着,吃的穿的戴的用的全是大牌,一条尺把长的小裙子就五六千块。
日子过得很华丽,可默生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什么?他自己似乎清楚又似乎不清楚。
吃完饭,默生和方格子沿着马路散步。他们在县一中的门前逗留了一会儿。大门重新修建了,全然找不到二十多年前的样子了。他们边缓步走着,边回忆着高中时代这条马路的样子:最头上是一家叫春风的音像店,全是盗版磁带和碟片,成天循环播放着最流行的歌曲;挨着音像店的理发店门口有个不断旋转的玻璃圆柱,圆柱里有彩丝带,男生们私底下一致认为那是有色情服务的暗号,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理发店的专用标志;理发店后面的那家澡堂是个单亲妈妈开的,她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澡堂边上有个修鞋的小瘸子,喜欢一边干活一边用收音机听单田芳的评书……
方格子说,你对这条街挺有感情啊。
默生说,这条街尽头左拐第二排平房就是你家嘛。
默生将后面的话咽了下去。他在方格子家胡同口的阴影里,抱过她。一个醉酒的男人在路中央撒尿,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方格子吓得惊叫一声,躲进了他怀里。那其实是半个拥抱,默生一只胳膊搂抱着她的腰,一只手紧握着她的手。那一刻,默生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无限大,他一抬头,似乎看见了金黄色的月亮,可是他无暇去分辨月亮的颜色,幸福的眩晕让他紧紧闭上了眼睛。
两人一时无语。到了酒店门口,默生邀请方格子上去喝杯茶。
默生泡的是菊花茶。白色小菊花开在金黄色的玻璃杯里,柔和雅静。默生又从一个精致的小罐子里取出两颗冰糖放进去,冰糖沉到杯底,一串细泡冒出来。
方格子微微一笑,似乎悟到了他的意思。菊花茶里加冰糖?
果然,默生说,这曾经是我有生以来受到的最高礼遇。有男生到家里找自己的女儿,做妈妈的非但没拿棍子赶出去,还招待茶水,茶水里面还特意加了冰糖,那不是一般的开明和自信!
方格子端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再抬起眼睛时,眼圈红了。她轻声说,我妈也去世一年多了。
默生一惊,年龄还不算老啊!
方格子说,心梗。
默生心里一阵钝痛。他还记得方格子妈妈的样子。烫着头发,喜欢笑,大嗓门说话,处处透着一种敞亮和热情。那年夏天,他去找方格子,方格子的妈妈很热情地泡了一壶菊花茶,然后往两个茶杯里放了冰糖。那天,默生喝着甜甜的茶水跟方格子聊了一个下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后来,默生的脚总是不由自主地走过音像店、理发店、澡堂、修鞋铺子,拐进胡同里,停在方格子家门口。很多时候他只是静静地站在树下,听到有人出来的声响便飞快地跑掉。即使那样,也很满足。
方格子的眼泪一颗一颗地滚下来。她说母亲去世的这一年多,她成天浑浑噩噩,开车在路上经常走神,有一次差点跟对面来的公交车相撞。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脸上长斑,口舌生疮,心慌气短,去阳台去厨房或者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都会呆愣上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大半年的中药,日子才渐渐变得像日子。
方格子说,默生,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感觉心底有个大窟窿,什么东西都不能填补。
默生握住了方格子的手,凝视着那双湿漉漉的眼睛,沉声说,我懂。这半辈子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他在十五岁那年就体会到了什么是丧家之犬。那天,默生步行了十里路从镇中学回到马家埠拿干粮。刚到家,天突然变了,乌云低垂在头顶上,厚得像是打翻了的墨汁子。默生拿上了干粮,却磨蹭着不肯走,眼角不停地瞥着母亲,希望母亲能留他吃晚饭,他特别想吃一顿水饺。可母亲却自顾自地勾着花,没说一个挽留的字。默生只好背上干粮走人。刚出了村口,大雨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雷在头顶上炸响,身上很快湿透。默生一边走一边哭,大声地哭,哭得嗓子嘶哑了,还是哭。这一次,让默生切实尝到了丧家犬的滋味。后来默生上了县一中,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可那丧家之犬的滋味就像一根刺,时不时地冒出来扎他。每月一次大休回来,宿舍里热闹得像是开茶话会,同学们都把自己带的饭盒拿出来堆在桌子上,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五香花生、虾酱炖鸡蛋、或者蒸的豆沙包、烙的葱油饼,家境好点的同学饭盒里会有炸五花肉、炸小银鱼。大家嘻嘻哈哈,欢闹异常。每当这时,默生总是找个借口躲出去。因为他除了生活费之外,不带任何吃食——就连炒咸菜丝母亲都没有给过。
将他心底的窟窿变小的,是十个蛋挞,圆圆的,金黄色,带着热乎乎的香气,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铁盒子里。方格子悄悄塞进他的桌洞里,说那是妈妈烤的,让他分给舍友们。默生抱着那个点心盒子,趴在课桌上,很久都没抬头。那是高中三年来,默生唯一一次在宿舍里和同学们聚餐。他和同学们一样,都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小点心。
方格子的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一下一下砸在默生心里。默生很愧疚在方格子最痛苦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他起身,把方格子的脸埋进胸前,低下头,想把她的眼泪舔掉,却亲到了她的嘴唇上。方格子颤抖了一下,本能地躲避,默生却更加勇猛地吻了上去。
默生浑身像是着了火,在火中疯狂地掠夺着方格子的身体,那是他以为的安抚她的最好方式。到高潮退去,两人便相拥着喘息。默生平生第一次体味到,欢爱还可以这般酣畅美妙。他把方格子紧紧搂在怀里,很快睡着了。
默生醒来,方格子不见了,装着水晶胸针的盒子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默生跳起来,拉开窗帘,外面一片灯光璀璨。
默生拨打方格子的手机,没人接听。一直地打,一直地没人接听。微信留言,没有回音。默生身上冒了汗,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歹,电话响了,方格子回复: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默生僵坐在沙发上,身上的汗顿时变得冰凉。窗外,月亮慢慢爬上了天空,默生盯着那蓝幽幽的月亮,无声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