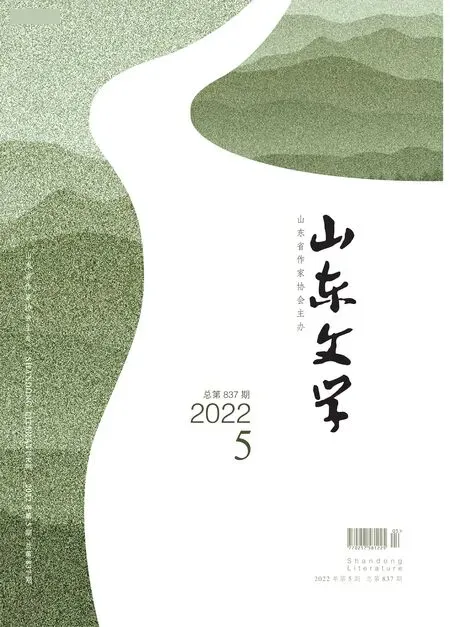小说二题
秋 泥
伊沙贝拉
贝拉一生喜欢赶时髦,她本就不多的工资都用来买时髦的衣服首饰,所以也没攒下什么积蓄。有时当她回首往事,她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恣意,命运好像并没有委屈她,并在三十五岁的时候赐予她一个时髦桂冠——大龄剩女。三十五岁是一个吓人的年龄,往前数就奔四张了。对剩女这个称呼,过去她是打死都不认的,现在也认了,是心态发生了变化。但她骨子里依然愤怒,自己怎么就没人待见了呢?渐渐地她开始喜欢听摇滚乐,新裤子、木马、刺猬等本土乐队,近来尤其喜欢二手玫瑰,每当她听到梁龙捏着嗓子喊:大哥你玩摇滚,你玩它有啥用啊。就喜欢得不得了,那混不吝的花腔令她怦然心动,是否暗合了她时下萎颓又满腔悲愤的心态呢?她自己也说不清。
她头上添了白发,皱纹也日渐明显,昂贵的皮肤护理没能减缓岁月的脚步,脸上没来由的会生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小东西,她本来就……她简直要崩溃了。其实走在街上她回头率还是蛮高的,这拜她苗条的身材所赐。用闺蜜的话说她臀部简直就像大蒜瓣一样鼓翘,走起路来左抛右甩,最勾男人魂了。但是她的脸和她傲人的身材并不匹配,她随母亲,赤红面。
赤红面是中医的叫法,人体面部毛血管由于极其细密,因此很容易发生瘀阻。西医称:红血丝综合症,也称为毛细血管扩张症。这种皮肤薄而敏感,过冷、过热、情绪激动、温度突然变化时脸色更红。小时候她看到母亲生气的时候,脸色会变得通红,那些蜘蛛网一样的血管会连成片,像公园里猴子的屁股。那时她很害怕自己将来也会像妈妈,但是好在她虽然遗传了妈妈赤红面,但没有妈妈那么红,奶奶欣慰地说,还好还好,咱贝拉不重,没完全随妈妈,真是万幸。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严重了,这让她心惊不已,于是开始疯狂护理的节奏。在多次相亲失败后,她没事就在同事面前撩起自己的裙子,你们看我的腿多白。这时同事都会说,是呀,你的皮肤多好呀,羡慕死我们了。她知道同事是在安慰她,皮肤好是事实,但没长对地方,能和脸换一下就好了。
后来她发现车间里宋工长那双大眼,老有意无意地往她腿上溜,令她很不自在。再后来宋工长竟然把她一个人叫到办公室专门谈她的腿,老宋说你是女孩子,有些话我跟你说似乎有点不合适,但我和你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你就当是来自一个长辈的关心吧。你看和你同期入厂的那一拨,差不多个人问题都解决了,你都三十多了还没有着落呢,别说对象连绯闻都和你不沾边,虽说这也算是好事,但也说明,是不……我和你师傅都看在眼里,没事也帮你分析了下你的问题。
听老宋这样讲贝拉脸都红了,她不好意思地说,有劳工长和师傅挂念了,我是真不争气。
你主要是战术不对,老宋说,你春夏秋冬穿着条牛仔裤,把你的优点都遮蔽了,你要多穿裙子,甚至多穿短裤头,亮出你美丽的大长腿,然后尽量在夏季里相亲,你的优点是一白遮百丑。靠,贝拉越发不好意思了,原来她误会老宋了,人家是关心她,这样想她心里就觉得很暖。
事实很快证明老宋的战术是有效的,不久后邻居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在一家铁路附属企业做钳工。男人长得斯斯文文的,个子不高,业余时间喜欢写小说,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作品,贝拉在背后戏称他小说家。贝拉听从了老宋的建议,穿着一条短短的牛仔热裤,亮着两条明晃晃的长腿就去了。果然,二人见面时贝拉感觉他的目光一直在瞄她的腿,而忽略她的脸,禁不住暗赞:老宋真乃高人也。
怎么说呢?贝拉觉得与小说家的恋爱谈的不踏实,男人的理想是将来做个著作等身的小说家,一上来就和她谈契诃夫、海明威、马尔克斯、卡夫卡等世界名家。开始时令她充满了新鲜感,但谈的多了呢,就难免让她产生疲倦感。什么意识流、什么拉美文学、什么后现代、什么西方浪漫主义等,让她有点打瞌睡。看着小说家被文学烧得通红的脸,觉得太脱离现实,有时贝拉会在他的兴头上委婉地说,咱唠点别的吧。小说家不为所动,继续说,小说最大的魅力就是虚构,虚构其实是最大的真实。小说的表达方式讲究藏,像冰山,你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是作家想给你看的部分,其实它最重要的部分都在水面以下。这种思维也会影响作家的行事风格,就像眼下,你看到的我,只是我想让你看到的我,并非真实的我,起码不是全部的我。
贝拉和小说家的爱情无疾而终。贝拉觉得小说家的脑袋脱离了人间烟火,他脑袋里都是别人的生活,像演戏,和这种人咋过日子。在贝拉看来,小说家是虚名,可满足虚荣心,在现实生活里没一点鸟用,但是小说家最后那个哀怨的眼神令她心里一颤,他说,祝你幸福贝拉。
大白腿效应只是让贝拉暂时有一个好的开端,却没有结局。后来的两段恋爱也都无结果,这让贝拉非常气恼。而且性感的小热裤也非常招风,特别是乘公交车的时候,老是有各色男人在她身后挤蹭,甚至……这让她气愤不已。男人真他妈不要脸,他们明明喜欢你的身体,却不爱你。
贝拉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她憎恨色狼,决心找机会教训一下他们。她开始跟视频学自卫术,练转身肘击和踢裆,据说这是最有效的防狼招数。
这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贝拉觉得有人在尾随自己,她走得快,那人也走得快;她走得慢,那人也会减速。后来她上了公交车,那人也跟了上来,就站在她身后,但那人并没有太过分行为,只是随着公交车的颠簸摇晃偶尔碰到自己,但她不能判断是不是故意行为。最后贝拉决定做个试验,在离单位还有一站地的时候她提前下了车。果然她下车,那人也跟下车了,贝拉发现马路对面有一个派出所,她穿过马路径直走进派出所办事大厅,一回头那人也亦步亦趋地跟了进来。
至此贝拉确认不疑,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色狼,而且还是色胆包天的色狼。这样想着她猛地回过身,借着转身的力量飞起一脚踢向色狼的下体,色狼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叫声惊动了那些警察,他们纷纷围了过来。贝拉大喊:抓色狼,快抓色狼!几个警察闻声一起冲过来,按住地上的男人,但他们很快就撒开手说,咦,这不是咱们伊沙所长吗?
看到地上痛苦翻滚的伊沙所长,大家心疼不已,天呀,不会把所长的蛋蛋踢坏了吧。
贝拉被留在派出所做笔录,然后让她回去等处理结果。一周后派出所把贝拉传了过去,接待她的正是那个倒霉蛋伊沙所长。贝拉想笑,但忍住了,她轻声说,您好些了吗?那天真对不起,我误会您了。伊沙问,你为什么这么做?贝拉说,我也是被色狼骚扰怕了,我恨他们。伊沙说,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我下死手啊,我和你有冤仇吗?贝拉说,没有没有,是我误会您了,我错了,希望您能原谅我。
虽然是误会,但我仍然感觉你那天是有意尾随我。贝拉又说。
你想听真话吗?伊沙说。
事实上我喜欢看风景,而你恰好出现在我的风景里。伊沙又说。
你这爱好代价有点大哈。贝拉说。
是的,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伊沙说完扔过来一张单子,说,这是公安医院做的医学鉴定,你看看吧。
轻微伤是什么意思?贝拉忐忑地问。
伊沙说,是指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碍,尚未构成重伤的轻微伤害损伤。我如果要追究你的责任,是要判刑的,按《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贝拉吓坏了,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下来,我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伊沙轻声说。
大哥,你别追究我啦,这么多年我一直就不顺,我真是个苦命人啊。
你给我个理由,让我不追究你的理由。伊沙说。
我没有理由……贝拉哭出了声。
良久,伊沙说,我倒是有个理由,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贝拉立即停止了哭泣,泪眼汪汪地看着伊沙。
一年后,在贝拉的婚礼上,一群年轻人起哄,非让新郎新娘讲讲恋爱经过,贝拉捂着嘴只是笑,而新郎伊沙的脸颊则掠过一丝苦笑,他说:当年我发现,我们的名字合在一起叫伊沙贝拉,这是一句外来语,原文是指上苍的旨意。如此说来,我们的缘分不是天定的吗?当年我把这层意思说给贝拉的时候,她的眼里闪烁出钻石般动人的光彩。
贝拉笑了,眼前却忽地飘过小说家哀怨的眼神,谢谢你的祝福。贝拉在心里说。
小说家
清晨,老曲开着114路公交车驶入卫工街站,一眼就看到了在道边等车的容老太。老曲心头忽地一暗,明媚的阳光和晴空万里带来的好心情不见了,心中暗自嘀咕,谁也不要招惹这个凶神般的容老太啊,否则准会经历一段糟心之旅。容老太不姓容,是老曲给她起的绰号,老曲跟车队同事讲起老太的时候说,像不像容嬷嬷,你们说像不像?
车停稳,老曲打开门。容老太脖子上挂着“盛京通”夕阳红卡,气嘟嘟地上了车。老曲以前曾经问过她,您老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点出来,这是干什么去呀?老曲其实是想说,您老坐车又不花钱,干嘛非得这个点出来跟上班的、上学的抢时间呢?容老太脑子灵光得很,她白了老曲一眼说,我干嘛去需要跟你个公交司机汇报吗?多嘴。老曲被怼得无语了,他十几年开公交的经验告诉他,这是一茬子,少惹为妙。事实果然应验了他的判断,没多久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被老太狂虐了一顿,她站在小姑娘身边,恶语滔滔,把小姑娘都骂蒙了。小姑娘怯生生地说,奶奶,我去上学,要做十五站地,今天身子不舒服才没给您让座,您至于这样骂人吗?小姑娘说着还是起身站到一边,老太甩过巨大的臀部气呼呼地坐下,嘴却没有打住的意思。她拧着眉头凶巴巴地瞪着小姑娘说,告诉你,我从来不会骂人,我骂的都不是人,都有娘养没娘教育的瘪犊子,是不懂尊老敬老的混账!还身子不舒服,我一辈子养了六个孩子,我啥没经历过,少拿那点逼事儿跟我扯。
小姑娘没到站就下车了,她站在道旁一边哭一边等着下一辆车。
车上的人就都觉得老太很过分,一个戴着鸭舌帽黑口罩的男子说:小姑娘不是给你让座了吗,干嘛还不依不饶的?谁家没孩子呀,大早上的给骂一顿还咋上课,真是。谁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老太真是好口才,嗓门大,气脉足,嘴像机关枪一样,荤素不怵张口就来,把一车人骂得鸦雀无声。末了老太太还来了一句,我们家过去是住在中街城里的正黄旗,是吃坐粮的铁杆庄稼,打小就是主子,你们这些包衣人的后代惹得起吗!
大家面面相觑,天呀天呀,这老太怎么这么厉害。
鸭舌帽似乎想站起来和老太理论,被边上人按住肩头,何必和这样的人理论。
老曲出来打圆场,大家都少说一句,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老太不买账,你少在那里装大尾巴狼,你也不是什么好饼,自打我上车你就说三道四。告诉你,就你这种人最不是东西,自古都是在讲的人。老曲苦笑,我还自古在讲,我在什么讲?老太用手点指老曲:
矬子心里三把刀,络腮胡子不可交,最毒不过是斜眼儿,斜眼儿都毒不过水蛇腰。
你说,你在讲不?你占了两样!
老曲一脸络腮胡子,还驼背,可不占两样吗。但这都是用以前的事儿了,老太佛挡杀佛,鬼挡杀鬼的架势,老曲现在哪敢去招惹她。其实谁没有点烦心事呢?老曲此刻就正烦着呢,上车前接到弟弟一个电话,说他丢邮件了,是一把日本武士刀。弟弟沮丧地说,那刀挺贵的,是在郊区那条村道上丢的。弟弟是下岗工人,现在靠送快递生活。现在人可真是让人搞不懂,买武士刀干嘛呢?法治社会,又不让你随便杀人。
汽车驶上卫工桥,被红灯拦住了,老曲突然看见一艘单人划橡皮艇从桥北侧河面上冲过来,皮艇五颜六色,在阳光下很耀眼,上边坐着一个戴着牛仔礼帽的男子,他一边挥手和岸边钓鱼的人打招呼,一边打着很响的呼哨。皮艇“忽”地没入桥下,又“忽”地从桥南钻出来,悠悠地漂向远方。河两岸的榆叶梅开得正好,把河水映得粉莹莹的,老曲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他想,那人是谁呢?他要坐着那条花船去哪里呢。
绿灯亮起,老曲一挂挡又开始前行。那老太还没找到座位,她横着身子往中间走去,眉头拧成了川字,仿佛满世界谁都欠她的。中间有那个戴着黑鸭舌帽黑口罩的男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老太眼尖忙不迭地冲过去,唯恐有人跟她抢座。但那男人又坐下了,他站起来好像只是看了看窗外的站牌。老太站在那里不停地清嗓子弄动静,男人却无动于衷。老曲说:请大家自觉给残疾人、老年人、抱小孩的妇女让下座位啊,学雷锋做好事。
没有人给老太让座,这个时间点坐车的都是老乘客,大家好像都知道这老太平时的倚老卖老,嚣张跋扈,打心眼里不愿给她让座。
老太无名火起,乜斜着眼前的男人开骂:还学雷锋,现在人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一个个打扮得废青似的,道德沦丧,猪狗都不如。狗尚且能看家,猪能过节杀了吃肉,你们能干啥?你就没有老的那一天吗?举头三尺有神明,迟早遭报应。
男人站起身说,您老是在骂我吗?我给你让座就是。说着男人扶着座椅背,挪了出来。老太哼了一声,没好气地坐下了,骂谁谁知道,人最有自知之明,没人平白无故地捡骂。
男人身子歪着,左手按着左腿,右手死死地把住椅背,车开动的时候他险些跌倒。这时大家才发现男人是个跛脚。老太显然也注意到了,她有些尴尬地看着男人说,呀,你是残疾人呀,那你坐吧。
男人摇摇头说,您老坐吧,我不敢坐。
见男人这样说,老太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你是残疾人怎么不说一声。
我跟谁说一声?男人问。
……
您老的意思是让我每次上车的时候都宣布一下,大家好,我是一个瘸子,求大家可怜可怜我给我让个座,是吗?我腿瘸,我的心不瘸,残疾人有残疾人的尊严。
车进站,司机踩了一脚刹车,男人又晃了一下,又险些跌倒。
两旁的人都站起身想给男人让座,男人拒绝了。他说,把残疾人不当残疾人,才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让座是义务行为,自觉自愿,你们给我让座说明你们懂礼貌,我就该知道感恩谢谢你们。你们没让也没有错,可能你们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人人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互相理解关心,那才真的是和谐社会。
不知谁喊了一声好,接着大家就“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车进沈阳站西广场,老太太慌慌张张地起身逃下了车。老曲说她应该到南市场下车呀,怎么提前下去了?大家笑了起来,都什么年月了,还拿满清的封建糟粕说事儿。老曲说,这同志也是好样的,身残志不残。男人听了,就在车过道里来回走了几步,然后又踢踢腿说,我不是残疾人,我是写小说的,见老太不懂事就用虚构的身份和她交流了一下,仅此而已。
老曲觉得很有意思,哈哈,小说家。更有意思的是,后来老曲再也没见到那个容老太,是不是老太有意回避错峰出行了呢?见到熟悉的乘客老曲就说,也不知道那个正黄旗的老太去了哪里?不管咋说也是个老人家。那个小说家倒是常见,还是戴着那顶黑色鸭舌帽和黑色口罩,一个人坐在那里,眼神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