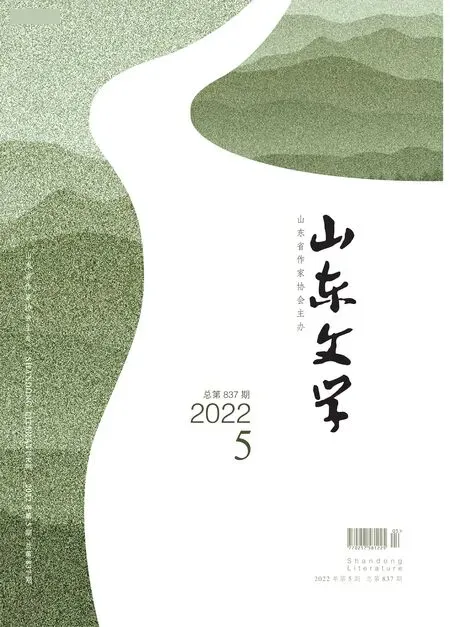那些花儿
刘学刚
木槿,锦上添花
植物之美是自然美,即不事雕琢的天然之美、自由率真的个性之美、安静恬然的纯净之美。多读几遍《诗经》,那些《诗经》里的植物就会开口说话,讲述人与植物的欣喜相逢,讲述青枝绿叶红果对人的容貌和美质的持续塑造。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国风·静女》),红彤管比野生的白茅贵重多了,男主淡淡地说了句彤管有光彩,却对少女心怀虔诚走远路采撷的小草喜爱有加;洵美且异的白茅传达着少女对纯洁爱情的热烈期待。在春秋这样一个植物胜利的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围绕着植物展开,植物的茎株上灿烂着人们如花朵一般幸福的笑容。尤其是《诗经》里的女子,有着鲜明的植物属性。“手如柔荑”,说女子的纤手柔滑白嫩,宛若初生的细长的茅芽。“齿如瓠犀”,牙齿洁白匀整如瓠瓜子儿。植物的美引领塑造着人的美。荑手葱指瓠齿樱唇杏眼柳眉,如许植物之美集于一身,会是怎样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只这两句八字,就描画出了女子的容颜之俏和形体之美。这样的好句子,看一眼,再看一眼,就会让人眼花缭乱,恍若每一根花枝上都生动着一张少女的俏脸,每一张少女的俏脸都弥散着一种醉人的花香。
花是木槿,即《诗经》里的舜华、舜英。好花知时节。读《礼记·月令》,读到“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的句子,满目繁华,恍若置身灯火通明的剧场。中国古代把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是说美的鹿开始脱角;二候蝉始鸣,说的是雄蝉演奏暖场音乐;三候半夏生,犹如小小的焰火,绿色的半夏草挺秀在夏天和大地的中心。仿佛三军列阵,旌旗猎猎,战鼓擂擂,这么盛大的场面,才配得上繁荣、茂盛、荣耀的木槿。夏天像汹涌澎湃的大海,白的、粉的、紫的木槿宛若朵朵浪花,美丽着浩瀚无垠的海面。
遥想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诗经》里的夏天,艳阳灿灿,蜂蝶翩翩,一辆马车一驶入乡村道路,即刻被路两侧的木槿簇拥着。马车像一只行驶在绿色水面的小船,前面是花,后面也是花;左边是花,右边还是花,车上的痴男情女陶醉在木槿花制造的香甜空气里,天长日暖,不知归路。木槿树高五六尺,列植于道侧或菜园四围,供观赏兼作花篱、绿篱,从《诗经》之后的诗词歌赋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村一直保存着这一栽培模式,就像木槿经历霜雪也遭遇斧斫,也没有改变它们的三裂叶和钟形花,勇敢而又固执,坚持着它们最初的笑容。
生活在槿篱边的每一秒钟都是美妙的。农民在菜田果园的四围植一溜木槿,挡鸡挡鸭,它是篱笆,也是鲜花、清露、鸟鸣乃至爱情的生发之所,培植着勤劳、淳朴、温善等诸多的美德。有千年流传的诗词为证。譬如,后唐词人孙光宪在他的《风流子》里这样写道:“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槿花是一种光,孕育于地心深处,沿着灰褐色的茎执拗地升至夏天的枝端,照亮了低低的茅舍,照亮了弯弯的溪水,也照亮了鸡鸣犬吠鹅呱鸭噪男耕女织等熙熙攘攘的生活现场。木槿为篱,芍药为栏,是古文人痴迷的田园仙境,槿篱药栏隐世且独立,是与庸常世俗对抗的古文人的倒影。宋人秦观也描述了槿篱守护的人间仙境:“槿篱护药红遮径,竹笕通泉白遍村。”这个盛夏的乡村用木槿、芍药、竹笕、泉水等材料建造而成,这些材料没有阶级、朝代的杂质,花开花落即为生活的节奏。
木槿的繁殖有播种、压条、扦插、分株几种。培植槿篱多用扦插。春分时节扦插,夏至见花。春分,木槿的树液从根部涌到顶部,但新叶未萌,选取去年新生的枝,截为学生直尺一般长短的小段,下面的切口剪成马蹄形,上切口平切。扦插时先用生铁炉条按株距预插一些小洞,再将槿条轻轻插入,培土压实。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一所乡村中学的甬路旁做着上述的事情。槿条是从学校南边村庄的行道树木槿上剪取的。疏篱夹路的几年里,我依然细心地剪枝、扦插,关心天气和绿叶,做一个育好花的园丁。后来的槿条扦插在槿篱的缝隙中,成活后移植校园的角角落落,或者赠给学生由此进入寻常农家,渗透到学生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朦胧的想象。我是语文教师,兼任学校的通讯员。写宣传稿,须挖掘新闻亮点。一个槿花开放的夏天,我写学校的环境育人,写每一朵鲜花都有自己的语言,并灵光一闪,确立了校树校花。校树是高高的白杨,追求着天空的寂寞。校花呢?是木槿,“槿”“锦”谐音,木槿花开满树,烂漫如锦,开花是锦上添花,结果是锦绣前程。
木槿的花瓣薄如蝉翼,其上密布细细的褶痕,宛若微风吹皱的小池。木槿花色深浅不一,有纯白、粉红、淡紫、紫红等几种。我喜欢粉色的木槿,黄黄的花蕊像一些小小的饭粒,落在红红的花心上,而粉粉的花瓣犹如水花四溅,看久了,眼睛都会蓄满湖水的。我栽培的槿篱是粉红的,像一片片朝霞铺满校园,每一次走在甬路上,都是晨曦初露的好时光。“腋下夹了书本,经过塔松氤氲着的庄重的气息,经过砖铺甬路和两边木槿天真的微笑,在教室门前,我准备着表情准备着可能精彩的开场白。”多年以后,当我回望那段乡下教书的过往,总是把这个场景与鲁中平原某条乡间小路上扛着锄头走向耕地的农民联系起来。我觉得,校园这个幸福的容器盛满我事业的甜蜜和青春的莽撞,我充实而紧凑的生活都围绕着排排木槿展开。
一个木槿花开的七月,我和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在甬路上打羽毛球。粉色的羽毛球像一朵会飞的槿花在空中翔舞。我说翔舞,是因为我尽心尽力地给她喂球,尽可能地把球打得高一些,球速慢一些,打到她乐开花的心坎坎上。一着不慎,羽毛球落花一般,飘落到浓密的木槿树丛里,再也没了踪影。那年冬天,木槿叶纷纷落下,我们惊喜地发现了那个羽毛球,像一朵槿花留恋在枝丫间,固守着一个浪漫夏季的许多粉红的回忆。当然,我们有许多可供击打的羽毛球,就像我们有旺盛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我们这种“羽随心动”的时间多为早晨和傍晚,呼应着木槿朝开暮敛的生命节奏。
木槿朝开夕凋,如朝露易干,也叫时客、朝生、朝颜(朝开暮落、如丰满人面的牵牛也叫朝颜)、朝开暮落花。它的别称“舜华”意即瞬间凋零的芳华。木槿以清晨的花容为最美。清晨,鲜嫩的花瓣儿沾着露水豆儿,如同少女鼓鼓的红红的脸蛋儿挂了几颗晶莹的泪珠,阳光成群结队地往花朵上一围,槿花的脸蛋儿暖暖的痒痒的,看上去十分的娇艳迷人,像极了一句古诗:“林花著雨胭脂湿。”槿花可食。含露的槿花吃在嘴里尤为清爽嫩滑,又面又甜。那甜里有露珠的味道,有空气的味道,也有对面女同事微笑的味道。女同事听了我的描述,搁下球拍,脸蛋儿贴近了一朵木槿,闭了眼睛,细细地嗅,那情那景,真的是“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中午,槿花最为饱满,而花色由浓而淡,像是一件被阳光洗白了的粉色衣衫。近黄昏,水分散去,槿花化身一只毛绒绒的小球,下垂着,仿佛女子衣裙上的配饰。崔道融《槿花》:“槿花不见夕,一日一回新。东风吹桃李,须到明年春。”小绒球凋落了,次日清晨,另一朵槿花倚风含露,笑脸盈盈。宛若一个小喜悦摁下了一个小忧伤,如此暮落朝开,绵延不绝地照耀着我们的视界和心灵,正是宋人杨万里咏叹的“占破半年犹道少,何曾一日不芳来”。
“何曾一日不芳来”,这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它是整体的,宏阔的,不拘泥于一时。“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清阴又得花”,杨万里的这两句诗,也是这样的美学视角,这种美感得益于天地自然的滋养。栽培槿篱是物质生活的需要,而清阴花朵是高于篱障之上的精神享受。有了这种感知和对大自然的绵绵情意,我们才会“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自然的美丽瞬间和人生的精彩段落相与为一,和谐共生。
夹竹桃,像竹又像桃
搬进新房的那一年,我在院子里养了许多的花,有鸡冠花、指甲花、一串红、喇叭花、马齿苋、蒲公英、夹竹桃等等。鸡冠花、指甲花、一串红是向别人讨要的种子。喇叭花、马齿苋、蒲公英是从打的猪草里挑出的有根的野花。唯独夹竹桃,是和锅碗瓢盆一起从旧房搬来的。砌一眼灶,埋下一口锅,屋顶盛开一朵炊烟的花。挖一个坑,移栽一棵花,剩下的事情是扎根结果。
夹竹桃是奶奶扦插成活的。如果你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譬如我的故乡,鲁中平原的一个灰墙土瓦的村庄,你一定目睹了红艳艳的夹竹桃开满长街短巷的盛景。“门前种棵夹竹桃,一家和睦不怕调。”奶奶抱着不满周岁的父亲改嫁到东朱耿,迎接她的是村道两侧的夹竹桃。有一年春天,奶奶剪了几根夹竹桃的枝条,插在一个废旧的脸盆里,盆里盛满松针土和晒干后砸碎的塘泥。盆里的夹竹桃长大以后,她就移栽在老宅的庭院里,而家里一旦又有破损漏水的脸盆,她就踮着小脚忙着剪枝挖土浇水。二叔长大结婚的年龄,父亲搬出老宅,挈妇将雏,独立门户。除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器具,父亲还带走了奶奶盆栽的夹竹桃。我们一家人一开始住的是租赁房,过了两年,有孙姓人家举家去了东北,父亲买下了他的旧房,我们和那盆夹竹桃就住了进去。
留存下来的有关夹竹桃的场景里总有一个佝偻而忙碌的身影。我家的新房和郝姓二叔的新房一墙之隔。两家轮流抚养奶奶,其实是奶奶作出的决定。我们这里五天一个大集,每逢集日,她就轮转到另一个儿子家。用奶奶的话说,逢四排九赶大集,好记;五天一轮,农忙时都能搭把手。
记忆里的夹竹桃开得很大很艳,五个大花瓣向上展开成漏斗状,如桃花一般艳丽,却比桃花大一些,有玫瑰花那么大;树下有几只老母鸡在刨食,爪子朝前急急地刨几下,又伸出尖尖的嘴巴不停地摩擦着刨出的小土坑,看那样子,非把小尖嘴磨成细细的绣花针不可。奶奶踮着小脚忙来忙去,她往猪槽加料,她去草垛抱柴,走起路来像铁镐开采荒地一样,细碎而紧凑。只要家务活一忙完,奶奶就盘腿坐在蒲团上,眼睛微闭,嘴唇翕张着,念佛。奶奶细若蚊蝇、软如棉花的声音在院子里飘来飘去。院子里的夹竹桃开花了。鸡冠花也开花了。指甲花也开花了。我恍惚觉得,是奶奶的念佛声落在草茎,落在花枝,绽放为美丽的花朵。
我家住进新房的第一个秋天,地里洁白的棉花大朵大朵地开着,院墙上晒满了金黄金黄的玉米棒子。玉米从地里运回家,剥皮的时候在玉米底部留两三片柔韧的玉米皮,玉米两两相系,挂在灰黄的墙头上格外金黄夺目,就像铺了一层漂亮气派的鱼鳞瓦。西墙根的一串红像一串串噼啪炸响的爆竹。鸡冠花则如公鸡打鸣一样,把一身的才华和光焰都呈现在接近天空的高度。东墙边的夹竹桃真是独特。首先是它的枝叶。叶深绿,窄披针形,纷披如竹叶。枝条灰绿色,奇妙的是它顶部的嫩枝一长就长出三条小枝,就像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再说它的花。花苞细细尖尖的,有些织布梭的样子,阳光的红线和枝叶的绿线经纬交织,一梭一梭织出一树繁花。更为惊奇的是,夹竹桃的飘落不像桃花梨花杏花那样一瓣一瓣的落下,如碎裂的泪滴;夹竹桃是整朵花落地,瓣瓣生死相依,落地三两天犹饱满红艳,一如新鲜红润的初开时光。
夹竹桃花量大,花期长,从芒种开到霜降。花开的那些时日,奶奶格外忙碌,好像夏耘夏收秋获秋播的枝条疯长,奶奶的烧水做饭洗衣喂鸡都是枝条上密密匝匝的花朵。那些时日,奶奶的唠叨也特别多。夹竹桃的花枝,不要折,有毒;新麦馒头,不要吃第一口,要先请去世的亲人尝尝;湾塘河渠水多,不要去;瓷碗摆供月的月饼鲜果,不洁不行;树上的柿子不要都摘掉,要留几个给鸟儿吃。那时,我有很多很傻很天真的问题。我喜欢和奶奶聊这些问题。让我深深记得的是,奶奶明明知道一些问题的答案,却声情并茂地给我讲了一些有时间、有地点、有氛围、有场景的故事。譬如:我是从哪里来的?奶奶说,大冬天,父亲到洪沟河那里拾干柴,从冷飕飕的桥洞里把我捡来的。奶奶、父亲、母亲去世以后,都埋在了洪沟河南岸的墓地。每次返乡上坟,经过洪沟河大桥的时候,我总是停留一些时间,让冷的风刮跑了热的泪,再去叩拜我的直系血亲。
夹竹桃为什么叫夹竹桃呢?奶奶说,女孩桃爱上了男孩竹,桃家人极力反对,二人殉情自杀,葬在一起,他们的墓地上长出了一种长叶似竹、花色如桃的植物,人们都叫它夹竹桃。
诚然,奶奶给我的答案并非现实的真实,却真实地在我的心中生枝发叶,搭建宽广的树冠。许多年以来,我在现实的困顿里左冲右突,在虚构的世界中驰骋纵横。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很傻很天真的小男孩,小男孩旁边是坐在蒲团上轻声念佛的奶奶,院子里的夹竹桃开得正欢,犹如灶膛里的干柴噼噼啪啪地燃烧,又像许多雀鸟挤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喊叫。
继续说说夹竹桃的名字吧。读归有光《房东夹竹桃花》:“奇卉来异境,粲粲敷红英。芳姿受命独,奚假桃竹名。”红英灿烂,长叶婆娑,那么美的奇花异卉,有着那么绵长的花期,“奚假桃竹名”,何必借助主流花木的光芒呢?这名字和奶奶的名讳郝赵氏有一些相似。丈夫英年早逝,幼子嗷嗷待哺,奶奶无奈地将自己残损的青春嫁接在郝姓人家的枝条上,又为郝家热血沸腾地生养了两男两女(一男夭折),奶奶的名字也叫了郝赵氏。
奶奶这一代的农村女人,大都有姓无名(乳名是有的),出嫁了改随夫姓,已婚妇女有两个姓氏。娘家长辈也不再称呼已婚妇女的乳名,而以夫家的村庄称之,似乎一个女子背负着一个村庄的宗族、风俗、仪式、香火、三餐、四季、五谷、六畜等等。
“昔来此花前,时闻步履声。今日花自好,兹人已远行。”归有光的诗中站着一个人,恍惚中觉得,那是我的奶奶。因为亲人的在场,一草一木都有着宽厚的情意,绵延不绝地容纳滋养着我们的心灵。
雪松有花
雪松,也叫香柏、塔松,常绿乔木。雪松的叶绿色,细若银针,大枝一针一束,散生;小枝顶端多针一束,簇生。大枝小枝叶繁密,且针叶上覆有一层淡淡的白粉,远望如白雪覆盖,遂叫雪松。
雪花落在雪松上,也有美丽的形状。雪松伸出一千只针叶的手,采撷雪花。针叶太细小了,兜不住多少雪花的。针叶基部挽留了一些雪花,雪花攒聚成小的雪球,像一群小白兔,呆头呆脑的。灰色的松枝挂了一些雪,就成为琼枝。唐人有诗曰:“虎溪闲月引相过,带雪松枝挂薜萝。”这松枝长在庐山东林寺的树上。如今,庐山雪松众多,唐人所见是否雪松不得而知。我更愿意把这庐山松看作万物的共生之地。雪花在其上敛起翅膀。如长臂猿一般的薜荔在树上开花,恋爱,养育着许多圆头圆脑的小宝宝。女萝灰绿色的披纱自上而下地垂着,轻柔而又飘逸。
观看雪松,当然是落雪的冬日。松青雪白犹如相互成全的雪菜冬笋,清鲜至极。宋代诗僧释正觉称雪松为“岁寒之容”。不识雪松,怎么会懂得冬天。古今有异的是,古人观看雪松,多去深山古刹;如今多站成闹市的景观树。古代的雪松在千百年的风雪和文人的动情描述中获得了清新清奇的面目。今天的雪松依旧是千年以前的样子,尖塔形,大枝沉稳地平展,小枝谦逊地稍稍下垂;针叶细而尖,从未弯曲,也从未改变自己的颜色。它就站在我们日日走过的路边,但很少有人停下匆匆脚步,细细端详雪松的模样。雪压青松挺且直,雪松在当下的形象被定格了,人们异口同声地喜欢“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泰山顶上的青松是雪松。他们说着泰山、雪松的时候,觉得呼吸顺畅,豪气上涌,仿佛就站在山巅,高出了熟悉的生活和人群。
我跟在风雪后面,观看了几次雪落雪松的场景。寒风到处乱跑,犹如一群不知疲倦的狗,叼走落叶,撕扯树枝,用刺耳的声音宣扬它们缺少花香缺少绿色的胜利。雪是温柔而美丽的,就像一个走亲戚的外省女孩,对看见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站得最高的雪松率先得到了它的青睐。它用清甜的气息拨开细密的针叶,温情地爱抚着面容苍老的枝条。就是下小雪吧。雪慢慢地下,针叶密密地缝,把雪松装扮成美丽的圣诞树。大雪也惬意。细的针叶承载不了几片雪的。树枝和簇生叶的基部雪多一些,积聚得多了,就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再也憋不住了,针叶微微颤抖,枝条稍稍弯曲,积雪就从树上滑落下来,弯曲的枝条又弹回平展的姿势。如此轻巧地弯了又弹,弹了又弯,大雪无法压树顶,哪怕天地之间风雪弥漫。
可是,很多书写者看不见这些。他们认为大雪覆盖宁折不弯的雪松才叫雪松,这样的雪松才让他们联想到宝塔、哨兵、巨人等形象。你若对他们说,红松黑松油松雪松的枝叶都会极力抖落积雪,他们就嘲讽你躲避困难。你若说雪松也开花结果,而且曲折离奇,他们觉得你在编故事,对你不屑一顾。
雪松也开花,开在百花后。有一年立冬,落叶别树的时节,我特意去看了针叶茂盛的雪松。那种优雅的树形很有仪式感,苍翠的针叶像是庆祝立冬节燃放的一束束礼花。我用相机镜头拉近高处的枝叶,突然,一些淡绿色的像蚕宝宝一样的东西闯进了我的视野。它们是雪松的雄花。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见雄花表层密布着许多绿色的小孢子叶,孢子叶聚生成,植物学把这描述为“孢子叶球”或“球花”。这种球花常常给人造成松果的错觉。其实,过了一些日子,这些手指状的球花会有奇妙的变化,它们弹奏着松枝的大弦,针叶的小弦,把雪松弹得郁郁苍苍,它们却慢慢变黄,像成熟的豆荚那样开裂,露出金黄的花粉。
雪松之国黎巴嫩,先知诞生之地。“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圣经》里反复述说的“黎巴嫩的香柏树”就是雪松,如今已是黎巴嫩的国花。黎巴嫩群山之上,雪松的生长姿势就是一种华美的绽放。相比树形,雪松的花儿极为质朴内敛,亦能诠释黎巴嫩人推崇的纯洁和永生。也许有的人并不认可雪松的花,花儿应有牡丹、玫瑰、菊花那样艳丽的花瓣,或者喷发丁香、茉莉、桂花那般浓郁的香气。如果以花色和花香来取舍花朵,世界将变得多么单调乏味。如果一种植物的花儿无法凭借颜色和香气吸引昆虫传粉,而它的家族旺盛千年,这样的繁衍壮大太惊心动魄了。
看见雪松雄花的次年秋天,一个废弃的工厂大院,我遇见了机缘向我展示的松果,《圣经》里佳美的果子。松果圆鼓鼓的,样子很像鹅蛋,个头也和鹅蛋差不多大。那些宛若神迹一样的绿色松果,在枝叶的烘托下,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沉静安然,如同镶嵌在天幕上的星星。
如同许多植物自花而果的路径一样,雪松的果是由雌花发育而成的。雌花绿色,也是卵圆形,开在树冠,个头却和玉米粒一般小。若是单纯地描述雪松花果的模样,显然漠视了雪松花的坚韧和执着,以及触手可及的幸福却擦肩而过的悲哀、悲哀中依然敞着心门的天真姿态。从初冬到来年秋天,一个玉米粒长成大鹅蛋未必称奇,但它的授粉有着无法想象的艰难。我们见到的雪松多是雌雄异株,即使偶有雌雄同株者,雌花犹如高傲的女皇姗姗来迟,比雄花晚开十天左右的时间,且高居短枝顶端,不接受低声下气的雄花的亲吻。更为离奇的是,雄株生长二十年以后才能开花;而它所思慕的雌株还有十年的光阴,才有高贵而自然的冲动。
诚然,枝条扦插可繁殖,但无法抹煞雪松貌似丑陋的花儿为追求优美之树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强大而有耐心的雄花,以一千朵花一万次的花粉飞舞,才可能在风的鼓动下,完成一次和雌花的幸福的拥吻。更多的时候,雄花凋落,雌花枯萎,而雪松依旧努力地生新枝,发绿叶,凌寒不凋其色,用它的大枝小枝讲述着昔日生机勃勃的原野,用针叶的清晰线条描画着内心的一次次颤动。
指甲花儿开
指甲花,凤仙花科草本植物,有单瓣者,有重瓣者。花色有粉红、大红、紫色、粉紫等多种。将捣烂的花瓣和叶子敷在指甲上,指甲色若胭脂,妖娆而妩媚,恍若指端开花,所以是指甲花。朱耿村的女孩儿也叫它女儿花。女孩儿指端的灿烂和内心的丰盈是同步绽放的。指甲花美丽了女孩们的青春芳华。
指甲花八月始花。绒花半遮粉面在高处羞答答地开了,荷花高擎粉碗在浅池娇滴滴地开了,终于迎来指甲花开。八月立秋,时近七夕,多有文人将立秋与七夕同吟共咏。谢迁《七夕立秋》:“七夕人间值立秋,斗杓回指火西流。乍闻细雨随风至,顿觉炎埃匝地浮。”秦观《渔家傲》:“七夕湖头闲眺望。风烟做出秋模样。”秋模样应该是这样一段美丽时光:一个穿碎花蓝裙的女子,坐在午后庭院的沉静里,低头绣着一朵有枝有叶的五瓣花,一针一线叶舒花开,夏尽秋来。
指甲花就是这样的。它像乡间的清丽女子,在篱边,在河畔,在林缘,生肉质的茎,茎上长狭长瘦削的披针形的叶,叶腋开两三朵清秀的花。指甲花不大,和豌豆花差不多大小,姿态也相似,很像翩然欲飞的蝴蝶。单朵指甲花的花期七天,一株指甲花的花季三个月。
如同足够用力的青春,在短短七天光阴里,指甲花的花瓣里涌动着白、紫、红三种颜色,而且花瓣多有不同,个性独具。初开时,洁白的花朵盛着一些艳丽的紫。那些紫柔柔的,亮亮的,在花花叶叶的烘托下,就像是少女忧郁而清纯的眼神,让人看了,心尖儿像触电似的麻酥酥地发颤。看着看着,花心里的紫竟然动了起来。这么一说,指甲花更像少女了,芳心颤动,满面飞红。每一朵指甲花都红得娇媚,红得像太阳一样从容自信。
再说花瓣的形状。朱耿村有三瓣的鸢尾、四瓣的连翘、五瓣的桃花、六瓣的萱草。或长圆形,或倒卵形,或轮状排列,或辐射状生长,一朵花的几个花瓣都是一样的容颜,犹如一群在田野里弯腰劳动的女子,那些荆钗布裙的背影宛如一棵树上的许多花瓣,绽放在禾苗的顶端。指甲花偏偏不一样。约略一看,它似有三个花瓣。其实不然,它五个花瓣分了三组。前面的一片花瓣,圆形兜状,叫旗瓣,离生,顶端有小小的花尖。另外四个花瓣两两合生,分列在旗瓣的两翼,称为翼瓣,翼瓣具短短的花柄。单个花瓣看并不出奇,离瓣合瓣组合起来,就有了气场,一朵一朵开得美丽而别致,花形很像展翅欲飞的小鸟,更有人说它像有百鸟之王称号的凤凰,旗瓣是华美的凤头,翼瓣是一对张开的翅膀。更为奇妙的是,有一枚萼片长得像漏斗,和花瓣同色,尖端发绿,后面有一个细细弯弯的长尾巴,植物学上称此萼片为唇瓣,心物相融的古人视为凤凰的身体和尾巴,凤仙花、金凤花由此得名。吴仁璧《凤仙花》:“香红嫩绿正开时,冷蝶饥蜂两不知。此际最宜何处看,朝阳初上碧梧枝。”仿佛面朝大海看春暖花开,赏花人由香红嫩绿而金凤碧梧,由一朵小花看见一场蓬勃生命的盛大狂欢,这是多么开阔的赏花路径,铺展着生命的波澜壮阔。
由萼片华丽转身的唇瓣不是花瓣,触之有叶片的肥厚感。旗瓣翼瓣柔软而轻薄,半透明,有着丝绸的光泽和柔滑;花瓣里含有天然的红棕色素,可以染发,染指甲,深得女孩子的喜爱。七月凤仙七月凉,织女鹊桥会牛郎。农历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七巧节、双七节。指甲花也叫女儿花。银针挑彩线,妙指绣华裳。七夕是少女乞巧、赛巧的重大节日。女儿花是为女儿节而绽放的花朵。女孩子七夕乞巧,必要染甲,以示敬重与虔诚。采摘指甲花是女孩子一年一度的大事。
在女孩们看来,巧真是个好东西。巧都多好呢?种地煮饭穿针引线都离不开这个巧,好女人都叫了巧姑姑巧媳妇巧婆婆。这么一说,巧就像天上的阳光或地上的河流一样不可或缺。巧有很多,巧多不压身,所有美丽的巧、奇妙的巧都将落在女孩一双会说话的手上。七夕前夕,那一双双手从粗糙的农事和琐碎的家务中抽出来,怀揣着心跳和期许,采七八朵立秋时节红艳艳的指甲花,再摘两三片绿嫩嫩的叶。指甲花的叶也好看,细长如桃叶,边缘有细细的锯齿,像是许多天真奇妙的小念头。宽宽的桑叶也要采两片的,扁豆叶、绿豆叶、南瓜叶也可。
指甲花染甲颇费工夫,需要细心的折腾和温柔的把控。染甲者心细手巧,这样才会得到巧的青睐。花柄水分多,花色素少,摘除;叶洗净,一并放入瓷碗里,加少许白矾(用食盐替代也可),用擀面杖的圆头儿轻轻地捣成泥糊状。这糊状物就是《红楼梦》里晴雯所涂的蔻丹,她临终前绞下三寸许的葱管般染了红蔻丹的指甲,交予宝玉,芳香消玉殒。白矾或食盐稍稍一多,会夺了花的红,变成黑乎乎的一坨。擀面杖不可抬得过高,太高了,会把天戳一个窟窿的,捣的时候用猛力,指甲花会很疼的,它一疼,就会紧闭心扉,不肯吐露内心的秘密。有聪慧的女孩加少许香灰、烟末,淋几滴香醋,捣出的花泥稠糊状,甜甜的浓香味儿尤为突出。香醋可消炎,又如油漆一般固定花色,使指甲上的花瓣持续红艳,穿越青春,盛开在暮年的回忆里。染甲之前,须先拿剪刀,稍稍刮一刮指甲表面(如今用指甲锉),再用碱性香皂洗净手指,然后用镊子夹取一点花泥,堆在指甲上,五指裹以桑叶,用细细的棉线缠上几圈。整个过程十分的专注和郑重,让人觉得:青春这场盛大的花季须从手指开始,而这样一双红若胭脂润如玉的巧手碰了丝线,丝线翻飞如花;抚了器物,器物光洁似镜;触了男人,男人心柔若水。
清人袁景澜在他的《吴郡岁华纪丽》记录了女孩子染红指甲的美丽场景:“夜听金盆捣凤仙,纤纤指甲染红鲜。投针巧验鸳鸯水,绣阁秋风又一年。”十朵近圆形的花瓣在女孩的十指上盛开着,那种鲜嫩嫩晶亮亮的红,明媚又妖娆,衬托着女孩嫩如荑、尖如笋的手。这样的指甲真是太好看了,有诗人比喻为相思豆,尤能撩拨观者的春心:“银甲暂教除,染上春纤,一夜深红透。绛点轻濡笼翠袖,数颗相思豆。”这样的一双手要做什么事情?投针巧验鸳鸯水。取井水河水各一瓢,或白天和夜晚的水,倒入一盆,称之鸳鸯水,搁在庭院里晒上一夜一天(七夕白天),水面就会依稀生出一些薄膜状物质。如果浮在水面的缝衣针在盆底的倒影是弯曲的,或者一头粗一头细,只要不是笔直的一条,则得巧,昭示着此女子头脑灵活、双手灵巧,有一套织丝缕为锦绣的软功夫。
于是,在葡萄架下秋虫窸窸窣窣的鸣叫中,在凉如水的夜色的覆盖下,在流萤飞舞、葫芦满枝的庭院里,染了红指甲的女孩手持银针,小心翼翼地走近水盆,虔诚满满地投下乞巧针。七夕节就在女孩们轻掩朱唇、抿嘴而笑的惊喜中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