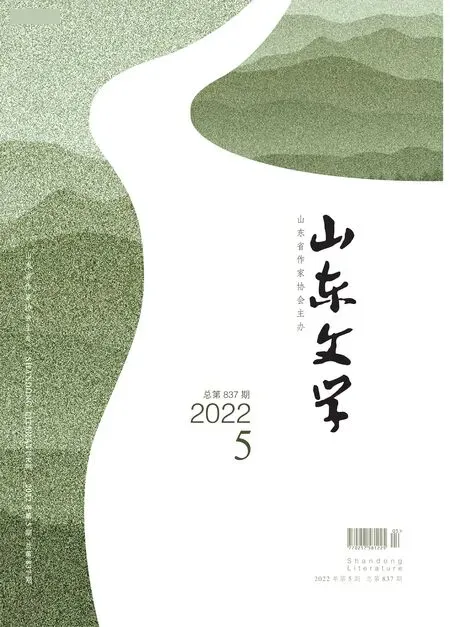父亲的夏天
——高密河村往事之五
李 蕾
1998年,我19岁,考上了大学。这一年的夏天,我和父亲到青岛卖西瓜。
西瓜,是父亲的责任田里种植和收获的。父亲种植的西瓜,生着浅绿色的皮,还带着深绿色的条纹。那些西瓜圆鼓鼓的,非常瓷实。父亲种植的西瓜,是我平生吃过的西瓜里最甜的,在我的眼中,父亲种的西瓜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他把自己用心培育的甜美的西瓜,千里迢迢地去卖给挑剔的城里人,换取我们姐弟三人读书的学费。
那时的青岛人爱吃西瓜,每天早晨一辆一辆满载着西瓜的三轮车、四轮车排着队地进入青岛,一车西瓜一天就卖完了。我觉得青岛是山东省最现代的一个城市,那里的男人长得高高的,吸收了山海的精华;那里的女人,得体的裙装露出的腿是白皙的,那是大海的水汽和海味滋养的。我的父亲,他和无数的农民一起,在2000年前后,往来于农村和城市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他们把自己土地里培育出的珍品卖给了城里人,城里人则把自己挣取的工资等收入等价地给了他们,让他们去培育儿女读大学。他们的儿女读了大学,成为了城里人,也建设城市去了。城市越来越繁荣,而农村却越来越凋敝,这恐怕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我跟父亲学会了,怎么挑拣和辨识熟得刚刚好的西瓜。父亲拿食指和中指,去敲一敲西瓜身,熟了的,噗通噗通的。如果熟大了,就是噗齐噗齐的。如果不熟,则是钢钢的。还可以看西瓜连着绿色瓜蔓处的蒂部,窝窝深的是熟的,窝窝浅的是生的。
父亲的三轮车只有一个座位,他又在旁边装上了一个铁架座,用电焊滋啦滋啦烧上的。我就坐在这个铁座上。
凌晨三点,我和父亲就从家里出发了。得赶在天亮前,到达那里,好把西瓜卖给早起的青岛人。父亲的三轮车沿着河村的中央大道就出了村子。一路上,小路时有颠簸。路旁的树影,如黑黑的鬼影般扑来又后退。父亲开着微弱的车灯。为了省电,只有听到前面有车也在行驶时,他才把车灯扭亮。凌晨五点,父亲让我给他捶背,他怕自己打瞌睡出事。河村到青岛,有200里路。父亲卟噔卟噔地开着他的三轮车,穿越夜色,三个小时就到了青岛。先到达市北区,再到了市南区。市北区和市南区是青岛的两个老城区。父亲在市南区的榉林山公园附近停车卖西瓜。
我和父亲在外,父亲对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近。在家里时,父亲是冷漠的,甚至是粗暴的。我和父亲在青岛卖西瓜,父亲怕我口渴,挑拣出一个最好的西瓜,让我用水果刀切开吃。中午,父亲让我去买了一袋炉包,让我一个人吃。他说他不饿,不想吃。我们父女在青岛的街头,父亲想着的只是:如何把这一大车西瓜卖出去,我们好早一点回家。
到了中午,来买西瓜的人就很少了。我们卖西瓜的不远处,就是青岛植物园。父亲怕我闷,给我钱,让我进去转转。那次逛植物园的新奇感,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看到鲁迅写的中国公园模式,我就想起我在青岛逛公园的记忆。父亲让我管收钱,卖西瓜所得的所有钱都在我随身背着的一个小包里。中山公园旁边,有一个报刊亭。我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买了一本杂志。偷了父亲十元钱这件事,我不敢告诉父亲。
到了下午一点钟,午睡完的人们又出来买西瓜消夏了。我们的西瓜好吃,又比水果摊上的便宜很多,来买的人很多。父亲用手掂掂,选出一个西瓜,用水果刀抠出一块三角形或者一切两半,摆在西瓜堆上作为展示,供买者参考。每一个西瓜都是好的,每一个西瓜都是甜的,红红的瓜瓤引诱着路人。买者在选购前,可以用水果刀切下一块,进行品尝。有时候找不到水果刀了,父亲就用拳头砸开一个西瓜,一分两半,一半放在瓜堆上展示,一半分给围拢来的人们吃。沙瓤的或者水红瓤的西瓜,掰一块都是甜的,汤汁流到人们的下巴上,甜腻腻的,人们用手指一揩就甩到了地上。
热辣辣的太阳,直射在父亲的黝黑发亮、健壮的赤裸的脊背上。父亲穿着一件绿色带黄条纹的背心,但是因为天热,他撸了上去,用背心擦脸上的汗,父亲的脸上因此有了一道道黑色的尘土混合着汗水的印。父亲同样黝黑发亮的粗大脚板,踩在城市滚烫、粗砺的石子路上。一个热心的老大妈,笑着对父亲说:“穿上鞋吧。”父亲黑黑的脸膛,憨憨而又大咧咧地笑着,“庄户人,没事。”父亲扛上一大编织袋西瓜就给买瓜人送去了。父亲一米七四的个子,身板健壮,也被压得弯下腰。好心的买瓜人要给父亲扶着,以减轻他的压力,父亲照样满不在乎地说:“没事。这点重量不算什么。”
我们在青岛卖西瓜,人们待我们是友善的。那时候,城里人的生活节奏没现在这么快,他们是从容的。每次,城里人跟父亲讲价,或者要求抹去零头,父亲总是痛快地说:“行。”父亲的眼神,总是看着远方。
有一次,父亲忙不开,让我去给买者送西瓜。大概有五六个西瓜,放在一个编织袋里,我背着。我行走在买者的楼梯里。那时候的青岛人,每次买西瓜,都买好几个。2002年我来到北京读研究生,留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发现北京人买西瓜,每次都买一个甚至半个。那时候,父亲这么友善地给买者提供服务,是想着:吸引他们成为回头客,下次继续买我们的西瓜。也或许因为,父亲就是善良。也或许,父亲认为,自己出一把子力气不算一回事。也或许因为,在城里人面前,父亲就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认为城里人就是尊贵的——你看,他们穿得多么体面多么门面,别让西瓜弄脏他们的衣服。城里人回报父亲的,也是友善。父亲从来没有跟任何买者发生过冲突。在我的记忆里,气氛都是柔和的,柔和得淡于无。父亲顶天立地,买者从从容容。
我进入买者的房屋。我想上厕所,买者友善地让我进入她家的卫生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城里人的卫生间,是白瓷的马桶。
父亲常去的几个小区,几个老大妈就跟他熟了。她们问我的情况。父亲不无满意地看着我说,“刚考上大学。”父亲说,我还有弟弟和妹妹,也在读书,学习也都挺好的。说这些话时,父亲的眉宇间不无欣慰和自豪。她们就都很感叹地说,那真是不容易,城里上班的哪里供得起三个孩子上学。离开卖西瓜的居民小区旁时,父亲会把地上的瓜叶、瓜皮等垃圾收拾一下,卷卷扔到垃圾桶里或者扔到三轮车的车厢里。
我的父母,用家里的15亩地,凭他们的辛勤劳动,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了中国最好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这是他们平生最骄傲和欣慰的事情。二妹君华从小被父母送给了邻村的人收养,父母不是因为家贫养不起或者放弃养育的责任,而是因为父亲想生儿子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父亲被迫把自己的二女儿送出去了。如果二妹是在家里长大的,父亲也是会这样供她读书的。
我和父亲这次在青岛卖西瓜,到了晚上,西瓜还剩下小半。父亲就把三轮车停靠在偏僻的路边,怕城管来干涉。有时候城管来抓卖西瓜的乡下人,没收他们的秤。卖西瓜的车主看到城管来了,就赶紧开着车逃跑,到处躲藏。停顿好,父亲让我睡在车篷里。父亲在车旁来来回回地走,偶尔能碰上夜行的人捎两个西瓜。
那个夏天,我就这样,跟着父亲到青岛卖了两三次西瓜。卖完西瓜回到家里时,我把钱都交给父亲,父亲数数里面的钱,嘀咕“不对呀”。他发现少了十块钱,我在心里想。一车西瓜有多少,能卖多少钱,他都是有数的,不过他能估得那么准确,我还是蛮吃惊的。父亲是数着手指头,算着,他挣多少钱才能给我们姐弟把学费挣出来,同时也说明,他是有经济头脑的。二十多年后,我小心翼翼、言辞躲闪地笑着在电话里告诉了父亲:当年,我拿了十块钱,买了本杂志。父亲呵呵地笑。这时的父亲,67岁了。
那年夏天,父亲除了带我去青岛卖西瓜,还带我的大妹去过。那时大妹17岁,正读着中专二年级。大妹是1997年考上中专的。那所中专叫山东银行学校,由高密一中代管。大妹入学时,父亲交给了高密一中1.1万元。其中,1万元是代管费,另外1千元是学杂费等。父亲感觉心在滴血。
那时的钱,太金贵了。1997年9月,父亲共拿出两万多元,给我、我的大妹、我的弟弟交学费。那年我读高三,父亲给我拿了学费等四千多元。那时,弟弟刚开始读初中一年级。大妹的中专,读了三年。从第二年9月开学开始,每年要交给高密一中3000元。
除了卖自家种的西瓜,父亲还到村里以及邻村种西瓜的农家去批发。父亲去一趟青岛卖西瓜,可以净赚300元。因此,3000元的学费,父亲需要跑十趟。那时候,父亲卖一车西瓜,成本是300元,收入600元,净赚300元。批发价是一斤9分钱或1角1分钱,父亲在青岛可卖每斤2角5分钱。卖到最后,卖不完的、被挑拣剩下的西瓜,就1元1个出售。因此,父亲的一车西瓜,大约是3000斤。这是按照大妹的说法,算出来的。但是父亲说批发价是每斤7至8分钱,售价每斤不到2角钱,一车西瓜拉2000斤,去一趟青岛净赚200元。我想父亲的说法应该更准确,也就是说,要凑足3000元钱,父亲要跑青岛十几趟。
那一次,父亲和大妹在青岛卖完了西瓜,已经到了傍晚。父亲开着三轮车,大妹坐在铁座上。晚上八九点钟时,父亲和妹妹到了蓝村,还没有到高密界,距离河村尚有70多里路。父亲开到了火车的铁轨处,有火车要过,父亲就停了下来。父亲去附近办点事。大妹坐在旁边等着他。这时,过来两个社会青年,问大妹,是哪里人。大妹毫无戒心地回答:高密人。大妹的衣兜里揣着700多元钱,这是这一趟的收入。父亲的三轮车车厢里,还放着一个席梦思床垫子,那是父亲从青岛捡的。两个社会青年一下明白了,父亲和大妹是做生意的。两个社会青年,是干抢劫勾当的,用高密方言就是“攥道的”,即在道路上拦劫的。
父亲马上回来了,开动了三轮车。这两个社会青年骑着摩托车,在父亲的三轮车后紧追。一个青年开着三轮车,另一个青年坐在车后座上。这两个社会青年是亡命之徒,父亲把油门踩到底。父亲想,这两个小混混如果追上他,他就可能被打死。摩托车紧追不舍,父亲的三轮车蹭到了摩托车。天太黑了,父亲什么也看不见,车后座的混混可能被撞到了路边的沟里了。开摩托车的小混混,拿出一把铁锤,就砸碎了父亲这侧的三轮车的窗户玻璃。玻璃碎片和碎渣,一下溅入三轮车车内,落到父亲的车座上,父亲的大腿上被扎得鲜血淋淋,一块长玻璃片把父亲的大腿划开了一道血口子。父亲看到,后面来了一辆警车。估计是警察看到了这起事故,想来处理。但是父亲不敢叫警察,一来父亲没有跟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和意识,二来父亲不敢停车唯恐自己被身后的小混混继续伤害。父亲踩着油门,继续往前开。父亲开进了一个村子,把三轮车停了下来,躲入了一个胡同的夹道里藏身。父亲和大妹听得见,两个歹徒开着汽车,绕着村找,在村里的大街上找。至于两个歹徒是如何弄到汽车的,这是父亲和大妹所不知道的。大妹想打110报警,父亲不同意。
17岁的大妹大胆得很,留父亲在原地,她一个人往北走,走了很远的路,看到一户人家亮着灯,她就敲门。门内人问她什么事,她说想报警。门内人不敢给她开门,她又一个人走回父亲的车旁。夜晚十二点了,月亮皎洁,照彻村庄。父亲大腿上的血凝结了,他已经忘记了疼痛。父亲和大妹就这样在那条胡同的夹道里蹲了一夜,父亲吓得要命。
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和大妹才走到远处的另一户人家,敲开了门。这是一户善良的人家,一看父亲大腿上的血,就明白发生了情况。这一家人赶紧招呼父亲和大妹进屋,并且说“别吓着孩子”。他们担心吓着大妹,但是大妹是镇静的,临危不乱。男主人去抱了一些玉米秸,把父亲的三轮车给掩盖了起来,防止被那两个歹徒看到。女主人招呼父亲和大妹到炕上暖和,还给父亲和大妹盖上被子,拿出刚热好的包子给父亲和大妹吃。这时已经是凌晨七点了。那时,整个河村只有村支书——我的大姑父陈振云家有座机。父亲用这户人家的电话给大姑父打了电话,简单说了一下情况,报了平安。
那两个歹徒寻了一夜,也没寻到父亲和大妹的动静。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护送着父亲和大妹出了村庄,上了公路。父亲和大妹开着三轮车,回到了河村。大妹回家睡觉去了。父亲开着三轮车到了镇上,去找在诊所上班的二姑。二姑一看,父亲的大腿上正淌着血,扎进去了许多碎的玻璃碴子。而且,父亲的大腿上,还有一道长口子,二姑以为父亲被人扎了一刀。二姑赶紧,给父亲清理腿上的玻璃碴子,用线给父亲缝伤口。
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敢到青岛卖西瓜了。他担心的是,如果他经过蓝村,被这两个社会青年发现,他就会有生命危险。那户善良的人家,父亲后来没有去报答,多年以后父亲依然深以为憾。
研究生刚毕业的那几年,我在北京每次看到路边赶着骡子、拉着一大车水果在卖的乡下人,我都会想起和父亲一起去青岛卖西瓜的那个夏天,就会体会到他们的辛苦,并送去一道深深的理解和祝他们好运的目光。
后来,城市的街头已经见不到乡下人卖水果的大车了。农民进城卖水果和蔬菜,需要集中进入一个市场摆摊位,市民购买没有那么方便了,瓜农和菜农的销售没有那么容易和赚钱了。我经常会想到,那土地上的农民靠什么收入,来供养他们的儿女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