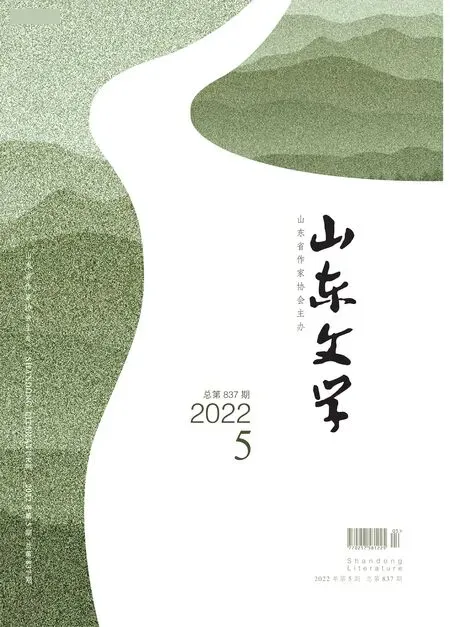河 床
鲍丰彩
你能想象这样的情景否?几个老太太在一起闲聊,聊起她们相互熟识的一位老人,说在某天下午,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起身伸手拿遥控器的瞬间,一头栽倒,再也没醒来。老太太们纷纷感叹,哎,人家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走得这么麻利,好命,真是好命呦。
我就生活在这样一群老太太之间。
我们在西街小区的一个胡同里。这是一个全是二层楼的农民自建房小区,位置极好,周围有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有大型商场和商业街。小区南面是一片十层楼高的住宅区,北面的住宅区也已经破土动工。要不了多久,我们这个西街小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城中村。
据老人说,这方土地,往下挖两米,就会挖出细腻洁白的河沙。老人们因此推断,许多年前,沭河的河床曾经覆盖整个县城,横跨东西,纵贯南北。岁月赓续,泥沙淤积,人们围河造田,在日渐枯萎的河床上婚丧嫁娶,繁衍生息,沭河才逐年东退。
六年前,我从杭州回到家乡小城,一眼就看中了这里,它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两层楼的身高让它与世隔绝,像这个亟待膨胀的城市中明哲保身的盆地。盆地中,门户之间不是上下关系,而是左右关系,最大限度地模拟了农村老家的地缘情感。我跟老公一拍即合,东拼西凑买下了这里的94号。
卖给我们房子的这户人家,儿子刚刚部队转业回来,自己谈了个对象。这个房子就是父母准备给儿子留作婚房的。儿媳妇被前呼后拥着转了一圈,临走的时候撇起嘴来。对硬币的反面进行了毫无余地地拒绝后,硬币的正面便堂而皇之地被提上了议程。就这样,机缘巧合地,我们两家进行了彼此称意的等价交换。
从村子里出去的年轻人,一旦见识过了外面的灯红酒绿,就不能再说服自己折返了。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守着老巢。当然,这里的老巢,是烫了金字的。在这座县城,提起西街村,简单的几个字凝聚着几十年的辉煌历程。最早的百货大楼,后来的人民商场、步行街,都是村子里的集体财产。村子里的每个人、每户门庭,每一年,都能领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分红收益。作为最早进行村集体经济产业改革创新的模范村,“西街村”这三个字,频繁地在我们当地的公共媒体上抛头露面。
按照我们鲁东南乡下的习俗,我得管左邻右舍上了点儿年纪的老太太叫作大娘。这个略显亲密的称呼中有了一个“娘”字,足显出鲁东南女人们在宗族亲缘中的重要地位。她们的老伴呢,转悠着在外面练太极、下棋、遛鸟,外面才是他们的天地。老了的男人也还是男人,也还得变着花样地征讨属于他的那片战场。就像老了的女人也还是女人,还是得守着自己的这个家这个院子这口锅这点小日子。
她们的一天是从凌晨5点左右开始的。夏季天亮得早,她们约在4点40分起床。秋冬季节,起床时间会推迟20分钟。在大部分人的一天开始之前,她们已经披着朝露晨光来回两趟。她们先在门口碰面,结伴去护城河走一圈。她们走得极慢,都是大半辈子的老邻居,各自熟悉彼此的步子,相互之间协调一致。已经到了不再跟时间讨价还价的年纪,她们并不赶时间。散步回来后,她们再各自骑上三轮车,去城南的蔬菜批发市场。这种人力三轮车,三个轮子撵出来的路程,都是靠左脚右脚交替发力蹬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劲。不论春夏秋冬她们都蹬得大汗淋漓,然后再大汗淋漓载回一日三餐。她们买得并不多,一捆韭菜,几根葱,几个土豆。93号大娘喂了几只鸡,隔三差五还要再捡回一车碎菜叶。
几乎每隔一周左右,她们都会不定时地上门来,带着自己的老年款手机。“小鲍,帮我看看,今天早晨闹钟没响啊?”“小鲍,手机声音太小了,帮我再调大一点。”“小鲍,你看看时间怎么不准了?”这样的老年机,声音特别大,也经常死机,然后我需要给它们重新设置或者重启。那些来电铃声带着久远的年代气息,《北京的金山上》《九九艳阳天》《驼铃》《常回家看看》……这些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又无一例外的高亢,响亮。我在厨房炒菜的时候,外面唱“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我在阳台上写教案,外面响起男女对唱“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哥哥惦记着呀小英莲;风向不定那个车难转,决心没有下呀怎么开言”……这声音被她们不失时机地摁断,然后她们对着话筒喊,嗓音的大小取决于电话另一头与她们的地理距离。
每天我出门上班的时间,几个大娘不约而同地坐在门口,用那种大串壶烧水。这是一种凝聚了农村人智慧的烧水器具,采用粗大高耸的中空筒状结构,在顶部有一个圆形的注水口,还有一个细长的出水口。烧水时,柴火从筒状结构的高处投下,火就会被整个风筒抽上来。用最少的柴禾,能烧开最多的水。
这类似于一种默契的生活仪式。在各种家用电器更加便捷的今天,在城中村,有这样的一群老人,选择用一种更慢的方式,来对抗慢腾腾的生活。她们蹲坐在矮板凳上,握着一把铁斧子,不紧不慢地劈开木头,尽量劈得外观整齐、长度统一。一块一块地投进去,这样的动作她们做得得心应手,准确又体面。最出色的木匠,做完一件木工活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木屑;最出色的画家,画完一幅泼墨山水,身上找不出一个墨点。一壶水烧开了,细长的壶嘴上“咕嘟咕嘟”泛起水蒸气和气泡,她们在这个时候起身,身上绝不沾半点木屑烟灰。
在城市里找木头是不容易的。她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十几年前,多的是庄稼的秸秆、秋风扫下的落叶、北方刮下来的枯树枝。十几年的时间里,那些庄稼、野生植物、草垛和村庄,被裹挟在滚滚车轮下踪迹全无。我总能看到她们骑着三轮车,把这座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旧日子拉回来。有时候是旧沙发,有时候是木门,还有破板凳,各式柜子,都是早些年的时兴款式。人们紧追着潮流毫不含糊,需要不断地舍弃来腾出新的空间。这些旧家具,几年前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占尽了风头,它们见证过赞叹、留恋、艳羡,也见证过一家人日升月落的平淡日子。它们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一开始独享风光,再后来负隅顽抗,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了人们喜新厌旧的凡俗心思。现在,它们无限辉煌的过去都裸露在一把旧斧子的敲打之下,还原成了最初的木质纹理。大娘们自有一套拆解它们的顺序:先拆那些五颜六色、材质各异的表皮,紫色真皮、橘色亚麻布、黑色绒布;再拆那些大的骨架,通常只需要几斧头,一个秩序井然的木质帝国就轰然倒塌。想当初,它们从一堆原料变成一个家具,经过了多少能工巧匠的细心打磨和雕琢,多少道繁琐精密的工序。然而,拆解它们却不再需要一个完全倒序的过程,大多数时候,只需要一把上了年纪的斧子和一只青筋凸起的手,已经足够了。
也有一些太紧固的部件,她们会请我来插手。我比她们多的是力气,少的是准头。我总是高举起那把斧头,让自己的力气尽可能多的向手臂末端汇集,通常要对准几次才能够成功。剩下的工作就是零碎的细活了。她们会在烧水的时候、吃完早饭无处可去的时候、日落黄昏的时候,一块一块地修理那些张牙舞爪的原料,把那些钉子卸掉,修理劈裂的木纹,再按照一定的尺寸劈出长短和粗细。这时候胡同里就回荡起有节奏的“噼啪”声。对于这座习惯了喇叭声、叫卖声和喧哗声的小城而言,这种声音略显陌生,它们像一枚枚楔子,牢牢地揳进小城流光溢彩的册页中。
我们的房子一层有个院子,院子上面除了留出四四方方的天井,剩下的都盖上了平整的屋顶。在我们鲁东南乡村,这种屋顶叫平屋顶。它的缺点明显,平面的结构扩大了与外界冷暖的接触面,冬冷夏炎。然而它的优点足也以让乡下人对它的缺点忽略不计——平面的屋顶可以囤土,种菜。这些离开土地住到楼房上的新式农民,突然拥有了一块几平方的土地——尽管这被钢筋水泥隔离在半空中的土地失了根,但他们又能把自己当作庄稼人使唤了。
就在这片平屋顶之上,一层层从各个角落汇集来的土壤堆起来了。它们越堆越厚,厚到完全可以支撑几垄油菜的根,可以让一棵辣椒扎下自己而不会倒伏,尽管当那些根茎深入泥土的最深处,会略带失望地改变方向,选择横向伸展。
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她们的菜园就已经蔚为壮观了。闲下来的时候,她们就会去二楼坐着。这些菜园,两平方的面积,却足以让她们保留自己庄稼人最后的尊严。在城里找土是难的,有限的裸露的泥土上,都栽种了绿化树木。她们就要骑着三轮车,去十几里外的城乡交界处,选无人看管的野地,用塑料袋装土。其实不只是土,她们每次出门,都要把一些生活中的细节揣到身上。看到土就捡土,看到树枝就捡树枝。家里的细节每一天都在改变,确切地说,是在增加,菜园里的土越积越厚,门口的木头越攒越多。一天天地,她们把自己年轻时候丢在外面的细节捡回来,像一条日渐枯萎的河,选择用一块块石头填补自己裸露的河床。
93号大娘最喜欢在菜园里种花生。花生的成长期要从春天一直覆盖到秋初。这意味着,在这几个月里,她只能在等待中看着其他邻居一茬一茬收获小油菜、小葱和韭菜。这样的等待,类似于一种幸福的煎熬。她照看得很细心。她时常拿着小板凳坐在菜园旁边,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就只是呆呆地坐着,保持着与一棵花生对峙的姿势。她能看到些什么呢?那些豆瓣状的叶子慢慢张开,那些触手一寸寸接近地面然后消失不见,平整的土层慢慢地隆起。她还看到这片土地原来的模样,那时候她还年轻,老伴儿也还在身边,孩子没有四散天涯,土地还没有被高楼占领。
95号大娘最钟情的是韭菜。这种似细镰刀的扁叶蔬菜,喜欢大肥大水,这对于距离地面3米多高的半空,多少有些异想天开。她尽力为它们打造最优渥的生长环境。浇粪水、埋草木灰、手工捉虫……她的韭菜因此长得又凶又壮,叶秆埋得很深,出土便是叶片,叶展极宽,叶尖沉沉地垂下来。
在她们的生活里,事物都有自己自成一体的生物链。烧出来的草木灰,挪到二楼菜园里就是很好的肥料;吃剩的果皮菜叶,沤在一个罐子里做有机肥;一棵菠菜可以挪到花盆里做绿植……她们尽量地让每一个经过自己双手的物件都物尽其用,用一道道工序剥蚀掉它最后的价值。年轻的时候,她们努力地将自己拉满弓,张满弦,生活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她们草木皆兵。这些积累了大半生的经验,最后都浓缩成了处理眼前这些鸡毛蒜皮的游刃有余。不过,只有一件事情除外:她们渐渐垮塌下来的身体,实在让她们措手不及。
96号大娘有严重的风湿病。一年四季,她的腿上都绑着厚厚的护膝,手指关节也弯曲变形。闲聊的时候,她总爱掐着双手来回搓,她无数次回忆起年轻时候受的苦。“月子里就得洗衣服做饭,下地干活,大冬天蹲在河水里洗麻袋,一天一顿饭。这都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养不回来了。”夏天我爱穿短裙,冬天我穿阔腿裤,她看到了就嗔怪我,说年轻人都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子。
95号大娘有腰腿疼的老毛病,走路时半个身子躬起来,像有一只大手,在她的腰上紧紧地攥了一把。她的手走路时总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个折叠的马扎。她立定,挺住腰,手一松,马扎稳稳落地,然后她顺势坐上去。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这是她能够把马扎放下来的最便捷的姿势,那些她事先没有想好的姿势,她的病症已经替她想好了。
小区往西十里路,是我们当地著名的浮来山。浮来山上多松树。秋冬季节,松树摇落了一地的松针,她们要结伴上山了。我见到她们出发前和归来后的场景。而这中间五六个小时的内容,我只能通过她们归来时满满的布袋和凌乱的头发来补充。原谅我匮乏的想象力,不能详实地补充上那些更加动人的细节。她们一定相互搀扶着过马路,95号大娘还是躬着她的腰,其他两个人就要照应她的节奏,放慢速度。她们在公交站台等公交车,2路,从汽车站开往浮来山的那条线。她们年轻的时候一定也经历过无数翘首等车的时刻。那时候,她们是等一趟班车载来让她们怦然心动的恋人,等一辆公交车载来暑假回家的儿女。这一次,她们为了自己等。公交车靠站,她们相互搀扶着上车,落座。也一定有年轻人微笑着让座,而她们一定会表示感谢后坐上去,她们的身体不允许自己谦让过头。路上不用担心坐过站,这是她们坐得最安心的一辆车,她们会等车缓缓靠站,等所有乘客都下车,然后再跟司机寒暄着下车。
从山脚下,她们一趟趟捡回松子、松针、野菜。秋收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她们会捡回花生、玉米、芋头。如果她们恰好经过了一条河,她们会带回来几块好看的石头,一块块地摆在门前的花盆里。她们就这样,一趟趟用山河树木丢掉的零件,加固自己的老年生活。那些松子和松针的身体里填满密实的松油,用来烧水,是上好的柴禾,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中散发出阵阵松香;那些野菜和花生,够她们在胡同地面上整整齐齐地翻摆晾晒一整天。
对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亲人”,一个操着本地口音的中年妇女,常年烫着一头黄色卷发。这个中年妇女同几位大娘都熟识,隔三差五地来,骑着一辆电动车,车后座上总绑一个大纸箱。她从里面掏出脸盆、洗衣粉、毛巾,我看着大娘们乐呵呵地接过去,口里说着客气话。中年妇女把车靠边停下,这时候就有一个大娘递过来一个马扎,“坐坐吧”。这几个字的话音刚落,大家就一齐坐下,一个亲热的拉家常的氛围就烘托出来了。中年妇女很关心大娘们的身体状况,开场都是“最近血压怎么样啊大姨?”“腿还疼吗?”“平时少吃点盐,不能久站,但也不能老坐着”。说这些话的时候,中年妇女还会带上手势,摸摸这个大娘的肩膀,拍拍那个大娘的手。这样的拉家常每半个月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偶尔中年妇女还会带来一台便携式血压仪,挨个地为她们量血压。她们相互惊叹或者羡慕着彼此的数字,笑一阵再伤一阵。她们的老年生活像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偶尔地甚至规律地扔下一块石子,荡起的涟漪足够在水面上来去几个回合。
有一次,中年妇女再来时换了一辆货车。货车停在胡同口,她开始一趟趟地往几个大娘家里搬箱子。一个个原色纸箱,包装简单,上面只贴了“某某羊奶”四个醒目的大字。“这次厂家的活动优惠力度很大,你们这样组团买,比之前还能多买两箱。” “您看咱这包装,越高端的品牌,越简单大气,绝对放心。”中年妇女拉住93号大娘的手,嘱咐她,一天冲一包,一定要在临睡前20分钟,用37℃左右的温水冲泡,“坚持喝,包治百病”。后来我问93号大娘,这种羊奶一箱多少钱?她说,一千二一箱,买一箱送一箱。一箱有60包。效果好吗?96号大娘回,她自从喝了这个羊奶,就很少感冒,精气神也好了很多。
按照我有限的经验,我大约知道了事情的端倪。有些事情,我想我就算知道了也不能说。在假面揭示之前,真相与假面之间可以完美地画上等号。在这个等号平行的天平上,她们一定会在每晚临睡前,神情庄重地撕开那个长条包装,颤颤巍巍地把一包洁白的粉末倒进水杯,然后旋转,搅拌,再一仰头喝掉,感觉身上顿时充满了力气。她们还会在某一个瞬间,暗自数算着时间,数算着那双膝盖能再跟她促膝坐着,摸摸她的手,拍拍她的腿,然后给她量量血压,再让她们笑上一阵伤上一阵也是好的。
她们不太提起时间,偶尔提起来,最常问的一句话是“小鲍,今天星期几了?”她们的日子里,很少用到星期。这种只有上班族和学生们才会用到的计日方法,被上班、会议、出差、课外辅导、兴趣班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一眼望进去全是匆忙的脚步与急促的喘息,这与她们风调雨顺的生活轨迹完全没有交集。她们只活在自己的农历时间里。
她们谨守着那些重要节气里的风俗。93号大娘总爱在秋分节气在门口支起炉灶,做好一锅热气腾腾的豆沫子菜。快出锅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她开始喊:“小鲍,拿碗来。”她总是嫌我拿的碗小了,一勺子菜就冒尖儿了。她总纳闷,为什么日子越过越好了,吃饭的碗却越来越小了。她一直用着早年间的粗瓷大碗,青花图案,碗底深窄,碗口阔大平展,一眼望去好日子都铺在大碗口里,看着安心舒坦。
95号大娘喜欢在端午节的一大早挨家挨户地插艾草。搬过来的第一个端午节前,她就跟我打了招呼,说这一整条胡同里的艾草都是她来插,从东插到西。“你们就安心睡觉。”第二天一开门,门前的艾草散发着清香在轻风中摇曳,门把手上还挂了几个热乎乎的粽子。
逢年过节,小区里的年轻人往外跑,她们安心地等在家里,一年中最不算孤家寡人的时刻,不再需要老邻居的时刻。在外工作的儿女们回来,在时间这条大河中逆流而上,来寻他们的根,来修补这片年久失修的河床。93号大娘的儿子在省城当兵,几年回来一趟。95号大娘有两个女儿,嫁到了外地,每逢春节就会携儿带女回娘家团聚。96号大娘的儿子在市里开一家饺子馆,生意红火。这一天,她们终于心安理得地闲下来,将自己当作一个老人,把攒了一年的笑容堆在脸上,接受儿女们迟来的问候、关心和祝愿。
不出去的时候,她们就在胡同口坐着,这是她们一天中极重要也极具仪式感的内容。她们几个小时地聊天,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就这样相互陪着。像一棵棵老树,就这样沉默地相互挨着靠着,一阵风来,她们就呼应以彼此嶙峋的树干和落叶。有时候,我也陪她们坐上一会儿,但是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我得上班,做一家人的饭菜,辅导孩子功课,我没有整块的时间就这样呆坐着,享受自己由身到心彻底放松的样子。她们都聊些什么呢?能有哪些话题,让她们以这样的姿势一坐就是几年、十几年,却毫不感到厌烦? 在这样的小地方,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大多是乏善可陈的,平凡而普通的。她们一定摸索了许久又矫正了许久,话题在她们的聊天内容中几经流变,从一开始的看护庄稼、喂养牲畜,到后来的照顾公婆、孩子成绩、嫁娶婚俗……再后来,大多数关于别人的话题,都从她们日渐裸露的河床中流走了。现在这条河已经瘦成了麻绳,瘦得游不了鱼、翻不起浪花、长不了水草,瘦得只剩下自己的身子了。她们这才开始聊起自己,用自身抵御自身,用时间消耗时间。她们只需要聊聊,年轻时一顿饭吃几大碗米饭,结婚时穿了怎样好看的大红袄,午饭吃了几口菜,降压药还剩下几片……
住在一片生命的高地中间,我是一处低矮的盆地。一条条翻涌的大河,冲刷着一片片年久失修的河床,源源不断地流经我,然后各奔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