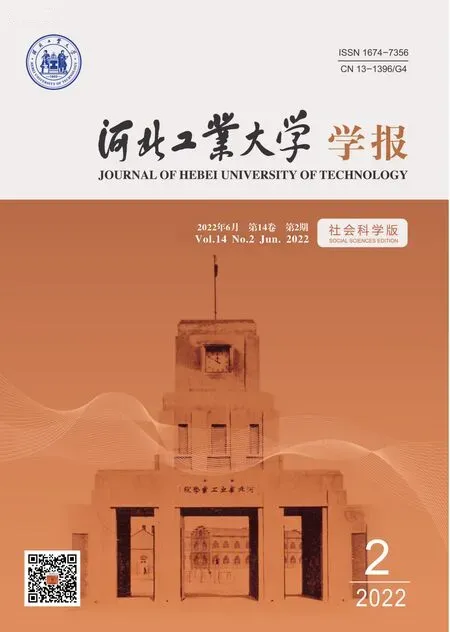论简·班尼特生态哲学中的物质施动性
马丽莉,钟道贤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传统哲学框架,包括以实证哲学为主线的科学主义和所有的新人本主义,自20 世纪50 年代末开始,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后现代转折。究其原因,与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现实紧密相关:全球消费主义泛滥,人与物的关系愈发疏远,物沦为单纯的感官刺激和身份幻觉,由此导致生态危机日渐严峻,地缘政治结构也随之剧烈变化。由此可见,充满活性的物质世界(vibrant matter),使现有的制度和理论受到考验,促使坚持生态感性的新唯物主义从哲学层面对物质性(materiality) 进行再思考,并对机械论展开批判。生机论和多变的一元论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早在18 世纪,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就认为仅仅用“广延性”无法解释纷繁的物质世界。他认为物质具有内在的能动性,即“感受性”;万物处于一个生生不息并不断转化的系统之中。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简·班尼特(Jane Bennett) 在其专著《活性物质》(Vibrant Matter) 中提出“生机唯物论”(vital materialism)。她认为,在无生命的事物中存在一种令人好奇的“物的力量”(thing-power),并且这种力量能够产生神奇而微妙的效果。她指出,“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里,非人类的物质拥有强大的力量,但自命不凡且追求自主的世俗的我(bourgeois I) 却予以否认。”。为了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论的窠臼,班尼特建议,我们“需要一种能量的源泉,即对世界的热爱或者对充满活性的物质世界的痴迷。”。班尼特的生态哲学拒斥西方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传统,坚持“多变的一元论”(protean monism),认为生命和意识是由无生命的自然物质生成的,这种生成过程是自主的,依赖于事物内在的自组织属性;并且这种变化过程复杂多变,难以通过线性的、单向度因果关系来分析,人类难以预测和理解。总而言之,班尼特对哲学、宇宙、政治和伦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倡导一种负责任的生态政治观以及更可持续、更少伤害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发生于2019 年的新冠病毒公共卫生事件,最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重大社会危机。这场危机在自然、社会和精神层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乎人们预料,更加促使政治科学研究从人本主义转向坚持生态感性的新唯物主义。我们必须悬置建立在特殊性基础上的“二元”或“人类中心主义”文化观,从新时代的普遍性视角出发,在消费主义盛行、危机频发的“人类纪”的当代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张举物质的施动性,体现了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后现代转折,具有鲜明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主体化的后人学倾向,是一种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新型世界观,是应对这些全球性危机和困局的可供参考的方法论和行动指南。因此,对班尼特生态哲学坚持生态感性的新转向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班尼特生态哲学的含义和基本特点
(一) 概念含义
班尼特的专著《活性物质》一书从哲学和政治两个层面论述了“事物的政治生态”(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班尼特生态哲学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生机唯物论”和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
班尼特认为,人们习惯于把世界万物进行二维划分,一种是“迟钝之物”(dull matter),例如物体和事物,另一种是“活力生命”(vibrant life),比如我们人类。班尼特在书中引用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 的观点,认为这种思考习惯“阻碍了人类明智的思考”。班尼特举例说,正如欧米伽-3 脂肪酸可以改变人类的情绪,生活垃圾可以释放出活性化合物,并产生挥发性甲烷气流一样,物质的活性确实存在,并利用其自身固有的内在力量不断影响着人类在现代性及其发展进程中的行为取向(Vibrant Matter:Preface)。
因此,班尼特提出“生机唯物论”,她认为人们需要一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所说的“物体的形而上学,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从来都不存在被客体化的深度的形而上学,物体从此提升自己的地位并逐渐为人类所认知”。
班尼特借用了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为体”概念来诠释“生机唯物论”。拉图尔认为,行为体是可以改变另一种实体的实体,既可以是人体,也可以是“非人”,比如食品、电力、风暴、金属、冠状病毒等。美国生物学家,“内共生理论(endosymbiotic theory)”创立者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 认为,“我们(人类) 是能走路会说话的矿物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 也指出,人类可以被视为特别丰富和复杂的物质集合体。行为体具有功效(efficacy),各个行为体不是预先给定的孤立存在,而是一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并且自身带有足够的活性,可以改变现状和事件的进程(Vibrant Matter:Prefaceⅷ)。美国城市巴尔的摩排水沟旁的一堆“垃圾”(一只大号的黑色塑胶工作手套,一片结实的橡木花粉垫子,一只尚未腐烂的死鼠,一个白色的塑料瓶盖,一根光秃秃的棍子) 引起班尼特深邃思考:首先,一方面,这些看似静默不动、令人忽视的物体让人联想起人类的活动,比如工人的劳作,扔垃圾者的投掷,毒鼠者的成功等;另一方面,它们还有超出人类意义之外不容忽视的自身存在。其次,这些物体展示出“物的力量”(thing-power):虽然“我”不甚理解,但它们发布一种诉求,至少在“我”心中激起诸多情感:死鼠(或者它只是在睡觉?) 令人不快,垃圾使人沮丧,尤其那只老鼠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离奇感,我还意识到花粉的构造,平淡无奇的水瓶盖使我想起它如何被批量制作。这些通常被认为迟钝的行为体,闪耀着生机和活力。如果没有黑色手套上阳光的映射,我也许看不到老鼠,如果老鼠不在那里,我可能就不会注意到瓶盖,如此等等。班尼特所主张的“生机唯物论”拒斥“美国唯物主义”(American materialism),后者要求人们在越来越短的周期内购买越来越多的产品,其本质与“物质性”是背道而驰的。
班尼特综合斯宾诺莎(Spinoza) 的“意动体”(conative bodies) 和德勒兹(Gilles Deleuze) 与瓜塔里(Felix Guattari) 的“组合体”(assemblage)(即多种活性物质各种不同元素的特殊组合体) 两种理论立场,认为物质的活性跨越了人类和非人类的界限,存在于一切行为体中。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 的短篇小说《家父之忧》 (Cares of a Family Man) 中的主人公奥德拉德克(Odradek),外形只是一个线轴,但却能跑能笑能清晰地说话,以木头的形式呈现出非人类物质的活力。班尼特认为奥德拉德克是介于惰性物质和活力生命之间的行为体,在本体上具有多重性。奥德拉德克既不是“人”,也不是“非人”,它(他/她) 是一个“干预者”,类似于德勒兹式的“拟因果算子”(quasicausal operator),在组合体中成为催化事件的决定性力量。十九世纪晚期俄罗斯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维尔纳德斯基(Vladimir Ivanovich Vernadsky) 认为,在物质和生命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区别,他把有机物定义为“普通矿物质的特殊分布形式”。班尼特认为,奥德拉德克展现了含水生命和岩石之间的延续性,从而突出了事物的生成过程(the becoming of things)。班尼特的“生机唯物论”赞同约翰·佛柔(John Frow) 的观点,认为各行为体存在同质性的同时,也存在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需要被扁平化,各行为体应该作为并列关系从水平的方向来解读,而不能从垂直方向以层级的存在结构来理解。我们人类愈是从水平的方向体验人和其他物质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愈是朝着生态感性迈近了一步。
班尼特在2001 年出版的专著《现代生活的魅力》(The Enchantment of Modern Life) 一书中,从伦理、美学和政治的范畴探讨了由各种“情感催化剂”(affective catalysts) 带来的人类情感,然而在《活性物质》中班尼特却更多的关注于催化剂本身。这些催化剂具有内生性,存在于非人类体内,班尼特把他们产生的力量称之为“非人格情感”(impersonal affect)。她吸收了斯宾诺莎的情感概念,认为无论是有机体还是无机体,自然之物还是文化之物,都具有情感性。班尼特引用大卫·科尔的话对“非人格情感”做了进一步阐释:“情感势必造成粒子力量的碰撞,由此带来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情感创建了一种力场,但这种力场并不倾向于凝成主观性。”(Vibrant Matter:Preface Ⅷ)。由此可见,“生机唯物论”把情感与物质性等量齐观,主张物质活力是内在和固有的,而传统意义上的“活力说”认为生命活力是独立和外加的——二者迥然不同。
班尼特期待通过人类周边环境以及人类自身具足的活性物质的真切发声,引发人们的共鸣,从而给予“物的力量”(the force of things) 应得的重视。如此一来,人们对政治事件的分析也许会发生改变,比如,假如我们改变观念,把面前的垃圾、废物和可回收利用物质看作是一堆堆不断累积并且存在潜在危险的活性行为体,那么人类的消费方式是否会发生改变呢?假如我们把饮食看作是各种不同个体之间的遭遇和混战,而且最终胜负难料,那么人类的公共健康水平能否得到些许改善?如果电力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资源、商品和工具,而且还可以被视为一种“行为体”,那么国家的能源政策和方针是否会受到影响?为了进一步阐述事物的政治生态,班尼特引入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组合体”(assemblage) 概念。
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认为,世间万物都由某种“原基”(primordia) 构成,斯宾诺莎也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种“共同物质”(common substance) 的不同样式(modes)。班尼特认为尽管这种同质性内部力量的束缚,组合体内各种各样的行为体仍然具足丰富的活性,形成一种悸动的活跃联合,从而发挥整体功能。组合体内各部分力量的分布虽然并不均匀,但却没有一个起绝对主导作用的“首领”(central head):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物质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单独持续决定整体组织的运行轨迹和影响力。组合体产生的合力绝不等同于内部各成员力量的简单累加,并且产生的效果具有突发性,比如一种创新的唯物论,一次大面积突然停电,一场飓风,一场反恐战争等。总之,虽然组合体内每位成员都有活性力量,但并不影响整体功效,即“组合体的施动性”(an agency of the assemblage);恰恰正是各成员具足的这种从整体脱离的“高能脉冲”(energetic pulse),使组合体成为一种开放的、具有独特生成史和有限生命周期的多变的集合体。
综上所述,班尼特的生态哲学把大自然视为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最不复杂的生命形式,甚至看似无生命形式的“迟钝之物”都具有稳定整个生物群落的作用,班尼特认为它们也是一种“民众力量”,发挥着自身的道德和政治责任,对大自然的整体健康运作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究其本质,班尼特所持守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
(二) 基本特点
班尼特的生态哲学体现了一种互相关联的全方位思想。在这个由互联的活性物质建构的世界网络中,伤害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等于伤害其自身。生态问题既涉及流域管理,同时也关乎文化和心理形成问题。文化不是人类独创的,而是由生物、地质和气候等多方力量协作而成。班尼特认为不存在脱离自然的绝对意义上的人类,人的自身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密不可分,可见,班尼特生态哲学的互联性还体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同一性。
班尼特认为我们决不能把活性物质仅仅视为人类或者上帝进行创造活动的原材料。她创造性地提出“民主生机唯物理论”,认为非人类物质与人类都是共同体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普通公民”(plain citizens);对物质的过度工具化利用会引发人们的狂妄自大以及可能招致地球毁灭的征服欲望和无节制的消费行为。
班尼特所主张的“多变的一元论”,既不同于张举人类中心主义的“浅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又有别于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 —既不是自然界各部分的“平稳和谐”(smooth harmony),也不是统一于某种“普遍灵魂”的多样性,而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多样化”(ontologically diverse)。她认为掌控事物本身生成过程的是一种自然倾向,或曰一种意外,而非线性或决定性的因果关系;并且组合体内个体之间的合作和对抗符合一种奇怪的不断变化的“湍流逻辑”(the strange logic of vortices),非人类所能完全了解和预测。因此,班尼特生态哲学的多变性还包含一种不可预测的偶然性。不仅如此,班尼特还颇具创新性地指出,生态健康有时要求人类“蹑手蹑脚”(tread lightly on the earth),但有时也需要更宏大和剧烈的能量消耗。因此,她认为人类既要谦恭,又要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更加巧妙地与自然相处。
二、主体的消解:兼具多重特征的物质施动性
施动性(agency) 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表明行为体的效能性(efficacy)、自反性(reflexivity) 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 等。班尼特认为,行为体从来不会单独发生作用,它们的施动性总是依赖于很多个体和力量的合作、配合或者相互干预。在二十世纪末期,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世界各个部分相互之间既紧密连接又高度冲突,全球资本主义呈现出现代性危机,学界随着传统人本主义衰微应运而生的后人学思潮,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支配论展开批判,倡导全球伦理。然而,在全球化看似正裂变为全球分化的今天,多元文化主义好像再也不是政治正确的语料库里最为顺手的话语武器了。世界各部分之间互相依赖又不断产生冲突和摩擦的这种共存共生关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概念对部分和整体的这种不稳定关系重新定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班尼特采用“组合体”这一结构范式研究物质施动性,进而言说她所主张的“事物的政治生态”,无疑具有重大的哲学和文化价值。
(一) “施事能力波谱”再延展
在传统语境中,施动性被归属于理性主体,比如个人和国家等实体,从而造成生成过程中施动能力的消长和变化被忽略。库尔(Diana Coole) 提出的“施事能力波谱”(spectrum of agentic capacities)概念,推翻了施动性专属于理性主体的认知,并成为班尼特生态哲学中物质施动性理论的试金石。她认为施事能力有时存乎个体的人,有时存乎人类生理学过程或者运动意向性,有时存乎人类社会结构或“间性世界”(interworld)。但是库尔的理论旨趣聚焦于政治施动性,并且把政治仅囿于人类学的范畴来研究。班尼特进一步延展了库尔的“施事能力波谱”,使其超越了人类主体和主体间领域,从而把施动性扩展至包含各种活性物质(既包含人类又包含非人类) 的组合体。班尼特举例说,未来大面积停电事件(比如发生在2003 年的北美洲大停电) 的预防需要依赖于诸多因素的协作配合:议会必须鼓起勇气与日益增长的工业需求做斗争,尽管这与很多人的利益相悖;但无功功率也必须发挥自身作用,条件是传输线路不能太长。在上述多种元素交互构成的组合体场域内,沿着连续体分布的物质施动性,从多个节点(比如离奇的电子流、自燃的大火以及笃信市场自由主义的议会成员等) 向外突出。由此可见,班尼特进一步延展了库尔的“波谱”,把物质施动性置于更广阔的政治生态范畴进行讨论。
(二) 主体消解后的新的伦理与政治
现象学注重在变化多端的情景之中探寻个别与普遍的贯通方式以及隐藏于表象之下的事物本质,因此,以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施动性可以认识事物的多变性和多样性,从而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中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现象学相比较,活力唯物论对人类主体性进行了更彻底的消解。除了行为体的效能性,班尼特还从运行轨迹(trajectory)、因果性(causality) 和责任性(responsibility) 对物质施动性进行探讨。首先,在施动性的传统定义中,效能的根本原因归结于“道德能力”(moral capacity) 或者 人类“意向性”(intentionality),然而,班尼特认为施动性具有创新性,效能的生成源并非人类主体(subject),而是一个内部既相互竞争又互相联合的“集群”(swarm)。在“集群”内人类和非人类的力量交互存在。其次,伦理学认为施动性的运行轨迹不但具有“指向性”(directionality),还兼具“目的性”(purposiveness),德里达却对这种意识中心说持不同观点。他认为施动性具有“弥世性”(Messianicity),即一种“开放的约定性”(open-ended promis-sory quality)。在德里达看来,这种未指明的承诺让我们一直充满悬念,但永远不会被兑现。德里达把这种无法履行的承诺视为任何事物出现的条件,从而为活力唯物论者证实组合体驱动力或者某种运行轨迹的存在铺平了道路。另外,班尼特认为,“集群”内最不确定的因素是因果性,但施动性的广延性和互联性又决定了因果关系的有效性。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动因是布什还是本·拉登?施动性在此更多表现出突发性,而不是效能性,更多的“分形”(fractal) 或曰碎片形,而不是线形(linear)。在这样一个施动性回路中,原因和结果互换位置并相互报偿。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学者威廉·康诺利(William E.Connolly) 认为,“我们不能说原因与其所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同……新的突发事件的形成,不但归因于被灌输进来的外力,而且还源于它自身以前从未开发过的、用于接待和自我组织的能力”。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教授诺特耶·马尔斯(Noortje Marres) 认为,促成某一特殊事件发生的施动性源头是很难把握的,也许这种“不可把握性”正是施动性的一种本质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此,班尼特最后仍然认为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共同构建的组合体依然存在政治责任性。生成功效的那种产出性力量实际上是一种“联盟”(confederacy),作为这种“联盟”构成要素的人类行为体自身,究其本源而言也是由工具、微生物、矿物质、声音和其他外来物质构成的联合体。因此,班尼特的活力论认为,人类个体并不能为其行为造成的后果负全部责任。然而,他们据此就可以拒绝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政府官员就不必对公众负责任吗?班尼特认为,这种“联合施动性”(confederate agency) 概念虽然减轻了责任性,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放弃有害后果的溯源。相反,这种概念反而拓宽了溯源的范围。在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源头清单中,人类及其意向虽然参与其中,但并不是组合体内唯一的或者总是起最大作用的行为体。因为施动性具有分散性(distributed agency),人们对单向的指责怀有迟疑的态度。虽然有时道德的义愤对民主和公平政治必不可少,但是政治如果缺乏对施动能力网络的洞察而过于专注道德谴责,那就很难产生良好效能。它会使复仇合法化,并将暴力提升为首要工具。对施动性的“分散性”(distributive) 和“联合性”(confederate) 的理解,因此会重新唤起人们将伦理学从道德主义中分离的必要性的思考,从而制定适合这个充满活性的物质世界的行动指南。
班尼特认为,组合体的施事能力归因于其构成物质的活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气”(Shi) 与这种组合体的施动性颇为类似。她认为“气”有助于阐明人类话语(discourse) 中一些难以表述的内容:这种潜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并非起源于人类主观,而是事物的自然倾向造成的结果。她认为“气”是特定安排的一组事物所固有的样式、能量、倾向、轨迹或者热忱,“气”的活性力量源于某种复杂的时空组合,而不是这个组合的任何单独元素。无独有偶,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 也认为,引发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在于一组元素的“偶然聚合”(contingent coming together)。由此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的“气”还是阿伦特的“偶然聚合”都与班尼特的“组合体”这一结构范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物质施动性的分散性相一致。
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勾画政治生态新图景
作为对全球化现实的回应,班尼特的生态哲学以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为立脚点,思考“去人类中心主义”(deanthropocentrism)。班尼特一方面拒斥西方形而上学中的机械唯物论和经典二元论,坚持“多变的一元论”和“水平的本体论”;另一方面,她又明辨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 的局限性,发展了瓜塔里的“三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指出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物质施动性的多重特征使班尼特展开拟人论思考,她创造性地认为政治系统本身构成了一种生态系统,提出“民主生机唯物理论”(a vital mater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从而勾画出一幅崭新的政治生态新图景,对生态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 对机械唯物论和二元论进行理论反拨
班尼特把物质施动性放在“组合体”的框架内考量,认为施动性具有联合性,这是对蛰伏于现代科学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否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机械论以机械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完全服从机械因果律,全部未来的事件都严格地取决于过去,事件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消失了。换言之,就像十八世纪机械论代表人物拉美特利所说“人是机械”“动物是机械”。班尼特的观点与之恰恰相反,她认为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 都是由“活性物质”(vibrant matter) 构成。这些物质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联合施动性”。因此,事件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西方形而上学中经典二元论认为,对立的双方处于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在这种等级性结构中,中心是本原,边缘是中心的派生并受制于本原。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坚持“多变的一元论”,集中关注自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生命可以从无生命发展而来,生命与无生命、人类与非人类在相互关联和交互重叠中消除了等级关系。其“多变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事物的生成过程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包含着自然界人类和非人类多种体系的交互融合;二是事物的状态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整个组合体在不断重组,是不稳定的。斯宾诺莎的“意动体”理论激发了班尼特的生态思考,在专著《活性物质》一书中,她参考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 的观点,认为组合体内各行为体既相互联合又相互对抗,存在一种包含一定偶然性的涡旋状进程(one vortical process),并且这种体现物质施动性的奇异结构(strange structuralism),在政治、物理、经济、生物、心理和气象学等领域广泛存在。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涡旋状进程不是任意或者无结构的,可以分为多个阶段,但每个阶段在规模、时间和复杂性度方面却又各不相同,包含一定不确定性(the aleatory)。
(二) 坚持分散的施动能力,倡导生态共同体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宇宙万物的中心。笛卡尔提出人要“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统治者”,洛克也主张“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自近代以来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工业文明及消费模式,使全球陷入了生态危机。瓜塔里的“三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认为,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环境的衰败,而是三个“生态寄存器”(three"ecological registers")(环境、社会和精神) 都遭受了损害。瓜塔里还坚持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极度紧密的,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整体,他美其名曰“世界资本主义联合”(Integrated World Capitalism)(IWC)。班尼特综合了拉图尔的观点,把瓜塔里的“三重生态学”往前推进了一步。她认为,没有被人类污染的“纯自然”(a pure nature) 是无法找到的,同理,那种所谓“纯人类”(something purely human) 的自我定义是愚蠢的。她以“横向”(transversal) 的思维范式,突破浅生态学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局限,描绘出一个在“人”与“非人”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界限的本体论领域。因此,自我(the self) 和自我利益(self-interest) 的概念需要重塑。班尼特坚持认为施动性具有分散性和广泛的分布,不再局限或附着于某个固定的主体(包括人类主体),而是存在于不同的体系之中。以此为立脚点,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关注生态共同体而非有机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而非个体主义的伦理学。在万物共生共存的集合体中,班尼特寻求更文明、更具战略性和更微妙的人类与非人类接触,倡导建构一种更可持续的生态共同体。
(三) “民主生机唯物理论”:一种崭新的生态政治观
班尼特综合了达尔文和拉图尔的观点,认为虫子、电力、脂肪、金属、干细胞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器具,或者如达尔文所说具有“微型施动性”(small agencies) 的任何事物,如果与其他机体(包括有机物和无机物) 有效联合,便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甚至对人类的历史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班尼特由此展开“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 思考。她吸收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 的观点,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政治系统本身构成了一种生态系统。“共同问题”(common problems) 吸引形形色色的行为体采取“共同行动”(conjoint action),并聚集到一起,从而形成由各种人类和非人类因素构成的政治集合体。因此,政治行动也可能起源于人类之外的行为体,譬如动植物、金属甚至机器等。“组合体”内的行为体虽然相互连接,但各部分之间并无固定不变的顺序。各行为体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情景,并非总是以某种一成不变的方式发挥施动性,他们有“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并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会导致对其他行为体的伤害。因此,活力唯物论的政治目标并不是各行为体之间完美的平等,而是组合体各成员之间更为畅通的沟通,或者如拉图尔所言,打造“血液流通更顺畅的集合体”(a more"vascularized"collective)。然而,受制于语言障碍,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的诸多行为体又如何交流呢?人类又该如何倾听非语言形式的建议呢?拉图尔建议召集“物质议会”(parliament of things),而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却借助于朗西埃的民主论提出“民主生机唯物理论”。朗西埃认为在“公众”(the public) 内部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打破现有秩序的“民众力量”(the force of the demos),政治就是对行为体分布秩序的“异常中断”(a singular disruption)。民众正是借助这种“异常中断”来建构一种场景,发表他们的“辩论性话语”(argumentative utterances),进而改变既有的政治制度。然而在朗西埃的“公众”概念里非人类元素却被拒斥于门外。班尼特的“民主生机唯物理论”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朗西埃的民主论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认为“民众”(the demos) 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同生并存的共同体。动物、植物、矿物质或者人工制品都可以促成公共事件的发生。因此,突发事件可以看作是相关行为体或者“民众”发布的“辩论性话语”。班尼特警告说,民主理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虽然是正常合理的,但也会导致一些严重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明辨那些“既有选区”(established constituencies) 和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建议的非人类行为体,人类将会遭到伤害。鉴于这种担忧,班尼特极具前瞻性地提出如下疑问:鸟类病毒能否传播到人类身上,从而对医疗保健系统、国际贸易和旅行造成严重破坏?不仅如此,班尼特还进行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与柏拉图给普通民众贴上智力缺陷的标签类似,把政治仅限于人类活动的狭窄范畴或许也是一种偏见;这是一种对非人类群体的偏见——错把它们仅仅当作了陪衬、约束与工具。班尼特的“民主生机唯物理论”力求在“言说者”(speaking subjects) 与“无言者”(mute subjects) 之间架构一座桥梁,使之成为具有差异倾向的多性能组合体。因此,班尼特建议,人类应该更加密集咨询非人类行为体,对自然界的突发事件、反对意见、法度和主张都应该认真倾听和回应,因为所有这些对我们人类赖以栖身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班尼特对人类与非人类平等看待,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物质皆有活性;物质施动性广泛存在,并在组合体内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作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有政治经济体系的反抗与批判,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及其物质施动性理论阐幽显微,尤其把自然环境和生态保护重点纳入考量,为当前生态恶化的后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
四、班尼特的生态哲学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
西方近代哲学局限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过于强调人的主体作用和理性力量,因而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难以自拔。班尼特的生态哲学对这种主体性哲学进行拒斥,提出“组合体”概念,从主客体本身以及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来理解社会本质。由此可见,班尼特并不是完全像旧唯物主义那样,以感性直观理解现实。虽然如此,本文认为,她仍然没有彻底冲破旧唯物主义樊笼,存在理论局限性。这里的旧唯物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第一,班尼特没有把唯物主义从物质相态推进到实践形态,秉持的仍然是旧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积极改造和推进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结果。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与班尼特的根本不同在于用实践的观点理解世界。马克思认为,连续不断的感性生产劳动和创造,构成了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班尼特虽然反对泛灵论,但她认为物质内部存在的真实而强大的“力”(force) 具有“不可识别性”(resistant to representation),并且“生化-社会系统”(biochemical-social system) 有时会意外分岔或者选择不可预见的发展路径。可见,班尼特的活力唯物论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沼,否认客观规律,排除社会实践的作用,恩格斯批评之为“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在列宁看来,既承认我们的感觉有一个物质的来源,又把它们能否给予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正确信息看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只是玩弄字眼而已。
第二,班尼特囿于对人的生物学理解。班尼特的生态哲学作为以生态保护为主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人学思潮,旗帜鲜明地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理论反拨,但过于强调物质的作用。在班尼特看来,人是肉体组织相同的单个人,与动物并无二致,,从而造成对人的主体向度的忽略。为了明辨物质的活性,班尼特主张暂时悬置人类内在性本质的探讨或者人类与动物、植物和其他事物的区别。她认为人类的肉体是由不同种群的微生物构成,具有“外来品质”(“alien”quality),因此她把人的施动性等同于“物力”(thing-power)。 在这一点上,班尼特和费尔巴哈一样,抛开实践,把社会历史过程完全当作物质过程来对待,对感性的人的活动缺乏理解,没有认识到实践和社会关系对人生成的决定意义。他们把人的本质这一哲学“最高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抛开政治和实践,转而求助所谓“类的平等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唯物主义。虽然班尼特从生物学的视角透视物质的施动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她却又囿于对人的生物学理解,以至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等量齐观,并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观点理解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认识人,人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个自然人,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
第三,班尼特对自然界的片面理解。班尼特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显然是唯物主义观点,但她却就此止步,没有认识到自然界同时也是历史和工业生产的结果。班尼特认为马克思试图使商品“非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并且把本来属于人类的施动性赋予商品,从而阻止人们对商品的盲目迷恋。但如此一来,会造成一种倾向,即物质的施动性被隐藏,而且政治施动性被还原为人类施动性。班尼特一方面反对这种倾向,另一方面,她又认为保持人和物之间本体论划分是必要的。班尼特承认,“主客对立的哲学观”(framework of subject versus object) 有时可以减轻人类的痛苦,但同时又拒斥康德的“自为目的定律”(treat humanity always as an end-in-itself),认为“非人类自然的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 of nonhuman nature) 会损害人类的长远利益。由此可见,班尼特的生态哲学过度强调物质施动性,她虽然拒斥人类中心主义,但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对自然界的片面理解。马克思认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把自然现实化,秉持以实践为中心的人化自然观。
五、结语
在危机频发的“人类纪”的当代历史语境中,班尼特的生态哲学持守一种张举物质性的哲学观点,把生态、自然环境和政治治理同时纳入考量。一方面,班尼特秉承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组合体”观念,坚持认为物质施动性存乎不同实体和物化过程之中,不同体系之间相互关联并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丧钟敲响,班尼特把自然与人类等量齐观,倡导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倾听自然的“辩论性话语”,体现出一种正确的政治生态观。由此可见,班尼特的生态哲学从新时代的普遍性视角出发,深刻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是一种应对当今全球性难题的可行方法论。然而,倘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审视,就会发现班尼特的生态哲学没有深刻把握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的深刻逻辑。马克思主义以其内蕴的实践属性和对实践的高度倚重,表现出更多“改变世界”的哲学意义,而这正是班尼特的生态哲学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