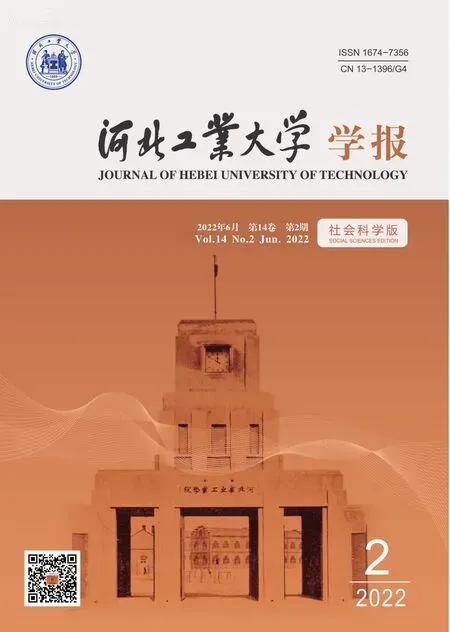他者凝视与主体认知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东方想象与身份认同
王雅麒,陈婷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自古以来,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在中外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共十三条,其中直接要求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在此居住及设派领事。自此,上海开始了它作为租界的近百年屈辱历史。而与此同时,上海在开埠后大量涌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商业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娱乐产业的发展也十分迅猛,这使得上海在短时间内展现出了国际化的都市面貌。这些访沪的外来人当中不乏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横光利一便是其中的一员。
横光利一(1898.3—1947.12) 是日本近代文坛上新感觉派的旗手,他受到欧美文坛意识流与表现主义的影响,认为即将步入现代领域的新文学应当以纷乱的快节奏和特殊的表现力为基础、按照作者理想的主观感受来进行创作。他的一生著作颇丰,作品中常见精巧的比喻、灵活的拟人及奇诡的辞藻,此外他的作品还强调外部事物与内部体验的结合,以思想见长,在细腻的笔触之外展现出了独特的深度。
对于横光利一来说,《上海》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一方面,在《上海》之后,横光利一的创作转向了心理主义文学创作。《上海》是横光利一最后一部新感觉派的文学作品,也是横光利一在新感觉派创作风格的探索道路上的集大成之作。另一方面,在创作《上海》之前,横光利一的政治倾向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而在《上海》完成后,横光利一逐渐转向了右倾。总的来说,《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横光利一这一时期在思想上的矛盾与挣扎,他对上海这个城市中方方面面的描写暗含着他对当时中国的看法以及他对自身存在的定位。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站在横光利一后期走向右倾这一结果的出发点上对《上海》进行分析,从而忽视了作品中展现出的横光利一思想上的挣扎与分裂。事实上,为了表现主人公参木矛盾的自我认知,横光利一在《上海》中花费了许多笔墨来展示不同思想的相互碰撞,这是《上海》一书思想性的重要体现,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横光利一私人化的上海之行
作为一名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在他的散文随笔中多次提及上海这个中国的城市,“上海”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单单是异国的一个城市,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意象和独特符号。横光利一对于上海的这份独特情结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金子光晴和佐藤春夫等近代日本颇具盛名的作家都曾经到上海这个城市进行过或长或短的旅行、并留下了相关的文字记录。
日本作家对中国的这份情结与中日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古时候,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就一直接受着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对汉学的了解程度曾一度成为衡量日本文人水平的刻度尺;而到了近现代,汉学在日本的影响与发展则成了日本文化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这样漫长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文化浸润,日本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文学家都对中国这个堪称其文化之父的国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究欲。而随着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上海作为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许多日本文学家们争相访问的城市。然而,当他们来到这里时,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无疑粉碎了他们曾经的美好想象——即便是在国际化的上海,他们所看到的也大多是肮脏的街道河流、瘦弱的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旖旎风光、才子佳人。由于美好的期望被彻底打破,这些日本文学家当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开始对中国产生强烈的负面情感,加上当时日本正开始实施入侵中国的野蛮计划,为了让“共建东亚大共荣圈”的军国主义思想更进一步被日本人民接受,有不少日本作家在日本政治氛围的影响下开始在作品当中对中国加以过度的贬低与嘲讽,以塑造中国亟须日本“拯救”的国家形象。因此,在近代日本文学家围绕上海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上海大多是以丑陋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
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也不例外,然而其原因却并不单是如此。首先,横光利一对上海的认知和他审视上海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1928 年4 月,横光利一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借住于友人家中,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上海之旅。既不同于凭借着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四处拜访中国名士的芥川龙之介,又不同于通过亲中人士内山完造结识了许多中国作家的谷崎润一郎,不通中文又没有翻译的横光利一的上海之行完全是他独自一人的“冒险”,这在为他带去了诸多不便的同时,也让他得以以一个完全的外来人的目光审视上海这座城市。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们的相关作品中找到证明: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的游记随笔中有许多对上海历史的追忆,其中很多评价都是来自他们接触到的这些中国文人;而横光利一笔下的上海则少了很多对其历史的回忆,而是着力于展现近代时期的它既肮脏衰败又时尚摩登的双重面貌。可以说,横光利一审视上海时的私人性使他笔下的上海烙印上了鲜明的独特性。此外,横光利一对上海的认知与他来到中国前的遭遇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横光利一前往中国前夕,日本文坛围绕日本文学的政治倾向问题发生过激烈的笔论。在晚年横光利一给中岛健藏的信中,他就提到过当时有许多日本文学家在辩论后踏上了“左倾”的政治路线。为了认真思考之后的道路问题,横光利一来到了上海,他后来的右倾选择正是在上海之旅后做出的。而他在上海之行中花费了大量时间在金钱交易所和棉花工厂等地、后又选择将五卅运动作为《上海》一书的主要题材,这都更加直接地说明了当时横光利一审视上海时是带着他自身的政治目光的。
在回到日本之后,横光利一拒绝了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发来的游记的写作请求,并向其解释了他的打算:“我不想写上海或那里的奇闻轶事,我想写的是成为东洋垃圾场的、让人感觉奇妙的大都市上海,那不是一篇游记或短文可以容纳的,我想把它写成一部长篇。”于是,在1928 年到1931 年这段时间里,横光利一在《改造》杂志上连载了他所写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连载期间,横光利一并没有给这部小说定下标题,根据他后来的说法,这部小说一开始是打算叫作《一个唯物论者》。而直到1932 年小说连载结束、准备发行单行本时,横光利一才定下《上海》这个书名。由此可见,在小说创作前期,横光利一其实并没有打算将自己上海之行的所见所感如实写成小说,他所想创造的是一个符号化的奇妙城市,而上海只是它的原型。此外,横光利一定下《上海》这一题目的前一年正是日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九一八事变的时间,这起事变是日军正式侵华的开端,而自1932 年1 月开始,日军也对中国其他地区逐步展开了侵略行为。横光利一在此时将这部政治意味浓厚的非写实小说定名为《上海》,不难看出其中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性,而且这与他此时撰写文章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美化的行为相互呼应。
由于横光利一完全私人化的上海体验和小说创作过程中的非写实计划,《上海》这部诞生在特殊时期的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注定不会是1928 年真实的上海,这也就意味着在这部名为《上海》 的小说里,必然存在着大量对真实上海的误释。
二、横光利一《上海》 中的东方想象
根据横光利一的说法,在《上海》的写作准备阶段,他看了四五百种有关上海的资料和书籍,且写作的时间更是长达四年之久,花费的心思相当多。事实上,在书中确实可以看到横光利一对上海标志性建筑、大小各条街道的还原,但整部作品刻画的上海相比真实的上海却让中国读者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这是因为《上海》一书归根到底还是横光利一的一次“东方想象”,上海的城市景象、民众生活和革命活动都因横光利一的个人视野而在书中产生了变形。
首先,横光利一对于近代上海的城市景象进行了带有偏见的描写。与同时代同为新感觉派文学家的中国作家穆时英笔下充满了现代性的上海不同的是,横光利一更侧重描写的是上海的混乱肮脏。书中的人物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地,映入眼帘的总有一条臭水沟,而横光利一也总是不吝笔墨地描绘臭水沟里的肮脏景象:“在她正看着的臭水沟上面,冒出泡来的黑色垃圾不断地汇集起来,竟然筑起了一个小岛。小岛中间,鸡雏黄色的尸骸和死猫膨胀的尸骸聚首一处”、“从船上卸到岸上的菜叶撒得到处都是,舷侧裂开缝来的破败的小船像皮肤一样长出了白菌。婴儿的尸体从积留在龙骨的一动不动的水泡中伸出一只腿来”、“臭水沟岸边,黑色的朽木桩子伫立在黑色的泡沫中”……而对于中国传统的街道及建筑,横光利一也是更强调它们的破旧,如“破败坍塌的砖砌的街道”,还有上海的旧弄堂,横光对其的描述是:“一条由歪歪斜斜的砖砌柱子支撑起来的长长的弄堂”。行走在上海街道上的人们看到的是“挂着鱼膘、滴着血的鲤鱼肉段”、堆到马路上的芒果和香蕉和无数头被剥了皮的猪,这些货物被作者堆放在读者眼前,给人以混乱无序的感觉,这些就是横光利一笔下近代上海街道上最常见的事物。与上海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装载着大理石的小船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由波浪推拥着在左旋右转”、“盛开的郁金香围成一个圆圈的草坪”、“舞厅周围,建筑物鳞次栉比”,而外国人办理事务的场所更是繁华得如同现代都市:“一走进商业中心地带,便可看到外汇经纪人的马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并排送礼的银行疾驶”、“大厅里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横光利一将贫民窟与租界两个区域的日常景象分开叙述,导致作品对上海的描绘存在一种强烈的分裂感。而从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出,横光利一制造这种分裂感并不是为了对这种现象加以批评,而是让人感到上海这个城市破败不堪的一面全都来自它自身,而外国人的到来才使得它拥有了一些难得的现代性。
其次,横光利一对于近代上海的民众生活也带有明显的贬低色彩。小说中登场的主要人物除去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女共产党芳秋兰以外,便都是外国人。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打算,或在上海这座城市中追名逐利、或在这里谈情说爱。而在横光利一笔下,本应是上海中最为重要的上海人却成了前者们发生故事的背景板。小说中对中国人的描述很多,男女老少均有出场,但他们都如同行尸走肉,过着死气沉沉、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小孩硬把自己的身高拉长到案桌的高度,把鼻子凑到那微微颤抖的淡黄色猪油上,一直死死地盯望着”、“从摆满油光光的猪肉、鸡肉的弄堂口上踉踉跄跄地走出几个抽鸦片抽得脸色灰白、目光痴呆的女人”。除去他们的麻木冷漠,横光利一还着重展现了中国人的丑陋与罪恶:“抬头望去,只见一张张默默无声的面孔从紧逼在眼前的四面墙壁的窗户中向外窥探着”,而街角或是柱子上总能看到中国人在闭着眼睛抽鸦片,俨然一副堕落的姿态。至于被作为美好事物加以描述的女共产党芳秋兰,横光利一对她过于梦幻的塑造手法使得她的形象与整个上海格格不入。一方面,作者显然是将芳秋兰当作美的化身来描写的。她刚出现于舞厅,其美貌便吸引了甲谷的注意力:“她那紧闭起来的嘴角、又大又黑的眼睛、鹭水式的刘海、蝴蝶形的首饰、银灰色的上衣和裙子”,以至于甲谷在她离开舞厅时抛弃了正在追求的宫子而选择乘坐黄包车追赶她。在负伤被参木救走的第二天,芳秋兰依然要换上古式湖色皮袄、拿着扇子坐在紫檀木椅子上与参木客气地聊天,显现出和那些遭受了侵害后走向麻木堕落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模样。横光利一对芳秋兰样貌、装扮的描写都在极力强调她的中国古典美,可见芳秋兰身上凝结着日本文人对古代中国的美好想象。而与之形成矛盾的是她在书中一直充当着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角色。尽管作者努力展现了芳秋兰的聪明坚定,但这一形象却由于其梦幻性而缺少应有的革命性,几乎没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在芳秋兰与参木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将芳秋兰塑造成了一个需要被参木救赎的对象。在故事一开始,几乎所有主要人物都知道芳秋兰的共产党身份,她之所以能领导工人运动,仿佛是因为这些外国人故意饶过她。而她前两次组织工人运动都是以被参木救下为结束,后又在最后一次运动中下落不明。在和参木就国家、革命等问题进行辩论时,她虽然勉强占了上风,但作者却有意强调她的“胜利”是感到失望的参木放弃与她争论才得来的。总的来说,这样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显然不过是横光利一“东方幻想”的一个表现而已。
最后,作为工人运动领导者的芳秋兰这一形象的不切实际性也反映出了横光利一对于五卅运动这一革命运动的错误理解,这更进一步地说明了他对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错误认识。五卅运动的发起要追溯到1925 年1 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的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并决定要在之后的革命运动中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而同年2 月起,上海22 家日商纱厂有近4 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压榨中国工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为了支持工人运动,中共中央甚至组织了这次罢工运动的委员会。随着运动的不断壮大,加上国外警察当街射杀参加运动的中国群众的行为激起了民愤,上海全市宣布罢岗,这场工人运动进一步演变成了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然而,这样一场富有历史意义的正义运动到了横光利一笔下却成了一场毫无理智可言的暴动,积极参与到运动当中去的中国人都被他称为“失业者”、“无赖之徒”。在主人公参木眼中,这场中国工人发起的革命运动只不过是他们因为金钱得不到满足而展开的一系列暴力行为,其目的不过是索要更多的工资。在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参木只是担心着日本工厂的运作和经济,而当这场运动愈发声势浩大的时候,他只觉得“一场中国史无前例的大罢工便像不知从何处蔓延开来的地方病一样,越来越大地张开了它那奇异的翅膀”。日本工厂打死的那名中国工人点燃了中国工人们的愤怒、成了运动的导火索,然而参木等人却觉得是有人在利用这个被打死的工人对中国群众进行煽动。书中有大量对群众发起运动的描写,然而这些描写都是在强调群众的非理性。例如,在一次运动中被挤入商店门口的参木透过商店上方的旋转窗看到了外面群众运动的景象,在他眼中,“骚乱的群众倒映在那窗玻璃上,那就像不见天空的海底一样。无数个肩膀在腿下边。他们一面勾画出险些坠落下来的奇异的悬垂形天盖,一面像水草一样,向前流淌又折返回来,折返回来又打旋,摇晃不止”。借着这类描写,横光利一将自发参与到革命运动中的群众描绘成了墙头草一样的存在,极大地消减了群众运动的正义性与革命性。而在和芳秋兰就运动问题产生辩论时,参木反复强调中国群众的这场运动看似是在打击日本的资产阶级,但实际上却是在伤害日本的无产阶级,这种混淆视听、转嫁矛盾的话语并不是参木故意找来的借口,而是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打从心里就是如此认为的。这种可笑的强盗逻辑却被横光利一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口吻反复在书中提及,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无视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伤痛与折磨、只知道一味地为自己国家损失的经济利益喊冤。这种既定立场的存在使得横光利一显然不可能对五卅运动有深刻的认识,这也就进一步导致了横光对近代上海乃至中国都产生了严重的错误认识。
在《上海》一书中,横光在城市景象、民众生活和革命活动三个方面对上海进行了错误的书写。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带有他者偏见色彩的上海的同时,彼此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横光对五卅运动的错误认识暴露了他对近代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误判,而这种误判表现在文本上,就是《上海》中对上海的城市景象和民众生活的贬低性描写。
三、横光利一《上海》 中的身份认同
既定立场的存在天然导致了横光利一无法理解被殖民的中国人民的痛苦,这呈现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了他对上海的误写。但事实上,在作品中,横光利一也表现出了他在立场问题上的思考与动摇,这主要经由主人公参木得以体现。书中参木对自身立场问题的思考,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他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
主人公参木在书中一直是一个城市漫游者的形象,他的这个漫游者身份一方面有利于作者借他的双眼来观察整个近代上海社会,另一方面有利于展现参木对自身摇摆不定的矛盾认知,这一点呈现在读者面前便是他自我分裂般的人物性格。在书中,参木的自我分裂主要体现在他在感情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上。
在感情问题的处理上,参木一直是优柔寡断的态度。参木与竞子、阿杉和芳秋兰的三段并行感情构成了他的整个爱情故事线,这也是《上海》这部作品在明面上的主线。参木最早爱上的女性——竞子在作品中其实从来没有正式登场过,但由于参木自始至终都在强调她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存在一直贯穿了整部作品。竞子是参木好友甲谷的妹妹,她在日本早已组建了家庭。故事一开始,参木就从好友口中得知了竞子丈夫病危的消息,于是尚未熄灭的爱火时不时地在他心中复燃。每当参木为其他女性动心的时候,竞子便毫无预兆地出现在他的脑海,而当他在感情问题中受挫时,竞子这一缥缈的女性形象便成了他用以慰藉心灵的避风港。参木在竞子身上的摇摆不定主要体现在每当参木想到自己与竞子在一起的前提是她丈夫的死亡时,传统道德意识极强的他就会开始按捺自己内心对竞子的情感。另外,他虽然经常强调着竞子对自己难以取代的意义,但事实上只有在他逃避其他感情问题时才会自我说服般地回忆竞子,这也说明了他对竞子的感情并不是那么坚定不移。
阿杉是参木来到上海后在常去的洗浴中心遇到的女性,和象征着纯洁缥缈的竞子不同,由于洗浴中心半色情的服务性质,参木虽然对阿杉表现得很尊重,但内心其实也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感情的备选对象。因此,在明白阿杉对自己的情感后,参木既没有选择坦率地接受她,也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她,而是一边以自己所谓的尊重为借口招惹阿杉、一边又表现出对阿杉的忽视。他以阿杉为借口挑衅洗浴中心泼辣的老板娘,直接导致了阿杉被辞退,但是他却一直将责任全部推卸到老板娘的嫉妒上、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寻找借口。之后参木虽然表示自己愿意让阿杉在自己家暂住,但是当好友甲谷强暴了阿杉之后,知道内情的他又丝毫没有替阿杉主持公道的打算,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纵容态度又促使阿杉沦落贫民窟、后又堕落为妓女。在小说最后,与芳秋兰彻底告别的参木漫游在上海街道,在被追杀的时候选择向住在贫民窟的阿杉求助,但依旧没有向阿杉作出爱情的承诺。
真正动摇参木对竞子的思念的女性是女共产党芳秋兰。对于参木而言,她是传统中国美的象征、还是亟待他拯救的对象。他难以自拔地被这个优雅聪明、温柔可爱的中国女性吸引,但是每当两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时,参木便会感到自己对芳秋兰的情感在慢慢消散。因为在他眼中,芳秋兰就像是个无理取闹、被环境迷昏了头脑的人,她参与革命运动的行为是阻隔两人感情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参木又希望芳秋兰能够将自己从缥缈的竞子和堕落的阿杉中拯救出来,他的这种不切实际又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他在感情问题上摇摆不定的一大表现。
纵观参木的这三段感情,不难发现对于他而言,女性或者说爱情只不过是他陷入迷茫痛苦时聊以纾解负面情感的工具而已,他对爱情的追求归根到底只是排解忧愁的途径。这三段情感勾勒出的参木形象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缺乏立场的流浪者姿态,而他对这三位女性的不同态度又与他在政治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一对应。
首先,参木对竞子的情感其实暗含了他对日本本土盛行的“亚细亚主义”的看法。尽管由于近代世界各国复杂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亚细亚主义”也具有其复杂性。但究其本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其实是日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美化,就像书中最为推行“亚细亚主义”的山口所说的那样,在他们眼中,“惟有日本军国主义才是拯救东洋的惟一武器”。当中国的李英朴针对“二十一条”对日本人进行指责时,山口却觉得他只是在无理取闹,甚至傲慢地反驳:“只有中国和印度都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亚洲才能联合起来”。对于“亚细亚主义”,主人公参木并没有像山口那样表示推崇,也没有像好友甲谷那样表现出明确的倾向,但是每当他在上海遇到挫折时,他就会回想起家乡的美好以及象征着美好回忆的竞子,并在“亚细亚主义”的问题上一步步表现出妥协乃至认同的态度。例如,明明是日本银行出现的贪污现象让他感到不满以至于被辞退,但是参木却借着回忆家乡的美好转而将问题推到上海这个“恶之都”上。同时,正如参木意识到自己和竞子的爱情是要建立在竞子丈夫的死亡的基础上那样,参木的传统道德意识也让他对“亚细亚主义”推行过程中产生的悲剧感到同情和痛苦,但是显然参木的这份同情与痛苦更多的是给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本人的——当他和好友甲谷在街道上看到一具中国人的尸体时,参木对于甲谷轻佻的态度没有做出任何批判,他心中类似于同情的情感也稍纵即逝。
其次,对于在“亚细亚主义”推行过程中遭遇不幸的日本人,参木在报以强烈的同情之情时,也在不停地将原因推脱到其他事物上,这与他对阿杉的感情有着共通之处。阿杉是被特殊时代命运裹挟入悲剧中的日本底层人物的代表,她每天都在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到悲伤,但是却始终看不明白自己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哪里,甚至对于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之地的罪魁祸首还报以期待。小说最后,当参木来到自己家寻求避难时,阿杉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沦为妓女后房间肮脏不堪,于是想尽办法不让他点灯。在参木盖着房间里的被子熟睡后,阿杉摸黑开始收拾混乱的房间,将苏州嫖客给自己的装饰品塞进了柜子里,最后又小心翼翼地靠在参木胸口、寻求安慰。这一结局显示出了阿杉的可悲可笑:导致自己沦为妓女的参木被她当作奢望中的依靠,而中国嫖客却仿佛成了她一切悲剧命运的原因;面对这个罪魁祸首,她却连自己悲惨的一面都不敢展露出来。
最后,参木与芳秋兰的情感拉扯则对应了他与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博弈。尽管参木并没有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但是他对这两者所做出的思考显然带有偏见。在他看来,中国群众高举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工人运动其实质是想要借着马克思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在他的思考中,马克思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的保护盾,他的这一判断恰恰说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上的误解。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他和芳秋兰永远都无法在中国工人运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而当芳秋兰强调中国工人作为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运动的正当性时,参木却将“亚细亚主义”下受到伤害的日本底层阶级拉出来作为挡箭牌,甚至堂而皇之地将外来殖民者称作中国发展的必要推动力。当芳秋兰立场坚定地回应他“这是我们必须经常思考的中国问题之一。不过,同时这种问题也是一个无须由作为各国资产阶级垃圾箱的公共租界的人们思考的问题”时,参木却表现出被冒犯的姿态,认为芳秋兰是在嘲笑自己的好意,于是单方面地宣布两人关系的断绝。
参木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出的肤浅、片面其实主要还是建立在他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上,再加上他本性懦弱、缺乏判断力,这就使他很多自以为是的观点显得十分可笑。他将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底层阶级制造出的伤害归因到中国工人运动上,无视外来殖民者给中国带来的摧残、傲慢地把侵略者美化成中国的救世主,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心态。同时,参木对政治问题做出的最终判断,其实是他摆脱了原先的主体分裂、确立了其身份认同的证明——在经历了传统道德观带来的自我挣扎后,他还是回归了日本“东亚大共荣”的主流思想的怀抱;而作为作者的发言人,他做出的最终选择实质上也反映出了作者横光利一在这一时期逐渐右倾的思想和畸形的中国观。
在上海之行前夕,横光利一针对日本文坛上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写下了《新感觉派与共产主义文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横光利一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认为文学可以保持其独立性。但是在上海之行后,他做出了右倾的选择,甚至在日本正式侵略中国之后,站在了侵略者的立场上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毋庸置疑,横光利一的这一思想转变与他在上海的所见所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在这一期间的所有思想历程也都借由《上海》主人公参木的身份认同呈现在了中外读者面前。正如参木说“我的身体乃是领土”一样,在横光利一以他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审视上海时,这座城市便成了他眼中需要被外来殖民者“拯救”的“恶之都”。
四、结语
由于近代中国的悲惨遭遇,上海成了供外国进行东方想象和他者凝视的对象,进而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这导致这座城市和城市原住民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外来摧残被怀着狭隘民族主义的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不断淡化。横光利一的《上海》一作无疑是这类文学创作中的一大代表。在描绘心中的“上海”这一文化符号的过程中,横光利一也完成了他自身主体由分裂到认同的任务。在畸形扭曲的殖民思想的影响下,他对于中国人民不幸痛苦的轻描淡写、对于日本殖民者傲慢行为的逐步美化都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追求的身份认同不过是一种狂妄的种族优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