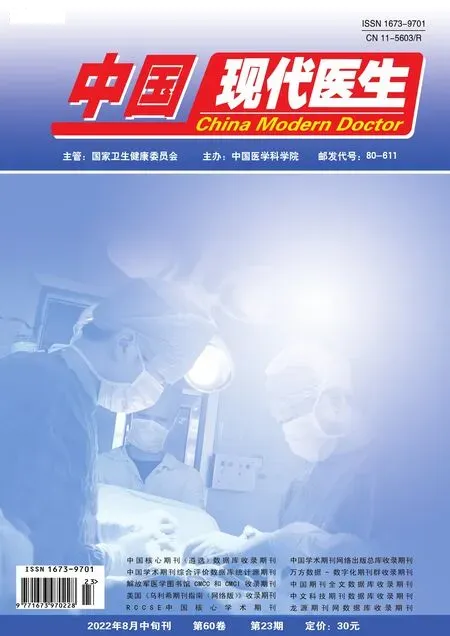托珠单抗治疗大动脉炎不良反应的临床分析
王莉莎 徐 锌 曲建昌 梁艳玲 赵红玉 王 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 医院内分泌风湿免疫科,北京 100039
大动脉炎(Takayasu’s arteritis,TA)是一种主要累及大动脉及其分支的慢性系统性血管炎,包括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肺动脉和冠状动脉、肾动脉等,引起管壁增厚、管腔狭窄或闭塞和动脉瘤的形成。TA 的治疗多以糖皮质激素为主,但糖皮质激素减量或停用时病情易出现复发,而传统免疫抑制剂(如环磷酰胺、甲氨蝶呤)治疗对于年轻女性生殖毒性的影响使其不能成为理想的治疗方案。多项研究发现,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6 在大动脉炎的发病及疾病活动中呈正相关。托珠单抗(tocilizumab,TCZ)是一种人源性IL-6 受体(IL-6R)抗体,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带来了确切的疗效,且为难治性大动脉炎的治疗带来了新的选择。新的治疗选择在带来疗效的同时仍应警惕不良反应的发生,本研究旨在探讨托珠单抗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自2014 年6 月至2020 年12 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 医院内分泌风湿免疫科门诊治疗的13例大动脉炎活动期患者,女12 例,男1 例,年龄17~37 岁,平均(24.30±5.75)岁,病程1~10 年,平均(3.84±2.67)年。纳入标准:①满足ACR1990 年制定美国风湿病学学会TA 的分类标准,血管超声和CTA 检查符合典型的大动脉炎血管受累的表现。②均曾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如来氟米特、环磷酰胺、环孢素、硫唑嘌呤、吗替麦考酚酯等)治疗,或因激素减量后出现疾病活动,或因药物不良反应等换用了托珠单抗治疗。排除标准:①急性或慢性活动性感染者;②心力衰竭者;③伴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等者;④妊娠期、哺乳期及近期计划受孕的女性者;⑤有肿瘤或结核病史(结核T-Spot 试验阳性或影像学阳性)者;⑥白细胞计数减少、严重肝肾功能不良者。本研究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2015 伦理第2号),且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托珠单抗注射液每4 周给药1 次,静脉滴注,每次静滴时间持续1h 以上,2 例患者每次4mg/kg,11 例患者每次8mg/kg,托珠单抗(雅美罗,日本罗氏制药批号B2117B02)治疗3~7 次。
1.3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基线期、第4、8、12 周患者血常规、谷丙转氨酶(liver transaminase)、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超敏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protein,hs-CRP)及血管超声进展情况,根据患者疾病改善情况对是否继续进行托珠单抗治疗进行评估,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2 结果
2.1 疗效评价
用来评价大动脉炎治疗疗效的指标主要是ESR、hs-CRP 等炎性指标,因此,在TCZ 治疗第4、8、12 周化验了患者的ESR、hs-CRP,12 周复查血管超声、记录患者头晕、头痛症状、血压均较基线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对基线期及治疗后12 周炎症指标进行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见表1。

表1 TCZ 治疗12 周前后炎性指标变化()
2.2 不良反应
1 例患者输注TCZ(8mg/kg)第1 次后1 周出现白细胞、粒细胞减少,谷丙转氨酶轻度升高,予保肝、升白胺治疗后继续第二次、第三输注,患者白细胞恢复正常,粒细胞轻度降低,谷丙转氨酶继续升高。另1 例患者在第一次输注TCZ(8mg/kg)后第4 天出现荨麻疹样皮疹,程度较轻;第2 次输注后皮疹加重为全身性斑丘疹,口服氯雷他定片后缓解。第3 例患者在第一次输注TCZ(8mg/kg)后第3~4 天出现颈部疼痛,疼痛呈持续性,较剧烈,夜间可影响睡眠,需口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对症治疗后疼痛才可缓解,持续约3d 后缓解,不影响下一次输注。第二次输注后出现腹部疼痛,为间断性,在第2 次输注后第3 天出现,持续约3d 左右缓解,未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对症治疗。
上述3 例患者最短随访6 个月,最长随访4 年,患者的疾病活动度监测包括血常规、谷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transaminase,ALT)、谷草氨酰胺转肽酶(glutamyl transpeptidase,GGT)、ESR和hs-CRP、治疗前后血管超声(3 个月至半年1 次)。3 例患者用TCZ 治疗3 次后ESR、hs-CRP 均很快降至正常范围。
3 例患者中1 例在第3 次输注后因转氨酶持续升高而停用了TCZ 治疗。1 例患者荨麻疹经抗过敏治疗后好转,第2 次、第3 次用药无不适症状。1 例颈部疼痛缓解后在第2 次输注后第3 天出现轻度腹痛,自行缓解,第3 次输注后无不良反应,此后完成7次TCZ 输注而停用,未再次出现颈部疼痛及腹痛。随访3 年后停用激素和吗替麦考酚酯,继续随访1年患者炎性反应指标及血管超声均在正常范围。
3 讨论
大动脉炎是主要累及生育期女性的一类血管炎,目前治疗尚无统一标准。激素是最常用的药物,但激素单药治疗有效性不到50%,且长期应用激素治疗也会带来诸多严重不良反应,包括白内障、感染、糖尿病、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等,且高达50%~80%的患者在激素减量过程中出现复发。环磷酰胺联合激素治疗虽然能有效抑制疾病的发展,但环磷酰胺的生殖毒性及药物累积量依赖的不良反应,限制了环磷酰胺的应用。近年来托珠单抗在早期和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明显的疗效。多项研究证实,大动脉炎患者血清中IL-6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多项临床研究也表明,托珠单抗能够有效治疗大动脉炎。本研究也证实了托珠单抗在大动脉炎治疗中的疗效,患者的血管超声持续无明显进展,且炎症指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下降,患者的临床症状基本完全缓解。在取得显著临床疗效的同时,其带来的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受到临床工作者的关注。托珠单抗常见的不良反应主要有皮肤、软组织感染、肝损伤、高胆固醇血症、嗜中性粒细胞减少及过敏反应,少数病例还可以出现疼痛反应。
本文中报道中1 例患者应用托珠单抗后出现肝功能损害,托珠单抗引起肝损害的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其抑制IL-6 信号通路有关。IL-6 可参与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当托珠单抗与其他肝毒性药物如甲氨蝶呤、来氟米特联用时,肝脏不良反应发生频率和程度会增加。有研究显示,约10%~40%的患者在接受托珠单抗治疗过程中会出现血清氨基转移酶水平的升高。血清ALT 升高一般可达正常上线的1~3 倍,在下一次输注前开始逐渐降低,有些情况下1%~2%患者的ALT 可升高到正常上限的5 倍以上,需立即停药。而ALT 的升高与药物剂量有一定的关系,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出现肝衰竭和肝萎缩,需要肝移植甚至造成死亡。有报道TA 患者在接受8mg/kg 托珠单抗治疗3 个月后出现严重肝炎,停药10 周后肝酶恢复正常,再次输注1 周后出现进展性黄疸,诊断为急性肝炎,病理结果为肝细胞球囊样变性,局灶性胆汁淤积和肝细胞坏死。本文出现肝损伤的患者应用剂量也是 8mg/kg,而应用4mg/kg 输注的患者未发现肝酶异常。因此,TCZ 应用期间应重视肝酶指标的复查,必要时减少用药剂量,有可能避免肝损伤的发生。
在托珠单抗治疗TA 的报道中,可出现短暂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副作用,多发生在用药后8 周内,而本研究中第1 例患者除出现谷丙转氨酶异常外,还伴有白细胞、粒细胞减少。发生在第1 次输注后1 周,第2 次及第3 次输注后复查白细胞及粒细胞均在正常范围,印证了托珠单抗引起粒细胞减少的短暂性病程,该患者在第3 次用药后持续肝酶异常而停药。
第2 例患者在托珠单抗输注后第4 天出现荨麻疹样皮疹,考虑为该药引起的过敏反应。有研究显示,接受托珠单抗治疗的患者中大约0.8%~2.0%会出现托珠单抗抗体,并逐渐出现中和性抗体,一般在第2 次至第4 次静脉输注时出现,与剂量无关,甚至有因过敏反应导致死亡的报道。因此,建议在应用托珠单抗时出现全身红斑、皮疹和荨麻疹时应立即停药,当患者出现严重超敏或过敏反应时,应停药并禁止再次使用。该患者输注2 次后应用抗组胺类药物治疗后迅速缓解,间隔1 个月后完成第3次输注,仅出现轻度皮肤瘙痒,未再次出现荨麻疹或斑丘疹,复查各项指标仍在正常范围。
第3 例患者为左锁骨下动脉、双肾动脉受累,经过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但激素减量过程中仍有炎性反应指标升高,加用托珠单抗治疗,在用药前无颈部、腹部疼痛不适症状。应用TCZ 后出现颈部疼痛,而颈部疼痛可能是大动脉炎活动的临床症状,多是由于受累动脉的炎性反应活动导致局部产生相应的症状,且疼痛会逐渐减轻。该患者在用药前无类似症状,且受累动脉为左锁骨下动脉,疼痛部位不符合大动脉炎活动所致,因此,认为该颈部疼痛是输注TCZ,而非大动脉炎活动引起。在RA 患者的治疗中,也有类似报道。Uda 等发现在接受TCZ 治疗的79 例RA 患者中,有36.7%的患者出现了TCZ 输注后的关节疼痛,而新出现的关节疼痛与常见的类风湿关节炎的受累部位,关节表现等均不同,将其命名为“非风湿性关节痛”。
经典信号通路中,IL-6 与膜结合IL-6 受体结合后经由信号受体蛋白gp130 发挥抗炎作用。只有少数细胞表达膜结合IL-6 受体,而所有细胞表面都表达gp130,但仅表达gp130 的细胞是不能单独对IL-6 产生应答,它们只能对IL-6 与天然可溶性IL-6受体结合的复合物产生应答。IL-6 的再生和抗炎作用是通过经典信号通路产生的,而致炎作用是通过可溶性受体信号通路产生。TCZ 是以剂量依赖的模式与可溶性IL-6 受体结合,当其血药浓度达到4mg/ml 时竞争性抑制IL-6 与可溶性受体结合,从而阻断了促炎的反式通路,发挥抗炎作用。在最初几次输注时,TCZ 的血药浓度未达到稳定的治疗水平,致使IL-6 可以继续通过其与可溶性受体结合发挥致炎作用,甚至可通过复杂的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导致细胞因子失衡,IL-6 水平进一步升高,从而诱导疼痛反应的发生,这也就能解释该例患者的疼痛发生在最初2 次的输注过程中,而在此后未再次发生。在RA 治疗中发生的“非风湿性疼痛”的患者其血清IL-6 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疼痛的患者组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本文在治疗大动脉患者的过程中观察到了TCZ对大动脉炎患者的确切治疗效果及发生的少见不良反应,为大动脉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方向,为多数年轻患者提供除了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以外的选项。我们总结的病例数有限,今后仍需扩大病例数及深入基础研究来探讨其可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