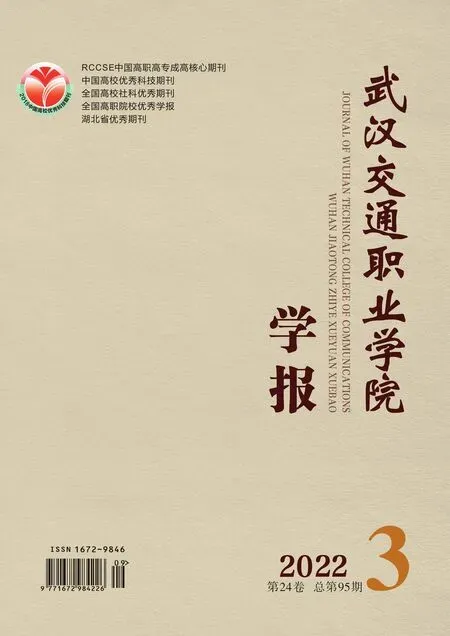欺诈投保中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适用困境及化解
姜智夫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1100)
一、问题的提出
(一)撤销权在现行法框架下的适用模糊
欺诈投保,意指投保人在故意的情形下,违反了保险合同法所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并通过积极或消极的方式使保险人陷入认识错误,进而对保险人承保的意愿与保险费率的确定造成了实质性影响的行为。与保险欺诈这一更为广义的概念不同,欺诈投保更倾向于规制保险合同成立过程中投保人对最大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违背的行为。然而前者可能会涉及保险金诈骗、虚构保险事故等更广泛的情形[1]59。对于投保人刻意隐瞒相关事实的欺诈行为,在现行法框架下主要有两条规制的道路,包括《保险法》第16条所赋予保险人的法定合同解除权和《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撤销权。由于《保险法》规定中的法定解除权与《民法典》规定的撤销权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相当的重合性,使得二者呈现出了“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表征,进而出现了法定解除权排除撤销权适用的“排除说”流派观点,与二者可以同时适用的“选择说”观点针锋相对。自“不可抗辩”条款于2009年引入以来,《保险法》与司法解释从未能对这两项权利的适用关系予以明确界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曾尝试于2013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第9条承认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选择适用,并于2015年《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第10条向社会大众征集两项权利选择适用还是排除适用的意见,但均因为争议过大而最终不了了之。由是,在欺诈投保案件中,撤销权可否适用成为了一个持续争议的问题。现行法的供给不足使得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无法清晰界分,更是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裁判不一的困窘局面。
(二)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分歧
理论上的模糊不清导致实践中司法裁判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标准,进而加剧了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分歧。曾有文章对2014年至2017年涉及欺诈投保撤销权司法裁判案例的观点立场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裁判案例排除了撤销权的适用[2]。为了进一步探讨近年来实践中法院对该问题的态度,笔者在北大法宝平台上以“欺诈”“解除合同”“撤销”为关键词,将法律依据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并将裁判文书设定为“判决书”,将审结期限设定为2018年之后,截至2022年8月6日,共搜得裁判文书281篇。经逐篇筛选,仅选择存在“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适用争议的裁判文书,并排除了基于集体诉讼造成的重复文书,共获得有效分析样本110例。其中,法院支持了撤销权适用可能性的案例有32例,占总案例数的29.09%。为了进一步观察对比近年来各省法院对撤销权适用的态度,笔者分别整理了支持与反对撤销权适用的裁判地域分布表,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 支持撤销权适用的裁判地域分布

表2 反对撤销权适用的裁判地域分布
由表1与表2可见,尽管2018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支持撤销权适用的占比不足1/3,但是在不同的省份中争议仍然很大。一些省份如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反对撤销权适用的案件数量与支持撤销权适用的案件数量近乎持平。但是在 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反对撤销权适用的意见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地位。由于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因此在同一省份中反对过撤销权适用的法院也完全有可能在另一份判决中转为支持撤销权的适用。这种不确定性也必然会影响后续欺诈投保案件中当事人对自身行为将导致的法律后果的预估。这会增加商事交易中的不稳定性,对发展稳定良好的保险行业秩序也会造成阻碍。另一方面,笔者将2018~2022年间关于撤销权适用与否的裁判制成如图1所示时间分布图。由图1可见,自2018年来,有关撤销权可否适用的案件在总数上呈现下降的态势。尽管反对撤销权适用的案件数量占比更高,但是支持撤销权适用的裁判每年都有出现。这体现出支持撤销权适用的裁判观点在实践中具有着一定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图1 2018~2022年间涉撤销权适用与否问题裁判数量
除此之外,在对各裁判案件中法院的裁判理由进行分析整理后,笔者发现在32例支持撤销权适用的案件中,仅有9例保险人最终成功适用撤销权,占比28.13%。阻碍撤销权成功适用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保险人自身未能举证证明投保人存在欺诈,共有16例案件。其二是保险人未提出撤销合同的诉讼请求,共有4例案件。剩下的案件中法院尽管也承认了撤销权适用的可能性,但以诸如“保险人已经适用了法定解除权”等其他无关紧要的理由阻碍了撤销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在反对撤销权适用的78例案件中,有46例案件的判决书未解释说明撤销权与解除权的关系而直接应用了《保险法》的解除权予以裁判,占比58.97%。对于剩下的32例含有解释论证的裁判案件,笔者制成如图2所示柱状图对法院排除撤销权适用的主要原因予以分析。由图2可见,大多数法院以“一般法优于特别法”为由,认为属于特别法的解除权排除了作为一般法的撤销权适用。少部分法院以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和公平原则等出发,认为撤销权较长的除斥期间会造成对两年不可抗辩期限的规避且保险人自身的审查义务不应当被降低。法院对撤销权适用与否的争议甚至还体现在了同一案件中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实证分析的案件范围中,有两例案件一审法院支持了撤销权的适用,但是被二审法院改判否定了撤销权的适用。这也更加体现了各省法院内部对该问题的矛盾态度。

图2 排除撤销权适用的论证理由及案件数量
主张排除说的学者认为《保险法》第16条第
总体来看,尽管撤销权在欺诈投保案件中适用与否这一问题在实务中存在持续的争议,但是排除撤销权适用的观点一直占据着实务中的主流地位。然而,在支持撤销权适用的裁判中,一些法院也列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点,使得这一问题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在福建省法院裁判的一起案例中,法官对撤销权与解除权二者“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提出了质疑。该法官认为,撤销权与解除权的构成要件并不是完全契合的,比如欺诈的撤销权以投保人故意实施了欺诈行为导致保险人陷入错误认识为条件,而解除权以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条件。二者对投保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要求并不一致①。在吉林省法院裁判的一起案例中,法官认为虽然《保险法》是《合同法》的特别法,但是《保险法》中只规定了合同的解除权,而没有规定撤销权。因此,解除权与撤销权的适用不属于同一事项,二者的适用不存在法律冲突②。在河北省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裁判的一起案件中,法官认为法律应当赋予欺诈投保案件中的保险人救济选择权。通过认可除斥期间更长的撤销权的适用,法律才能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欺诈的恶意主体予以惩罚,进而维护诚实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③。可见,支持撤销权适用的立场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撤销权可否适用这一问题,我们在关注裁判数量这一表面现象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对两种立场的理论依据进行分析。基于此,下文拟对“不可抗辩”条款引入保险法后在欺诈投保案件中应否适用撤销权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适用的理论争议
欺诈投保中保险人能否适用撤销权一问题在学理上的争议亦是颇为激烈。目前学理上就此问题的主流观点包括否认撤销权应用的“排除说”和肯定撤销权可以适用的“选择说”[3]。除此之外,亦有文章提出了“折衷说”的主张,认为撤销权与《保险法》规定的法定撤销权仅在构成欺诈情况下可以重复适用[4]。进而目前学界对保险人的撤销权适用问题呈现了三元进路的态势。
(一)排除说
二款对法定解除权的规定排除了《民法典》或《合同法》中规定的撤销权的应用。此类观点称法定解除权和撤销权二者在立法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亦具有着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特征[5]120。具体而言,二者均具有保护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立法目的,并分别体现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原则。从构成要件上看,在法律的适用方面,一般法构成要件的涵摄范围应当覆盖乃至超越特别法构成要件的涵摄范围[6]。在这个维度上,撤销权的行使事由除了包括投保人故意欺诈之外,还包括胁迫、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这几种情形。然而《保险法》框架下法定解除权的行使仅涵盖了投保人故意欺诈投保与重大过失未能如实告知这两种情形,分别对应了撤销权中的欺诈和重大误解的民事法律行为。故此撤销权的涵摄范围完全超过了法定解除权的射程区域,二者具有“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之关系,进而作为特别法的法定解除权排除了作为一般法的撤销权之适用。
在法律效果上看,支持排除说的学者认为,在投保人故意欺诈的情况下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法律效果相似,均为使合同关系消灭,而仅仅在保险人是否需要退还保费的问题上出现了差异[5]122。《保险法》第16条所规定合同法定解除权在法律效果上应当同属于一般合同解除权效果的序列,即合同的权利义务就此终止。在行使解除权后,保险人依然可以依据保险合同向投保人主张违约责任。但若行使撤销权,保险人主要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寻求救济。尽管两项权利行使的法律效果存在细微差异,却并不会动摇二者之间的排除适用关系。从法律效果上来看,法定解除权所给予的救济更为充分,更有利于弥补保险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同意投保所遭受的损失。基于民事赔偿的填平原则,法定解除权的适用显然排除了撤销权的适用空间。此外,如果承认了除斥期间更长的撤销权的适用,则无疑会对现行保险法的体系架构造成破坏,导致《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被架空和“不可抗辩”条款对保险人行权期限的限制被规避等问题的出现[1]64。因此《保险法》对法定解除权的规定排除了撤销权的适用。
(二)选择说
与排除说相反,支持选择说的学者认为在欺诈投保的案件中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并未排除撤销权的适用。第一,二者在立法意旨上存在差异,法定解除权旨在保障如实告知义务的落实,而撤销权旨在保护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自由真实。在构成要件上,针对欺诈行为的撤销权仅以故意为要件,而法定解除权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为构成要件。此外,撤销权与合同解除权本就分属于两项性质不同的权利,在法律效果上也具有差异。撤销权侧重于对原有法律关系的恢复,而合同解除权则侧重于对守约方所受损失的弥补。因此,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并非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也并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冲突[7]。第二,排除撤销权的适用意味着保险人必须在合同成立两年内发现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对于保险人施加的审查义务过于严苛[8],这迫使保险公司加大对投保人参保时的审查力度,无疑会为保险公司的审查造成更大的经济负担,与保险公司现行的以保险事故发生后进行倒查为主的商业实践相悖。加之在电子合同日渐普及的当下,剥夺保险人撤销权的救济途径不利于保险业的飞速发展。第三,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应当以公平地分配风险为目标。然而投保人的欺诈行为会事实上增加整体的风险程度,进而诱使保险人提高产品的保险费率并将风险转嫁给全体投保人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发生[9]。第四点缘由以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不当行为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认为撤销权的排除适用助长了恶意投保人投机取巧、规避法律的心理。我国“不可抗辩”条款设定的2年期限导致法定解除权不足以震慑恶意欺诈的行为[10]。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地位考虑,排除撤销权的适用而对恶意投保人予以倾斜保护并不合适,反而会有破坏保险业市场最大诚信原则的贯彻,造成对公序良俗的违背。因此,撤销权理应被排除于适用范围之外。
(三)折衷说
折衷说又称为“错误排除说”,将意思表示瑕疵中的认识错误与欺诈行为相区别,并只在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欺诈投保时承认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的选择适用,但在投保人重大过失时只能寻求法定解除权而非重大误解事项的撤销权予以救济[11]。该观点在投保人故意欺诈投保的范围内与选择说持相同立场,而在投保人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要求保险人只能诉诸法定解除权予以救济。这一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重大误解并不要求投保人重大过失,一般的过失亦可能成立重大误解,而造成对法定解除权制度更为严重的破坏。然而自《民法典》颁布以来,原规定于《合同法》第55条涵盖的诸如欺诈、重大过失、显示公平等事由的撤销权被分散到了《民法典》总则编不同的条文之中。故此目前针对更为频繁的欺诈投保案件,主要的争议是集中于《民法典》第148条欺诈法律行为的撤销权和《保险法》第16条第二款的法定解除权适用关系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区分折衷说与选择说的意义并非特别明显。
三、保险人撤销权适用困境之域外考察与启示
欺诈投保中保险人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之适用争议主要源于我国2009年《保险法》修改后“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该条款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行使附加了客观上自合同成立起2年的最长期限限制和主观上自知道解除事由始30日的消灭期限限制,相较之下远短于撤销权客观上行为发生之日5年内和主观上知道欺诈事由起1年内的时限。除此之外,2009年对《保险法》的修改将法定解除权的适用范围由原先的投保人过错限定为投保人主观上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也削弱了法定解除权的适用范围。故此,针对学界与实务界激烈热议的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适用关系这一问题,应当从分析“不可抗辩”条款引入我国的目的和该制度设计的初衷出发,探寻承认撤销权的适用是否会对该立法目的与制度设计初衷造成实质性背离。由于我国“不可抗辩”条款制度的创设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的经验,而其2年的最长期限又因远短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不可抗辩”条款的期限而饱受争议,因此有必要分别对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不可抗辩”条款适用情况分别进行比较分析[12]195。
(一)英美法系视角下保险人“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考察
“不可抗辩”条款的应用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的英国,而后被广泛应用于美国[13]。该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处在市场优势地位的保险公司为平息广大消费者对保险行业的不满情绪并重拾社会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而由保险公司自愿在约定的保险合同条款中加入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限制[14]。英国《保险法案》第8条规定了非消费类保险中受保人在因为对公允表达义务的违反而导致保险人订立合同或同意了条款中约定的事项时,可依据《保险法》中Schedule 1的规定获得救济④,而Schedule 1的救济途径对受保人的过错程度亦进行了区分。当受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且无需承担保险责任或退还保险费⑤。然而对于其他情形,则要区分受保人对公允义务的违反程度。如果受保人的违反是合同订立错误的直接导火索,那么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是需要退还保费⑥。但是当受保人违反公允义务只是导致保险人对除保险费率之外的个别条款意见不同时,则只是这些条款无效,其他条款仍然有效⑦。当保险人对于违反公允告知义务的受保人只是认为约定的保险费率不够公允时,其可以选择按照相应比例减少对保险金额的支付,同时不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⑧。
相比之下,美国在欺诈投保的规制方面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由于美国是一个多法域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因此对于欺诈投保的规制在各个州之间也不尽相同。美国大部分州都在人寿保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中施加了客观上2年的最长行使期限限制,有的州还为“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配备了法定除外情形[12]207。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典》第10113.5.(a)条便对人寿保险施加了自合同生效2年后且受保人在2年内尚在人世则保险条款“不可抗辩”的限制。在此之外,还附加了受保人拒付保险费情形和另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的附加利益纠纷除外的规定⑨。而无论是美国保险法,抑或是英国保险法,均只将“不可抗辩”条款的期限规定附加在了人身保险上,而非于财产保险之上[12]210-212。由于在英美国家的合同法体系之中并没有像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合同撤销权制度的规定,而且欺诈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合同的无效,因此在英美保险法体系下投保人在行使法定解除权时无需担忧所谓的“撤销权与解除权相排斥”等问题⑩。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做法:以德、日为例
尽管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与日本在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与其他欺诈性合同救济途径的关系上所持态度亦存在着些许差异。德国以立法的形式在《保险合同法》第22条中规定保险人对违反披露义务的投保人行使权利终止合同不影响其寻求其他与欺诈性陈述有关的权利救济⑪。此外,德国《保险合同法》就保险人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的法定解除权区分了投保人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三种情形。对于一般的过失,保险人只能在一个月内终止合同,而不能解除合同⑫。最受国内学者所瞩目的是德国《保险合同法》中合同解除权对投保人的主观恶意程度进行了区分,对非故意违反告知义务的投保人设置了5年客观行权期限,而对故意欺诈的投保人设置了较长的10年行权期限。与一般的“不可抗辩”条款将期限起算点设置在合同订立时起算不同,德国客观上最长行权期限限制自合同失效时起算⑬。德国《保险合同法》对故意的欺诈投保行为最长规制时间与德国《民法典》中对欺诈行为可撤销的最长行权时间相同,均为10年⑭。这也导致《民法典》中对欺诈行为的救济途径较之《保险合同法》中欺诈投保法定解除权的方式,并未体现出明显的优势。故两条权利救济的路径相互干扰的程度并不激烈。
相比之下,日本对法定解除权与民法规定的撤销权之间的适用关系之争则历经了大审院民事部和刑事部意见不统一、民刑事联合部意见一致承认民法中欺诈与错误行为撤销权的适用和以“错误规定排除说”为主导的三个阶段[15]70-71。目前日本现行判例通说“错误规定排除说”仅承认在投保人故意欺诈的情形且该欺诈具有具体的行为表现时投保人可选择民法中的欺诈途径撤销合同,抑或是通过保险法案中的法定解除权来实现救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保险法将告知义务的违反和由此产生的法定解除权针对非人寿保险、人寿保险和伤病定额保险三种类型进行了区分,但是保险人最长解除期限在三种保险合同类型下是相同的,均为主观上自知道解除事由起1年和客观上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5年内行使。这个期限要远远短于《日本民法典》中对因欺诈等行为撤销权的可行使期限,后者是主观上知道撤销事由起5年内、客观上自可撤销行为作出起20年内行使⑮。目前日本学界多数观点同意欺诈投保时可以适用除斥期间更长的撤销权,因为此类投保人主观恶性过强而不值得特别保护。同时,这一主流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德国法中不排除其他欺诈救济途径适用的影响[15]72。尽管日本法对于非欺诈情况下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限定了法定合同解除权这一的救济途径,与德国法存在差异,但是在故意欺诈层次两国法律仍然持相似的立场,即均认可保险人也可借助民法对欺诈行为予以规制和救济。这一点颇似我国学界“选择说”的立场。
(三)对我国的启示与镜鉴
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从立法上将“不可抗辩”条款作为法律规定而非合同约定的事由,体现了国家对保险行业的强监管政策,同时较短的法定解除权行使期限亦具有对投保人倾斜保护的特征。这体现出我国《保险法》之修订更倾向于限制投保人的权利,而非如同德、日一样以遏制恶意投保人为主要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撤销权的适用问题上不应当盲目借鉴德、日经验,而是要以实现“不可抗辩”条款引入的立法初衷为首要目标。此外,尽管学界提出“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系国家的经验,但是相较之下我国对于投保人告知义务违反时的区分较为粗糙,未能规定保险人在不愿解除合同时对保险条款内容的修改权利与“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的除外情形。相较于大陆法系的实践,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法定解除权客观最长行使期限未能像德国一样针对故意欺诈与过失予以区分对待,亦没有像日本法那样将长达20年的民法典欺诈行为撤销权的规定作为替代的救济途径。我国《保险法》针对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时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其他法律框架下的救济途径之间的衔接关系尚无明确规定,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实务中法律适用的模糊性。故此,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的权益保障机制尚有亟需进一步完善之处。通过吸纳域外经验中的合理因素,结合本土现实情况对投保人恶意欺诈行为的规制方式予以细化,方能克服司法实践中这一痼疾。
四、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适用困境之化解
(一)在法律的解释路径上排除撤销权在欺诈投保中的适用
诚然,目前我国《保险法》体系下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法定解除权的行使要求较域外法更为严苛,也印证了选择说对法定解除权难堪重任的担忧,但是对撤销权适用与否的分析除了要考虑法律条文本身的语义陈述之外,更应当保障保险法自身体系的完整性并兼顾立法目的的实现。选择说对承认撤销权适用的一个重要理由为二者的立法意旨不同,故此互不冲突。然而,尽管“不可抗辩”条款诞生之初以限制保险人权利、平息广大投保人的不满情绪、缓解市场的压力为目的,且法定解除权的直接目的在于保障如实告知义务的落实,但是二者共同指向的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仍是以保护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意思表示真实、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增加的保险人经营成本为立足点。对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以法定解除权予以规制是保险法中公序良俗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亦是对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法定解除权不但有着惩罚恶意欺诈投保人的功能,也可作为意思表示瑕疵时的重要救济渠道。故而,《保险法》第16条对投保人法定解除权规定的立法目的与撤销权并没有实质性差异。且2009年《保险法》的修改亦体现出立法者意欲通过“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来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地位和利益关系。与域外法规定不同,我国《民法典》中对欺诈行为撤销权的规定的确会对《保险法》框架下法定解除权的救济途径造成实质性架空。在英国和美国,并没有所谓撤销权的规定来分散法定解除权的救济功能。德国和日本虽然认可欺诈投保时保险人可以选择适用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但是两个国家对法定解除权行使的期限限制均比我国要长很多。故民法体系下的撤销权对于法定解除权的适用尚不构成实质性的替代,且对于保险人优势地位的制约力度较弱。
相比之下,我国对于“不可抗辩”条款2年期限的限制明显体现了对于投保人的倾斜保护,而承认撤销权的适用则可能会对该倾斜保护的立法意图构成规避。因此,在解释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的适用问题时,应当将立法者对投保人的倾斜保护的立法意旨考虑在内。在符合规范目的的前提下,再进一步考虑对恶意欺诈行为的惩治与防止投保人因自己的错误行为获利等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应当以破坏保险法的现行框架和牺牲“不可抗辩”条款制度引入时的立法初衷为代价。
选择说的一个主要论点即为撤销权与解除权在构成要件上存在差异,且二者在本质上应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利模式。然而,正如前文排除说所主张的那样,解除权的构成要件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且二者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此外,新颁布的《民法典》第148条的规定更是将欺诈撤销权单独列出,与重大误解等行为所产生的撤销权相区分,进一步印证了欺诈投保案件中解除权在构成要件上对撤销权构成要件的包含。正如世界著名的法理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述,特别法与一般法间关系的形成除了既体现在了构成要件的包容关系上,又体现在了规范间互相排斥的法律后果上[16]。从这一点来看,二者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观点并未忽略两项权利之间的不同之处。基于此,在欺诈投保案件中,将合同解除权视为特别法而排除适用作为一般法的撤销权是合理可行的解释路径,应当成为该问题解答的首要选择。
(二)从成本—收益角度肯定法定解除权规制欺诈投保的独立价值
选择说立场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要通过适用撤销权惩罚主观恶性较大的欺诈投保人,维护诚信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然而,撤销权所基于的民法以公平和诚信为主要的价值目标,但是解除权所基于的保险法则属于以效率为优先的商法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强调单个交易的公正诚信,不如督促保险人及时建立高效完善的事先风险审查体系,将恶意欺诈带来的风险提前排除于资金池之外。这样不但能提升交易的速度,降低对欺诈投保事后矫正救济所产生的成本损失,还有利于形成稳定的保险关系,对无辜的第三人也可提供稳定的保障。除此之外,从最小防范成本的角度而言,增加保险人对事先风险审查体系的投入和完善所需要的成本要远远小于阻止广大投保人因对巨额保险金的觊觎而欺诈投保的成本。仅仅寄希望于保障单个交易中的公平诚信,来规制一个行业的经营秩序,是十分困难的。对于欺诈投保人而言,撤销权成功适用所产生的成本不足以对抗保险金带来的诱惑。然而对于保险人而言,具有“不可抗辩”期限限制的解除权却切切实实地关系着其自身利益,并可以成为督促保险人完善业内事先风险审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由此可见,排除撤销权的适用,更能发挥解除权对保险行业发展的良性促进作用。将风险与效率挂钩后,市场自然会主动作出调整适应,通过保险人对事先风险审查体系的完善进而保障保险市场公平诚信的交易秩序。
保险制度最初创设的目的是风险的分摊,侧重对安全价值的追求。然而在商业实践中,营利性与效率也成为保险人追逐的主要价值目标。这固然无可厚非,也有利于保险行业的繁荣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使得通过《保险法》上的强监管来保障保险“安全”这一功能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不可抗辩”条款在促进保险“安全”价值实现的同时,亦能反映出其相较于撤销权而言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具体来说,撤销权虽然能矫正当事人之间的瑕疵意思表示,但其“恢复原状”与通过“缔约过失责任”予以救济的法律效果难积极替代当事人做出正确的意志选择[17]。在撤销权适用的情形下,投保人尽管无法获得保险利益,但是尚能取回保险费,且所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往往因为实务中举证困难而作用受限。然而,法定解除权在保险人无需返还保费的同时还可追究投保人的违约责任,对于被发现的投保人欺诈投保行为所施加的成本要高于撤销权施加的成本。此外,允许欺诈撤销权的适用会导致保险人过于依赖除斥期间更长的撤销权,进而怠于对保险准入的审查。如此,保险人降低了自己的经营成本,而扩充了用于保险经营的资金池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对于保险人而言,吸收更多的投保人资金所带来的收益要超过个别投保人索赔时带来的成本,那么保险人事先规避防范风险的意识就会削减。故此,保险人对投保人准入审查力度的降低在扩充资金池的同时也会导致整体保险风险的增加。对于商事实践中风险的控制,仅仅凭借投保人的诚信自觉与保险人的事后倒查不足以满足保险产品“安全”这一价值属性,保险人对利益的追逐也会削弱保险对风险分担的功能。
撤销权或许足以矫正错误的意思表示,但是要规制一个如此具有射幸性特征的保险行业欺诈行为还是力有不逮。故此,投保人需要开展积极的保险准入审查,将事前的危险排除在承保的范围外。这样不但能保证现有保险资金池的整体安全,也可以避免因为恶意投保人的欺诈行为而将增加的事前风险分摊到了广大善意投保人这一不公正现象的出现。如果在现行法下允许保险人依赖撤销权规制投保人的积极恶意,保险人很可能会选择成本小收益高的救济途径,即允许该保险金在自己的资金池中多存续3年,而后再以撤销权的途径退还保险费且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对于保险人而言,保险费在资金池中3年的使用期限已经带来了相当的利益,而不会过于在意保险费的退还,亦不会对欺诈投保带来的危险进行积极预防。故此,法定解除权2年的最长适用期限不但服务于敦促保险人积极行权的规范意涵,也能够避免在规制投保人积极的恶意时诱发保险人消极不作为的举措,进而促进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
(三)补强法定解除权对恶意欺诈投保行为的规制力度
尽管选择说的主要论点不足以否认撤销权和解除权间“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适用,且不能快速地刺激一个诚信高效的保险市场的发展,但是要结束选择说与排除说间的巨大争议,关键还是在于完善《保险法》的表述。现行《保险法》第16条关于保险人法定解除权能否排除撤销权适用的模糊规定正是两派立场争论的起点。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典型案例“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明确了“不可抗辩”条款针对合同订立两年后才发生的保险事故适用,但是这也是在对现行条文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原规定进行目的论限缩解释后才达成的效果⑯。同时,关于撤销权与法定解除权能否选择适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次尝试均以争议较大而无法形成一致意见而黯然收场。这表明,对于欺诈投保案件中撤销权是否被排除适用根源上还是应当在立法上得到层次解决,而不应仅在现行实定法基础上通过法律解释与各方利益考量达成一种“妥协式”的平衡。在对欺诈投保问题的规制上,应当“将保险事故发生于合同成立两年之后”重新定位为客观最长“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条件,同时明确法定解除权与撤销权的适用关系。此外,为了加大对投保人欺诈投保的打击力度,也可以适当对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予以进一步的区分。比如可以参考德国立法经验,适当延长故意情形下“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期限。这样在不破坏保险法现行框架且维持对投保人倾斜保护的同时,也能对恶意欺诈投保行为予以更为强力的规制。由于保险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于资金池的稳定与扩充,故法定解除权的补强应当以刺激保险人在追求效益的同时兼顾维护保险安全的属性为目标,在适当延长“不可抗辩”条款期限、赋予保险人更加充分救济途径的同时也可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对弃权条款的细化等方式对保险人的优势地位予以平衡,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五、结语
对于欺诈投保案件的规制,应当排除保险人撤销权的适用。尽管撤销权延长了对保险人受故意欺诈情况下的权利保护期限,但是撤销权较长的除斥期限在构成对“不可抗辩”条款的实质性规避同时,也不利于敦促保险人建立完善高效的事前风险审查体系。保险产品尽管是商业实践的产物,具有着营利的属性,但是保险制度更为核心的价值应当是安全。将风险与效率挂钩后,市场主体会主动积极地作出调整,并以完善高效的事先风险审查体系来保障公平诚信的交易秩序的实现。故此,对于欺诈投保的法律规制仍然应当以《保险法》框架下的法定解除权为主线,通过补强对恶意投保的规制力度实现各项利益价值的平衡,而不能以破坏保险法体系为代价,轻易承认撤销权的适用。在立法框架下现行法供给模糊时,“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仍然是排除撤销权适用的合理可行的解释途径,这样做也有利于维护“不可抗辩”条款的引入初衷。此外,为了充分发挥法定解除权的功效,可基于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主观恶意程度不同的投保人在行权期限上进行细化区分,进而为“不可抗辩”条款的完善提供指引。
注释:
①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德中心支公司、林胜勤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2019)闽0981民初882号民事判决书。
② 朱思怡诉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吉0104民初5441号民事判决书。
③ 薛建月、彭玉欣等与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2019)冀8601民初1221号民事判决书。
④ Insurance Act 2015: 8: (1): The insurer has a remedy against the insured for a breach of the duty of fair presentation only if the insurer shows that, but for the breach, the insurer (a) would not have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of insurance at all, or (b) would have done so only on different terms. (2) The remedies are set out in Schedule 1.
⑤ Insurance Act 2015: Schedule 1: 2: If a qualifying breach was deliberate or reckless, the insurer (a) may avoid the contract and refuse all claims, and (b) need not return any of the premiums paid.
⑥ Insurance Act 2015: Schedule 1: 4: If, in the absence of the qualifying breach, the insurer would not have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on any terms, the insurer may avoid the contract and refuse all claims, but must in that event return the premiums paid.
⑦ Insurance Act 2015: Schedule 1: 5: If the insurer would have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but on different terms (other than terms relating to the premium), the contract is to be treated as if it had been entered into on those different terms if the insurer so requires.
⑧ Insurance Act 2015: Schedule 1: 6: (1): In addition, if the insurer would have entered into the contract (whether the terms relating to matters other than the premium would have been the same or different), but would have charged a higher premium, the insurer may reduce proportionately the amount to be paid on a claim.
⑨ California Insurance Code:10113.5.: (a) An individual life insurance policy delivered or issued for delivery in this state shall contain a provision that it is incontestable after it has been in force,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 insured, for a period of not more than two years after its date of issue, except for nonpayment of premiums and except for any of the supplemental benefits described in Section 10271, to the extent that the contestability of those benefits is otherwise set forth in the policy or contract supplemental thereto. An individual life insurance policy, upon reinstatement, may be contested on account of fraud or misrepresentation of facts material to the reinstatement only for the same period following reinstatement, and with the same conditions and exceptions, as the policy provides with respect to contestability after original issuance.
⑩ Davis v. Clinton, 74 F. App'x 452 (2003).
⑪ German Insurance Contract Act: Section 22: The right of the insurer to avoid the contract on account of fraudulent misrepresentation shall remain unaffected.
⑫ German Insurance Contract Act: Section 19(3): The insurer’s right to withdraw from the contract shall be ruled out if the policyholder breached his duty of disclosure neither intentionally nor by acting with gross negligence. In such cases the insur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subject to a notice period of one month.
⑬ German Insurance Contract Act: Section 21(3): The rights of the insurer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9 (2) to (4) shall lapse five years after the contract expires;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insured events which occurred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time limit. If the policyholder has breached the duty of disclosure intentionally or by acting fraudulently, this period shall be ten years.
⑭ German Civil Code: Section 124 (1) The avoidance of a declaration of intent voidable under section 123 may be effected only within one year.
⑮ Japanese Civil Code: Article 126: The right to rescind an act shall be extinguished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prescription if it is not exercised within five years from the time when it becomes possible to ratify the act. The same shall apply when twenty years has elapsed from the time of the act.
⑯ 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19起合同纠纷典型案例之二,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