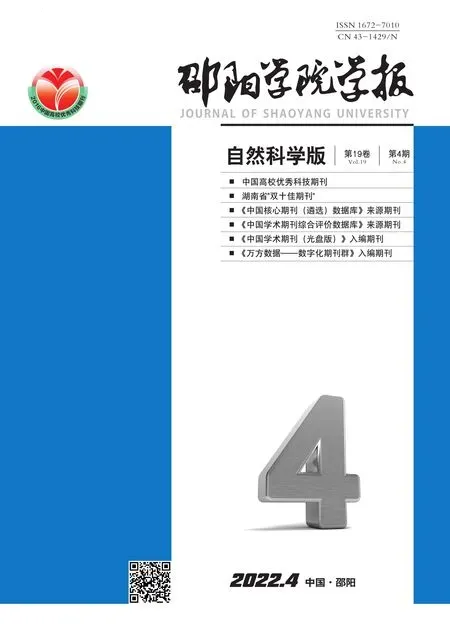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汪瑶,王玉龙
(1.邵阳学院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湖南 邵阳,422000;2.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认知与人类行为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410081)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大部分的青少年更愿意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进行互动和交流,尽管网络给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网络已经成为青少年暴力的载体[1],并产生了新型暴力形式——网络暴力[2]。
网络暴力虽然是暴力在网络中的延伸,但其实比传统暴力更为普遍,因为它的发生不受时间、空间和地点的限制[3]。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网络暴力的分析,可以发现网络暴力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4-6]:1)网络暴力具有强制性,其强制性通过制造心理压力来实现,受害者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2)网络暴力具有攻击性,网民可以在网上对他人进行肆意的人身攻击,比如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3)网络暴力具有盲目性,网络暴力行为开始于网民出于维护正义的自发性道德审判,但这种基于网络空间的审判往往依据的是主观判断和个人感受,缺乏真实的事实材料;4)网络暴力具有隐蔽性,这是由网络的匿名性造成的。网络暴力是一种软暴力,只限于网络中发生的行为,与现实中暴力类似,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因此,本研究将网络暴力界定为:“网络对当事人或组织实施的以制造心理压力为手段,以迫使当事人或组织屈服的网络攻击行为的总称”[6]。
问卷调查和量表是衡量网络暴力的主要手段。国内对网络暴力的测量,大多是问题清单形式,缺乏系统性的结构问卷,如江根源[7]对青少年网络暴力行为进行研究时,也只是采用诸如“骚扰性的手机短消息或图片、在网络上上传转发丑陋的不道德的图片或视频”等这样的问题式清单对青少年进行调查,缺乏可信度,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研究探讨的是网络欺负[2],可用于有效评定青少年网络暴力的量表几乎以网络欺负的形式出现,如网络欺凌清单[8]和网络欺负评定问卷[9]等。
网络暴力比网络欺负囊括的范围更为广泛,如果直接采用测量网络欺负的工具衡量青少年网络暴力行为,可能导致网络暴力现象被低估。网络欺负的调查问卷或量表大多是没有确定因素结构的,或者只是一维结构,并不能完全解释网络欺负,更加不能完全解释网络暴力。已有研究发现,网络暴力是由不同的行为构成的,这些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彼此之间又紧密相连[6]。因此,构建一个多维结构的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探索网络暴力和其他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从网络暴力的因子结构出发,深入探讨施暴者和受害者对于不同形式网络暴力的反应及应对策略。
综上,本研究拟编制一个多维结构的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为准确全面地评估青少年网络暴力水平提供可靠有效的测量工具,也为探索青少年网络暴力发生机制提供可能。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半结构性访谈样本:在长沙市某中学选取30名学生和6名老师作为访谈对象,被试学生中,男生18名,女生12名,初一到高三年级各5名,年龄为(14.29±1.69岁);被试老师中,2名是心理老师,4名是班主任。
初测样本:所得数据用于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长沙、邵阳两地选取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60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68份,有效率为94.67%。其中,男生283人,女生285人;初一97人,初二94人,初三102人,高一96人,高二87人,高三92人;年龄为(14.50±1.79)岁。
正式施测样本:所得数据用于量表的信效度检验。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长沙、邵阳两地选取中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77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695份,有效率90.26%。其中,男生232人,女生463人;初一96人,初二103人,初三106人,高一127人,高二153人,高三110人;城镇378人,农村317人;年龄为(14.75±1.75)岁。
重测样本:所得数据用于量表的重测信度检验。从正式施测样本中方便选取183名学生间隔4周进行重测,男生85人,女生98人。
1.2 效标工具
网络欺负问卷(cyberbullying inventory,CBI)[9],问卷为单维设计,共18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总分>18分表示至少有过一次网络欺负行为,分数越高,网络欺负行为的频率越高。问卷的信效度良好。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初测样本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变异法),对正式施测样本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以Cronbach’s α系数为信度指标)和效标效度检验,对重测样本进行重测信度分析,采用AMOS 21.0统计软件对正式施测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1.4 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条目的编制
在查阅前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究网络暴力的概念建构,以陈代波[6]对网络暴力的划分类型为问卷的理论框架,初步提出网络暴力是由人身攻击、舆论暴力、黑客攻击和网络勒索构成的4维度理论模型。人身攻击是指在网络中使用语音、文字与符号等对他人所进行的攻击行为;舆论暴力是指在网络中通过散布谣言和传播他人私密照片或视频的方式制造舆论,从而让受害者承担巨大心理压力,并对其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行为;黑客攻击在网络中使用黑客工具或手段攻击他人或网站的行为;网络勒索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让其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获取受害者财产的行为。
参考网络欺负评定问卷[9]中的部分条目,同时,根据我国青少年在网络中所从事的行为和上网习惯,设计访谈提纲并对6位中学老师和30名中学生进行半结构性访谈。通过分析访谈文本材料提炼出能较好地反映青少年网络暴力内容资料,以此作为编写问卷题项的参考。同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相关项目进行增补,如网络勒索,有研究者把网络勒索分为“发帖型”勒索与“删帖型”勒索,据此编制网络勒索维度的项目,如“我在网络上以发布负面信息或隐私信息为要挟,索取对方财物”“我在网络上以删除负面信息或隐私信息为要挟,索取对方财物”。
为了使量表条目表达准确和规范,邀请1名心理学副教授和4名心理学硕士对所得条目进行审查与评估,并根据其意见进行修改。通过以上方式建立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项目池,共37个条目,被试需要对每个条目所描述的行为频率进行1~4级的评分,1~4级分别代表从不、偶尔、经常、总是。
2 结果与分析
2.1 项目分析
采用区分度检验和与总分相关筛选条目,删除临界比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4个条目和与总分的相关系数<0.4的7个条目,最终保留26个条目。项目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各条目的项目分析
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釆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s)和最大变异法(varimax)对保留的26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采用斜交旋转法生成特征值>1的因子6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59%。根据碎石图及卡特尔的“陡坡检验”原理抽取3个因子,再根据以下标准逐步删除题项[10]:1)共同度<0.30;2)因素负荷值<0.40;3)同时在多个因子上负荷值均>0.40;4)与所在因子的其他条目的意义差异较大,归类不当。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最终抽取3个因子,12个条目,载荷均>0.63,共同度均>0.42,可解释总变异的61.0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青少年网络暴力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旋转后)
2.3 内在一致性信度
对正式施测样本所得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显示,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总分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0.70和0.81。对重测样本的前后测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量表总分的重测信度为0.81,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5、0.74和0.71。以上结果说明该量表信度良好。
2.4 结构效度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正式施测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该模型的χ2/df=4.31,GFI=0.95,AGFI=0.92,CFI=0.83,IFI=0.83,RMSEA=0.07,说明模型拟合良好。如图1所示,青少年网络暴力暴力量表三因子与相应的观测指标之间的负荷值在0.44~0.94之间,三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0~0.74之间,说明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的因子结构是合理的,也支持了探索性因素的结果。

图1 青少年网络暴力结构方程模型图
2.5 效标效度
以网络欺负(CBI)作为关联效标,对青少年网络暴力和网络欺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网络暴力与网络欺负显著正相关(r=0.52,P<0.001),说明该量表的效标效度良好。
3 讨论
本研究以网络暴力实施方式的分类[6]为问卷编制的理论模型,参照已成型的网络欺负评定问卷,基于我国青少年对网络暴力的理解和实施网络暴力的现状,通过质性分析、半结构性访谈和专家评定等方式形成包含37个条目的青少年网络暴力初始问卷。初始问卷在经过条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后,形成了包含12个条目的正式问卷。正式问卷较初始问卷的不同在于删除了网络勒索,保留了人身攻击、舆论暴力和黑客攻击3个维度。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网络勒索维度下的条目负荷较低或具有多重负荷,使得网络勒索维度对于量表贡献的解释率较小。在对初测被试进行分析时发现进行过网络勒索的青少年只有7人,仅占总人数的1%,这表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网络勒索现象并不普遍。这可能与网络勒索事件性质相关,网络勒索已经触及法律层面,属于网络犯罪行为,根据相关统计,我国90%网络犯罪主体年龄在20~35岁之间,国外网络犯罪低龄化趋势更显突出,如美国为10~17岁,加拿大为12~17岁,俄罗斯为15~17岁,国内外青少年犯罪年龄的显著差异可能与各国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水平及教育环境等因素有关[11-12]。
本研究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考察量表的可信度。KAPLAN等[13]认为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以上,则具有较好的信度。若量表总体的Cronbach’s α系数>0.8,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0.7,则量表非常理想[14]。一般认为重测信度在0.40~0.75之间为中等到较好,0.75以上则为极好[15-16]。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70~0.83之间,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1,各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65~0.74之间,说明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各条目质量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指数x2/df<5,RMSEA<0.08,GFI、AGFI都>0.9,CFI、IFI>0.8,PGFI>0.5,说明模型拟合良好,青少年网络暴力三维度结构模型是可以被接受的。在效标效度方面,量表总分与CBI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52,且相关显著,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校标效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的青少年网络暴力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评估青少年网络暴力水平的测量工具。但本研究仍存有不足之处,首先,网络暴力是现代智能技术催生的新型暴力形式,是比较复杂的社会现象,将其分为人身攻击、舆论暴力和黑客攻击3个维度可能过于简单,未来需要丰富和加强网络暴力的理论结构。其次,被试群体主要来自于中学生,忽视了非学生青少年这一群体,之后的研究可以扩大取样范围。另外,本量表是否适用于其他学生群体,有待进一步考证。
——美创科技“诺亚”防勒索系统向勒索病毒“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