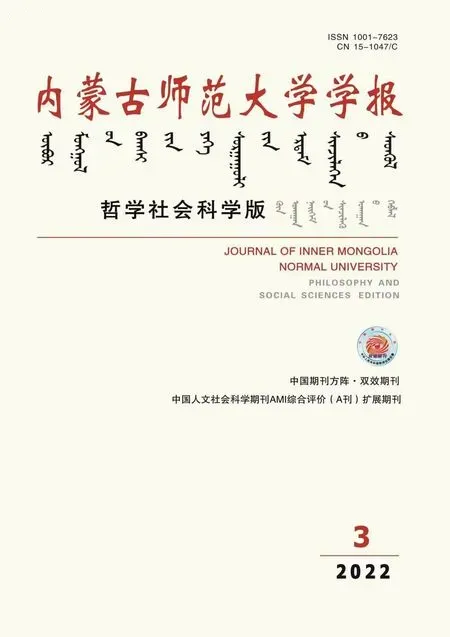《琵琶歌》在百老汇改编与搬演的得失及启示
张勇风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琵琶记》是元代最重要的南戏作品,被改编为音乐剧《琵琶歌》(LuteSong),于1946年搬上百老汇舞台。这次改编和搬演完全出自美国人之手,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美国传播[1]81,也是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史上的重要个案。改编者主要为美国资深新闻撰稿人威尔·厄文(Will Irwin),由当时百老汇最具号召力的女演员玛丽·马丁(Mary Martin)担任女主角,《纽约时报》多次刊登大幅广告和文章进行宣传,一时颇为轰动。然而,演出并未取得预期成功,舆论评价毁誉参半。因此,探讨《琵琶歌》在百老汇改编和搬演的得失,可为中国戏曲“走出去”提供有益借鉴,值得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一
《琵琶歌》在美国改编和上演,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该剧的主要改编者威尔·厄文萌发改编此剧的想法,始于20世纪初观赏在美华人演出粤剧《琵琶记》的体验。威尔·厄文时为《纽约时报》记者和业余剧作家。据《威尔·厄文传》记载:厄文对中国文化很着迷,立志成为中美交流方面的代言人,他经常和朋友们出入华盛顿和杰克逊街头的中国剧院。一个冬天的晚上,他看到比《哈姆雷特》早两百年、与伊丽莎白戏剧风格非常相近的《琵琶记》时,感到无比震惊。他认为这部剧作很美,很有魅力,充满了幽默、讽刺、怜悯、悬念和深刻的人格魅力。他决定未来一定要将这部剧作改编到美国舞台上[2]27。之后,厄文联系到德国汉学家祖克,获得法国汉学家巴赞的法文版《琵琶记》。祖克曾于1925年出版《中国戏剧》①,书中大量篇幅探讨《琵琶记》[3]43—68,厄文对该剧的认识亦应受到此书影响。获得法文版《琵琶记》后,厄文才着手改编该剧。后来他找到西德尼·霍华德一起合作改编,霍华德是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百老汇著名剧作家。经过一个较为艰辛且长期的过程,《琵琶记》被改编为《琵琶歌》。
该剧被搬演到百老汇舞台上,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930年该剧在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剧场首次公演后,百老汇音乐剧的投资者最初都觉得这部作品“既不性感,又乏趣味”,没有商业投资价值[2]156。直到1944年,制片人迈克·麦尔伯格才决定投资《琵琶歌》,并为百老汇当红女演员玛丽·马丁量身打造。该制片人也因此被称为“经典怪戏的赞助者”。

图1 《纽约时报》刊载的《琵琶歌》广告(一)

图2 《纽约时报》刊载的《琵琶歌》广告(二)
历经波折,该剧最终于1946年2月6日在纽约百老汇普利茅斯剧院上演。《纽约时报》连日刊登大幅广告进行宣传(见图1、图2),还出现一些评论文章为该剧的演出造势。演出持续了5个月,上演了142场,后续在其他地方还有一些演出。对于该剧的搬演,当时的美国媒体评价不一,大多持尊重态度,同时又认为演出并不成功。《时代》杂志评论云:“本季最可爱的制作及最迷人的失败。一个五百年前的中国故事经典重现,搭配着音乐、舞蹈及壮观的表演,它仍没抓住艺术的光芒或掀起剧场外的波澜,它应该减少一些大场面或是删减一点故事。这个故事新编的长度适中,但因为可爱的诠释和华丽的干扰,使其观众感受不到流动与角色的内在。”《告示牌》杂志评论道:“当观众离开剧场仍不断讨论服装与布景时,你可以想见这个戏的票房会有多么惨。”《纽约邮报》也评论道:“很有品位,华丽的气氛也营造很好,但是一切被一种百无聊赖笼罩。”[4]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研究的推进,学者逐渐注意到该剧在百老汇被改编和搬演的情况。都文伟《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认为:《琵琶歌》在纽约普利茅斯剧院,五个月演出了142场次,着实不凡[1]84。石峻山也认为,这样的演出次数在该时期普遍认为不差,并谈到该作品通常被评价为部分成功或部分失败[4]。百老汇音乐剧的专门研究者爱瑟·墨登在《美丽的晨曦:1940s百老汇音乐剧研究》中直言:“《琵琶歌》失败了。由于它给马丁的追随者们发出的交叉信号,以及亚洲戏剧普遍的内敛性质,该剧几乎不得不这样做。”[5]244墨登是百老汇音乐剧研究专家,曾撰写《相信:1920s百老汇音乐剧研究》《到来的玫瑰:1950s百老汇音乐剧研究》等著作,其说法当更具权威性。他谈道:
《琵琶歌》的唱片,听起来很好,但并不正确,感觉像是罗杰和哈默斯坦之类自成一格的内容,是一种革新化的音乐剧。不对,该剧甚至不是音乐剧,它只是表演得像音乐剧一样。所有的演员,穿着夸张的服饰来回闲逛,摆出鲜艳的造型,听到敲锣声,就突然转向[5]244。
《琵琶歌》的舞台搬演,我们已无法看到。只能查找到一张收录了玛丽·马丁《与维纳斯的一次接触》《琵琶歌》两部剧作曲子的光盘[6]。其中收录《琵琶歌》六支曲子,《山高谷深》《看猴子》《你在哪》《梦幻之歌/苦难的收获》四支曲子由马丁演唱,《皇家行军曲》《挽歌》为管弦乐曲。马丁的演唱虽然悦耳动听、深情婉转,但这些曲子的风格与百老汇音乐剧一人或多人边唱边舞,将音乐、舞蹈、剧情融为一体的表演风格相去甚远。这些曲子更像是插曲,并没有和舞蹈、剧情完美地融汇在一起,有的曲子甚至不知所云,如《看猴子》(SeeTheMonkey)。我欣赏了剧本,不知这支曲子曾用在什么地方。如墨登所言:“七支曲子,都是为马丁或博瑞纳设计②,这些曲子是一个奇怪的组合。其中《柳树》(WillowTree)反映的是东方的感觉,但五音都有问题。然后试图给马丁一个流行曲调《你在哪》(WhereYouAre),这使她不至于在电台尴尬。后尝试主题曲《琵琶歌》(TheLuteSong),包含传统的飙升音又非常和谐,接着设计了一个不相干的疯狂曲子《看猴子》。最后终于找到了饱含永恒之美的合适旋律《山高谷深》(MountainHigh,ValleyLow),这个标题很少见,符合当时的标准,但后来完全被忘记了。”[5]244
观众只能看到华丽的服饰,感受不到角色的内在,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剧的演出并不成功。除表演风格与百老汇音乐剧相偏离之外,《琵琶歌》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戏剧冲突的内在张力不足,这与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和文本重构时情节的架构密切相关。
二
对于《琵琶歌》在百老汇演出不够成功,研究者多归因于中西文化差异。都文伟认为原剧中“孝”的主题被改编为《琵琶歌》中“爱”的主题,而这样全剧便体现的是“西方观念中被基督教爱或神爱拔高了的中世纪式的情爱”,而“爱情故事更合西方人的口味”[1]92—93。文化差异,是一切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它不应成为《琵琶歌》未获成功的根本原因。通过考察《琵琶歌》改编和搬演的过程,并深入研读原剧《琵琶记》,我认为《琵琶歌》在百老汇没能获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文化疏离。《琵琶歌》与原剧丰富的文化内涵相疏离,被改编为一部具有异域风情的爱情剧。《琵琶记》讲述的是蔡伯喈被迫上京赶考,一举考中状元,被迫入赘牛府。家乡连年遭灾,妻子赵五娘独立撑持,父母双双饿死,赵五娘身背琵琶上京寻夫。牛小姐得知实情,在她的安排下,赵五娘与蔡伯喈团圆。最终蔡伯喈携两位妻子回乡守墓,获得满门旌表。全剧篇幅宏大,内容丰富。该剧为元末南人高明创作,高明曾中过进士,担任过处州录事、浙江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等职[7]359。但他与当时诸多南方文人一样,数忤权贵、厌弃官场,归隐思想浓烈。他不仅从方国珍处辞官,且拒绝朱元璋的招纳,《琵琶记》便是他在晚年归隐宁波栎社后创作而成。该剧除表现赵五娘孝顺、贞烈等传统伦理观念和部分内容表现吏治腐败的内涵外,更重在借晚年失节的历史人物蔡伯喈,通过他入赘相府的失身行为,表现高明认为入仕即失吾故的辞仕、归隐思想[8]。刘祯先生曾云:高明是一位充满矛盾和痛苦的思想者,他改编该剧是出于“表达思想的需要”[9]。高明生逢元末乱世,好友刘基、宋濂、陈基等被朱元璋招募至麾下,他们的处境与身处汉末乱世的蔡伯喈颇有几分相似。因此,高明《琵琶记》中辞仕、归隐的主旨表现得颇为隐匿。因为重在呈现蔡伯喈的内心思索和心理活动,该剧甚至没有激烈的外在矛盾冲突。对于《琵琶记》这样一部富含思想深度和戏剧冲突并不强烈的剧作,若改编者仅选取其一些重要场次搬上西方剧场,彰显中国戏曲的魅力,也是可行的。德人洪涛生曾节译包括《琵琶记》在内的多部中国经典剧作,还组织德国剧团,于20世纪30年代将这些作品搬上舞台。在北平、上海等城市演出,取得成功后,还赴德国哈纳克剧院和奥地利霍夫堡剧院进行演出,大获赞誉[10]。
《琵琶歌》则将其改编成一部浪漫的爱情剧,讲述了蔡伯喈被迫入京赴试,高中状元后,牛王子逼迫他迎娶牛公主,他坚执不从。他偷偷托人往家里捎信和钱财,被牛王子发现,又被严加看守。家乡连年灾荒,蔡氏父母双双饿死,埋葬公婆之后,赵五娘前往京城。几经辗转,赵五娘来到牛府。牛公主让蔡伯喈在她和赵五娘中间进行选择,蔡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赵五娘。赵五娘对蔡伯喈说:“像凤凰和它的伴侣一样,我们生死相依,永不分离。”[11]82该剧被搬上百老汇舞台时,《纽约时报》的主打广告词便是“一个音乐爱情故事”(见图2)。被墨登肯定的最美的一支曲子《山高谷深》,副歌是“不管山有多高,不管谷有多深,我都会永远跟着你”,爱情表现得真挚、唯美。该剧主题发生的变化,若都教授所言:西方倾向于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来表现中国的传统题材[1]105。但这种改编,无疑剥离了原剧诸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仅剩一层肤浅的异域情调的躯壳而已。《琵琶歌》较之原剧,虽改动很大,但全剧仍有较大篇幅表现赵五娘独立持家的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和蔡伯喈面对牛王子不断逼迫的奋力抗争,几无轻松欢快的情节。这与百老汇音乐剧幽默风趣、轻松活泼的风格亦不甚吻合。
第二,文本重构不力。原剧“情节多破绽”没有被合理解释,在文本重构中又演变为新的漏洞。文学作品的每一次改编都意味着文本的重构,从中国传统的《琵琶记》到美国百老汇的《琵琶歌》更是如此。祖克在《中国戏剧》中曾云:“除了对话和舞台设计,《琵琶记》更像是一部小说。将其编剧技法撇开不说的话,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便是对儒家思想的传达(这种思想也在明代复兴)。该思想在家族系统的表现,便是其中我们看到的老年人的自私。看过主人公蔡伯喈的传奇经历之后,西方人可以理解为何儒家经典谈到寡妇和婴儿的同时,也会列举‘无子之父’。该剧的冲突集中在对高一级还是低一级意志的服从,也就是为国家服务,还是为家庭服务。但是当蔡伯喈以光耀门楣的名义去为国家服务时,这个问题模糊了,直至最终也没有解决。总体来说,这部字里行间充满中国式说教的剧作,与西方人重视实际的思想大相径庭。”[3]45
《琵琶记》重在表现蔡伯喈的心理活动和内在冲突,鲜少激烈的外在戏剧冲突。如牛丞相逼迫蔡伯喈娶牛小姐,他开始坚决反对,但当他向皇帝辞官不成后,还颇有些高兴地入赘到相府中。蔡伯喈的人身一直是自由的,但他并没有试图逃离牛府,也没有想方设法救助家人。也因此,该剧被认为情节上有诸多漏洞。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曾云:“若以针线论,元曲之最疏者,莫过于《琵琶》,无论大关节目背谬甚多,如子中状元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荣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报于路人。”[12]336冯俊杰教授在对《琵琶记》进行系统、详尽的注释和评析后,也曾说:“情节多破绽,是《琵琶记》最不可取处。”[7]285其实,《琵琶记》中除了情节设置有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之处外,还有多处与史实相悖。比如蔡伯喈与赵五娘、牛小姐“一夫二妇”的婚姻事实与宋元律法不符③。蔡伯喈中状元后入赘牛相府的情节,亦与史实不符。士子及第高中是为了光耀自家门楣,不是丧身失节,做上门女婿,去光耀别人家门楣,且蔡伯喈已娶赵五娘,不符合娶不起妻子需要入赘的基本条件。“长才硕学”“以名节自励”的高明为何这样架构情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为赵五娘设置特定的戏剧情境,让她独立撑持灾荒中的家庭,孝养公婆,以凸显“有贞有烈”赵五娘的形象。第二,表现高明辞仕归隐思想,做官就像入赘一样,身不由己,连自己的家人都无法照顾。
由于《琵琶记》采用隐喻的方式表现主旨,甚为隐匿。更由于中西文化和戏剧表现手法的差异,使得西方人接受该剧的诸多内容时更为不易。厄文在改编时,遂依托原剧的人物和故事框架,进行了大胆的文本重构。重构时,原剧“情节多破绽”没有被合理解决,反而又衍生出新的漏洞。比如赵五娘赴京到达牛府后,牛小姐让蔡伯喈在她和赵五娘之间进行选择。该情节的设置是厄文应女主角马丁要求改编而成,马丁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她不想和公主分享她的丈夫,更改之后作品对孝道的重视便转变为对婚姻的忠诚。厄文虽然很愤怒,但还是妥协了[2]174。从整个剧情来看,这一重要情节被更改成一道没有悬念的选择题。《琵琶歌》表现的是爱情主题。之前蔡伯喈面对牛王子的逼婚和拘禁,他不断奋力抗争,一直思念着父母和赵五娘。在寺庙中,他错失赵五娘,懊悔至极,疯狂地到处寻找。等他看到赵五娘,便狂奔过去,跪在赵五娘膝前。牛公主说道:“赵五娘,他选择你做他的妻子。”这样毫无悬念的情节设置大大降低了戏剧冲突的张力,对观众自然缺乏吸引力,观众难免有“百无聊赖”之感。又如一直逼迫、压制蔡伯喈的牛王子,一度为了女儿的婚事,拿蔡伯喈父母、妻子生命相威胁的牛王子,最后居然突然被蔡伯喈和赵五娘真挚的爱情所感动。他说道:“为这个孝顺的传奇故事,我要拜倒在他的光辉面前。甚至我要撰写一部历史专论来延续这一传奇。”[11]82蔡伯喈和牛王子之间激烈的戏剧冲突,在牛王子的顿悟中瞬间化解。这样的情节编排缺乏内在的逻辑和说服力,难免有评论指出“观众感受不到流动与角色的内在”。
三
《琵琶歌》在美国百老汇改编和搬演没有成功,至少给我们两方面的启示:第一,中国戏曲本土研究的重要性。《琵琶歌》在百老汇搬演没有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受众认为作品思想贫乏、人物缺乏生命力。剥离掉原剧丰富的文化内涵,仅剩下一副异域风情的躯壳,其思想必然是贫乏和单薄的。没有文化承载的人物,也必然是无生命可言的。反观该剧之前在国内的研究,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便是对该剧主旨理解得不够深刻。国人都不能很好地理解富含本土传统文化内涵的作品,有文化之隔的异域学者和受众就更难理解了。王国维在《译本琵琶记序》中曾言:
欲知古人,必先论其世;欲知后代,必先求诸古。欲知一国之文学,非知其国古今之情状学术不可也。近二百年来,瀛海大通,欧洲之人,讲求我国故者亦伙矣,而真知我国文学者盖鲜,则岂不以道德风俗之悬殊,而所知、所感,亦因之而异欤?抑无形之情感,固较有形之事物为难知欤?要之,疆界所存,非徒在语言文字而已[13]248。
王国维所言主要是就中国戏剧的翻译而言。其实,对中国戏剧的域外改编来说,更是如此。《琵琶歌》的改编,源于厄文对其原作《琵琶记》的猎奇心理。但从祖克对《琵琶记》的分析来看,受国内学界认为该剧是表现封建传统“忠”“孝”伦理观念的影响,西方学者将该剧定位为一部宣扬“孝道”的剧作。但当用孝道来审视该剧时,又会发现诸多难以理解的情节设置,国内学者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漏洞和剧作家编排水平不够。比如冯俊杰先生曾说:“作者既要写悲剧,又要写团圆;既要写伯喈背亲弃妇,又要写他全忠全孝;既要写牛相的冷酷自私,以势压人,又要写他尚有仁心慈肠,长者之风。于是作者只好让牛相‘暗中思忖觉前非’,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借以解决多种矛盾,及创作中的两难处境。至于因此而会造成多少个不自然,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他统统顾不得了。”[7]285熟谙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国内学者也只能如此理解,西方人遂只能剥离掉他们不能理解的内容,改编为适合西方人审美习惯的情节。要想促进戏曲的传播,必须重视戏曲作品本体研究。要想深入理解富含本土传统文化的戏曲作品,必须重视戏曲的本土研究。
第二,寻求不同地域文化的契合点,是中国戏剧海外传播的核心所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北杂剧《赵氏孤儿》和《灰阑记》,便是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传播的作品。前者的成功,主要基于此部作品与西方悲剧观念比较吻合,正如王国维所云: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3]85。后者的成功,则是基于中西方对母子亲情的礼赞和对智慧的推崇。《灰阑记》最核心的情节是包拯利用灰阑断案。根据母亲爱子护子的心理,包拯巧设灰阑计,把孩子放在用石灰画成的圆圈之中,让孩子的生母张海棠和霸占孩子的马氏从两边拉小孩。并说道:“若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得出来;不是他亲养的孩儿,便拽不出来。”[14]2845张海棠因担心拉伤孩子而不忍用力,马氏两次将孩子拽出。包拯由此断定孩子的生母是张海棠,并将孩子判归其有。《圣经·列王纪上》“智慧的断案”条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两个妓女都生了一个男孩,两人住在一起。一天夜里,一位妓女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就把另一位妓女的孩子抱到自己怀里,并将已死去的孩子放在那位妓女怀里。那位妓女醒后发现怀里已死的孩子不是自己的,于是她们发生争执,最后告到所罗门那里。所罗门见二人各执一词,于是就让人拿刀来,并言道要将活孩子劈为两半,一人一半。活孩子的母亲央求道:“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死孩子的母亲则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所罗门于是将孩子判给不要杀孩子的那位母亲。母子亲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遭遇不幸寻求公正是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对比两则故事,包公断案之智慧更引人入胜。我认为这是《灰阑记》能够在西方广泛传播、被成功接受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赵氏孤儿》和《灰阑记》是西方人找到了与自身文化相契合的方面而主动接受的话,那么梅兰芳访日演出则是国人积极主动推进中国戏曲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例证。梅兰芳一生共有三次访日演出,其中1919年第一次访日演出最受欢迎的剧目是《天女散花》和《御碑亭》。《天女散花》塑造了一位超凡脱俗的仙女形象,载歌载舞,唯美的艺术效果自然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受众产生共通的审美享受。正如袁英明所云:“《天女散花》是佛教题材,舞蹈动作吸取了佛教以及敦煌艺术要素。舞蹈和造型优美、庄严、飘逸、典雅,具有东方文化和东方艺术的意蕴。对于日本观众来说,即使语言不通也不至于产生审美抵触,反倒容易接受,产生审美愉悦,形成审美共鸣。”[15]199《御碑亭》与《天女散花》不同,是一部表现女性和男性不平等地位的戏曲作品。《御碑亭》原名《王有道休妻》,剧写王有道赴京赶考,其妻孟月华独自归宁。孟氏返程途中,适逢下雨,避于御碑亭中,到亭子来避雨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秀才。二人终宵未交一语,早晨雨停,各自离去。孟氏感秀才守礼,归告小姑子淑英。王有道赴试回来后得知此事,怀疑孟氏和书生有私,遂将孟氏休掉。后王有道获知真相,向孟氏请罪,二人重归于好。梅兰芳饰演孟月华,他重在揣摩人物的内在心理,将孟氏在御碑亭避雨时那种担心、羞涩复杂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感人至深。该剧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日本女性的地位与中国女性相近,正如梅兰芳所言:
这出戏引起一般妇女观众的共鸣,原因是日本妇女和从前中国的妇女一样,都是长期的受尽了封建制度的折磨。自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严申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之义以后,夫妻之间,夫权至高的现象有加无已地发展着。据说日本歌舞伎“世话物狂言”所反映的就多半是妇女被冤屈以及恋爱不自由等等故事。以“御碑亭”的本事来讲,因为一点误会,就被王有道使用至高的夫权,几乎给一个善良的妇女造成悲惨的前途,这一点使一般日本妇女寄予无限的同情[16]。
找准了中日文化的契合点,是梅兰芳《天女散花》《御碑亭》能够在日本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
20世纪上半叶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重要时期。中国经典剧作《琵琶记》凄美的情感、厚重的文化内涵及承载它的传统戏曲形态,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对中国文化无限好奇的美国年轻人厄文。基于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和欣赏该剧的一次独特体验,在汲取欧洲汉学营养的基础上,他抱着猎奇心理和对该剧的尊重态度,与霍华德一起改编为音乐剧《琵琶歌》。但他们并没有理解该剧深刻的精神内核,也没有找准与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在搬上百老汇舞台的过程中,他们又受到投资者、主演要求的掣肘和服装、道具、舞蹈指导等诸方面因素的牵制。总之,这是一次“高尚且真诚”的尝试。这次尝试虽使该剧呈现出“既非中国的亦非音乐喜剧”的稚拙,但它对中国戏曲域外传播提供的启示,值得我们进一步品味和思考。
注 释:
① 该书第三章为《明代戏剧和〈琵琶记〉》,除用两页篇幅简要介绍明代戏剧发展的概况外,其余内容便是分析和探讨《琵琶记》。《琵琶记》为元代南戏,祖克受当时欧洲汉学的影响,误将《琵琶记》当成明代剧作,这对后世西方学者影响比较大。
② 马丁是女主角,饰演赵五娘;博瑞纳(Brynner)是男主角,饰演蔡伯喈。
③ 《宋刑统·户婚律》载:“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见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大元通制条格·户令》“嫁娶”条明文规定:“有妻更娶妻者,虽会赦,犹离之。”见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
——探索人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