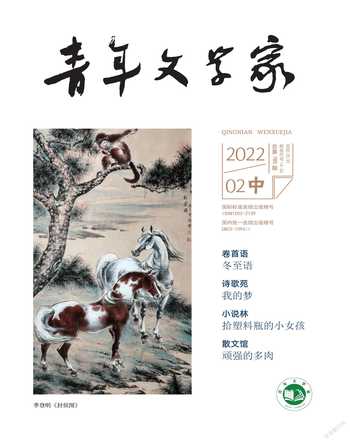知人论世视角下《琵琶记》的矛盾合理化
王志超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至正四年参加乡试,次年考中进士,任处州录事,此后为官多年,不见显宦。《琵琶记》写于其旅居宁波栎社沈氏楼中,高明少有大才,抱有儒家传统的入仕为官的有为思想。且高明出生于一个诗礼之家,自小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就学于大儒黃溍,其思想内核中的理学观念影响着他的言行与创作。
通过研读《琵琶记》,不难发现其本身存在着一些矛盾之处。首先,是《琵琶记》的主题矛盾,这一矛盾屡屡形成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其次,是《琵琶记》中蔡伯喈形象之矛盾,这一矛盾也是历代戏曲名家讨论的重点。两大矛盾又以作者对科举制的矛盾态度相联结,对读者把握《琵琶记》的主题、形象、内在动力造成了相对的困难,因此也产生了许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当高明的生平遭际被引入到戏文阅读中,这些看似对立的矛盾却有了同一性的内核,表现出合理化的倾向。
一、《琵琶记》主题矛盾的合理性
《琵琶记》的主题历来有两种相悖的理解,体现着《琵琶记》在主题方面的矛盾。高明在《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的《水调歌头》一词中点明剧本主题是“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宣扬伦理道德是高明创作这一戏文的目的;刻画“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是其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戏文内容中,作者要表现的主题发生了偏差。赵贞女依旧“有贞有烈”,但是其形象核心却深化为“孝”。赵贞女的贞烈并未被鲜明地突出,但是贤惠、坚忍、吃苦耐劳,竭力赡养公婆的典型孝妇形象却出现在舞台中心。而蔡伯喈,“全忠全孝”实则沦落为不忠不孝,本以考中科举尽忠尽孝,但因科举忠孝难两全。由此,《琵琶记》的主题被解读为是揭露封建社会旧道德、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指出悲剧的来源就是封建礼教观念的束缚。为何作者明确提出此剧“关乎风化”,却在内容上发生矛盾呢?观照高明生平遭际和思想观念,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合理化解释。
(一)“全忠全孝”主题在道德层面的实现
观照高明生平可知,他深受家庭诗教观和师学传承的影响,在理学体系影响下,他立身处世都符合儒家道统要求。在戏曲创作上,突出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关乎风化,宣扬伦理道德。从这个层面来看,蔡伯喈确是“全忠全孝”的。“三不从”就是蔡伯喈“全忠全孝”的表现。
首先,“辞试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孝”。在第二出为二老祝寿时,蔡公就说:“卑陋,论做人要光前耀后。劝我儿青云,万里驰骤。”在第四出,蔡公更是强迫新婚燕尔的蔡伯喈上京赶考,说:“孩儿,天子诏招取贤良,秀才每都求着科试。快赴春闱,急急整着行李。”面对父亲的强烈要求,恪守“父父子子”伦理观的蔡伯喈只得遵从。虽然蔡婆极力反对蔡伯喈远游,说“万一有些差池,教兀谁管来?你真个没饭吃便着饿死,没衣穿便着冻死”,但是在封建家庭“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下,蔡婆的意见却无关紧要。因此,遵顺了父亲意愿,进京赶考的蔡伯喈在当时是“全孝”的,只是这种愚孝的行为反而造成了不孝的后果。
其次,“辞官不从”体现了蔡伯喈的“忠”。当蔡伯喈“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时,本来皆大欢喜的高中,却让蔡伯喈陷入两难。入仕为官表明他完成了父命,实现了孝道,但是入仕之后的牛丞相逼婚,使他身恼心烦,一方面他担心牛丞相上奏皇帝,请求赐婚;另一方面,蔡伯喈已从牛丞相势大压人的行为看到了官场的艰难。所以,他上旨辞官,请求回乡,结果却被认为是嫌官小,皇帝驳回蔡伯喈的请求,而蔡伯喈只能卑微顺从。单单就蔡伯喈这一顺从的行为来看,蔡伯喈在君臣纲常上做到了“忠”,并且他在请旨的时候,只说“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要“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这些无力的请求和决心,或许表现了他潜意识下不愿辞官,只是借助外力消解自我矛盾中的一种方式。
最后,“辞婚不从”也表现了蔡伯喈的“表面道德”。一方面,在儒家道德观念影响下,糟糠之妻不可抛这一道德要求是造成蔡伯喈矛盾心理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花容月貌的丞相千金又时刻激发着蔡伯喈的本我情欲,在道德和情欲的冲突下,蔡伯喈选择借道德收获情欲的方式,再次借助外力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在道德外衣下,他多次辞婚,搬出许多道理,试图为自己寻找道德站位,并从道德层面消解自己富贵忘妻的愧疚感。但是,牛丞相的权势无视蔡伯喈的道德攻击,“强鸾就凤”中蔡伯喈完成了道德和情欲的双重收获。
因此,光从道德层面看,蔡伯喈听从并完成父命,他是“全孝”的;他辞官未遂,入仕为官,是“全忠”的;他试图从道德层面瓦解牛丞相的逼婚之举,却迫于丞相势大而屈从。在表面上,蔡伯喈的道德形象是无法否认的,他的行为都是在顺从,都符合作为孝道主体的父亲和忠义主体的皇帝的要求。
(二)“全忠全孝”在情欲层面的破碎
在道德层面,蔡伯喈是“全忠全孝”的。但是从情欲层面来说,他的“全忠全孝”消融于“不自由”之中。从“三不从”来看,蔡伯喈本身就是矛盾的结合体,他既想要“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的功名富贵,又推掉举荐,想着“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他既在《杏园春宴》中对金榜题名喜不自胜,又以“事父母、乐田里,初心愿如此而已”为由辞官回乡;他既幻想“未许姮娥爱少年”,痴醉于牛小姐的花容月貌,又纠结于富贵不忘糟糠之妻的道德伦理。在情欲与道德的碰撞中,他是不自由的。
反观高明的一生,他似乎也对此深有体会。高明入仕元朝,在至正八年时,参与镇压方国珍义军,但是他与主帅意见不合,深感于自己官微言轻,所以再不管事。当被镇压者招安翻身,摇身变作封疆大吏时,面对方国珍的招揽,高明或许心有芥蒂,自己入仕八年,仍是一谋士。于是,他推辞告归,旅居四方。在当时那个年代,文人在政治上是极不自由的,延及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戏剧家,他们只得用戏曲文艺寄托情怀,以剧中人物表现自己的不自由。对于高明来说,蔡伯喈这一形象就是极好的代表。蔡伯喈的原型是东汉末年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时代背景与元末的时代背景相似,蔡伯喈的文人身份与自己相似,同时蔡少有大名,博学强识,而高明认为自己也是博学多闻之人。此外,对儒家道统的信服也是高明选择蔡邕的原因。因此,在东汉末年不自由的蔡伯喈成为在元末不自由的高明的化身,他寄托着高明想要科举入仕,功成名就的政治理想,也是高明理学思想影响下重视风化的道德化身。
“不自由”是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普遍状态,蔡伯喈在戏文中的不自由,或许可以看做是当时文人生态环境的现实投射。
总之,《琵琶记》主题的矛盾在道德方面是可被消解的,在情欲方面是可被理解的。不论是表面道德,还是情欲上的不自由,或許都是造成蔡伯喈忠孝矛盾的原因。
二、历史和戏文中蔡伯喈矛盾形象之合理性
《琵琶记》本于南宋早期南戏《赵贞女蔡二郎》,高明在这部南戏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了大幅的增改,且丰富了戏文的曲词。《琵琶记》的男主角蔡伯喈是东汉末年名士蔡邕的戏文化身,但是对比二者形象,历史中和戏文中的蔡伯喈差别较大。《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蔡邕少年博学,孝行、人品、学问冠名当世,司徒桥玄征辟蔡邕为官,后又任河平长,拜郎中,迁议郎,迫于董卓势力,担任侍御史、侍中、左中郎将等官职。这与《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有差距,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中的负心汉更是相去甚远。在《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中,东汉名士蔡邕的为人和结局被极尽贬低,据徐渭《南词叙录》载“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蔡邕被冠上忘恩负义、天罚身亡的耻辱标签。但同为文人,高明应该对传统戏文中的恶形象蔡伯喈排斥且弃用,为何高明在写这一戏文时,仍选取蔡伯喈为男主人公?虽然作者心目中的蔡伯喈是“全忠全孝”的代表,但是戏文却为何多次表露出蔡伯喈这一形象的人性弱点?从高明视角出发,或许可以得到以下合理解释。
(一)历史形象与戏文形象相映照
《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这说明历史中的蔡邕本身就是大孝子。同时,蔡邕博学有名,才华卓越,是当世公认的名士。这非常符合高明的创作初心,“性笃孝”满足“全孝”的条件,拥护汉朝,反对董卓是“忠”的表现,才学突出是高中状元必备的条件。历史中的蔡伯喈在这些方面都符合作者的要求。
此外,历史中的蔡伯喈也不自由,他反对董卓,但是迫于董卓势大,只得在董卓手下为官,一生遭遇坎坷,最终死于狱中。从情欲的不自由层面来看,历史中的蔡伯喈也与戏文中矛盾的蔡伯喈相契合。
而戏文中的蔡伯喈在南宋就被赋予负心形象,《陆游》曾作《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中有“死后是非谁管的,满村听说蔡中郎”。这说明在陆游之前,蔡伯喈在戏文中被打成负心汉就已出现。陆游的这首诗,似乎是为蔡邕鸣不平。当高明开始创作这一题材时将“背亲弃妇”的蔡二郎改写成“全忠全孝”的蔡伯喈,试图为蔡伯喈洗冤。这不仅是出于对古代贤人被恶意诽谤行为的不满,也是借蔡伯喈浇自己胸中块垒。
这种为蔡伯喈洗冤的说法早已有之。明人黄溥言在《闲中今古录》中写到“元末,永嘉高明……编《琵琶记》,用雪伯喈之耻”,徐渭在《南词叙录》中也说“(高明)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由此看,为蔡伯喈雪耻的说法广泛流传,虽然在李贽看来这纯粹是高明用来解嘲的“鬼语”,沈德符明确表示“雪冤”不可能,但是从高明的儒学观念和《琵琶记》的戏文可以看出,高明对蔡伯喈这个形象是认可的,虽然包蕴着许多矛盾,但是很可能是借之抒发自己的不自由。从这一角度来看,高明仍然选取蔡伯喈作为男主人公既是为古代贤者洗白,也是寻找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形象寄托情怀。
(二)文人相惜意识下对蔡伯喈形象的洗白
在相似性格、相同遭遇之外,高明将自己的遭遇寄托其中,在自视、他视中完成了蔡伯喈这一形象的再创造,这是高明的创新。
在养亲方面,蔡伯喈在大孝科举和小孝守家的矛盾中被撕裂,最终大孝战胜了小孝,落了一个功名换伦理的悲剧结果。造成这一悲剧的因素有封建家教的愚孝观、金榜题名的功利观、文人怀才的社会观,这些观念都被科举至上的社会理念所统驭,其结果就是蔡伯喈落得一个忠孝难两全的境地。在《琵琶记》中,高明为蔡伯喈的养亲行为做了很多辩解,如在《高堂称庆》中蔡伯喈唱道:“十载亲灯火,论高才绝学,休夸斑马。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鱼龙将化。沉吟一和,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这说明蔡伯喈在赡养父母和实现个人价值二者间是极其矛盾的,因而产生了逃避心理,将功名富贵寄托于天命。思索再三,他选择了孝,为了父母放弃了个人理想。但蔡父“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大义逼试蔡伯喈,使之再次为了父母改变个人决定。可以说,在高明心中,蔡伯喈是孝的,只是忠孝难两全,文人的命衰体现于此。
蔡伯喈的科举之难反映了古代读书人的普遍境遇,高明也不例外。高明出生书香门第,从小接触的文化熏陶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仕宦观,在人种限制的元蒙王朝依旧科举入仕,虽未能显宦,但也经历着仕宦之痛:一是怀才不遇之痛,二是游宦离乡之痛。因此,戏文中的蔡伯喈既呈现着这种痛苦矛盾,又寄寓着作者未就的梦想。金榜题名、榜下捉婿、皇帝重用、娇妻贤妇,这是文人的梦想;忠孝难两全、游宦思乡、高官压迫、难有自由,这是现实之痛。且高明受到理学思想节欲修理的观念影响,对能激发功名观的科举本就矛盾,所以,体现在蔡伯喈身上也必然是矛盾的。因此,在文人共同命运的观照下,高明笔下的蔡伯喈形象是矛盾重重的,这些矛盾不尽然是文人自身的懦弱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观念下的不自由。
《琵琶记》的矛盾之处还有很多,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推敲其中矛盾的合理性是可行的。不论是主题矛盾,还是形象矛盾,都统一于高明的创作机制和创作心态。甚至于,将《琵琶记》放到元末的大环境中,可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价值观念观照戏文,从而找寻到《琵琶记》诸多矛盾的内在合理性。
——探索人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