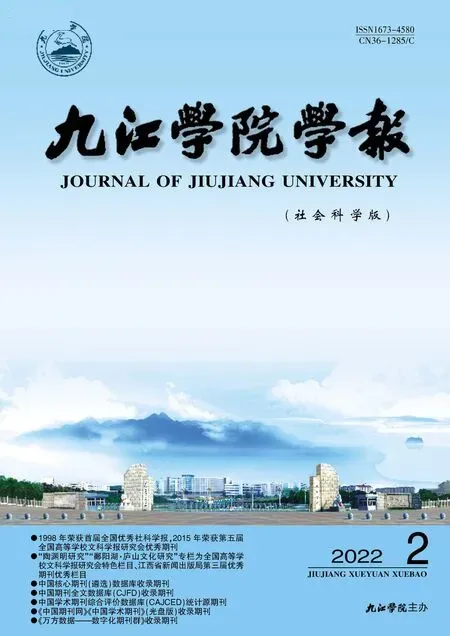《南北朝新语》体例摭谈
王贝贝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南北朝新语》是一部“世说体”小说,明代林茂桂辑,詹子忠评,有天启元年(1621)序刊本,天津古籍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了高洪钧校注版《南北朝新语》,后者现为通行本。《南北朝新语》全书共四卷,卷一包括孝友、烈义、严正、鲠直等15门,卷二包括品鉴、标誉、学问、作述等16门,卷三包括宫闱、恩宠、除爵、政迹等16门,卷四包括俭啬、汰侈、狎侮、诞傲等15门。全书共2300则故事,主要记录了南北朝时期士族文人的遗闻轶事,是一部南北朝士人的“写真集”。
“世说体”一词,最早由宁稼雨先生提出,他说:“‘世说体’是指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的一种结构方式。这种方式,把书中的故事按内容分为若干门类。每一门类中以不同人物的故事,表现相同的故事,表现相同的主题。”[1]后来,宁稼雨对“世说体”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世说体”小说是“以知识分子队伍为《世说新语》这类小说的作者主体”,并且,“问题的关键在于志人小说的作者能把自己的生活追求、审美情趣与作品中的文人相互作用,能从更为广阔的范围上,表现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2]宁稼雨在其著作《中国志人小说史》中提出:“琐言小说多摹仿《世说》以类相从的体例,以记载文人事迹为主;……逸事小说在形式上则追随《西京杂记》,不分门类,只分卷次,……,为方便起见,笔者将此二类小说分别称为‘世说体’和‘杂记体’。”[3]《南北朝新语》作为“世说体”小说,正如刘强所言:“此书分类,显然受《焦氏类林》诸书之影响,于《世说》有破有立,其中如‘见败’‘阴德’‘征兆’‘古物’等多门,为此前《世说》仿作所未见。虽然分类驳杂繁琐,‘类书化’倾向明显,且颇杂搜神志怪之谈,有乖《世说》‘志人’之特质,但仍然体现了作者对《世说》分类学进一步探索的努力。”[4]此评价很公允,道出了《南北朝新语》体例方面的特点和贡献。
《南北朝新语》延续《世说新语》的体例,具体表现为:分门隶事,以类相从:将全书2270则故事分门别类且“品目倍于《世说》”。依人而述,品第褒贬:《新语》延续《世说》人物品评之风,以人为本,勾勒出南北朝士人的品貌思想。断而不断,勾连互见:《新语》截取人物言行片段,但又在不同门类展现同一人物的不同形象,让某些人物更加立体鲜活。
一、分门隶事,以类相从
刘知几《史通》中将小说分为十类:“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5]《世说新语》属于“琐言”:“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6]《世说新语》既然作为“琐言”,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大放异彩,这就涉及到《世说》的体例问题,它分门别类地把这些内容进行排列,为作者的思想意图增势,并且在分裂中又能实现聚合,让一个人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
刘熙载《艺概·文概》亦言:“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7]可见《世说新语》的文体新创之功,《南北朝新语》的体例首先体现在对《世说》“分门隶事,以类相从”的继承。林茂桂《南北朝新语》自序言:“余雅好齐、梁间绮语,少年浮猎一二,以供操觚,未能概睹其盛。归田三十年来,乃得游意恣收,纸窗竹屋之中,松雨梧烟之下,若与颜、鲍、温、庾诸君相对语,洋洋如也。常恨刘义庆不生于武德中,尽两京八朝而诊缕之,俾后之捉麈者得以窥炙輠悬河之奥,而摛藻者亦得以穷游鱼翰鸟之趣。几上置《世说新语》一编,思有以比拟之。……夫晋人尚清谈,每吐一语,辄玄淡简远,诙谐多致。义庆虽宋实晋也,沐浴江左之风流,故独能发其逸韵,而因以旁及于汉魏。无论宋、元人,不能肖其吻角。既以开元、天宝间语参之,亦觉有龃龉不相入者。何氏之蒙讥也固然,然临川摇笔之际,已为齐、梁以下之滥觞矣。……屏居无事,辄取南北朝汇之,积以岁月,不觉成帙,部为四卷,品目倍于《世说》,而标题仍其旧名。其敢与临川王扬镳争道,亦聊以毕吾志也。”[8]林茂桂在自序中指出自己编纂此书的缘由,是因为对南北朝时期的佳丽词句甚是喜爱,又因政治原因归田数十年,既无俗务缠身,又爱好齐梁绮语,且追慕《世说》,各种因缘际会下作成《南北朝新语》一书。《南北朝新语》可以说是林茂桂读书期间的摘录性质的读书笔记,积少成多之后,按照《世说》的体例,但又因品目倍于《世说》,所以比之《世说》会有新变,詹子忠在《南北朝新语》又序中言:“林德芬读书,尽窥瑯嬛之秘。弱冠魁南宫,授深州刺史。辍罢归田间,牢骚愤懑之气,毕以舒泄于汲书蠹简之中。”好友詹子忠认为林茂桂著书是因为抒发不平之气,从《南北朝新语》的类目设置和材料的选取中不难窥见林茂桂对邪恶的批判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任肩生在题《南北朝新语》叙中言:“今德芬林氏,取南北朝佳事佳话,辑为卷四,亦称‘新语’,于以羽翼临川而节缩元朗,用志勤矣,厥功伟矣。” 南北朝作为接续魏晋的朝代,南北朝士人受魏晋风度的影响颇深,他们的很多言行举止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继承,因此《南北朝新语》纯写南北朝故事,让魏晋六朝士人的风神气韵能够实现串联,让后世得以窥见全貌。由上述序言可知林茂桂编撰《南北朝新语》的意图主要是:追慕《世说》;抒其胸臆;垂范世人。
《南北朝新语》是典型的“世说体”小说,取材于《南》《北》史,截取部分内容,体制短小,全书共分六十二门,将其与《世说新语》的类目进行比对,具体见表1:

表1 《南北朝新语》与《世说新语》类目比较
由上表可知,《世说新语》对《南北朝新语》影响之深远。另外,《南北朝新语》根据需要另行开辟新的门类,并重新排列,又有其创新性,有很多门类是林茂桂的自我创造。如孝友、烈义、清介、恬洁、谦慎、料事、见败、图新、阴德、玄解、机警、命名、书法、游览、交游、酒食、宫闱、除爵、才略、镇定、荐引、报酬、膂力、佞幸、黜免、赦宥、惩戒、死徙、狎侮、痴呆、黩货、征兆、异迹、古物。林茂桂将这些零散小篇按照内容和思想的相似性大致归为一类,如《孝友》专门记录南北朝士人的孝亲行为,第一条言:“臧盾有孝性,居丧五年,不出庐户。官至御史中丞。”臧盾之母刘氏暴亡,其左手中指疼痛不能眠,是为母子感应,及父丧,臧盾形容憔悴,家人不识,居丧五年。至于累迁至御史中丞,臧盾有孝性并非直接原因,但此条编者经过剪裁,给人一种臧盾因有孝性才官至御史中丞,可见编者垂范世人的意图。第十七言:“元子华母房氏,曾就亲人饮食,夜还大吐,人以为中毒,母甚忧惧。子华遂掬吐尽噉之,其母乃安。”詹子忠评曰:“假使真毒,噉吐不重,忧其母耶。”元子华为了使母亲心安,竟“掬吐尽噉之”,为了孝道,能为人所不能为。第十九言:“崔子豹,五岁丧父,不肯食肉。后丧母,哀毁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风吹即倒。’”崔九作孝,为人所敬,编出歌来传颂,可见时人对此类孝心的推崇。这些短篇,有些符合雅正的礼制规范,但有些行为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然都能表达共同的崇尚孝道的主题,因而被编者收录进《孝友》一类。再如《严正》一门,第十五言:“柳彧为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所惮。时杨素以小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之,于阶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据案端坐,立素于庭前,辨诘事状。上方信任,素亦未有以中之。”评曰:“可谓不避权贵矣。”第十六言:“邢峙以经授皇太子,厨宰进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评曰:“忠臣爱君,防微杜渐。”有人不避权贵,有人谨慎入微,但都是严正的君子,因而被编者录进《严正》这一门类。
总之,《南北朝新语》作为一部重要的“世说体”小说,它自然地承继了《世说新语》的体例特征,但由于林茂桂为明人,虽记录南北朝事,但在材料的选用和剪裁上亦能看出编撰者受到自身经历和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林茂桂受诬而被罢官,因而他编撰《南北朝新语》时所生发的门类恰能体现出他内心的愤懑如佞幸、黜免、赦宥、惩戒等。受到晚明思想解放思潮的影响,他追慕魏晋风度,因而设置了和《世说》相类似的门类来和魏晋风度映照。
二、依人而述,品第褒贬
《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小说,《南北朝新语》作为“世说体”小说,同样是“依人而述,品第褒贬。”此书志人,描写生动,在门类中即寓褒贬,这种品评人物的风气是承继《世说新语》而来,《世说新语》又是受汉末人物品藻和魏晋玄学清谈风气的影响。《南北朝新语》门类的划分大致按照人物的道德、品性标准,各个门类之间又大致遵从由褒到贬的规律。《论语·先进》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朱熹评曰:“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9]此条主要体现的是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观念,但是同样体现出了孔子对这十个弟子的赏誉和品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科”,孔子因材而施教,亦可看作人物品评的早期样态。《世说新语》因撰者和时代的原因首冠“孔门四科”,在形式上标举儒学,“德行”即道德,“言语”即言谈、谈话,“政事”即行政事务,“文学”即文章、学术。
《南北朝新语》虽然没有直接从名称上承继“四科”,但从其内在思想和类目设置可以看出,很多门类仍不出“孔门四科”的范畴,如与“德行”相类似的门类,孝友、烈义、严正、鲠直、清介等皆为标举德行,如《孝友》第一条:“臧盾有孝性,居丧五年,不出庐户。官至御史中丞。”突出臧盾“孝”的德行,《烈义》第十条:“王昕少时,与河间刑邵为友。及守东莱郡,邵举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从弟,会兵将执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执子才,当先执我。’邵乃获免。”突出王昕“义”的德行。这些都是德行的内涵,分散开来是独立的门类,但是也都可以统一在“德行”这一门类之下。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这些具有德行的孔门弟子,正是具有孝友、烈义、严正、鲠直、清介诸种德行。
与“言语”相近的门类如《清言》篇第三言:“元帝谓朝士曰:‘晋氏平吴,喜获二陆。今我讨贼,亦得两周。’尝著《金楼子》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情转无穷,亦一时名士也。弘王善清谈,梁末为玄宗之冠。’”可见南朝时期的清谈余音仍在,清妙玄淡的语言仍然为很多士人所推崇。第五条言:“来绘神情朗俊,河间邢晏之甥也。绘与清言,叹其高远,每称曰:‘若披重重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生。’”清言如珠玉,令人欣赏喜悦。第十二言:“阳休之除吏部尚书,谱悉氏族,每谓人曰:‘此官实自清华,但烦剧,妨吾赏适,真是樊笼。’”俱是志趣清高的言语。士人谈玄,往往侃侃而谈,甚或你来我往地进行论辩,且言谈清朗曼妙,听来使人敬服论者的口才,并且使人流连忘返。孔子周游列国,良好的口才是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手段,因而言语同样是孔子看中的特质。南北朝虽不用口才求官,但与人清谈论辩,拥有好口才同样很重要。
与“政事”相近的类目如《政迹》第一言:“南宋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词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言谈当笑,弥日未尝倦。若暇则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评曰:“如此通才,亦自难得。”体现出刘穆之的政治才能,能一心数用,且处理政事井井有条。《政迹》第四言:“王弘字休元,博练政体,斟酌时宜。将加爵于人,每先诃责,然后施予。若接语欣欢,必无所谐。人问其故,答曰:‘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若求者既无以为惠,人又不借颜色,即大成怨府。’问者悦服。”评曰:“自是持世善物。”突出王弘善于世务的才能,善于用人,恩威并施。入仕为官,兼济天下是儒家学者的理想人生范式,因而“政事”必然成为孔门四科之一,《南北朝新语》中“政迹”这一门类,显然是追随《世说》冠以四科的体例。
与“文学”相近的类目如《作述》第一:“谢徵美风采,善属文。梁武帝饯魏中山王元略还北,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帝深鉴赏。”魏晋六朝时期文学发展蓬勃兴盛,文学氛围浓厚,许多大家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文学开始走向自觉。因此著述作文,成为士人学者的追求。《作述》第六言:“张融以《海赋》示镇军顾顗之。顾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未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四语后所足。”评曰:“妙绝。”精彩的词句可为著作增光添彩,善美文也可以得到尊崇和赏识。孔子重视文学著述,既表达人生真谛,又宣扬政治思想。
除了受《论语》的影响,“世说体”小说的体例亦受到了汉末人物品藻风气和魏晋玄学清谈的影响,除了“孔门四科”之外,《南北朝新语》其他类目亦以人为本,以人物品评的词语为主,孝友指具有孝悌品格的人,烈义指忠义烈性的人,严正、鲠直是指正直的人,清介是指清廉的人,恬洁是指恬静自贵的人,谦慎是指谦虚谨慎的人,雅量是指有度量的人,贤媛是指贤德的女子,夙惠是指早慧的少儿,豪爽是指豪纵不羁的人,镇定是指淡定自若的人,佞幸是指奸佞的官吏,俭啬是指过度节省吝啬的人,汰侈是指铺张浪费奢侈的人,诞傲是指放诞不拘的人,险谲是指阴险诡谲的人……这些都是品评人物的词汇,看门类名称即可明白大概的主题内容。体现了“世说体”以人为主,品第褒贬的特点。
三、断而不断,勾连互见
范子烨在《<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中解析凌濛初对《世说》体例“断而不断”的特点时言:“其所谓‘断而不断’确是《世说》在体例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断’即各条分立;‘不断’,即各条之间相互勾连。”[10]《南北朝新语》亦如是,所谓“断”是指各条分立,一条就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条目的上下之间没有联系,所谓“不断”是指各条之间相互勾连,一个人物的不同侧面在不同条目中勾连互见,从而组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形象。
这种“断而不断”的手法,应该说也是《世说》承袭前人的结果,司马迁作《史记》最善用“互见法”,刘松来在《史记“互见法”初探》中提出:“从狭义来说,‘互见法’就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所指出的,所谓‘语在某某事中’的写作手法。”“从广义来说,‘互见法’则指《史记》全书在结构布局,在处理史实与相关人物关系,在艺术的典型化方面,所采用的‘此详彼略,互为补充,连类对比,两相照应’的一种运用十分广泛的表现手法”[11]。《世说》“断而不断”的体例特征就和《史记》“互见法”异曲同工,李士彪在《互见法溯源》一文中也提出:“其实,互见法作为一种撰文方法,并不仅仅限于史书,条件一但成熟,它就会油然而生。”[12]《南北朝新语》的这种“断而不断、互见勾连”的特征和互见法的内核原理是一致的,都是想要更全面地塑造人物形象。亦有不同之处,《史记》中的互见法同时也是为了更全面的叙述历史事件,而且互见法塑造人物力求人物事迹全面,而《南北朝新语》则是通过择取一个个片段来展示人物的多个侧面,但范围不出编撰者所设置门类。这种体例特征并不是为了互见而互见,而是编撰者在剪裁史料,择取录入的时候对某个人有倾向性或者他的事迹刚好符合此门类,因而录入。因为《南北朝新语》等“世说体”小说门类设置的丰富性加上以人为主的人物品藻特征,因而形成了这种和“互见法”同中有异的“断而不断,勾连互见”的体例特征。
从这个方面来说,《南北朝新语》的这种体例特征和《庄子》的编撰体例有些相像,吴琴提出:“《庄子》为了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每篇都有一个主题,每篇主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论述。但其书体例精严,各篇章之间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贯通的。庄子的思想是如此深邃高远,一个篇章往往难以承载如此丰富的思想观念,于是他就在一个主题之下专论一点,而将其它论点放入他篇中补充完整,或在其它篇章中用另一种形式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13]《南北朝新语》也是每篇围绕一个主题,一个人物在不同主题下出现,逐渐形成一个珠串式的完整的形象。
如《南北朝新语》中任昉出现了十次,分别在《孝友》《品鉴》《标誉》《学问》《作述》《清言》《异迹》等门类中。《孝友》第六:“任昉父遥,性重槟榔,临病求之;剖百许口,无一可者,寻卒。昉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父亲临终前想吃槟榔而未得以致抱憾而终,任昉便终身不食槟榔来弥补这一遗憾。第九:“任昉居丧过损,武帝谓其伯任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非直亡卿之宝,亦时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劝进饮食,回即呕出。”任昉居丧,哀痛至深,不思饮食,甚至损伤了自己的身体,武帝让其伯父任遐劝他进食,但他回家之后又全部吐出,可见亲人去世对任昉的打击,这两条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任昉其人孝亲至深。《品鉴》第二十言:“上谓任昉曰:‘诸到可谓才子?’昉曰:‘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任昉对别人的评价赞赏,有善于发现他人之美的品格。第六十七言:“任昉常自叹曰:‘知我者以叔则,不知我者亦以叔则。’时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王融有才?,自谓无对,见任昉文,恍然自失。”任昉对自己的评价以及王融对任昉的评价,突出任昉的文学才能。《标誉》:“任昉为中丞,欲造阮孝绪而不散,望而叹曰:‘其室虽迩,其人甚远。’殷芸欲赠孝绪诗。任昉曰:‘趣舍既异,何必相干。’”此条突出了任昉鲠直的个性,不与异趣者合流。《学问》第四十七:“任昉曰:‘酒有千日醉是与?’刘杳曰:‘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出杨元凤撰事。’”《作述》:“任昉为御史中丞,后世皆崇之号曰兰台聚。陆倕赠昉诗云:‘和风杂美气,下有真人游。壮矣荀文若,贤哉陈太丘。今则兰台聚,万古信为俦。任君本远识,张子复清修(率)。既有绝尘倒(溉兄弟),复见黄中刘(孝绰、范、孺、显也)。’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陆倕以诗对任昉进行品评,谓任昉为任君,比之为汉之三君,东汉时期,刘淑、窦武、陈蕃三人,是当时著名的名士清流,为世人所敬仰,东汉三君犹以陈仲举最为出名,刘义庆称其为士人的准则典范,有澄清天下的志向。任昉卓见远识,文采斐然,亦可称为一代之宗。第三十八:“任昉赠王僧孺诗曰:‘唯子见知,唯余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卷,升高有属,嘉尔晨灯,惜予夜烛。’”此为任昉给王僧孺的赠诗,突出任昉的词句佳丽,更显示出任昉对友人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深情厚谊。《清言》第十六言:“梁武与任昉相遇竟陵王西邸,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任昉被皇帝调笑,反而给予回击,显示出任昉不畏权贵的放诞性格,和魏晋风度契合,《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很多不畏权贵,自我觉醒,放诞不羁的名士,他们生活得肆意洒脱,不被礼法所拘,任昉此举正是魏晋风度的体现。《异迹》第二十五:“任昉字彦升,母裴氏,梦五色彩旗四角悬铃,其一铃落入怀中而孕,遂生昉。早称神悟。八岁自制《月仪》,辞义甚美。”评曰:“五色文采陆离,已应能文之兆。”任昉主要以文名于后世,此条颇具神幻色彩,给任昉此人注入了神话色彩,更具有小说化的色彩,突出了任昉能文的天赋。
《南北朝新语》亦多处提及谢灵运。《见败》第七言:“谢灵运问谢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曰:‘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容曰:‘若处贵而能遗权,则是非而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明哲保身,其在此乎。’”体现出谢灵运对人文学才能的看重,评价一人,要知人论世,不仅要代入时代,也要人文合一,虽潘、陆才情甚高,但游于权贵始终为后士文人所诟病,陆机要匡复家族,且因孙吴战败而入晋,自然要小心恭谨。潘安作《闲居赋》,现实中对贾谧极尽谄媚,望尘而拜。但是谢灵运对二人评价甚高,是因为对二人的文学造诣的认同,不因人废言。可见谢灵运文学追求的纯粹。《品鉴》第二十五言:“谢灵运,奕之曾孙而方明从子也。父瑍生而不慧,官秘书,早亡。灵运幼便颖悟,祖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儿何为不及我。’袭封康乐公,世咸称谢康乐云。”体现出谢灵运聪颖有悟性,从小便被寄予厚望,承担起家族兴旺的责任。《标誉》第七言:“谢灵运诗书兼绝,文帝称为二宝。”文帝把谢灵运的诗文和书法称为两样不可多得的宝贝,突出谢灵运在诗书上造诣之深。《机警》第二言:“灵运父瑍无才能,为秘书郎,早亡。而灵运好臧否人物,谢琨患之,欲加裁抑,乃使瞻与灵运同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说明谢灵运善于审时度势,能够听取别人的建议并作出改变。《游览》第一:“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游遨,遍历诸郡,动逾旬朔。在郡一周,称疾去职。移籍会稽,修营旧业。因祖公之姿,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每寻岩陟岺,必造幽峻,尝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评曰:“东山故老,悠然自得。”谢灵运爱游山玩水,且颇有心得,制作出适合登山下山的木屐,谢公的木屐被后世文人视为风雅之物,谢灵运不为庶务缠身,不为官禄裹挟,因而才能具有如此心境。《游览》第二言:“谢灵运既东,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颖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谢灵运爱游山泽,开山水诗风气之先,能和自然互相交融,从自然中汲取精华。
《南北朝新语》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个人物的多个方面散见于各个类目中,这种断而不断、勾连互现的方式,让人物形象更加的丰满立体,让人物更加鲜活灵动。这种体例结构不仅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南北朝士人群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编者林茂桂在《世说》的类目下又增加了很多自创的类目,力求更加全面地展现南北朝士人的容止和风神,南北朝士人和魏晋名士的同与不同,也更加清晰可见了。
文章辨体自古以来就是历代文人关注的重点,研究作品的体例,有助于深入研究此类作品,能够把具体的作品放在同类架构中进行类比研究,可以分析出同与不同。《南北朝新语》作为“世说体”小说的典型代表,研究《南北朝新语》的体例,有助于增加“世说体”小说体例研究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