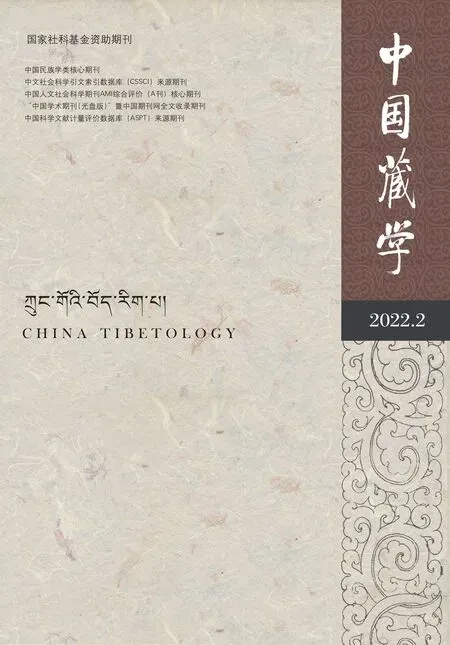藏文《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译注及相关史事研究①
李志明 索南旺姆
一、引 言
北京大隆善护国寺建于元代,原名崇国寺,明宣德四年 (1429)敕赐寺名 “大隆善寺”,成化七年 (1471)加赐 “护国”二字,简称护国寺。有明一代,护国寺是北京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大智法王班丹扎释 (1377—?)等一大批高僧驻锡寺内,或在内地译经传法,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或往藏地宣谕王化,加强明朝对西藏的有效控制。明宣宗、宪宗、武宗等帝王先后敕谕重修、敕赐寺名、御制碑记,在护国寺留下不少碑刻资料。明清以来,多有学者著录护国寺碑文,考证寺院历史及相关史事。①有关护国寺碑刻的介绍,参见 [明]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00、223页;[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3—36页;[清]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8—79页;[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42—847页。但以往所录碑文,大都限于汉文,对藏文等非汉文字碑刻关注不多。
护国寺诸多碑刻中,正德七年 (1512)藏文《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以下简称《御制碑》),记载了明武宗于正德五年 (1510)十一月至次年八月敕谕重修护国寺的详细经过,以及重修完成后佛殿的布局。这是北京地区独一无二的明代御制藏文碑。传世的明代御制汉藏合璧碑文屈指可数,大都集中在甘青地区,如青海乐都瞿昙寺的永乐十六年 (1418)《御制金佛像碑》、洪熙元年(1425)《御制瞿昙寺碑》、宣德二年 (1427)《御制瞿昙寺后殿碑》,甘肃岷县的宣德四年 (1429)《御制大崇教寺碑》等。北京虽为明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镇,但目前所知的明代御制藏文碑,则仅此《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一通。此碑原位于护国寺延寿殿右侧,现已下落不明,仅有三种拓片传世:1931—1932年,北平研究院组织的北平庙宇调查制作了碑文拓片,规格为300×124厘米;②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材料汇编·内四区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国家图书馆所藏此碑拓片编号8419,规格为252×124+46×32(额)厘米,据王建海老师介绍,国家图书馆的此碑拓片也出自1931—1932年的北平庙宇调查;③2021年9月5日电话采访。法国亚洲学会图书馆也有此碑拓片,编号SA030,252×124厘米。根据拓片显示,碑文正文共42行,1400多字。相比之下,前两种拓片比第三种多碑额,但第三种拓片更为清晰。
此碑拓片流传已近百年,但根据拓片录文进行研究则是较为晚近的事。黄颢先生《在北京的藏族文物》一书根据残碑进行录文,共340多字。经与拓片比对,黄颢先生的录文为原碑第1、10—14、18—26行和第42行的部分内容,约占全文四分之一,是此碑已知的最早录文。④黄颢:《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96页。恰噶·旦正先生和谢继胜先生等转录了黄颢先生录文,并将其译为汉文。⑤恰噶·旦正:《藏文碑文研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6—228页;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明)》,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9—210页。2017年出版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以下简称《碑刻志》),根据法国亚洲学会拓片首次录写了完整碑文。⑥[法]吕敏主编,鞠熙等著:《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四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610—614页。据《致读者》部分介绍,录文者为王薇和次陈桑杰 ()。
综上所述,已知《御制碑》共有三种拓片、四种录文和两种汉译文,但仅有《碑刻志》是根据拓片所录的完整碑文,尚无完整汉译文。有鉴于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参阅现有拓片和录文,查缺补漏,重新著录,尝试将碑文进行完整汉译,并考察此碑的流传情况、书写特点,以及碑文提及的寺院修缮过程和大庆法王身份等相关问题。
二、录文与汉译
(一)录文
1.碑额
《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一书和国家图书馆所藏拓片8419号,均有碑额拓片,规格为46×32厘米。但需注意的是,前者在刊布时将碑额倒置于正文上部。
碑额内容竖排两列, 从右往左书写, 为八思巴字“’aeu i'euŋ seiw tey luŋ/šêm ɣu gwuê sei i bur”,①碑额部分八思巴字的识别得到桑吉扎西和王宣力二位老师的指点,特此致谢。对应的藏文为 “”,系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的音译。用八思巴字音译御制碑额,在现存明代碑文中尚未见到第二例。其余几通明代御制碑文的藏文碑额都是意译或音译和意译结合,而非单纯音译。例如永乐十六年的瞿昙寺 “御制金佛像碑”,藏文碑额用楷体 ()横书作 “”;洪熙元年的 “御制瞿昙寺碑”,藏文碑额楷体横书作 “”;宣德二年的 “御制瞿昙寺后殿碑”,藏文碑额也是楷体横书作;宣德四年 “御制大崇教寺碑”,碑额以一种较为独特的藏文 “篆书”(),竖排三列写作。②四幅碑额图片,图1采自《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材料汇编·内四区卷》,第116页;图2至图4采自吴景山:《安多藏族地区金石录》,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72、54、64页。
《御制碑》用八思巴字音译碑额,似与大崇教寺宣德御制碑之藏文 “篆书”碑额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形式上与汉文碑 “篆额”部分完美对应。吐蕃时期的藏文碑刻似无碑额之设,遑论 “篆额”。藏文碑额,尤其是 “篆额”的刻写,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

图1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碑额

图2 《御制大崇教寺碑》藏文碑额

图3 《御制瞿昙寺金佛像》藏文碑额

图4 《御制瞿昙寺后殿碑》藏文碑额
2.正文
(二)汉译文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朕惟帝王以道治天下,
皇恩浩荡施于民,……功德也。治国者若知民不安乐,则如将己之水
注入渠中般,凡其民均沾福泽,常系于心。其道之大,惟愿
同享雍熙泰和,皇图永固,物阜民丰;其道之小,祈祷祭祀,灾殃
……培植福田,常行如法祭祀,其义均在为民祈福。然此道之
外,朕思佛氏之道,利益福田,以慈悲导引群迷,与皇恩浩荡泽被

图5 《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碑记》正文①参见《碑刻志》,第610页。
万民一理也。东汉以来,有国家天下者多崇仰佛教,
常修建寺宇,以为僧众归依之所,塑金像以事崇奉,为生民
祈福。帝王以其慈悲辅助治世,其义流传已久。京城西北隅
有佛寺曰“大隆善护国寺”,元代名“崇国寺”,至元乙酉(1285)、皇庆、延佑、至正
年间,代有修缮。积岁滋久,复又颓圮。宣德己酉(1429),皇高祖[宣宗章皇帝]
敕谕有司(),撤而新之。为使国政兴隆,不舍佛道,
故赐寺名曰“大隆善寺”。成化壬辰(1472),皇祖考[宪宗纯皇帝]再次修缮,加赐
“护国”二字,故今名“大隆善护国寺”。又历多年,再次倾颓。朕闻之,发心[重修],敕谕
内官近臣等曰:“此寺先皇所遗,弗忍弃也。”敕谕太监谷大用、张雄董修造之事。
又因旧寺地狭,僧人无处住坐,故贸易民地,弘拓故址。
初于正德五年十一月兴工,越明年八月告竣。部分旧屋修葺
一新,又于荒地新建房屋。所需资财,皆出内帑,未费有司()之财。工匠人等
给予佣金财物,[未予]损害军民人等。所议修缮之事,一如前例,不得
有违。寺基前方建三门,中间依旧例置寺额。其内为金刚殿,□□天王
殿。东西两侧为钟鼓楼。再内有大殿三:曰大延寿殿、
曰大崇寿殿、曰三圣千佛殿①此殿名一般写作 “三仙千佛殿”。查《西天佛子源流录》,有正统年间班丹扎释在 “三圣千佛殿”举行法事的记载,故从之。。[三大殿两]侧有小殿六:曰慈悲文殊殿、曰大乘秘密殿、
曰伽蓝殿、曰祖师殿、曰大悲殿、曰地藏殿。
以上佛殿四周依次建有房屋。佛殿房梁高耸,如入云端。金像庄严,
焕然辉映。幢幡宝座、宝灯妙香、响器供具等莫不完备。后部
建僧舍、藏经阁、仓厨及斋堂。修缮之后极为完善。斋堂内
僧人座位分列左右。东西两侧各有甬道。石碑之间凿水井。寺院布局
极为佳妙,遍周圆满,内外有别。昨日内府绘寺院图来进,朕观之,甚为嘉悦。
此寺之建,乃继志述事,为生民祈福也。爰依寺院
故址,述其缘由,勒于贞石,俾传后世。
敕谕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大觉法王着肖藏卜等总领僧众,作庆赞
法事毕。又系之诗曰:帝王如法治世间,乃为万民种福田。民众经历之苦难,
如同己身得病患。初安雍熙泰和世,万物如春广繁衍。参透有无事业成,具咒术者乃
神仙。释迦如来佛教法,慈悲双运广流传。阴翊默相佑皇度,利济无间幽与显。
继志述事崇佛教,谨守祖宗之成宪。佛寺殿宇光粲然,旧有地基历有年。
皇统传承至于今,屡有废弃屡兴建。朕惟别无多求也,只为殊胜妙功德。历代传承如法行,
殷勤抚育众生民。祖宗之朝奉佛法,子子孙孙善护卫。当如朕一般传承,
朕之臣宰广传宣。勤修善业令增盛,成一民众依止处。建成清净新殿宇,
皇城之内一胜观。钟鼓声声相呼应,其音铿锵响耳边。警醒寺内之僧伽,
一切行止不怠慢。咒术犹如影相随,众生俱沾大福德。水火金木土谷修,春夏秋冬四季
和。消除一切病灾苦,人伦盛世共成就。至心祭拜来发愿,
若非亲耳得听闻。吁戏尔等诸君子,请观此贞石文字。正德七年十月初一。
三、碑文内容及书写特点
(一)碑文主要内容
碑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1—9行,指出帝王以道治天下,然儒道之外,佛氏亦有阴翊皇度之功,故历代帝王多崇佛建寺,度僧造像。
第9—32行,交代建寺缘起和过程。指出此寺乃元代古刹,自至元年间建立以来多有修缮,特别强调宣德、成化年间宣宗和宪宗曾修缮寺院敕赐寺名,标榜自己此次重修乃继志述事。具体修缮过程为,购买民田拓展了地基,敕谕太监谷大用和张雄二人负责修造,自正德五年十一月动工,次年八月竣工,所需财物皆出内帑,不劳军民之费。重修以后的佛殿主体部分有六层建筑:最前方为三门 (山门),在中间之门依旧例置寺额;第二层为金刚殿;第三层为天王殿;第四层为大延寿殿;第五层为大崇寿殿;第六层为三圣千佛殿。二三层之间东西两侧为钟楼、鼓楼;后三层之两侧为小殿六:慈悲文殊殿、大乘秘密殿、伽蓝殿、祖师殿、大悲殿和地藏殿。后部建有僧舍、藏经阁、仓厨及斋堂。东西两侧各有通道。石碑之间凿有水井。在看过内官所献寺院图之后,武宗敕谕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大觉法王着肖藏卜等总领僧众,做庆赞法事。
第32—42行为赞诗,共44句,以诗歌形式重复了前文内容。最后记载立碑时间为正德七年十月初一日,即在寺院建成近一年之后。这一立碑时间与寺内《僧众职名碑》立碑时间完全相同。
(二)碑文书写特点
从文风来看,藏文碑文显然由汉文翻译而成,直译、硬译痕迹非常明显。译者往往只考虑语词对应,而罔顾藏文表达习惯,译文难称雅驯,语法错误、拼写错误俯拾皆是。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不太精通藏文的汉族译师的作品。


四、碑文流传情况
如前所述,藏文《御制碑》应该是依据武宗御制的汉文碑文翻译而成。也就是说,护国寺内最初应立有汉藏两种《御制碑》。未知何故,万历二十一年 (1593)刊印的《宛署杂记》,称护国寺御制碑仅成化八年一通,未提到正德七年御制碑。②沈榜:《宛署杂记》,第200、223页;但崇祯八年 (1635)付梓的《帝京景物略》载,护国寺内 “正德七年勅碑二,梵字碑二”。③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33页。所谓正德七年勅碑二,一通当是与《御制碑》同日所立《僧众职名碑》,另一通应即与此藏文御制碑对应之汉文碑。“梵字碑”,即 “番字碑”,一通应即藏文《御制碑》。至于另一通,因为现存有拓片的顺治九年 (1652)藏文《敕建大隆善护国寺志碑》其时尚未树立,故其所指或是现已佚失的另一藏文碑。
谈迁 (1594—1658)顺治十一年 (1654)八月踏访护国寺后写道:“北入大隆善护国寺,元崇国寺,宣德间重建,改今名,而人犹旧称。正德七年太监谷大用、张雄奉勅修,门殿伟丽。时西僧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大觉法王着肖藏卜总领僧众。有碑列西僧职名,御制寺记碑二。汉书、西天书。”④谈迁:《北游录》,第78—79页。此处 “御制寺记碑二”,其一当是成化八年《御制大隆善护国寺碑》,⑤沈榜:《宛署杂记》,第200页。另一通应该就是正德汉文《御制碑》。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藏文《御制碑》,目前尚未在其他更早期的史料中见到谷大用、张雄负责重修护国寺一事。我们推测,谈迁这一信息或取材于当时尚存的汉文碑。此处 “西天书”,即《帝京景物略》所称 “梵字碑”即藏文碑。也就是说,清朝初年,正德七年汉文《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应该仍在寺内。
乾隆年间成书的《日下旧闻考》载:“(护国寺)正德七年二碑及天顺二年二碑今各存其一,梵字碑二俱存。”因后世流传的护国寺正德七年碑仅有《僧众职名碑》,也就是说汉文《御制碑》至迟于乾隆年间已经不存。
民国时期,关振生、刘敦桢、陈宗蕃等先生和北平研究院对护国寺进行过详细调查,均未见到汉文正德《御制碑》。这表明汉文《御制碑》应确实已于乾隆年间佚失。佚失的原因,除了损毁之外,也可能是后代又在此碑上刻写了新的内容,因为与此碑同日所立《僧众职名碑》之碑阴,便于顺治十八年 (1661)刻写了《京都大隆善护国寺新续临济正宗碑记》。
五、碑文所见护国寺格局
因为汉文《御制碑》佚失,藏文碑文此前又未全文汉译,学界在论及护国寺的修缮历史时,往往忽略了正德年间的重修在寺院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例如刘敦桢先生便认为:“此寺自定演创建以来,迄今六百五十余年,经元皇庆、延祐、至正及明宣德、正统、成化与清康熙数度增修,蔚为巨刹。然考元代诸碑,其时主要建筑仅大殿、经阁、钟楼、山门、舍利塔、法堂、云堂及伽蓝、祖师二堂,似较现寺规模不逮远甚。又以遗物推之,明以前者,唯存千佛殿残壁与舍利塔及元碑数通,皆萃聚于殿之前后。其余北部护法、功课二殿,与南部崇寿、延寿、天王、金刚诸殿,及钟鼓二楼、廊庑杂屋,依式样判断,咸属明清二代所建,而主要建筑属于明代者尤多。则现寺规模,决为明宣德、成化间增扩无疑矣。”①刘敦桢:《北平护国寺残迹》,《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6卷第2期,1935年,第6页。
但依碑文来看,以往论者没有提及的正德年间这次重修规模很大。一方面,购置民田拓展了寺基;另一方面,在维修旧殿之外,还新修了一些佛殿。由此可见,此碑碑阴所刻未著年代之《四至官员人匠职名碑》,很可能是与藏文碑同时所刻,刻碑意图在于明确变动以后的寺院四至。②参见《碑刻志》第4卷 (下),第619—621页。考诸寺内碑文,正德以后护国寺重要的修缮主要是顺治九年 (1652)和康熙六十一年 (1722)两次。前者“外部修缮主要是修建了围墙,内部则修缮了依止法物”,③同上,第622页。原文为藏文:未提到兴建佛殿之事。后者 “盖栋宇仍旧而丹雘增焕矣”,④参见《碑刻志》第4卷 (下),第635页。同样未提到寺院格局的变化。
经比对,《御制碑》所载寺院主体部分格局,与民国时期关振生、陈宗蕃、刘敦桢等先生和北平研究院实地考察后所留下的文字、照片及平面图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上引刘敦桢关于寺院建筑年代的推断,似应改为 “则现寺规模,决为明正德间增扩无疑”。可以说,正德年间的重修,奠定了护国寺此后400多年的基本格局。
六、碑文中 “大庆法王”系明武宗本人说
大庆法王领占班丹何许人也?《明武宗实录》载,正德五年六月庚子,“命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上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一号云”。②参见《明实录》第6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407页。此封号与《僧众职名碑》所载相同,应该就是《御制碑》中的大庆法王,即明武宗本人。但在各种史料中,对大庆法王的身份却有不同看法。《帝京景物略》称 “西番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北游录》称 “西僧大庆法王领占班丹”,《日下旧闻考》写成 “西番大庆法王凌戬巴勒丹”③参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第33页;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843页。,显然都将大庆法王视作 “番僧”。康熙六十一年《御制崇国寺碑文》亦称:“至明正德间,命大庆法王居之”,藏文作:,意为 “明正德年间,命喇嘛大庆法王居此”。④参见《碑刻志》第631页拓片。同书第633页之录文中缺 “”二字。 《藏文碑文研究》第290页之录文,将“”(大庆法王)误录为看来也是将大庆法王视为一 “喇嘛”。
与上述史料记载相应,学术界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大庆法王有两位,一位是明武宗本人,另一位是一名藏僧。具体而言,才让、熊文彬、谢继胜等认为,大庆法王本系明武宗给自己的封号,后又赐予岷州僧人领占班丹⑤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23—30页;熊文彬:《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年,第63、125、126页;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明)》,第418—420页。;何孝荣认为,武宗虽有大庆法王之号,但无领占班丹之名,领占班丹是武宗赐封的岷州僧人⑥何孝荣:《明武宗自号大宝法王、大庆法王及大护国保安寺考析》,载氏著《明朝佛教史论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96—316页。;卓鸿泽 (Hoong Teik Toh)认为大庆法王有 “双包现象”(duplication),一为明武宗,另一为其 “替僧”领占班丹。⑦Hoong Teik Toh,Tibetan Buddhism in Mi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2004,pp.189—190.另见氏著:《正德的番回倾向》,载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420—424页。这些学者用以佐证各自观点的主要史料依据,是《明武宗实录》的以下两条记载:
正德八年二月辛亥,大隆善护国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等,谋往陕西洮、临、巩、岷等处设熬广茶而还,因献驼马,求赏。礼部执奏无例。诏特给之。⑧《明武宗实录》卷97,正德八年二月辛亥条。参见《明实录》第66册,第2040页。
正德八年十一月辛未,赐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番行童度牒三千,听自收度。先是,有旨度番汉僧行道士四万人,其番行童,多中国人冒名者,为礼部所持,故领占班丹奏欲自便云。⑨《明武宗实录》卷106,参见《明实录》第66册,第2172页。
诚然,若从字面来看,上引两条史料中的大庆法王确似一 “番僧”,而非武宗本人。但应注意,明武宗之所以自封大庆法王,目的即在于掩人耳目,以法王身份来从事一些不便以皇帝身份来做的事,这与其自封为总督军务大将军等职衔御驾亲征的荒唐举措如出一辙。但这种做法在当时并非秘密,《殊域周咨录》载:“六年,上方 (指武宗——引者)好佛,自名 ‘大庆法王’。外廷虽闻之,无可据以进谏。会番僧奏讨腴田百顷为 ‘大庆法王’下院,乃书 ‘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礼部尚书傅珪佯不知,执奏曰:‘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书之,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当诛。’诏勿问,田亦竟止。”①参见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第372页。这条史料也见于《明史·傅珪传》:“正德六年 (傅珪——引者注)代费宏为礼部尚书。礼部事视他部为简,自珪数有执争,章奏遂多。帝好佛,自称大庆法王。番僧乞田百顷为法王下院,中旨下部,称大庆法王与圣旨并。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敢与至尊并书,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184,第4885页。礼部尚书傅珪抓住 “大庆法王”与 “至尊”并书这一不合礼制的把柄,坚称应对此严加查处。武宗自知理亏,只得下诏不必深究。
由此观之,前引大庆法王自陕西洮、临、巩、岷等地熬茶回京后求赏 (大庆法王当然不必亲自前往熬茶),不过是武宗自导自演的 “双簧”。礼部也是 “将计就计”,以没有先例而拒绝给赏。武宗无奈,只得以至高无上的皇权 “诏特给之”。至于敕赐度牒一事,《明史》亦有载:“已,封领占班丹为大庆法王,给番僧度牒三千,听其自度。或言,大庆法王,即帝自号也。”②参见《明史》,第8578页。《明史》的编纂者似乎不太确定此大庆法王是否武宗本人。但若与另两条史料结合来看,这不过也是武宗故伎重演,以皇帝身份给予法王身份的自己又一特权。反言之,若非武宗本人,试想还有谁敢在礼部明确反对度僧之后仍 “奏欲自便”并能获准?
岷州番僧领占班丹为另一大庆法王之说并不成立。此人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例,即《明英宗实录》景泰五年 (1454)四月甲辰条:“陕西岷州大崇教寺国师锁南藏卜遣番僧领占班丹……等来朝贡马,赐彩币、钞锭有差。”③参见《明英宗实录》卷240。可见领占班丹当时只是岷州大崇教寺的一位普通僧人,并无任何封号。学者将其与56年之后的正德五年 (1510)骤然出现在史料中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视为同一人,仅仅是因为二者名字相同。退而言之,若此岷州领占班丹果于近60年后受封法王,根据惯例定会在《明实录》等史料中留下其职位变化之相关记载,但迄今并未见到朝廷封赠此人的任何记录。
另外,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载,岷州高僧大善法王释迦室哩有一名为领占班丹的侄子,曾任岷州圆觉寺住持。④智观巴·贡却乎旦巴饶吉:《安多政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86页,吴均、毛继祖、马也林汉译本,甘肃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646页。才让先生推测此人或为另一大庆法王。然而,释迦室哩景泰七年 (1456)受封大善法王,故其侄子领占班丹似可与上述景泰五年入朝贡马之大崇教寺领占班丹比定为同一人,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另一大庆法王,否则《安多政教史》似乎不大可能只字不提其与皇室的关系或其在北京的活动情况。
至于认为武宗有大庆法王之号,而无领占班丹之名;或大庆法王本为武宗所有,后又转赠给领占班丹之说也不成立。黎吉生 (Hugh E.Richardson)在楚布寺发现了一件明武宗以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名义,于正德十一年 (1516)九月十五日写给第八世噶玛巴弥觉多吉 (1507—1554)的汉藏文对照信件。①Hugh E.Richardson, High Peaks, Pure Earth: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8,pp.364—365, 375—376.说明武宗确有法名领占班丹,且一直在使用大庆法王的封号。
卓鸿泽先生所谓另一大庆法王系明武宗 “替僧”之说,也仅是在假定有两位大庆法王的前提下做出的假设,其依据是张居正所书《敕建承恩寺碑文》记载万历皇帝有一名为 “志善”的替僧。②卓鸿泽:《正德的番回倾向》,载林富士主编:《中国史新论:宗教史分册》,第421页。即便是明武宗真有替僧,似乎也不必赐予其与自己完全一样的法王封号。
还需澄清一点,传世唐卡中正德七年两幅、九年两幅、十年一幅、十四年两幅的题款中有 “大护国保安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发心施”字样,③何孝荣:《明武宗自号大宝法王、大庆法王及大护国保安寺考析》,载氏著《明朝佛教史论稿》,第308—310页。也被当作有两位大庆法王的证据。以往囿于史料,有学者推测保安寺与护国寺或为同一寺院。④欧朝贵:《大庆法王领占班丹绣施普贤菩萨像考释》,《西藏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9—132页;David Kidd,“Tibetan Painting in China:New Light on a Puzzling Group of Dated Tangkas,” Oriental Art, n.s.XXI, No.1(Spring 1975):56; “Tibetan Painting in China:Author's Postscript,”Oriental Art,n.s.XXI,No.2(Spring 1975);谢继胜、魏文、贾维维主编:《北京藏传佛教艺术 (明)》,第419页。但新出土的《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表明,大护国保安寺位于京西阳台山下的管家岭村。⑤张文大:《大善法王墓志铭揭开大墙圈之谜底》,海淀区党史地方志网站,http://hdszb.bjhd.gov.cn/gzdt/dqgz/201704/t20170 428_1366989.htm.最后浏览时间:2021年10月27日。那么,护国寺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为何又以保安寺法王身份施赠唐卡?
大护国保安寺始建年代不详。《顺天府志》称其建于正德年间。⑥光绪《顺天府志》卷16《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日下旧闻考》载寺内 “有磬二,一铸明正德五年制字”。⑦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第773页。《敕建大护国保安寺圆寂大善法王墓志铭》载,曾任大隆善护国寺主持的大善法王星吉班丹 (1452—1515)于正德五年七月出任大护国保安寺住持。⑧李志明:《汉藏交融:明清时期岷州藏传佛教史研究》,2018年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106—110页。又,《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年五月辛亥条载:“大护国保安寺右觉义班丹伦竹为其祖师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礼部执奏无例。上特许之,命工部给葬价二千两。”⑨《明武宗实录》卷125。这说明星吉班丹为大护国保安寺祖师。
结合上述几条史料,大护国保安寺应该建成于武宗自封为大庆法王的正德五年,星吉班丹为寺院首任住持即祖师。保安寺与护国寺关系极为密切。先后出任保安寺主持的大善法王星吉班丹和大德法王绰吉俄些儿 ()也列名于护国寺《僧众职名碑》,这与明武宗以保安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身份施赠唐卡是一个道理。武宗本非真正的僧人,当然不必固定驻锡于某一寺院。多幅传世唐卡均为大庆法王施赠应非偶然,作为一国之君的武宗,当然有实力施赠如此众多的唐卡。
无论自称大隆善护国寺还是大护国保安寺大庆法王领占班丹,不过都是明武宗掩人耳目的手段。如果我们认为武宗不是大庆法王,或在武宗之外还有另一位名为领占班丹的大庆法王,无疑正中其下怀。
七、结 语
通过对藏文《御制重修大隆善护国寺志碑》的初步解读,我们发现,无论从碑额的刻写,还是汉语音译词汇的使用和书仪规范,此碑都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碑文表明,正德五年十一月至次年八月的重修,奠定了护国寺之后400多年间的基本格局。碑文中的大庆法王领占班丹就是明武宗本人,除此之外并没有另外一名大庆法王。
诚如舒乙先生对北京藏文碑刻的评价:“这是一组极其重要的涉及祖国统一大业的 ‘国宝’,完全有必要刻不容缓地把它们挖掘出来,刻意地指明它们的政治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形成一组特殊的、专门的、不可替代的爱国主义活教材和维系祖国统一大业的伟大历史见证。”①舒乙:《见证亲密:纪北京承德两市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3页。近年来,涉藏碑刻资料的文物和史料价值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产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②有关涉藏碑刻研究现状的综述,参见桑丁才仁:《“涉藏金石总录”课题实施情况与涉藏金石铭文研究现状》,《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第206—212页。然而,相关研究除了对一些特别有名的碑刻,如乾隆御制《喇嘛说》等关注较多以外,其他涉藏碑刻内容的研究和史料价值的挖掘,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