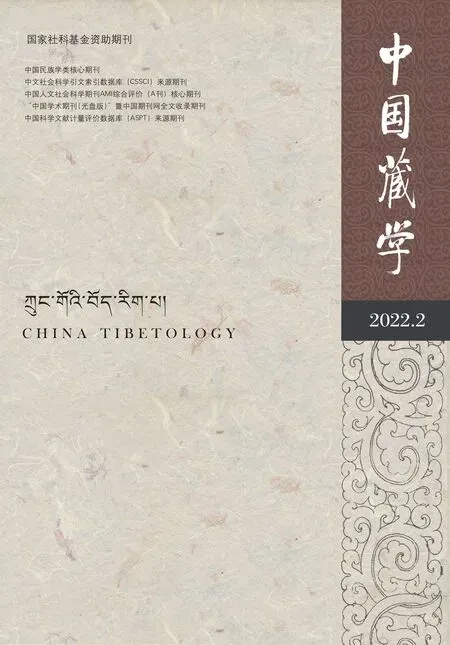唐卡造像量度图式传习:身体记忆与体化实践①
刘冬梅
在中国传统文化论著中,有关身体实践和口传心授的经验性描述不胜枚举。例如,《庄子》中的佝偻者承蜩、津人操舟、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均褒扬了经由刻苦训练与反复领悟而达成的道技合一的匠人精神。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如果说明人解缙的 “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②[明]解缙:《春雨杂述·评书》,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95—496页。指出了书法传承中师生间身心互动的关键意义,学生只有接受老师面对面的示范、训练、点拨等才能真正掌握其间要义,这是单纯靠临帖难以达到的,那么清末民初武术大师王芗斋谈及 “习拳有得于师者,有得于己者;得于师者为规矩,得于己者乃循规矩,经体认,实得于身之妙用也”③王芗斋:《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第119—120页。则更进一步强调学习者唯有通过亲自践行与体悟才能将师传之规矩内化为己身能力。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诸如音乐、舞蹈、戏剧、手工艺、武术、体育竞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习得研究不断深入,口传心授在文化代际传递中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且这一传承方式的身体性特征也愈加受到重视。④钱永平:《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形态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6页。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将知识借由身体实践传递的过程称为 “体化实践”(incorporated practices),这一概念强调了身体技艺的记忆属性,有助于我们探寻身体如何在被动的形塑和能动的创造中传承与书写历史。
从西藏唐卡的传习来说,临摹造像量度图绘范本一直都是学徒修习的核心课程。这种造像量度图绘范本可以理解为贡布里希 (E.H.Gombrich)所说的 “预成图式”⑤贡布里希著,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以独特的文化感知模式将描述对象符码化,赋予其秩序、语法以及可把握和理解的形式。在唐卡的传习过程中,对于造像量度图式的理解、运用与呈现,属于师徒间口传心授的内容。为此,笔者从2008年至2016年先后跟随嘎玛嘎赤画派唐卡大师嘎玛德勒、勉唐画派唐卡大师丹巴绕旦学习造像量度手绘基础,其间又对西藏唐卡画院、嘎玛嘎赤唐卡画院等传习基地进行了深度考察。在此基础上,尝试从体化实践的视角分析造像量度图式在唐卡传习中的意义,具体以处于不同阶段的学徒为例,考察随着图式记忆、造型能力、艺术构思的创建与拓展,以及在与老师、同门互动中,其身心被重新塑造的过程,由此切入有关 “习得”并 “活用”文化知识的探讨。⑥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载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一、身体规训:坐姿与运笔手势的习得
在经验层面,与武术、戏曲等模仿训练相似,初学者首先要接受身体的全面规训,需要对身体各个部位进行焦点式的评判,故很难自学入门,只有在老师的示范与纠正之下,习练者才能逐渐掌握相关拳种、套路、身体图式的正确姿势与操作路径。⑦涂琳琳:《对武术 “口传心授”的重释及其时代意义探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208页。徐蕾:《谈戏曲表演教学中的 “口传心授”》,《戏剧之家》2014年第2期,第32页。在理论层面,有关社会记忆的研究已经指出那些通常被视为是 “自然的”行为习惯实际上是后天通过重复动作而形成的记忆。而作为文化特有种类的身体实践,也是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相结合的产物。①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因此,在入门阶段,唐卡学徒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重新习得坐姿与运笔手势。
绘制唐卡需要久坐、静心,全神贯注投入,因此对初学者坐姿的训练是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西藏唐卡画院院长罗布斯达便将坐姿作为一项基本功对初入门学徒进行严格要求:
画唐卡要像修行打坐那样的盘腿坐姿,不能歪着扭着坐,要先坐端正,才能把心安静下来画画。有的小孩子刚来时,特别坐不住,还有的坐惯了凳子,不习惯盘坐,问题很多。盘腿坐是禅修的坐姿,能够调整气息、保持内气,只有学会这样的坐姿,才能适应今后长期久坐的绘画生涯。在西藏唐卡画院,初级班的坐榻上没有靠背,是专门设计成这样的,目的是让学徒在学画画的初期练习坐姿。有的小孩子画着画着坐姿就歪了或散了,我们的老师看到了马上就要过去纠正。②被访谈人:罗布斯达,男,1968年出生,西藏唐卡画院院长;访谈人:刘冬梅;访谈时间:2015年1月15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东路西藏唐卡画院。
罗布斯达还认为初学绘画者年龄在7—13岁为佳,最好不要超过18岁,否则骨骼都已发育成熟了,盘腿坐不住,手脚也会比较僵硬,难以训练。初学量度手绘时,学徒还有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不会控制手部力道,下笔很重,像写字一样,画的线条很粗,造型也不准,用橡皮擦反复擦拭,修改后在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画面不干净不清爽。故而初学时要加强对手部力量的控制训练,特别是腕部、虎口与手指的配合,这对握笔、运笔方式及绘画工具都有特殊的讲究。在罗布斯达看来,传统的绘画工具更有利于训练学徒的腕力和手指的灵活性:
我们小时候学画画时,最初是在木板上抹上一层酥油和灶灰,用小树枝削成笔作画。这样的好处是必须悬腕练习,否则会破坏画面并使油和灰沾到手上。长期悬腕练习能够训练腕部力量,使其灵活自如,尤其在描绘较大的形体关系与线条时才能更加收放自如、灵动;在木板上的练习过关后,就可在画布上用传统的炭条起稿。炭条特别松软易断,因此就特别考验指尖和虎口力量控制,对细节描绘更加准确、运笔轻灵;练习毛笔勾线时,可以用拇指、食指、中指握笔,小指作为画面的支撑进行运笔,这样更加稳定、准确。
笔者2008年初次在西藏昌都嘎玛乡学习造像量度手绘时,一开始极不习惯只用拇指和食指握笔,觉得力道不足。坐在旁边的学徒见状就会好心过来加以纠正,并描述握笔时拇指与食指之间得能容下一个鸡蛋,其余三指要紧握,做到滴水不漏,如此运笔才会有力。因此,在学习初期,学徒需要从外部视角、从他人审视的目光注视自己的身体,观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③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12页。由于长时间埋头绘画,一开始肩背、虎口等部分会酸痛异常,1个月之后身体才能逐渐适应,手指变得不那么僵硬,笔触也从粗重变得轻柔细腻。
技艺习得之初的身体规训常常被类比为 “玉不琢不成器”,身体被视为亟待加工的工艺原材料,需要打磨和锤炼。①刘珩:《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学术传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第340页。此时的身体状态经常是笨拙、不协调的。戴维·萨德诺 (David Sudnow)将其学习演奏爵士乐的最初经历戏称为 “临场行为控制”的失败。②David Sudnow, Ways of the Hand:The Organization of Improvised Conduct, MIT Press, 1993, p.30.为此,需要用自我反观和他者监督来觉察并努力修正存在于社会认可的身体和个人拥有的身体之间的距离。老师不断纠正学生的身体动作,让其保持应有的读写姿势,如同操演一种微型体操。③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96页。从文化的意义来看,这些特定的姿势操演为我们提供了身体的助记方法。
二、反复临摹:视知觉模式与基本图式记忆
在中国古代绘画教学中,临摹一直备受历代画家重视,也形成了中国画程式性和继承性的特点,并归纳总结成画论见诸于笔端。如南齐谢赫 “六法论”中的 “传移模写”④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第355页。和顾恺之的 “模写要法”⑤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第365页。均体现了临摹的重要性。造像量度图式作为唐卡教学的造型基础课,训练途径亦是临摹。有关视知觉的研究表明人的 “看”并不是生理学意义的 “纯真之眼”,而是被文化赋予了多元的感知与描绘对象的模式。⑥贡布里希著,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艺术与错觉》,第107页。唐卡画师是以绘画的方式将无形的神灵可视化,其 “视”受到了 “知”的影响。于是初入门的学徒首先要练习最基本的造像量度图式,学习在二维平面空间中运用线条和装饰手法造型和构图,这与西方艺术家以 “照相式的”焦点透视法模仿三维立体空间幻觉大相径庭。
在传统上,唐卡学徒的 “第一课”通常是根据老师手绘的释迦牟尼佛头像量度图进行临摹学习。例如,在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一位学徒行完拜师礼后,丹巴绕旦老师会现场亲自示范绘制一幅释迦牟尼佛的头像,让其临摹。在丹巴绕旦老师看来,释迦牟尼佛头像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课程,如同初学藏文时的30个字母,一定要由最好的老师来传授,因为这代表着传承之源,有特别的加持力。⑦被访谈人:旦增平措,男,1985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校长;访谈人:刘冬梅;访谈时间:2015年7月12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仙足岛生态小区。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摹释迦牟尼佛造像量度图可为学徒创建最基本的图式,并训练其视知觉模式:比例与对称。
学徒首先要学习利用面度尺和量度格等辅助工具。面度尺的藏语称为 “协才”,一个 “协才”是佛像面部的高度,又可译为面度,等于12指宽。其本质是比例尺,由白纸条或竹片临时自制,标上刻度与数据,便于测量。量度格的藏语称为 “忒康”,俗称打线、画线房、打格子等,由比例线和动态线组成。比例线由多组纵向的垂直线与横向的平行线构成,辅助学徒确定身体关键部位的比例。动态线是多组斜线构成,用于辅助确定因颈、腰、肘、膝等关节运动而形成的动态变化。利用量度格既可帮助初入门的学徒对照临摹,也可有效地帮助其记忆佛身比例与造型。
为了将释迦牟尼佛肉身坐像这一基本图式熟稔于心,初入门的学徒需要长期反复练习。日喀则唐卡画师扎西谈到自己初学绘画时,曾每日反复临摹释迦牟尼佛肉身坐像长达一年半之久,并认为这段学习经历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①被访谈人:扎西,男,1989年生,日喀则勉萨派画师;访谈人:刘冬梅、李健;访谈时间:2017年7月26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夏鲁寺。昌都画师桑珠罗布在教授初入门的学徒时,会让他们先单独练习佛的头部和手足,认为这是佛像绘制的重点难点。其中,五官、手和脚之间的长短距离、高低、大小等对称与协调关系是练习的首要目标。②被访谈人:桑珠罗布,男,1969年生,藏族唐卡嘎玛嘎赤派画师;访谈人:刘冬梅、当增扎西;访谈时间:2019年8月18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察马村。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学徒洛桑在介绍学习经验时谈到,训练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才更加有效,数量、质量、速度都要达到自己的极限。③被访谈人:洛桑,男,1992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学徒;访谈人:刘冬梅;访谈时间:2015年7月2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仙足岛生态小区。昌都嘎玛乡画师嘎玛斯加则提到了自己在初学阶段是如何由易入难准确记忆佛身比例和造型的:
第一步:严格打好量度格,临摹范图。第二步:不打量度格,只打一根中垂线,对照范图临摹,再打量度格进行检查。第三步:只打一根中垂线,将范图背临下来,再打量度格进行检查。④被访谈人:嘎玛斯加,男,1989年生,藏族唐卡嘎玛嘎赤派画师;访谈人:刘冬梅;访谈时间:2010年3月2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比如村。
因此,唐卡传习作为专业领域的身体实践,需要把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结合起来。首先,被体化的是一种视觉习惯:把对象认同于唐卡。其次,反复练习一整套绘制流程与动作,不仅让学徒反复回忆有关唐卡造像量度图式的分类系统,也要求产生习惯记忆。通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身体能开始协调越来越大范围的肌肉活动,动作变得越来越自然,直至出现一套行云流水般连贯流畅的固定习惯动作。此处,反复练习作为规则性控制,就是在一套身势和整个身体的姿势之间建立最佳联系,成为效率和速度的条件。⑤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4页。而这套使用身体的模式也会在学徒和量度图式的互动中变得根深蒂固。最后,反复临摹并不意味着机械复制,而是通过加强重点难点、提高强度与准确性等方式进行训练,从量变到质变,形成永久记忆。通过这种程式化的图式记忆训练,使学徒将其内化为视觉审美与身体惯习,重塑了观察、感知、思维的模式,并最终使这套身体技艺内化为 “第二天性”。于是,姿势、动作、性格、气质作为习惯记忆被养成身体外形。这些身体的记忆表明习惯是一种知识,当我们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 “理解”。⑥同上,第117页。
三、磨练心性:克服身体惯习与刻意训练
传统上,唐卡的教学不设年级和学制,老师根据每位学徒的具体情况把握教学进度,因材施教。在完成释迦牟尼佛坐像这一基本造像量度图式的训练之后,老师会按照类型化记忆方式对学徒进行造像量度图式系统训练。在这一阶段,对身体技艺也有更高的要求,需要学徒不断克服身体惯习,培养专注力,故这也是一个心性磨练的过程。
造像量度图式的系统学习需要2—3年时间,尽管不必交学费,但学徒不仅没有收入,还需要生活费与住宿费,故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也意味着更长的教育成本周期。此外,也有学徒在学会了基本量度图式之后,就只依赖身体惯习重复动作,很难再进步,便逐渐放弃继续学习。这些内外因素使得能够坚持学习完成造像量度图式系统的学徒只有入门阶段的十分之一。
在康纳顿看来,当习惯最终被养成,便不用再借助判断意识了。换言之,当技艺变得熟练以后,即使不再投以特别的注意力,也仍能自然而然达到目的。然而,艾利克森 (Anders Ericsson)则将此批评为 “天真的练习”,并指出如果对技能的学习只满足于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水平,那么即使再重复数年也不会再有更多进步,甚至还会缓慢退化,为此他提出 “刻意训练”才是从新手成长为大师的关键。①安德斯·艾利克森、罗伯特·普尔著,王正林译:《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30—33页。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卡学徒的心性磨练阶段便是克服 “天真的练习”进入 “刻意训练”的过程。与日常生活技能不同,专业领域的技艺提升是不断挑战固有身体习惯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使用 “惯习”替代 “习惯”,便是试图强调这一行为的开放性与能动性。正如华康德所言,如果要彻底领悟惯习,那就得去思考想要成就某种惯习的背后需要多少刻意安排的教学练习。②洛易克·华康德著,李睿译:《作为主题与工具的惯习:对拳手经历的反思》,《体育与科学》2016年第1期,第66页。
克服身体惯习需要做大量刻意练习,包括四个要素:一是有具体的目标,二是专注力,三是对错误的反馈,四是走出舒适区。③安德斯·艾利克森、罗伯特·普尔著,王正林译:《刻意练习:如何从新手到大师》,第33页。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采用进阶式教学法,即丹巴绕旦老师把造像量度图式系统分解为一系列学习单元,并制定具体教学目标。学校还制定了考勤制度,夏令时间为早上8点半上课、中午1点下课,下午2点半上课、晚上8点放学;冬令时间为早上9点上课、晚上7点放学。每位学徒都有自己的固定位置,每天到校后便各自进行训练,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在这一阶段,学徒需要集中精力,专注于画面造型与线条的细微区别。许多学徒都曾提及当他们进入一种忘我状态时,体验到时间与空间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例如,会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心理时间比实际时间变短,享受学习的过程并沉浸其间。学徒都爱使用笔芯更细的自动铅笔,并用砂纸将笔尖打磨得极细,其注意力转移到了笔下,以便能描绘出更多的细节。同时,对外界的感知也似乎关闭了,呼吸变得平稳,手也越来越稳,很多学徒因此逐渐变得内向而温和。
在这里,每位学徒都清楚自己的目标,不断被逼出手与眼的舒适区,通过老师的反馈纠正错误,从而克服身体惯习。近80岁高龄的丹巴绕旦老师几乎每天都会来学校批改作业,指出学徒习作存在的问题,或是表扬进步,询问学徒学习情况和生活状况,叮嘱其好好学画等。看完正面,还会习惯性地翻过来看看背面,然后又回到正面在右上方画钩,写上学徒姓名、编号、批改日期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习惯动作,其实是丹巴绕旦老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
据说以前曾有学徒借别人的习作凑成10幅作业上交给老师,试图蒙混过关,但很快就败露了。从此丹巴绕旦老师每次批改习作时都会在佛像右上角画钩,然后用藏文写上学生的名字并编号。此后,又有调皮的学徒把老师批改过的记号用小刀先裁剪下来,再用白纸补上,又补绘上裁掉的内容,使正面看起来像新绘的习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又被老师识破了。从此丹巴绕旦老师每次都会翻过来看背面是否有补丁,①被访谈人:顿珠尼玛,男,1982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画师;格桑平措,男,1981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画师;访谈人:旦增平措、刘冬梅;访谈时间:2015年8月13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蔡公堂乡白定村支沟。如果一切正常,学徒完成了规定的练习数量,且造型与线条水平均达到预期的目标,丹巴绕旦老师便批准该学徒结业过关,进入下一幅量度图式的临摹学习。每天有谁过关,谁得到表扬,都是学徒们在茶余饭后聊天的热门话题。师徒之间形成督促与信任的关系,同学之间相互形成参照比拼对象。总之,这种教学方式使学徒在学习过程中有如游戏闯关式地充满挑战性,将漫长而枯燥的训练分割成数段短期目标,使之有了前进的动力。
唐卡学校中的教学互动使我们看到情感和身体惯习不是通过规则学会,而是通过 “和那些习惯于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人在一起”②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29页。才学会的。刻意训练的过程还体现了 “学习的共同体”③让·莱夫、爱丁纳·温格著,王文静译:《情景学习: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之重要意义。处于不同技艺水平的唐卡学徒和画师组成了这个共同体,并以技艺为参考形成 “中心”与“边缘”。学习便是位于共同体周边成员的向心性参与行为。学徒沿着旁观者、参与者到成熟实践的示范者的轨迹前进,从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者逐步到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其身份不断进行着再生产。
四、类型化训练:扩展量度图式记忆系统
藏传佛教造像的数量多到无法计量,图式系统训练时并不是让学徒将每一尊造像都画一遍,而是以类型学的方式,按照其身量比例和造型上的复杂程度次第进阶练习。释迦牟尼佛量度图式是一切佛像的基础,也是佛类与菩萨类、上师类造像的基础,之后练习绿度母和金刚手的造像量度图式。绿度母是佛母类造像的基础;金刚手则是怒相类造像的基础。然后便进入类型化训练阶段,从静善相的菩萨类到半怒相类、怒相类,造型难度逐步递增,按照进阶式训练扩展造像量度图式记忆系统。在这一阶段,学徒按照严格步骤画完一幅量度图通常需要1周时间,每尊造像需练习10幅,完成系统训练需要2年左右。
不同类型的造像遵照不同的比例进行绘制。佛、菩萨、上师类造像遵照120指的身量比例,绿度母等佛母类造像遵照108指的身量比例,金刚手等大部分怒相类造像遵照96指的身量比例。每类造像身体各部位的具体比例也有详细的规定,学徒都需要打详细的量度格进行临摹和记忆。同类造像的比例与服饰基本相似,只是在手印持物、身姿动态等局部细节进行区分。例如,菩萨类造像可在释迦牟尼佛袈裟装量度图与绿度母着衣像量度图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教学。
在学习四臂观音量度图时,其身量比例细节、量度格、五官、坐姿、莲台等都与释迦牟尼佛一样,扩展的内容一是多了两臂,且四条手臂的动态、手印、持物不同;二是要练习背光部分增加的装饰图案;三是菩萨像装束与释迦牟尼佛为比丘相时所着的袈裟装不同,但与绿度母的装束相似。在学习文殊菩萨量度图时,在四臂观音的基础之上扩展的内容:一是四臂的动态、手印、持物不同,且需练习手印在量度格之外的绘制;二是颈部与腰部增加了动态线,但这又与绿度母的动态线相同 (见下表)。①被访谈人:旦增平措,男,1985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校长;访谈人:刘冬梅;访谈时间:2015年11月21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仙足岛生态小区。

造像量度图式的扩展记忆训练 (菩萨类)
体化实践中的类型化训练作为有效的记忆手段被康纳顿所关注。他指出,纪念仪式的形式化机制使之具有可操演性。操演话语被编码成不变的姿势、手势和动作,为仪式语言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库。在世界各地的口头文学中也存在与仪式言语类似的标准排比、韵律节奏等特征,作为一种记忆手段和传承方式而具有重要意义。①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68页。造像量度图式在身量比例、五官面相、坐姿、手印与持物,装束、头光与背光等方面体现出高度程式化特征,成为唐卡传习过程中有效的记忆手段。量度图式之间既保持着相似的造型程式又存在细微区别,使之既保证了对过去的延续,又成为拓展与创新的基础。新学习的图式是在前面图式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扩展记忆,既迫使学徒走出舒适区,又不至于将难度提得太高。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扩展记忆,学徒逐渐积累语汇,形成语汇表,内化为图式系统记忆库。
五、眼、手、心的契合:精微描绘与概括提炼
在完成菩萨类、半怒相类、怒相类等造像量度图式的记忆拓展训练之后,便会进入五大本尊和微型造像图式的学习。五大本尊包括大威德金刚、时轮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喜金刚,其形象特征是多头多臂、手持各种法器、身佩复杂饰物,是造型最为复杂的量度图式,需要打量度格绘制。微型造像图式意译为 “估量”或音译为 “勉昂”,只打简约的辅助线:中线、顶线、底线、动态线,不打比例线,只将比例记在心中,或是点在中线和底线上提醒。这一阶段的学徒通常都已经有长达3—5年的学龄,主要训练其极度精微刻画的能力与概括提炼的能力,使眼、手、心的配合更加默契,为毕业唐卡创作做准备。
据毕业于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的画师顿珠介绍,造像量度图式训练最难的内容一是特别复杂的、多头、多臂的造像;二是特别大的造像;三是特别小的造像:
比如胜乐金刚、喜金刚、密集金刚、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等五大本尊像就是最复杂的,有的身上挂着许多骷髅头,脚下踩着好多小鬼,比豌豆还小,但眉毛、眼睛、鼻子、嘴巴、牙齿都要全部画出来,外面的人看的话还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六年级练习微型佛像,这个是练习对量度经的灵活运用。我觉得更难的是画很大的佛像和很小的佛像,功底训练是关键。②被访谈人:顿珠尼玛,男,1982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画师;访谈人:刘冬梅、桑吉东智,访谈时间:2015年2月2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军民路哈答小区。
量度格与 “勉昂”这两种方式,是造型训练的不同路径。一方面,在量度格中绘制佛像的训练方式,是在做加法,训练学徒描绘精微细节的能力,这在五大本尊量度图式的练习中发挥到极致。这种能力是对日常生活 “粗受”(粗略的身体知觉)的超越,被称为是 “细受”(细微的身体知觉)的感知方式。③[尼泊尔]咏给·明就仁波切:《根道果:禅修的方法与次第》,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另一方面,以 “勉昂”的方式画佛像,是在做减法,训练学徒对整体比例关系的掌握,尤其是概括提炼的能力。从详细的量度格到 “勉昂”的训练变化,达到从可视的量度到心中的量度的转变,培养学徒在整体与细节之间灵活转换的技能。唐卡老师还会经常向学徒讲述古代大师能够在指甲盖、豌豆、青稞上画佛像的传说,还有古代大师以绘画获得大成就的故事,这些将技艺发挥到登峰造极的范例激励着学徒们走向更高的境界。
在同一文化和行业领域内部,身体感知能力的精进程度,成为分辨技艺能手及其行业身份地位的基础。①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载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24页。相较之下,感知能力较精进者更容易成长为杰出的画师。在此,体化实践不仅是康纳顿所关注的知识的社会传递,更是形成历史动力的重要因素。因为,以眼、手、心相契合为指向的身体训练过程,不仅强调学徒的艺术感知力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加以形塑,更使我们注意到那些杰出画师还能够通过量度图式训练发展新的身体感知项目,在身体经验层面超越常人的认知范围,甚至如太极拳修习者般表现出诸多常人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体知能力,②杨大卫:《身体实践与文化秩序:对太极拳作为文化现象的身体人类学考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或类似戏曲艺人所达到的 “肌肉思维化”,即让肌肉敏感、细致到能解人语、能传感情,使身体语言能产生无声胜有声的感染力。③吕珍珍:《口传心授的补充:传统戏曲艺人的书面文化习得》,《中国戏曲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第116页。于是,身体既是被认知和改造的客体,接受着既有文化法则的规训和塑造,同时也发挥着主体性,可以创造和产生新的感知世界。
六、体知合一:实现创造性构思与自由表达
在 “勉昂”和开眼④开眼课程内容是学习头像的彩绘技法,重点学习眼、口、鼻等五官的细节渲染。等课程修习完毕后,就可进入毕业唐卡创作阶段。毕业唐卡藏语叫 “呑唐”,从准备到完成往往需要2—3年时间,这代表学徒通过数年求学在技艺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丹巴绕旦老师会在毕业唐卡下方专门的位置题注、签字、盖章,对绘制者所掌握的唐卡技艺水平进行评价,合格者方能获得毕业证书。画师赤增绕旦于2013年以优秀等级从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他认为造像量度图式系统训练为毕业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大量研习古代经典作品、开阔视野,了解唐卡艺术已经达到的最高成就,由此创作构思出优秀的当代作品:
我是2010年至2013年,用了3年时间创作毕业唐卡。选题是我自己选的,是关于西藏各教派的法脉传承,然后丹巴绕旦老师写了不同教派主要人物的名字给我,还有如何构图、人物背景、量度比例、大小、位置等都给予了指点,在艺术技法上要以勉唐派风格作为根本。勉唐派已有600年的历史,历代艺术大师留下了很多杰作,不同时期风格也有差异。……那段时间,我请假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查阅资料,看了很多老的唐卡,例如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收藏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第司·桑杰嘉措时期绘制的唐卡,这是勉唐派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作品。我用一年多的时间研习了这些经典作品。……以前都是高僧大德与大画师合作创作,是结合理论与心境画出来的。要将自己的身、语、意与闻、思、修结合起来,才能画好唐卡。①被访谈人:赤增绕旦,男,1979年生,西藏丹巴绕旦唐卡艺术学校毕业画师;访谈人:冯莉、刘冬梅;访谈时间:2014年9月16日;访谈地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西路西藏宾馆。
在毕业创作阶段,尽管学徒将老师传授的造像量度图式系统都谙熟于心,但构思毕业唐卡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照搬老师传授的画稿或将各类量度图式进行剪切拼粘,而是需要大量地观摩与研习历史上的经典图式,还包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写生,在审美鉴赏、理论修养、信仰心境等方面突破瓶颈,自由调用图式并联结 “所知”与 “所见”,实现创造性构思与个性化表达。正如郑板桥对艺术创作过程中从 “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到 “手中之竹”②卞孝萱编:《郑板桥全集·研究资料·诗词书信》,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199页。的阐述,或如中国传统戏曲的传承中,习者通过心受与身受,由 “会”到 “通”最终达到 “化”的过程。③朱玉江:《论非遗传承人音乐习得的生物学范式》,《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79页。在此,造像量度图式系统的体化实践触及了物与身体感研究常提及的读入 (read into)与读出 (read from)④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载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46页。的关系。读入阶段表现为身体感知学习与能力培养的过程,造像量度图式系统逐渐从概念与知识层面转化成为自己有能力驾驭和判断价值的身体经验,内化为与外部世界对话的方式。于是,身体本身成为用以衡量的器物或尺度,表现出取舍万物的从容和自信。⑤Michael Herzfeld, The Body Impolitic:Artisans and Artifice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34.身体的感知 (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与思想密切结合在一起,成为知识习得的本质。⑥刘珩:《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学术传记》,第340页。正是不断磨炼的身体越发与思想相契合,从而培养出将文化从物与图式中读出的能力,⑦余舜德:《从田野经验到身体感的研究》,载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26页。使画师在进行创作构思时能够运用既有之身体记忆与图式来经验新的对象。画师以在文化中培育出来的方式来感知唐卡及其文化脉络,他们于体悟中确认,再生产出新的图式与意义。并且,此过程不会就此结束,而是处于开放状态,随着身体技艺的提高,读入与读出之间的关系不断被重新定义。
结 语
与基于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散漫的默会知识研究有所不同,西藏唐卡造像量度图式传习过程提供的是一个专业领域的、精微化的体化实践体系。在上述论及的 “六步法”中,前三步是基本功训练,对抗以往日常生活养成的身体惯习,进入专业领域的感知训练。第四步与第五步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建立新的习惯记忆,将造像量度图式内化于身体。如果说前五步是一个读入的过程,是对既有知识的习得,那么,最后一步就是一个读出的过程,是对习得知识的活用。从读入到读出的过程是身体成为行为主体的过程,将身体本身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以新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在康纳顿看来,体化实践之所以具有特别的记忆效果主要依赖其两个特征:存在方式与获得方式。即体化实践不会独立于操演而 “客观地”存在,同时,其获得方式不需要明确反省它们的操演。①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25页。然而,唐卡造像量度图式传习过程却让我们看到体化实践并非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无意识行为,而是刻意训练的过程。体化实践的身体记忆属性,揭示了技艺是身心达到的一种状态,而非一劳永逸的知识原理。大量重复的训练并不是表面上的原地踏步,相反,每一次训练都是对固有身体惯习的超越,由此积累逐渐改变其身心关系。因此,造像量度图式习得的过程也是文化意义建构的过程,体化实践则是个人学习、知识的社会传递乃至开创新的文化图景的重要方式。
在藏族艺术研究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造像量度束缚了藏族唐卡画师的思想,导致西藏艺术缺乏创造力,甚至有人主张以素描训练取代造像量度作为唐卡学徒的必修课。然而,身体技艺不仅显现出身体与物的关系,而且透露出身体与文化的关联。造像量度图式训练重塑了学徒观看的方式和审美思维模式,是藏传佛教美学观念的表达,并不能简单地用素描训练方式加以替代。其教学内容不是书本知识,而是与唐卡相关的感知模式、道德情感、价值判断等体化实践的内容。艺术教育以类似修行的方式促使学徒挑战着技艺的极限,同时也是在不断追求人格的完善。
相对于西方艺术对天赋的强调,西藏唐卡的艺术传承制度认可每一位学徒的潜能,并主张因材施教开发其感知能力,故而这种强调后天习得的态度更加具有人类学意义。从造像量度图式传习的六步法来看,唐卡学徒获得艺术创造力的过程犹如学术科研洞察力的训练,是建立在大量前人成果之上的循序渐进式的突破。这种创造性属于集体实践的区域而非个体成就。这意味着风格与创新并不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一个群体、数代人的积累,且天赋与习得在传承中都同样重要。身体技艺的获得过程显示为画师身心契合程度的曲线图,同时也反映着画师在行业群体中的社会关系轨迹。在藏族文化的语境中,传承首先指代代相传不能间断,其中大部分传承人的职责是以内化的身体记忆守住文化之脉,将其保持下去,等待着有能力创造新图式的大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