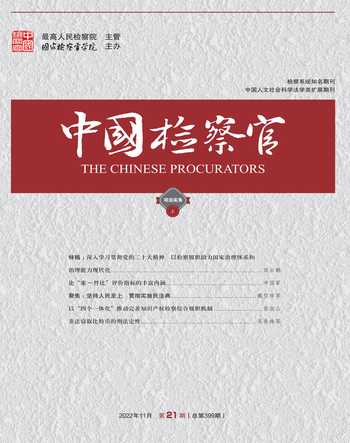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风险的检察应对
李学东 何旭霞 周俊生
摘 要: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适用中缺乏辩护权、对抗式诉讼模式等程序保障,可能出现公权力行使失当、侵犯财产权、实体处理错误等风险。司法机关主要通过参照适用普通刑事程序的诉权保障和严格证明标准来控制风险,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与公正和效率价值平衡的要求不尽相符,需进一步完善,其关键是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突出审前阶段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以及完善提起介入机制,引导形成证明标准适用共识。
关键詞:司法风险 诉权保障 证明标准 法律监督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以下简称“特别没收程序”)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重要法律手段,在创设时被寄予厚望,但并未广泛适用。对此,实务部门和学界强调要扩大其适用范围,但却未深入研究制约其广泛适用的实际原因。[1]实际上,特别没收程序扩大适用的难点不仅是法律适用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法官、检察官在适用该程序时怎么做、怎么想的问题。因其扩大适用最终有赖于司法者积极主动作为,故笔者综合运用座谈调研和判例分析的实证方法[2],探析司法者在特别没收程序实践中的所行所思,研究破解制约其扩大适用的主客观障碍,以期为推动程序适用提供指引。
一、特别没收程序适用的潜在风险
调研中,笔者发现司法机关对特别没收程序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是贯穿其适用全过程的核心逻辑。这是因为当事人的缺席连带造成辩护权缺位、对抗式诉讼模式消解、公开审判限缩等问题,可能引发较大的司法风险。
(一)公权力行使失当的风险
一方面,适用特别没收程序的案件,监察、侦查机关负责在诉前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检察机关、当事人缺乏参与其中、对取证活动进行监督的程序机制,容易引发不规范取证、诉权保障不足等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消解,控诉权的行使失去辩护权的制衡,既容易使检察机关怠于行使诉讼监督职能,也容易滋生不当行使控诉权的问题。
(二)不当侵犯财产权的风险
特别没收程序的核心是涉案财产的归属问题,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同时,往往牵涉民事法律关系,但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的程序保障,既低于普通刑事程序也低于民事诉讼程序。涉案财产的权利人面对国家机关,在程序上仅有异议权,难以形成实质的平等对抗,导致涉案财产权被侵犯的风险较普通刑事程序和民事诉讼程序大幅增加。
(三)实体处理错误的风险
适用特别没收程序案件的证据体系往往缺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多为“零口供”案件,本身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难度、不确定性就比较大,加之诉前取证活动缺乏当事人、律师参与和有效的检察监督,其取证行为的规范性和可靠性弱于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因而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难度更大,偏离客观真实的风险更大。
二、特别没收程序适用风险的实践应对
调研中,可发现司法人员对以上风险大多有清醒认识,并有意识地通过参照适用普通刑事程序的程序保障机制来合理控制风险。在操作层面,主要是通过强化利害关系人诉权保障和升格证明标准两种方式来对冲风险。
(一)强化利害关系人诉权保障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299条、第300条的规定,特别没收程序中,涉案财产的利害关系人享有在法院公告过程中申请参与诉讼的权利,以及对违法所得提出异议和二审上诉等权利。“两高”2017年《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7年《规定》),明确了法院向利害关系人送达的职责和利害关系人公告期满的例外参与权——赋予了利害关系人更高规格的知情权和更完整的参与权。此外,法院在实践中还会给予利害关系人更进一步的诉权保障。
在与法院座谈调研时,有法官提到,实践中许多利害关系人不愿参加特别没收程序,但法庭仍会敦促其积极参加,以免当事人和公众质疑程序适用的公正性。从判例来看,法院积极敦促的倾向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法院在立案受理后,主动询问利害关系人是否参加诉讼,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定的公告或者送达程序予以告知。如在王某某受贿申请没收违法所得一案中,法院向被告人妻子直接送达,征求其有无异议、是否参加庭审的意见。[3]二是法院强制利害关系人以诉讼参加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如在张某受贿申请没收违法所得一案中,尽管被告人妻子对涉案财产没收没有任何异议,但法院仍传唤其到庭参加诉讼。[4]
实践中,有的法官在落实庭审实质化上表现出一种比普通程序更加自觉主动的倾向,重视利害关系人参与权对追诉权的制衡作用和对实体公正的促进作用。检察机关对加强利害关系人诉讼保障也持一种积极态度,2017年《规定》第12条明确将利害关系人相关情况作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书的必备内容。司法者对诉权保障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一种防范风险的替代补偿心理,意图以此弥补特别没收程序正当性不足可能引发的司法风险。如座谈时有法官提到,之所以特别重视敦促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主要是考虑特别没收程序本质上是一种未定罪没收,相较于普通刑事审判程序而言,其财产没收的决定并未建立在稳固的定罪基础之上,存在一定的司法风险,故而对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权等权利保障更加积极主动,有时甚至出现“过头”的“强制”倾向。
(二)升格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并未直接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证明标准。2017年《规定》第9、10条和第17条对犯罪事实的审查与对涉案财产性质的审查分别规定适用“有证据证明”和“具有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这两者的文字表述有所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优势证明标准”的范畴。[5]同时,审查涉案财产的性质是审查认定犯罪行为与涉案财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属于犯罪事实查明的一部分,因而应将“具有高度可能性”理解为“有证据证明”的量化标准,即只要达到“高度可能性”的程度,就满足“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要求。
2017年《规定》的证据标准并未被实践完全接受。调研中发现,特别没收程序的庭审中,很多法官仍是按照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流程进行,习惯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严格证明标准来认定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事实,这导致对犯罪行为与涉案财产关联性的审理间接适用了严格证明标准。有法官提到,即便利害关系人或被害人未提出异议,但法院认为案件的犯罪事实不清的,也会开庭审理,对案件的犯罪事实展开独立调查,以确保达到严格证明标准。如在潘某某贪污、受贿案中,法院在刑事裁定书中明确指出由于某一项受贿事实“无法形成证据锁链”,故对该项受贿事实及违法所得不予认定。[6]
升格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证明标准的倾向,也主要是受防范风险的替代补偿心理影响。如座谈时有法官指出,虽然按照2017年《规定》,法庭无需按“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审查认定犯罪事实,只需专注于审理违法所得是否应当没收,但是在未查清犯罪事实的前提下进行违法所得没收的处置,犹如“建房子没有地基”,面临较大的错判风险,故更倾向于选择升格证明标准以求将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错判风险控制在与普通刑事案件同一水平上。
三、特别没收程序适用风险应对的完善建议
通过加强诉权保障和升格证明标准控制特别没收程序的风险,有利于实现实体公正,但同时也会加重特别没收程序适用的司法成本,削弱其服务于追逃追赃的司法效益。立法者创设特别没收程序,初衷是为解决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所造成的案件久拖不决、涉案违法所得迟迟无法追缴等问题,追求的是司法诉讼的效益价值。因此,应从实现公正与效率平衡的价值目标出发,优化诉权保障和证明标准的适用机制,以合理控制特别没收程序的司法风险,这其中的关键是发挥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
(一)完善审前阶段利害关系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体系
对抗式诉讼模式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有效机制。在当事人缺席时,可以通过强化利害关系人诉权保障来构建替代的对抗式诉讼模式,即赋予利害关系人“准当事人”或类似于民事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以此在特别没收程序中“模拟”对抗式诉讼模式:检控机关—利害关系人—审判机关。目前,司法实践对利害关系人的诉权保障集中在审判阶段,应当将此权利保障追溯至审前阶段,即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涉案违法所得的侦查、调查和审查起诉过程的权利,以完整“模拟”对抗式诉讼模式。这要求检察机关严格落实人权保障职责要求:一是在诉前阶段,要通过案件会商工作机制,敦促监察、侦查机关在启动程序时即查明涉案财产利害关系人情况、向其调取相关证言和告知相关情况。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要加强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情况的审查,必要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严格保障其参与权、知情权乃至抗辩权等权利。
(二)健全合理適用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证明标准的工作机制
当下司法实务部门对没收违法所得案件事实的认定采用严格证明标准,混淆了特别没收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的性质:前者是对物之诉,后者是对人之诉。换言之,在特别没收程序中,犯罪行为事实的认定并不苛以当事人刑事责任,而仅是作为没收行为的事实条件,并且没收行为不是刑罚,而是作为一种保安处分措施[7],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应采用2017年《规定》的证明标准。目前,我国刑事审判实践存在适用严格证明标准的惯性,检察机关应当能动履职,进一步完善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的证据收集和诉讼监督机制:一是在审前阶段,要通过提前介入机制,引导监察、侦查机关按照普通刑事程序的严格证明标准来调取证据,尽最大努力实现证据确实、充分的举证责任,排除错案风险。二是在审判阶段,要通过庭前会议机制加强与法院沟通,理性客观看待没收违法所得案件证据情况,推动法检共同按照2017年《规定》的证明标准审查认定没收违法所得案件事实,避免对案件证据再作过高要求,以进一步提高特别没收程序诉讼效率,更好发挥其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制度效能。
*本文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2020年度检察理论研究课题“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GDJC202012)阶段性成果。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长、二级高级检察官[510623]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510623]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一级检察官助理[510623]
[1] 参见韩晓峰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据审查相关问题探讨——以涉外追逃追赃案件为视角》,《人民检察》2022年第5期。
[2] 本文调研座谈范围为广州地区监察、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办案人员,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2018至2021年期间全国各地公开的适用特别没收程序的案件26件作为分析样本。
[3] 参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9)冀09刑没初1号。
[4]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20)云01刑没1号。
[5] 参见裴显鼎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重点疑难问题解读》,《法律适用》2017年第13期。
[6] 参见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8)陕10刑没1号。
[7] 参见朱孝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几个问题》,《人民检察》2014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