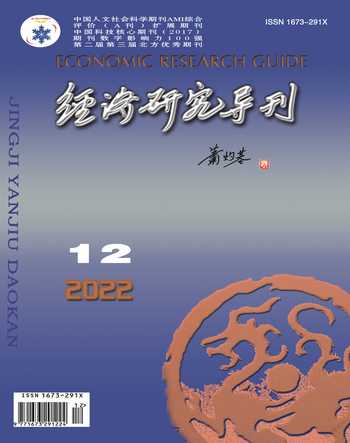劝服理论视域下不同类型主播直播带货的比较研究
李鲤
关键词:直播带货;劝服理论;劝服机制;农产品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2)12-0058-03
引言
主播是消费者进行产品评估和购买决策的重要外部线索[1]。数据显示,2021年“双十一”期间,两大淘宝头部主播预售成交额近200亿,远超仅9.3亿的第三名主播[2],马太效应明显。费鸿萍等设计了三个实验,探讨了主播与品牌存在不同匹配形式时,传统明星主播和KOL主播带货谁更有效的问题[3]。孟陆等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度访谈和计量模型的方法验证了直播网红影响购买意愿的心理机制,并重点讨论了不同类型直播网红信息源特征对消费搜索及购买行为的影响[4]。然而,将传播学的劝服理论作为统摄性视角来系统地观察网络直播购物过程中受众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多[5],且已有的将劝服理论引入网络直播购物的研究文献中既考量不同主播传播效果差异又关注消费者在不同产品购物中决策差异的文章较少。鉴于此,本文从劝服理论出发,以农产品直播带货为例,对不同带货能力主播的直播策略进行比较分析,试图从信源、内容、信道和信宿四个环节剖析不同类型主播的有效劝服机制,为底部主播带货提供可能的发展思路。
一、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本文將网络主播按照拥有粉丝的数量和一段时间内的带货成交额GMV(Gross Merchandise Volume)为标准划分为头部主播、腰部主播和底部主播三种类型。其中头部主播是指粉丝数量大于100万且年GMV超过百亿元的主播。腰部主播指粉丝数量大于10万小于等于100万的同时,年GMV大于1亿小于百亿的主播;底部主播指粉丝数量小于等于10万且年GMV小于1亿元的主播。原因有两点:首先,以主播过去销售数据为划分依据更符合企业对主播的甄选标准;其次,本文着眼于农产品这一商品类别,选用同类商品的带货成交量指标更有利于进行不同主播劝服效果的比较。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淘宝直播平台,时间跨度为2021年11月1日至12月1日。由于头部主播带货种类丰富,因此样本的选择以底部主播为主。首先,以“家乡好货”作为商品类别的关键词,搜索以“农产品”为带货标的物的主播群;接着,在前述主播群的基础上,剔除了从事“农产品代购”“农产品经销”以及“农产品天猫旗舰店铺”的主播,确定以专门开展农产品直播的个人农户为底部主播的样本来源;其次,通过对比头部主播和底部主播的带货商品,找出其有相同带货商品直播的底部主播;最后,在这些底部主播中筛选出近30天内有成交记录的对象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并通过开源工具,收集了包括商品名称、平均客单价、优惠信息、粉丝数量、开播场次、场均观看人数、场均销售额、直播时长等数据信息。
二、不同主播农产品直播带货的劝服机制比较
(一)信源:头部主播充当意见领袖,底部主播突出农民身份
对将要传播的信息进行一定的选择、组织及加工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而不同的信源对消费者有着不同的劝服机制。对农产品开展直播带货时,头部主播往往为品牌商品带货,更接近于推销员的角色,看重单次带货成交量的大小;而底部主播通常是产供销一体的模式,追求更持久的盈利能力。因此这两类主播在个人形象塑造和带货信息的组织中存在着明显差异。
已有的直播数据显示,头部主播直播时间相对稳定,尽管场均直播时长超过4小时,但由于每场带货的商品种类较多,导致每件商品从开始介绍到完成交易只有5—10分钟时间。因此,头部主播会利用自身庞大的粉丝数量,塑造“购买者”“使用者”的身份,充当产品意见领袖的角色,以增加信息的劝服力。
底部主播通常缺乏良好的直播间搭建环境,且直播场次和直播时长均波动较大。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纯天然”的追求,绝大多数直接以自身农民形象出现,塑造自然、淳朴的个人形象,传递给消费者值得信赖的印象,降低消费的可感知风险。
(二)内容:头部主播构建场景,底部主播强调真实
在农产品直播带货中,传播的信息内容包括产品信息、主播的语言信息和直播间信息三个部分。现有头部主播由于其庞大的粉丝群和“推广者”的角色具有更大的商品选择范围及议价权。在农产品类别中多以经过加工后的农产品甚至是包装食品为主,这类商品已经经过规模化的流通加工作业实现统一包装,便于物流运输。头部主播除了介绍商品品牌、成分分析、热销信息、产品优势等消费者关注的卖点信息外,还会通过与其他助播(包括明星)一起构建一个小型的商品选购和消费场景来共同营造火热的直播间购买氛围。最后再配合大量的限时打折、优惠券、限量供应等促销手段,快速促成交易。在这个过程中,头部主播向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猎新猎奇及个人身份认同的心理,在直播间形成一种抢购氛围,从而实现高成交量。
底部主播带货的商品通常自产自销。由于有限的加工能力及农作物的季节性特征,直播的时间和场景往往选在农作物耕种、施肥、收割、家禽的喂养等劳动环节。底部主播的语言信息表现出零散、随意的特征。除了对产品处理过程的简单说明和介绍外,更多的信息是通过直播间的现场画面传递的。直播间通常只有一个画面,也不对直播场景进行过多的人为修饰和处理。画面内容包括现场采摘、宰杀、切割、称量、简单包装等贴近大自然、原生态的乡村作业环境。尽管没有品牌加持,也没有过多的营销信息,但其对客观环境的复原及一镜到底的直播间拍摄过程,极大地增加了人物和产品细节的真实性,同样能让消费者产生产品值得信赖、价格合理的印象。可见,从传播内容角度,底部主播自身对产品的了解、生产环节的把控和其产品纯天然、有机的特征能对追求农产品品质的消费者形成有效劝服并促成购买行为。
(三)信道:头部主播单一平台运作,底部主播多平台运营
不论是头部主播还是底部主播都是通过互联网实施传播活动的,但在直播平台的选择上存在差异。目前电商直播中的头部主播主要分布在淘宝、抖音和快手三大平台中,其中鉴于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主导地位,又以淘宝的头部主播最多,同时不同平台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推荐机制。
从劝服角度来看,由于头部主播前期已经在对应的平台获得了大量粉丝的关注,因此她们往往会在一个固定的平台进行直播,同时通过门户网站或社交平台等其他信息渠道提前发布直播清单预告,以获得更高的直播观看量。在平台直播中,高达数百万的粉丝基数与单个商品有限的库存数差异,极易让消费者形成供不应求的印象,加之购买决策的时间压力和对成熟电子商务平台售后服务的信任,进一步促成了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对底部主播而言,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多是起“吸粉”的作用。在單一直播平台粉丝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的方式来提升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从而获得较为稳定的客户群。
(四)信宿:头部主播主打年轻女性,底部主播以家庭主妇为主
农产品的主要购买者为女性,但头部主播与底部主播针对的用户群并不完全重合,且劝服机制也不一样。头部主播的数据显示,半数以上为“95后”女性,她们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有较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单身居多,追求生活品质及自我价值。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倾向于简单、方便。通常头部主播的直播时间从晚上7点、8点开始,这时粉丝们大多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或家务进入休息状态,观看直播对他们来说不仅是购物的需要,也满足了放松娱乐的需求。因此他们乐于通过直播间弹幕的方式与主播进行互动,而当主播回应弹幕时,极易引起观看者的正面情绪,鼓励其继续参与到观看和购买环节。
大多数底部主播的直播安排在白天,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粉丝群的职业和年龄。尽管她们也可能分布在一、二线城市,但多以家庭主妇为主,消费农产品时更为理性。她们观看直播间的时间不多,也极少带有娱乐的需求,参与直播间互动的频率也较低。但直播间中对消费者过去消费经历记忆的有效唤起是形成有效劝服并最终促成购买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原籍为产地的用户,真实的乡村生活画面更能引起心理上的共鸣进而产生信任感。
三、结论与讨论
头部主播因其突出的带货成绩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不断提高的直播坑位费和佣金显示出品牌商们对头部主播资源追捧热情的持续高涨。这种扎堆头部主播的行为不但降低了企业议价权,也极大地压缩了中小主播的生存空间,加速了个体垄断的形成。既打破了企业网络营销的良性竞争格局,也不利于直播行业的长期发展。本文以农产品为例,将不同带货能力的主播作为研究对象,从劝服传播的视角分析和比较了头部主播与底部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信息选择、组织、传播渠道及目标人群的差异,探讨了其不同的劝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头部主播开播前会依据粉丝需求选品并进行直播前的宣传和预告,吸引感兴趣用户观看。直播过程中通常会先介绍品牌信息传递“高档、时髦、优质”的形象,引导消费者将商品的消费和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形成对“理想自我”的身份构建,提升购买欲。随后与多名助播共同营造出多人现场买货比货的场景并随时与观看者进行互动答疑,增加消费者的临场感。接着通过直播价、优惠券和赠品信息的介绍突出产品低价实惠的特征再配合有限的商品数量营造“抢购”的销售氛围。尤其是商品抢购一空后,主播还会对未能及时付款的买家进行清理,以腾出商品重新上架给第一轮没抢到的客户再次下单购买,这一操作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抢拍热情并压缩了购买决策的犹豫时间,督促其立即付款完成交易。第二,底部主播首先通过原始的自然环境和朴实的个人形象让消费者形成信赖感。当主播提供农作物种植或家禽喂养信息时,能有效塑造主播“专家”的身份,增强消费者对主播及产品的信任度,更易形成产品天然、健康、无公害的形象认知。直播间中对农作物生长、采摘、简单加工场景的直接展示有利于帮助观看者了解真实而完整的商品生产流程,对追求安全放心的消费者有较强的劝服力。最后原产地直发的价格优势也极大地缩短了消费者的决策时间,最终形成购买行为。
本文通过对头部主播和底部主播直播带货劝服机制的比较揭示了头部主播带货能力的构建逻辑。尽管个人主播不具备庞大粉丝基础和资本运作的优势,但仍能运用独特的劝服机制改善其网络运营的能力。这不仅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可持续增加,也有利于直播带货行业的健康发展,更有利于乡村振兴的顺利实现。然而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局限:一是从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对不同主播的直播内容进行比较的定性分析方法,缺乏数据验证;二是从研究结论上,本文结论建立在农产品为带货主体的直播类型中。未来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及实验法对本研究结论进行数据验证;也可以扩大研究范围,对以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进行直播带货的中小主播的劝服机制开展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 黄敏学,叶钰芊,王薇.不同类型产品下直播主播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和行为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2021,(9).
[2]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李佳琦薇娅头部效应之下:直播带货的风会向哪吹?[EB/OL].网易网,2021-11-05.
[3] 费鸿萍,周成臣.主播类型与品牌态度及购买意愿——基于网络直播购物场景的实验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80-89.
[4] 孟陆,刘凤军,陈斯允,段珅.我可以唤起你吗——不同类型直播网红信息源特性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0,(1):131-143.
[5] 曾丽红,黄蝶.是什么在主导网络直播购物意愿——说服理论视域下对直播购物受众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7):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