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彀”:明清科场八股文的去取标准
师雅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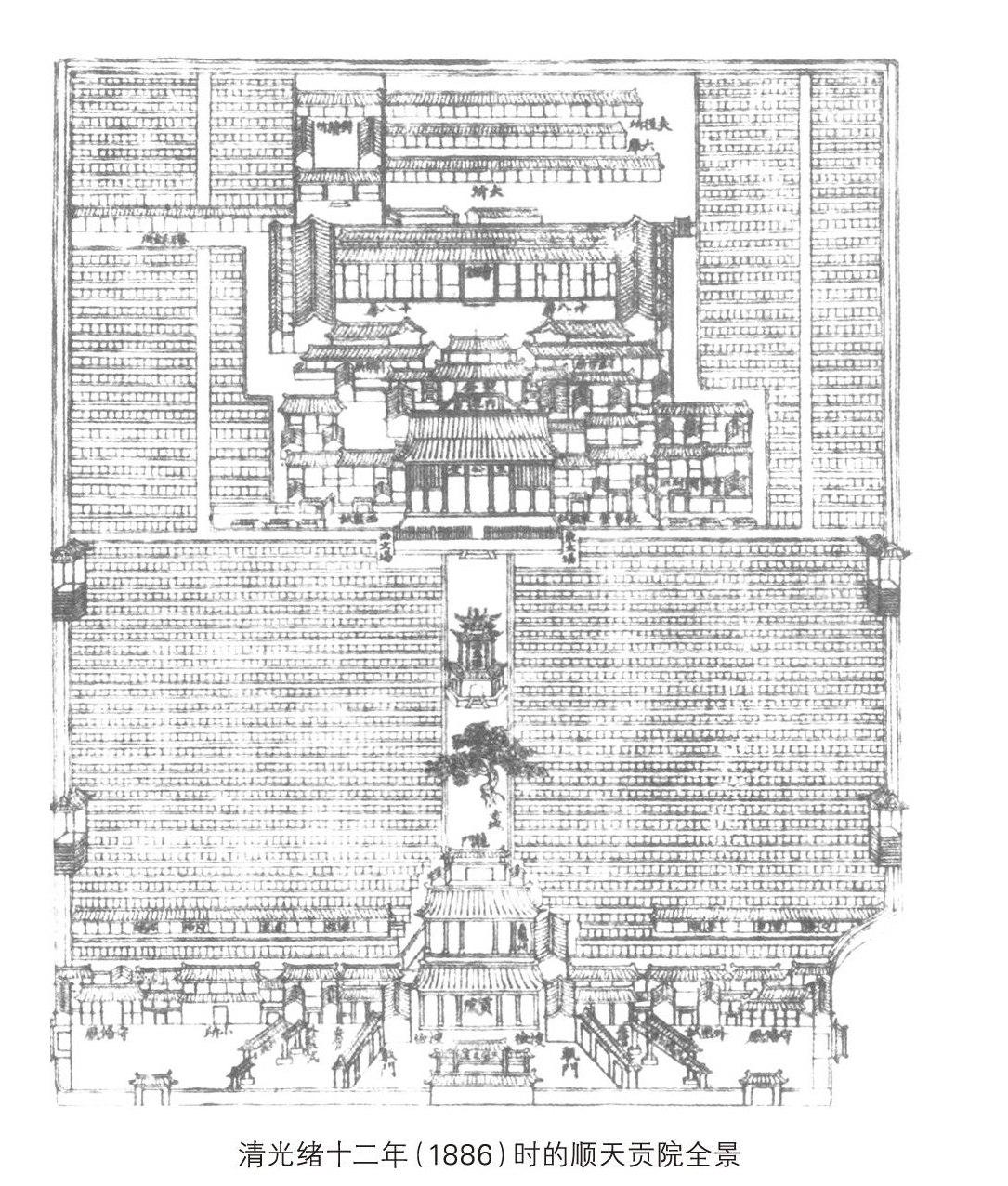
明清两代以文章试士,乡、会试首场三篇文字,题目取自“四书”“五经”,解题需遵循官方所定宋元注解,又需“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明史·选举志二》)。这种科场文体,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逐渐完备、定型,因其主体部分通常由四组八句两两相对的句子组成,故被称为八股文,又有八比文、制义、制艺、时艺、时文、举业等多种别称。乡、会试虽有三场,除八股文外,还要考诏、诰、表、策等,但三场之中,最重首场,首场八股文的好坏,是能否取得科名的关键。因此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时期一般读书人“童而习之”、最为熟悉的文体。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中,马二先生曾有一番宏论,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这里的“文章”,指的就是八股文。马二先生这番话虽然迂腐,但也可以反映出八股文在当日士子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科场文体,八股文本身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文章属性。八股文在体制上兼有辞赋、古文的特点,在功能上亦与古文、辞赋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作者的情感、志向。另一种是功令属性,即它担负着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任,士子要在两天一夜的短暂时间中写出三篇文章,考官则要通过这三篇文章,评判士子的道德修养、学问识见等是否能达到从政水平。这两种属性,决定了八股文写作中的两种倾向。从文章属性出发,自可以用八股表见才情,抒发怀抱,如清初尤侗以《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句为题的游戏八股文,描写世上为情痴狂的儿女情态,惟妙惟肖,宛然如画;又如清康熙年间方舟的八股文,深沉平稳,娓娓道来,其中的忧世之心,感人至深,龚自珍称赞其为“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沈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龚自珍《题方百川遗文》)。从功令属性出发,则是要将八股当作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把考场得中作为八股写作的唯一目的,所谓“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而在科举时代,能够无视八股功令属性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八股文作者,首要任务都是学会写能“中彀”的文章。
那么,什么样的八股文才容易被取中呢?明清笔记中常见一句俗谚:“窗下莫论命,场中莫论文”,就是说文章能否取中,主要取决于冥冥之中,而和文章好坏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文章写得很好,考运却很差的著名文人,如明代归有光,清代姜宸英、沈德潜,等等。但还有不少人“不信邪”,认为“命在文中,不在文外”(薛鼎铭《墨谱》卷一)。为此,他们精研历科考官所作的示范文章即“程文”,与历科得中士子的考场文字即“墨卷”,力图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这一类研究“程墨”的人,被称为“墨派”“揣摩家”。揣摩家中,固然有不学无术、迂腐不堪之徒,但也不乏两榜出身、见识通透的人物。他们对科场文字的分析解说,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普通读书人的文章观念,提供了更贴近历史实际的视角。近年来,学界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人谈论八股文的文献,其中不少即属于“揣摩家言”。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揣摩家”们对于“中彀”文章之风格特点的看法,大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说理清楚。八股文“代圣贤立言”,好的八股文,必须对题目中蕴含的圣贤义理有清晰的阐述,这一点,是明清朝野的共识。朝廷方面,明代王英《正统七年会试录序》谈到科举考试去取甚严,“惟平易畅达,不失于理者取焉”。清代雍正、乾隆两位皇帝曾多次颁布谕令,强调科场文字要“雅正清真”。乾隆初年《钦定四书文》的编选者方苞在《进四书文选表》中解释“清真”说:“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在“揣摩家”那里,说理清晰、透彻同样是“中彀”之文的基本要求。顺治十六年(1659)会元朱岵思著有《会元薪传》,认为“论题论文,论天论人,题理不得,文虽工,无益也”。也即八股文要以阐发“题理”为写作的第一要务,不能以文胜质、喧宾夺主。又说:“文之贵清也,以介立骨,以妍赴时。不染一尘,介之至也。若吐清沘,妍之符也。”乾隆间薛鼎铭对《会元薪传》进行注解,认为:“文之清者,多是廊庙之器。意理不杂之谓清。雅淡者清,绚者亦清。简净者清,畅茂者亦清。人但见墨卷之浓,而不知其自首至尾,只‘清字不易及。”(《墨谱》卷一)“不染一尘”“意理不杂”,就是说文章所论与题目恰相符合,没有遗漏,也没有超出题目范围,所谓“不漏不溢”;又能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所谓“不蔓不枝”。能做到此,便称得上“与题无负”“得题之窾”。
二是文辞既要典雅,又要浅显。科场文章谈论的是圣贤修齐治平之理,阅卷者是朝廷官员,有“敷奏以言”的郑重意义,因此辞句需典雅。明末清初人唐彪《读书作文谱》引程楷语:“修辞无他巧,唯要知换字之法。琐碎字宜以冠冕字换之,庸俗字宜以文雅字换之,务令自然,毋使杜撰。”“冠冕”“文雅”字眼,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与古文名篇,诸子外道之辞则在摒弃之列。如薛鼎铭认为八股语辞,“除《六经》外,秦汉八家语之精粹者可用。稍涉粗豪,不可阑入,况老、庄诸子乎”(《墨谱》卷一)。“典雅”的同时,又要浅近不深奥。这主要是从阅卷者的角度考虑。阅卷者的水平不一,过于生僻古奥的文句,极有可能被一些腹中空空的考官认为“不通”,所以莫不如在写作时有意避开过僻之典、之辞。这一点,尤为谈“墨裁”者所强调,如薛鼎铭认为:“房官亦间有生疏者,故如《书》之《盘》《诰》,《礼》之《内则》,及三《传》中非时文常用者,究宜慎之。”(《墨谱》卷一)清嘉庆、道光间(1796—1850)人仲振履认为:“用典太僻,自以为新奇,而场中往往误事。”(《秀才秘钥》)清光绪间(1875—1908)人孙万春也说:“经文固宜典雅,十分僻典亦宜禁用。”(《缙山书院文话》卷三)又,时文家论考场文字,多强调“醒”“豁”,如清康熙间王汝骧论文有“醒”字诀,要求文章“醒豁不晦闷”(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朱岵思说科场文字“豁最要紧”(《会元薪传》),薛鼎铭亦说“墨卷切忌肤浮,又忌深晦,切实而能爽朗,无不售者”(《墨谱》卷一)。醒豁爽朗,方能打动阅卷者心目。而辞句的浅近明显,正是达到“醒豁”文风的必要手段。
三是文势要流畅贯通、一气呵成。这亦是一种“阅卷者视角”。明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状元、万历十九年会试第二、殿试榜眼王衡认为:“相文之法,大类相人,惟以神气为主,非必五官六体,事事称量,乃为无失。相文者但疾读一过,利钝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细细求之,则十无一验矣。”(《学艺初言》)考官阅卷时间有限,不可能对每篇文字进行细读,因此,文章最重要的是“整体印象”,而非字句的推求。对于“中彀”之文的整体气象,王衡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凡文之蓬蓬勃勃,如釜上气者,利之途也;掩掩抑抑,如窗隙风者,钝之途也。鲜鲜润润,如丛花带雨者,利之途也;孑孑直直,如孤干擎风者,钝之途也。活活泼泼,如游鱼飞鸟者,利之途也;悉悉率率,如虫行蚁息者,钝之途也。如物在口,探之即得者,利之途也;结塞胸中,若呕若吐者,钝之途也。如鼎在世,古色驳荦者,利之途也,如铁在水,黯然沉碧者,钝之途也。宫商杂奏,嘈然满耳者,利之途也;独坐弹琴,如怨如慕者,钝之途也。”(《学艺初言》)这段话中,与“利”之文相似的物象,均有飞动、爽朗、热切之征;与“钝”之文类似的物象,则是晦涩、凝滞、孤高冷淡的。这番“利钝论”,也是王衡同时代人的普遍看法,如万历十六年陕西解元、万历十七年进士武之望认为:“场中文字,要一气呵成,观一篇,只如一股,观七篇,只如一篇,不打咯噔,不挂牙齿,然后易于入彀。”(《举业卮言》卷一)隆庆二年进士张位认为:“主司看文,如走马看花,须七篇一气呵成,有行云流水之妙,更无一毫滞碍,此青钱也,万选万中矣。”(《看书作文法十六则》)“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也就是王衡所说的“蓬蓬勃勃”“活活泼泼”。这些观点,被后世揣摩家们认可并发扬光大,如薛鼎铭说:“上乘文字,以神理为主。今日场中,理不必太精,神亦未必尽能领取,只争一个‘气字耳。气盛自足以夺人。若节节为之,推敲字句间,而气更销沮,未论文之工拙,已先输却别人矣。”(《墨谱》卷二)孙万春也说:“尝见遇合之文,乍观之令人吃惊,及至将其文读熟,又似无甚好处者,此无他,一股热气鼓荡于字里行间,故看去甚好也……若工夫不密者,场中作了一句,再想一句,无振笔疾书之乐,安得有气乎?”(《缙山书院文话》卷三)古文家讲究“气盛言宜”,其“养气”功夫,主要从道德、学问修养入手。而薛、孙二人所说的“气盛”,似乎更为强调文字外在的流动性。依照他们的观点,有两种人的文字无法做到“气盛”,一种是长年不作文、手笔生疏的人,“作了一句,再想一句”,水平太差,自然无法入选。另一种则是宿儒名家,下笔慎重,处处推敲,文气亦会凝滞不畅。因此,科场文字要想得中,必须放开胆量,潇洒落笔,把握好“锤炼”的分寸。
四是声调响亮。周作人曾说,八股文是一种具有“音乐分子”的文体(《看云集·论八股文》)。好的八股,读来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能在科场中脱颖而出的八股,则在平仄协调的基础上,声调响亮、高昂。这一点,也是揣摩家们的共识。如薛鼎铭说场中作文,“理不必异人,只赌得一声高耳”(《墨谱》卷二)。仲振履也说:“文无论有无酝酿,只要声调高。高则中矣。”(《秀才秘钥》)。作文只讲“腔调”,当然会有华而不实甚至不知所云的弊病,但揣摩家的“炼调”之法,却多有与汉语语音规律相符之处。如他们注意到,文章声调,主要由句首句尾之连接词、语气词决定,《制义丛话》卷二四载当日作墨卷者有“偷调”之法,“有偷明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所谓“偷调”,就是从优秀范文的虚字入手,通过对他文句式、虚字的借用而实现对他文声调乃至整体风格的化用、模仿。又如他们看重仄声字在整篇文章声调中的作用,《制义丛话》卷二四、《缙山书院文话》卷二均记载晚清科场曾流行一种“且夫”调:“每于提比(作者注:即八股文开头“起讲”后的两小比)之后,或末比之前,突用‘且夫以振其势。”“且夫”在文章结构上有“提顿”之用,且声调仄起,有突出之概,因此能使文势随之振起。《缙山书院文话》卷四还记载了一个抬高文章声调的诀窍,是在一段语气结束后,用“五百年”“八百国”“十六字”等“突接”。“五”“八”“十”皆为急促高昂的仄声,可以使文章整体音调上扬,达到“越唱越高”的效果。
五是遵循“中庸”之道。科场之文,最重要的是“中庸”。在自我才情的抒发上,要行“中”道,如明人陈懿典说八股文“非若诗古文可以逞才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无才;非若诗古文之可以炫学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无学;非若诗古文之可以才与学惟吾意之所适也,而为之又不可以拘拘谫谫,不惟吾意之所适”(《论文二章》)。即要在“逞才”“炫学”与“合规”的两端求得平衡;在遣词造句上,也要行“中”道,如袁黄列举了一系列八股文写作中需要小心平衡的风格与作法:“文欲极新,又欲极稳;欲极奇,又欲极平;欲说理,又不欲著色相;欲切题,又不欲粘皮带骨。”“不锻炼则不精,过于锻炼则伤气;不敷衍则不畅,过于敷衍则伤骨。”(《心鹄》)至于如何做到这种平衡,则只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外,在八股写作中争议最大的“学古”与“趋时”的问题上,揣摩家们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大多在“古”与“今”之间采取了一种融通的态度,并不一味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道。如清人司徒德进认为,文章“理法本诸先正,风气参乎时尚”,方可“百发百中”(《举业度针》)。孙万春教人要从古文、先辈名家文中学其“风骨”,从“时墨”中学其“采泽”,如此表里均到,“纵不成名,亦必寿世”(《缙山书院文话》卷二)。薛鼎铭则认为,时文既要学古文之“劲气”,又要注意因学古而“笔力太高”的情况(《墨谱》卷一)。清代流行的殷价人《劝学诗》中,有“不浅不深期恰好”之句,八股作法千变万化,要想“中彀”,关键是要“恰好”,即能得“中”道。处处“恰好”的文字,或许个性不足,甚至可以说平庸,但这种面面俱到、无懈可击的平庸,正是思想、技巧规范化的体现,因此是科场文字的最佳选择。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