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伊藤仁斋《论语古义》思想建构
董灏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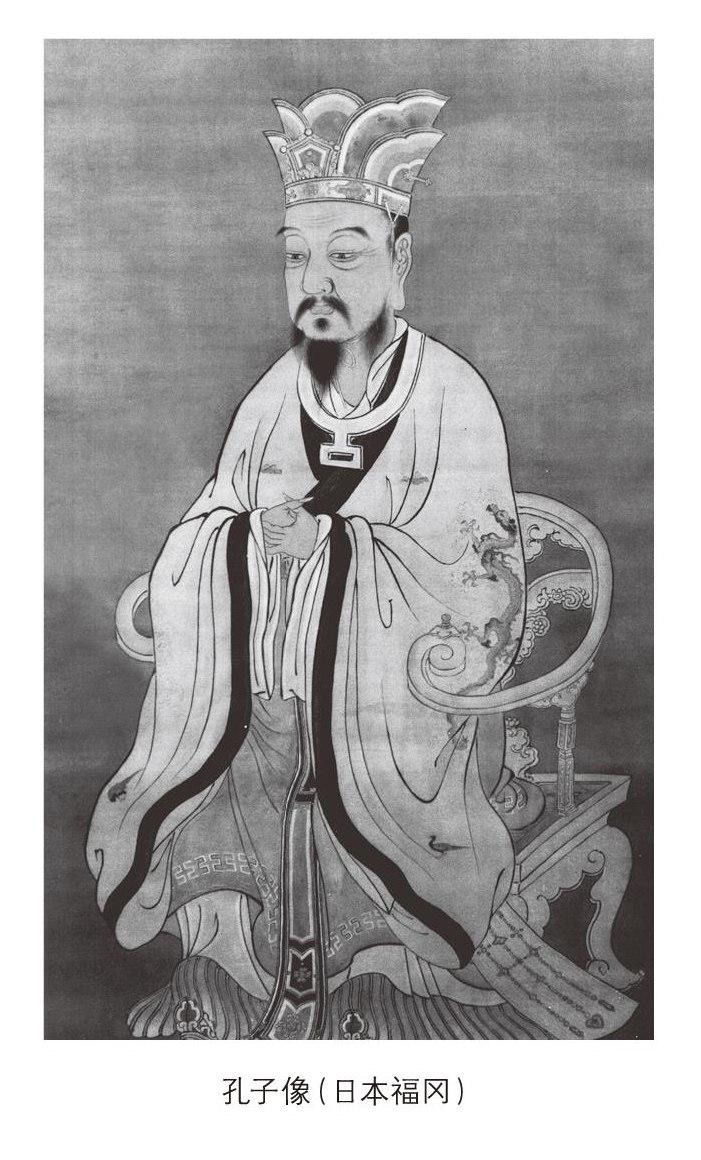

《论语》一书在后世的影响力以及所获得的殊荣恐怕是子贡、子夏、子张等编撰者也未曾想到的,但后人对《论语》的最高评价却不是出自中国儒者之口,而是日本江户时代古义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下文简称“仁斋”),他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其中,“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中的任何一个评价词语都足以凸显出《论语》举足轻重的地位,仁斋却三者连用,足见他对《论语》的推崇程度之高。
考察中日典籍交流史,《论语》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虽难以知晓,但根据《古事记》的记载,《论语》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就已传入日本。此后,《论语》开始在日本社会流传,先后成为日本皇室、贵族、平民知识人的必读之书。但是,《论语》在日本的广泛流行却是在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对儒学(主要是朱子学)的提倡,使得官学、藩校以及“寺子屋”等教育机构蓬勃发展,推动了《论语》等中国儒学典籍在日本的传播。在这一背景下,朱子学派、古学派、阳明学派、兰学派、折衷学派、考据学派等学者出版了大量注解《论语》的著作,在此不一一例举。其中,仁斋的《论语古义》和徂徕的《论语征》最具代表性,二书不仅直接影响到江户中后期折衷学派、考据学派的《论语》解读,还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了中国清儒的《论语》注疏。关键的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正是出自《论语古义》的“总论·纲领”之中,而仁斋为何会得出这一认识?这既得益于《论语》自身的魅力,又与仁斋的学术走向密切相关,并不是仁斋简单地接受、推崇中国文化的结果。
考察仁斋的学术历程,无论是作为朱子学者还是作为古学者,甚至在他由朱子学转向古学的过程中,《论语》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少年和青年时代,《论语》是仁斋的启蒙书籍之一,但因中国朱子学在日本江户的盛行,故仁斋所阅读的《论语》并不是原典《论语》,而是经由朱熹等人注解过的“四书”中的《论语》,朱子学的思想被赋予其中。仁斋早年深受朱子学的影响而启蒙开悟,“余十六七岁时,读朱子四书,窃自以为是训诂之学,非圣门德行之学,然家无他书。语录、或问、近思录、性理大全等书,尊信珍重,熟思体玩。积以岁月,渐得其肯綮”(伊藤仁斋《同志会笔记》二七)。在二十七八岁时(1653—1654),仁斋先后写成《太极论》《性善论》《心学原论》,此三篇文章详细阐述“危微精一”之旨,即朱子学的“孔门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然而,随着对朱子学研习的深入,仁斋不仅得出了不同于朱子学的观点,还在“格物穷理”的实践中陷入了困境,进而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精神危机”,大病一场,“俄而罹羸疾,惊悸弗宁者,殆十年所,俯首傍几,不出门庭。左近里人,多不识其面”(伊藤东涯《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这意味着,仁斋与后来王阳明“格竹而病”的经历极为相似。由于仁斋对朱子学深信不疑,并依照朱子学的说教进行“格物穷理”,结果在实践过程中却事与愿违。于是,仁斋僦居松下巷读书,其目的是解决思想困惑。因而,仁斋将读书的范围扩展至王阳明、罗近溪等人的心学之作,并修习禅宗的“白骨观”法。然而,无论是心学还是禅学,其思想取向与朱子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较为侧重“心性”层面的发挥,从“宇宙本体”的高度强调“格物穷理”或“发明本心”。所以,这一做法非但未能帮助仁斋解决难题,反而加剧了他的思想混乱。重要的是,多年“精神危机”让仁斋对早年信奉不已的朱子学产生了严重质疑,尤其是针对朱子学最为推崇的圣人之道(以孔孟为主)。仁斋通过直接阅读未经朱子学者注解的《论语》《孟子》,使他意识到体用理气、明镜止水、冲漠无朕等朱子学说,全是佛老的续馀,绝不是孔孟之道的主旨,但当时流行于日本的《论语》和《孟子》多是以朱子学的注解为主,完全曲解了圣人的原意,必须全部抛弃。于是,仁斋的思想取向开始由朱子学转向古学,提出“气一元论”,批判朱子学的理气二元论、居敬主静等说,并主张尽废宋儒注脚,重解《论语》和《孟子》。
据《先府君古学先生行状》载,仁斋对《论语》注解首次完成于三十六岁(1662),此即《论语古义》的初稿,而这一注解正是仁斋经历了“精神危机”后按照“己意”解读《论语》的成果,虽然仁斋的古学思想尚未定型,但已明显不同于朱子学者的《论语》解读。十年后,仁斋完成了《孟子古义》的初稿,后因京都大火他仅持《论语古义》的部分手稿避居大恩寺。十一年后仁斋经进一步修订、完善而写成了《论语古义》(第二本)和《孟子古义》(自笔本)。此后直至去世,二十多年间,仁斋反复注解《论语》,最终的《论语古义》于1704年(仁斋于1705年去世)由其弟子林景范笔写而成。由此可见,仁斋对《论语》绝不是仅停留在学习层面,还用了超过半生的时间注释《论语》,诚如佐藤正范和伊藤东涯在《刊论语古义序》中的评价:“其书成于毕生研钻之馀,易稿凡五,晚年遂能成之”,“改窜补辑,向五十霜,稿凡五易,白首纷如。”这意味着,《论语古义》是仁斋穷年累月解读《论语》的结晶,他甚至将《论语》置于“六经”之上,并进一步言道:“《论语》一书,万世道学规矩之准则。其言至正至当,彻上彻下,增一字则多馀,减一字则不足,道至乎此而尽矣,学至乎此而极矣,犹天地之无穷,人在其中而不知其大,通万世而不变,准四海而不达。呜呼大矣哉!”(伊藤仁斋《论语古义·纲领》)即使《论语》中有多处重复内容,仁斋甚至认为这不是编者的失误,而是孔子反复言及的内容,弟子们分别记载而共同编入《论语》之中,其意味深长,更需后学深入审思。
无疑,仁斋一生中对《论语》用功之勤、用功之久是其提出《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的底气,但《论语》为“圣人之道”的载体则是仁斋称其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的第一个原因。如众所知,《论语》虽非孔子之作,但却是孔子的弟子们所编纂的孔子言论集:“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实为孔子思想的载体。通过《论语》原文,仁斋意识到,孔子罕言“天道”,主言“人道”,而“人道”中绝无“格物穷理”之说。因此,仁斋提出了其古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圣人之道以人伦日用为主”,他以“路”解“道”,即“往来通行”之意,并将“道”分为三类:天道、地道和人道,并指出它们的不同:“阴阳交运,谓之天道。刚柔相须,谓之地道。仁义相行,谓之人道。”(伊藤仁斋《语孟字义》)天道、地道、人道各司其职,不可混而一,尤其是不能以阴阳为人之道、不可以仁义为天之道,而朱子学之失就是将天道与人道合二为一,明显违背了孔子之道。在仁斋看来,孔子的人道才是真正“圣人之道”的主体,此道犹如“大路”,贵贱尊卑皆可通行。只有王公大人可行而匹夫匹妇不得行,则非“圣人之道”。只有贤智者可行而愚不肖者不得行,则非“圣人之道”。是故,凡是远离“人道”的高远广大、难知难行之道,既无资于人伦,也无益于国家之治,仁斋皆视为“邪说”。不宁唯是,仁斋还指出,由于孔子之道以“人道”教化育人,故孔子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尧舜等人:“尧舜,天子也。宜其声教之远暨,而馀泽之久流,然治绩不过于九州,子孙袭封亦不及后世。仲尼,匹夫也,旅人也,然道德远暨,不可限量。以地,则自邹鲁之乡,不问海之内外,至西夷之远。凡有文字国,莫不尊崇夫子之教,以礼,则身被天子服裳,用天子礼乐……以时,则自夫子时到今,既二千馀年,犹一日也,其子孙亦相袭封爵,到今不绝。”(伊藤仁斋《童子问》)正因如此,仁斋称赞孔子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圣人”,将孔子的地位与《论语》的地位等同,皆冠以“最上至极宇宙第一”的赞誉,可见二者在仁斋古学中的地位。
重要的是,《论语》不只彰显出“圣人之道”即“人伦之道”的取向,还以“仁”作为“圣人之道”的主体,并以“为仁”之道作为“圣人之教”,此为仁斋称赞《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的第二个原因。在仁斋看来,《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为人道之大本,众善之总要,是“圣门学问第一字”,它的含义在《论语》中虽未明确给出,但这不是孔子及弟子们的失误,是因为孔子弟子皆知“道为人伦之道”,“仁”为其中的常事,故不问孔子“仁”之含义,唯问如何实现“为仁之方”,孔子亦只以“所以为”之方告之。譬如种花,“仁”犹如花,“为仁之方”如同灌溉培植之法,而未尝言及花的形状颜色,故《论语》中的弟子所问,孔子所答,皆是围绕着“为仁之方”而展开。但是,对于“仁”的具体含义,仁斋提出了“语孟一体”的解读方式,认为,《孟子》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三处,是孟子论“仁”之含义的关键点,将此与《论语》中论“仁”之处结合考察,“爱人”是对“仁”字最好的解释,因而,“为仁之道”就是教人如何做到“爱人”。具体而言,君臣之间的“爱”谓之义,父子之间的“爱”谓之亲,夫妇之间的“爱”谓之别,兄弟之间的“爱”谓之叙,朋友之间的“爱”谓之信。《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关于“仁”的论述皆自“爱人”而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道都不离“爱人”二字,此为人道之全体。从中可知,仁斋虽从《孟子》的视域解读“仁”,但基本上符合《论语》中“仁”的原始意涵。关键是,仁斋对“仁”的理解并不完全局限在“爱人”,而是强调“爱有等差”的“仁爱”必须以“义”配之,才能知其所当为而为之、所不当为而不为之,否则,一味地强调“爱人”而不顾其他,就与墨家“爱无差等”式的“兼爱”没有本质区别了。这意味着,仁斋不仅将《论语》与《孟子》做一体观瞻,更以“仁义”并称,强调“义”为“仁”之配,仁之与义,犹如阴之与阳,二者密不可分,仁而无义则非仁,义而无仁则非义。因此,《论语》以仁为宗,以义为辅,礼、孝、悌、文、行、忠、信、敬、恕、让等皆在“仁义”的基础上展开,是实现“仁义”的不同方法。所以,《论语》中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等,表面上看似乎与“仁义”无关的说教,实则关联甚深。由此可知,作为《论语》核心的“仁义”并无复杂的含义,故孔子只用平实而易知的言语教授弟子如何实现“仁义”的方法。很明显,仁斋将《孟子》中“义”赋予《论语》之中,虽然有悖于《论语》的原意,但却补充了“仁”的内涵,进而突出《论语》的主旨在于教人“修道德”,为“圣人之教”的主体,而程朱等人将《论语》“理学化”,视“格物穷理”为“圣人之教”的重要内容,完全是误解《论语》。
如果说,《论语》为“圣人之道”与“圣人之教”的载体是仁斋盛赞《论语》的主要原因,那么,《论语》中所凸显的“华夷观”则是仁斋称赞其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的第三个原因。《论语》中论及“华夷”关系的内容主要包括:“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等。虽然,孔子生于春秋乱世,面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惨状而严防“华夷之辨”,但孔子却以是否行“仁义”、知“礼义”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故孔子会有“乘桴浮于海”“居九夷”的想法。关键是,仁斋不但继承了孔子的华夷观,突出强调“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还指出“华”与“夷”的身份并不绝对,并且“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岂能拘泥于“华夷之辨”?后世学者以“华夷之辨”为圣人之道的主旨实是害道不浅。尤为重要的是,仁斋将“九夷”解释为“日本”:“九夷,未详其种,徐淮二夷见经传,若我日东,《后汉书》已立传,即扶桑、朝鲜等名,皆见于史传,夫子所谓九夷者,恐指此类而言。”(伊藤仁斋《论语古义》)这样一来,孔子所去之地就变成了日本,已不是中国的“九夷”之地。之所以将“九夷”视为“日本”,是因为日本具有中国不具备的“皇统从未中断”的优越特性。在仁斋看来,日本从人皇神武天皇(前660)开国至今,皇统绵延不绝,从未出现过乱臣贼子篡夺天皇皇位之事,相反,中国王朝的篡弑之事时常发生,仅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所以孔子有了欲去“中国”而居“日本”的想法。显然,仁斋的说法缺少史事及文献依据,即便是同为古学派学者的荻生徂徕也对仁斋的“九夷”解释颇有微词,将其视为“阿谀奉承之言”,认为“九夷”必是孔子所去过之地,不可能是未知之地,仁斋以“日本”解之实是不识“文辞”有古今之别,以至于出现了以“今言”解“古言”的失误,但徂徕与仁斋的相似之处在于他解释“九夷”的过程亦凸出日本的优越性,“吾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传会《论语》,妄作无稽之言乎!”(荻生徂徕《论语征》)然而,即便仁斋解读“九夷”有误,但他赋予其中的日本优越特性却被后世学者继承,对江户学者的“日本优越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仁斋经由《论语》而凸显出“孔子欲居日本”的取向,无形之中提高了日本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中国学者赋予日本的“夷狄”身份,亦从另一层面折射出仁斋对《论语》极度推崇实有一定的“日本主义”取向。
由上可知,仁斋对《论语》的推崇与他的学术取向紧密相关,尤其是在他转向古学之后。对于日本《论语》的研究,不能简单地看作中国“《论语》学”的翻版或支流,而是应从日本历史及日本思想脉络入手才能了解日本“《论语》学”的特质。所以说,仁斋称《论语》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称孔子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圣人”,并不是简单地推崇中国思想,而是借用中国思想来构筑自身的思想体系,进而折射出日本学术取向的优越特质,在这一脉络下,仁斋对《论语》的推崇便不难理解了。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