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作家的两份名单
傅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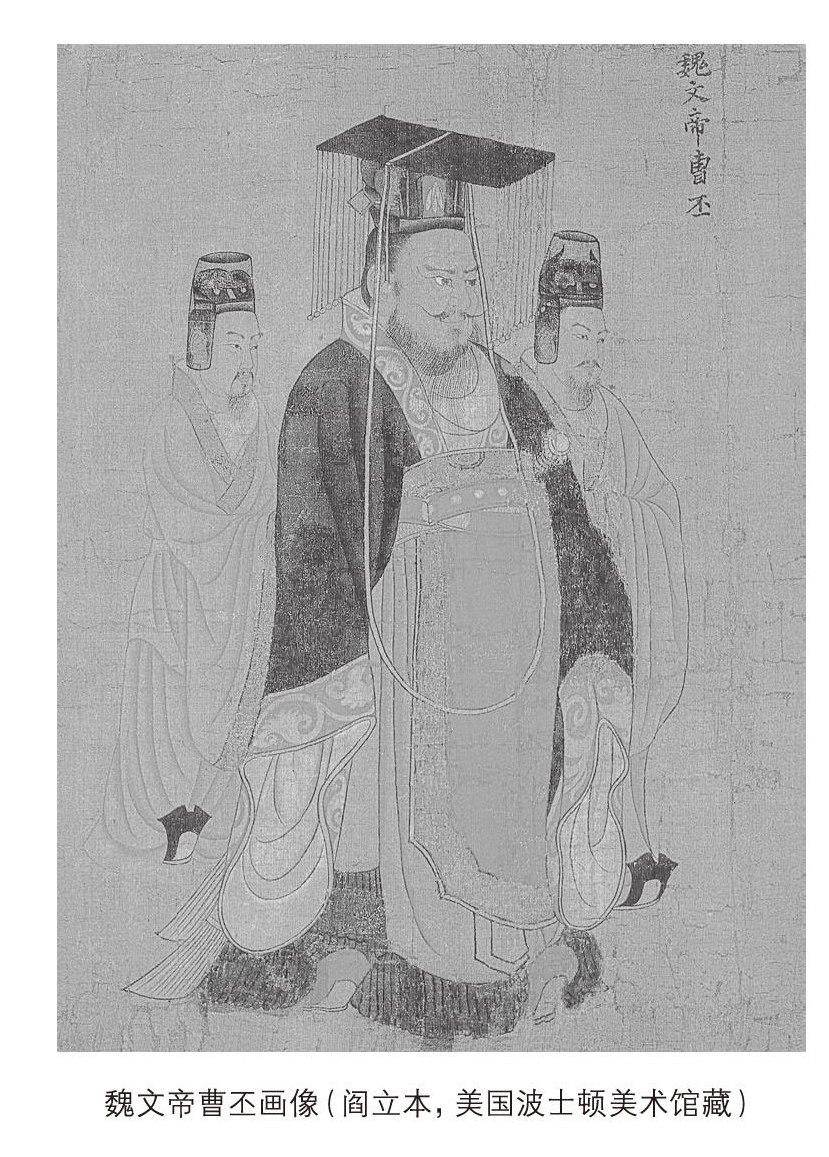
建安作家一般以“七子”为代表,这出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曹丕开列的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作家名单,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也开列了一份名单,与曹丕开列的名单略有不同。这两份名单有同有异,其中却蕴含不同的政治意义。
一 两份名单的产生
1.曹植《与杨德祖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216)
是书说“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至建安二十一年适二十五岁,可知是书作于建安二十一年。
《与杨德祖书》:“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这是建安二十一年曹植与杨修的信中所列当时建安作家的名单,主要是: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和杨修。
2.曹丕《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之后。
《典论·论文》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里所列的名单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所谓“建安七子”。
曹丕建安二十二年冬在《与王朗书》中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样看来,曹丕《典论》在建安二十二年被立为太子时就已写好。不过中华书局版《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魏书》于“故所论撰”之后断为史家言,非曹丕《书》语,这样断句也有道理。高敏先生便据此断《典论》是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至黄初初年(220)所写(参高敏《对“异议”的异议》,《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张亚新先生认为这样说不妥,因为《魏书》明言“所著”,这就说明《典论》是在黄初之前写好的(《〈典论·论文〉写作时间考辨》,载《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并且张先生说曹丕在黄初即位后不可能有馀暇去从容撰《典论》。按,张亚新先生说得对,即使如中华书局所标点的,也并不排除曹丕在二十二年冬十月之后撰写的可能性。《全三国文》卷三〇载卞兰一篇《赞述太子赋》,《序》曰:“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奉读无倦。”观卞兰所赞,即《典论》内容。如“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即赞《论文》,又“匿天威之严厉,扬恺悌之和舒”,即赞《奸谗》一篇,这也可证明《典论》是曹丕为太子时作。《典论》早佚,严可均《全三国文》辑有一卷,内中有《太子》一篇,曹丕说:“余蒙隆宠,忝当上嗣,忧惶踧踖,上书自陈,欲繁辞博称,则父子之间不文也,欲略言直说,则喜惧之心不达也。”察其激动之语气,乃丕初为太子时的欢喜之词,这和《资治通鉴》卷六八所载事实相符:“太子抱议郎辛毗颈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因此《典论》虽不可明确断其时间,但说它是作者于建安二十二年冬被立为太子后的不长时间内所作,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二 两份名单隐藏了什么政治意义
这两份名单涉及的人物有不同,曹植所称“今世作者”是: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和杨修。曹丕所称的“今之文人”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两相对比,差的是孔融、阮瑀、杨修,即除了王粲、陈琳、刘桢、徐干、应玚五人是曹植和曹丕都认可的外,曹植的名单里没有孔融、阮瑀,曹丕的名单里没有杨修。对于这个不同,最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由郑州大学高敏先生首先生提出来,他在《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一文中发现了这两份名单的差异,认为这个差异是与当时曹丕、曹植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高敏先生主要的看法是:“曹丕与曹植的政治斗争,就不能不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待某些文学家的评价与看法。更有甚者,从曹植的党羽吹捧曹植的情况来看,说明他们极力突出曹植的文学才华,希望以此作为同曹王争夺太子地位的资本,事实上曹操所以爱幸曹植,也确实因为他‘才捷。这就是说,曹丕、曹植为了争夺太子地位,除了玩弄了各种阴谋手段之外,还在各自争取当时的著名文学家的支持,并各自把自己置于这批文学家的领导地位,实为他们扩大影响和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这样就埋下了他们要各自对当时著名文学家作出评论的政治动因。由于他们对当时文人的政治爱憎不同,就自然要影响到他们关于当时著名文学家究应为哪些人的具体看法,于是歧异就产生了。”对高敏先生的这个看法,我非常同意,这个发现很好地说明了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一些文学史材料,并不能简单地从文学本身检视,很多都隐藏有政治的动机。
高敏先生的这个发现,在当时引起了争议,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非常反感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干涉有关。但时至今日,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后再看历史现象,我们会发现,文学真的离不开政治。曹植与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对他们所说的“今世作者”和“今之文人”,的确离不开一定的政治考虑。
我们同意高敏先生的基本意见,认同曹植与曹丕这两封信的写作和发表都是具有政治考虑的,但通过对当世作者的点评来表达政治意见,是怎样发生的呢?就曹植和曹丕这两篇文章看,似乎曹植首先使用了这个手段。曹植此书写于建安二十一年,曹丕的《典论·论文》写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其被立为太子以后。这样看来,是曹丕看出了曹植写信的用心,因此便在《典论·论文》中重新确定名单,表达他对当代文学的看法。高敏先生分析了曹丕、曹植兄弟二人争太子过程中的表现,揭露出当时二人间的政治斗争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说二人在文章中对文学的评议只是为了争取著名文学家的支持这一看法,可能要有所修正。因为,曹丕《典论·论文》写于其已经做太子之后,他已经不需要争取文学家的支持来做太子了,而曹植也并非要表现文学上的才能,进而拉拢当时的文学家,而是要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抱负。因此我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还得对建安时期以曹丕、曹植为首所领导的文学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即曹植和曹丕的这两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的,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观点?针对什么?有什么意义?
我们注意到,对于建安时期的文学活动,在曹植之前,曹丕已经在与吴质的通信里就讨论过了。写于建安二十年的与朝歌令吴质的信里,曹丕就提到著名的文学活动“南皮之游”:“每念昔日南皮之游。”南皮之游似乎是非常著名的文学活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晋宋以后,南皮之游已经成为后人的传说了。但实际上,南皮之游,我们只在曹丕的书信中见过,其馀建安作家皆未提到南皮之游。南皮,属冀州渤海郡,距邺城五百多里,不可想象曹丕的文学之游能够远跨五百多里路至南皮一游。因此,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37—38页),考为建安十年曹操破南皮,斩袁谭时。我深以为是。《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松之注曰:“太子即王位,又与质书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龙飞,或将或侯。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初,曹真、曹休亦与质等俱在渤海游处,时休、真亦以宗亲并受爵封,出为列将,而质故为长史。王顾质有望,故称二人以慰之。”正谓参加南皮之游者有曹休、曹真等武人,盖破谭为一大事,战胜之后诸人在南皮作游,有文人亦有武人,与后之邺城时文学活动性质不同。据曹丕《与吴质书》说:“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从曹丕对这个活动的描写看,似乎更是文人的雅兴,虽曹休、曹真亦预南皮之游,但未必都又参加了“白日既匿,继以朗月”的夜游。如果南皮之游确实发生在建安十年,则见建安文学活动在戎马倥偬之际已经开展了。南皮之游参加的人应该有孔融、阮瑀、陈琳、徐干、应玚等,其馀如杨修、繁钦、吴质早在幕中(《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未列吴质,但曹丕是与吴质书中提及此事,吴质当预其游),曹丕时为十九,曹植时为十四。南皮之游,为曹丕心心系之,但似不见于曹植的文字中,则南皮之文学活动属于曹丕,未必属于曹植(俞绍初先生《“南皮之游”发微》不同意曹、沈之说,考订为建安十六年,可备一说)。
从这个记载看,以曹丕为首倡导的文学写作活动,在邺城攻下之后就发生了,他的文学领袖地位也很早就建立了。曹丕是曹操次子,但其兄曹昂于建安二年死于张绣叛乱中,因此,曹丕即为长子。随着曹操地位的日益增高,曹操继承人,也即可能是太子,越来越成为问题了。本来曹丕作为长子,作为继承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曹操却是一个不循常规的人,他几次表示对曹植的欣赏,主要是因为曹植的文学才华。所以在曹丕和曹植之间便渐渐形成了竞争,而建安十六年,曹操为诸子高选官属,曹丕、曹植各自拥有自己的班底。曹丕以五官中郎将置文学官属,天下向慕,宾客如云,曹植亦积极收拢人才,《魏书·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才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大概在建安十六年曹操封诸子时开始,曹丕、曹植兄弟的争储便转为公开而激烈。曹植以文学才华盛,公私物议皆奖饰曹植,曹丕每每有所失,但曹丕更多的是组织文学活动,我们看建安十六年开始的邺下文学时期,存留的诗文多以曹丕为中心。因此,曹丕除了在政治上表现得深厚持正,更在文学活动上表现个人的组织能力。因此,写于建安二十年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便以南皮之游为题,表明他对文学的倡导之功。南皮之游时,曹植仅十四岁,还不足以与曹丕相抗,所以曹丕信中的描述,显示出他在文学活动上的资历和身份。此外,曹丕的文学才能其实并不比其弟差多少,二人风格不同而已。陈寿说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文强识,才艺兼该”(《三国志·文帝纪评》),并不是虚言。刘勰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又说“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文心雕龙·才略》)。这是公允的评价。
吴质是曹丕的朋友,也是他政治集团中人,建安二十年,也是曹丕、曹植兄弟争储趋于激烈之际,曹丕发表此信,应该是有用意的。对于曹丕的这个动作,曹植身为其弟,也采用与杨修通信的方式,以更为高扬的气势纵论当代作家,他在信里特意点出六位,应是当时最得人望的作家。相比于曹丕的回忆过往的文学活动,曹植则以藩王身份对这些作家展开批评,显示出高视群雄的气势。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曹植并不是表示自己的文学才能,恰恰相反,他明确说自己志不在写作上。他一方面公开说自己远远超过这些作家,如说“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文选》卷四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7,593页),另一方面他公开说“辞赋小道”,又说自己“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已经是明确表示他对太子之位的想望了。至于他所列六位作家名单,我想这可能并没有特别的用意,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在文学上向他哥哥挑战,只是选择当时有名的几位作家评论而已。他的名单里之所以没有孔融,一是因为孔融辈份非其他诸子可比,二是因为曹植明确说是“今世作者”,这个今世,是指当时存世的人,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已经被杀,所以不入曹植的名单。阮瑀也是如此,他卒于建安十七年,也不是曹植所说的“今世作者”。因此我们说曹植不评孔融、阮瑀,与他所限定的“今世”有关,虽然存有政治意义,但并没有针对曹丕的某一个做法。但是当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再论“今之文人”,专门提出“七子”时,则具有针对性了。
《典论·论文》的批评史意义,笔者写过《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一文,对曹丕为什么能够提出有关文学价值、文气、文体、风格等问题,作过专门的讨论,也曾在《论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一文中讨论过曹丕、曹植兄弟二人的文学观实际上并无不同,之所以在他们的书信和文章中表现得不同,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些我们不论,仅从《典论·论文》所列的这七位作家名单看,曹丕针对曹植的意思是很明显的。
曹丕这里所列的七子,有两位是曹植不论的,一是孔融,一是阮瑀,曹植所论六位作家,有一位是曹丕不论的,即杨修。曹植不论孔融,是因为孔融在建安十三年就已经被杀,不在“今世作者”之列。阮瑀也是如此,除了他不是今世作者外,估计当时还未入曹植法眼。阮瑀于建安初入曹操幕府,长于书记,但在文名上可能还不能与王粲、刘桢诸人相比。曹丕的不论杨修,当然是因为杨修是曹植集团中人,其卷入丕、植兄弟二人政治斗争太深,以致被曹操杀死。若论文名,杨修自然名列前茅。这里注意的是,曹丕专门增列了孔融和阮瑀,则值得讨论了。诚如高敏先生所说,孔融辈分与建安诸子不同,是与曹操一辈的人物,不应被列入,且他在建安十三年被杀,并没有参加邺下文学活动,那么曹丕还要将他列入,则是有用意的了。从字面上看,曹丕也是论“今之文人”,但很明显,曹丕的“今”与曹植不同,而是包含了已故作家。曹丕对“今之文人”的范围划定,大于曹植,显示了作为太子的曹丕对建安文学的整体把握。而他之所以将孔融划作“今之文人”,当是以南皮之游作为根据,也就是说他认为建安文学起点是从南皮之游开始。这样一来,曹丕所讨论的“今之文人”,实际上是他对全部当代文学所作的理论总结和指导,这个高度,当然不是曹植可以比拟的。
孔融在生前已经享有大名,其在死后,亦受世人尊重。曹丕甚爱孔融文,孔融死后,曹丕专门命人搜集孔融作品(《后汉书·郑孔荀列传》:“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因此,曹丕《典论·论文》首列孔融,并不意外,但以阮瑀入于七子,则是阮瑀首次进入建安文学的核心榜。阮瑀虽有曹操烧山始出的传说,但经考订,属于不实之说(事见《魏志·王粲传》附《阮瑀传》注引《文士传》,裴松之辨此事为不实)。不过,曹丕对阮瑀的器重,并不是在曹植建安二十一年写信给杨修后,阮瑀生前,应该也是得到了曹丕的看重,如阮瑀死后,曹丕写过《寡妇赋》等作品,并命群臣和作,可能与阮瑀曾经参加过南皮之游有关。阮瑀是曹丕早年组织文学活动中人,曹丕对他的评价与曹植不同。阮瑀一者因为早卒,二者文名未达于前茅,所以在曹丕之前,未见有人扬举阮瑀。而曹丕以太子之尊,将他列入七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对阮瑀地位的抬高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阮瑀死于建安十七年,不及见曹丕对他的褒扬,但却对他的后人有极大的帮助。阮籍的成长,就是在曹丕的这种关爱中完成的。这又是一个要说的事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