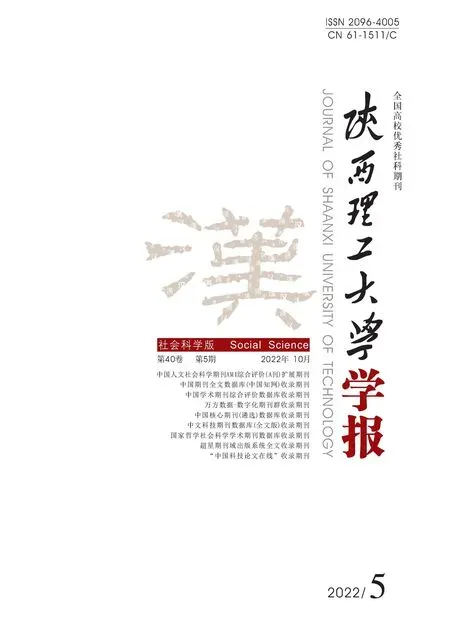布兰肯伯格“自然自明性的失落”的治疗裨补
——以表达性艺术治疗为例
陈 禅, 刘 毅
(南京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3)
艺术为什么可以对精神分裂症(schizopherenia)有一定的疗愈功效?艺术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是基于怎样的病理学分析,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治疗?一般来看,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难以定义且施治棘手的精神疾病,对其进行干预治疗多集中于药物治疗或以电疗等传统手段,辅之以一定的心理咨询、团体疗愈等。尽管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手段随着对病理认识的逐渐深入变得愈发多样且疗效显著,然正如徐献军所总结的那样:“人们已经花费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试图弄清精神分裂的病理发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成功,因为人们始终无法确定精神分裂的本质。”[1]当代主流的精神分裂研究几乎都集中在生理病因的分析上,而以布兰肯伯格(Wolfgang Blankenburg)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分裂理论以更加丰富和坚实的人文主义根基和价值论取向在该领域中获得广泛认同和长足发展。布兰肯伯格在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还原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精妙且颇具说服力的治疗理论和临床分析,其核心论点是将精神分裂主观经验的核心变异设定为“自然自明性的失落”,由胡塞尔的超越现象学原理解析出四种不同的变异表现,并由此奠定了精神分裂病理学现象学分析一派的理论基础。但颇为遗憾的是,布兰肯伯格的理论尽管在病理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仍有未能求全之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是主观经验的解释,布兰肯伯格竟未能提出与之对应的纾解手段。若其病理分析依旧对应使用旧有的治疗手段,那么其实际意义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主观病因论突出强调病理的主观性,如若不能有运用于治疗的可能,布兰肯伯格难免给人留下“臆断”的口实。显然,他的病理分析和治疗实践存在着肉眼可见的断裂,这亟需后学进行弥合与缝补。而艺术治疗,尤其是表达性艺术治疗,将是耦合其理论并用于治疗实践的最佳途径。
艺术治疗(Art Therapy)作为一门学科勃兴于20世纪50年代,在疗愈战后欧美世界的精神创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最初意义上的艺术治疗是由美国艺术治疗学家南姆伯格(Margaret Naumburg)创建的“艺术心理治疗”。顾名思义,该方法是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加入艺术创作活动以辅助心理疗愈。这种治疗方式源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荣格(Carl Jung)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治疗者试图从患者的涂鸦之作中探测他们隐秘的无意识世界并进而辅助心理治疗,南姆伯格将此称之为“Art in therapy”(艺术用于治疗);这是艺术在心理治疗领域最初的运用形态;20世纪60至80年代,随着存在主义哲学在欧美学界的兴盛,艺术被视为人类存在于世的基本活动,人与艺术由此获得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联结与互融;因而,英国的艺术治疗师协会一直标举着“艺术即治疗”(Art as therapy)的口号。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治疗的种类不断丰富,治疗方式也在不断拓展。艺术治疗从过往的以视觉艺术为中心逐渐转向多元化、自由化和综合化的治疗模式。由此,表达性艺术治疗(Expressive Arts Therapy,简称表达疗法)便成为20世纪以来艺术治疗领域最为兴盛的一支流派。它主要来源于现象学心理学以及罗洛·梅(Rollo May)、罗杰斯(Carl Rogers)等学者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代表人物有娜塔莉·罗杰斯(Natalie Rogers)、肖恩·麦克尼夫(Shaun McNiff)、艾伦·莱文(Ellen G.Levine)等,主要的理论和实践阵地在美国的莱斯利大学。表达疗法一改“艺术心理治疗”中艺术的从属地位,将各类艺术活动本身视为治疗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手段。他们坚持认为,在艺术创造和艺术表达的始终,在身体、画笔、刻刀等媒介的艺术活动中,艺术就已经发挥了应有的疗愈作用。表达疗法的基础主要在于现象学,尤其是尼采(F.Nietzsch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在对作品、自我、他者、世界关系的思考中,表达疗法建立了与布兰肯伯格病因理论的对话和互补空间。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布兰肯伯格的研究并不算热门,主要集中于他提出的“共通感(common sense)”,其中关注度较高的是Aaron L. Mishara 的论文“OnWolfgangBlankenburg,CommonSense,andSchizophrenia”;[2]在国内,徐献军等学者不遗余力地在哲学心理学领域引进布兰肯伯格的代表作《自然自明性的失落》,并发表了颇多研究布兰肯伯格的相关论文,但这其中将表达疗法与布兰肯伯格的精神分裂病理分析相关联的研究仍然不足。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艺术治疗的病理分析在国外已然颇具规模 ,但国内的讨论却较为寥落。目前,国内对艺术治疗的研究以孟沛欣、李世武等学者为代表,前者在译著与临床治疗上颇有建树,后者在结合人类学分析艺术治疗上也有很多成果,但关于艺术治疗,尤其是对表达疗法的原理探究尚属少数。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曾于《黄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表达疗法哲学肌理的综述性文章(1)周显宝教授曾发表于《黄钟》杂志的两篇表达疗法的相关文章:《身心健康之维——表现艺术治疗学的历史与哲学考略(上)》,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身心健康之维——表现艺术治疗学的历史与哲学考略(下)》,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其理论基础和疗法特点,但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实际上,将艺术引入精神分裂临床治疗的案例在国内外比比皆是:通过文献检索可知,将戏剧 、舞蹈、绘画、雕塑应用于精神分裂治疗实践的文章极多。遗憾的是,这些论文所记录、论证的心理实验或治疗测试普遍来源于疗愈实践层面,如运用一些常规心理实验方法结合数据分析得出有效结论等,并未形成综合性、探究性的深度研究论述,仅停留在点对点的实验报告阶段。这种关于客观实验的经验分析固然可以成为艺术疗法的佐证,但显然欠缺深层意义上的原理探析,也缺乏深入研究的张力。本文则有意撇开临床实验,旨在探索以表达疗法弥补布兰肯伯格精神分裂症病理分析在实践维度的缺憾,求证表达疗法与布兰肯伯格理论在原理意义上的互补与对话关系。
一、 表达疗法与“自然自明性的失落”
表达疗法的疗愈原理与布兰肯伯格的病理分析都源于现象学理论。当然,相较而言,前者更多地来自于海德格尔的艺术论、存在主义世界观以及现象学的身体主体论。表达疗法的核心要义是强调以团体、个人、对话等各种形式及绘画、雕塑、舞蹈、音乐等多样媒介在艺术创作与表达中完成自我疗愈。溯源其哲学基底,艾伦·莱文认为,生成(希腊文poisis,或译为创造、创制)是表达疗法的奠基理念。“我清楚地认识到,生成活动不仅指艺术创作,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与其他动物物种不同,人类并非生来就能适应环境。相反,他们必须想办法对他们所处的世界做出反应,然后想办法塑造这个世界,使它成为一个适合他们生活的地方。塑造‘所给予的’就是我所说的生成。”[3]26莱文在这里将人类在世生存的基石锚定为“生成”,将存在本身视为一种“生成”活动,故而使表达疗法中的艺术创作有了不可退让的存在论根基。因而,在生存中所遭遇的苦难必将用“生存/创造”本身去解决。在治愈痛苦的过程中,艺术创作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解放的世界。在创作活动中,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联系,在创作中宣泄自己的苦痛与愁怨,并在与作品的对话中重新发现自我与重构主体,并最终达到主体间性的人际疗愈。与当前精神分裂症日益丰富的治疗实践相对应的恰是其病理学分析层面的贫瘠,因此,从病理学出发探究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原理是当前较为急切的任务。诚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言:“精神病理学本身在方法论上就显出了许多不足,因为精神医生根本无法理解精神病人的主观世界。”[4]5而布兰肯伯格所主张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提供了对精神疾病主观经验的丰富描述。在其理论框架中,精神疾病不仅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大脑机能异常,而且是在意识与经验的前维度上的紊乱。他认为:自然自明性失落,是精神分裂主观病理的核心,这也是他分析、解释以及最终朝向治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所谓“自然自明性的失落”,源自于布兰肯伯格一位叫Anne Rau的女病人:“我到底缺了什么呢? 如此细微的东西,如此奇怪的东西,如此重要的东西, 而且没有它,我就无法生活。……我缺失的就是自然自明性”[1]。对此,布兰肯伯格解释到,对于健康的人来说,那些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事情,在精神分裂症病人这里都成为了需要加倍注意和分析的事。因而,病人总会出现各种荒谬的、难以理解的行为。在《自然自明性的失落》一书中,他以胡塞尔的超越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从世界、时间性、主体、交互主体四个方面分别论述精神分裂症患者主观经验上的四种变异。这四个方面涵盖了现象学视域下人在世存在(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此在”即Dasign)的基本结构。尽管布兰肯伯格从现象学出发为精神分裂症阐发出一套极具说服力的病理分析,但缺少了治疗实践向度上的补充终究是有缺憾、甚至是不完整的。由前述可知,布兰肯伯格的精神分裂病理分析架构于现象学,而表达疗法的哲学基础同样源于现象学,由此,表达疗法的运用似乎能够为布兰肯伯格的病理分析予以补充和完善。下面将主要以表达疗法中的图画艺术为例,尝试分析表达治疗是如何裨补自然自明性的失落后的四重变异的。
二、 重整支离的生活世界
徐献军指出,自然自明性首先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每个人在做事时自然而然的思考方式、游戏规则、基础等等。但是,精神分裂症病人却丧失了天然具有的这些“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工作和学习。“正常人是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拥有了日常的自明性,并简单地生活在世界中,但在病人这里,一切都是计划的。”[1]换句话说,精神分裂症病人失去了对世界正常的认知和把控能力,陷入了一种怀疑、迷茫和错觉中。布兰肯伯格从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出发,认为日常生活行为的发生,多是 建立在“习性”的基础上。大多数的建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态度,根本无需进行反思。人们多数是靠着“联想”下的“被动综合”(即无意识地建构认识)来感知世界的。比如听到“鸣笛”而联想到“有车”,通过“咳嗽”联想到“有人”等,但精神分裂症病人却失去了这种被动综合能力。他们似乎无处不在地进行现象学的“悬隔”(Epoche),病态地怀疑一切自然和自明性。比如连洗手这样简单的事他们都会不断逼问自己:洗干净没有?要不要一直洗下去等等。因而,其作为正常人生存于世界的各种基础能力处于支离破碎之中,修复其碎片化的日常经验是走向治愈的第一步。为整合精神分裂症病人零散的世界,艺术治疗学家莱文经常援引叶芝(Yeats)的《基督降临》中的名句来形容它:“一切都分崩离析,所谓的中心,也丧失了统摄力。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5]。他认为,表达疗法的核心立场恰好就是为患者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以艺术为媒介、以个人为主体、以创伤为驱动力对患者原初世界秩序进行重新整饬和涤净。以图画艺术为例,患者可以用手中的笔构建出任何他所想要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和热爱的世界。它可以是一堆混乱的线条,也可以是一大团杂乱的色块。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认为,艺术治疗首先要从心灵世界秩序的恢复来探讨治疗的可能性。“对他(阿恩海姆)来说,艺术治疗师能够帮助病人找到一种艺术形式,这一形式正是他们混乱的内心世界中缺失的结构。因此,艺术变成了创造一种意义和秩序的方式,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能够稳定外部现实那难以控制的混乱的避难所。”[6]102再者,麦克尼夫强调,人类的个性是通过身体在世界中表达出来的。因而,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必须依靠艺术创作中的身体律动完成治疗。他认为“绘画和雕塑的动作、舞蹈的姿态和歌唱共振的音腔等等,都是呼唤身体与世界重新对话的方式,甚至是病人感觉在世的唯一方式。”[7]137-139布鲁斯·穆恩(Bruce Moon)认为,艺术治疗是从使用媒介开始,而媒介来自于现实,来自于一个创作者真正存在的世界。即“创作者借由绘画、剪贴、雕塑与媒材‘共舞’的历程,经验真实且存在。创作的过程彷佛是一种在‘出世’与‘入世’间不断过渡的旅程,其间充满着想象、隐喻与冒险,一切尽在不言中。‘不言’不代表没有发声,作品为创作者说话或与创作者对话,是两者‘共舞’后存在的永恒,也是一种存在过后的见证。”[8]11
三、 重建错乱的时间意识
布兰肯伯格认为,“与世界的关系的改变密切相关的是时间的改变,这其实是时间意识的意义建构作用的改变。”[9]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第二种变异是时间建构的错乱。布兰肯伯格援引病人的话“让我痛苦的是记忆丧失或类似的东西:很多概念突然让我感到陌生。我首先必须重新开始建立习惯。这些概念以新的面目出现,尽管如此,我不是全然遗忘了它们。只是它们令我不习惯。”[10]132显然,在病人的世界里,所有过去的一切都无法存留在自己的时间经验中。布兰肯伯格援引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论认为,内时间中的“意识之流”是人们得以认识事物的始基:在任意当下的时间刻度中,既存在着过去时间的滞留,也有着未来时间的前摄,而内时间意识中的前摄和滞留无法进入患者的经验。[1]通俗一点说,未来以过去为参考并承载着过去;未来与过去在当下时刻汇聚,三者如绵绵流水一般连续不断。而病人因病丧失了对过去时间和未来时间的感知,因而也意味着失去了当下。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日常生活本就千篇一律、习以为常。但病人发生了时间上的紊乱,他们就会总是不断地“重新”生活,这就意味着失去了正常的时间意识。
生活经验的错乱本质上是时间意识的模糊。从人类治疗方式的发展史来看,能够凝聚时间的方式有很多种,艺术恰好是最值得推崇的一种。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艺术的慰藉》一书中列举了艺术的七项功能,第一项便是——记忆。他认为:“我们终将遗忘泰姬玛哈陵、遗忘乡间的漫步,更重要的是,也终不免遗忘那个七岁九个月大的孩子坐在客厅地毯上用高积木搭建房屋的模样。”[11]9尽管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艺术实践并没有德波顿所描绘的如此浪漫和温馨,他们的遗忘是病态性或强迫性的遗忘,而艺术治疗需要做的,正是通过艺术的技艺、保存和对话功能重新接续起病人已经断裂的时间之流。表达疗法强调,病人的作品是个体生命体验的保存和滞留,实际上是用艺术作品来替代“时间意识”以储存过去经验和表达未来规划。 表达治疗师芭芭拉·加宁(Babara Ganim)希望病人能够将图画视为一位熟知自己的老朋友,它能够帮助患者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了解自己内心的欲求。她认为:“当一位旧日好友向我们倾诉逝去的时光、学习到的经验以及所有共同的记忆时,我们会感到一种亲切的温柔。当我们向这位朋友征求建议时,我们知道他的建议会非常友善,并且会将我们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而这也正是我们与自己的图画交谈时发生的事情,它们会给予我们建议,并诉说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我们的图画正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它们的言语既亲密又充满了智慧。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会让我们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取得联系,帮助我们重新发现真实的自我。”[12]89
艺术治疗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接连起精神分裂症患者支离破碎的时间流,真正能够以与作品对话的方式重新建立起时间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也就像保罗·克尼尔(Paolo J.Knill)总结的那样,创作是一个能有效记录日常经验的活动,这并不只是因为它可以克服时间和过程,成为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作品可以保留创作生活中反复无常的特质。[6]“就好像是生存于这世上,创作的象征性生存可以记录生活的变迁,使其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13]65而这所谓的基础,正是来源于日常时间经验的平滑与顺遂,从而使得生活得以寻常而正常。
四、 重构分裂的自我主体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第三种变异是自我建构的挑战。自然自明性的失落,与病人本身丧失自我建构能力有关。布兰肯伯格在著作中如是记录:“他人都有自明性。我没有。他人的行动可以就是这样的……他人有整个人格作依靠。我却没有。我不能……我没有依靠。只要我的身体有力气……我就如此地折磨自己。”[10]139迷失自我的病人无法确认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也无法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甚至每天都会陷入“我是谁”的疑问之中。因此,有时病人会表现得宛如一个婴儿,失去了亲人的照料就无法生存。而自立性和自明性的关系是互为建构的,“自明性缺乏会导致自立缺乏与自我虚弱,而自明性的健康发育可以产生自立与自强。”[1]在胡塞尔看来,超越性的自我,即自我的构想和目标,是原初的、第一性的;而现存的、经验的自我是此生的、第二性的。[1]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自我形象,显然是超越自我的阙如。病人丧失的是根基性的在世的依靠,任何外部的援助和支持都无法长久地保证他们的自立和自明。
主张表达疗法的艺术治疗学家和布兰肯伯格一样,对“自我”这一概念极为重视。娜塔莉·罗杰斯指出:“治疗的目标是全面的、自我实现的,因此艺术最有可能凸显其必要性,因为艺术能够表达自我的全面性。”[14]6从某种程度来说,治疗师也将患者主体的分裂和无助感视为疾病的主要根源。在《表达性艺术治疗理论与实务》一书中,作者总结到:“通常的个案会进入治疗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失序,陷入分离的经验常刺激人们去寻求协助。自我的不完整感是极度痛苦的;使人失去意义和目的感,以及经常经历着无助感。”[13]44显然,治疗师已经意识到通过艺术重建主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道格拉斯·吉尔伯特(Douglas Gilbert)则更为直接:“图画是灵魂天生的语言,在我们发掘自身独特性的过程中,将会找到通往内心非凡智慧的入口。”[12]169布鲁斯·穆恩也认为,表达疗法重建主体奠基于一个简单的原理:即作品是主体的存在之镜。[8]表达疗法所坚持的,就是要在对作品的创作、体悟和阐发中发现自己内心世界真实的自己,或是从破碎和残损的形象中重构活生生的自我形象。娜塔莉·罗杰斯从其父卡尔·罗杰斯“患者中心”的观点出发,强调了“患者—作品—治疗师”的三维中心。三者之间处于良性的交融互渗之中,创作作品取代了言语,在解释、记忆和回想中又肯定了语言的作用。最终达到将主体重新置于“自我—作品—他者”的三重场域之中。在患者进入这一场域后,语言、艺术、他者在反复质询、领悟且建构着主体。因而,患者能够得以在与图像构建的特殊阈限中映衬自身,也能够在探索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寻觅真正的自我。
五、 重塑与他者的交互关系
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第四种变异是交互主体性的拆解甚至毁灭。“当代精神病学将这种改变称为无社会性(asociality) 和社会失能(social dysfunction), 即病人明显缺乏社会交互的兴趣、意志力或能力。”[1]布兰肯伯格则发展了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他认为交互主体性的丧失是精神病理学的核心要义。就人的本质来说,人是社会性动物。自我与他者共在于世是人不可逃脱的宿命,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在”。萨特曾经精辟地分析过他者的目光对自我产生的焦虑。“被看见使我成了对一个不是我的自由的、自由不设防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认为自己是‘奴隶’,因为我们对他人显现出来”。[15]132因他人的注视而感觉到紧张、焦虑、束缚和由此产生的抗拒、愤怒和懊恼是精神分裂症病人常见的病症。布兰肯伯格认为,由于病人自身自然自明性的失落,当他们目睹他者能够自然地生存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时,他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怀疑和失落,进而会不断地自责并对自己大加挞伐,即所谓“自然自明性的丧失,不仅与他人相关,而且与共在世界相关,因为自然自明性就是在共在世界中、被他人一起建构出来的。”[10]207
不仅如此,病人丧失了自然自明性,意味着人类共通感(common sense)的缺席。共通感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论述颇多的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共通感被认为是人类一同建构感官世界的基石;而康德从他无功利、无目的、无概念的审美观出发,认为共通感是人们获得普遍审美趣味的根本能力。在康德看来,共通感是保证人们共情能力的基础,只有拥有共通感,人们才能将自己的感情转移到他者的视角上,以此达到共享和交流。[16]“但缺乏共通感的病人就无法进行这种置换,或只能有意识地、徒劳无功地进行置换(结果导致了精神分裂性衰弱),因此他们日复一日地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中。”[1]病人要么对他者的感情表示不解,力图与对方站在一起却最终失败,要么直接选择孤立自己,撤退到自己的世界中。于是就会在“走进”和“走出”个人世界的摇摆中苦痛不堪。而共通感在审美领域的核心作用显然意味着其在个体世界的重建会隐隐指向艺术。
团体治疗一直是心理治疗中长盛不衰的治疗方式。这种方式在疗愈患者对他人关系认知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麦克尼夫创造性地在表达疗法中使用了团体创作。他坚持打造一个“团体创作”工作室,希望患者能够在表达疗法的工作室中通过相互激发、相互协作、相互阐释、相互评价等方式增进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创作的相互激荡中牵引出彼此真实的样子,也能够在和谐安宁的环境中寻找安全感和团体感。麦克尼夫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由一起工作的人们共同建立起来的,他们相互关爱,并对彼此的工作作出阐发,所以群体环境决定治疗质量。”[7]他总结道,许多艺术家(实指患者)参与我的工作室是为了体验一种团体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患者可以大胆地放下熟悉的表达方式,如语言诉说或是躁动发狂等等,而能够把自己的艺术带到新的、或许是更具挑战性的地方。[7]“此时,他们会发现,其他人会陪伴他们的旅程,而不会诋毁他们的表达方式,并能够在患者质疑和失落甚至毁灭的时候坚定地支持他们。”[7]在表达疗法的支持下,患者所创作的一切作品都可以得到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式的支持和理解。他们创造、他们交谈,直到他们得到治疗。
综上所述,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研究在理论上是对生物学病理分析的一次改进和反拨,他舒张了精神分裂病理的主观病因的分析范围,重新为病人打开了一个名唤“存在”的主体与世界,再次将“人生在世”的基本命题放置在精神病理学的面前。这不得不说是以布兰肯伯格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巨大贡献。但是,主观经验的病因如果仅仅依靠生物学和物理学角度的缓释与治疗,显然与病理分析有着巨大的、不可弥合的错位,也会为其病理分析招来质疑。而为了弥补布兰肯伯格理论的缺憾,从表达疗法的基本原理出发对 “自然自明性的失落”所带来的四种变异进行深入分析和逐步“修补”,即可尝试为从病理分析到临床实践的治疗模式提供理论依据。罗伯特·索尔索(Robert L.Solso)在分析艺术与治疗精神疾病的关系时认为,“为了避免沉溺于神经科学、轴突、血流以及有意识大脑进化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必须谨记:艺术,所有类型的艺术,都是一个人生命中最为高贵的表达。艺术能够点亮心灵,沟通彼此,发人深省,亦能唤起人类的所有情感。艺术之为艺术正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去追求它、享受它、理解它。”[17]1实际上,中国艺术理论中历来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表达方法,也有“发愤著诗”“不平则鸣”的疗愈理念;而表达疗法作为当今欧美最为流行的艺术治疗方法,在重新构建“自然自明性”的疑难问题上有着极为优越的治疗效果,遗憾的是,国内学术界既没能重视布兰肯伯格的病理分析理论,也未能对表达疗法进行广泛研究,更没有涉及到如何从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建构艺术治疗中国理论的视角出发对表达疗法进行深入挖掘。诚然,艺术治疗沿着本土化和中国化相结合的路径前行并取得长足发展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