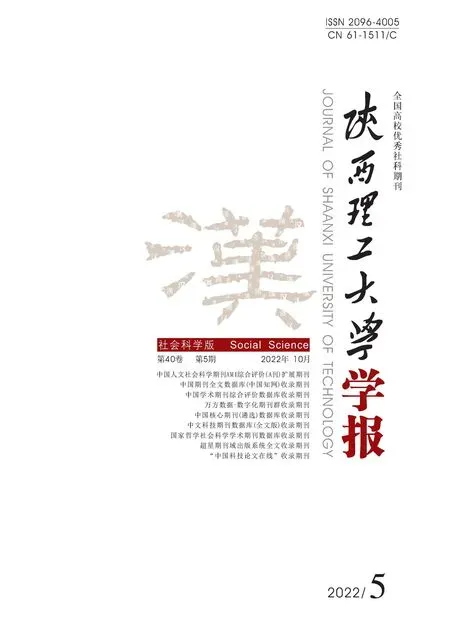感物思维:《文心雕龙》的文思发生论
刘 欣, 梁 明
(1.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交通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7)
刘勰的“感物”说历来颇受研究者关注。学界或挖掘其理论渊源,或分析其概念内涵,或阐发其思想影响,取得了丰富成果。详细审之,人们普遍将“感物”作为揭示文艺整体性的美学范畴,强调文艺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统一的理论意义。这是对“感物”内涵的泛化理解。而刘勰的“感物”论基本上是从文艺活动开启阶段的思维体验出发的,他系统回答了文思发生时心物何以感应、物我如何感应、感物之思如何导向文艺创作的问题,概括了文思发生的完整环节。本文力图从文思发生论的视角入手,分析刘勰“感物”范畴的美学内涵和意义。
一、 切身之“物”与摇荡之“心”
“物”与“心”是感物的基本要素。心物何以发生感应,怎样的心物才能发生感应,这在早期的《乐记》“物感”说那里没有明确说明,“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1527是心物感应关系的描述,而未对心物内涵作出阐释。至班固以“感物造耑”释“登高能赋”之言,隐含着心物的意向性内涵。曹丕《感物赋》表达物迁兴废之叹,陆机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揭示感物中的心物关系,“物”的切身意义与“心”的情感性内涵更加具体、丰富。刘勰从汉末魏晋以来文艺美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心物的诗学内涵与审美意蕴。
1.“物”:鲜活的生命与现实的生活
“物”的感发意义来自于其切身性,即与人之生存体验的内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正是主客体达成审美契合的关节,刘勰注意在切身性意义上阐释“物”的内涵。“物”分别在生命本体同构性的生命化、生活现实亲近性的审美化中达到了意义深化。刘勰以物色论阐释自然物的“感物”意义,从生命本体的同构性视野强调自然物之生命内涵。
传统的自然审美建立在美善合一的观念逻辑之上,自然与人构成伦理主导型同构关系。儒家“比德”观是典型的伦理同构,孔子见水必观、以玉比德、以松柏后凋比附君子品性,以物的特征比附人的道德,自然物被赋予伦理内涵,成为道德理性的寄托。道家则强调一种自然伦理同构。“无以人灭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老庄看来,人是万物的一部分,强调顺天应命,不是以人的价值理性去建构“物”,而是努力消解人的功利欲求,以物的存在规律实现人向自然的复归。无论以社会价值还是以自然规律为主导,物与人都是一种伦理性同构关系,在美善合一的文化观念中,善的内涵大于美的价值,甚至很大程度上显现为以善为美的伦理美学意义。
魏晋以来,自然物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不再是伦理价值的比附对象,而是具有独立美的价值的生命体。人们自觉以审美的目光亲近自然,美善结合的伦理性诉求转化为优游畅神的情意性审美追寻,“比德”承担的自然审美意义,被生命沟通形成的情致化审美内涵所代替。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2]215山水与深情的交汇是在生命同构的亲和性意义上的交通融合。正是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亲缘意识基础上,“物”的审美意义获得极大解放,成为具有丰富生命灵气的亲缘对象。“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3]48鸟兽亲人,山川自映,云行雨施,鸢飞鱼跃,人们在自然事物身上,发现了与人一样生命化的意义,自然风物在这里具有了灵动鲜活的生命情调和美学韵致。刘勰从这样的审美视野出发对自然物的感发意义作了理论阐发。“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物”的文思感召力正来自于这“与人共舞”的生命同构: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4]493
四时更替带来物象的荣枯生息和人心的感荡起伏。刘勰从四序轮回的自然气感出发揭示物与人共同的生命类属关系,为论证基于生命同构的审美感兴提供了依据。作为受感对象的自然物,在四时更替的主宰下成为凝缩了律动的生命意蕴的“活”的生命景观。这种鲜活的生命气息,给人带来特别的亲近感,物因而具有了特别动人的感召力、感染力。“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霰雪无垠”,四序纷回与物象景观的互文组合,强调了物“与时偕行”的生命化意义;与之相应,“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沉之志”“矜肃之虑”,强调了物的生命化在审美感兴意义上给人的心理激发。这样,在“物”的现实化、具体化概括中,刘勰通过确认感物对象与人通灵的生命体意义,赋予了“物”强大的切身的审美感召力。
刘勰的“物”也包括现实生活内涵,他从具体生活的亲近性角度,强调社会事物丰富的审美化内涵。
汉儒“物感”论的鲜明特征是强调社会政治感发意义,从政治功能取向上界定文艺价值,要求以寓教于乐的感动性实现以诗牧民的政教功用。“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1]1528《乐记》的价值定调指定了“物”指向现实政治的理解方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5]63《诗大序》明确把“物”代表的政治伦理内涵表达出来。可以说,汉儒之“物”基本上限于服务政教的内容,即便至班固明确道出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世俗感发意义,也还约束在“观风俗,知厚薄”的政治功用价值之内。
魏晋以来,随着多元思想的汇流,多彩的现实生活成为文艺活动重要的感召因缘,战乱与民生、生死与时空、出处与游宴、亲情与友谊等切近日常生活的内容成为文思的重要感发源。这种生活所见、所触的切身事物,既构成了作家生存、情感生成的现实语境,同时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又具有着激发作家心绪的感发意义。这种切身的生活,密切关联着人也深刻影响着人,因而具有特别的审美感染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文思论意义上正是对现实之“物”时空独特性的宏观强调。文思的发生注定受到具体时代和社会风情的影响、受到一定时空生态中现实的社会生活的感发。刘勰在《辨骚》篇肯定“情怨”“离居”等现实问题的感物意义;在《明诗》中强调建安诗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感发内容,都是对社会生活事物之文思感召力的充分肯定。可以说,刘勰释“物”,在群体性功利价值导向之外,展开了个体性日常生活内涵的拓展,从生活现实的亲近性角度建构了社会事物与诗人个体在情感上的亲密联系,强化了“物”的文思感召力和感染力。在这个向度上与刘勰形成巧妙配合的是稍后的钟嵘,他像刘勰物色论一样,完整建构了社会生活事物的诗意感召图谱:“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6]20-21钟嵘补充了刘勰发而未尽的内容,也更明确了社会生活事物“感荡心灵”的文思感发价值。
2.“心”:能动的个体与审美的主体
刘勰的理论阐发丰富了“物”的生命意蕴、生活韵致,实际上对“物”新的理解正得益于主体新视角的拓展,得益于感物主体能动性、审美性的提升,成为摇荡着审美情思的感动之心。
《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强调心灵的感动是“物”的感应决定的。这种以物为主的心物关系逻辑,在强调“物”的价值的同时,压抑了人心的感应主体性。同时,在汉儒诗教伦理主导下,心物感应基于表现公共理性、政治教化的内容,虽提出了“情动于中”“吟咏情性”的主张但受束于讽喻教化的观念逻辑之内,个体人心感应的能动性与感性空间非常有限。
魏晋以来,人的主体价值和感性情意被重新发现,能动、个体的审美旨趣得到重视。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对作家个体的气质个性、禀赋才能予以强调。王弼指出圣人以喜怒哀乐的情感以应物,但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在感应中保持着自由性、独立性。殷浩喊出“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口号,对个体自我的独立意义予以肯定。在自我意识、主体性觉醒基础上,人不再是应感而动的被动受体,而是能够自主对待感物对象、自觉导引感物取向的能动主体。陆机曰:“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7]169现实中平常的物象,在作者强烈怀土心绪下无不沾灌了浓重的乡愁气息,具有触动和深化作者思乡情怀的感动意义,主体能动性在此得到了根本提升。刘勰对此颇有论述,“物以情观”“依情待实”“情往似赠”等都强调了人的审美能动性。同时,主体能动性还表现为对于对象的自主选择,体现出感应中的个体性、独特性。刘勰提出“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4]518,不同审美主体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有选择地对接感应对象,在心物关系意义上揭示了感物思维中“心”的个体性与独特性。
审美性内涵的提升是刘勰心物感应中主体发展的又一表现。情感深沉化、纯粹化是主体审美感应自觉追求的动力。魏晋以来,人们对深沉情感有了自觉的意识。桓伊闻清歌而呼奈何,谢安谓之“一往有深情”;王戎丧子哀痛,自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里对于深情的执着已走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约束,感性化的生活情趣、审美感情成为占据人们心灵的主导意绪。以情意为本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的响亮口号。刘勰“为情而造文”“文质本乎性情”“以情志为神明”等论断,鲜明地强调了文艺的情意本体性,强化了主体在文艺中的重要地位和情感在创作中的核心作用。感物之“情”的审美性内涵得到突出强调。刘勰提出“人秉七情,应物斯感”,表明情感在感物思维中的基础性意义,这里情感已获得了纯粹化的审美内涵。在传统认识中“情”的内涵比较复杂,人们把情作为需要约束和修整的对象。《礼记·礼运》将“人情”比作“圣王之田”,要求“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1]1426《乐记》指出“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强调“以道制欲”[1]1536。魏晋以来的情感论摈除了以往“人情”论中驳杂趋恶的内涵,发展为较为纯粹的审美情感。刘勰的“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言说的,“七情”在刘勰那里已被“作为一个褒义的、具有鲜活的生命本质的内容加以继承下来”。[8]195纯粹化巩固了情感在审美感应中的基础性地位,剥离了庸俗情绪对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作家以情观物,为深入的审美感兴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 双边互动与交流会通
感物思维开启之际,心物是如何感应的?对此刘勰有过许多精彩论述:
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4]81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4]493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4]494
刘勰上述论说一直是人们广泛关注的课题,其心物交融的理论逻辑存在两种主要阐释路径。刘永济从“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逻辑思路出发,把心物交融分别为“物来动情”与“情往感物”两种形态,并指出“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景交融,物我双会之际矣。”[9]161王元化以“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为切入,从创作论角度指出二者存在着物我对峙情况,认为文学创作要统一这二者矛盾,“以物我对峙为起点,以物我交融为结束。……‘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可以说是这种物我交融、和谐默契的最高境界。”[10]60可以发现,二人的切入点分别是心物的交流互感与心物的独立价值,但前者同时也不忘关切心物的分别作用,后者也最终落脚于心物的互动会通。其实,心物感应的完整模式正是两种心物关系同时并在、同步运行的整体过程。一方面是心物的相对价值和协同作用,一方面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与融会交流,心与物在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感通的作用中,才能够形成互动往来的有效对话,激发意趣盎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冲动。
这种感应交流的感物模式,根本上说是感物思维本原性内涵的复归和审美逻辑的提升。“感”从本来意义上是一个标称交互关系的范畴。《周易》“咸”卦“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1]46刚柔相济,二气谐和,天地氤氲,感应双方相反相成、交融共生,以此为根据实现化生万物、感通天下的现实功能。这里,刚柔、阴阳、天地等对应范畴之间,具有鲜明的不同风格特征,同时对应范畴的边界又是模糊的,相互之间相对待而存在,并在相对意义上流动感通、化育生生。这种感应关系,在刘勰的心物关系论中得到落实,并进一步发展为赠答交流的感物思维模式。一方面是“物”的感召力量在生命化、生活化方向上向人靠近,“物”成为人的生命生活中休戚相连的感动源泉;一方面是“心”的审美感动性在能动化、纯粹化向度上提升,人成为去除了世俗功利的能动的感性主体:心物在全新的状态中相遇,物我的边界进一步拉近、打通;相互的感应关系进一步加强、深化,形成合作与对话。在这里“心与物并非是谁决定谁的‘线型’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赠答式的‘立体交叉型’的双边关系。”[12]232这种“双边”关系,意味着物我双方的通力作用和交流对话。
“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揭示了物我双方在“双边”感应的中的合作关系。“合作”意味着参与者双方各自在感应中担当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双方各以自身独特的功能贡献于感应活动,形成协同作用的“合力”。这里的“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其实并不是王元化理解的“一方面要求以物为主,以心服从于物;另一方面又要求以心为主,用心去驾驭物”[10]59强调物我的对峙对立,而是强调物我在感应中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和各自独特的作用发挥,强调双方的通力合作。感物从来不是“物”或“心”的单方面活动,而是物我双方的一种关系范畴。这种关系首先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作用基础上的张力平衡。这种合作性心物关系,历史上也不乏论证。明代谢榛曰:“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13]69清人刘熙载曰:“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14]98情景内外的合作是成就诗赋创作的关键,情感与景物在感应中各自发挥功能,相互成就彼此,在相摩相荡中协同作用,形成通力合作又互动往来的“双边”感应关系。
“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主要揭示了感应双方对话地位的平等性、作用发挥的协同性;“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则主要阐发了物与我“双边”对话的展开机理与运作逻辑。
“情以物兴”标志的是“物来动情”的感应向度和对话路程。传统“物感说”特别强调这种物使心动的感应逻辑。《说文》曰“感,动人心也”,强调感“动人心”的体验性和物感心动的思维逻辑。《乐记》的“感于物而动”“物使之然”,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都遵循了这种“事物诱发—人心感动”的思维形式。萧子显曰:“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15]259物态极妍,江山多娇,多魅的物色成为文思丰富有力的感召源,使人感思连连、不能自已。刘勰的“情以物兴”正是在这个思维向度言说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是“情以物兴”思维向度的整体概括。刘勰强调“七情”是人之应物生感的心理前提,在此基础上应物而动,与物相应的情感类型凸显出来,成为兴发感思的主导性情感,推进人的审美运思不断向前。刘勰强调“物”在生命化、生活化上与人亲近的意义,这种亲近正在于以有力的审美感召促成“物使心动”的思维路向的达成。“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刘勰在一段之中反复讨论这一思维逻辑,突出了物色的动人魅力和物感生思的现实合理性。
“物以情观”标志的是“情往感物”的运思向度和对话路向。这是刘勰对感物思维向度的开拓与补充。“‘物以情观’,乃通过自己之感情以观物,物亦蒙上观者之感情,物因而感情化,以进入于作者的性情之中。”[16]191这种“物以情观”的情性化感应向度,也就是陆机的“方思之殷,何物不感”的运思逻辑。这里,事物的存在及其显现特征是客观的,而观者的情感作为先在的因素主导着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在强烈的主观情感的影响下,观者不自觉地选取合于主观情感的物象,强化对事物表现人的当下心理状态的特征的印象。这样,如果按照刘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概括逻辑,此处“物以情观”的进一步阐释当是:“物有多姿,应情而彰”。这种“情往感物”的运思路径不乏阐释者。萧绎曰:“捣衣清而彻,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于心,捣衣感于外,内外相感,愁情结悲,然后哀怨生焉。苟无感,何嗟何怨也?”[17]827此言秋士之悲感,生于以悲心观物。旧题王昌龄《诗格》曰:“感兴势者,人心至感,必有应说,物色万象,爽然有如感会。……如常建诗云:‘冷冷七弦遍,万木澄幽音。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又王维《哭殷四诗》云:‘泱莽寒郊外,萧条闻哭声。愁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18]156感兴揭示的是主体以主观情感看待客观景物,景物之存在因观者情感的状态而不同,这些都是在“物以情观”思维向度上的丰富拓展。
可以说,感物思维是一种双向感应的对话思维,它不是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也不是主客相抗的对立关系,而是在区别着内外你我的基础上,解放着主体的创造活力和对象的现实生命意义、生活情趣;物我之间形成交流对话的感应状态,并提升为一种审美化的境界。这才是感物思维的完整逻辑。
三、 “触兴致情”与“联类不穷”
心物感应何以导向文艺创作?这要从感物作为文思之开启的阶段性思维体验说起。它是感物思维的成果与结点,也是开启进一步文思活动的动力和基础,具有发生和过渡的双重属质。刘勰的感物思维体验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触兴致情”,揭示了作家运思中情致盎然、思意深沉的兴感体验;一是“联类不穷”,揭示了心物感应中触类感思、情象融会的运思体验。
1.触兴致情
心物往还的感物运思,带来审美情感的兴发和深化,刘勰以“触兴致情”“兴情”概括这一思维体验。首先是情感的生发、生成。“兴者,起也。”动词意义上的“兴”继承了诗学范畴之“兴”的发生之义。朱自清在探究《毛传》所标“兴也”之句时指出:“《毛传》‘兴也’的‘兴’有两个意义,一是发端,一是譬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块儿才是兴。”[19]42-43这一概括,阐发了《毛传》之“兴”的深刻内蕴,但这里“兴”的“发端”“譬喻”之意,主要还停留在汉儒“讽谏”意义上。东汉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提出“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晋挚虞提出:“兴者,有感之辞也。”“兴”的内涵在审美感物、触感兴发意义上进一步拓展。以此为契机,刘勰强调了“兴”的“起情”意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4]394虽然刘勰这段论述还是带有很强的儒家政治伦理意味,但他明确提出了兴之所起旨在致情的观点。特别是在与“比”之“附理”内涵相比较意义上,“兴”的情感发生性内涵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
刘勰《诠赋》对“兴”的审美情感兴发意义有更明确的阐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触兴致情,因变取会。”强调赋文创作要以情为本,而且情感的生成要避免空疏、有所依凭,揭示了感物运思的情感发生内涵。萧统提出“触兴”“睹物兴情”的观点,与刘勰形成了默契的呼应:“炎凉始贸,触兴自高,睹物兴情,更向篇什。”[20]330“触兴致情”“睹物兴情”,情之所起当由睹物触物而兴,这一方面强调了感物生情的运思逻辑意义,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所兴之“情”摆脱了“止乎礼义”的功利把控,具有较为“纯粹”的感动意义。这种比较纯粹意义上的感动性,是伴随感物运思生成的意致盎然的兴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兴”没有停留在情感发生的动词性内涵表述上,而是作为具有深刻内涵的独立概念,鲜明地强调了审美情感生成的现实体验性,对“情”的意蕴作出重要界定和补充。
首先,“兴”的一个突出的理论要义就是强调感应中强烈的情感状态和审美冲动,这是一种审美热情激活状态下的感动性运思体验。刘勰强调“触兴致情”。詹锳指出:“‘致’引起。‘触兴致情’谓触物起兴而动情。”[21]289“触”是触景触物,“致情”是引发与导向情感。从逻辑上看,“起兴”当由“触物”而致,“起兴”而又致于“动情”,但“兴”在这里不是一个由物到情的转换中介,而是主体在“物”的感召下,外接于物,内感于心,主客内外往来感通过程中引动兴致盎然、触动无限的感物思维体验。如果说,文学创作情感是日常情感状态的升华,那么这升华的过程及其所燃起的进一步审美运思的热情和冲动,就是“兴”的体验性内涵。这一点不乏论据,如谢灵运自谓“事由于外,兴不自已”;旧题王昌龄《诗格》提出“兴发意生,精神顿爽”;旧题贾岛《二南密旨》曰:“感物曰兴”,又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18]372可见,“兴”之感思带来“情不可遏”的强烈情感体验和审美动力。
其次,刘勰以“兴”论“起情”的感思体验,还从理论的高度揭示了“感”的诗意蕴蓄给创作情思赋予的深沉内涵、蕴藉品格。如前所述,触兴致情,“情”已具有较为“纯粹”的感动意义,它不是庸常的俗情,也不是没有来由的情绪,而是经过了充分的意趣酝酿,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内涵包蕴的审美情感。这是“兴”之蕴藉的结果,通过兴感作用情感更加含蓄而充实。刘勰提出“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唐孔颖达提出“比显而兴隐”,都强调了“兴”蕴于情的寄托性内涵。清叶燮说:“原夫作诗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22]5缘物起兴,触感兴意,经过“兴”的兴发感动和感思蕴藉,情与物在这里开始化合蕴蓄,现实的诉求开始内化为深层的情感意蕴,这为情感在进一步运思中的深化,并最终酝酿成真切丰盈、含蓄隽永的文学情意奠定了基础。这是“兴”的“发端”“譬喻”内涵在感物思维中融会化合的结果。“兴情”把深沉的思想和隐婉的品格“感”到“情”里面去,是为发生阶段运思体验的显在特征和重要标志。
2.联类不穷
审美情感的酝酿不仅在于自身体验的丰满和深化,还在于作家与物相接过程中,伴随情感的深入而自觉展开对“物”的感知体验和内化沉思。这既是一个情感的对象化过程,也是一个物象的感知升华过程。“联类不穷”揭示了文思发生阶段这种诗人触物动思、感思运象的思维体验。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4]493
这段阐述在《物色》篇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这种起承所关联的运思体验,决定了其表述内涵在前后两种意义指向中的徘徊与游移,既是对上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一段的总结升华,强调了物色动人、令人流连不已的感思体验,也是开启后面意象创构和情貌书写的转换中介,强调了作者由现实物色的感召而进入情象融会深切体验。因此对这句话的理解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展开。
在物象感思的层次上,“联类不穷”概括了“诗人”在感应中体验到现实物象的丰富、鲜活,以“类同”的视角和身份与现实外物感应交流,获得深切的认同与感动。“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人们在耳目所见的纷纭万象之中流连忘返、运思吟味。这是对上文“物色之动,心亦摇焉”丰富内容的总结。“联类”在这个意义上是“以类连物”。“这是一个充满召唤、感发和吸引力的大千世界,既然人是这个世界的物质存在,他不可能保持‘安’的状态,避开大千事物的摩肩接踵。因此,在作家周围的环境和他的‘情’之间有一种有机联系。”[23]290这种“有机联系”就是人与外物的共同类属关系,人是世间万物的一份子,人在欣赏和感受自然时,他与外物的关系不是“主客关系”,“他‘徘徊’在事物周围”“参与自然中的事物”[23]292。这样,人不仅是大千世界纷纭物色的客观观察者,同时也是现实万象荣枯生息的切身参与者、体验者。郑毓瑜分析了“感物”的类应机制,认为“‘引喻’‘譬类’或‘应感’,其实原来涵括于一个共识性的世界观、宇宙观,‘时—事(物)’‘物—我’之间必然存在于早经认可熟悉,同时处于‘类应’(类固相召,气同则合)以‘穿通’的互联状态中。”“‘联类’……是指类别间的不断系连。”[24]173也就是说,物我之感应系连建立在人的观念世界中的类属认同基础上,物与人的“联类”需要在感应时放弃次级的“跨界”分别,而在更根本意义上寻求类属关系的统一性,建立“有机联系”。在这个层次上,“联类不穷”就是要在“以类连物”的切身投入中感受现实物象的丰富、生动,在与物休戚、生生与共的生命共振中流连不尽、感动不已。
在情象融会的层面上,“联类不穷”揭示了诗人由物象触发转入深层的心象活动,诗人开始从与外物的现实关联进入到无限遐思的内化运思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的“万象”“视听”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实指现实的外物外境,而开始内化为诗人精神化的对象。作为内观启动之际的观游,这是一种较浅程度的精神活动。张节末说:“‘物感’或‘触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极为重要的感性经验,它并不表现为繁复的想象,而是十分简捷的联想和感悟……”[25]这种简捷的联想感悟,在直接的运思体验上是诗兴情韵和精神观游的结合。这是文思运构中的一大进步,此时诗人的精神倾注不再是对现实物象的感知体认,而是初步展开内心视象的择取和处理。“这里的‘诗人’似乎把自己交出了,交给那个普遍过程,他既随物而动,又‘写’物。”[23]291这个“普遍过程”就是文思运作和文学创作的整体过程,而此处诗人联想感悟、心象处理无疑是开启“写物”之旅的门径。“写物”之“写”,不是对物象的写实刻画,而恰在于对心物融合的意象的抒写。意象创构和抒写的起点,就在于这感物思维阶段的心象情思的调取加工、内在情物的凝铸融合。周振甫说:“感物虽然是从景物引起的感触,是跟景物有联系的,但‘联类不穷’,即引起的感触是不穷的,这个‘不穷’,正是从‘情有余’里来的。”又说:“‘联类不穷’,指联系物类、情思无穷,‘不穷’指情思说。”[26]这一阐释强调了情感在心象处理中的根本意义。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周振甫分析“灼灼状桃花之鲜”指出:“《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灼灼’不仅形容桃花的红,还有红艳如火的意味,用来衬托新嫁娘青春的光艳,所以‘灼灼’既形容桃花,又反映了诗人的感情。”[26]强调诗人写桃花之灼灼正是由现实的桃花物象所触动,以类感物,同时将丰富的内心情感倾注到所抒写的对象之中,开启了情象融会的意象创构之门。在这个层次上,“联类不穷”就是在触物生感中将运思视角转向内心,在脑海中展开无限遐想,将跃动的心象和深切的情感熔铸为一的思维体验。
情感激发,内涵蕴蓄,物象类感,情象融会,是文艺运思发生阶段收获的丰赡美妙的思维体验。在动态整体的文思活动中,这丰赡美妙的运思体验,恰成为作家踏入进一步思维运构的进阶。一方面,审美创造情感的兴起和内涵深化,提供了作家思想开展的内在动力,激发着作家的灵感和创作冲动,导引着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物象的感思与情象的融会,为情感的“对象化”提供了着陆之基,推动着心象的进一步加工深化,为进入“神与物游”的想象性思维境界,形成“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深度思维运作,并最终为生产出情孕意成的丰满意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