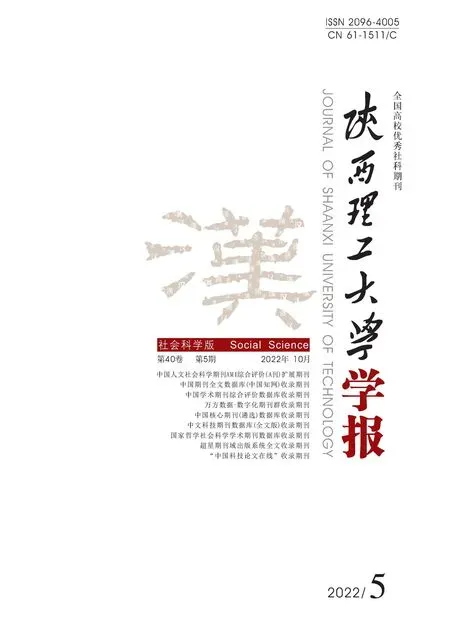论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母亲形象
任 竹 良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2.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 安徽 阜阳236037)
王安忆凭借多变的风格、多样的题材、出色的语言表现力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之一。她初期创作的雯雯系列作品侧重抒写个人经验,以《小鲍庄》为标志,她开始从文化层面进行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作品为代表,王安忆开始探索人性和人的生命本相。20世纪90年代以后,她的创作主要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及在左翼叙事中对革命、政治与人的存在的重新思考。而她最为人所关注、产生影响最大的是她对上海的书写,《长恨歌》在书写王琦瑶“锦绣烟尘”式传奇人生的过程中呈现特色鲜明的上海城市文化,《考工记》则通过审视人、老宅与城市的命运关系来演绎低回慢转的上海别传,她也因此常常被认为是当代文坛海派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但实际上,“王安忆是一个很难归于某种思潮或流派,却不断稳健地实现自我突破的作家”[1]131。
王安忆的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最先发表于《收获》杂志2020年第5期,2021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以厨艺为引延续《天香》《考工记》的“物事”书写,在饮食生活的讲述中铺陈出淮扬名厨陈诚跨越两国多地的漂泊经历和烟火人生,同时创新性地塑造了一个独特的“缺席又在场”的母亲形象。这位母亲由特殊历史时期的“反革命”到拨乱反正后的“烈士”的命运变迁,本身就耐人寻味,而她对儿女的现实人生产生持久而复杂的影响,映照出时代更替的轨迹里“日常”与“历史”的关联与疏离。“《一把刀,千个字》不仅延伸王安忆左翼叙事辩证,也代表她近年借小说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最新尝试。”[2]60王安忆独具匠心的叙述使得这个母亲的形象别具意味,呈现出意蕴丰富的艺术张力,可谓是历史纵深里独特的“这一个”。
一、 从文本存在到人物设置:缺席又在场
在小说文本中,王安忆用一明一暗的双重叙事模式来书写母亲这一形象。明写陈诚的成长经历,十分详细地展示他的迁徙之路:从七岁时上海虹口的弄堂开始,到长江边的扬州、高邮,再到上海,最后定居美国。他也从一个寄人篱下的无知幼儿成长为名厨,在陈诚看似成功的背后似乎隐藏着巨大的人生秘密。显然,从叙事明线来看,母亲是缺席的。幼年陈诚对母亲的印象模糊。最开始他以为带他出走的母亲的女同学是母亲。在上海弄堂里,孃孃向他和小毛展示相册时,一张全家福中的陌生女人是幼年的他对母亲的最初印象。在这惊鸿一瞥之后,母亲又消失在他的生活中。在小说的上部中,母亲这一人物从始至终没有出场,只在叙述者的只言片语中侧面反映出母亲对于整个家庭的深刻影响。血亲的母亲是缺席的,一些带有“母亲”色彩的女性陆续出现在陈诚的生命中。对于陈诚来说,嬢嬢、姐姐与师师这些女性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母亲”的特质,成为了替代性的“母亲”。一生无子的嬢嬢教他识字、阅读,带他拜名师,陪他认识世界。姐姐是他幼年时期的依靠,代替父母照看他,了解他的痛苦又呵护他成长。师师是他的妻子,像母亲一样陪伴他,帮他处理一切生活上的琐事,让他感受到母亲般的温暖。三位女性的身份是不同的,但相同的是,她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失去母亲的陈诚内心的缺憾,让他感受到“母亲”般的指引和关爱,让他拥有安全感和认同感。然而,她们的替代始终是短暂的,无法取代母亲在陈诚心中的地位,母亲始终是他心中无法填补的空缺。
从暗线来讲,作为矛盾冲突的关键,母亲成为小说上部中多次铺垫但未展开叙述的人物。作品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引起读者对母亲的缺位做出各种猜想。父亲和姐姐因为母亲的两次争吵是上部中的两个高潮,不仅从侧面反映出缺位的母亲始终深刻影响着父亲和姐姐,也营造出一种紧张刺激的氛围,节奏感陡然增强,使读者对母亲这一人物的好奇心被充分激发。小说的下部,在揭示陈诚被遮蔽的身世的过程中,母亲的人生故事终于得以讲述,全家人命运变迁的缘由更由此铺陈开来。从陈诚的人生归处回头看,缺席的母亲带有一种隐喻的意味,母亲的缺席恰恰反映实际上母亲在精神上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母亲,他受形势逼迫出走,寄居上海小巷失去身份;当母亲恢复名誉后,陈诚以英雄之子的身份光荣回归却不堪这一身份带来的重负,再次逃离;远渡重洋,离开母亲身份的影响在异国他乡生活,但内心仍难以自安;因嬢嬢去世归来,最终在故地与挥之不去的故人记忆达成一种宽慰式的和解。读者能够感受到,母亲本人的故事早已结束,但在陈诚的精神世界里,母亲从未消失,母亲以这种精神在场的方式持久影响着陈诚的生活。用王安忆自己的话来讲,“文字本身就是隐喻,它的本质是事实的代码。‘母亲’,对于这个孩子就像是时代精神的转述,看不见,摸不着,说出来他也听不懂,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息息相关。”[3]9
“视角转换可以使读者避免产生审美疲劳,可以更好地揭示人物性格和社会情态”[4]31。这种叙事手法在当代小说中运用十分广泛,能使作品产生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王安忆在塑造母亲这个形象时,出色地运用了叙事视角的转换。在小说上部中,母亲的故事是用陈诚的感受讲述的,限知性叙事视角的采用使母亲这一形象充满神秘感。而在下部中讲述母亲的故事时采用了全知性叙事视角,母亲的来路与归途娓娓道来,上部中所有谜题的谜底都水落石出。但是在母亲的故事中,陈诚因年幼而没有丝毫直接参与的痕迹。小说将陈诚和母亲的故事分开叙述,使两人的世界相互独立但又以隐形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小说的文本中,更在陈诚的成长中,母亲的存在方式是独特的“缺席又在场”。
二、 从“孤勇者”到“女英雄”:自我意识的彰显与遮蔽
作品一共有十一章,正面书写母亲故事的章节只有两章,“有关母亲的描写仅集中在短短几十页里,这短短的篇幅却支撑了全书”[2]60。母亲实际上是整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父亲、姐姐和陈诚的故事都从侧面烘托出母亲的独特经历和深远影响。通过小说下部的叙述,我们可以梳理出母亲的人生脉络:母亲出生于哈市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成长,她音乐才华出众,外语水平突出,在工业大学读电气机械系,是学校“校花”级的风云人物,工作后在单位里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与因读大学从扬州来到哈市的杨帆结婚,养育一双儿女。这本是新中国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全家的命运在那场大运动中因母亲的命运变化而全部改变。充满政治热情的母亲,参加了大串联,深感社会失去了理性,“读书是不够的,她说,要到实践中去。”[5]217于是她将不支持任何一方的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墙上,标题为“人民政权和群众运动”,落款“一名中共候补党员”,并署上了真实姓名。母亲因此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最终性命不保。拨乱反正后母亲被平反,并被追认为“烈士”,她英勇无畏追求真理的英雄事迹被媒体广为宣传,也为世人称颂。特殊历史时期的“反革命”和平反之后的“女英雄”,这种矛盾统一的独特人生呈现出时间流转与历史变迁之下母亲生前身后反差的命运,更显示出历史的曲折。从“反革命”到“女英雄”,这不是《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式成长的革命叙事,母亲的生命早已终结,变化的是历史;这也不存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知识女性由个人主义“向左转”的困境与自我分裂,母亲就是真真切切无所畏惧,为真理而斗争。
(一)真理至上的“孤勇者”
母亲拥有卓越不凡的能力,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她形单影只的处境。随着她的成长,她收敛了特立独行的作风,积极融入集体,力求自身与集体达到平衡。但几番波折之后她还是选择做自己,坚定做觉醒的“孤勇者”,为追求真理至上毅然前行。即便她走入世俗的婚姻生活,生儿育女拥有了“母亲”身份,她也依然是不受束缚、奋勇向前的“革命者”。“从根本上说,‘她’从来都不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而只是天然地属于金戈铁马的社会政治生活”[6]121。身为丈夫的杨帆也被妻子对政治信仰的热情和勇气所感染:“他惊讶她的能量,不知源头在哪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精神丰盈,漫溢到自身以外,感染周围的人”[5]175。但杨帆在了解她之后也感叹“世上有一种渴望牺牲的人,就像飞蛾扑火,由着光的吸引,直向祭坛”[5]213。小说中写到她的一次长途旅行,实际上这也是她一个人大串联的经历。在天津和大学同学相聚,她针对自己所见的“疯狂”追问理性哪里去了,她选择读书,读的是《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马列著作,也就在这次谈话中她表示她的“实践”就是用行动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于是就有了她将不支持任何一方的大字报贴到了省委大院墙上的举动。在特殊历史时期她逃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她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二)被历史正名的“女英雄”
母亲用生命的代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捍卫自己的理想,最终历史为她正名,拨乱反正后她被追认为“烈士”。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都宣传她的事迹,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俨然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回望母亲的人生,读书、结婚、工作,到过东北、天津等地,在多次社会运动中,她认识到真理的价值,做出了牺牲自我、维护真理的人生选择。面对错误的历史浪潮,她能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正反衬出她的先见之明和英勇无畏。母亲不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的弱者,她不愿意迎合“疯狂”的时局,而是如同圣女贞德,据理力争,以一己之力反驳政见相悖者,竭力捍卫心目中的真理。在动乱的年代,她敢于质疑,敢于站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对立面说“不”,敢于站在风口浪尖上真实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内心的笃定让她不顾后果,用自己全部的热情拥抱真理,从未因生活和社会的阻碍而畏首畏尾,进了监狱也“死不悔改”,即使牺牲生命,也奋力向前,从不后退。这样的母亲在后世的人看来是大无畏的“女英雄”,她也因此得到无数赞誉,赢得身后名。在小说下部历时性叙事中,王安忆明白地揭示出在时间的流变中母亲的命运走向,让读者对这位母亲经历了由好奇到揭秘的心理变化,也让读者在“原来如此”的了然中品味“女英雄”的人生况味。
(三)自我意识的彰显与遮蔽
从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始,人类对自我的探索从未停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先哲都曾对“自我”进行思考和阐释。“‘认识你自己’不是自我意识提出的最终要义,自我意识的发展也在促使人类了解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个性差异,想要回答的不仅是‘我是谁?’的问题,更是‘我要成为怎样的我?’的问题。”[7]12而在男权文化下,女性被忽视的命运,注定难以拥有真正的自我。波伏娃在其著名的著作《第二性》中就论述了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丧失了自我意识的处境。因而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书写的是女性缺乏自我的悲哀。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进而书写女性对自我的体验和反思。但相较于男性,女性即使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了独立,她们在面对如何实现精神解放时仍要付出更大的勇气和力量,摆脱束缚和压力。女性完全自我的实现显得十分艰难。在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弟兄们》中,女性彼此为“弟兄们”,但却是姐妹关系,老大被传统观念裹挟,她试图通过不生孩子来摆脱社会给她带来的束缚,但最终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向生活妥协。老大这样的母亲本质上尚不拥有强大的自我,当人格的自我追寻和社会现实产生矛盾得不到任何支持时,最终就会走向妥协的道路。这一时期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仍没有摆脱传统束缚的影子。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母亲不再是被家庭束缚的传统女性,王安忆将她塑造成一个纯粹追求自我价值的人。这个母亲形象“脱离父权文化期待之外的对未来生活的精心筹划,有实现自我生命欲望的所具有未来期待的意识”[8]13。这位母亲的一生始终彰显了她追求理想的自我,有主见、有行动。“她的真理在星空,我们的,在日复一日之中”[5]290。在这条探索自我价值的道路上,母亲像是一个记录历史的纪念碑,而追求平稳生活的陈诚们就是“驮碑的龟”[5]291或纪念碑旁的杂草,平凡而普通。可以说,这位被历史追认为“烈士”的母亲不是被“历史”选中,而是她选择了“历史”,她成为了她自己。在整部作品中,她以母亲的身份被叙述,但实质上她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她在“母亲”身份之下一个彰显自我但并不突出性别意识的人的一生。母亲心路历程中作为女性成长的那部分自我是被遮蔽的,或者说,王安忆着力要表现的是母亲这种历史化的人生轨迹,而忽略那些细微的人性感受,所以,读者无从得知母亲在面对爱情、婚姻、友情以及严酷的批斗、年幼的子女、生命的终结时经历过怎样复杂的情感体验,女性日常化的“小我”被遮蔽于革命的“大我”之中。
三、 意义的生成:历史思辨、精神探索与日常生活
“母亲”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了丰富多样的母亲形象,鲁迅塑造的多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以及不觉醒的母亲形象,冰心则在作品中热情讴歌“母爱神圣”的母亲,张爱玲《金锁记》刻画被金钱和情欲困住的母亲,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书写旧时代“典妻”陋习下苦难的母亲,等等。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女性写作的热潮,一大批女作家重新书写女性题材。铁凝、陈染、徐小斌、残雪、王安忆等女作家们站在女性的角度审视世界、质疑男权文化、表达女性观点。当代女作家们力求改变文学中对母亲形象的扁平化书写,还原母亲的本来面貌,揭露其生存现状,探索女性身上的“母性”和“人性”。她们试图从不同角度重塑母亲形象,重新定义新时代的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价值,获得女性话语和力量。王安忆是其中笔耕不辍、孜孜以求的代表。
在王安忆的早期小说作品中,她书写的是一系列传统蒙昧的母亲形象,将笔触多停留在无私的母爱和盲目的付出上,揭示在无私奉献背后她们的悲惨命运。《小鲍庄》中落后的农村母亲沦为生殖工具,缺乏对自我的认知;《小城之恋》中无知的女孩未婚先孕,但对孩子产生天然母爱;《叔叔的故事》中妻子面对丈夫的出轨,用无限退让的方式来维护家庭完整。王安忆始终以第三者的视角书写这群可怜又可悲的母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理性的态度揭露受封建道德文化影响的母亲的悲惨命运。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生命体验的不断丰富,她开始新的尝试,塑造了一系列异化的母亲形象,如《长恨歌》里物质至上的母亲,《启蒙时代》中抛弃孩子去追求个人事业的母亲,《流水十三章》中女儿性大于母性的母亲。这些异化的母亲突破了传统的慈母形象,大多是都市女性,受先进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由于现实的诸多束缚导致她们不能进一步发展,最终产生异化。除此之外,王安忆并没有停止对理想母亲的探寻。在《流逝》中瑞丽兼具母性和父性色彩,不再依附他人,可以独立地实现自我价值。在创作追求中,王安忆试图突破极端“慈母”和“恶母”形象的禁锢,将探讨外在环境对母亲形象的影响转向反思母亲的自我主体意识觉醒。她力图客观地讲述多样的母亲生存状态,真实再现母亲生存场景,深入挖掘母亲身上的人性欲望,书写的母亲形象随之更加立体而丰满。“王安忆透过母亲形象,还原女性的生存真貌,饱含了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怀与体贴,对复杂深邃人性的执着追寻。”[9]56但是,在《一把刀,千个字》中,王安忆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却不是停留在对女性(母亲身份)问题的关注上,而是由母亲这个人物命运的书写延展到对历史和人生的叩问,探索历史的复杂面向和人的精神困境,并有意完成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调配。
(一)具有意味的历史思辨
《一把刀,千个字》看上去所讲述的故事是关于淮扬厨师陈诚漂泊的人生和颠沛的生活,实际上让读者深深感喟的是,那个有着非同寻常历史经历的母亲在后来的现实中始终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这位在特定历史时期敢于抗争并在事后被追认为“烈士”的“英雄母亲”,如此持久地影响甚至困扰着她的亲人们的命运走向,这反映出书写者王安忆对历史颇具意味的思辨。五四传统下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的彰显是“人的文学”的自觉书写,但这个拥有强大自我的母亲的命运却在历史的流转中显出复杂而矛盾的意味,王安忆“不仅最终把自己的笔触探向历史的深处,而且也还对这段一直到现在都暧昧不清的历史提出强有力的思考与诘问”。[6]123她通过对陈诚等人生活际遇的叙述,揭示人与历史、与自己、与他人真正和解的艰难,从人性的幽微处洞察庸常生活中的人们难以实现精神超脱的困境,“用母亲的说法是真理,在父亲,可能就是常识,姐姐是对错的概念,到了他,只不过是合乎伦理的生活。”[3]11处在无名状态的“她”,特殊历史时期英勇无畏彰显“大我”的“英雄母亲”,却又成为子女历史记忆里的精神藩篱,使得他们在平凡庸常的生活里精神自渡,在“人生总要继续下去”的宽慰里寻求心灵的安稳与释然。王安忆在这部小说中看似是对这一家人的人生浮沉的书写,但可贵的是她借此在思想层面做出了对历史的深思。
(二)揭示人生而孤独的精神境遇
王安忆的书写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在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纵深里对平凡个体人生的审视和人性的观照。孤独是人的一种生命存在状态,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都在书写现代人的孤独意识。鲁迅在《故乡》中写出中年的“我”与闰土之间的隔膜,在《孤独者》中更是写出魏连殳不被理解的绝望和悲哀。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实际上已经展露出现代人都市生存“在而不属于”的孤独感,这种以“城”表现“人”的孤独书写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王安忆的小说也书写孤独主题,她曾塑造过一些在灰色地带生存、在情感破碎中悲伤的孤独者形象。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她无意书写空间中的孤独,而着力表现时间之下的孤独。小说中的母亲生前是孤勇的革命者,在动乱年代她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那种人生的孤独感在历史的回望中愈发强烈和明显。尽管平反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她在媒体上得到极大推崇,但实质上她生前不被时代理解,死后不被家人真正认同。她之所以对子女在精神上持久产生影响,其实也在于她的这些家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刻意的疏离反倒构筑起记忆的藩篱。王安忆自言对作品中人物起名是相当谨慎的,但她却没有给这位母亲赋予具体姓名,只以女性的“她”作为对这位母亲的标识。“命名的抽象化并不是无力命名的结果,而是对根本特性的强调与概括。小说用第三人称‘她’来指称母亲正与陈诚对母亲的疏离感相匹配。”[10]171王安忆有意让陈诚认定自己内心的不如意、生活的孤独感是由于母亲造成的。她在《纪实与虚构》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母亲是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母亲是我在这世界里,最方便找到的罪魁祸首,她是我简而又简的社会关系中的第一人,她往往成为我一切情感的对象。”[11]14这种对母亲“罪魁祸首”的指认在《一把刀,千个字》中也透射在陈诚身上。小说中多次提到陈诚与其他人之间的疏离状态,究其根本是母亲的缺席和长期漂泊异乡导致了陈诚不知如何与人相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疏离感更加明显。他与嬢嬢不亲近,不愿喊嬢嬢“妈妈”;与父亲之间相处的尴尬需要妻子来从中调和;与妻子之间产生矛盾后的冷处理、不沟通……这些行为都是他内心孤独的外在表现。在母亲身份被揭开后,陈诚接受不了成为烈士之子的压力和关注,选择逃离到异乡。与成长环境迥然不同的纽约也不能填平他内心的缺失,甚至加重了灵魂的孤独感。表面上看,陈诚一直承受着母亲带给他的心灵上的负累;深层次上,王安忆将这种孤独投注在文本中,为读者揭示了陈诚烟火人生表面之下无法躲避的孤独。母亲是孤独的,陈诚的孤独似乎也是一种必然的走向。“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可以欣慰的是,当一个人孤独地与他自己作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孤独地与自己作战。我想,我的文学,就将是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连与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12]1陈诚与他的母亲心灵上并不相通,然而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内心孤独的个体。“想着人多么像无根的浮萍时,孤独……正在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内心。熙熙攘攘而又繁华热闹的人群也不能拯救我们,……孤独成为无法克服的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11]132孤独正是生命本身的况味。王安忆书写这个具有“大我”的母亲及其影响,但又将这份影响消解,以一种豁达的孤独观揭示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境遇。这是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延续其文学创作所表达的不变的哲思,也印证了“文学是人学”的永恒主题。
(三)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
日常生活蕴含着丰富的话语空间。西方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对日常生活进行文化审视,做出了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阐释,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就著有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宏大叙事转向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尤其是“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更凸显对个体化日常生活的文学表达。王安忆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巧妙地以母亲形象的刻画勾连起现实的日常与记忆中的历史。作为“英雄母亲”的“她”彰显了强大的自我,但“她”指向的是“宏大叙事”,缺乏日常烟火气息。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状况,也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症候。她与家人的情感应通过日常生活联结,她的“宏大叙事”被媒体铺天盖地宣传,但打动不了家人的心。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一个关于人生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小说中,姐姐鸽子就呈现了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的生活选择。她先以母亲作为人生理想,显出与母亲相似的聪慧和敏锐,她模仿母亲,学习母亲,处处争先,自小具有领袖型人格,上学时是学校里第一个红小兵。母亲被判罪后,她和父亲迅速与母亲划清界限,这意味着她最初的理想破灭。在历史的浪潮中她发现“我们这种人总是错的”[5]37,她本有天赋和志向沿着母亲追求真理的道路继续探索,但最终选择主动放弃与历史的联系,远赴异国他乡重新开始,过起了平凡人的生活。对她而言,平凡是一种救赎,也是一种归宿。“人毕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从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每一件事,其实都蕴藏着无限丰富和异常复杂的历史文化气息;日常生活本身,也是确认我们自身存在价值的重要载体。”[13]3这也正是《一把刀,千个字》蕴含的潜台词。王安忆在思辨历史的同时也在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她的写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回望历史更面向当下和未来。“在王安忆看来,振臂一呼而能应者云集的‘英雄’毕竟不是常有的,小人物的‘庸常’或许才是‘生活’的本真常态。”[14]86王安忆通过母亲和女儿不同人生选择的呈现,引领读者思考“何为良好生活”“究竟该选择怎样的人生”这些既日常又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显然,王安忆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调配,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过去,“女性被看作物的形态对象化,其角色作用体现在家庭范围中,女人的价值只在繁衍上,而她的其他社会功能被忽略。”[15]65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女性的社会价值被重新认识。王安忆在多部作品中对母亲形象进行了丰富的刻画,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是她对母亲形象书写的又一次突破与创新,她为当代文学中的母亲形象谱系书写了新的“这一个”。小说看似以淮扬厨师陈诚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其实母亲才是勾连历史与现实的关键人物。王安忆通过书写“母亲”这个人物及其对子女的影响真诚地思考在时代潮流裹挟下的个人命运和选择,探讨如何平衡烟火人生与追寻自我的永恒命题。她尝试将个人、历史、时代有机融合在一起,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方面进行新的突破,串连起小说里陈诚追寻心安的“自我”与“英雄母亲”的独立“自我”之间一场漫长的灵魂对话。这对话跨越时空和生死,无声无息,对峙而又纠缠,难以和解。平凡人生唯有接受遗憾,以搁置为放下,以忘却为解脱,继续前行。厨师陈诚烟火人生里挣扎的内心与“大我”母亲暗暗搏斗的精神历程,映照出时代更替的轨迹里“日常”与“历史”的关联与疏离。跨越时间长河,王安忆对历史的诘问和人生的探寻,让《一把刀,千个字》留给读者久久回味和沉思的文本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