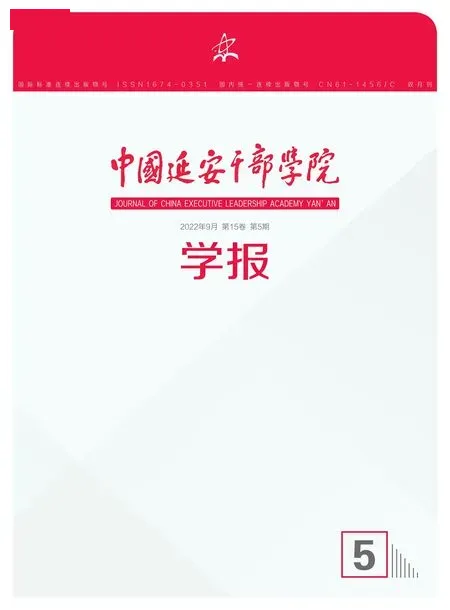毛泽东著作在华北沦陷城市的传播、阅读与反响
——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例
王富聪
(团结报社 文史周刊,北京 东城 100005)
近年来,学术界从阅读史和传播学的视角对抗战时期毛泽东论著进行研究,关于抗战时期毛泽东论著的阅读、传播和影响,以往多注意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乃至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但对其在沦陷城市的传播和研究则不是很清楚。以毛泽东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例①,以往研究关注到《论持久战》在中共抗日根据地中下层干部与基层兵民的阅读与接受[1],或对国统区的传播和影响[2],在沦陷区的传播和影响较为薄弱,虽然关注到在上海的传播,但对华北沦陷区的接受情况则不清楚②。仅有一篇研究注意到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的传播及反响③,但该文对《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传播的描述极为简短,且在地域上,仅关注到在孤岛上海的传播。在视角上,没有考察书籍是如何进入受众视野,哪些人在阅读,民众是如何阅读的,阅读了之后产生怎样的反应,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实际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城市的宣传。因此,《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成为中共对沦陷区开展工作的重要宣传品。通过根据地城工部门和地下党的秘密渠道,沦陷区特别是沦陷城市不少民众也阅读了这两篇文章,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有多个版本,本文依据的版本是当时民众所见到的版本④。
一、中共重视在沦陷城市宣传《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也逐渐重视在华北沦陷城市积蓄秘密抵抗力量。抗战初期,“平津唐点线委员会”就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城市坚持秘密宣传和组织活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领导人逐渐加强了沦陷城市工作。从1940年中央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都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面向根据地周边的大中城市开展工作。到1944年6月5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3]518相应地,重视城市工作势必要重视对沦陷区民众的宣传,特别是对毛泽东论著《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宣传。
1941 年,彭德怀在北方局扩大会议中强调,知识分子“是开展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的桥梁”,要向他们积极传递“《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4]361943 年3 月15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对山东分局作出总结和指示,指出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方面,“要特别注意质量,印发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到敌占区、游击区广泛散发,并用一切办法保障送到觉悟知识分子及伪军伪组织上层分子手里”[5]448。
北方局下属的山东分局和晋察冀分局各级城工部门对此非常重视,开办了专门针对城市工作的培训班,并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论著列入城工部的重点培训课程。
山东城工部门培训的主要内容就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根据地领导人讲形势报告,党的政策及敌占城市建党问题的材料,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技术,纪律教育和革命气节等。以山东分局为例,要求“须从解答疑问,联系到毛主席的三大著作⑤与目前政治形势及一定分量的阶级教育,确定其人生观、世界观;加强文化娱乐及俱乐部的工作(可挂一般抗战图表与图画、伟人像等);到各地参观作讲演”⑥。1944年,山东分局指示鲁中区党委和济南工委,应“做到有组织的经常的供应与散发”“中央所指示的有计划的印发毛主席的三大著作之类的小册子”[6]296。在山东根据地鲁中区,由济南市到根据地来要求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学生日益增多,济南工委举办了青年训练班。先后有百多名青年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等,山东分局城工部举办青年训练班,“集中训练了三百多个由大中城市来的青年学生”[7]156-158。冉成1944 年2 月进入山东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被分到青年队。他回忆道:“这个队里的青年都是从城市来的学生……大家共同学习《论持久战》。”[8]69
晋察冀分局城工部的培训课程中也包括《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两书。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有计划地派遣人员打入到学校前,进行短期的培训。在北平主要是派往学校、机关和小工厂。“在派出以前,一般都经过了短期(两星期至一个月)的训练。训练内容为隐蔽精干政策、敌占城市建党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如何看伪报以及一些技术上的问题。”[9]38据张大中回忆,1942 年开始,晋察冀城工委的党内学习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党章》等。[10]19在对北平地下党的整训中,选拔了一些有条件在北平立足的同志派进去,城委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等。[10]25地下党员刘北海回忆,“支部从昌平输送7 名同志到冀热察区党委办训练班学习。学习内容是《论持久战》和国内外政治形势,训练班由姚依林同志主持”[11]93。北平地下党员王若君回忆,“学习训练内容: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党的政策及敌占城市建党问题的材料”[12]58。辅仁学生侯维城回忆,1945年春他到城工部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形势、秘密工作方法后返回北京[13]70-78。北平地下交通员安捷回忆,她在晋察冀城委所在地培训期间也学习《论持久战》[14]488。张绪潭回忆,他到达城工部后,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生活……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有“《新民主主义论》……经常阅读《毛泽东选集》”[15]307。据佘涤清、杨伯箴回忆,从1943 年开始去解放区的北平学生陆续增多了。“一部分到解放区各条战线去工作,大部分训练后再派进城。从1943 年秋到1944 年底,在晋察冀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学习的大中学生已有一百多人。在城工部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文章”[16]15。
除分局一级外,各分局下属的区党委、地委、县委也成立城工部和城工科,具体负责城市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区的几十个县都曾向北平城内派过地下工作人员,这些同志进城后发展了一定的关系”[17]116。济南工委“两年来(1943 年9月至1945年9月下旬)工委在市内发展了480多个群众地下工作关系……打入干部70 人,发展党员30多名”[18]79。
这些派遣打入干部接受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课程教学,他们被派遣入沦陷城市继续做秘密工作,这些人往往成为“种子”,在那里生根发芽,并发展了更多的干部和关系。城工部对他们讲授毛泽东论著,既是对他们的业务培训,也影响到他们在地下工作中宣传这些党的文件精神。
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传播途径
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自公开发表后,便引起了中共、沦陷区报刊、日本媒体的关注。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立场进行选择性刊登,不同程度地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做了宣传。
(一)《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秘密传播途径
相比于大后方的公开运输,《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如何输送到沦陷城市受众手里显得极为关键。中共对沦陷区的秘密宣传受到日伪的监视。伪北平警察局要求旅栈配合密查“旅客有宣传共党之嫌或书籍者”[19]。伪北平警察局特务科科长袁规曾报告上司,“据职科谍报称:近获得八路军反动宣传品之《晋察冀日报》《群众报》”等九种宣传品[20]186。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根据地曾以“伪装书”的办法向沦陷区输送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就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对进步书刊伪装封面或变换封面及伪托出版社的做法是通常的办法[21],但以往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些“伪装书”是如何运进沦陷城市的。实际上,由于日伪禁止抗战书刊在其占领区发行,从根据地往沦陷城市输送书籍依靠城工部门的秘密交通线[22]。
首先,通过城工干部和秘密交通员带入。派遣打入的干部都要进入沦陷城市工作,他们往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随身携带书籍。前述北平地下党员刘北海曾被派到冀热察区党委办训练班学习,学习内容有《论持久战》。结业后,城工部部长武光安排他仍回昌平开展地下交通工作,负责传递根据地与北平、北平和冀东之间的书信。1942 年4 月,他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日本宪兵在搜查刘北海住宅时,就发现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4本书[23]222。
天津圣功中学是教会学校,读书会接受地下党的领导。读书会会员从地下党员何方那里能“看到带来的八路军的传单和材料。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就是这样看到的”[24]603。陈典明于1944 年底被冀中七地委城工部派到天津电信局做地下工作,他住在弟弟家,选好发展对象后,“便把带来的解放区的书刊拿给他们看,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25]14。
在山东,1943 年,焦英被党组织派往敌占区的鲁北鸿文中学做青年学生工作。这是鲁北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党支部组织了“读书会”,“我们从解放区带进了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也在读书会中秘密传读”[26]322。
《晋察冀日报》将“《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曾多次重印出版,并以伪装本发到敌占区的北平、天津、保定、太原,以及沈阳、大连等地”[27]248。据周明、方炎军回忆,《晋察冀日报》社把《论持久战》伪装为《文史通义》(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等多种伪装的书名,经过城工部发行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大同、太原、张家口等地⑦。
一些交通员多次在根据地和沦陷城市往来,带入大量的宣传品。秘密交通员携带书籍非常秘密,一般以特殊装置藏好,通过做生意等办法通过封锁。据地下党员张大中回忆:中共北方分局城工部干部陆续把在根据地出版的许多“伪装书”(如封面印的是《山海经》《水经注》之类,内容则是毛泽东著作或编纂成册的新华社评论),……等隐藏在毛驴、驮子里运进北平,秘密传阅,发动群众参加地下斗争[28]318-320。天津抗联传阅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是“从解放区带来”。天津抗联负责人康力回忆称,“从解放区往市内带文件,由一个文安县姓严的同志用自行车带,伪装贩卖鸡蛋,他用一辆自行车带两个鸡蛋筐,筐底是双层的,文件放在里面,垫筐用的一块木头是空的,也可放文件”[29]659。
其次,通过去根据地的城市进步青年返城时带入。抗战时期,城市地下党动员沦陷城市进步青年秘密到根据地去参观、学习或短期培训,他们返回城市时往往也携带有毛泽东论著。北平是大中学校集中地,据北平地下党员崔月犁回忆,他在北平发展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培训。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曲阳的秘密交通线送走了十几个人”到根据地。其中就有人携带书籍返回城市。“由于张德吾、王用孚都有伪职身份,刘仁同志就指示他俩从根据地往敌占区带秘密宣传品,如《晋察冀画报》《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工作由他俩直接到城工部去取材料,然后带到北平。”然后崔月犁“到……吴继文大夫家去取《晋察冀画报》《新民主主义论》”[30]399。
在天津,1942 年7 月至1943 年5 月,田英、张继兰、朱瑛、苏更、辛东、石中等相继加入了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组织——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1943 年8 月更名为“抗联”)。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决定派田英去游击区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以便恢复联系。在完成任务之后,她携带着《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学习文件返回了天津[31]289。在青岛,崇德中学支部建立秘密图书馆,从根据地秘密带进来《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书[32]194。
再次,在沦陷城市就地秘密印刷小册子和复写书籍,宣传《论持久战》等内容。为了满足更多的进步青年的学习需要,一些地下党秘密印刷小册子。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自办了《自学》刊物,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33]44。天津抗日救国联合会“除阅读进步书籍,……学一些解放区的歌曲……出了一个抄写的刊物,名字叫《抗联》,封面是毛主席的木刻像,是内部传阅的刊物”[34]650。天津地下党康力、楚云领导的天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编印室于1944年3月3日“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翻印”[35]275。
一些人还在沦陷城市内复写或抄写毛泽东论著。据在北平做学生工作的张大中回忆,“党内的学习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等,主要是从平西根据地送来的油印本,也有的是在城内用很薄的美浓纸复写的”[36]19-24。辅仁女中学生安捷回忆,她常向“民先”小组汇报读书会的活动情况,并把“齐克君的传抄品、节录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等,带给王彤和读书会的其他成员传阅”[37]123。
在残酷的沦陷城市环境中,无论是从根据地输入还是秘密就地印刷毛泽东论著,中共地下党的力量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作用。从日伪侧面证据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论著在沦陷城市的传播。王甦是华北临时政府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学监,给伪军官教授战术,他回忆称,“我作为学监可以得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38]259-260。
(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公开传播途径
除了从根据地秘密输入和就地印刷、抄写等方式外,在沦陷城市内公开发行和流通的报刊上刊发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介绍。
沦陷城市公开发行伪政权所属报刊大多间接介绍过《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容。北平的《益世报》1939 年报道称,《论持久战》“自谓必得最后之胜利,且分‘持久战论’为三期,即:第一阶段——敌强我弱之防御战,第二阶段——敌我势力均等之相持战,第三阶段——敌弱我强之胜利战”[39]。1944 年2 月20 日的《新申报》发表社论称:“共党领袖毛泽东又出版了理论书《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40]据《解放日报》1944 年7 月13 日报道转述,1944 年4 月15 日出版的北平伪《新民声》杂志一卷八期刊发的吴利仁著《论中共与苏联关系》一文,内称毛泽东:“尤以彼所著之‘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三大论著,……作了中共目前进行‘抗日战争的理论根据’。”[41]
除了中文刊物外,甚至有刊发《论持久战》报道的日本刊物输入北平,一些知识分子间接学习。据北平辅仁中学生施宗恕回忆,其舅父储皖峰为北平辅仁大学教授。“有一次,我舅父从一本叫《扬子江》的日文杂志上,看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42]302虽然他们并不太懂日文,但他们看懂了大意。考察日文《扬子江》杂志,1938 年11 月确实刊发过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报道[43]。以上伪政权所属的报刊和日文杂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城市被阅读,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尽管这些伪政权刊物是从反面宣传的立场对毛泽东论著进行转引和曲解评论,但对毛泽东论著的基本观点还是作了客观引述。例如,司徒雷登在囚禁期间能读到《大阪每日新闻》的英文版,以及德文版的《公报》,尽管日本的出版物“内容假得离谱。但是他们不管怎么编造,总会露出一些真实的消息”[44]101。
由于这些报刊是公开合法发行,且发行量从几千份到数万份不等,传播面更广,据1941 年《实报》统计,北平人口174万余,户数32万4693户[45]。发行量较大,客观上让广大沦陷市民得以了解《论持久战》的基本观点。
三、沦陷城市民众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的阅读方式和反响
考察书籍和社会的关系,关键在于阅读方式和阅读反应。这些毛泽东书籍输入沦陷城市后在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等之间秘密传阅,受众阅读书籍的方式既有个人阅读,也有集体阅读,还有自发的个人阅读,总体上,阅读之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向效果。
(一)地下党组织的个别阅读
除了自发性的个人阅读外,中共城工部门领导的地下党也组织了进步青年秘密阅读。北平女一中学生俞立回忆,女一中同学不少人阅读进步书刊。她回忆道:“组织上经常给我们书籍和从根据地带来的文件,印刷品。”“印象最深的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地下党“赵元珠、黄云来时,经常带一些书供我们传阅。记得有一次曾拿到一木箱书籍,数量很多,我把它存放在孙阿妥家的地下室,陆续取出阅读”[46]52-53。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余贻倜回忆,地下工作者“李道宗(崔月犁)还经常给我捎来一些《晋察冀日报》,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阅读。书里的话入情入理,说在了我的心上”[47]19。后来余贻倜才知崔月犁是八路军的一名医生,来做地下抗日工作。余贻倜在崔月犁的影响和帮助下,开始做一些革命工作。抗战胜利后,把崔月犁安置在他的放射科里干事,改名李士英,继续掩护革命工作。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除了在青年学生中秘密传阅外,也在市民中宣传。1942 年秋冬,张海泉、崔英、刘勇、郭敬等奉博野县委城工部指示赴北平,在原北平外一区、外三区等地开展地下工作。开展宣传工作,提高群众觉悟。其内容为“宣传《论持久战》,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增加对我党的好感”[48]203。到1944年8月份,他们发展了更多人员,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下设两个支部。
(二)地下党组织的集体阅读
除个别传阅外,地下党组织了读书会,在小范围秘密集体阅读[49]。1941 年,北平育英中学成立了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是张大中。地下党利用育英公开合法的宗教团体——团契为掩护,联系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和小社团,如“铁流社”“前进社”。“表面上读《圣经》,暗中传阅进步书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萍踪寄语》以及苏联政治、文艺作品。”[50]245李光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1944 年到晋察冀城工部学习班学习了一个月,回到北平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女附中的地下党支部宣传抗日,“秘密组织了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包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论持久战》等书”[51]214。
有的读书会多次学习毛泽东论著,甚至写读后感,互相讨论。天津圣功中学读书会同学虽已读过《论持久战》,但仍然再次学习,并进行讨论式学习。“1939 年11 月,张凛组织几个同学再次学习《论持久战》,在这次讨论后她约苏菁单独到她家楼上,作入党前的第一次谈话。”随即被组织上“决定接受入党”[52]604。有的写读后感。李春龙回忆道:“对政治可靠、准备发展入党的对象,进一步看《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共产党宣言》等;看书后听读后感等。”[53]218-226
有的将《论持久战》作为课程讲授,对伪军进行间接宣传。华北临时政府治安军宣导训练所学监王甦1944 年3 月经地下党人薛成业介绍入党,他给伪军官兵教授战术,因看过《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籍,“讲授的效果实际上是宣传了共产党、八路军,对学员有相当的影响”[38]259-260。
有的对工人和商人进行讲解式集体教育。王见欣⑧1938 年至1940 年时为济南工委书记,打入济南城内后,他找到了济南鲁麟洋行经理毛晓亭,“把《论持久战》等书给他看,对他表示信任”。并对该行职工一谈起时局,讲国际国内形势,和他们一起读报分析问题,送进步书刊,“还把从根据地带来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送给他们传阅”[54]300。经过一段时间,便在该行发展了两批党员,并在济南仁丰纱厂、复兴印刷公司、日本商行等发展了第三批党员。他回忆称:“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有28 个党员,除去到根据地工作的5 人,还有23 人。”[54]302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工作就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我们深入到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针对不同对象把从根据地带来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以及其他小册子,给他们阅读”[54]303。可见,毛泽东论著成为地下党教育沦陷区民众的非常重要且有效果的宣传品。据毛晓亭回忆称,他读了《论持久战》后很受启发。他回忆,地下党人王见欣等人晚上“组织工人学习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根据工人中对抗战形势存在的模糊思想,几次给工人宣传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我曾参加过两次,对我教育启发很大,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韩文一同志的讲解,使我的心胸豁然亮堂了”[55]15。他还回忆,当时他所任经理的复新印刷局三十余人,中共济南地下工委发展了九名党员,印证了王见欣的回忆。
还有的对《论持久战》活学活用开展宣传。冀中区安国县委城工部挑选一批熟悉天津情况的干部及工作人员潜入天津各大小药栈,王治、崔巍秘密刊印宣传材料,“正值抗日战争由相持阶段逐步转入反攻阶段。第一篇文章标题大概用的是《黎明前的号角》,就是根据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精神写的”[56]202。1945 年春,周方(原名赵锡中)当时是燕京大学攻读音乐即将毕业,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前线文工队通过周方的同乡学生商殷去北平动员他加入剧社,文工队工作人员和商殷一起研究《论持久战》,武装了商殷的头脑[57]24。用《论持久战》宣传抗战必胜的力量,动员赵锡中到根据地[58]113。
(三)自发性的个人阅读
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有些人自发阅读《论持久战》。王健是天津法商学院“民先”会员,抗战爆发后,他在天津时“已看过毛主席《论持久战》”[45]22。后到上海准备考学,他回忆称:“每天上午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看书……我认真地读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民主主义论》(我记忆中,这本书作者在封面上印的是“列御寇”)。另一本是厚厚的《唯物论辩证法》……这两本书使我受益匪浅。”[59]27
伊敏是北平正阳门车务段列车员,1938 年6月,“认识了天津车务段的列车行李员杨世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北宁铁路职工抗日救国会”,该会办了一个秘密刊物,名叫《铁球》。他在这个刊物上见到了“《论持久战》的要点”[60]95。此后,伊敏利用业务时间,和朋友互相借阅进步书刊秘密传看,“传递《铁球》”,1940 年,伊敏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走上革命道路。
前文已经提到,北平辅仁中学生施宗恕和他的舅父在日本杂志《扬子江》上阅读《论持久战》,就是个人阅读。他表示:“正在黑暗中痛苦地摸索前进道路的我,犹如看到光芒四射的灯塔,增添了无穷的勇气、信心和力量。”1942年冬天,施宗恕在地下党项子明的带领下,一面在辅仁大学读书,一面在外国语专科学校教书,开展抗日工作[61]303。
一些小城市的人也有机会看到《论持久战》。江村回忆,七七事变后,济南中学解散,他回到老家后决心投身抗日,次年,通过当地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他“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62]237。1940 年,江村加入中国共产党。济南一中毕业的王文彬,1938 年秋到过上海,“先后阅读了《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63]197。1943 年,王文彬返回高密县任县里中学教员,开展抗日教育。
总之,通过学习《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进步道路,地下党通过秘密读书会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动员了许多学生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或在沦陷城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余 论
从书籍的传播主体来看,中共城工部门和地下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打入人员和交通人员为书籍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打入人员普遍都开展了发展组织和宣传工作。他们影响了更多的同志或关系网中的熟人阅读,实现了更加广泛的二次宣传。这些关系都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传播的潜在力量。
从传播的范围来看,本文以华北沦陷城市为考察范围,实际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其他沦陷城市也被地下党和进步青年传播和阅读。伪满洲建国大学图书馆“有日文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64]121。1942年,东北“建大”二期生戴励明等人在日本《东亚》《东亚旬刊》上读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重要部分、《新民主主义论》的一部分。”后弄到《新民主主义论》全文日译本,“分别抄写,译成中文,秘密传阅”[65]226。李子秀考入伪满洲建国大学,参加地下进步组织“读书研究会”,阅读《论持久战》[66]158。孔越山曾将《新华日报》上《论持久战》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套在棉袄内,带回新乡进行传播[67]267。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这也说明《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城市被阅读的广泛性。
此外,沦陷城市的《论持久战》也传到了国外,传播给更多受众,产生了更大影响。《论持久战》被及时译为日文,刊发在日本杂志上也印证了这一点。有人研究发现,在日本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改造》杂志⑨1938 年发表的《论持久战》就是山本实彦(《改造》杂志社社长)在中国沦陷区得到的,“山本实彦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情况,几乎每年都前往中国考察”[68]。进一步的考证可以发现,山本1938 年7 月在北平⑩。又据周作人1938年7月11日致松枝茂夫书信言,“改造社山本社长来此间,曾得会见两三次”[69]62。山本实彦回日本不久,《改造》杂志便刊发了《论持久战》节选版。又据日人松枝茂夫言,改造社“搜集了很多中国的新闻杂志和新版书,增田先生沉醉其间,正热心地读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70]217。1939 年改造社又出版了其他专著,收录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一文[71]。由此可见,《论持久战》在日本首次传播与山本实彦在北平期间搜集中共宣传品密切相关。而在日本出版的这些书籍,又影响了中国国内的阅读群体。田风1938 年在日本东京留学,发现了“毛主席所著的《论持久战》……是翻译成日文的,同时还读过《八路军从军记》……从这三本书里我发现了我的出路”[72]8。1939 年,田风回到北平。女友王兰写信说:“你如果要同我结合,那只有我们一同出城。”[72]9思想也趋近于中共。魏焉1939 年到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他所在的小组“开始向伪满建国大学、长春法政大学、工科大学,哈尔滨军医大学输送共产主义书刊”[73]298。输送的书有日文本《论持久战》。魏焉后回北平,在伪绥靖军宣导训练所任少校教官,1944 年经同宿舍薛成业介绍入党。
从书籍被民众的阅读来看,进步书籍特别是社会科学书籍,对于苦闷的青年不仅予以知识,而且启发其对现状的不满,建立抗日思想。在当时,北平“一般青年却沉醉于灯红酒绿的桃色氛围里,或专心于个人的享乐,出入电影院,话剧团,咖啡馆”[74]。正是书籍启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天津地下党员康力、楚云认为“对学生的启发和教育,书是一个最有力的工具。能因互相看书而建立了感情,更能因书的启示而予以思想认识上的进步”[35]277。在爱国情怀和个人生存的双重驱使下,进步青年有的去根据地工作,有的加入中共,有的则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有的则成为中国革命的同盟者或同情人员。
不可忽视的还有一点,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虽然身在日伪统治之下,但也有相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山东分局城工部打入济南正谊中学的赵鼎夫正在校长綦际霖掩护下“进入正谊中学担任了语文、史、地教员”。赵鼎夫通过细心观察,“深感校长、教务主任吴鸣岗、庶务主任杨德斋都是在沦陷区具有爱国思想、民族观念的人”[75]98-99。许多地下工作者之所以能打入城市站稳脚跟并开展秘密宣传工作,固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做桥梁密不可分,但周遭环境的默许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掩护作用。
注释:
①选取《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考察,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是作为单行本被最广泛的传播的毛泽东著作。据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厂长所述,1943年到1945年,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印行毛泽东著作的伪装本,以“《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印得最多”。见周明等《印行毛泽东著作伪装本的回忆》,《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②有人注意到《论持久战》传播到沦陷区,中共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协同在上海出版的《每日译报》1938年8 月23 日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全文,该文对传播和影响的论述集中在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对沦陷区仅限于上海孤岛一地。见张文波《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传播与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③“抗战期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实现了向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跨域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程美东、裴植:《抗战期间〈新民主主义论〉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传播及反响》。又见《近十年国内〈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综述》,《党的文献》2020年第2期。
④已有研究指出,《论持久战》版本虽多,但真正重要且具影响力的,实际上只有四种版本。抗战时期主要是1938年7月1日《解放》周刊版、1938年7月解放社初版。
⑤《毛主席三大名著》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晋绥分局1943 年10 月印制的。决定指出:毛泽东的三大名著,是指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与具体方略,所有共产党员都应熟读深思,领会贯通,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各机关部队应认真组织学习讨论,作为经常课本。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⑥山东分局常委:《关于开展大城市青年工作经验介绍》(1943 年9 月),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084-014。
⑦周明、方炎军:《烽火十年忆邓拓》,载《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第14页。“为了开展对敌宣传,向敌占区人民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晋察冀日报社曾专门出版了向平、津、保等敌占区人民宣传的书刊……有的还用敌伪宣传品《大东亚共荣圈》的封面、扉页、版权页,伪装成敌人的宣传品。这些书是通过我们的城市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去的”。见贾呈祥《〈晋察冀日报〉回忆片断》,载《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资料选编》第44页。
⑧王见欣又名王见新,后从济南回到山东分局任城工科科长。1941 年,城工科合并到敌工部,任敌工部副部长兼城工科长,负责济南、青岛、徐州的地下工作。
⑨《改造》杂志是从大正末期到昭和30年,与《中央公论》《太阳》一起是日本主要综合杂志,刊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是“对关注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的综合杂志”。参见許丹青:《1920、30 年代の日本出版文化における対中国イメージと中国認識》。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2021年,第29页。
⑩山本实彦于1937年8月来到北平,作为随军记者在中国访问,在中国期间,他访问了不少人。这些人中既有日本军部的人,也有中国政治方面的要人。参见許丹青:《1920、30 年代の日本出版文化における対中国イメージと中国認識》。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2021年,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