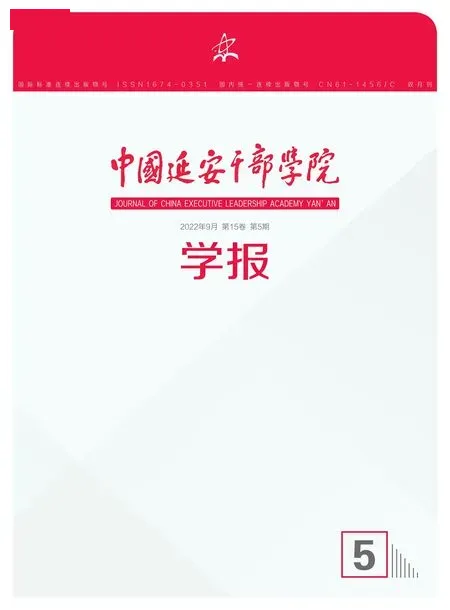试解读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最新表述
黄少群
(原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遵义会议历来被称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个“转折点”和“转变”,就在于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历史地位及其所产生的伟大历史作用。
一、党的历史上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表述
一百年来,党的历史上有过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即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都专门地和特别突出地对遵义会议作出了表述。从内容上看来,三个决议的表述基本相似,又有所不同,特别是第三个决议所添加的新的词语,对遵义会议的表述赋予了新的意境。
(一)三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表述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对于理解这三个历史决议、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表述,笔者想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为便于理解和比较,现将三个历史决议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第一个历史决议表述:“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1]969-970
第二个历史决议表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2]5-6
第三个历史决议则这样表述:“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3]24-25(以上引文中加黑部分为笔者所加)
所谓“相似”,就是三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作了表述;所谓“不同”,就是第二和第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有所增删,特别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增加的新词语和新内容,使遵义会议的表述有了新意境。
(二)三个历史决议关于遵义会议的表述,是由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作这样的表述,完全是出于当时党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党的七大时期,党内刚刚经过全党整风运动,对给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全面彻底的批判,正式形成了政治上成熟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毛、朱、刘、周、任),第一次明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明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决议对遵义会议作这样的表述,就在于说明: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我们党才取得了今天(党的七大时)的辉煌。这对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绝对必要,正式表达了全党意志和决心。正是这个决议,统一了全党认识,加强了全党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而由于当时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资料还相当匮乏,参加遵义会议的老同志虽然也都出席了党的七大,但也还来不及和不大可能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作详细回顾。所以,第一个历史决议这样表述,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和历史需要。
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历史发展和历史经验,更主要的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历史教训。针对当时出现的一股所谓“非毛化”的倾向,党需要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所以决议开头认为“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历史,以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因为只是“简略地回顾”,所以对遵义会议基本上是按照第一个历史决议“简略地”来表述的,并进一步总结提出了“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样的名句。
说它“相似”,就是决议都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为“开始了……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和“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一个意思。说它“不同”,就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有所“增删”:“增”,是在“党中央”前面加了“红军”两个字;“删”,即只说到“胜利地完成长征”,以下都删去了。这样,意思也就很完整了。而且当时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资料还比较匮乏。为什么要加“红军”这两个字?因为遵义会议的主题,就是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当时军事问题是第一位的,就是如何带领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的重兵包围圈,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所以,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报告”,内容就是反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长篇发言”,也是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而要解决军事问题,当然必须解决党中央的领导问题。所以,在“党中央”前面加上“红军”两个字,就更能显出遵义会议的主题、伟大意义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问题。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基础上增加的四个新词语和三条新内容,使对遵义会议的表述有了新意境。而新意境,正是由新词语和新内容所产生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注意到了前两个历史决议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当代历史发展,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资料和会议当事人的回忆录等,都已经比较充分公布于世;同时为了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郑重加上了四个词语和三条内容,进一步表述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原遵义会议的历史原貌,笔者认为这是最尊重也是最符合党的历史发展事实的。前两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历史地位,都使用了明确而肯定的语气,即是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就是(说通俗一点)党中央和红军的“第一把手”了。而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表述虽然继承了前两个历史决议的基本内容,但却新加了四条词语和三条内容,即“事实上”确立了、“开始确立”……、“开始形成”……、“开启了”……。第一条词语“事实上”,是对前两个历史决议表述的补正;后面三条词语及其后的内容,都是新增加的,是对遵义会议历史内容的新补充。
对这四个词语,笔者在这里做一下注解:“事实上”确立了,即还没有正式确立,就是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还不是第一把手,但在“事实上”他却起着“第一把手”的作用;“开始确立”……,即刚刚开始确立,还没有完全确立;“开始形成”……,即刚刚开始形成,还没有完全形成;“开启了”……,即刚刚跨出第一步,还要继续前进。正是这四个词语和三条内容,才是对遵义会议最新、最全面、最完整、最准确的表述,使遵义会议表述有了新的意境。而且,理解了第一条,后面三条便迎刃而解了,因为后面的三条是与第一条是相对应的,是第一条的必然结果。
二、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的解读
下面,本文着重对第三个历史决议新增加的四个词语中的第一条作出解读。对于“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事实上”三个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遵义会议在组织上并没有“开始了……”和“确立了……”,毛泽东虽然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但他不是第一把手,按会后的两次常委分工,他的地位是第三把手。我们先来看看遵义会议的决定和会后常委两次分工的情况。
第一次分工:1月18日(即遵义会议后的第二天)上午,总书记博古按照遵义会议“常委中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主持召集常委会研究。研究结果是:博古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闻天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个常委分工情况说明,博古仍然是第一把手,张闻天排在第二位,周恩来排在第三位,毛泽东则位居第四。而遵义会议后的军事行动,虽然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周恩来、朱德则是按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来“指挥军事”的,这正是遵义会议的主题。所以,博古后来说的遵义会议后有个“军事三人团”(不是后来的毛、周、王“三人团”),就是指的毛、周、朱。
第二次分工:这里需要说明为什么要有第二次分工,以及第二次分工为什么能顺利进行。遵义会议经过讨论,明确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李德和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二人在会上受到重点批判。博古在党内特别在军事上已经失去领导威信,不可能再领导下去了;而且当时党和红军正处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之中,如何带领红军冲破包围,是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军事问题是迫在眉睫第一位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博古又不懂军事。所以,遵义会议虽然没有罢免博古总书记的职务,但撤换掉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已经是势在必行;博古自己也觉得这个总书记当不下去了,思想一时也不通,表现得很消极,有点撂挑子。有关老同志曾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有二十多天党内没有总书记。遵义会议上曾提到改选总书记,周恩来、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当总书记。周恩来回忆说:“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么。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4]446周恩来的这个回忆说明有两层意思:其一,遵义会议上和会后,党内、军内大事,“事实上”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改选总书记这样的大事,首先是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其二,为什么毛泽东当时推辞担任总书记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当时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他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领导人,是只相信“国际派”(即从莫斯科留学回来、受过共产国际培训的),而不相信“本土派”(即没有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现在撤换掉一个“国际派”博古,而改换成“本土派”毛泽东,可能引起共产国际和王明的不同意见;将总书记换成另一个“国际派”张闻天,而他本来也是常委,就能够向共产国际和王明交代了。根据当时遵义会议上的情况,毛泽东也明白,由他出任最高领袖的条件还不成熟,还不能得到全体一致的拥护,如凯丰等在会上就公开反对毛泽东,维护博古;博古当时对毛泽东也是不服气的,按博古的本意,遵义会议上是要“批判”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小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也没有当上总书记,他是在会后二十多天常委再次分工时,才在毛泽东提议下,担任“总书记”(当时也称“负总责”)的;毛泽东的第三把手的位置,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这也有个过程。上面说了,遵义会议后,党内有二十多天没有总书记。当然,军事行动不能停止。由于军事上已经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主动多了,虽然一时还不能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但国民党军队也阻挡不了毛泽东的“十六字诀”的运用,再不能包围和消灭红军了。——但是党内总不能没有总书记。如果强行改换总书记,当然也可以。但如果博古能够主动表态辞去总书记职务,然后再推举出一位总书记,那就会主动得多,就更能名正言顺地得到共产国际和王明的认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立了不世之功,他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即劝说博古主动辞职。据博古后来的回忆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和他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既诚恳说明博古确实是不适合当党的领导人,又深刻说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自己为什么真诚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博古听从了周恩来的劝说,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正是这样,2 月5 日中共中央才能再次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分工,博古主动提出辞职,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即总书记);博古按周恩来的意见,退下来暂时接替王稼祥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来由于张国焘的一再反对,博古让出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改由陈昌浩兼任。
这样,按党内常委排位,总书记张闻天是第一把手,军事“负责者”周恩来是第二把手,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是第三把手,博古居于第四把手的位置(因为他还是常委)。毛泽东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但他还不是第一位即“为首”。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第二,为什么又说“事实上确立了……”呢?如上所述,从组织上看,毛泽东确实不是第一把手;但从事实上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的军事决策和党的政治决策上,却确实起着了第一把手的作用。战争时期,军权就是领导权。所以说是“事实上”,而不是“已经”,还因为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还不稳定,他又遭受过三次挫折。
一是博古的讥诮。由于周恩来的信任,和各军团领导人的一致拥护,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军事决策、行动和指挥,实际上由毛泽东提出和执行。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 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制定和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四川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跳出敌人包围圈,建立新的根据地。于是开展了土城战斗——在土城以北青杠坡地区围歼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夺取北渡长江的渡口。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由毛泽东实际负责指挥的。1 月28 日战斗开始,“激战终日,战斗失利”,损失红军上千人。遵义会议后,思想一时还不平静的博古当时曾经语带讥诮地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①指挥也不成”[5]364。这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还不稳定。
二是被撤销职务。3月初,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中央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亦称前敌总部),张闻天提议并决定: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总指挥。说明土城战斗失败后,张闻天、周恩来等依旧信任毛泽东,将红军军事指挥权交给毛泽东。10 日,在苟坝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发动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战斗的建议。会议在要不要攻打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力主不打,但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毛泽东遂以“去就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就是说:你们要打,我就不去当那个前敌总指挥(总政委)。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多数人意见,做了取消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6]174-175。
毛泽东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政委职务,仅一个礼拜就被取消了。这也进一步说明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不稳定,还未取得党内、军内领导人的完全信任。毛泽东并未因此而袖手不管,出于对党和军队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他仍然坚持己见,在当晚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恩来;次日(11 日)晨,周恩来召集中央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终于说服了大家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由于毛泽东的坚持,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三是军事指挥遭到公开反对。毛泽东从打鼓新场事件中进一步得到一条教训: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总是开中央会议由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这样难免会贻误战机,提议成立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来指挥,更利于作战。张闻天和周恩来都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在3 月11 日或1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张闻天提出、经会议讨论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组”,亦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以周恩来为“团长”[7],但在军事战略指挥上,周恩来完全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正是在“新三人团”(毛泽东)的指挥下,3月16日和20日中央红军随即又三渡、四渡赤水河,演出了“四渡赤水”的神奇史剧,牵着敌人鼻子走,使中央红军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避开了敌人的跟踪追击;接着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成功北渡金沙江,将国民党几十万“追剿”部队甩在了金沙江以南,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四渡赤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一段佳话。毛泽东后来自己说:我平生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但是,却由此引起了党内、军内的一场争论。
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的过程中,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部队部分指战员也因不了解敌人动向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艺术,开始有人反对“打腿仗”(指跑路多)和出现不满;甚至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也有意见,反对毛泽东的“兜圈子”、与敌人捉迷藏式的指挥,责备使部队来回走了不少冤枉路,还说打鼓新场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即是说,如果攻下打鼓新场,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林彪公开写给中革军委的信中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弯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还行?”意思是说:行军打仗,应该多走“弓弦路”(直线),不应该走那么多“弓背路”。因此,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8]198。因为战斗紧张,对这些问题不可能及时展开讨论。渡过金沙江以后,红军得以在四川会理休整5 天。长征途中红军从来没有能在一个地方休息5 天。5月12 日,张闻天在此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统一了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讨论渡过金沙江以后的行动计划,并着重解决前一阶段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特别对林彪的那封信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发言批评了林彪。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5]353张闻天在报告中也批评了林彪的这一错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博古的态度也有了较大转变,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博古此时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完全服气了。会理会议统一了党内、军内的认识,维护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和党内的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的反对,未能撼动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反而助推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前进了一步。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以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都是毛泽东指挥和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因周恩来病重,不能工作,8 月19 日在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常委分工等问题,第一次明确:“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并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中央常委会每周至少开一次,以发挥常委会的作用[4]467。而随后长征途中的中央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上,大都由毛泽东作军事或政治问题的报告:按党内规矩,这说明毛泽东事实上起着常委会核心的作用,特别是对张国焘的斗争策略,基本上都是由毛泽东提出而由中央决定的。
沙窝会议只是临时分工。1935 年10 月19 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27 日在吴起镇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部队工作、行动方针及常委分工。关于常委分工,会议同意张闻天提议方案: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政府工作。这个分工是第一次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则成为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助手”。这样,长征结束后,军事上“毛正周副”的格局就正式形成了。但是,按照中共党内的规则,常委会决定的事项,还须政治局会议通过,才算最后决定。
1935 年11 月3 日,中央在陕北甘泉县下寺湾边区特委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中央对外名义及中央组织问题,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并提议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成员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他们全权决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和军委后方办事处,统一由周恩来负责。”[4]484这样,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毛泽东正式走上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岗位。当然,中央总书记还是张闻天。就是说,从组织上看,毛泽东还不是党中央第一把手。毛泽东成为党中央第一把手,是后来经过1938 年10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3 年3 月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过程才算正式完成了。
三、对“开始确立”“开始形成”“开启了”三条词语的解读
说清楚了第一条词语,下面三条词语就顺理成章了。当然也需要做些解释:正因为有了第一条“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当然也必须把以他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开始在党内逐步确立,第一个历史决议中说“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这个“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在党内得到逐步的实施,到党的七大正式完成。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才开始形成。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政治上成熟的领导集体(毛、朱、刘、周、任),是在延安党的七大时正式形成的,而遵义会议期间,这个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已经都是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了。至于刘少奇,是在1937 年5 月白区工作会议后,才开始进入毛泽东的视线;而任弼时则是在1938 年3 月政治局会议和10 月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1943 年3 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和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三人书记处,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如此,刘、任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也才得以开启。所谓“开启”,是刚刚打开了踏进“新阶段”的这扇大门。
第二个历史决议和第三个历史决议提道:“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阶段”,就是说,遵义会议的成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随后才逐步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走上新阶段,这个“新局面”和“新阶段”就是:正确地领导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至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也正是毛泽东所说的:“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9]150
最后,笔者还想说明一点,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新加的“事实上”三个字,也是笔者多年来,即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不仅在笔者的文章、著作中,还在多次有关学说研讨会上的发言中,都曾经作过表达。仅举两例:一是笔者和马齐彬、刘文军(由笔者主笔)合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一书中就强调说明: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理论和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0]545;二是笔者的封笔专著《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泽东的奋斗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年版)一书中,还对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确立了……”及“以后各种史书均持此说”等,专门谈过“一点不同意见”,即“我认为这个定论不十分恰当”[11]583,并提出:“我的意见,是否可以这样表达: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常委,军内是第二把手。而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党内生活的历史上以前是没有过的。”[11]
注释:
①中央苏区时期,“左”倾中央指责毛泽东的游击战战术思想为“狭隘经验论”,给毛泽东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