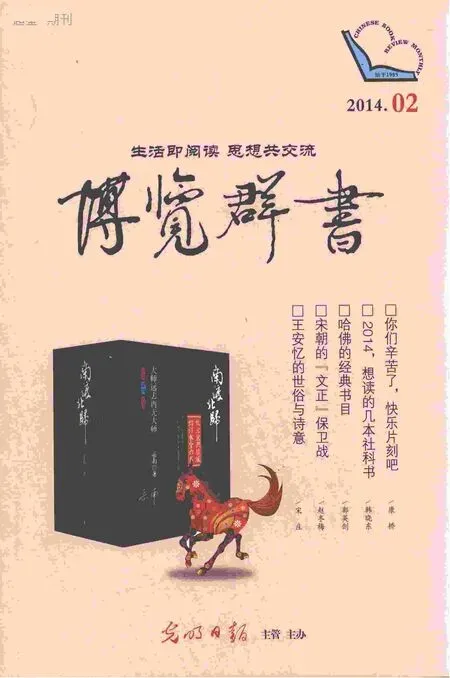向商鞅变法问“使民之道”
李琪
商鞅变法是一场应时而生的变革。当时秦国内部“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韩非子·奸劫弑臣》),外部又有邻国威胁。秦孝公广求贤者,而商鞅以霸道之术说之,为秦国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商君书·更法》开篇便明确变法是为“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即在考虑到战国时期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风气下,整顿秦国法度,寻求统治民众的方法,以达到强秦之用,为征战做好准备。
在商鞅看来,统治民众的最高境界是“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商君书·农战》)。要达到使民如臂使指,商鞅提出应当抓住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由君主借助名利与刑罚来引导民众,使政胜于民。人们长久生活在明文法令下,将之内化为行为准则,自觉遵守维护法令,国家才能富足强大。为此,商鞅在变法时着重从人口、行业、社会风气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加强秦国对民众的统治。
战国时期,拥有更多人口就等于有更多战士、劳力、税收来源。人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资源,农战强国框架也需要充足的人口填充。
商鞅对人口的管控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通过户籍掌握人口增减、流动情况,“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在户籍管理基础之上,又设立什伍连坐制,令民互为监督;二是致力于增加人员数量,包括对内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史记·商君列传》)政策,对外招揽三晋民众等。
从秦国统治层面而言,户籍制度自秦献公时期推行,后又经商鞅完善,已经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国内人口变动情况,为拟定相关政治、经济政策做好准备。同时,配合“废逆旅”“声服无通于百县”(《商君书·垦令》)等规定,将民众基本束缚在固定范围,避免了人口大幅流失、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不匹配、偷税漏税等问题,集中人力发展农战。什伍连坐制的实行又加强了民众基层自治,加上商鞅推广普法教育,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家机关的治理压力。此外,分户政策以增税为手段,半强制性将家族分裂为若干小家庭,促使个体小农经济发展,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从秦国民众层面而言,户籍制度使得移民、经商活动受限。什伍连坐制使社会转向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局面,互相检举揭发表面上看起来如商鞅所言“任奸则罪诛”(《商君书·说民》),内里却由于破损伦常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导致生活暗流涌动,并不稳定。此类法令只适合短期見效使用,不适于作为长期国策。不过,如果只有负面作用,那么民众的不满情绪溢出并不利于统治,因此兼顾利好才能令其产生与秦国间的黏性。在人口流动频繁的战国时期,秦人能获得的好处包括但不限于耕种的土地、晋爵机会、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等。
孟子曾论述过“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有恒产方有恒心,只有满足基本生存条件,民众才有余力参与国家建设,因而农业正是战国时期各国都视为本业的重中之重。但仅国家重视是不够的,还需要百姓自发投身农耕而非其他行业。《商君书·算地》中谈到民众天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又说“国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针对尚未自觉形成农本意识的民众,商鞅通过赋税、赏罚、打压其他行业等方面进行引导,令其只能从农耕谋求生计,逐渐安于农而喜于农。
商鞅变法中有若干土地政策,如“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战国策·秦策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商君列传》),“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食货志》)等。政策总体上围绕土地占有制度展开,允许民众买卖土地、开荒耕作,所得除上缴赋税外均可自留,极大调动了民众积极性。赋税方面,商鞅采取双线并行的方法,普通百姓訾粟而税,缴纳数额与当年国家标准亩产,以及该户拥有的土地数量、亩产挂钩;贵族以“食口之数”缴税,以此迫使他们遣散门客从属,从而解放更多人力资源到农耕事业上,正能补足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开垦不佳的状况。
鼓励、优待务农的同时,商鞅对其他行业极为抵斥,认为不愿吃苦、投机取巧的人太多会使国家亏空。《商君书·垦令》中有“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的提案,从商的经济压力远大于务农;有“壹山泽”之法,统一管理山林、湖泊,禁止随意狩猎捕鱼;“重关市之赋”,打压工商业。又如“废逆旅”、不得随意迁徙等法令,对行商者多有限制。另外《史记·商君列传》中有“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记述,经商致贫有全家变成奴隶的风险。商鞅从民众温饱需求出发,将变法重心定于农耕,又封堵其他谋生方式,民众在综合考量各行业利弊后很容易产生农耕是最好选择的想法。同时,打压商人、游士不仅能解放更多人力到农业中去,还会减少不必要信息交流与传播,让已经务农的人不再生出其他念想。
秦国由改革农业措施而提高了生产水平,改变了原本多畜牧而不重农业的风气,为此后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众在秦国得到了安稳的环境,在乱世中也的确是值得欢慰的事。不过,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从精神上对民众灌输国家意识,降低或消解个人意识,再在实际生活中切实给予惠利。民众普遍缺乏教育,信息闭塞,而安于农耕,自然质朴顺从,也就成了商鞅理想的、便于引领的样子。
战国时期的秦国兵农一体,《商君书·外内》有“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的评说,农与战正是商鞅变法的两大核心要素,也是为民众求生存、求名利而铺设的两条既成途径。《商君书·赏刑》:“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对秦国任何人而言,都唯有上战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同时《兵令》写到,若有敌人来犯,要马上整理簿册发出征兵文告,人人都有出战机会。
《商君书·画策》:“能壹民于战者,民勇。”然而战争随时有丧命危险,如何让人舍弃生死之忧而勇猛杀敌呢?商鞅建立的军功军爵制给出了答案。总体看来,秦人参战机会较多,且奖励丰厚,“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商君书·境内》)。爵位带来尊荣的地位、优渥的物质条件,甚至有专配的仆从,爵位高的人还有审判爵位低的人的资格。再加上参战者都有可能获得爵位,与家境、身份毫无关系,还有可能破除森严等级壁垒,带来社会阶层流动,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是极具驱动力的。军功军爵体系又不同于从政为官体系,也不会招致贵族的强烈反对,对新兴地主阶层而言也是提升地位的好方法,几乎称得上是共赢局面了。《荀子·富国》:“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从务农生活到名利双收的爵位,无疑是巨大的诱惑。秦国需要的也正是骁勇善战的民众,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由此得以一致。
在用名利鼓动民众积極参战的同时,商鞅也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史记·商君列传》),对内刑而对外赏,“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商君书·战法》)。由此,秦国在原本就尚武的风气上形成了以战为荣、闻战而喜的价值观念,就连士兵的家人也会劝勉他们英勇杀敌、获取军功。不过爵位也不是容易拿的,违背军令会有严厉的惩罚,且军队中也设有连坐制,“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战及死吏,而轻短兵,能一首则优”(《商君书·境内》),杀敌的功劳不一定抵得过队友死去的罪名。有的爵位层级晋升要斩敌首几千,普通士兵很难达成要求。
《韩非子·定法》中有对商鞅军功军爵制弊端的评价:“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这是中允的,商鞅此法在秦国取得的功绩不可置疑,但仍有缺陷。全民皆兵、人人为爵的趋势使得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占据优势,然而以农战为导向的政令会相应减少其他行业人员,即便是没有受到压制的行业,人们也较少将之作为生计选择。
《商君书·算地》:“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法令得以在全国推广普及的前提是所立之法符合国情,而商鞅变法正是从秦国问题集中的地方着手施行。商鞅所制定的法令与现今社会所说法律是不同的,总体仍旧是以刑为主,普及法治也是有刑罚作为保障。在商鞅看来,“法详则刑繁,刑繁则刑省”(《商君书·说民》),同时要保证“法令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如此才能使民畏惧,而不以私利妨害国法,养成令行禁止的习惯。
为使民众自觉遵守法令,让他们知法懂法是必要的。《商君书·定分》对如何普法有清晰的说明,其中与管理民众直接相关的措施为:在各郡县设立法官,标准参照国都,百姓和其他官吏都可向他们咨询法令内容,所咨询问题将被记录下来,如果答错将受到相应惩罚。如此一来,“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商君书·定分》),一套方法同时监管了官吏与民众,双方都难以藏私。民众知晓懂法有益时,也自然会对学法产生兴趣。此外,“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商君书·说民》),国家要提高治理效率,以法为教也无疑是上佳的方法。
在民众社会地位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能让他们凭借法令维护自身权利,甚至于监管、反对官吏的不当行为,算得上是突破性的进步。尽管法的有效对象受时代限制,无法将国君、储君等纳入,商鞅依法治民的目的仍是为了让民众顺从,便于统治。但是,以法为教实质上维护了法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支持了法律权威性,确实为民众提供了权利保障。并且,商鞅在秦国展开的一系列普法行动有较为完整的体系与方法,在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现在依然值得重视。
《商君书·修权》讲“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国家治理的根本是为了天下黎民。商鞅作为战国乱世诸子之一,又何尝没有救世之思,但在实践过程中,民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而是先抟聚民力发展国家。他的使民之道就本质而言,是以统治者意志为主导,变革统治方式,提高效能,让民众自我管理、为国奉献,以此更快达成国家霸业。
商鞅的治民理念在实践中证实了效用,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民众已然接受变法,甚至于自发拥护支持法令。究其原因,商鞅变法中的土地政策、军功军爵等内容带给民众相对稳定的生活与提升阶层的希望,法令严苛之余也使得社会环境趋于稳定,无怪乎得到支持。
当然,他的使民之道也有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诸如连坐法、“民愚则易治”(《商君书·定分》)的愚民及弱民等思想,“把所有人的心灵与行动都严格管束起来”(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违背人道精神,缺乏对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这些都是要批判的,应当辩证地看待问题。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