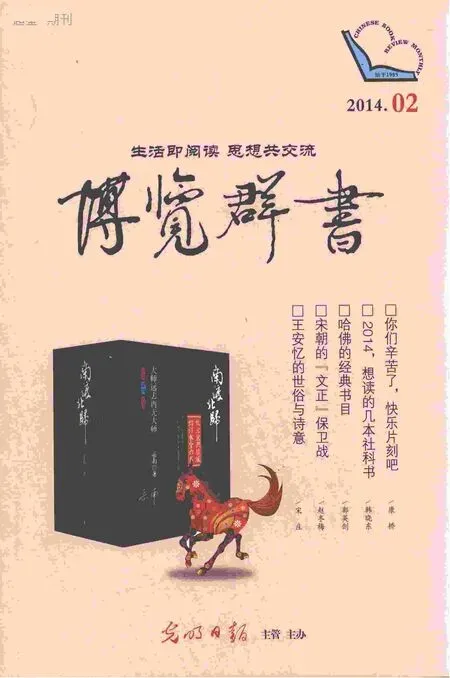与《马桥辞典》共品“表达之饿”
凌子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之基本需求无外乎衣食住行,其中温饱问题便是重中之重,原始人类可以衣不蔽体,但不可缺粮。这粮也分物质之粮和精神之粮,“仓廪实而知礼节”,酒足饭饱,便觉表达之饿,表达之不足,便觉精神之饿,社交之饿,理想之饿。
《马桥词典》(后称《词典》)的诞生便与这表达之饿密不可分。1999年8月,当韩少功在海南《天涯》杂志被问到为何用方言串联小说时,他明确地表明,在阅读逻辑严密、有主导情节的小说时感到的“饿”的状态:连成一片、榫卯精巧的文本即使是读上几十页仍觉不饱。在国际华语纽曼文学奖授奖晚宴上,他再次强调了文学真实的模糊性,“文学总是有一幅多疑的面孔”,为了“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更多可能性开放”,需要展现“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
出于完满真实的情结,作者认为小说的不完满、断裂、无序感才更能在知觉上带给读者自行觅食的能力,让他们大小不同、弹性各异的肚子有饱腹之感。为了实现“真实”的自助,他借鉴了古代绘画的散点透视和笔记小说的散文形式,把《词典》写成了以方言为骨架,笔记为肌理的小说。“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乱舞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果说瞿秋白是在精神的饿途中迷茫,在实践的花火中寻找到希望,韩少功则是以方言为药方,要在日渐脱离生活、语言系统化和结构化的小说大厦边建个奇形怪状的小楼,让读者在两相对比中,开始警惕关于现实的种种定见。
《词典》这部以地域方言为载体的词典体小说诞生在湘楚之国——这片湿热、巫史文化盛行的浪漫土地。韩少功认为,他笔下的方言虽亦真亦幻,但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也符合语言学规律。大抵是为了弥补官话遮蔽的部分,他在文中说道:
一、 方言是广义普通话永远无法照亮的黑夜,例如嘴煞气、白话等;
二、 时代更容易造成语义较难翻译的语言群落,例如,懒;
三、 即便超越了地域和时域的语言屏障,共同语言也永远都成为人类一个十分遥远的目标。
由此可见,韩少功认为“词本是有生命的东西”,是人类丰富生存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与崔卫平对谈时多次提到,《词典》的许多情节来自知青经历和语言研究。书中的大部分人物都真实的存在过,方言区的读者还能凭经验敏锐地感觉出文中的词语来自湘方言中的哪个片区。除此之外,作者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明末清初到20世纪70年代间马桥村的几次重大变故,从称呼江西人为“老表”的故事出发,以“莲匪”血案后“十万赣人填湘”影射了马桥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衰败凋零的处境,从而将方言和历史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让读者觉得充满戏谑却又那么真实,更是表达了作者对有着百年苦难史的马桥方言的珍视与对其脱离现代文明而不自知的无奈。
在这部写作历时十多年的作品中,韩少功向我们讲述了马桥村繁荣、革命、失败、衰落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思绪随着方言词条的转换不断跳动,奇特的时空交错,神秘的宗教文化,不可思议的乡村公约等现象一一展示在读者眼前。不管韩少功是否承认,《词典》写了一个寓言——围绕着方言的命运,马桥村乃至中国南方边陲小镇、整个中国乡村内部都将在“现代”来临之际面临的走向衰落的危机。
从当时的文化语境来看,这种“现代”是经济全球化的隐喻,对衰落的描述和方言的自主意识体现了作家对失语的焦虑。20世纪90年代,大陆先锋文学对翻译问题及书面语的模仿,当代作家对外国作家的追捧已成偏执之势,如同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区隔,中文和英文、地方与世界之间也逐渐形成等级,这也很容易让人认同李锐对方言合法化的倡导:
在这样的网络时代,在这样的处境中,抗拒格式化,抗拒“中心语言”的霸权强制,坚持方言的独立性,重新审视方言的价值和意义,并确立语言的平等,是文学,也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李锐:《网络时代的方言》,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P44)
这样的评论在当时文坛不胜枚举,我们大可通过小说中的细节和论述,把方言问题上升到民族国家、全球化与地方政治的高度,对作品的主题进行一番解读。然而这种阐释的漏洞在于,无论是从写作意图还是社会主题出发,对文字的解释,都是一厢情愿的,对马桥的理解,应该从马桥自身出发。
马桥世界里的方言是饥渴的,当我们受作者影响,带着他想要“为马桥每一处地方立传”“用语言强有力的干预世界”的有色眼镜看待小说时,所得结论常常是带有偏见的,这些偏见不仅来源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也有意见领袖的影响。事实上,当我们平心阅读作品,便可发现,与其说作者对方言的起源、用法、流变的处理都来源于他个人的生活經历,不如说他是要借马桥的一草一木来表达他反对抽象化的语言观。这表现在《爸爸爸》及《山南水北》等诸多之后的作品中,方言常常和生活有更近的距离,即使其间掺杂了其他语言,那也是自己抓着自己的毛发想要逃离地球,它的根依旧是扎进泥土了。于是,我们在韩少功的作品中时常发现,哪怕革命、科学、电灯已经驶入了马桥,村民们依旧能用自己的感官体验让它们“马桥化”,他们把科学说成懒惰,把飞机称作大鸟,无论革命如何变换,大家的生活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方言的意义并未因作者的阐释而变得确定,相反,它脱离了标准化的序列,变得令人怀疑,所谓的渴,成了在思辨和统一断裂处的生机勃勃的剩余物。
试想一下,当你第一次看到《词典》这本书时,是如何期待它的?一本语言指南?地方志?然而当真正打开,笔者才惊呼受骗,哪里是地方献志,分明是披着方言外皮的心灵传记。
在乍一看规整的词条下面,解释常常摇摆于个体经验与集体认知之间。在对词条的意义进行阐释后,叙述者又自顾陷入怀疑之中,村民的回忆是否有其他版本,口述中的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过?不仅在事实层面,在叙述上,作者常常煞有介事地看似要论证某一词条,但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常常残缺,反手记载了一路人、村口小儿的闲言碎语,并从此敷衍,遐想连篇,似乎回归了“小说”在古代道听途说的本义。
这样的呓语被韩少功称作人类童年的思维,小孩子总以自己为标杆,说话做事总以为别人跟他一样,也不讲究个前因后果,“我认识的人你怎么可能不认识?”韩少功把从小孩子那里受到的教育用在小说中,人物出场没有什么铺垫,到第二次出现时人们才意识重要,返过头看时,文字又如此轻描淡写,好像叙事者认识这个人,读者也必须和他们天生认识一样。韩把这种合法性归因于更高意义上的“真”,在《白话》中,他写道:
不仅是小说,所有的语言也不过是语言,不过是一些描述事实的符号,就像钟表只是描述事件的符号。不管钟表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塑造了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时间,但钟表依然不是时间。即使所有的钟表砸碎了,即使所有的计时工具都砸碎了,实践依旧会照样行进。因此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语言也是严格意义下的“白话”,作用不应该被过于夸大。
语言和事实关系的表述在韩少功小说中俯拾皆是,《飞过蓝天》《回望茅草地》《女女女》《爸爸爸》《暗示》《日夜书》,哪怕是散文《革命后记》里也能看见这样的影子。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韩是将存在放置在语言之先的,他时刻将表现真实作为文学的第一要义。因而当发觉晚清后的白话文学在技术上向西方靠齐,而和中国的精神图谱日渐疏离时,他表达了深切担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放弃了部分方言叙事,转而以大众能读懂的标准书面文字来承担小说的叙事功能,这也使得《受活》《爸爸爸》之后的作品显得不再怪诞。但是这种深层融合的尝试毕竟烙印着作者深刻的心灵碎语,于是,小说中既有“唱完了国事就唱家事”的发歌,也有要“肩锄头”“积凼粪”“浸禾种”的公社,还有“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的马鸣,他对方言的刻画并非寻求一个纯粹的地域典型,更多的是在尝试描绘世界的各种角度与生存的各种可能。
可以说,此举无论有心无心,方言问题已不再是地方与全球、方言与普通话等单纯问题,其背后是对人类物欲的反抗和精神缺陷的深切忧思。但与其他方言作家不同,韩少功并不认为这种语言的驳杂性是一种亟待规范的社会问题,相反,他的视野更加深远,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造成这种宏观的、哲学思考的,是他对人生的宿命感和轮回感的体悟。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对“永恒轮回”做出了经典分析。他借恶魔之口,宣称“生命中所有无以言传的大大小小的事体”都必将在人们身上重现,他预言这种西西弗斯的痛苦将作为最大的重负压在人们的行动上面,而生活则不能比这最后的永恒保证更多的东西(尼采:《快乐的哲学》,利科版《尼采著作全集(第3卷)》,P571)。韩少功提取了“最大重负”的表述,在答崔卫平语言功能时说“语言是负担事实重力的跳高”,并提出历史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时间观。在马桥方言中,完和元的读音是相同的,这暗示着在坚持完和元分离,还是完和元合一问题上,韩少功站在了后者立场上,所谓的历史是“一个永远重复的圆环,他们是不断前进的倒退,不断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劳”,这让人不禁联想到本雅明在《历史的概念》中为保罗·克利的《新天使》所做的解释:
他把脸别过去,面对着往昔。从那里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只是一连串事件,从那里他所看见的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无休无止的残片层叠在残片之上越堆越高……他大概想要停留一下,把死者唤醒,并将那些打碎了的残片凭借恢复起来,然而从天堂刮来一阵暴风……暴风势不可挡地将天使吹往他所背向的未来,与此同时,在他面前的那片废墟则堆砌得直通天际。(《历史的概念》,载《上海文化》,2014年9月,P85-90)。
在西方传统中,有关过去的探讨都能梳理出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在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名字:基督耶稣、亚伯拉罕、奥古斯丁、尼采、海德格尔、歌德。“过去”的源头在犹太-基督神学的语境里便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种反逻辑的循环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小说中非常普遍,阎连科、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试图超越语言的纯形式实验,把语言当作生活的纵深,用吊诡的时空和它的不可思议来反衬现有伦理、权力、制度的局限。可以说,韩少功就是这个队伍的一员,他眼中方言有种似于“弥赛亚”的神秘力量,它或隐藏于“先人遗落下来的零星言词”和“巫公符咒”,或遁匿在“梦婆的癔语”之中。似乎只有一点“觉”意(睡意),两点“宝气”(稀里糊涂),像风月宝鉴般自照出精神缺陷与欲望,不致让才智变成了荒唐、勤奋铸成了过错,热情造成了罪孽。
在马桥人眼中“苏醒就是愚蠢,睡觉倒是聪明”,这点昏昏沉沉成了韩解决饿的药方,他认为饿的真正病因在于语言规范系统对个体情感与经验的磨灭,这种抽象性由间接造成了小说的离地。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让小说回归个人,让个人主体性充分显现。但是,这一问题在于,作者的野心很大,它希望用记述的形式,哲学的内核去表达他的一套混融的语言观、世界观,因此使用了大量议论和哲理式意见,使得《词典》中的村民成了他棋局中的棋子,村民生活始终和他的思考之间存在着距离,读者刚刚逃离传统小说塑造的牢笼又掉入了作者编织的意见中。在这两者之间,缓下步伐,是否能启迪更丰富的历史、存在、自由的想象?
正如崔卫平指出的,这部小说并非用方言语音写成,马桥人的发音仅仅提供了一个想象力的起点。方言本身在小说里是残缺的,作为“过去”,方言无法将历史原貌还原于眼前;身处“当下”,方言又被各种话语裹挟,每一种阐释都是自圆其说,每一个立场又相互矛盾。作为抽象、共时的文化产物,方言的合法性随时随地的在小说中遭到质疑,它在一开始便不具有和具体的物质对象世界精确的映射关系。然而,借助方言来表现不可能表现之物本身的悲剧性本身能带来我们对手握之尺的反思,“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停下来”,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这一张张面孔避免在马桥土地的沉陷”——显然这里的方言既是真实展现的场所,又是真实叙述的掘墓者。
当一连串的事件在小说中展开,正如本雅明批判的历史主义及兰克等编年史家所倡导的那种“事无巨细”,(《历史的概念》,载《上海文化》,2014年9月,P84),一场历史的分崩离析也就降临了。于是,“马桥最后成为一个无,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个世界里已经坍缩的部分”。这一方面是和村民自我意识缺乏有关,他们在韩笔下常常是充满野性的生物,有故事、有生活的烟火气息,但缺乏思想。同时,自省在韩看来也是有隐患的,像《修改过程》《日夜书》里的知识分子一样,叙述者有创造性、跨越性的视野,但像被命运遏住了喉咙,无法呐喊,常常处于失声状态。这也许与知青经历不无关系,但也使得他们在主导者位置上重新规整记忆时常常陷入困境:一方面,他们想要唤醒感知、想象力与野性思维,但重新整理骸山的愿望又常常以增加更多的残骸为终结,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超乎作家所能承载,他们缺乏力量,同时又被裹挟在历史旋涡之中,任何叙述只能改变有关真实的话语形态,却无法触及真实本身。
因而笔者认为,要想用言语召唤心灵,第一要义便是自身拥有强力意志和对生活深切关怀。在阅读《词典》时,笔者常常感到作者与作品世界若即若离的关系。韩对语言的归纳是基于经验的概念思维,他在评论时常常显露出西方非理性和思辨传统,而这与马桥人的直觉和经验的象思维是相悖的,马桥人用“晕街”“闻到汽油就呕吐”来描述现代城市化,用“长沙大会战那年”“张家坊竹子开花那年”来表述1948,作者在描绘一个“拒绝科学家的世界图景”的同时,也重新片段记忆组织了一套有关马桥世界新的逻辑关系。
尽管如此,《词典》仍对我们有所启示,作者对马桥世界冷静的白描展现了存在之真,而这点“真”对于生存在贫困边缘的马桥人而言,只能是存在性的,他们生活的一张一弛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出现又消失。语言留下的残迹需要作家们、历史家们、人类学家门不断地理解、演繹,才能具有新的认知和审美形式,然而当语言通过新的形式被组织起来时,它就与“真”原发的场所相距甚远了。这点悲剧性颇有点佛家万法皆空的意味,距离中国本土哲学的“象”远,与“念念说空,不识真空”(《坛经》)之“相”近,使得它又多了些空幻和迷障感。
于是我们不禁感叹,在填充语言真实性的饥饿游戏里,饿了谁,又充了谁的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