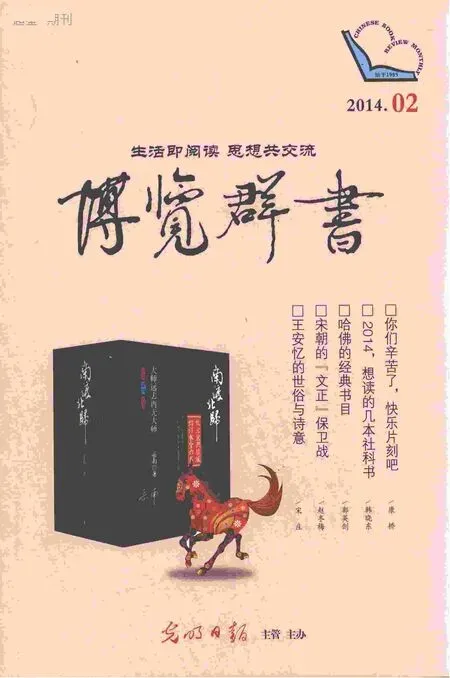对动物傲慢意味着人类的灾难
林科吉
美国学者博里亚·萨克斯的《神话动物园》一书,为我们介绍的动物将近百种,包括空中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细分为18个类别,汇集了神话、传说与文学中的动物故事,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精彩纷呈、饶有趣味的堪称“文化动物学”或“象征动物学”的专著。
人类生存于自然环境中,组成这个环境的除了东、西文化公认的宇宙基本元素如地水风火、或金木水火土之外,恐怕跟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动、植物界了,它们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基本生存之所恃、所需。相比而言,动物更是跟人类相伴相随、相助相依,它们充当过人类的祖先、兄弟,也是人类的亲密伙伴与忠实助手。初民社会崇拜的图腾大多是动物形象,特别是那些庞然大物,总是令人敬畏,中国古典文献记载有“铸鼎象物”之说,意即在青铜大鼎上铸塑神圣之物的图像,掌握了神物的图像,就控制了此类物种的能量,“象”与“物”的“原型”即神圣之象和牛,该著中提到的熊、狮、猪、鹿、野牛、老虎、豹子、大象、河马等,也都因为块头巨大,拥有令人惊异的力量和速度,与之相比,人类往往感到自惭形秽。在原始分类观念中,人们常常将这些动物与人类划为同一个种类,而且动物是长兄,人类则甘当小弟。中国古人崇拜的“四灵”,代表的是各自类别中的最高典范和“老大”,人类中的圣人与之同级,具有同等的象征价值。但是,并不是说那些小小的动物就会被人们轻视和忽略,其实它们自有天赋异禀和神奇之处,都拥有令人羡慕的神秘力量,如公鸡召唤太阳,燕子带来春天,青蛙是雨水的使者,蝴蝶则是再生的象征,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动物共同形成了人类的世界,虽然达尔文早就告诉我们,猿猴才是人类的亲戚,但是在人类的感觉里,远亲不如近邻,人们对身边的动物感到亲切和亲热,比如我们视之为家庭组成部分的“六畜”,以及房舍周围的蜘蛛、蜻蜓、蛤蟆和蟋蟀等,已经完全融入人们的饮食起居和情感思维,它们与人类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共栖环境”。
地球的年龄长达40多亿年,地球上生命存在有35亿年以上,人类的出现也有200万年之久,在这样漫长浩渺的宇宙时间里,各种生物最终使地球变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仰观俯察,宇宙之大,品类之盛,经过自然大化繁衍出了万千生命形式和样态,人类作为其中的一个种类,与之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正如每一种动物都有各自喜好的食物,都有其搭窝筑巢的特殊材料,及固定的疆界,有它们自身的生命成长的周期、节律等,其天性模式是经过精确的调节而获得适应的。人类同样依其性命,与环境的时空协调、合拍,并与他周围的生命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这样方可尽力扩展其生命的幅度。我们必须在各种生命的联系中,才能参悟人类自身生命的本质;只有当我们深刻体察到自身的动物本性,生活才会更加踏实。
宇宙大化至为神秘莫测,众人只知其然,但圣人能知其所以然。《文心雕龙》云:“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虎豹,云霞草木,皆天地之文,圣人静观默察,正是通过为诸物立象,才“有以见天下之赜”,最终领悟到自然万物的幽深微妙。圣人的工作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进行协调,将自然事物予以人文化、象征化,而又不伤害其天性。人类学家、神话学家一般都会承认,人类是处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动物,像荣格那样的心理学家也发现,理性只有跟本能相协调,一个人才可拥有完整的自性。有理由相信,人类最早的智慧并非通过近代哲学家所谓的“我思”而获得的,而是在对身边之物的观照和模仿中逐渐有所领悟。因此,可以说动物发挥了最早的人类“镜像”的功能,我们在青蛙身上看到了多产和丰沛,在野猪身上见到了勇敢和刚烈,知了和蟋蟀的弹奏使整个秋季渗透了诗歌的韵味,鹰类意味着沟通天地、阴阳和生死……这些都是人类想要拥有而又缺乏的能力。马文·哈里斯曾提到有些动物比如猪、牛等,对于人类来说不但“好吃”,而且“好想”,它们的肌肉可供人类的肉食所需,皮毛供我们御寒之用。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通过它们建构了自身的文化,它们不但满足了人类的生物性需求,也通过象征意象参与到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如果我们要问:一种文化为什么在不可胜计的事物中,偏偏拣选出某些特别的种类作为表征符号?细读《神话动物园》也许能找到理解的线索。
人、动物与其环境,共享同一个生命网络,共处一个生物系统,现代人类非常傲慢地将自己置于生物链的顶端,这其实是一种灾难性的观点,人类拥有的能力确实变得越来越强大,但也变得越来越恐怖,如果我们将其他一切生物都划分为食物与非食物、可吃与不可吃,这样极端的二元对立,许多动物就会因为对人类“无用”而被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一种动物、一个物种就代表大自然的一扇生命之门,“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化生,生生不息,当人类将一种动物赶尽杀绝,也就意味着这个地球上有一扇生命之门对我们关闭了,当地球上只剩下人类时,也就代表所有的生命之门彻底关闭,这将是一幅恐怖的景象。
阅读这本著作,不禁令人想起弗雷澤及其《金枝》,因为材料收集范围从西到东、自古及今,涵盖了神话、传说、童话、小说、诗歌、戏剧,乃至科学调查报告、宣传画、早期印刷品、卡通、影视作品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研究难度超乎想象”。文学人类学研究也正是提倡用这种方法研究神话:不但要求全球视野,还要有广泛的收集、海量的阅读与深刻的沉思。最后,除了感谢作者带给我们如此丰富和有趣的动物象征知识外,也还有略感遗憾的地方,作者虽然偶尔也有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动物形象与故事,毕竟只是蜻蜓点水,比如熊、猪、燕子等这些动物意象,在中国传统中应该潜存着更加精彩的、更为深邃的文化信息。相信《神话动物园》这本专著作为开端,可以启发中国文学人类学者在此主题上有更深的发掘。
(作者系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