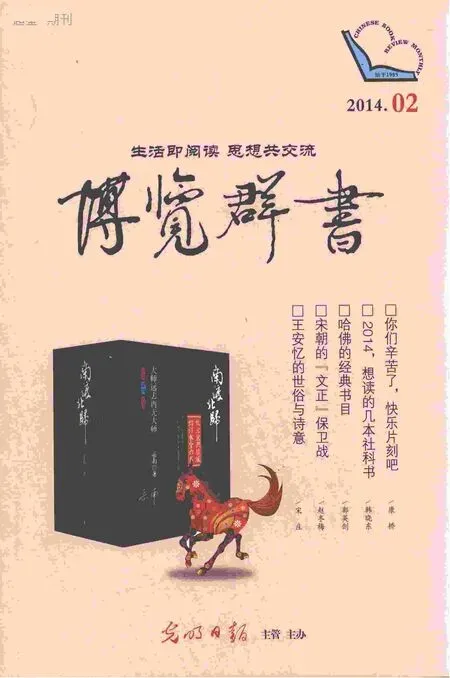刘亮程的《凿空》为什么不够“新疆”
高竞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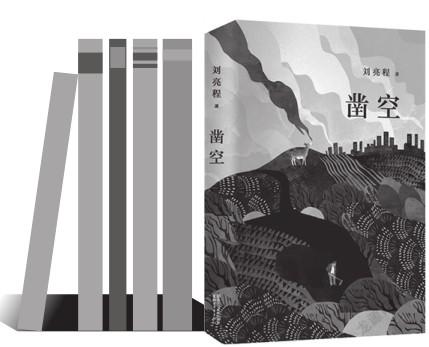
“你会说新疆话吗?”
这是生长在乌鲁木齐的我去北京上大学后,常被问到的问题。作为说“疆普”的汉族人,我每次都热情而有点尴尬地解释“我们平常就是这么说话的呀”。后来才意识到,不少人对“新疆話”的预期其实是维吾尔语。
这种对说话不“新疆”、长相不“新疆”的小疑问,让我意识到家乡话的丰富和复杂,校仲彝就在《新疆的语言与文字》中说新疆历来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字的地区。而我们的生活体验——新疆汉语方言比较接近“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应该没有大错,有“权威”为证:《中国语言地图集·官话之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划分出了北京官话北疆片、兰银官话北疆片、中原官话南疆片、未调查地区。也有类似的学术定义:
新疆北疆汉语方言属于在甘肃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兰银官话。它的词汇系统的来源内容丰富:有从西北其他地区方言中吸收的词汇,还有借自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词汇。(张慧慧《新疆北疆汉语方言词汇来源及特点探究——以沙湾县为例》)
另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方言”不仅指汉语方言,还指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我们可以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把汉语按地域分为方言与普通话,但在多民族和多文化交融的地区,则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主体和语言的多层级概念划分,而且多种语言、方言往往互相动态影响。
因此,“新疆话”“新疆方言”成了笼统的、想象的语言,有的“丫头子”“儿娃子”在自媒体上干脆称其为“新疆土话”,推出“搞笑科普”,但随着热度消退,离疆日久,或停止更新,或悄悄转型,褪尽“土味”和地方色彩。实际上,新疆因其位置偏远和经济文化有待发展,而成为“地方中的地方”,尤其像《凿空》中的龟兹县阿不旦村,几乎是与“中心”断绝的边缘飞地。其实若从字面的地名上看,古代的龟兹和罗布人的阿不旦村早已消失,这使这个关于“挖掘”的世纪之交现实故事有了渺远的历史纵深。
总之,这番略显冗长的铺垫不仅是为了解释后文新疆作家刘亮程为何不太“方言”、不太“新疆”,也是我试图解答自己的困惑。问题落在“方言”这一聚讼纷纭的概念上,这个“地域的声音标签”已显示出语言、地域或许也是一种现代化逻辑下的建构。
“黄金钩子西风腿”,这是刘亮程在《虚土》中说的一句俗语,意思是人的屁股(钩子)比金子还沉,一坐下就不容易起来。与它对应的是追溯西风的脚步。这句话提纲挈领地暗示了《虚土》中的生活史:二十来户甘肃人从埋满死人的老村子逃荒出来,走了几千里到新疆种地,他们在沙湾县的一道梁上被虚土“陷住脚”,精疲力竭,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虚土庄。同时,它浓缩了刘亮程本人的进疆经历,他系列散文中的“刘二”就是从甘肃金塔县来到新疆沙湾县的黄沙梁村,在进疆的火车上出生。
这句话也极粗略地概括了1949年以来从“口里”到新疆的人口迁徙史,从屯垦戍边、知青下放、支援边疆、西行谋生,到现在的驻村和对口支援,全国各地的汉族人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迁徙与安定,游牧与耕作,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就开始了,让这片丝绸之路穿越的腹地逐渐演变为地域与口音的斑驳拼图,紧紧镶嵌。众声游牧其间,如同风一样来到此地的人。
《凿空》就是这样一部群响嘈杂的听觉小说,也诉说着人的迁移和通路的凿空,主人公们热衷于暗中挖地道,同时全阿不旦村的人都期待集体承包石油工程的挖沟埋管任务。透过泥土与空气,小说充斥着各类自然的声音:鸡鸣犬吠驴叫羊咩。如果说声音是广义的语言,那《凿空》就是自然形式下关于语言的小说,人语只是其中之一。刘亮程当过农机管理员,在种地之余写作,善于表达“脱离尘世”的偏远乡村万物有灵和物我互化的道家气息。《凿空》的叙事人是因为矿井工作致聋的张金,他的父亲张旺才多年前因家乡河南发大水只身逃到新疆。
张旺才被阿不旦村村民收留,盖房置地,娶了一位同样逃荒至此的甘肃武威女子王兰兰。张旺才爱喝糊糊,王兰兰说他“说话口音也像舌头在嘴里搅糊糊,一股河南味”,张旺才说王兰兰的武威话“就像一截木头莽莽撞撞”。两人结婚时说着相互难以听懂的汉话,多年以后还是听不惯对方的河南调、武威腔。张旺才在和村里人共同生活几年后听懂了龟兹话,但说得不是很好,和村里人打交道要靠王兰兰武威腔很重的龟兹语。他们的儿子张金、女儿张银则能对父亲说河南话,对母亲说武威话,和村里人说河南甘肃味儿混合的龟兹话。张金在一片驴叫中出生,他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接生的邻居“阿娜”(妈妈)古丽阿娜说的龟兹语:
对我妈说:“巴郎子,巴郎子。”然后我开始哭。我妈说,她听我“啊,啊”地哭叫,声音没连在一起,跟外面毛驴的叫声一样。
张金在村里的龟兹语班上到五年级,彻底变成了村里的巴郎子(男孩),还让村里好多孩子学会说河南调加甘肃武威腔的汉语。整个“凿空”的故事也是他用龟兹语记录的,医生对他说回忆听觉有助于恢复听觉。
与选择古代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地区)和“阿不旦”作为小说中当下实存的地点一样,作者也让维吾尔语化身为龟兹语这种古代流行在新疆吐鲁番、焉耆和库车一带的语言。这些都使《凿空》像散文集《虚土》一样似真似幻,将过往和现实交错起来。不过,小说中“穿越”的异族语言和汉语的交融,的确已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了数千年。
张旺才、王兰兰像许多迁来新疆的内地人一样,不但说起了母语之外的少数民族语言,两种话之间也互相留下口语痕迹,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汉语中两种方言之间的影响力。孩子们更能自主选择“语言杂交”——嫌母亲说话不好听,就向河南话靠拢,都变成了河南人,喜欢喝糊糊。这个很有喜剧感的过程生动说明了语言习得和身份生成的事实。如果说张旺才和王兰兰被故土的文化辎重牵绊,那么两个孩子则可以自由成为河南人、武威人、龟兹巴郎子,村里的孩子甚至也能成为汉人。在张旺才一家的方言融合与创造中,语言、地域、身份之间的联系异常松散,它们在多种语音和鸡鸣驴叫中漂移、游牧。
除了张旺才这阿不旦村唯一一户汉人,小说中的其他人也时刻面临语言和口音的碰撞:“西气东输”石油井架旁一个个“美容院”板房里的内地女孩,操着五花八门的口音,“四川调、河南腔、甘肃土话、广西鸟语”。在大西北荒滩下的黑色黄金汩汩流向发达东部沿海的同时,四面八方的人声也从数不清的管路涌来,震颤着古老维吾尔村落的土地。佛窟研究所的王加的研究兴趣从佛窟壁画转向坎土曼,王加也是河南人,他来阿不旦村调查坎土曼时,用整个身体——手比画、眼睛做动作,加上半吊子龟兹语才能和村民交流。他和张旺才说起河南家乡话,“嘴和舌头马上找到了家”——家并不一定是具体的地域,而可能存在于口语带来的身体动作和感觉中。而对于村民和“少数民族”汉族人,无论他们是否身在家园,都已在语言的碰撞中走向奥德修斯般的迁徙和冒险:王加与铁匠吐迪“各说各”,都用一半龟兹语和一半汉语交流共同感兴趣的坎土曼。冒险的终点也不是原来的家园,就像电影《湮灭》里人和所处环境中的动植物基因不知不觉互相杂合一样,经过一次交谈,他们不再是“自己”,而是暂时抵达了一个漂浮的、穿透古今的文化共同体。
阿不旦人只用两种农具:坎土曼和镰刀。坎土曼是维吾尔族农民的“万能工具”,它既是小说中的地方物品,也是维语和新疆汉语方言中的典型词汇之一,其他的还有:萨朗(傻子)、羊缸子(妻子,妇女)、海买斯(全部)、麻扎(坟墓)、麻达(麻烦)、理识(理会)……刘亮程只是时不时用这些话调剂着对话的味道,大部分叙述和描写仍是平实优美的正式书面语。这虽然是新疆汉语方言自身特点决定的,但“调味料”的气氛、语调与思维已经渗入每一行,搭起了小说叙述的生活和时间世界。
坎土曼这个名词、这件农具就是这样,阿不旦人的嘴和手都熟了它,刘亮程更渴望从它身上讲出垂直的历史变迁故事。他有意无意地化用了少数民族农民“诗性”的构词和思维,把“西气东输”工程翻译成“坎土曼挖沟”工程——阿不旦人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他们来说,坎土曼凝聚着不同历史时期集体劳动的记忆:60年代挖矿炼钢铁、70年代大修水库、改革开放承包盖房、80年代修路植树,而最后凿空阿不旦土地的“西气东输”,却令坎土曼让路。同时,坎土曼也是小说中维吾尔族传统手工业的灵魂,凭借一把出土坎土曼上的指甲印记,铁匠吐迪辨认出这正是自己家族的产品。新月形的指甲印、佛窟壁画的月牙形挖痕同时也隐喻了伊斯兰宗教。
作者刘亮程则化身为佛窟研究所的王加,在坎土曼上寄寓了历史变迁和多重文化的哲思。王加的研究兴趣从佛窟壁画转向坎土曼,他在临摹壁画时,发现原来看上去以佛为中心和光源的壁画,也是以坎土曼为起点铺展开去的:
这是一个从坎土曼开始的世界。尽管王加没有夸大坎土曼和拿坎土曼的人,但整幅壁画完成后,坎土曼明显成了壁画的中心。它那么引人注目,坎土曼黑黑的,和上方佛的脸相呼应。更有意思的是,佛平视的目光中,有一缕斜溢下来,悲悯地看着那把坎土曼。
他还发现,方形坎土曼可能随佛一起来到龟兹开凿佛窟,千年来,无数把坎土曼在佛窟内壁留下无数整齐细密的凿痕。后来坎土曼变圆了,龟兹人也改变了信仰,坎土曼砍挖毁掉佛像佛寺,开始建清真寺,而因为坎土曼这种工具的限制,大量壁画保留下来。王加的坎土曼研究从龟兹佛窟开始,走向打制坎土曼的铁匠家族、坎土曼形状及磨损速度和时代的关系(比如“大跃进”和“西气东输”时的坎土曼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坎土曼与西域历史等。他学会龟兹语,申报了坎土曼研究课题,已建立起一门在学界引起反响的新学科:坎土曼学,并将几十年的研究成果结集而成《坎土曼学》。
实际上,《坎土曼学》是刘亮程自己写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与《凿空》里有关坎土曼的部分相似。这种自我引用的互文游戏或许并不是要把坎土曼知识化、科学化,把它写进新疆文化旅游手册,最终送进博物馆,而是传达了一种朴素而深刻的见微知著意识,就像吐迪的铁匠铺墙上写的一句老歌中的箴言:“当坎土曼刃扳直的那一天,一切都会被改变。”在刘亮程的“坎土曼学”中,最令汉族读者印象深刻的估计就是坎土曼与汉人的铁锨的关系了:坎土曼朝后刨土,干的活都在后面;铁锨往前挖土,干的活摆在前面。休息的时候它们的分别也一样彻底,坎土曼躺着,铁锨站着。但如果把坎土曼的刃扳直,它就成了铁锨,如果把铁锨头弯折90度,就变成了坎土曼,它们的分化就在于这一个弯折。
坎土曼与铁锨,它们所属的民族、生活与信仰不同,但本来是一个东西。这或许也寓意着文化和语言的相异与合体,在远古的时候,龟兹语和汉语也是紧密贴合——在阿不旦村出土的古铜钱上,一面是古龟兹文,一面是古汉文。它们的子孙语言们仍在这片天空下游牧共生。
作品一旦说了“方言”,它仪表盘上的指针就偏离文字而接近语音,或者说,它被“说”出来时才算发挥尽兴。《凿空》就是这样一部小说,看起来标准规矩,说出来别具风味。譬如“牲口毛驴子”,为什么这样写?是同义反复吗?实际上新疆人民会说成“森口毛驴子”,有时指驴,有时骂人——有犟驴脾气的人。刘亮程自诩为“通驴性的人”,驴是他散文和小说中的主角,是《凿空》中超过了坎土曼的核心。刘亮程再次化身为从北京来做毛驴调查报告的裴教授,裴教授说他在网上看过一篇叫《龟兹驴志》的文章,也是刘亮程自己写的。
“驴是阿不旦声音世界里的王”,驴叫统摄众声,拥有形状、色彩和动能,开辟了广阔的声音世界:
驴叫刚出口时,是紫红色,白杨树干一样直戳天空,到空中爆炸成红色蘑菇云,向四面八方覆盖下来。驴叫时人的耳朵和心里都充满血,仿佛自己的另一个喉咙在叫。人没有另一个喉咙,叫不出驴叫。人的声音低哑地混杂在拖拉机、汽车和各种动物的叫声中。
这个世界在地缘上虽属偏远的底层,是古老蒙昧的,但作者却让它发出最高亢、最野性的声音以证明自己的存在。而且驴在作者笔下还拥有充沛的生殖力与生产力,有坚韧耐劳的性格,它们和朴实的阿不旦人重合了。“毛驴子语言”统治的声音世界取消了人的中心位置,原有的地域和权力格局似乎全都消弭在声音的等高图中。然而,人和驴和谐共居的村庄、和毛驴有关的古老生活方式和手工业体系也正逐渐消失,在“西气东输”工程、“文物研究热”等一系列事件中被开掘和解魅。驴慢慢被“铁牲口”拖拉机、三轮车取代,被阿胶厂收购,就像阿不旦农民面对市场的冲击而无所适从一样。人得跟上时代的脚步,毛驴却在巴扎上制造了一场“万驴齐鸣”的异变。所谓的“上层”“中心”和“先进”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在阿不旦村的故事里却引发了乡愁和怀古之情,使故事变成“反现代”或“后现代”的寓言。作者的原始与底层意识和自甘于边地的态度由此可见。
韩子勇在《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这本书中认为,西部物象给人的视知觉经验具有一种强烈的直接性和极端性:
西部空间与地域的强烈的“相似性”,使物质的速度趋于消失,使“中心结构”的观念开始动摇,每一个部分都是游移的、通兑的。
西部的听觉经验或许也与此类似,但和带着“畸零”与“刑惩”意味的物象不同,声音因其悠扬有力而色彩鲜艳、质地饱满。
语言就是这声音里的一支,在跨语言环境中生活和写作的新疆作家,也十分尊重语言的声音本色,并没有将对话悉数化为熟悉的汉语,而是假道这“另一种语言”凸显了“少数民族形式”,其实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又何尝是绝对的“多数”呢。《凿空》里许多语句带有维吾尔族人说汉语的腔调:“鞋子烂烂的,裤子烂烂的,身上没有好衣服,肚子里没有好食物。”“哎呀,我们的亲戚来了,咋不骑着毛驴子来呢?我们的毛驴子天天想你的毛驴子,你也不骑过来让他们相好一下。”在王刚的体验中,乌鲁木齐、乌拉泊、干沟、库米什、库尔勒、拜城、库车、阿克苏、阿图什这一路前往喀什噶尔的地名,如同e小调音阶,颜色暗暗发绿(《喀什噶尔》)。李娟的对话有时用标点和语气词重现哈萨克牧人半生不熟的汉话:
尔沙说:“冬窝子嘛,,,没有风,没有雪,,,……还是有雪的,雪少,,,很少,,,也不是很少,,,羊嘛,就慢慢地走,,,慢慢地吃……”(《阿勒泰的角落》)
李娟珍贵的“纯真”特质和与她们一起生活的哈萨克人的朴拙大概不无关系。
语言是人的家园。而在少数民族和汉族人眉目示意、手舞足蹈、口音交融的谈笑中,在人伴着驴叫、风声、琴声的神游中,他们是否已经易屋而居呢?或许,无数段“黄金钩子西风腿”已让人不再执着于心中的旧屋,而是像德勒兹所说的“块茎”一样在旷野上游牧——无中心,无根系,互相联系而又异质多元。新疆的声音来自中华大地各处,又像艾德莱丝绸的丝线紧密交织在一起。它像无地域的白话散文一样亲切近人,或许也寄寓着一种新疆写作者的心愿:多元文化的疆域上诞生的文学,要让五湖四海的读者顺畅地赏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