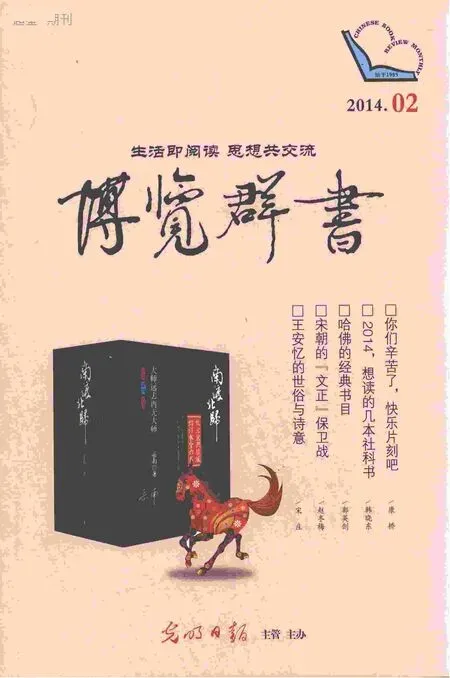《无风之树》是吕梁山的低声絮语
任悦
赵树理虽然是语言大师,但有人做过统计,他的小说中每万字大约才出现方言词4次。也就是说,在其作品中,方言土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似可忽略不计。何以如此?这其实是他的自觉追求。因为早在1941年他就琢磨过通俗化与大众语的关系,认为“不可采用过‘土’的土话”,原因在于,那些土眉土眼的土话“既没有特别的优点,又为他处人所不懂,就是应该避免的”(《通俗化与“拖住”》)。于是,尽管赵树理把通俗化做到了极致,但他靠的是别的本事。
从1956年起,“推广普通话”成为一项持久性的国家战略,如此一来,作家也大都让他笔下的人物说起了普通话,其叙述语言也成了中规中矩的书面语。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样一种局面却被打破了。虽然在现实层面,“推普”工作已大见成效,但在文学层面,一些作家却开始爱上了方言写作或口语写作,北京的王朔、湖南的韩少功、山西的李锐、曹乃谦等,数起来,这会是一串长长的名单,直至金宇澄用上海话写出的《繁花》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03年,敬文东出过一本文学评论集,书名叫作《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很能说明问题。
方言被委以重任,这个“重任”又该作何解?我想不外乎关联着走向民间,重视个体,让底层说话,使众声喧哗等要义。甚至我还想到,方言写作很可能与引进过来的“语言学转向”存在着隐秘关联。李锐说:“正是这表面上被我们‘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到头来却不过是只能如此的书写和言说。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麻木和忽略可谓久矣。”(《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这种思路不是有一种结构主义的味道吗?
本组文章中,四位作者都触及了方言写作的一个面向,其笔下引发出的还没有被当代文学评论界充分注意到的问题,或许更值得深长思之。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方言是很多作家勾勒文化乡土的重要一笔,韩少功的马桥镇、阎连科的耙耧山脉,都有其独特的声音。作家李锐曾经在山西吕梁山区做过六年知青,那里的深沟险境、荒山兀顶,以及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他们用很少被人倾听的吕梁土音诉说着自己的悲欢时,李锐感受到了深刻的悲凉和同情。因此,李锐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这些吕梁山区的农民,他们的苦难与孤独,愛与死亡,需要被铭记。在《无风之树》这部小说中,李锐将目光转向了一群更为特殊的人。用当地的话来说,这是一群瘤拐。他们生活在吕梁山区一个离县城最远的地方——矮人坪,他们难以拥有正常的家庭,也难以走出大山,从生到死,扎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正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李锐放弃了用一种书面的、启蒙姿态的语言讲述他们的创作方式,悉心安抚着这些苦难的、粗粝的生命,让这些人物开口说话。而方言就是他们讲述的支点。对于这些生活在吕梁山区的农民而言,每一个方言语汇都蕴含着不同的生命体验。为了更好地倾听和传达这种声音本身,李锐选择了一种絮语的文体,小说的情节被淡化,语言则占据重要位置。这种尝试和创作不过是要见证和记录,在寂静、荒凉的山脉中曾经有许多孤独的生命存在,还原那些被宏大话语所遮蔽的声音。
李锐在《春色何必看邻家——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浅议当代汉语的主体性》一文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他在《无风之树》等长篇小说中回归口语倾诉的主要原因在于,方言和口语很少受到语言流行病的侵染,更没有所谓的语言等级。换句话说,方言和口语中保留了语言最淳朴、丰富、自由的状态。对生活在方言世界的人而言,方言不仅仅是叙述的工具,更是他们存在的方式。逃离高度统一、秩序井然的书面语、普通话,向广阔的口语之海回归,就是一场向生命本身的回归。
在《无风之树》中,李锐采用口语叙述的方式,作者隐退其后,主要人物轮番登场,依次发声,每个人表露着自己的心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在众声喧哗中,矮人坪这个立体的世界交错展开。李锐的创造性在于给予这些曾经的沉默者说话的权利。正如其所言:
我想让那些千千万万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出声音,我想取消那个外在的叙述者,让叙述和叙述者成为一体,于是我就创造了一种他们的口语,我要让他们不断地倾诉,我要让那些千千万万永远被忽略世世代代永远不说话的人,站起来说话。(《李锐王尧对话录》)
于是,一个沾满了泥土、灰尘的世界在吱吱呀呀的方音土语中向我们打开,只不过这一次我们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俯下身,倾听他们那刻骨铭心的表达和感叹,那从来都无以言说的歌哭。
方言就贯穿在口语叙述之中。在《无风之树》中,李锐使用了不少山西吕梁地区的方言语汇,如“凄惶”“假门三道”“供献”“熬媳妇”等,还有“糖蛋蛋”“傻憨憨”等,这些地道的土语蕴含了吕梁山脉的独特声音,有着独特的情感意蕴。还有语气词的大量使用,如:
天柱,人家这回是要清理队伍,整顿阶级,其实人家是要清理我呢,又是要找我的事情。天柱,你说这回能不能换个别人呐,不能回回都是我呀。
拐叔虽然一辈子住在马号,也没有娶妻生子,却因守着家族的几亩地而被扣上了“富农”的帽子。天柱等干部为了完成清理整顿的任务,只能反复批斗拐叔。这段话是拐叔在跟天柱诉苦,“呢”“呐”“呀”等语气词的使用更体现出他的敢怒而不敢言。再如:
大嫂说,来,娃娃们,给你小叔叔跪下……油灯底下,一圈娃娃们的脸都对着我,我就说,咳呀,快起来吧,这叫干啥呀,这叫干啥呀?咳呀!泪水就从我脸上流下来。
拐叔的家人为了谋生计,离开了矮人坪,只留下他一人守着家族的根。与家人分别的时刻,拐叔那一声声“咳呀”就像一声声叹息,包含了太多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为口语叙述增色不少,如:
传灯爷传灯爷我爸叫你和二牛哥哥赶快去给拐爷做棺材去呢我们啥也没看见我们就是吃了一把煮豆子拐爷的头上有根绳子刘主任就用斧头把他砍下来啦村里的人都看见啦就是他砍的他一砍拐爷就掉下来啦你们快去吧我爸还在村里等着你们呢我们还要买烟呢我爸说差一分钱他就锤死我俩呀。
这段话是拐叔上吊后,被派去跑腿的两个孩子(大狗与二狗)对传灯爷(木匠)说的,标点符号的取消将两个孩子当时的慌张、着急、害怕生动地展现出来。《无风之树》中最具特色的还有对方言中特殊句式的大量使用,如:“你快走吧你”“你怕啥呀你怕”“这是哪儿呀这是”等等。这种“ABA”的句式在山西方言中极为典型,此类重复句式虽然对推进情节发展没有帮助,却让整部作品的叙述语气更加柔软、迂回,也传达出矮人坪人们的整体气质和生活状态。
这些不同质地、色彩的方言,经过选取、搭配,以口语倾诉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能够直击人物内心,更标记出属于矮人坪的独特声音,使整篇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那是一种从寂静、荒凉的山脉中发出的低语,带着一丝逆来顺受,一些软弱与胆怯。与所有的宏大话语相比,这偏远山区最底层的声音其实很难被听到。李锐则将话筒交给了这些几乎从未有过发言权的人,耐心地将这微小却沉重的气息传达了出来。
在与王尧的对谈中,李锐提到他在《无风之树》中使用的语言,只是夹杂了一些当地方言,但对他而言,那是一个别人都没有用过的语言,是独屬于他的“创造的口语”。仔细琢磨,这种“创造的口语”其实自有章法。李锐选择了一种絮语的小说体式,将方言串连在这条暗线中,将矮人坪独有的声音传递了出来。何为絮语?絮语是连续不断地低声说话或唠叨的话。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几乎都在自言自语,不停地倾诉、发问,看似繁乱,其实保持了情感、思想的连贯和凝聚。全书使用最多的方言词汇就是“凄惶”,这其实也奠定了全书的主题。每个人都在讲述着自己的“凄惶”,同时也在可怜着别人的“凄惶”,只有不断倾诉,才能疗愈他们心中的创伤。因此,采用絮语这种文体,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对苦难的书写和记忆,对这些人物最真实的生存境遇的关注。
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暖玉的絮语。暖玉和家人逃荒来到矮人坪,她的弟弟因为吃了太多榆皮面,在她面前死去。下面这段就是暖玉在弟弟死后对家人说的话:
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二弟,我要让他少吃一碗面,他也撑不死了,我就是后悔没看住他,我那会儿也不知是咋啦,睁着个眼啥也看不见,就和个傻子一样。我真是后悔没看住二弟,我要是看住他,说啥也不能叫他吃最后那一碗,不吃最后那一碗,二弟就能跟着你们回老家了。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不断地向人倾诉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遭遇,以缓解郁积在心中的丧子之痛。暖玉也有着同样悲惨的经历,她把弟弟的死归结在自己身上,反复地言说着“我真是后悔没看住二弟”,可见这件事情给她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在看到与她二弟长相相似、年龄相仿的二牛在狼吞虎咽地吃饭时,暖玉心中那块伤口又在无意中被撕裂开来,她开始不自觉地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开始了絮叨:
她说,你俩连吃饭也像。你真是像他呀!你俩咋这么像呀你俩!
她说,二牛,你慢慢吃。你别着急。
她说,二牛,你慢慢吃。你别着急。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她说,二牛,二牛,我不是不让你吃。那年我二弟就是吃面条撑死的。那一回我要是多看看他,多留点神,不让他吃最后那一碗,虎牛就死不了,虎牛就能回老家了。虎牛要是回了老家,他就能来看我来了。
暖玉不断地重复“二牛,你慢慢吃。你别着急”,看似是在关心二牛,实则是在借此解开自己的心结。此刻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能平安无事地填饱肚子,她心里的创伤便能得到片刻疗愈。
如果说暖玉是亲身经历了亲人离世的悲痛而不断倾诉自己的“凄惶”,那么矮人坪的那群瘤拐,他们的絮语以及对苦难的宣泄则是由他人的遭遇(拐叔的死)引发的。拐叔作为矮人坪最有声望的长者,因为不愿在逼迫下交待所谓与暖玉的私情,在悄无声息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让矮人坪的人们感到讶异和无措。他们那日渐被生活磨得坚硬、麻木的心也感觉到了疼痛。正如小说中的糊米所言:
没有穿孝的,没有打幡的,没有哭丧的……拐叔你可真是凄惶。当个光棍可真是凄惶。
他们在哀叹着拐叔的“凄惶”,也在宣泄着自己的“凄惶”。“瘤拐”“光棍”,这从出生就刻在骨子里的字眼,这难以逃脱的命运,是他们永远的痛。尽管拐叔的死没有给矮人坪带来任何变化,人们在给拐叔送葬,饱食一顿羊肉面后又回归了重复的生活,但是糊米、丑娃、捞饭们等开始了言说:
我说,糊米,你说人这一辈子呼塌呼塌走过来走过去的,到底是要干啥呀,啊?
活着的糊涂!死了的也糊涂!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你说什么叫享福?什么叫受罪呀?像拐叔这样活这样死就叫受罪?像我和天柱这样活就叫享福?叫吗?啊?不叫?啊?哎,说不清楚。……说来说去,这事情归老天爷管,不归人管。
这是拐叔上吊后,糊米和丑娃的闲谈。在短短的篇幅内,他们多次发问,这些重复的发问,其实并不求回答,也没有实际的意义。与其说是主动的思考,不如说是对拐叔上吊而死这件事情的消化。他们有着与拐叔相同的“瘤拐”“光棍”的身份,所以尽管没有亲身经历拐叔的遭遇,但这种感同身受,以及死亡带来的冲击和恐慌,让他们难以排解自己的情绪,也因此有了一个彼此诉说的机会。不论是发问还是咒骂,都是一种对苦难的宣泄以及对命运的不解。他们不知道苦难的根源何在,也不知道作为瘤拐而活又有何意义,他们只知道日子还得这样“呼塌呼塌”过着,除了自我安慰,别无出路。这些声音笼罩在矮人坪的上空,镌刻在黄土地的沟沟坎坎里,那是来自最底层的人的孤独和凄惶。
陈思和教授《关于长篇小说的历史意义》一文在评价《无风之树》时认为:“李锐第一次写出了庙堂以外的民间世界的完整性,以及它与入侵的庙堂势力的对立。”这一观点值得深入思考。阅读整部小说就会发现,这种对立主要体现为两种话语——方言和公共话语的交织、摩擦和对抗。苦根儿代表的是矮人坪外的世界,使用的是公共话语。拐叔等人代表的则是生活在这里的瘤拐,他们使用方言表达和交流。不论是苦根儿,还是拐叔,小说中几乎所有人都在絮絮叨叨地讲述,但他们发出了不同的絮语,有着不同的语调和声音。如果说拐叔等人发出的是沉重的、断断续续的低语,那么苦根儿发出的就是持续且有力的高音。在这一高一低,一强一弱两种絮语的对比中,更见庙堂与民间的差异,以及其间难以弥合的缝隙。
最為鲜明的一处对比就是在对待暖玉的态度上。暖玉和一家人逃荒来到矮人坪,为了报答矮人坪对她家人的救济,也为了陪伴在这里去世的二弟,她留在了这里,成为矮人坪瘤拐们的“公妻”,和他们相互依靠、相互取暖。这看似荒谬且有悖伦理的做法,实则也是这些极度贫困且身体残缺的男人们的无奈之举。但在苦根儿看来,暖玉的这些经历肮脏且不值一提:
这是个妖精!暖玉经常在村子里和人说她受过的苦,说她二弟怎么先是差点饿死,后来又怎么活活撑死,说她一个十六岁的姑娘怎么才换了一口袋玉米,说她二弟一条命怎么换了一头驴……暖玉说这些苦的时候根本不分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根本就没有一点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主席这句话就是对暖玉这样的人说的!这样的群众怎么能不教育?他们怎么能理解我呢他们?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怎么能理解我呀他们?
在拐叔眼中,暖玉就是一个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人:
我说,天柱,苦根儿,我不知道你们还要干啥,反正从宽,从严,我都不能说,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欺负暖玉,欺负一个女人家算是啥东西呀。再说暖玉那女人一辈子够个凄惶了,我不能和你们一块欺负她。
相较而言,拐叔的语言偏口语化,苦根儿的独白书面气息更浓郁。拐叔的语气是柔软、复杂的,其中有对暖玉的同情与不忍心,也有面对苦根儿时的畏缩和无奈。苦根儿的语气则更加坚硬,带有浓烈的斗争色彩。暖玉的倾诉在苦根儿的宏大话语面前是可以被省略的,也不被倾听和接受。苦根儿一直很苦恼,他反复地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能理解我呢他们?”但在矮人坪的人看来,苦根儿也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们。借用暖玉的话来说:“苦根儿这一辈子也猜不着矮人坪的问题。苦根儿这一辈子也看不见那些骨碌骨碌的大眼睛。”这种相互之间的难以理解其实也表明了公共话语难以侵入方言世界,以及二者之间交流的困难。这在苦根儿与拐叔的对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拐叔被苦根儿逼迫交代与暖玉的关系时,他选择了沉默,以死抵抗,这也就意味着两种话语间交流的失效。在这种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宏大话语面前,微小的个人话语常常面临失语的状态,难以被倾听和公正对待。这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苦根儿遵循的是以指令为导向的官方标准,他的眼中只有清理、教育、改造的对象,因此他不理解暖玉、拐叔们的“凄惶”,也难以真正听懂矮人坪方音背后的情感意蕴。矮人坪的人们遵循的则是以情感为导向的民间标准。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凄惶”,他们似乎具有无限容纳和接受苦难的能力。虽然无力去改变生存的境遇,但至少可以在相互倾诉与倾听中获得慰藉。矮人坪的问题似乎永远无法解决,清理和斗争结束后,一切都会好转吗?那些饥饿的肚子、空洞的眼神、悲凉的生命还会存在吗?李锐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也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案。但在整部小说的结尾,天柱的傻媳妇在叫喊着:“呜哇哇哇哇……呀哇哇哇哇。”这一串串无人能听懂的字符就像一声声歌哭,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吕梁山区有这样一群艰难生存的人,就像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们一样,用自己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苦难。李锐用这种方式表明,这种絮语虽微弱,却不会终止。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