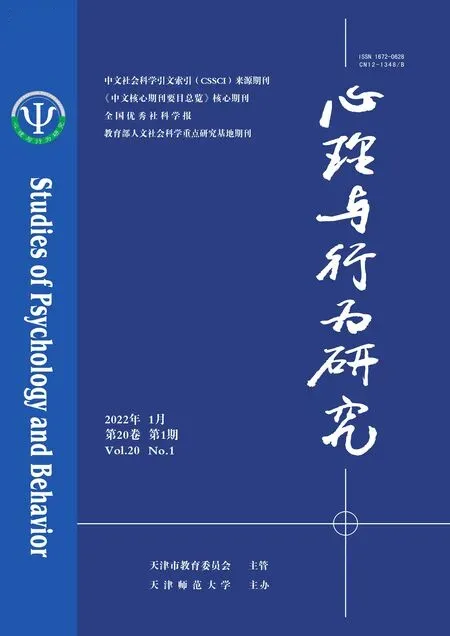眼睛注视线索对经济领域风险决策的影响:基于框架效应范式 *
徐 慧 李美佳 彭华茂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早地意识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考虑到25岁及以下人群多为学生或职场新人,在资产积累方面尚未成熟,风险承受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更需要谨慎应对高风险投资。然而据《互联网理财与消费升级研究报告》显示,相比其他年龄段,21~25岁理财用户中激进型投资者占比更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蚂蚁集团研究院, 202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年轻投资者在风险规避方面存在不足,适当减少其在经济决策中的风险寻求行为可能有助于提升实际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是一种常见的经济决策,因其结果常具有不确定性,也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风险决策之一(Weber et al., 2002)。和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 making)类似,经济投资也会因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述导致个体选择的变化,上述现象被称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Tversky &Kahneman, 1981)。多项研究发现,面临风险经济决策时,“收益”形式的表述会使个体更倾向于选择确定项,表现为风险规避偏好;而在“损失”形式的表述下,个体更倾向于选择风险项,表现为风险寻求偏好(李晓明, 谭谱, 2018;Kahneman & Tversky, 1984; Mayhorn et al., 2002)。
前景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框架效应的产生。根据前景理论,个体的风险决策结果会同时受到主观价值感知与概率权重的作用。相比“收益”,个体对“损失”更敏感;同时,在非极端概率的情况下,个体会低估风险项,而高估确定项的发生可能性(Kahneman & Tversky, 1979)。前景理论从对损失/收益、确定/风险的感知变化的角度,为个体的决策偏差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视角,即个体对决策信息的感知变化可能影响其最终决策。
除了框架带来的影响,外部环境线索也能作为“助推剂”显著影响个体行为,其中就包括眼睛注视线索(Haley & Fessler, 2005; Nettle et al.,2013)。探究眼睛效应机制的相关研究表明,虽然没有真人在场,但眼睛图片或抽象的眼睛线索可以自动激活被观察的感觉,让人产生“受监督感”(吴琴, 崔丽莹, 2020; Bateson et al., 2006;Emery, 2000)。个体为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或是避免违反社会规范可能带来的惩罚,可能会选择改变自身的行为(Oda et al., 2015; Oda et al., 2011)。观察感的产生同样会影响风险行为。有研究考察个体的风险偏好是否受到虚拟同伴观察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独自完成任务的控制组被试,相信存在他人观察的成年被试的风险倾向更低(Haddad et al., 2014)。脑成像的相关研究发现,上述结果可能与认知控制过程和奖赏系统的活动相关,当相信有他人观察自己时,成年被试左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会参与抑制对奖赏系统的输出(Chein et al., 2011)。因此眼睛线索对个体风险行为的作用可能是通过引发观察感,从而影响奖赏回路相关脑区的活动和对潜在收益的感知造成的。同时,决策过程中腹侧纹状体、前额叶及杏仁核等区域的激活,也被证实会影响个体对收益(或损失)及未来事件的主观价值的评估(Trepel et al., 2005),即与前景理论中的价值与权重评估过程相关。基于此,本研究推测,眼睛注视作为实际生活中较为常见,且可能通过触发认知变化从而影响个体行为的有效社会线索之一(Oda et al.,2015; Sparks & Barclay, 2013),可能会影响个体对损益的感知及风险决策结果,这一影响在经济决策中表现为更低的风险寻求倾向。值得注意的是,眼睛注视线索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伴随情绪发挥作用,不同情绪效价的眼睛线索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Li et al., 2021),这也提示,关注眼睛注视线索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时,可以加入情绪信息进一步探索。
因此,本研究基于框架效应经典范式改编的风险决策任务,考察不同情绪效价的眼睛注视线索对个体在基金投资中的风险寻求行为的影响。同时结合眼动技术考察被试对决策任务中风险项、确定项、收益、损失等关键内容的注意情况。Just和Carpenter(1980)提出的阅读过程的眼动理论认为,只要个体正在加工某个词,他就会保持注视,即注视与信息加工是同步进行的;同样地,如果个体对某一区域的信息进行了加工,在加工过程中便会注视这个区域。基于此,本研究计划通过分析被试在任务区域的眼动结果考察其信息加工过程,并提出如下假设。
(1)框架类型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行为。在正框架下,被试的风险寻求行为较少,表现为风险规避倾向,而在负框架下表现为风险寻求倾向。(2)框架类型和眼睛注视线索会共同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行为。相比控制组被试在不同框架下的风险寻求倾向差异,眼睛注视组(积极、中性、消极)被试的风险寻求倾向更低,且差异更小,即眼睛注视组被试的框架效应更小。不同效价的眼睛注视线索产生的具体影响差异,因缺少直接的证据支持,仅进行探索性研究。(3)眼睛注视线索对被试风险寻求倾向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改变个体对确定/风险或收益/损失的关注造成的。各组被试均对损失更敏感,因此负框架下的均字注视次数显著大于正框架,且眼睛注视组被试在不同框架下的眼动结果差异小于控制组被试;同时,眼睛注视线索可能降低被试对确定/风险、收益/损失的概率权重的估计差异,因此与控制组相比,眼睛注视组被试对确定损益和风险损益的关注差异,即均字注视次数的差异更小。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对此暂不做方向性假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在北京地区随机招募被试133名,多于G*Power3.1软件计算所得最小被试量(120人)。所有被试年龄在18~32岁之间,随机分配至不同实验组别。其中,中性眼睛组33名(女性17名),平均年龄23.24±2.75岁;积极眼睛组34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23.76±2.91岁;消极眼睛组33名(女性20名),平均年龄23.30±2.43岁;控制组33名(女性23名),平均年龄23.67±2.57岁。人口学信息见表1。

表1 各组被试背景变量描述统计结果
2.2 实验设计
研究采用4(眼睛注视条件:中性眼睛组、积极眼睛组、消极眼睛组、控制组)×2(框架类型:正框架、负框架)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眼睛注视条件为被试间变量,框架类型为被试内变量。以风险项选择比例为因变量,考察个体的风险决策行为是否受不同眼睛注视线索的影响,并结合眼动追踪技术分析被试的注意分配情况。控制组被试进行决策时,屏幕背景为一张普通的中性图片,其余组别则呈现对应情绪效价的眼睛图片;每个试次更换一张背景图片。
2.3 实验仪器
本研究使用加拿大SR Research公司的EyeLink 1000型眼动追踪系统,单眼瞳孔-角膜反射系统进行记录,只记录被试完成任务时右眼的眼动数据。实验时用下颌托固定被试的头部进行阅读,采样率1000 Hz。屏幕分辨率1680×1050像素。刺激材料的可视区域的水平视角28.7度,垂直视角22.9度,显示器19英寸,屏幕比例5∶4,眼睛距屏幕70 cm。
2.4 实验材料
本实验所用的基金投资决策任务由框架效应经典范式改编,包括封面故事和决策任务两部分。由于个体在遭遇损失时的表现对未来的投资收益十分重要(张剑 等, 2014),因此本实验在面临损失的大前提下,设置初始金额为50 000元,浮动亏损最高为2000元,生成2(框架类型:正框架、负框架)×5(概率水平:30%、40%、50%、60%、70%)10类,共20道题目。正框架下决策任务示例见图1。负框架下决策任务中A方案内容示例为“肯定会损失600元”,B方案内容示例为“70%的概率没有损失,但有30%的可能2000元全部损失”。其中,A方案为确定项,即风险规避项;B方案为风险项,即风险寻求项,两者无正误之分。以被试在20道题目中选择风险项的比例作为衡量个体风险寻求行为的指标。

图1 基金决策任务材料及AOI划分示例
为分析被试在阅读题目过程中对关键信息的注意分配差异,分别定义眼睛注视区域(AOI1)、确定项内容区域(AOI2)和风险项内容区域(AOI3)为兴趣区(area of interests, AOIs),兴趣区划分示例见图1。参考前人研究,同时考虑到本研究所关注兴趣区(确定项和风险项区域)内短句字数不一致的影响,以均字注视次数(兴趣区内注视总次数除以该区域字数)为因变量指标(闫国利, 孟珠, 2018; 闫国利 等, 2013)。
实验中作为背景的眼睛图片均选自中国面孔情绪图片系统(CFAPS)(龚栩 等, 2011),从中选取若干面孔图片形成备选图库,对图片进行裁剪和统一处理。正式实验前招募34名年轻人,采用自我情绪评定量表(Self-Assessment Manikin,SAM)(Bradley & Lang, 1994)对所选材料的情绪效价和唤醒度分别进行9点评分(效价: 1=非常消极, 9=非常积极; 唤醒度: 1=非常平静, 9=非常不平静),最终从备选图库中选择积极(“愉悦”)、消极(“悲伤”)和中性(“平静”)眼睛图片各10张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对上述图片的效价和唤醒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三组图片的效价[F(3,36)=137.82,p<0.001]和唤醒度 [F(3, 36)=13.61,p<0.001]均存在显著差异,与备选图库的差异检验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在满足研究需求的基础上,已对所选眼睛图片的情绪唤醒度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控制。三组图片保证了显著的效价差异,同时唤醒度均在中等偏低程度。
作为控制组背景的普通中性图片选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IAPS)(Bradley & Lang, 2017)。参照图片系统的原始评定结果选择实验材料,对所选材料的情绪效价和唤醒度分别进行9点评分,最终得到10张中性图片(效价:M=4.66,SD=0.39; 唤醒度:M=3.84,SD=0.56),对图片进行与统一处理,正式实验材料示例见图2。

图2 不同背景图片示例
2.5 实验流程
被试首先签订知情同意书,登记基本人口学信息;随后测量基线情绪状态,并通过练习环节熟悉答题规则。正式实验共20题,顺序随机,同时平衡确定项与风险项的呈现位置。记录所有被试的决策结果。正式决策任务结束后,被试还需完成若干金融经验相关的测量任务。
3 结果
3.1 操纵检验结果
决策任务结束后,要求被试完成背景图片再认任务。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分析。
将各组被试的背景图片正确再认率与0.5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仅对消极眼睛图片(M消极=0.53,SD=0.09)的正确再认率高于50%,t(32)=2.13,p=0.040;其余三类图片的正确再认率均未显著高于概率水平(M中性=0.44,SD=0.10;M积极=0.47,SD=0.10;M控制=0.53,SD=0.11)。这可能与本研究所用的图片仅保留了眼睛部位有关,再认图片的相似性相对较大,再认难度更高,同时年轻人的消极偏见使其对消极刺激更为关注,记忆效果也更好(Baumeister et al., 2001)。
以被试在眼睛或中性背景图片区域的总注视次数和总注视时间为主要眼动指标,进一步考察被试对不同背景图片的关注情况。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四组被试对背景图片区域的总注视次数(M中性=2.67,SD=3.10;M积极=2.00,SD=2.71;M消极=1.32,SD=1.04;M控制=1.57,SD=2.73)差异不显著,F(3,129)=1.81,p=0.149;总注视时间(M中性=502 ms,SD=597 ms;M积极=411 ms,SD=609 ms;M消极=264 ms,SD=218 ms;M控制=305 ms,SD=534 ms)的差异也不显著,F(3, 129)=1.43,p=0.236。综上,四组被试均注意到了背景图片的存在。
3.2 眼睛注视线索对风险寻求行为的影响
各组被试的决策结果见表2。为探究眼睛注视条件对风险寻求行为的影响,以被试在各条件下的风险项选择比例为因变量,进行4(眼睛注视条件:中性眼睛组、积极眼睛组、消极眼睛组、控制组)×2(框架类型:正框架、负框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框架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 129)=165.49,p<0.001,=0.56,相比正框架,负框架下的风险寻求倾向更高,各组被试均表现出显著的框架效应。眼睛注视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3, 129)=1.06,p=0.369,各组被试在风险项选择比例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2 各组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风险项选择比例
框架类型与眼睛注视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F(3, 129)=3.39,p=0.020,=0.07。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正框架下,各组被试的风险项选择差异不显著,F(3, 129)=0.48,ps>0.05;负框架下差异显著,F(3, 129)=3.42,p=0.019,=0.07,具体表现为消极眼睛组被试的风险项选择比例显著高于中性眼睛组(p=0.002)与积极眼睛组(p=0.038);控制组的风险项选择比例与其余各组均无显著差异,ps>0.05。同时,各组被试在负框架下的风险项选择比例均显著高于正框架,ps<0.001,计算可得消极眼睛组的框架效应最强。
3.3 眼睛注视线索对兴趣区均字注视次数的影响
本研究眼动数据采用Data Viewer进行预处理。分组后,删去正式实验试次中未被完整记录的试次;随后按照四步筛选法对数据进行筛选,去掉注视时间小于80 ms或大于1200 ms的数据(Slattery et al., 2011)。采用SPSS 26.0对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以均字注视次数为因变量,进行4(眼睛注视条件:中性眼睛组、积极眼睛组、消极眼睛组、控制组)×2(框架类型:正框架、负框架)×2(兴趣区:确定项、风险项)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统计结果可见表3。

表3 确定项及风险项均字注视次数
结果发现,眼睛注视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3, 129)=0.66,p=0.579,不同眼睛注视条件下被试的均字注视次数不存在显著差异。框架的主效应显著,F(1, 129)=83.82,p<0.001,=0.39,相比正框架,被试在负框架下的均字注视次数更多。兴趣区的主效应显著,F(1, 129)=197.06,p<0.001,=0.60,确定项的均字注视次数显著多于风险项。框架类型与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9)=16.00,p<0.001,=0.11。
三阶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眼睛注视、框架类型和兴趣区三阶交互作用显著(结果可见图3),F(3, 129)=4.53,p=0.005,=0.10。当呈现中性眼睛注视线索时,框架类型与兴趣区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29)=11.52,p<0.001,=0.08;被试在负框架下对不同兴趣区的均字注视次数均显著大于正框架条件[确定项:F(1, 129)=28.96,p<0.001,=0.18; 风险项:F(1, 129)=7.29,p=0.008,=0.05],但对确定损益的关注差异大于对风险损益的关注差异。当呈现积极眼睛注视线索时,框架类型与兴趣区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 129)=16.54,p<0.001,=0.11;负框架下各兴趣区的均字注视次数显著大于正框架[确定项:F(1, 129)=41.07,p<0.001,=0.24; 风险项:F(1, 129)=10.13,p=0.002,=0.07]。当呈现消极眼睛注视线索时,被试对损失的关注大于对收益的关注[F(1, 129)=14.75,p<0.001,=0.10],对确定项的关注大于对风险项的关注 [F(1, 129)= 62.96,p<0.001,=0.33];但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 129)=0.37,p=0.545。控制组条件下,框架类型[F(1, 129)=11.90,p=0.001,=0.08]和兴趣区[F(1, 129)=46.67,p<0.001,=0.27]的主效应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F(1,129)=1.38,p=0.242。

图3 框架类型与兴趣区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基金投资的任务背景,探究眼睛注视线索会如何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决策。结果发现,各组被试在正框架下表现出风险规避的倾向,而在负框架下表现为风险寻求,即存在显著的框架效应;这一结果也与过往众多框架效应研究结果保持一致(Mayhorn et al., 2002; Pu et al.,2017)。
进一步分析眼睛注视条件与框架类型对个体风险寻求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发现,消极眼睛注视线索对被试风险寻求行为的影响受框架类型的调节作用。正框架下,各组被试的风险寻求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在负框架下,消极眼睛组被试的风险寻求倾向显著高于中性眼睛组和积极眼睛组。消极眼睛组与中性眼睛组、积极眼睛组在风险寻求行为上的差异,说明眼睛注视线索中蕴含的情绪信息可能是改变人们风险寻求行为的原因所在。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包括图片、视频在内的多种刺激形式均能影响接收者的观点与情绪(van Kleef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中的眼睛注视线索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可能是由于悲伤的眼睛注视线索传达出相对负面的信息,导致被试在负框架下的损失厌恶增强(Raghunathan &Pham, 1999),从而为规避损失选择风险项;也可能是眼睛所携带的情绪内隐地改变了个体对风险的感知所导致的(van Winden et al., 2011)。结合眼动数据结果发现,消极眼睛组被试的眼动模式与中性眼睛组、积极眼睛组存在差异。均字注视次数作为反映个体认知资源投入的眼动指标(Kuo et al., 2009),当呈现中性眼睛和积极眼睛注视线索时,被试对确定损益的关注差异显著大于风险损益;在消极眼睛注视条件下,被试对损失项的关注显著大于收益项,对确定项的关注也大于对风险项的关注,但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这可能表明消极眼睛组被试没有因为确定/风险的变化而赋予收益/损失不同的权重。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中性和积极眼睛注视线索增强了被试对决策信息的敏感性,而消极眼睛线索在整体上降低了被试对确定/风险的敏感性造成的。上述过程还可能涉及神经生理活动的改变。以往研究发现,杏仁核的激活与情绪信息的识别过程密切相关,且杏仁核激活的增强会引起个体损失规避倾向的增强(De Martino et al., 2006)。因此,情绪眼睛的存在,尤其是消极眼睛线索,可能会增强杏仁核的激活,导致个体为避免既定的损失而选择承担更高的风险,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认知神经研究加以佐证。
此外,控制组被试在行为结果上与其余眼睛注视组均无显著差异,而消极眼睛组和其余眼睛组的行为结果差异显著,进一步说明被试在决策任务中的行为改变可能不是眼睛注视线索本身引起的,而与眼睛线索携带的情绪信息相关。本研究未发现眼睛注视线索自身的作用,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并未在指导语中强调眼睛线索的存在,也并未要求被试注意眼睛线索,眼睛注视线索的作用可能处于无意识层面(Oda et al., 2015; Sparks &Barclay, 2013)。这一推测也与再认任务中被试对中性眼睛和积极眼睛图片较低的正确率相符。眼动分析发现,控制组被试与消极眼睛组表现出相近的结果模式,与中性眼睛组和积极眼睛组不同,其中原因尚不明确。本研究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控制组采用的普通场景图片中还包含着其他线索,也可能是背景图片这一分心刺激的存在造成了眼动的变化。虽然眼睛注视组的背景图片本身也是分心刺激,但“眼睛”可能是一种相对特殊的刺激,所以眼睛注视组和控制组的眼动模式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后续研究可能还需要增加无背景图片组、其他情绪线索组,才能进一步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在具有一定风险的基金投资决策情境下,不同类型的眼睛注视线索对投资者风险寻求行为的影响,同时结合眼动技术考察其关注点的变化。虽然未能发现眼睛注视线索的存在对投资者理性经济决策的促进作用,但仍为基金用户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在经济决策中,尤其是面临投资亏损时,为做出更稳定、理性的决策,应尽量避免消极的眼睛注视线索;其他包含消极信息的社会线索,例如悲伤的音乐等,也可能影响人们的投资决策。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本研究在保证眼睛图片的情绪效价的基础上,未能完全控制各组眼睛图片的唤醒度一致。虽然从结果来看,消极眼睛组,而非积极眼睛组表现出了更多行为差异,但眼睛情绪唤醒度是否会对被试决策产生影响仍需更进一步的探索。第二,本研究未发现各眼睛注视组与控制组在行为结果上的显著差异,即眼睛图片的作用强度相对不足。这可能与眼睛线索的性质与呈现方式有关。有研究发现,相比长时静止的呈现方式,短时间歇呈现的眼睛图片会产生更强的监督感(Sparks & Barclay,2013)。因此后续研究可以探讨眼睛注视线索的呈现方式对个体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第三,本研究仅选择了悲伤与愉悦的情绪眼睛图片作为实验材料,而在现实生活中,眼睛注视蕴含的情绪信息更为丰富,因此其他类型的情绪眼睛线索及各类社会线索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索。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察社会线索影响个体决策的心理机制,同时关注情绪与奖赏相关脑区可能发挥的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框架效应经典范式改编的基金投资决策任务,探究了不同情绪效价的眼睛注视线索对个体风险决策结果的影响。结果发现消极眼睛注视线索会增强个体的风险寻求,这一影响可能是由眼睛注视线索蕴含的情绪信息影响了个体对确定和风险的感知引起的。